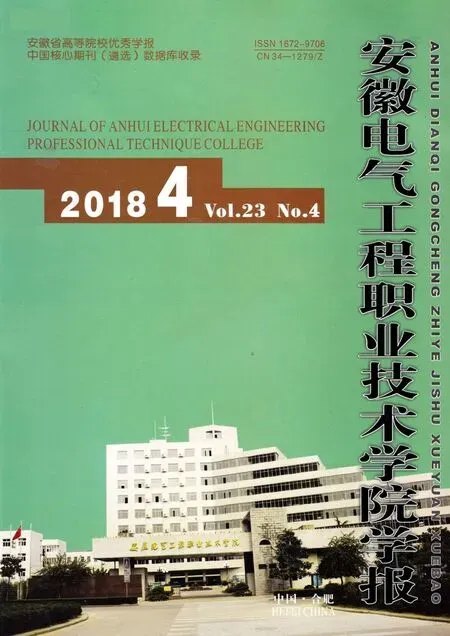中日环境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梁 淼, 葛娇敏
(江西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一、日本环境犯罪立法
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片面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复兴,而忽视了对社会的管理、对人们身体健康的重视,致使大量公害事件发生,日本也因此被世人称做“公害列岛”。关于公害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根据现行《环境基本法》中对公害的定义,所谓公害即是指伴随企事业活动等人为活动而产生的相当范围的公害事件(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振动、地面沉降和恶臭等),由此对人的健康以及生活环境产生的危害,此定义即为狭义定义,而广义定义则是指食品公害、药品公害,甚至亦包含相邻建筑物之间阻挡日照而引起的公害,主要是指由于企业活动而引起周围人们的生活、健康而受到损害。环境法正是从公害法中发展起来,以对自然环境或者环境媒介(大气、水、土壤等)的损害为必要条件,可以说环境犯罪属于公害犯罪的一部分。[注][日]长井圆:《環境刑法の基礎·未来世代法益》,《神奈川法学》2002年第35卷2号,第5、19页。因此,日本的环境犯罪主要是指刑法典中第十五章关于饮用水的犯罪、单行刑法(《关于处罚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罪法》)以及各种行政管制法之内的环境刑罚条款。
(一)《关于涉及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处罚的法律》
该法作为日本首部环境保护单行法,仅仅只用7个条文就对公害犯罪的罪状、刑罚、诉讼时效以及管辖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形成了环境刑事制裁的基础模式,表明了政府重视公害问题的姿态。这部法律不仅是规制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产生危害的行为,同时也将具体危险行为(危险犯)作为规制的对象进行处罚。可以说,和公害问题的事后损害赔偿相比,该法起到了事前防止的作用,这无疑是有关公害规制法律方面的进步。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了公害犯罪的罪过形式。该法第2条和第3条明确规定了公害犯罪的罪过形式,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2)采纳了两罚制度。该法第4条是对两罚制度的采纳,规定法人的代表人、法人的代理人或者雇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在实施公害犯罪后,除处罚行为人外,也对该法人或其他人员进行处罚。两罚制度的采纳是对传统刑法“罪及个人”的突破,将企业-企业领导人-行为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加大了对公害犯罪的处罚力度,有利于对环境的保护。(3)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适用。该法第5条明确规定,如果有人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排放出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其排放量已经达到危害公众健康的程度,对由此给公众造成的损害结果可推定是由该行为人造成。该原则的适用对于缓解环境犯罪中控方举证责任上的困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刑法典中关于饮用水犯罪的规定
日本现行刑法典是于1907年公布,1908年施行,分为总则编(第1条-第72条)和各罪编(第73条-第264条)。各罪编是按照针对国家法益的侵害(第2章-第7章)、社会法益的侵害(第8章-第24章)、个人法益的侵害(第26章-第40章)的顺序进行的排列[注]但是,由于对保护法益的认识不同,并不是所有的犯罪类型都能够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排列。例如、“贪污罪”位于第25章,但却是对国家法益的侵害。,其中关于饮用水罪的犯罪通说认为保护的法益是公众的身心健康。因此,也被称之为刑法典上的公害犯罪[注]参见[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六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56页。,具体包括第142条污染净水罪、第143条污染自来水管道罪、第144条毒物混入净水罪、第145条净水污染致死伤罪、第146条毒物混入自来水管道罪等。其中“污染净水罪”是指,污染供人饮用的净水而导致无法使用的行为,根据该法规定会被判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者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95元)以下的罚款,在这里,“无法使用”是指普通人对于饮用水的物理上的、心理上的使用不能。而污染经由自来水管道供给人使用的净水或者水源的行为,属于“污染自来水管道罪”,会被判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向供人饮用的净水投入毒物或者会使人健康受损的物质,不管是否对人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只要实施了该行为,就会被判处3年以下徒刑,属于“毒物混入净水罪”。第145条规定犯前三款之罪,又致人死伤的,较之伤害罪,会重处。第146条规定,向经由自来水管道供给人使用的净水或水源投入毒物或者会使人健康受损的物质,将会被判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将会判处死刑或者无期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法条后半部分规定了该罪的结果加重犯,即使是致伤结果,也成立“毒物混入自来水管道罪”。另外,如果有伤害的故意,就不再适用伤害罪,而只适用本罪。同样,如果有杀人的故意,也不适用杀人罪,这是因为本罪的法定刑比伤害罪、杀人罪更重。
(三)行政法之内的刑事罚则
最值得探讨的是最具实践意义的行政法之内的刑事罚则。目前在日本,环境犯罪或者公害犯罪最主要是根据环境行政法规进行规制。环境行政法规是环境规制中最具效果、最具规模的法律体系。
1.《大气污染防止法》
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国民的健康以及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而于1968年制定该法。为了使日本全国达到环境基本法所规定的环境标准,该法对排放大气污染物质的工厂企业进行了规制,包括对产生煤烟的设施、排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设施、产生普通粉尘的设施、产生特定粉尘(石棉)的设施以及与石棉有关的作业现场的规制。对于排污企业产生的煤烟、粉尘以及机动车尾气,自大气污染防止法制定以来一直是法律控制的对象,有害大气污染物是在1996年修订后,VOC是在2004年修订后新增的对象[注]参见日本国环境省:日本的大气环境对策,2015年3月。。特色之处在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一直通过单纯的管控来实现减排,而有害大气污染物和VOC的减排对策则采取了管控和自主性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日本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不断扩大大气污染对策的对象范围,且不仅依靠管控的方式,也有效发挥了自主性措施的作用。该法分为总则、对排污企业的物质燃烧等产生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粉尘、有害大气污染物、机动车尾气等的排放规制,以及相应的损害赔偿和有关罚则的规定。其中第六章是对罚则的描述,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
2.《水质污染防止法》
《水质污染防止法》制定之前,日本实行的是保护公共用水水质的法律《关于保全公共水域水质的法律》、规制工厂排水的《关于控制工厂排水等的法律》。这两部法律,是在震惊世界的“水俣病”与“痛痛病”发生之后,日本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以应对严峻的公害犯罪。但由于其只是针对水质污染的某个领域,实用性并不强。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发生了第二“水俣病”那样的公害事件[注]第二水俣病是1965年确认的四大公害病之一。因与熊本县的水俣病症状相同,而得此名。因发生在新潟县阿贺野川下流,因此又名“新潟水俣病”及“阿贺野川有机水银中毒”。(参见https://baike.so.com/doc/5979980-25359538.html)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对水质污染做到事前预防,于1970制定了《水质污染防止法》。该法将《水质保全法》、《工厂排水规制法》一体化,废止用这些法律进行的个别水域规制,以全水域为对象进行统一排水标准的规定。同时,通过强化地方自治团体的权限,以条例的规定,设置了追加排水标准、违法处罚标准等内容。
3.《土壤污染对策法》
《土壤污染对策法》(简称土对法),是在日本政府将土壤污染追加为典型七大公害后,为了应对全国各地涌现的重金属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造成的土壤危机,于2003年正式颁行该法,并于2010年进行了大幅修改。该法作为一种事后对策,规定了一般条款、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指定污染区、土壤污染损害预防、委派调查机构、委派促进法律实体、罚则等共计八章四十二个条文。对土壤污染情况的测量(包括调查污染状况、公示污染区域、准备和储存、保管指定区域记录的措施)、相应的防止措施(消除污染的措施命令、土地性质变更的通知和行动计划变更的命令)以及规定了污染土壤的运输标准,在违反这一情况的情形下,将受到刑事处罚,主要责任形式有罚金和有期徒刑两种。其中,对单位犯罪亦实行双罚制,既处罚违犯相关法定义务的单位,对单位的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等也给予相应处罚。
4.《有关废弃物处理以及清扫的法律》
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由生活垃圾造成的环境问题变得触目惊心,日本政府为了妥善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于1970年在“公害国会”上制定了该法(以下简称《废弃物处理法》),经过一系列频繁的修改(分别是1976年、1991年、1997年、2000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10年),最终强化了对废弃物处理行为的规制。具体内容:总则、一般废弃物的处理、产业废弃物的处理、废弃物导致的土地性状的改变、杂则、以及相应的罚则。
二、我国环境犯罪立法
和日本的刑法典、公害罪法和环境行政罚则相比,我国针对环境犯罪的处罚依据是以刑法典为主,通过制定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等来确定环境犯罪。本章所探讨的对象正是我国刑法典中关于环境犯罪的各项规定。
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是和外交事业同步进行。1972年6月5日,我国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随着环境污染引起的社会矛盾日趋严重,1979年政府公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到1989年这十年间,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立法急速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由此奠基,环境法理论研究发展迅速,环境立法进入“快车道”[1]。有关我国环境污染的刑事规定起步于1979年,但不可否认的是1979年刑法有关环境犯罪方面的规定主要是从经济、财产、人身安全等角度出发的,没能真正体现保护生态平衡和生态环境的宗旨[2]。因此,在1979年的刑法典中并没有采用独立的章节来规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条文,而是根据侵害法益和行为样态在不同的章节中,分散规定与环境破坏有关的犯罪形式。从当时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规制有以下特点:第一,刑法中的环境、资源保护规定是并没有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角度出发制定。因此,我国的环境犯罪最初被视为公共危险犯的一种。第二,当时关于环境的罚则规定是公共危险罪的规定,具有行政独立性。在确定环境违法行为的时候,需要考虑是否违反行政规定。
从1997年刑法开始,我国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采用了统一的立法模式,即具体罪刑条文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3]。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设立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该法颁布之后,立法机关针对环境资源保护有关的犯罪条文进行了数次修改。2001年8月31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二),2002年12月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四)和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都规定了针对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犯罪。刑法修改案(二)和刑法修改案(四)中的修改,是针对破坏资源犯罪和废弃物的非法进口罪进行的。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到破坏环境媒介的相关犯罪,但在此次修订中,仍旧能够看到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态度。
首先,有关环境和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对象的范围正在扩大。例如,从耕地到农用地,从珍贵树木到国家特别保护的植物和该产品,保护对象不断扩大。其次,环境和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行为也在不断扩大。例如,对植物的直接破坏行为从砍伐、损坏行为到运输、加工及销售行为,处罚对象行为也已扩大。
刑法修正案(八)对于环境资源保护类犯罪表现出了严惩态度,将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自此,我国刑法中有关环境犯罪的体系就大致形成为:(1)危害环境罪(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2)破坏自然资源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3)与危害环境直接关联的其他犯罪这三种类型。
我国刑法的第六章第六节以“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章节名,实质上是包含了破坏环境和破坏资源两方面的内容。我国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环境犯罪规定是针对环境污染行为或者环境媒介的破坏行为的处罚规定,即刑法第338条和第339条第1款以及第2款的规定。而广义的环境规制则既包括了对破坏环境媒介的规制,也含有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维持相应的生态平衡。
三、借鉴
(一)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的盛行
法益,是法律要保护的利益和价值。刑法法益,就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和价值。法益概念具有两种功能:方法论的功能和批判的功能。前者是指司法者对于法益的界定,会影响到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即会影响到人们如何去理解刑法条文中的具体规定,也可以理解成刑法规范保护目的;而后者则是指法益概念的界定会去约束司法者,防止司法者滥用解释权,以求达到法益保护与罪刑法定的平衡。因此,对于环境犯罪的法益如何解释对司法、立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日本学界亦存在相关争论。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1)生态学的法益观;(2)纯粹人类中心法益观;(3)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纯粹人类中心法益观是对传统法益观的坚持,该学说支持者认为环境刑法应该对法益的扩大化和抽象化进行批判,也就是法益范围应该仅限定在对传统法益(个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利益)的保护[注]伊藤司.環境(刑)法総論—環境利益と刑法的規制[J].九州大学法政研究,第59巻(1993 年),第673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风险社会的来临,如果环境犯罪的法益只局限于传统法益内涵,那么处罚范围将会变得过于狭窄。在风险社会中,超个人法益的盛行具有明显趋势,具体在环境犯罪中,环境污染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不仅局限于个人法益,更是损害了生态环境。从表面上看,生态学法益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的重视,包括对环境要素以及环境媒介,以及由此形成的环境系统,但是该学说仍旧会产生以下一些问题:(1)如果从环境角度进行法益的思考,那么对自然产生影响的所有改变都将被认为是对环境法益的侵害。这样,保护法益的范围就会扩大,进而处罚范围也就变得无法限定;(2)如果对“自然的权利”的承认,就应该认同自然作为权利的主体,基于对环境伦理有力的思考所提出的生态学法益观,环境犯罪处罚的目的不仅仅是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制的回应,同时也是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问题的伦理意识的觉醒。但是,从近代刑法的发展来看,结果无价值的观点载于违法性的本质应该先是在于法益的侵害,然后才是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3)生态学的法益观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会产生选择上的冲突。根据生态学的法益观,可能会做出以人类社会的利益牺牲为代价的选择。随着违法性本质争论的演变(结果无价值一元论和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的对立),人们试图通过二元论的法益构想来解决以上两种学说的问题,特别是“将来的人类一代,居住和利用的环境”被认为是刑法保护的对象。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应该是综合考虑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共同利益,应该是以人类的重要利益有关的范围之内,担保能够用刑法保护环境法益。
(二)危险犯理论的完善
仔细探究环境犯罪的相关案例,不难发现,长期性和隐蔽性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是此类犯罪的共同特点。从日本环境犯罪的制裁法律模式的转变当中,反应了立法者对用刑罚保护早期化的重视,形成了以保护生态法益的抽象危险为核心的抽象危险犯。危险犯,在刑法理论上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制造了刑法规定上的危险状态就被认定为犯罪既遂。而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不单单是指违反刑法,还应包括违反相关行政法规中的刑罚规定。显而易见,对过失犯的立法增设是日本法律对社会中越来越多环境犯罪的严厉制裁,也反应了机能主义的型法观在日本的立足。在风险社会,安全与秩序价值被看作是重中之重,其自身蕴含了浓郁的法益精神化气质。因此,在刑事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犯罪刑事政策不能仅满足于对环保目标的迎合,还要为完善权利救助体系勾画蓝图,在其目标层级中,必须包括对个人环境权和公共环境权的保护[4]。也即,将危险犯理论进行扩充和完善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刑事立法模式的多元化
日本针对环境犯罪的立法规制具体来说有以下3种形式:(1)以行政法规和行政行为为前提,用刑事处罚的方式来确保行为人严格按照相应的环境标准来实施相应行为。针对违法行为,多采用直罚制度(以大气污染防止法、水质污染防止法为例)。(2)在刑法典中将相应的环境媒介作为保护法益(关于饮用水的犯罪)。(3)将环境法益作为独自的保护法益以行政法规和行政行为独立的形式,以特别法对公共危险犯进行规制(公害犯罪处罚法)。具体来说,第一种形式是对人类中心法益的具体危险发生的不重视,而对环境媒介的直接危险的关注。因此,既能对广阔的生态资源进行保护,又能对给人造成间接危险的预防。从这一点来说,具有较强的预防功能。第二种模式,是在具有较强伦理色彩的刑法中对环境媒介进行保护,保护法益自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环境保护,自然是与人类的利益相吻合。第三种模式,是以特别法的形式。不拘泥于刑法的谦抑性,而又将公共危险化引起的具有抽象危险性的环境媒介给予积极保护。尽管在日本国内针对环境犯罪立法体系有一定批判之声,尤其是在面对福岛核电站事故引起人们对放射物质扩散深深地恐惧,而法律又没有相应的立法规制背景之下,以呼吁重新建构环境刑法的应有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体系帮助日本在培育国民形成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而反观我国的“单一型”立法模式,即用一部刑法典涵盖了所有的环境犯罪规定,虽然有利于民众全面系统地了解环境犯罪的犯罪构成和刑罚配置,能较好的实现刑法的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类型立法模式的封闭性将导致社会变革与立法发展的严重脱钩,阻碍刑法机能的实现。另外,虽然在形式上存在行政法之内的环境罚则,但并无实际意义上的罚则规定,例如,《水污染防止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第101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第127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等,这种法律规定直接导致了处罚范围的不明确,最终也就造成了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打击环境犯罪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