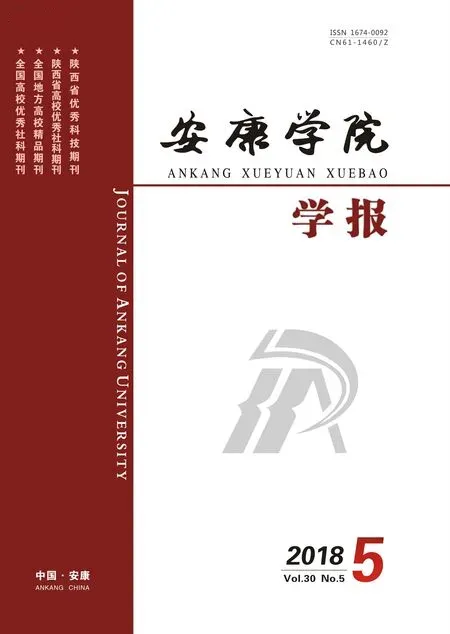被湮埋的研究视野
——“准则英雄”的三重维度观照
丁 萌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海明威研究是世界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中国学术界在海明威研究领域的成果亦相当丰硕。以历时角度看,中国海明威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1937年抗战前开始至新中国成立;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至1965年;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第四时期从1976年至今[1]。在众多研究中,“准则英雄”或“硬汉形象”的提法广为中外研究者所关注。“准则英雄”(Code Hero) 的概念,由美国海明威研究专家菲利普·扬(Philip Young) 提出,传至国内,由于翻译与接受的需要与改造,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如赵家壁先生以“硬心肠”代指,董衡巽先生以“硬汉性格”[2]代称,后又出现“硬汉子”等,保留至今。由“准则英雄”到“硬汉性格”或“硬汉子”,不仅仅只是翻译上换了面目,也出现了问题,即这一置换已不能完整、准确地还原其本有的综合涵义。本文将从菲利普·扬的“准则英雄”的原始定义以及海明威作品中的“准则英雄”精神内核出发,尝试还原背后的三重维度指向。
一、集体性:“准则英雄”图卷下的女性气质
菲利普·扬(PhilipYoung)对“准则英雄”的解释为:“重压下的优雅风度”,拆分为“重压”“优雅”“风度”,大意指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都可以化精神上的压力为动力,进而迸发出坚毅的力量,从逆境中不断寻找新的出路,历经磨难成为真正的英雄。值得商榷的是,菲利普并没有就此详细阐述这一精神气质所指的对象范围与性别维度。以此精神品质来看,海明威笔下的“准则英雄”并不排斥女性的参与,而这一点是为众多研究者所忽视的。
“准则英雄”气质的展示,不单单指向于某一个人物。按照菲利普的原意,其更侧重于精神品质,指向海明威笔下那一系列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斗争品格与进取精神。董衡巽先生将其解释为:“这是些面对失败还奋斗不息、身临险境而视死如归,从而保持了个人的尊严的‘畸零人’。”[3]仅从汉语语境出发,“硬汉性格”或“硬汉子”倾向于海明威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几乎都是男性形象,但海明威本人的女性观是否在“准则英雄”中有所体现,是否也指向女性,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关于海明威的女性观,国内研究者总体上持两种态度,即“天使”和“妖女”两种类型,一部分评论家认为海明威是歧视女性的男权主义者,另一部分评论家则认为海明威是支持妇女运动的女权拥护者。海明威的女性观很难界定,但歧视女性之见略有偏颇,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正如海明威本人而言“女性人物最难处理,但当别人批评没有你所写的这种女人时,你千万不要担心。那只表明你的女性人物不同于他们的女性人物”[4],认识到这种不同,就否定了海明威本人歧视女性的专制视角。我们以具体的文本分析来检验,在《永别了,武器》中,凯瑟琳就表现出了这种不同于其他女性人物的独特性。首先,凯瑟琳最初并非是以“新女性”的形象出现,经历了前后转变的过程。在凯瑟琳最初的婚姻里,她的角色设定为被束缚在传统观念中的屈服者,因为战争毁灭了她的爱情与婚姻,相应地解构了她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推动了凯瑟琳的转变。其次,凯瑟琳旧有价值观的崩塌,还原了她身上业已存在的独立精神与刚毅品格。凯瑟琳的转变不是战争一蹴而就的,她骨子里一直具有经受命运考验的韧性。比如她在反驳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懦夫千死,勇者只有一死”时说:“说这话的人大概还是个懦夫,他对懦夫很熟悉,对勇者可全不知道。勇者倘若是聪明人的话,也许要死上两千次。他只是不说出来就是啦”[5];又比如她努力避孕,虽然失败并没有流于愤怒、懊悔,而是坦然接受。命运在凯瑟琳的世界观里是无从逃避的,但如何应对取决于自己;再如面对死亡,难产之际她一直安慰着近乎崩溃的亨利,始终保持着镇静与从容。综上,凯瑟琳不是威猛的硬汉,但她绝对是一个能够直面人生与死亡的勇者,坚持为生而活、直面死亡的人生准则,从精神品质来看,她绝对是一个绝境中懂得自救以及帮助亨利直视命运的“英雄”。
“准则英雄”是对“重压下的优雅风度”的人物的精神品格的概括,它从来不指向单个的人物形象性格,而是一个集体性名词,绝非仅限于男性角色,在面对灾难和失败时,能否表现出坚忍不拔的承受力与抵抗力,保持生而为人的尊严,才是衡量人物是海明威式“准则英雄”的考量标准,以此来看,海明威笔下塑造的女性角色也符合这一标准。
二、建构性:“准则英雄”的演变机制
“准则英雄”作为人物气质、精神的浓缩,不仅是一系列人物所表现出的集体属性,而且其形成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建构性,与海明威本人的创作观以及生活阅历紧密关联。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可以按时间顺序参照海明威的五部长篇小说,概括为“萌芽—雏形—觉醒—成熟—典型”的线性发展过程,我们集中以五部小说中的五个角色来梳理此建构历程与演变机制。
(一) 尼克·亚当斯
海明威生前以尼克为主人公的小说并没有得以面世,散见于断断续续的创作之中。1972年《尼克·亚当斯故事集》的出版,以尼克为主人公的作品才得以展现给读者。故事集讲述了尼克的成长历程,可看作为成长小说,表现了尼克在经历诱惑、磨难、战争后的成长历变,也引出了海明威作品中一贯的反战主题与死亡主题。尤其是在死亡面前尼克真实性的展现,如在《印第安人营地》中,尼克以少年懵懂的视角亲身经历了生与死的同步发生,产妇难产的痛苦竟会令女子丈夫割喉自杀,这是触目心惊的年少体验。尼克并非是以直面死亡的硬汉形象出现的,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更多的是压抑与迷茫,甚至有些苍白。但尼克见证了死亡的真实性而选择勇敢地活下去,没有丧失生存的勇气,可以看作为“准则英雄”的精神萌芽。
(二) 杰克·巴恩斯
杰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摧毁了杰克的伦理观念与精神信仰,是杰克一度精神死亡的罪魁祸首。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杰克在经历毁灭之后的失落感和空虚感,面对布莱特虽感情炙热,却没有行动的自信与勇气。战争使他丧失了性能力,也使得他成为一个安于现状的沉默者。这种沉默是一种从容的活法,不抱怨,不哀声叹气,不回忆那场噩梦般的战争。但杰克的生存状态并非是由沉默走向堕落,相反他一直坚毅地默默忍受着生理与心理的重压,不表现出来,全部压在心底,仍能以一种“洒脱”的态度按照自己的方式活下去,这正是“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在小说第二部,杰克的转变,重新唤醒了他生而为人的活力。他从放荡的生活中惊醒,决定找回“和土地的联系”。在罗梅罗与公牛搏斗的过程中,他寻找到了作为一个男性的尊严与生命的热血,也找到了坚持活下去的人生准则:战争剥夺了他作为男性的生理权力,但没有剥夺他作为人所保留的尊严。罗梅罗这个斗牛士的出现,不仅唤醒了杰克,也成为海明威笔下角色转换的标志,即“英雄”将不再迷惘,唤醒如斗牛士般的刚强意志而勇敢接受命运的挑战。在杰克身上,他就是具有“准则英雄”气质的英雄雏形,预示着海明威对“准则英雄”创作的真正起步,开始思考他笔下的主人公会经历怎样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对于他后来的小说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 德里克·亨利
亨利的成长之路代表着“准则英雄”气质的彻底觉醒。这种觉醒也是通过亨利的前后变化来揭示的,以亨利为引,展示了旧有价值观的崩塌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亨利参战的目的并非保家卫国、飞黄腾达,他随波逐流,并没有为国献身的宏伟抱负。对待爱情,也是半推半就,与凯瑟琳最初交往时,他也只是觉得比逛窑子有意思。可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负伤与凯瑟琳无微不至的照顾,开始重建亨利的精神世界。凯瑟琳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二人迅速坠入爱河,亨利也于此开始走上觉醒之路。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对战时任务,都表现出一种庄重、严肃的态度。尤其是对战争的态度,如果之前作战只是为了完成使命,现在他清醒认识到了战争的可怕,只想一心完成任务,早日离开战场。死亡信号的降临对于亨利是一场真相的曝光,即当他被当作德国间谍处死之时,亨利彻底明白了战争的本质,“圣战”“荣誉”只不过是利用爱国的冲动而编织的糖衣炮弹,于是他决定与凯瑟琳奔赴瑞士。亨利前后不同的视角昭显了命运悲剧的必然性,也消解了亨利作为逃兵的软弱性。他并非软弱,从意大利逃往瑞士,这是亨利在战时反抗命运的一种特殊方式。他的选择是能被理解的。奔赴瑞士的情节安排,表明在海明威的准则英雄世界里的双向思考,即这一精神品质并非等同于何时何地都一往无前的人道主义英雄。相比杰克·巴恩斯,亨利敢于同黑暗世界进行抗争,反抗现实的意识自觉意味着“准则英雄”身上抗争意识的真正觉醒。
(四) 罗伯特·乔丹
乔丹代表着“准则英雄”精神品格的基本定型,已能够表达海明威式的硬汉性格的所有含义,这主要是针对乔丹敢于反抗的自觉行动而言的。在《丧钟为谁而鸣》中透露着浓郁的悲剧色彩,海明威本人也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作品还原了西班牙内战的真实状况,把乔丹塑造成了一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献身的人道主义英雄,是一个“为人类高尚的生存权利而战斗”的真正英雄。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选择忍受;在《永别了,武器》中,亨利选择远离战争奔赴瑞士。但只有到了罗伯特·乔丹,这种抗争才发展成为毫不妥协式的反抗,近乎一种被神化的人类英雄塑造。英雄不论成败,乔丹这一悲剧形象迸发出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光辉。更为不同的是,乔丹不同于杰克、亨利,彰显的是个体价值,海明威把乔丹的所作所为与人类命运相联系,故乔丹形象的塑造在海明威英雄谱系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标志着海明威笔下要传达的“准则英雄”精神的成熟与定型,展现了由小我到全人类的英雄形象。
(五)桑地亚哥
桑地亚哥已是“准则英雄”中的典型形象了,最能代表海明威本人对“准则英雄”之含义的完整思考。称其完整,是因为桑地亚哥一反海明威之前四部小说的战争主题,从宏观的战争、人类群体收缩到典型的海洋、渔夫中来,但所要表达的“准则英雄”精神中的“准则”之义,却比前四部小说更具力度与代表性。桑地亚哥并非站在全人类之上的“英雄”,而是具有哲学超脱意义的人物符号,英雄并非面对的都是全人类,或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命运悲剧,诸如战争,而是持有超越肉体生死的生命执念:“一个人并不是生来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种直面死亡、向死而生的信念,经得起包括死亡在内的所有检验,所以桑地亚哥敢于同未知又无可逃避的命运抗争到底,即使面对的是海洋、鲨鱼、命运甚至是神秘的未知力量。他是一个不可能被打败的英雄。小说中出现的几次狮子,包括最后归途中梦到的狮子,既是桑地亚哥喜欢的拥有刚强气魄的动物,又是他自身不屈服于命运的真实写照。桑地亚哥以一个典型渔夫的个体身份,表现了“准则英雄”所具有的性格特征:英雄不一定要拯救世界,在和世界的联系与抗争中,死亡也是检验人性的标尺。向死而生,强者自救,而自救的关键是永远不要丧失生而为人的尊严与勇气,一旦意志被打败了,一切就被打败了。
在经历了这五个发展阶段之后,海明威所要表达的“准则英雄”气质已完整展现于读者面前了。这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建构性过程不能被忽视。这个变化的过程,既是海明威对人物的不断思考与提炼,也是自身对生命不断深入思考的显现。海明威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与以往的传统英雄形象略有不同,失败、逃避就不能称其为英雄么?英雄必须要拯救世界与全人类么?在他笔下的角色中,我们似乎能找到答案。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压下的优雅风度”。
三、自传性: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
海明威的小说带有极强的自传性:“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角色,他们必须出自作者自己经过消化了的经验,出自他的知识,出自他的头脑,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切他身上的东西。”[6]84所以小说中经常能看到海明威式性格的人物和他所喜好的景象。海明威的世界是一个典型的男人世界,“男子气概”是一种规范、一种理念。海明威的生命哲学是向死而生的哲学,向死而生突出的是“生”的要义,所以海明威的生平中充满了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与死亡亲密接触,不是藐视生命,而是敬畏生命的庄严。海明威喜欢打猎、钓鱼、拳击、斗牛、战争、极限运动,这些在他的小说中均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里,热爱打猎、斗牛;《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斗牛士罗梅罗被击倒十五次后仍顽强地站起来,以顽强的意志力最终战胜对手;《老人与海》描写的是桑地亚哥与鲨鱼、与命运的斗争过程;《太阳照常升起》 《永别了,武器》以一战为背景,《丧钟为谁而鸣》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都是海明威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
以死亡观为例,海明威不同时期的作品所表现出的这一系列变化的死亡主题,与海明威本人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随着对生活和战争的认识的深入,海明威对生命与死亡的认识也在不断超越与升华,这一过程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中均能得到体现。
(一)对死亡的恐惧与思索
在早期以尼克为代表的自传性小说创作过程中,海明威刚从一战的战场回归,患上了失眠症,夜间不敢熄灯,并且整个人变得消沉。海明威自己也回忆说:“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啦!”而尼克也是在夜晚独自一人的帐篷中难以睡去,后来因经历战争也患上了失眠症。海明威在战场上经历了战友的死亡,这种震撼与心理阴影不亚于尼克目睹印第安男子割喉自尽的场景。海明威早期对于死亡的恐惧与疑问,如同尼克一直在追问“他为什么会死”这个问题一样,不断叩问、思索面对死亡时应该怎么办,这是海明威对死亡问题进行思索的开始。
(二)痛恨死亡带来的不幸
战争不仅让他经历了对死亡困惑,随后又让他对生活的意义产生困惑,这个阶段,海明威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开始由恐惧、疑惑转向痛恨死亡带来的不幸结局。海明威对生活的热情在战后逐渐被吞噬,成为“迷惘的一代”。在作品中以杰克为代表来传递自己的声音,战争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创伤,那种无法治愈的心理阴影让杰克“失去了和土地的联系”。然后怎么办呢?海明威将目光投向了斗牛场。斗牛士不仅要时刻做好丢失性命的准备,还要将这份不惧死亡的勇气以斗牛的过程、技巧展现出来,罗梅罗的出现意义非凡,他表现出的那份直面死亡的优雅风度,让杰克找到了作为男人的尊严。再来看《太阳照常升起》,整部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悲观色彩,依旧表明海明威本人还未能达到完全直视死亡的地步。1928年,父亲开枪自杀,使海明威再一次背负上了“家庭的诅咒”。可以说,父亲的自杀是海明威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这种死亡带来的悲痛感在《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身上得到了传达。亨利躲过了死亡,躲过了战争,却逃不过命运,凯瑟琳死于难产。死亡不仅是战争的附属品,也成为命运的必然归属,海明威传递了这种现实:“不要以为我向你们展现的残酷和破坏只局限于战争,它们是生活本身的状况”[6]225。
(三)直面死亡,勇于承担起死亡的重担
海明威并没有因见证朋友、亲人的死亡而选择做死神的奴隶,他坦然接受了命运的裁决,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深入报道前线战事,所以在他的小说里都有对战争的真实反映,如一战、西班牙土耳其战争、西班牙内战、二战等,在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中,海明威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创作于1936年,直接把主人公置身于死亡门前。哈里大好年华曾一度浪费在金钱与享乐之中,濒临死亡时才幡然醒悟。死亡对于哈里来说,也经历了由恐惧到坦然的过程。哈里是逐渐走向死亡的,在描述逼近死亡之际展现意识的流动,在意识流动中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体悟。哈里最初被深深的恐惧所支配,然后接受了死亡的事实,最后在濒死之际完成了对死亡的超越。通过这部小说,表明这一时期的海明威已经在死亡问题上开始逐渐摆脱挣扎与困惑,开始尝试直面死亡。再来看《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死亡的出现已祛除了恐惧的痕迹。面对生命最后一程而出现的爱情,他依然没有动摇完成使命的决心。他选择为全人类而死,他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已经使他能够自觉完成对死亡的超越,一直坚持到死亡的最后一刻。这充分显示出向死而生的坚定与自觉。
(四)超越生死,战胜死亡
海明威于1961年自杀,《老人与海》发表于1952年,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揭示了海明威晚年对死亡的超越。当传记作家库尔特·辛格问他这部小说的题材从何而来时,他说:“我遇见一位老渔民,我们两人交谈起来,他向我讲了这个故事,他一想起这段经历,甚至于脸上也不禁露出痛苦和失望的神情。那是一场悲剧”[7]。在桑地亚哥身上表现出的不惧死亡、超越生死的哲学超脱,折射出海明威本人对死亡的超越与升华。人虽只有一生,却不得不与战争和虚无为伴。死亡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恐惧在所难免。在桑地亚哥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义无反顾地搏斗与抗争,无论马林鱼、鲨鱼、海洋,也无论命运、自然、神秘这些无可言说的力量给予生命怎样的重担,在桑地亚哥自我的世界里,没有屈服与恐惧,只有永不妥协的斗志与不惧死亡的勇气。老人身上就没有一丁点妥协与退让么?这也不一定,小说中老人曾9次在精疲力竭之时说到“要是那孩子在就好了”。硬汉柔骨,孩子也是老人内心寄托的一部分。这不是软弱,人并非生来就有钢铁般的不屈意志,老人也有“弱”的一面,他忍受不了孤独,忍受不了没有孩子的陪伴。在爱的面前,服软;在苦难与死亡面前,绝不低头。老人在苦难前没有表现出一丝怯懦,以“狮子”般的勇气挺立于海洋之上,悲壮的叙事氛围中透露出一股庄重的英雄之气,那就是战胜死亡、超越死亡的美学意义。
综上,海明威小说中的这些故事基本都取材于海明威自身的经历与思想变化,所以“准则英雄”的精神品格带有海明威式的英雄气质与铁骨柔情,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色彩。
四、结语
“准则英雄”作为海明威笔下的英雄群像,是海明威美学思想的集中展示,是一种超脱悲剧、直面命运、奋力搏击的豁达洒脱,更是一种强者自救、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仅仅用“硬汉子”或“硬汉性格”来概括这一群体的精神内涵,是对海明威本人生命哲学的局部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