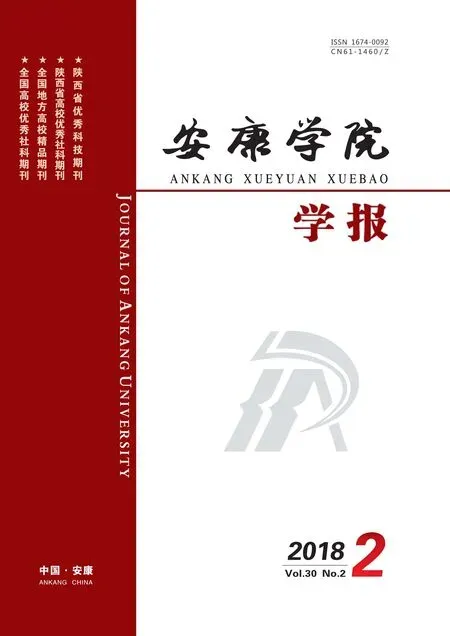论《白鹿原》的叙事立场与话语谱系
朱 云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文学作品具有独立于作家的主体性,文学批评可以不去关注作家,只需面对文本说话,这已是学界共识。不过,在开放作品丰富解读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批评家都是带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立场进入文本的,这就有可能造成他们对作品理解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有时甚至会南辕北辙、互相对立。后一点在关于《白鹿原》的评论中显得尤为明显,赞扬者称赞这部作品是一部“史诗”“大书”“奇书”,贬低者指责这部作品艺术构思混杂、文化立场保守[1]。针对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时过于注重自身的立场,从而带来的“批评歧见”,有学者提出:“我们在面对作家作品时,不能把批评的权利和它与社会思潮的联盟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此同时也应该从作家的后记和访谈录中这些被压制的历史文献中去反问,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不是都是应该的?在千百万次想当然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文学作品的本来意愿是不是也被压制了?”[2]251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了解作家创作的原初意图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能告知我们作品的原意是怎样的,以及它为何是这样的。当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家的创作意图往往有其“历史的根据”,它与此前的创作潮流、艺术流派有密切的关联,解读作品显然不能忽略这些因素。这样才能更好地接近“更具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不是告诉我们它是什么,与此同时也应该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是这样的。”[2]40
本文试图从《白鹿原》中存在的一个疑点以及白鹿的象征含义入手,结合作家自述及文学史周边材料,探究《白鹿原》的叙事立场,解读作品中的一些争议焦点,分析其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关系,进而探求作品形成的“历史来路”和话语谱系。白鹿的象征含义之所以会成为疑点,是因为它在作品中既象征大儒朱先生,又象征革命战士白灵,而朱先生和白灵的形象差距很大,给人有分裂之感,有论者甚至认为这是作品的一个败笔:“赋予白鹿多重象征的意味,在具体的情景里它们当然都是成立的,亦无不当。可是如果将整个故事连起来,其象征意味随场合而变,就损害了亚里士多德说的整一性原则了”[3]。是否败笔,我们姑且不论。从“症候式”分析的角度看,作品中一旦出现矛盾或者裂痕,这往往是绝佳的分析入口。本文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小说周边资料展开论析。
一、《白鹿原》中的白鹿描写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认为,以意象来联结故事,以此“增加叙事过程的诗化程度和审美浓度”,是“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4]。从陈忠实的创作自述来看,他的小说创作似乎很少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但用象征或者意象来丰富作品的意蕴内涵,《白鹿原》却接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精髓。从艺术谱系的角度看,正如有论者分析的那样,《白鹿原》中大量象征意象的出现,显然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的“形式自觉”有密切关系[5]。关于这一点,从《爸爸爸》 《小鲍庄》 《黑骏马》 《棋王》 《最后一个渔佬》等“寻根小说”的象征运用就不难理解。当然,对于陈忠实而言,南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若没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形式自觉”的文学氛围,其影响效能是否有现在这么大是值得怀疑的。通览整部小说,《白鹿原》存在多个“可以点醒故事的精神”的意象,如白鹿、白狼、鏊子、白嘉轩挺直的腰杆,这些意象散布在故事之中,不仅自然适度,而且以其高度的意义概括功能显著地揭示了作品的特定意蕴。受篇幅限制,本文不拟对其他意象进行过多辨析,而是着力探求与论题相关的白鹿意象。
白鹿意象一共在文本中出现过七次。前五次的寓意比较一致,它代表美好与祥和:宋代小吏途径当地,偶遇白鹿一跃而隐,遂买地建房定居,使“四个孙子齐摆摆成了四个进士”;白嘉轩独自发现大雪后形似白鹿的野草,遂设计与鹿子霖换地,将父亲的坟地迁往此处,从此人丁兴旺,家道中兴(此一形象在小说末尾又同义反复出现了一次,这里只算作一次);在一个不知传自哪个年代的古老传说中:“一只雪白的神鹿,柔弱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乐康”;白灵入党宣誓之后,鹿兆鹏问白灵想起了什么,白灵说她想起了“奶奶讲下的白鹿。咱们原上那只鹿。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在镇压小娥鬼魂的塔上刻了两只可爱的白鹿,塔修好后,瘟疫灭了,鹿三也不鬼魂附体了。如果对照后来陈忠实创作自述中对白鹿的解释,白灵入党时对于白鹿的理解其实就是陈忠实的理解,陈忠实是在借白灵之口阐述他赋予白鹿的象征含义。在《原的剥离》一文中,陈忠实这样描述白鹿传说:“据《竹书纪年》的文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读到原上先民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的想往里的生活景象,当即联想到早已储存于心底的共产主义美好图景……我不在意民间神话传说和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的不可类比的差别,但有一点却使我顿然豁朗,人们对于富裕和和平生活的想往和期待,从先民时期就开始构思了,其实这不过是作为人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6]。可见,在陈忠实的心中,白鹿象征着人类的基本生存要求,代表人们追求富裕与和平的生活愿望。
疑问主要存在于白鹿的后两次出现:白灵被冤杀的那天,白嘉轩刚睡着就梦见了一只白鹿,“我清清楚楚地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停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走了。刚掉头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了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朱先生去世的当儿,他的夫人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这两次出现,白鹿都象征着人,但这两个人的身份却非常悬殊:一个是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在小说中,用同一个意象来象征不同的事物,这两件事物之间必须具有相似点。比如钱钟书的《围城》,“围城”既可象征婚姻,没结婚的人想进去,结了婚的人想出来;也可象征人生,某一种生活,没有进去过很向往,进去后发现也就这样,于是想出来。在《白鹿原》中,无论怎么看,朱先生和白灵都难有相似之处,作家将两个如此不相似的人用同一个意象来形容,难怪有论者会质疑其“损害了亚里士多德说的整一性原则”。那么,陈忠实用白鹿同时象征朱先生和白灵是否如表象显示得那样有割裂,又如何将这里的人物象征与前面的象征寓意统一起来?这里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下朱先生和白灵这两个人物形象。
二、《白鹿原》对朱先生的描写
朱先生和白嘉轩一般被看作是儒家文化人格的代表,但仔细审视,作品中对他们的塑造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人物身份的不同,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导师,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的具体实践者,更是形象内涵和思想意蕴的差别。
阅读文本可以发现:白嘉轩作为儒家文化的实践者,在彰显其儒家道德光彩的同时,还承载了浓重的儒家文化负面因素,比如对小娥压迫的冷酷,阻止两个儿子进城读书的保守,断绝与白灵父女关系的守旧;朱先生就不一样了,作为儒家文化的播种者,虽然白嘉轩实践的“乡约”是由他抄写的,但小说很少从负面的角度描写他。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教书先生,朱先生虽然也有守旧的一面,比如开办学堂但不教“新学”,以致于学生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关门;但是,小说中却没有花费笔墨来渲染他的守旧,与五四启蒙语境中刻板的私塾先生对照,《白鹿原》中没有语言描述他对学生自由个性的压制。小说中一个有意味的例子是,白灵上学后与白嘉轩起了严重的价值观冲突,但在朱先生这里得到了宽容地对待。小说对朱先生唯一的负面描写,是他出主意修塔镇压小娥的鬼魂,而这还是在人们认为小娥的鬼魂作怪,以瘟疫害死了很多人之后。以此相对的是,作者用了很多篇幅刻画他在民生面临威胁时的挺身而出:白鹿原种植罂粟成风之时,他厉行禁烟;白嘉轩和鹿子霖为争夺一块田地互不相让,导致白鹿两族斗殴的危险时刻,他用一封信成功调和;“反正”之后,当民众面临战争生灵涂炭的危险时,他只身退敌;日本侵略中国之后,他又是发声明,又是要参军,力图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民国干旱席卷大地的饥荒年月,他慨然出山主持赈灾。与白嘉轩相比较,作品对朱先生思想行为的描写过于理想化和正面化,再加上他死后对“文革”的神秘预测,评论界普遍认为这个人物塑造得不如白嘉轩丰满和真实。雷达在《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中就认为作者在刻画朱先生时采用了“浪漫笔调”,并认为这是作者对传统文化寄予了过多期望的缘故[7]。认为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的时候,不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寄予了过多期望并不是个案,而是相当多批评家的选择①参阅南帆《文化的尴尬——重读〈白鹿原〉》,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第62-69页;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的悖论》,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第91-97页。。在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
陈忠实在《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中直接从“寻根小说”兴起的1985年开始谈起,这显示出当时文学氛围对他的影响。众所周知,“寻根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有韩少功式的批判,也有阿城式对传统正统文化有选择性的肯定,还有李杭育式对传统边缘文化的追寻。从陈忠实后来的自述看,他的文化立场与阿城式态度基本一致。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阿城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其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8]。言下之意,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过于激烈了,它在批判传统文化负面基因的同时,将传统文化的正面因素也一并批判了,最终与后续的历史运动一起造成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当代的“断裂”。与此相似,在谈到《阿Q正传》对赵老太爷、《家》对高老太爷的批判时,陈忠实有如下表述:“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要革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要把他们化为腐朽的形象,作为反封建的批判对象是合理的。到了今天,时代过去近乎一个世纪之后,我再来写,我就希望写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来,既批判他(指白嘉轩——引着注)落后的东西,又写出他精神世界里为我们这民族应该继承的东西”[9]418。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出于“对我们文学世界画廊的一个补充”,他有意凸显了朱先生和白嘉轩两人身上的儒家道德光彩:“我写朱先生和白嘉轩就是要写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到上个世纪初一直传递下来的,存在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最优秀的东西,要把它集中体现出来。我有一个看法: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上个世纪初国衰民穷,已经腐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存在于我们底层民族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并没有消亡,它不是一堆豆腐渣,它的精神一直传承了下来,如果我们民族没有这些优秀的东西,它不可能延续几千年,它早就被另一个民族所同化或异化了,甚至亡国亡种了”[9]398。
从上面的引文,至少可以发现两点:一是陈忠实确实有意凸显朱先生和白嘉轩两个人物的道德光彩,以颂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二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我们文学世界画廊的一个补充”,即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封建地主写得那么坏。换句话说,他凸显朱先生和白嘉轩的道德光彩,有恢复人物塑造复杂性的意图。在谈到他是否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时,陈忠实斩钉截铁地回答:“那是没有的事!无论是写白灵还是小娥,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物,我都是要写人的复杂性!”[9]415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不难看出这与20世纪80年代建立在“人的文学”基础上的“性格组合论”的关系。刘再复在1984年和1985年分别发表了《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10]和《论文学的主体性》[11],在前文中,他从性格二重组合的角度对人性的复杂作了系统论述,认为人物性格从构成上说有灵与肉、善与恶、进步与落后、美与丑的区别,从变动的角度有随时间流动和空间转移的差异;在后文中,他将人物塑造作为文学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论析,反对只从环境、阶级的角度对人物进行机械式塑造,也反对只写人物的外在冲突,而不涉及人的内心灵魂。刘再复的两篇论文反响巨大,如果以此为标准审视《白鹿原》的人物塑造,可以说这部作品确实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延展至90年代的一部“总结性”作品:人物不仅有外在动作描写,而且有内在灵魂的塑造;人与人的关系有善与恶、进步与落后的区别;人自身有好与坏、灵与肉的纠缠,而且性格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变迁。
由以上分析可见,陈忠实凸显朱先生和白嘉轩的道德光彩,一是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二是追求封建地主形象的人性塑造的复杂,但他否认自己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指责陈忠实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家显然没有充分注意到陈忠实的自我辩解。虽然文学文本创作出来后会突破作家赋予它的原意,但即使从文本的角度考察,陈忠实对儒家思想负面基因的批判一点也不比他对儒家文化优秀基因的颂扬弱。事实上,小说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儒家文化的保守性和腐朽性。比如白嘉轩阻止两个儿子去城里读书接受新学、白灵去城里读书后与他发生了严重的价值观冲突,尤其是小说令人震撼地描写了小娥和鹿冷氏所受到的人身和精神压迫,这些都显示出了《白鹿原》与20世纪80年代高扬的五四批判精神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因此,说《白鹿原》唱了一曲儒家文化的挽歌,实在只看到了作品思想意蕴的一个倾向。
如果进一步分析,在挖掘朱先生和白嘉轩两个人物的儒家道德光彩时,陈忠实赋予他们的意蕴内涵又各有侧重。在白嘉轩身上,陈忠实主要赋予了其一些高贵的人格,比如勤劳、正直、以德报怨等;而在朱先生身上,则侧重挖掘了其民本思想。无论是禁烟、调和、退兵、从军还是赈灾,朱先生的行为都是为了民众的生存福祉。可以说,对民众物质生存现实的关注,一直是朱先生行为处事的标准。大革命风潮中,又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白嘉轩出于一山不容二虎的焦虑,向朱先生寻求面对这一两难处境的方法时,朱先生大笑说:“我可不管闲事。无论是谁,只要不夺我一碗苞谷糁子我就不管他弄啥”。后来,国共反目,由此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影响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安宁,朱先生不仅以鏊子说对其进行反讽,而且当着鹿兆鹏的面,直斥国共围绕农运的斗争是争权夺利:“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倡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戕杀?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饸饹的争斗也无非是为独占集市!”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长期以来备受争议,这里也需要辨析一下。本文认为朱先生用鏊子说比喻国共争斗,认为两党反目是为了争权夺利,用于形容历史上的国共内战是不适当的,但用来形容小说中两党在白鹿原上围绕农运而展开的斗争则有其合理性。从小说描写的内容来看,田福贤、鹿子霖等革命新贵,以权谋私,对国民党辛亥革命的目标基本不理解;而从黑娃等人在农运中和农运后的表现来看,他们搞农运也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并没有真正理解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所以黑娃后来当了土匪,而且革命成功之后竟然回归传统“学为好人”。因此,仅就小说中的这一场斗争来看,双方确实有争权夺利的功利动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白鹿原》对“革命”的这种叙述,与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历史小说”非常相似。正像评论家们分析得那样,“新历史小说”在叙述革命时“首先是革命起源与动机的欲望化,即革命主要来源自个体内在心理、情感和欲望的匮乏(或扭曲)”[12]。在《白鹿原》中,鹿子霖参加辛亥革命是为了与白嘉轩相抗衡,黑娃参加农运是为了不满和报复,白孝文无论前面捕杀共产党,还是后来归降都是为了利益,即他们参加革命是因为“心理、情感和欲望的匮乏(或扭曲)”。与此相对,具有先进革命思想的革命党人,其“革命者”形象往往比较弱。与《红旗谱》中掌握强大革命话语思想的贾湘农相比,鹿兆鹏这个鼓动黑娃革命的启蒙者,其“革命者”形象实在不够饱满,除了干革命不屈不饶外,其对革命目的、方式和意义的论证非常模糊。
从此后的采访自述看,陈忠实这样写的目的,除了恢复“文学是人学”的生命色彩和人性复杂外,还和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历史文化反思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领袖李泽厚认为,“真正的传统是己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家孔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溶化浸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之中了,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广大农民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孔子,但孔子开创的那一套通由长期的宗法制度,从长幼尊卑的秩序到‘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早已浸透在他们遵循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之中”[13],而这不是说变就能变的。从陈忠实的相关表述看,他接受了这一思想,在谈到关中地区的文化时,他说:“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14]。在谈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时,他说:“我们民族,几千年来读着一本大书……虽然解放后不读那本大书了,且那本书受到批判。但它依然以无形的形态影响着乡里人,也影响着城里人。要彻底摆脱那本书的影响,恐怕不是一代两代人的事”[15]。从上下文,不难体会“这本大书”就是儒家文化。在陈忠实看来,已经凝结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不是一场革命说变就能变的。事实上,从鹿子霖、白孝文,再到姜政委,我们能梳理出一条只重自身利益的“革命”人物谱系。就像当年阿Q以为革命是杀仇人、抢财产和夺老婆一样,这些人物的思想素质和阿Q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可以说,《白鹿原》对民族文化心理艰难蜕变的反思,深化了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主题,显示了其与启蒙批判精神的深度思想联系,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白鹿原》的叙事立场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
由于朱先生身上浓重的民本思想,而白鹿又象征着人们对富裕与和平生活的期望,所以朱先生逝世的时候,陈忠实用白鹿来形容他。这里需要分析的是,富裕与和平生活的愿望不应该仅仅是物质的满足,还应当包含精神的丰富和自由。后者显然是朱先生无法承担的。在小说中,虽然朱先生基本没有参与直接的“礼教吃人”实践,但作为“乡约”的抄写人和白嘉轩的精神导师,白鹿原上“礼教吃人”的责任,他难逃其咎,追根究底,他是白鹿原“礼教吃人”的重要嫁接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将他当作人类追求富裕与和平生活的象征来描写是有局限的,因为他身上负载的“礼教吃人”(小说中对此虽然没有强调,但客观存在)会压抑人的自由和生命活力。所以,朱先生只能成为人们物质上求得富裕与和平生活愿望的象征,而无法成为人们精神上求得富裕与和平生活愿望的象征,虽然他在道德追求上恪尽“仁义”,但其精神世界内蕴的儒家文化负面因素会扼杀人性的一些合理欲求。也许是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白鹿原》出现了另一个可以用白鹿来概括的人物,即白灵。饶有意味的是,如果说朱先生非常关注民众的现实生存福祉,那么白灵则更加重视思想和精神的自由。
三、《白鹿原》对白灵的描写
和鹿兆鹏一样,作为具有新思想的革命女性,白灵的“革命者”形象也不是很饱满,但这并不影响白灵是一个非常出彩的女性人物形象。众所周知,《白鹿原》中有三类女性人物形象,一类是恪守封建礼教的“贤妻良母”,如朱白氏、仙草;一类是生理合理欲求受到压抑做出不轨行为的“叛女”形象,如小娥、鹿冷氏;还有一类就是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女性形象,如白灵。白灵不仅不同于《白鹿原》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革命女性形象相比,也性格独具。将白灵和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正像评论家所论述的那样,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经历了两次转向,一次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离家出走与余永泽在北大同居;一次是对日常庸俗生活的不满,寻求走入社会,从个人幸福的追求走向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革命[16]。与林道静不同,白灵虽然也反抗过封建包办婚姻,但这并不是她出走家庭的最初原因,她走出封建家庭藩篱的最初原因是对自由天性的热爱;而她走上共产党革命的道路,也并非对日常庸俗生活的不满,而是出自一种对国民党残酷杀戮的义愤,是一种道义的选择。可以说,白灵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因为生存压迫,而是出自性格天性中对自由和道义的大胆追求。
为了刻画白灵对自由、道义的大胆追求,陈忠实侧重描写了她求学、拒婚、入党、择偶、冤杀五个故事。白灵这一人物形象初次显示出动人的光彩是在第八章,反正之后,城里的表姐们回乡探亲,得知表姐们在城里念书后,白灵提出自己也要到城里念书。一直溺爱女儿的白嘉轩没有同意白灵的要求,但还是将她送到了村里的私塾学校去念书。一到学校念书,白灵聪慧自由的本性就彰显了出来,她不仅学习比哥哥们好,而且两年下来毛笔字也超过了先生,更有趣的是,她完全无视礼法,竟然在先生上厕所的时候对其进行作弄。后来,当表姐再一次回乡探亲时,她不经过父亲的同意,十天后竟私自离家出走,跑到城里念书去了,而且在白嘉轩追过来强迫她回去时说:“爸!你要是逼我回去,我就死给你看!”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追求自由上,白灵比起她的两个哥哥来,要更加大胆和勇敢,因为他的两个哥哥也提出过到城里上学的请求,但被白嘉轩呵斥一声后就不敢再强求了。
不久,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她不仅在城里和鹿兆海谈恋爱,而且积极投身到大革命运动中。当她从学校返回家时,白嘉轩对她的行为非常恼火,强行将她反锁在屋子里,试图用父母之命的婚姻锁上她自由飞翔的翅膀,而她再一次以死相威胁,在威胁不奏效的情况下,想办法又一次逃出了家门,并在墙上写下一行字:“谁阻挡革命就把他踏倒!”从墙面上所写的字,我们能感受到白灵不仅酷爱自由,而且勇于追求道义。此后,她出于对国民党残酷杀害共产党行为的义愤,认清了国民党一党独裁、迫害异己、戕害自由的行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此时,她热爱的恋人鹿兆海却加入了国民党,两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她为了追求自由和道义,痛苦而遗憾地与鹿兆海分手。后来,在与鹿兆鹏假扮夫妻从事地下斗争的过程中,她勇敢地向鹿兆鹏表达了自己的爱情,并最终走到了一起。由于怀孕,她撤离到南梁革命根据地,在与左倾分子的斗争中,她同样由于坚守自由与道义,在大骂中被活埋。纵观白灵的一生,大胆追寻自由,勇于坚守道义,构成她在白鹿原上行为处事的基本动因。
尽管从陈忠实的创作自述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作家用白鹿形容白灵,是期望用她的精神来充实白鹿寓意的人类追求富裕与和平生活的愿望,同时还包括对精神的追求,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从小说文本的角度看,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朱先生和白灵是唯一两个被“白鹿”指称的人,而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关注民众物质生存现实,一个重视个体精神自由,把他们分别解读为象征人类追求富裕与和平生活愿望的物质和精神层面是比较合理的。而从陈忠实此前的文学创作来看,更是有迹可循。评论家已经发现,《白鹿原》中的思想和故事情节其实在他此前的文学创作中就已经出现①参阅孔范今《陈忠实研究资料》中的陈涌《关于陈忠实的创作》、李建军《廊庑渐大:陈忠实过渡期小说创作状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比如《舔碗》与《白鹿原》的第六章几乎是一样的;又比如《蓝袍先生》中徐慎之由革命到回归传统与黑娃的“学为好人”有近似之处,而徐的父亲对他婚姻的干涉,与白嘉轩对白孝文婚后生活的介入也有相似之处;1987年写就的《窝囊》中被活埋的主人公张景文直接就是《白鹿原》中白灵的原型。在《白鹿原》中,白灵被活埋多少写得有些简略,但《窝囊》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刻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关于张景文被活埋原因的描写,由于特务的渗透,根据地对来自西安的同志进行甄别,张景文因为出身很好,革命理由不够充分,最终被认定为特务遭到活埋,就如活埋她的两个小战士所说的那样:“你怎么从西安跑到这儿来?又不是党派你来,又不是像俺俩一样,受压迫受不住了才来造反!你不是没吃没穿,又能念书,你跑到这山沟来闹啥革命嘛!洋学生……”两个小战士对张景文的挖苦和不理解,显示了张景文闹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生存,而是为了追寻精神的自由和光明,这在《白鹿原》中化做了白灵最显耀的性格特征。如果再对照创作于1986年的《四妹子》,陈忠实对张景文(白灵)自由精神追求的推崇会显得更加明显。这部小说写的是出生于陕北的四妹子,由于没有吃和穿,无奈来到富庶的关中投奔姑姑,目的是为了在这边找个人嫁了,以解决物质生存问题。然而出嫁之后,物质生存问题解决了,精神自由却出了问题。陕北乐观、自由、浪漫的精神个性与关中注重“礼”节、讲究规范的儒家文化精神个性发生了严重冲突,她的哼歌、串门等在公公看来成了“不规矩”的表现。为了解放自己的精神,四妹子开始想办法通过“改革”途径来获取经济的独立,并取得了成功。《四妹子》发表以后,评论家刚开始把这部小说读作是改革小说。陈忠实的解释是“《四妹子》就是写她的人生不自在”[17],换句话说,他是想通过陕北文化和关中文化的冲突来反思和批判关中儒家文化对人的精神自由个性的压抑,“中篇小说《四妹子》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其实是关于文化冲突的事象体系。它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一种古老的文化,不仅要尊重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还必须尊重人的精神生活,保护人的个性的自由舒展和情感生活的充分展开”[18]。可见,在《白鹿原》创作之前,陈忠实就已经充分意识到儒家文化压抑人的精神个性的不合理性,并通过小说创作强调了人的精神自由的可贵。从白灵的形象塑造看,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忠实此一时期的思想探索进入了《白鹿原》的写作,所以白灵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反思革命内部的左倾思想,还有高扬人的精神自由的意味。后一点显然是陈忠实所看重的,所以他用白鹿来指称白灵,以作为朱先生民本思想的补充。在这里我们发现,陈忠实对精神自由的高扬和同期的“新写实小说”在价值追求上有明显的区别。“新写实”小说搁置人的精神追求,凸显人“食”和“色”的生存本相,陈忠实显然并不完全如此。从他对朱先生民本思想的肯定,以及对小娥、鹿冷氏生理合理欲求的同情看,陈忠实和“新写实小说”一样重视人的物质生存现实;但从白灵蕴含的人的精神追求上说,其思想谱系承接的还是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思潮对更理想生活的追求。换句话说,《白鹿原》既重视物质诉求,更重视精神追求,在世俗化思潮冲击下的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其价值追求体现出一种非常可贵的完整的“人的文学”诉求。
四、结语
由于朱先生和白灵分别代表人类追求富裕与和平生活愿望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所以尽管两人身份悬殊,在他们死后,作家都用白鹿来形容他们并不分裂。相反,这里体现出了一种完整的“人的文学”的诉求。陈忠实以此诉求为基点,对儒家文化、革命历史、人性描写和艺术呈现上进行了全新整合。在文化评价上,既肯定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人格和民本思想,又批判了其对人的精神个性和生命活力的压抑;在革命历史的描写上,侧重批判了国民心中的自私和窝里斗,以鲜活的形象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蜕变的艰辛;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承接20世纪80年代“性格组合论”的成果,刻画出了善恶交织、灵肉一体、静变相交的人物形象系列;在表现手法上,续接寻根小说在象征意象、民间事象等方面的探索,有力地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力。无论是思想诉求,还是艺术表现,《白鹿原》都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延展至9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
参考文献:
[1]杨匡汉.白鹿原上的仁道与梦幻——当代文学札记[J].中华文化论坛.2015(11):58-65.
[2]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3]林岗.两种小说传统之间——读《白鹿原》[J].小说评论,2016(3):4-11.
[4]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7-352.
[5]余坚.新时期“寻根小说”的象征研究[D].银川:宁夏大学,2013.
[6]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05.
[7]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文学评论,1993(6):105-118.
[8]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M]//阿城.阿城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284.
[9]陈忠实.在自我反省中寻求艺术突破——与武汉大学博士生李遇春对话[M]//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七卷.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
[10]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J].文学评论,1984(3):24—141.
[11]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J].文学评论,1985(6):11-26.
[12]陈娇华.论新历史小说的革命书写[J].当代文坛,2009(2):62-91.
[13]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M]//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42.
[14]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之一[J].小说评论,2007(7):41-50.
[15]李星,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M]//孔范今.陈忠实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33-34.
[16]刘骥鹏.从“林道静道路”到“白灵道路”[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4):5-8.
[17]陈忠实.关于《四妹子》的附言[M]//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六卷.广州:广州文艺出版社,2004:386.
[18]李建军.廊庑渐大:陈忠实过渡期小说创作状况[M]//孔范今.陈忠实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