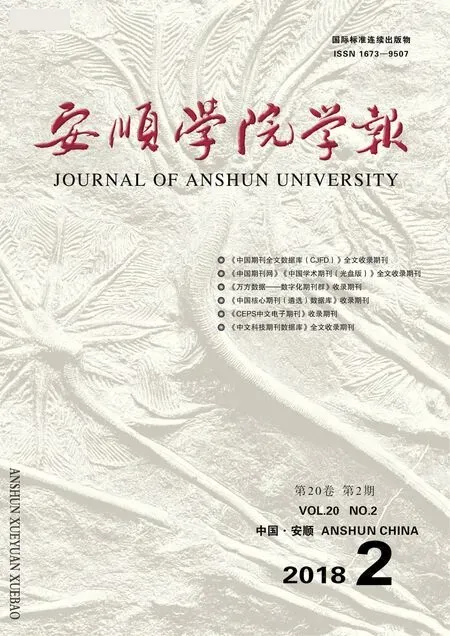从过渡礼仪理论考察蒙正苗族成人礼仪
(、.安顺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安顺56000)
法国范热内普《过渡礼仪》提出了人生礼仪对完成人生各阶段、确立个体身份、地位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只有通过“过渡礼仪”,个体生命进程中的各阶段(不同身份、地位、阶段等)才得以相互衔接并确立各自的权利责任。结合范氏理论,文章以黔中地区蒙正苗族的成年礼仪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蒙正苗族的发型、服饰、礼仪规范的变化,阐述其成人礼仪的特征及文化内涵。
一、 过渡礼仪中的成人礼仪
1.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
范热内普提出的“过渡礼仪”理论,是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不可忽略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范热内普认为,“每个个体的一生均由具有相似开头与结尾的一系列阶段组成,即诞生、社会成熟期、结婚、为人之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职业专业化以及死亡等。其中每个事件都伴随着仪式,其根本目标相同:使个体能够从一确定的境地过渡到另一同样确定的境地。”[1]3-4也就是说,人生的诸多礼仪,如出生、成人、订婚、结婚、丧葬等等都是通过一定的仪式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或是状态,以赋予或取消该个体一定的资格或能力。
过渡礼仪可以分为三层结构。首先,可以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全部过程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阶段,形成一个过渡礼仪体系。这其中所产生或举行的种种礼仪活动或行为表现,视为不同人生阶段的过渡礼仪。对于一个生命个体而言,经过出生礼仪,他便脱离了“神圣”(灵魂)阶段,被赋予了生存的资格,进入世俗世界;成年礼赋予了婚恋及参与社会事务的资格;婚姻及生育礼完成了成年个体的责任;其后通过死亡(丧葬)礼仪取消该个体的生命资格,并将之与世俗世界隔离,回归“神圣”。通过一环环的过渡礼仪,个体才能过渡到下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在前后两个重要阶段的过渡,如怀孕(胎儿)到新生儿、从儿童到成人、临终到死亡后的灵魂过渡等,在这些特殊的时间点所举行的过渡仪式。以普遍性的出生礼仪为例,通过命名、祭祖等仪式来消除死亡世界(基于生从死亡而来的思想)对婴儿的束缚,赋予婴儿生的权利,使灵魂正式归于肉体,让新生命正式纳入族群。在范热内普看来,便是一个婴儿从“旧有的死亡状态”过渡到“新生的生命状态”的过渡礼仪。
第三,是具体某一仪式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可能又包含了不同的过渡礼仪类型。范内热普进一步将过渡礼仪分为三个亚类型:分隔礼仪、聚合礼仪以及边缘礼仪。“分隔礼仪在丧葬意识中占主要成分;聚合礼仪在结婚仪式中占主要部分;边缘礼仪则在怀孕、订婚和成人礼仪中占重要角色。”[1]10如蒙正苗族的结婚礼仪中,新娘出门前要吃“离娘饭”,便属于“分隔礼仪”,让新娘与娘家通过仪式完成分离;在进入夫家大门前,要由一名寨老左手拉住新娘,右手提着一只公鸡在新娘头上舞三转,并念诵祝词,以示吉利,这属于聚合礼仪,让新娘融入夫家;而从定亲到新娘回门结束这整个过程又可以视为边缘礼仪,在这个阶段(也就是阈限内)新娘逐步脱离原有的身份(家庭、村落、氏族),但又没有一次性获得新的身份(即正式被夫家认可的已婚女性,被夫家所属的氏族所认可),这中间经历了一段过程。在这个期间内,新娘的身份即是“边缘化”的,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而礼仪赋予了这一时期以神圣性和合理性。
2.对成年礼仪过渡性的普遍性考察
结合过渡礼仪理论以及多民族、多地区成年礼仪风俗的表现,可以看出,成年礼仪并非一个独立的阶段,而是婚恋活动、社会活动的衔接阶段。
(1)成年与婚恋的过渡
成年和婚恋在多种文化中都是不可分割的。《礼记·曲礼上》记载,“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郑玄注:“以许嫁为成人。”[2]64又《礼记·内则》:“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郑玄注:“谓应年许嫁者,女子许嫁,笄而字之;其未许嫁,二十则笄。”[2]1014女子订婚后至出嫁前,大约15岁左右便要举行笄礼,若一直未定婚约,晚至20岁左右也要履行。少数民族的情况也多有相似,其中青海贵德藏区的藏族女孩有一个隆重的成年仪式——“戴天头”,13-15岁左右时,少女母亲将为女儿举行一场婚礼,其仪式与正式婚礼相同,但并没有新郎。这一天母亲要为女儿梳上成人发型,并举行一系列的仪式[3]。这一地区藏族女性的成年礼采用了婚礼的形式,相当程度凸显了成年与婚恋活动之间的必然性。
成人与婚恋活动之所以联系得如此紧密,当然有生理性和社会性的原因。男女性在12、13岁后便逐渐进入了性成熟期,但这一时期地域、民族、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时间,但不可否认需要对这一特殊的时期进行一定的“处理”,也即是范热内普所说的“人生每一变化都是神圣与世俗间之作用与反作用——其作用与反作用需要被统一和监护,以便整个社会不受挫折或伤害。”[1]3少年钟情、少女怀春的原始本能需要在成型的社会文化中得以合理地释放。从社会角度来看,成人意味着开始承担族群一员应有的义务,儒家冠笄之礼通过仪式让个体认识“礼”,但在儒家文化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男性被视为只有成家(进入婚姻)后才算真正地成人,可以承担社会责任。
(2)群体身份的过渡
成人礼仪也意味着从儿童群体过渡到成人群体和社会群体。成人礼的重要性正在于标志着某人正式被社会和族群认可,并因此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
汉人的冠笄礼作为将儿童过渡至成人阶段的礼仪,特别是男性的冠礼,其中包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精神。“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冠礼’的设计,考虑的并不是个体身体发育是否成熟的问题,也不是个体生存技能(的手段、工具——引者补注)是否独立的问题,而是基于一种先天的逻辑——即合乎天理、物理与情理——以培养娴于‘待人接物’之身体技能的文化体系。它强调‘以身作则’,强调个体言行要合乎先验的人伦规范。人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成人’,要‘听其言、观其行’;个体则要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衣着、名号等来展演自己的成人身份。”[4]冠礼之后的成年男性其实从生理上来说并没有完全成熟,也并不会马上承担起作为一家、一族、一国成员的责任。但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他必须将“礼”作为最重要的人生准则,舍弃儿童时期单纯的生理需求和行为模式,社会和群体会以成人的标准来看待他。经过一定时间的浸淫,这一个体将会达到“成人”的标准。
贵州黔东南地区的岜沙苗族,男孩至15岁(虚岁)时举行“镰刀剃发”的成年礼,意味着该男子从儿童变为成年人,获得持枪这一重要的社会成员权利,同样被视为族群中的正式一员,实现了群体身份的过渡。
二、蒙正苗族的成年礼仪
蒙正苗族聚居于黔中地区的安顺市西秀区、镇宁县、紫云县交界一带,包含江龙镇、革利乡、本寨乡、宁谷镇、猫云镇等区域,人口三万多人。蒙正苗族信仰祖先神“竹王”,其民族信仰、穿着打扮、生活习俗上颇有特点。但如果不考虑仪式名称、时间等细节的话,其婚丧嫁娶等重大人生习俗上与其他苗族亦有共性。
1.成年礼之发型的改变
蒙正苗族的成人礼也采用了改变发型发饰的方法,虽然不像中原汉族或是其他少数民族有操办宴席或是举行特定的祭祀仪式等较为隆重的仪式,但是在蒙正苗族人们的意识中,发型发饰的改变对于认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婚恋活动资格有着重要的意义。蒙正苗族12岁左右,男性要戴帽、女性开始盘发,这标志着他们从儿童到青年的转换。正如古代中原汉族的男性冠礼和女性的笄礼一样,服饰的改变也象征其身份的变化。
蒙正苗族成年女性的发型十分特别,将8寸长的“月牙型”木梳截为两节,用线绑扎在长1尺5寸、宽1寸的2块竹片两端,将头发绕于其上,使发髻斜挂于头部右侧,表示对竹王先祖的崇拜。蒙正苗族男性发型上的改变是用一丈二尺青色布做成头帕,将头发藏于其中,头帕有序交叉依次叠成三角形,最后形成一个端正的六角帽。
对发型的改变是常见的成人礼仪。范热内普也通过列举摩洛哥拉乎纳人女性在不同时期发型变化的例子,提出“发式不仅用来标志人生阶段,而且也显示所处不同女性群体的身份。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而我所希望指出的是,对头发的处理常常属于过渡礼仪的类型”[1]122。
根据《安顺苗族》一书的统计[5]53-64,以语言为标准,将安顺地区的苗族划分为川黔滇方言十六类和黔东方言二类,试举其中数分支来看:
(1)川黔滇方言之一:女性12岁开始盘发,用头发和毛线将发髻盘于头顶,并插入一个八寸长半月形红木梳;
(2)川黔滇方言之二:少女及未婚时期女性不戴头饰,留发辫盘于头顶,已婚妇女要盘发于右侧;
(3)川黔滇方言之八:该苗族支系将女性划分为三个阶段:少女时期佩戴苗语名为 “帽羌纳”的头帽,青色布料制成,帽顶有圆孔,帽尾呈圆弧形,有绣花装饰;成年未婚女性的头帕(头帽)有便装“戴幅”和盛装“勾幅”两种,前者帽顶有3-5寸椎体,后者在颈后方向有6寸左右的绣边白布带相连的耍须;而已婚女性的头帕则成为“郜幅”,由两块青色或藏青色“风筝”形头帕包裹锥形竹编框架而成;
(4)川黔滇方言之十五:未成年男孩不戴套头,成年男性包青色丝帕套头;女孩留长发至十三、四岁后剪下来,将部分头发搓成细头索后全部与真发一起绾成发髻。
可见,苗族普遍通过发型的改变来区分成年与未成年以及婚否状况。作为过渡礼仪的一种表现形式,发型对于苗族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心理和现实意义。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必须要到18岁,传统的成人礼在法律或生活层面上不具备现实意义,但苗族人民依旧遵循着传统的成年礼仪,通过改变发型或是服饰等来确立一个人的身份和在族群中的地位及行为标准。
2.男性成年礼:改名及立竹王
蒙正苗族男性同样在12岁左右便要改变发型,佩戴六角帽,这是一种较为明显但并不隆重的成年礼仪,传统上经过这一礼仪后的男性便可与参加“晒月亮”“跳花”等恋爱社交活动,可以自由选择心仪的对象,经过交往后可以通过媒人向女方家族提亲等。但是考察蒙正男性人生的重大礼仪我们可以发现,男性的成人礼尚未结束,在结婚后还需要举行两项重要的人生礼仪,即在婚礼第二天举行的“改名”和婚后视财力等具体情况举行的“立竹王”仪式,这两项仪式同样具有成人礼的特征。
改名:婚后第二天,家族中要给新郎取个成人名,舍弃自幼使用的乳名,名字由家族中事先商定(不能与祖辈重复),只让姑爹知道。在堂屋中摆一桌酒席,中间桌上用一棵竹签穿上猪尾巴,由主持人用手一拨,猪尾巴转对谁,谁就要给新郎猜个名,猜不着就罚喝一碗酒。待猪尾巴转对姑爹时,姑爹就给新郎猜个名,此时姑爹给新郎猜的这个名得到家族中的认可,就先敬姑爹三碗酒,请姑爹到大门外当众宣布。姑爹身披着蓑衣站在大门外当众宣布,大家从今以后只能用新名字称呼新郎。
“立竹王”:是一系列复杂而隆重的仪式,在这一阶段包括“安竹王位”、“束竹王偶像”两大程序,要祭祀母猪,邀请祭司来家中操办仪式、用刺竹来制作“竹王像”、掩口舌、举行庆祝活动等等,才能得到祖先认可,在世时能得到护佑,死后亡人身上需佩有“竹王像”上的竹片作为凭证,灵魂才能回归先祖之处。
在蒙正苗族的观念中,完成了改名、立竹王仪式的蒙正男性才算是得到了先祖的认可,可以独立成人,成为一家之主。
三、蒙正苗族成年礼仪边缘性的体现
范热内普在研究成人礼仪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分“生理成熟期”和“社会成熟期”的主张。成人礼仪并不意味着生理成熟,更多是一种社会性成熟,象征社会集体对个体的认定和期待;而结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理性成熟,能够为族群完成繁衍后代的重大责任,能够作为家庭主要成员贡献力量、承担族群基本单位的职责,象征着个体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换。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阈限,成人礼仪完成了从童年到成年的转变,而结婚礼仪是对成人礼仪的最后确立(其中还存在着订婚这一边缘礼仪)。
也即是说,个体在履行完成年礼后,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他既不是稚嫩的儿童,但也并没有成为完整的、被社会所认可的“成年人”,只有当他在“成人礼——婚礼”这个时期完成了一系列的仪式后(学习参与一定的社会事务、恋爱、成婚),他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个体,可以脱离其原本的家庭(观念上,不一定是分家等具体结构的改变)成为一家之主。范内热普理论中的“边缘”是一个中性词汇,更准确的是指一个持续性的过渡时期。这一边缘性主要表现在成人礼仪是对婚恋活动的衔接,以及在正式成人前处于一个过渡性的边缘状态。
1.男性成年礼仪的“边缘性”
一般来说,成年礼仪是在婚前举行,然而蒙正男性的两个重要礼仪都是在婚后完成,这恰好体现了其成年礼仪的过渡性。与其他的成人礼仪相比较,蒙正苗族的男性成年礼仪更具有特点,除了标志着儿童至成人的过渡,另外一整套礼仪本身所表现出的时间跨度、仪式特点、心理变化等,都体现了范热内普理论中的“边缘性”。
蒙正苗族男性成人仪式的第一阶段是12岁时的戴帽,这标志着男性开始进入成人世界,获得了婚恋和一定社会事务的权利;第二阶段是男性成婚后的“改名”仪式,其中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在于该男子孩童时期的乳名至此时才完全被舍弃,而并非是在十二岁时就改变名字,这意味着男子过渡至此阶段才获得了另一个成人身份的标志——成人的名字。
而对于蒙正苗族来说,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竹王”祖先的认可,成婚后男性均可通过“立竹王”的仪式来获得这一成人标志。在蒙正苗族的传说中,先祖“多同”诞生于顺水漂流而下的竹筒中,后繁衍出此支系,至今蒙正苗族家中均供奉用刺竹制作而成的“竹王像”。 一般来说蒙正苗族男性均要供奉竹王,但因仪式复杂,财力负担有限的家庭可能存在“父供子不供”、“一家兄弟中长子供”、“一辈兄弟中长兄供”等情况,女性不作为一家之主,所以不供竹王。举行立竹王的仪式,标志着该男子独立成为一家之主。
原镇宁县政协主席杨文金先生本人便是蒙正苗族,长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发掘与保护,是研究蒙正苗族的专家。2017年9月笔者及项目组成员共同探访了他,并实地考察了蒙正苗族的村寨,根据杨文金先生提供的资料也可以看出,“立竹王”仪式作为成人礼仪的特征及其对于蒙正苗族男性的重要性。杨文金先生提到,蒙正苗族男性如果一生中没有“供竹王”,死后没有带着“竹片”到祖宗那里去报到,哪怕是80岁的老人,也得不到祖宗的承认,只能当小孩看待。从仪式举行的时间上也可以看出,一般在婚后就举行的仪式,假设由于各种原因婚后没有及时举行,年老后其个人和家族也要举行供竹王仪式。
从上述礼仪对于蒙正苗族的意义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成人礼仪体现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蒙正苗族男性的成人礼呈现出了一个时间性、心理性的阈限,从戴帽、“改名”到“立竹王”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男性经过一环环的礼仪最终达到被聚合入成人这一群体。
此外,从戴帽到立竹王为止的蒙正男性处于范热内普认为的“边缘”状态。蒙正男性通过改变发型这一分离礼仪从儿童群体中脱离出来,经过一定时期(恋爱、订婚、结婚),最后通过婚礼、改名、立竹王等礼仪聚合入成年群体。处于边缘时期的蒙正苗族男性,身体上逐渐成人化、性成熟化,能够承担劳作和生育的职责,心理上正好进入青春期,有恋爱和独立的需求;社会给予这一群体一定的特殊照顾,给予他们恋爱的自由、参与并学习社会事务的权利,精神上也逐渐成熟,可以成家立业。最终的成人确立于结婚这一重要阶段。
2.婚恋活动的“边缘性”
在生产力较落后的时代,对于苗族这样历史上长期流散、久居于贫瘠环境中的少数民族来说,族人的成年和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这意味着一批新劳动力的形成,同时族群的繁衍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人口是族群生存的基础,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孩童的成年率并不高,每一个孩子能够顺利成长到一定年纪,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而男女之间的恋爱与婚姻又意味着劳动资源的再整合,并为将来提供了再生产的核心动力。因此在苗族的观念和习俗中,成年与婚姻是前后相接的阶段,“成年”意味着可以开始恋爱活动,可以选择婚姻对象并组成家庭,婚姻中的一些礼仪也代表着对个体成年的社会认可。“婚姻才是现代苗族人心理意义上的成年礼仪,它标志着人的成熟和社会角色的完全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6]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成人礼仪给婚恋活动提供了一种 “正当性”,使得自由的恋爱交往、乃至私奔具有了伦理基础,也为族群的生存延续提供了保障。苗族自古以来崇尚自由恋爱,男女青年在成人礼后便可以参加“跳花”“晒月亮”等社交活动,遇见心仪的对象可通过交换定情信物的方式确立恋爱关系,稳定后男方便可向女方正式提亲。
《安顺苗族》一书概述中提到苗族恋爱风俗:“山野间恋爱之男女,有男拉女者,有女拉男者,挽劝者,怂恿者笑语喧,其乐融融,家属不加干涉。此苗人之极乐天、自由地,盖以俗使然,方之西俗自由恋爱,并不稍逊。”[5]4这种相当自由的恋爱方式正是以男女的成年为界限,不论是出于族群繁衍的集体意识,还是满足男女青年正当的生理心理需求,成人礼仪都为男女青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保证。以“晒月亮”为例,顾名思义在夜晚举行,年轻人自行邀约到固定的场所,交谈、对歌、相互认识,这里并没有父母长辈的严格监管,也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无法正常交往的男女青年甚至可以利用“晒月亮”的机会私定终身。
此外,男女私定终身之事虽非常规,但也在情理之内。蒙正苗族有“引婚”的习俗,如女方已有父母媒妁之婚约却又想另嫁他人,或是一对男女恋爱后男方拿不出彩礼钱的情况下,男女双方假装“晒月亮”,待到夜深人静,女方悄悄地回家,把自己早就收拾准备好的衣裙、首饰等随身行李递与男方,并跟随男方一起到男方家去。女方进门时,早有准备的男方家请一老年人提着一只公鸡在女方头上绕三转进行“扫鸡”,之后女方就正式成为男方家的人了,得到了当地苗族群众的承认。成年礼仪之后,个体对自身婚姻、生活的取舍所拥有的自主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所以悔婚、逃婚、私定婚事等非常规行为在苗族人民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接纳,同时也表现出苗族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由的勇气。
结 语
蒙正苗族的成年礼是对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理论的印证。蒙正苗族通过发型的改变,将个体从孩童过渡至成人阶段,使之获得人生下一阶段所应具备的身份、权利等,并且在这一阶段赋予了男女青年婚恋活动的自由。而蒙正苗族男性的成人礼仪从戴帽开始持续至婚后“立竹王”仪式的完成,展现出了一个明显的时间上、心理上的过渡阶段,体现了过渡礼仪亚分类中“边缘礼仪”的特点。通过对蒙正苗族成年礼仪的研究,可以从理论上加深对该民族的认识,同时使“过渡礼仪”这一经典理论得到实践的验证。
[1](法)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M].(东汉)郑玄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刘军君.成年礼与婚姻规制建构——青海贵德藏族“戴天头”的田野考察[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5):27-31.
[4]吕微.“过渡礼仪”理论概念与实践模型的描述与建构——对话张举文:民俗学经典理论概念的实践运用[J].民间文化论坛,2016(1):15.
[5]安顺市苗学会.安顺苗族[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
[6]张凌波.苗族人生礼仪的生命美学意蕴[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