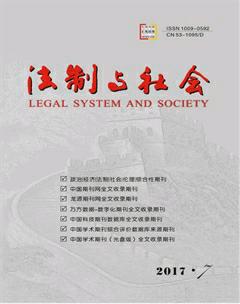论约定任意解除权与诚实信用原则
摘 要 中国《合同法》总则中规定了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条件两种约定解除合同的模式,并在分则部分针对特定的有名合同规定了任意解除权。在实践中,双方當事人是否有权通过意思自治而约定任意解除权,允许一方或双方无需提出理由即可摆脱先前订立的有约束的承诺,目前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约定任意解除权使得具有强势经济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可利用合同自由而任藐视合同有约必守的基本原则,其本身也不符合诚实信用的要求。但约定任意解除权从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实现效率价值,使当事人可以以一种便利的方式从难以继续执行的合同中解脱出来,具有积极的意义,此时,滥用任意解除权与约定任意解除权本身应当予以区分。判断是否构成权利的滥用,应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
关键词 约定任意解除权 合同解除 诚实信用原则 无理由终止
作者简介:李晶,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研究方向:国际商法。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008
约定任意解除权是现代国际商事合同中常见合同条款,旨在通过双方意思自治而赋予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因便利而终止合同的权利,提出终止时无需提出理由,但应提前给予对方通知,并赔偿对方因终止而造成的损失。在英美法下,这项权利在合同中通常使用“因便利而终止”(Termination for Convenience)作为条款标题。为便于与中国法进行对比分析,本文中该权利在英美法下将被称之为“便利终止权”。从表面来看,这种权利似乎有悖于契约神圣规则和有约必守的要求,使当事人将其有约束力的承诺成为了可以任意解除的陈述,不应当得以鼓励和支持。然该权利的日渐流行,又有其合理之处。本文将从英美法下便利终止权的法理渊源着手分析,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对该权利在中国法下的适用性进行论证,以期对于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和平衡立法目标提供帮助。
一、约定任意解除权的英美法探源
英美法下便利终止权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与私有主体签订了大量的军备采购合同。考虑到战争一旦结束,这些军备采购合同便没有必要继续执行 ,这种得以“便利”而终止的兜底性终止权利由此而生,给予了联邦政府一方无理由终止合同的权利。在当时,这种便利终止的权利仅允许作为公有主体的一方行使,但基于合同的公平正义,行使终止权的公有主体会对私有一方的损失进行赔偿。
随着国际商事交易的日渐成熟,许多私有主体也认识到了约定便利终止权的好处,尤其是建设工程施工这种承揽关系下或为建设工程施工而采购的买卖关系下,总能见到这种权利存在的身影。例如在某大型国际设备制造公司的采购合同范本中,就约定了买方有权因便利而无理由终止合同,但买方应支付高额的终止费。这种“便利”往往指向合同履约中那些未能遇见却又不构成不可抗力的事件,例如,建设工程的业主未能获得项目融资而暂停或终止项目。
最初私有主体间签订合同的便利终止权并没有广泛得到认可,因为如果允许一方自由逃避合同义务,等同于其做出了一项无约束力的承诺,这种无约束力的承诺丧失了对价基础,不应得到支持。 但在Questar Builders, Inc. v CB Flooring, LLC案 中,美国马里兰州上诉法院针对私有主体之间签订的因便利而终止合同权利的有效性,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裁决:该合同权利是否能够得以有效执行,取决于一项默示义务的履行,即该方的终止行为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交易原则。
相比之下,英国法则给予了双方当事人极大的意思自治空间,认为无论双方合同终止的约定是否合理,只要不违反衡平法对于剥夺合同利益的救济规则 ,均允许一方当事人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终止合同(而无论对方是否构成了根本违约),或因某一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为由终止合同,甚至可以仅根据一方的意愿而赋予该方自由终止合同的权利。 英国法下的合同终止甚至都无需考虑诚实信用原则 。因此,在英国法下无理由终止合同权利的适用是非常广泛的,无论是在软件使用许可合同 中,租船合同 中,或是建设工程合同 中,均能够看到因便利而终止合同或无理由终止合同的条款约定。
二、诚实信用原则对“因便利而终止合同”条款效力的影响
(一)美国Questar v CB Flooring 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Questar v CB Flooring是美国马里兰州法院管辖的案件。在该案件中,承包商与报价最低的分包商签订了分包合同,约定承包商享有便利终止权。然而,在施工过程中,双方针对工作范围产生了争议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是承包商行使了该便利终止权,向分包商发出了终止通知。之后,承包商与另一家分包商签订了分包合同。分包商认为,因承包商在终止合同前就计划更换分包商,这种不诚信的行为是承包商想要终止的根本原因,因此,承包商无权基于一种不诚信的基础而行使便利终止权。
针对便利终止权条款的有效性,上诉法院认为关键在于是否该条款将一个履约承诺转变成了一个虚假的陈述。法院认为,便利终止权条款的作用在于合理分配经济风险,其本身是真实有效的条款,但承包商并不能基于绝对任意的突发奇想而行使该权利。因此,本案中,只有在承包商认为继续履行分包合同将遭受经济损失或其他风险时,承包商才有权终止合同。最终,该案件确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对便利解除权条款效力的重要作用:该合同权利是否能够得以有效执行,取决于一项默示义务的履行,即该方的终止行为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交易原则。
此外,美国民事上诉委员会审理的Sigal Construction v GSA案 ,也对诚实信用原则做出了要求。在这个案件中,承包商之所以因便利而单方任意终止合同,是因为其想要聘用另外一家更低报价的分包商。上诉委员会认为承包商的终止行为是不恰当的,这种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违约。endprint
(二) TSG v South Anglia 案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与Questar v CB Flooring判决相反,英国TSG v South Anglia案则认为便利终止权的约定是双方意思自治的范畴,不承认诚实信用原则与行使终止权之间的关联。
该案中TSG是一家建筑公司,为South Anglia提供房屋建造和维护服务。合同第1.1条规定双方签订合同应基于“信任、公平与相互合作”,第13.3条规定任何一方均有权在提前3个月通知前提下,无理由终止合同。2010年7月20日,TSG向South Anglia发信函,提出(1)TSG之前的分包商所完成的维护工程存在瑕疵,(2)South Anglia聘用的其他分包商行为干扰了TSG正常的施工行为,(3)South Anglia未能及时付款等,影响了TSG的合同履行。2010年8月23日,South Anglia依据第13.3条向TSG发出了终止合同的信函。South Anglia没有对其终止的原因进行解释,但从内部沟通的邮件中,可以推定这一决定是基于目前双方的争议、沟通以及后续的风险而做出的。但TSG认为根本原因是South Anglia所面临的财务困境。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是否诚实信用原则对于便利解除权条款的效力产生影响?最终法院判决认为,由于第1.1条规定双方的合作关系为“信任、公平与相互合作”,并没有对诚实信用做出要求,那么,双方便没有对对方做出这样的限制。此外,即使该合同中存在诚实信用这一要求,也不能对双方明示约定的便利解除权做出限制,因为该条款允许任何一方无论是否提出理由,提出了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理由,均可以在合同期限内任意终止合同。这是双方在订约时自愿承担的风险。
(三)各国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深受罗马法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多将诚实信用原则奉为“帝王规则”。例如,德国学者Hedemann指出,“诚实信用原则之作用力,世罕其匹,为一般条项之首位”。 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任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 欧盟法中广泛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来认定是否某条款属于不公平 ,或某一商业行为是否构成不公平。
英美法系国家针对诚实信用原则存在不同的处理规则。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205条中,规定当事人在履行任何合同时都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澳大利亚法律也广泛认可诚实信用原则,尤其是针对合同终止事宜,在Burger King Corporation v Hungry Jacks Pty Ltd 中,法院認为Burger King只有在遵守合理性及诚实信用原则时,才可以针对Hungry Jack的一项轻微违约而终止合同;另外,合同范本中也应当包含合理性和诚实信用的默示义务,特别是在这些范本中泛泛的规定了合同终止权时。 尽管早期加拿大的判例对于是否采用诚实信用原则比较保守,但在其权威性的Bhasin v Hrynew案 中,最高法院裁决认定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组织性原则,为其他更为具体的原则提供支持,并且在不同情况下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
然而作为英美法系最为典型的英国法,是否承认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项合同基本原则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尽管在1766年Cater v Boehm案 中,法官认为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一方在交易磋商过程中,隐藏某些只有其一方知晓的事实,以使对方产生误解,并要求双方仅可以针对双方均知晓的事实保持沉默。但现代多数英国学者认为,除了合同自由和有约必守原则,英国法并没有普遍适用的诚实信用原则。正如Bingham法官在Interfoto v Stilletto案 中提到,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或普通法系之外的绝大多数法系国家,通常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项帝王原则。但该原则并不是简单的要求一方不欺骗另一方,其本质上的作用在于保护交易的公平性,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更是一项公平交易原则。虽然英国法并没有诚实信用原则,但其涉及不公平交易的大量规则足以实现同样的目的。
由于英国法没有诚实信用原则,其在处理约定任意解除权问题上,采纳了绝对的契约神圣主义,而其他将诚实信用原则奉为“帝王规则”的法律体系,则将约定任意解除权设定了行使的界限,仅能够秉持诚实信用来行使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
三、《合同法》约定任意解除权之我见
中国《合同法》总则部分并没有对任意解除权做出明确规定,仅在分则中对特定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赋予了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任意解除权,实质上是一种法定解除权,只有法律明确赋予了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才能够随意的终止合同而无需提出理由。换言之,任意解除权不能基于意思自治而产生,约定任意解除权的条款无效。 然而约定任意解除权在实践中又是广泛存在的,反映出交易双方当事人对这一权利的价值需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希望能够通过一种便利的方式从难以继续执行的合同中解脱出来,而被解除的一方也允许通过补偿其损失的方式使双方重获自由。
(一)约定任意解除权的性质分析
中国合同法体系下的解除制度,要求以法定的或以约定的条件为前提,后者包括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和约定解除的条件。那么,任意解除权不作为与法定解除与约定解除之外的独立的解除形式,要么服从于法定解除,要么归属于约定解除。
我国合同法及其他特别法律中,明确规定了数种任意解除权,例如承揽合同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第251条);不定期租赁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第232条);委托合同中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第410条)等。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法律明确规定的任意解除权,应当视为特殊的法定解除权。
那么,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解除权,是否可以通过双方约定而使之成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要求?由于法律并没有明文做出禁止,那么这首先产生了合同自由与契约神圣之间的博弈。
《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如果允许一方或双方可以不基于任何理由而随时摆脱其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将使双方的承诺和合意成为儿戏,这有悖于契约神圣的基本精神。但是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合同自由不仅包括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也包括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自由,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当事人有权控制合同成立后的整个生命发展历程”。 由于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约定任意解除权,笔者认为,这种约定应属于特殊的约定解除权范畴,通过合同订约自由,将“一方发出解除通知”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endprint
(二)约定任意解除权的合法性评价
对约定任意解除权的合法性进行评价时,首先应从法所追求的价值符合性角度进行判断。“法的价值是法对于满足个体、群体、社会或国家需要的积极意义”, 那么,约定任意解除权是否合法,则取决于它所带来的是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是否符合法所追求的价值。
约定任意解除权最根本目的在于追求效率价值,即在合同出现某种导致继续履约陷入困境的情由时,使当事人可以无需提出理由而从这种困境中得以解脱,提高解约的效率。约定任意解除权应与滥用任意解除权往往会产生混淆,前者并未突破法律所做出的任何强制性规定,旨在通过合同自由而对双方的商务风险进行分配,这种经济上的风险分配并没有违背合同的任何一项基本规则;而后者,则是违背了合同诚实信用及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是表面平等但实际并不平等的主体中的强势一方利用其经济地位而迫使对方不得不接受一种不公平的对待。区分是否构成了约定任意解除权的滥用,最关键的则是判断解除权人对另一方的经济补偿是否合理。这就如同法律允许设定格式条款,但是不正当的利用格式条款而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归于无效。
因此,约定任意解除权有助于双方当事人对其交易的商务风险进行分配,在非解约方的损失得以合理补偿时,实现解约的效率,这是良好的积极的价值,应当得以肯定。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任意解除权的效力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由于约定任意解除权无需通过提出理由即可解约,易造成解除权人对该约定权利的滥用,进而带来消极的后果,那么,法律也应当对于任意解除权的滥用做出限制,以为实现法的价值而保驾护航。
(三)行使约定任意解除权的限制——诚实信用原则
为了避免垄断行业或强势订约方利用其因经济实力或地位的优势而滥用合同自由,这要求约定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并非是完全任意的。尽管法律并没有对约定任意解除权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帝王规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可通过填补法律上的空白而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平衡,对滥用任意解除权的行为加以限制。
首先,虽然享有解除权的一方或双方,可以无需提出理由而随时解除,但“无需提出理由”并不是不存在解约的理由,这个真实存在的理由必须是善意、诚信的。解除合同是一项救济手段,其目的在于將双方当事人从继续履行的僵局中解脱出来,而不是赋予一方藐视合同神圣效力的权利。因此,法院可以对当事人的解约动机进行推定,恶意任意解除合同的行为应当属于明示毁约。
其次,行使任意解除权的一方,因不存在致使合同目的落空的情由而得以免责,也不存在对方的违约行为使其受损,为实现合同的公平公正,其应当赔偿另一方因其解除行为而产生的损失并补偿受损一方的可得利益。也就是说,享有任意解除权的一方,只有在试图去弥补对方的经济损失时,才能说其行为是善意和诚实信用的。
再次,为了减轻非解约方潜在的商业损失,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效果不能是即时的,该方必须提前向非解约方发出解约通知,预留充分的时间使非解约方得以对后续的商业利益进行重新安排,减小因任意解约而带来的潜在风险。任何立即解除合同的行为,都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解除权人不诚实、不善意的动机。
总之,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必须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前提,判断标准应从是否存在善意的解约理由?是否试图对非解除权人的损失进行补偿?及是否提前向对方发出了解约通知?三个方面去考察当事人行为的善意程度。
四、结语
尽管在民法草案建议稿中,我国学者建议增加有名合同类别并对约定任意解除权做出规定, 但考虑到多变发展的社会生活,使得稳定保守的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因此,有名合同永远都不可能穷尽各种合同的类型。也就是说,通过对有名合同设定特殊的法定的任意解除权,不仅不能够改善法的滞后性,反而因为大量的有名合同中各有不同的任意解除权行使要求,增加了理解法律、适用法律的复杂性。
通过对本文中约定任意解除权的性质分析和价值考量,笔者认为,虽然在有名合同中明确设定特殊的、法定的任意解除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明确法律的适用,但在法律中或司法解释中认可约定任意解除权合法性,并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该权利行使限制的通用要求更有助于缓解法律的滞后性,有助于保障双方的合同自由而对自主交易的风险进行分配,实现效率价值。
注释:
Loulakis, Michael and Mclaughlin,Lauren, “When is a Termination for Convenience Improper?” Civil Engineering, Oct 2011, Vol.81(10).96.
Katz, Gerald, “Courts Uphold Good Faith Use of “Termination for Convenience”, Pavement, Feb 2010, Vol.25(2).48.
英文术语为Relief against forfeiture,例如买方在收货前分期付款支付了90%,卖方若因未支付10%余款而提出终止合同,则会导致卖方在未转让货物所有权前得到了90%的合同款,剥夺了买方的合同利益,此时基于衡平法,可对买方给予救济。
Joseph Chitty, Chitty on Contracts, (31st ed.,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15).22-048.段1-039。
TSG Building Services Plc v South Anglia Housing Ltd, [2013] EWHC 1151 (TCC).
Northrop Grumman Mission Systems Europe Ltd v BAE Systems, [2014] EWHC 2955 (TCC).endprint
BP Exploration Operating Co Ltd v Dolphin Drilling Ltd, [2009] EWHC 3119 (Comm).
Hadley Design Associates Ltd v Westminster City Council, [2003] EWHC 1617(TCC).
Questar Builders, Inc. v CB Flooring, LLC, 978 A.2d 651.
“such clauses in private contracts “may be enforceable, subject to an implied obligation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terminate in good faith and in accordance with fair dealing.”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61.
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1994(2).25.
Directive 2011/7/EU on combating late payment in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2011] O.J. 48/1,第7(1)条;Consumer Rights Act 2015 第62(4)条。
Directive 2005/29/EC,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2005] O.J. L149/16,第5(2)条和第2(h)条。
[2001] NSWCA 187.
Anthony Gray, “Termination for Convenience Clause and Good Fai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and Technology, July 2012, vol.7(3).
[2014] 3 S.C.R. 494.
(1766) 3 Burr. 1905, 1910.
Interfoto Picture Library Ltd v Stilletto Visual Programmes Ltd [1989] 1 Q.B. 433, 439.
李晓玉.合同解除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3月.98,95.
崔建远.合同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0.19.
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