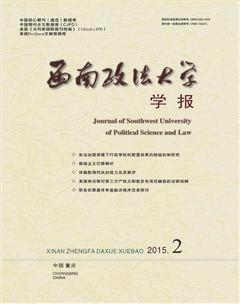诈骗取得判决的效力及其救济
摘要:关于诈骗取得判决有无既判力的问题,德国、日本的学术界和实务界向来有肯定说与否定说的争执。其争论的焦点是确定判决的既判力能否不经再审程序而直接破除的问题。在民事诉讼中,程序安定等程序基本要求固然重要,但也并非恒定优先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在此意义之下,一味强调程序安定的优先性而绝对地承认诈骗取得判决的既判力,或者反之,均非所宜。因此,原则上应当依据程序安定的基本要求承认诈骗取得判决的既判力,受害方当事人为了救济自身的权利,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以破除其既判力;在例外情形下,允许依据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否定诈骗取得判决的既判力,受害方当事人可以直接起诉要求损害赔偿以获得救济。
关键词:诈骗取得判决;再审;既判力;诚实信用原则
中图分类号:DF7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5.02.09
根据民事诉讼既判力理论,一旦法院作出了生效的确定判决,那么原则上该判决内容对法院及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亦即,同一事项再度成为当事人之间所争执的问题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提出与该判断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也不得作出相矛盾的判断。此时,不论当事人或法院均应将该判断作为纠纷解决的基准,以尊重该纠纷之终局解决。赋予确定判决以既判力,是制度上为强制确保该终局判断受到尊重的手段。纠纷的终局解决是民事诉讼所欲达到的终极目的,既判力便是赋予此等确定的终局判决以定纷止息的效力。
但是,如果该确定判决是因为不正当的行为或状态而错误形成的,那么立法者规定有民事诉讼的再审程序以否定错误判决。当事人以诈骗方法恶意对于法院或对方当事人施以诈术获得确定胜诉判决后,对方当事人可否申请再审?抑或应当主张该确定判决当然无效,不经再审程序之诉撤销该确定判决,直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获得救济呢?此种法律问题,涉及确定判决的既判力能否不经再审程序而直接破除的问题。换言之,这属于对于确定判决的具体妥当性与法律安定性两者的冲突如何进行调和的理论问题。本文主要介绍德日两国的相关判例与学说,为我国实务界及学界讨论此问题提供素材,以抛砖引玉。
一、瑕疵判决与诈取判决(一)瑕疵判决的种类与效力
在任何情况下,判决都有可能会发生瑕疵。此种瑕疵判决的种类和效力与诈骗取得判决的情形有关,可以先行观察分析。
1.非判决(Nichturteil)
非判决又称为表面判决(Scheinurteil),此种看似判决的判决,仅仅是在表述上称之为判决而已。表面判决实际上根本欠缺成立判决的基本要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判决。例如,不具备法官身份的人所作出的判决、未经宣告的判决草稿,均属于非判决。欲成立判决,必须是由法官作出,而且由法官将判决内容向外宣告才可以。由于非判决不符合成立判决的基本要件,所以根本不产生判决的效力。其救济方法是,当事人可以请求受诉法院重新指派有法官资格的人重新开始审判,或由原法官将其已制作完成的判决草稿按法定程序公开对外宣告[1]。
2.无效判决(Wirkungsloses Urteil)
无效判决是由法官作出的,其在法律上确实有判决存在的形式。但是因有重大瑕疵,不发生判决的效力。例如,对于无审判权的外国外交官所作出的法院判决、对于根本不存在而被虚构的当事人所作出的判决、对于已合法离婚而不存在的婚姻所作出的离婚判决。无效判决不产生实质上的既判力、执行力、形成力[2]。但无效判决对法院有自我拘束力,法院对其自己所作出的无效判决不得于宣判后自行撤销。无效判决确定时有形式上的既判力,所以当事人对于法院所作出的无效判决不宜置之不理,应当依规定通过上诉或再审撤销无效判决。
3.不属非判决亦不属无效判决的瑕疵判决
该判决虽然有程序上瑕疵或有实体上的瑕疵存在,但就判决的效力而言,此种有瑕疵的判决有实质上既判力及形式上既判力。但是,因为该判决有瑕疵存在,所以可以通过上诉或再审的渠道,消除判决的瑕疵。属于此类判决者,例如,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法官所作出的判决、法院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作出的判决、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出的判决等。诉讼实务上,最为常见的有瑕疵的判决就属此类瑕疵判决,至于无效判决与非判决并不常见。此类瑕疵判决的救济方法是通过上诉或再审程序,诉请法院废弃不利于己的判决而改为对己有利的判决[3]。
在学理上区分无效判决与上述瑕疵判决,其实益在于,一旦错过启动上诉或再审程序的不变期间,无法通过上诉或再审程序撤销判决时,无效判决因不产生实质上的既判力、执行力、形成力,当事人不会在实体法律关系方面发生不利益的问题[1]68。然而,不属无效判决的瑕疵判决虽然也存在瑕疵,但是其有实质上的既判力、执行力、形成力,对当事人在实体法律关系上会发生不利益的结果。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包冰锋:诈骗取得判决的效力及其救济当事人通过诈骗法院所取得的判决,应当归属于何种瑕疵判决?学者有将其归为无效判决的,也有将其归为不属无效判决的瑕疵判决的,也有将其独立自成一种的,其目的主要在于说明诈骗取得确定判决的效力及其救济途径的问题[1]69。
(二)诈取判决的含义与分类
1. 诈取判决的含义
关于诈骗取得确定判决的含义究何所指,学者们的见解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其是指一方当事人以恶意欺骗对方当事人、法院,而不当取得判决的情形[4]。有学者认为,其是指一方当事人以恶意或违反公序良俗的方法,欺骗对方当事人、法院,而不当取得判决的情形[5]。有学者认为,其是指一方当事人以恶意或违反公序良俗的方法,妨碍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资料,或加工、伪造判决的基础资料,欺骗法院而取得确定判决的情形或者是双方当事人通谋而不当取得确定判决的情形[6]。也有学者认为其是指当事人以加害对方当事人的意图,妨碍对方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或提出诉讼资料,或加工、伪造判决的基础资料,以欺骗法院而取得违反客观真实、内容不当的判决[7]。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故意欺骗对方当事人或法院而取得确定判决[8]。学者们的定义基本上大同小异,但是笔者认为绀谷浩司教授的定义较为合理,因为其定义包括了双方当事人通谋而不当取得确定判决的情形。
2. 诈取判决的类型
学者就诈骗取得确定判决的类型,见解也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应当将其区别为:伪称被告住所不明而进行公告送达、当事人利用伪造证据或作伪证而获得胜诉判决两种类型[4]522。也有学者将其区别为如下两种类型:第一,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机会为对方当事人所剥夺,导致法院作出对其不利益且内容不当的判决;第二,一方当事人虽然没有剥夺对方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机会,但是因为无法排除其作伪证等不诚实的诉讼活动,导致法院作出对于对方当事人不利益且内容不当的判决[9]。也有学者将其区别为:第一,当事人伪造证据或唆使证人作伪证,或胁迫对方当事人而取得胜诉判决;第二,伪称对方当事人住所不明而申请公告送达,或以与当事人熟稔者的住所为被告的住所而对被告送达,以在对方当事人全然不知情的状况下获得胜诉判决;第三,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外达成撤回诉讼的合意,但是并未依照约定撤回诉讼而获得胜诉判决[5]309。另外,也有学者将其区别为:第一,一方当事人以不法手段自己取得确定判决的情形;第二,双方当事人共同通谋作虚伪的陈述,而取得确定判决的情形[10]。笔者认为加藤哲夫教授的分类较为合理,因为一方面其分类较为简明,涵盖内容较广,避免列举式分类的挂一漏万;另一方面,其分类也考虑了双方当事人共同通谋而诈取确定判决的情形。
二、既判力与再审程序的关系(一)既判力的学说
赋予确定判决的判断以通用性或拘束力,即所谓既判力。这是为了使裁判有实效性,也避免作成终局判断的裁判再发生动摇。就相同纠纷作出不同的判决,是无法为制度所容忍的,因此应当赋予确定判决以既判力。然而,为何法院的判断必须受此等效力的拘束?此外,与真实实体法状态不符的不当判决是否产生拘束力?关于此等问题的解答,即既判力本质论所欲探讨的内容。对此问题的学理说明,德国最初有实体法说,后有诉讼法说,其后在日本有权利实在说,二战后在日本出现程序保障说[3]619。
1. 实体法说
实体法说认为,判决能将不存在的权利变为存在,也能将存在的权利变为不存在。换言之,判决能创造权利状态而不发生错误的权利状态问题。确定判决之所以有既判力的依据,在于判决不产生错误而且法院及双方当事人不可能进行相反的争执,从而当然受判决内容的拘束,法律安定性得以确保。
2. 诉讼法说
诉讼法说认为,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基于国家统一法律见解的必要,法院及双方当事人应当受确定判决内容的拘束。既判力的依据在于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具有权威性。即使法院确定判决所认定的权利状态与既存的真正权利状态不相符,然而,基于国家公权判断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也必须维持此种误判内容的效力。因此,不论法院确定判决的内容是否正确,均有既判力。
3. 权利实在说
无论实体法说或诉讼法说,均认为诉讼程序进行之前当事人权利已然存在。然而与此相反,权利实在说认为,法律与权利均属于精神世界的文化存在,是人类精神作用所产生的抽象的存在。法律及权利的概念作为抽象的观念存在,应当经过人类的行为赋予其正当力量,才能由精神文化的存在转化为社会经验的存在。在诉讼之前,当事人依据法律所主张的权利只是假定的存在;经过法院以诉讼程序作出终局的确定判决后,主张的权利才被社会所公认并且具有通用力。权利实在化的过程,便是当事人之间解决纠纷的过程。通过判决所产生的真正实在的权利也成为规范法院及当事人的基准。
4. 程序保障说
程序保障说认为,判决之所以有既判力而拘束当事人,是因为法律已经在先前的诉讼程序中充分赋予当事人机会,在程序上保障当事人尽力主张或防御的权利。如果当事人不掌握此种法律赋予的程序保障机会,应当自负其责,不能事后推诿责任。程序保障说是将法律程序赋予权利保障的机会与当事人自我负责两者之间的关系直接相连,作为说明既判力的根据。
(二)再审程序对既判力的冲击
为维护确定判决的法律安定性,双方当事人及法院均不得于事后对判决内容作相反的主张及争执,这是既判力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但是法院判决毕竟是由人作出的,而不是由神作出的,难免因为诉讼程序发生重大瑕疵或其他异常情形的存在而导致确定判决发生错误。在此种情况下,如果绝对贯彻法律安定性的要求而不赋予重新审判的机会,那么就无法兼顾判决正确性及法律正义的要求[1]71。民事诉讼设立再审制度的目的正是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允许再审原告提起再审之诉,打破判决的既判力并恢复判决的正确内容,从而维持法律正义。
既然再审程序是非常程序,那么启动再审的事由必须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属于真正必要的情形。因此,大陆法系德国、日本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38条规定:“在有下列事由的情况下,对于确定的终局判决,可以以再审之诉提出不服声明。但是,当事人已经以控诉或上告主张该事由时,不在此限。(1)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组成作出判决的法院的;(2)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参与判决的法官参与判决的;(3)对法定代理权、诉讼代理权或代理人为诉讼行为欠缺必要授权的;(4)参与判决法官,犯有与案件有关职务上的犯罪的;(5)依据他人在刑事上应处罚的行为而自认或妨碍提出可以影响判决的攻击或防御方法的;(6)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物件,是经过伪造或变造的;(7)以证人、鉴定人、翻译或经宣誓的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的虚伪陈述作为判决的证据的;(8)作为判决基础的民事或刑事判决及其他的裁判或行政处分,根据其后的裁判或行政处分而变更的;(9)对于能影响判决的重要的事项遗漏判断的;(10)声明不服的判决,与此之前确定的判决相抵触的。在具有本条前款第4项至第7项所列的事由的情况下,限于对应处罚行为的有罪判决或罚金的裁判已经确定时,或者因证据不足以外的理由不能作出有罪的确定判决或罚款的确定裁判时,可以提起再审之诉。在控诉审已对案件作出本案判决时,不得对第一审的判决提起再审之诉。”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于再审事由的规定,均是采取列举式的方法。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成为再审事由的原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明确规定了13种再审事由,即“(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7)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8)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9)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10)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11)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12)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13)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由此可见,在兼顾法律安定性及判决正确性的要求下,通过再审程序来打破既判力所受的限制颇为严格。
三、诈骗取得判决效力的德日见解(一)德国见解
1.德国判例见解
虽然德国《民事诉讼法》对于再审事由的规定采取限制性列举方法,但是德国判例自战前的帝国法院时代迄战后的联邦最高法院,却一再进行扩张解释。其认为对于当事人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诈骗取得的确定判决,可以通过再审程序打破其既判力。依帝国法院相关判例的意旨,诈骗取得的确定判决的基础是给予不正义以正义假象的违法行为,所以其根本不发生既判力,从而不必进行再审程序,可以直接根据德国《民法》第826条德国《民法》第826条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地加损害于他人的人,负有向该他人赔偿损害的义务。”有关故意违反善良风俗的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又依帝国法院相关判例的意旨,原告明知被告住所地而利用法院的公告送达,以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诈骗取得的确定判决,虽然没有对应的再审事由,但是被告基于德国《民法》第826条的规定,可以在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前请求不予执行;如果已经经过强制执行,受害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1]73。
帝国法院认为德国《民事诉讼法》对于再审事由的规定过于狭窄,但是对法律列举的情形又不能普遍进行扩充。因此,帝国法院的判例试图使既判力发生其他突破,特别是通过当事人依据德国《民法》第826条的规定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途径来加以突破。上述帝国法院的判例,于战后被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所继受。不仅如此,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更行扩张解释,认为原告知悉其强制执行不正当而且其变价违背善良风俗时,则可以依据德国《民法》第826条的规定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打破确定判决的既判力[2]337。此外,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把打破既判力重复地建立在德国《民法》第826条的基础上,而是寻求更为“柔软”的规定——德国《民法》第242条的规定。德国《民法》第242条规定:“债务人有义务斟酌交易习惯,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给付。”该条规定是有关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条款。
2.德国学界见解
德国学者多数对于帝国法院及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判例持反对态度,认为无论如何法院不能直接认定确定判决有错误而打破判决的既判力。如果原告的申请符合再审事由时,那么应当启动较为复杂而且有不变期间限制的再审程序。如果单纯主张原确定判决有错就进而直接否定原判决的既判力,那么此举会违反判决的安定性,而且与立法者设立再审程序的目的相违背。
3.小结
上述德国法院判例与多数学者之间见解发生对立的真正原因,在于德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再审事由过于狭窄而且不完整。但是,德国法院又很难期待立法者能迅速就其《民事诉讼法》的再审事由进行修正。当然,也有学者是支持德国法院判例的。其认为德国《民法》第826条是彰显法律正义的规定,应当成为《民法》及《民事诉讼法》中正义理念的共同基础。所以,德国《民法》第826条的法律正义应当优先于既判力中法律安定的理念[1]74。从而认为,法院可以直接打破诈骗取得判决的既判力而不受其拘束,当事人可以不经再审程序直接提起德国《民法》第82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诉讼,俾以救济。
(二)日本见解
1.日本判例见解
(1)日本最高法院昭和43年(1968年)2月27日判例
A于昭和25年(1950年)9月4日出售T地给X﹙即本案原告﹚,但是没有进行移转登记。B、C得知上述情况后,于是通谋盗刻A的印鉴,并盗盖于C所受领、以D为发票人的无记名本票上,使A成为系争本票的受款人,并于背书人一栏中记载A为背书人﹙以B的住所伪为A的住所记载其上﹚。其后,C以系争本票申请对A发支付命令与假执行的宣告,为法院所准﹙其间相关的裁判正本,一概送达于B的住所,并由B伪称A而受领﹚。于1957年6月1日,C基于附假执行宣告的支付命令,申请强制执行A名下的T地。之后由Y﹙本案被告﹚于9月14日拍定,并于10月17日进行所有权的转移登记后,建屋其上﹙其间相关的裁判文书,概送达于B的住所,并由B伪称为A而受领﹚。1961年11月16日,B、C伪造私文书诈欺罪的有罪判决确定。A基于此提起再审之诉,再审判决于1963年8月10日确定,并致使作为执行名义的附假执行宣告的支付命令被撤销。X于是以Y为被告,起诉请求为:①确认Y对于T地的所有权不存在;②涂销T地的所有权移转登记;③拆屋并返还T地。
第一、二审程序X均败诉。于是X上诉至第三审程序,其上诉理由为:作为本案执行名义的支付命令,因为并未送达于债务人A,致其完全不知悉情况,因此就与A的关系而言,支付命令根本不存在。原审判决在未予债务人任何声明不服机会的前提下,将支付命令、执行程序视为有效,而使A丧失T地的所有权,这一做法明显违反民事诉讼程序的攻防平等原则,实为适用法律错误。对于X的上诉理由,最高法院判示如下:“在C、B通谋的情形下,C宣称对于第三者A享有金钱债权。为对A骗取执行名义,C于是以B的住所伪为A的住所,就主张的债权以A为债务人申请支付命令与假执行的宣告。针对上述诉讼行为,法院亦为一连串的诉讼行为。但是,B则伪为A本人受领法院所送达的附假执行宣告的支付命令等裁判文书正本,且未提出任何不服的声明。因此,在该裁判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纵使在形式上C就上述债权取得以A为债务人的执行名义,但是,该执行名义的效力应视为不及于A。就对于A的关系而言,该执行名义无效。所以,在此情形之下,C与B通谋借由一定的欺诈行为,故意使执行债务人A不知悉支付命令裁定的存在,从而剥夺了A采取防御手段的机会。因此,参照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就C对于A的关系而言,应不为裁判的效力所及。”[11]
本案的情形是在债务人全然未被赋予任何攻击防御方法机会的前提下,是否应当承认执行名义效力的问题,即所谓骗取的确定判决或不当取得的确定判决的效力问题。向来关于此等案例的议论,探讨的焦点是集中于如何妥善调和、兼顾具体案件的妥当性与程序的安定性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应否承认诈骗取得判决的既判力?如何赋予被害人以救济的权利?
(2)日本最高法院昭和44年(1969年)7月8日判例
Y(前诉原告)对X(前诉被告)提起请求返还借款的诉讼(该诉讼称之为前诉),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裁判外达成了和解。X向Y偿付了借款,但Y并未按照双方的合意而撤诉,进而获得了胜诉判决,最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是,X就不得不对同一个债务再次进行偿付,这才使得Y撤回强制执行的申请。不过,其后X以Y的这种行为构成不当取得、不当使用确定判决为由提起了损害赔偿之诉(该诉讼称之为后诉)。尽管在后诉的原审中,法院驳回了X的请求,但最高法院却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最高法院的主要判决理由论述如下:“在判决的成立过程中,诉讼当事人为了达到侵害当事人权利之目的,通过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了种种妨碍对方当事人参与诉讼以及以虚假的事实欺骗法院的不正当行为,该当事人因此而获得本来不应当获得的确定判决,并且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因为判决已经确定而不能直接追究该当事人这种不正当行为的责任。即便遭受损害的当事人存在着再审事由而可以对上述的确定判决提起再审之诉,这也不妨碍其可以通过独立的诉讼来请求因该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害赔偿。”[12]
2.日本学界见解
对于骗取确定判决的情形,受害方当事人可否以对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由,据以否定判决的既判力的问题,学术界向来有争论。
(1)否定说
持否定说的学者,是着眼于程序法安定性的要求,认为即使在不当取得判决的情形下,受害方当事人必须再行上诉或提起再审程序以谋求救济,不得径直主张判决为当然无效[13]。其理由如下:第一,为维持程序法的安定性,不宜径直以对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是权利滥用或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而否定确定判决的既判力。所以,如果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将有害于保障诉讼程序进行所不可或缺的程序安定性,则必须排除其适用。而既判力是国家为确保法的安定性所设的制度,仅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权利滥用为由,并不足以成为正当化否定确定判决既判力的合理根据。第二,《民事诉讼法》为谋求程序安定性与具体案件妥当性的调和,已经设有再审制度。如果否认不当取得的判决的既判力,必然与设置再审制度的旨意相悖。
(2)肯定说
主张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在不当取得判决的情形下,必须否定该判决的既判力[14],其理由为:第一,既判力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持程序的安定性,但是此等目的尚必须让位于更高层次的司法目的——正义的实现﹙即具体案件的妥当性﹚。第二,再审制度就申请期间与再审事由设有限制,如果认为在不当取得判决的情形下,受害方当事人非依再审程序不得消灭判决的既判力,显然是对受害方当事人强加额外的负担。因为再审程序并非当事人轻易就能启动的非常程序。再者,并非所有案件的受害方均能依再审程序消灭不当判决的既判力,此类情形无异阻绝受害方请求救济的途径。第三,如果认为既判力的正当根据是对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则在不当取得判决的情形下,由于对受害方当事人欠缺程序保障,并不具备既判力的正当化基础。因此,于此情形否定判决的既判力并不抵触既判力制度。第四,在不当取得判决的情形下,由于当事人违反了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必须否定该判决的既判力。
3.小结
日本早期的通说认为,允许以诈骗取得判决为理由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属于违反判决既判力的情形,从而反对日本实务界的判例。二战后,日本学者新堂幸司教授提出既判力正当化的依据在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这使得早期的通说发生转向,不再坚持既判力正当化的依据在于维持法院确定判决的安定性。现在日本的多数见解认为,如果在诉讼过程中法律已经赋予双方当事人以充分的攻击防御机会,那么判决确定时,败诉方当事人对败诉结果也应当自己负责而不得再就判决结果进行争执。胜诉方当事人也能信赖该判决结果,从而法律地位的安定性受到尊重。从而,日本学者在探求再审事由的合理依据时认为,如果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正当程序保障受到实质性的妨碍时,那么该当事人有权根据再审事由而否定判决的既判力。很显然,在诈骗取得确定判决的情形下,利益受损方的当事人并未受到正当程序的保障。因此,从先前结论推之,诈骗取得的判决应当不发生既判力而属于无效判决,利益受损方的当事人可以不受判决效力的拘束。
四、本文见解:折中说及其展开(一)折中说的要义
关于诈骗取得判决有无既判力的问题,相较于德日的肯定说与否定说,笔者倾向于折中说。笔者以为,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协调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个衡平性原则,缺乏统一而确定的标准,具有不同个性和偏好的法官就相同案件常作出不同的判决。因此,诚实信用原则与程序安定等基本要求通常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与程序安定等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要求,应当依据各诉讼主体的利益状态或归责程度以及各诉讼行为的类型、特性之不同而定。程序安定等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要求固然重要,但也并非恒定优先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15]。我们应当立足于平衡、兼顾发现真实与程序保障的观点,科学界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
在此意义之下,一味强调程序安定等民事诉讼程序基本要求的优先性,而绝对地承认诈骗取得的判决的既判力,或者一味强调诚实信用原则的优先性,而绝对地否认诈骗取得判决的既判力,均非所宜。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间寻求一条恰当的中间道路,应当是我们思考的方向。进而,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当依据程序安定的基本要求承认诈骗取得判决的既判力,受害方当事人为了救济自身的权利,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以破除其既判力;在例外情形下,允许依据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否定诈骗取得判决的既判力,受害方当事人可以直接起诉要求损害赔偿以获得救济。
(二)折中说的理由
第一,诈骗取得的判决不属于无效判决的类型,从而诈骗取得判决有实质上的既判力。无论该确定判决内容是否错误,原则上双方当事人及法院均不得未经再审程序而主张与判决相反的内容。这是既判力理论的应有之义。
第二,再审制度是为了谋求程序的安定性与判决内容的妥当性之间的调和而设置的,如果从宽认定判决的无效,那么将使再审制度的功能无从发挥。因此,即使在诈骗取得判决的情形下,除了因再审的提起将导致承受不利益的对方当事人负担过大的情形,可以例外允许受不利益的当事人主张判决无效外,原则上受害方当事人应当先依循再审程序消灭诈骗取得判决的既判力。换言之,关于诈骗取得判决既判力有无的问题,关系到程序的安定性与具体案件的妥当性之间的调和,意欲一般性地判定何者居于优先地位均非所宜。
(三)折中说与我国现行法的衔接
如上所述,关于诈骗取得判决的问题,其解决的途径必须是尽可能利用再审救济,仅在少数例外无法依再审救济的特殊案件﹙例如受限于再审事由、提诉期间﹚,才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破坏程序的安定性,直接起诉请求损害赔偿,以实现具体案件妥当性的要求。当事人欲启动再审程序,应当先依据再审事由申请再审。基于再审程序的严肃性,再审事由必然是《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
但是,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明确规定的13种再审事由中,并没有“诈骗取得判决”。因此,笔者建议,在将来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将“诈骗取得判决”增订为再审事由之一。但是,在修法完善再审制度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扩张解释或类推解释的方法使得“诈骗取得判决”符合法定的再审事由。比如,原审中一方当事人通过伪造证据诈取判决,那么受害方当事人可以依据“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这一事由申请再审。再比如,一方当事人谎称对方下落不明而滥用公告送达的,那么受害方当事人可以依据“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这一事由申请再审。如果诈骗取得判决的受害者是案外人,那么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下,案外人可以通过申请再审或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来救济自身的权利。JS
参考文献:
[1] 陈荣宗.第三人撤销诉讼与民事程序法[M].台北:三民书局,2005:67.
[2] 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M].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4.
[3] 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M].台北:三民书局,2005:594.
[4] 中野贞一郎,松浦馨,铃木正裕.民事诉讼法讲义——判决手续的基础理论[M].东京:有斐阁,1997:521.
[5] 森勇.确定判决的骗取与无效[C]//青山善充,伊藤真.民事诉讼法的争点.3版东京:有斐阁,1998:308.
[6] 绀谷浩司.确定判决的无效与诈取[C]//三月章,青山善充.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新版.东京:有斐阁,1988:332.
[7] 石川明.不当取得判决とその救济[C]//中野贞一郎.民事手续法革新.东京:有斐阁,1991:3.
[8] 上田彻一郎.民事诉讼法[M].东京:法学书院,2000:438.
[9] 住吉博.确定判决的骗取[C]//新堂幸司,青山善充,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判例百选(Ⅱ).东京:有斐阁,1998:339.
[10] 加藤哲夫.再审事由[C]//伊藤真,德田和幸.新民事诉讼法讲座(Ⅲ).东京:弘文堂,1998:130.
[11] 中田淳一.不当取得的债务名义的强制执行效力[J].民商法杂志,1968,(3):446-458.
[12] 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85592.
[13] 小室直人.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东京:法律文化社,1998:182.
[14] 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70.
[15] 包冰锋.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之客体范围探究[J].现代法学,2009,(6):10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