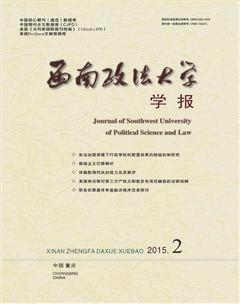论情理推断方法在刑事司法事实认定中的运用
摘要:情理推断是事实认定的基本方法,它具备案件事实认定的启发性功能、证明性功能以及证据材料可靠性的评判功能。情理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特征,推断过程遵循了认识过程的基本推理方法,情理推断下的事实认定具有合理可接受性。印证证明也是一种情理推断的特别方法,但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与印证证明方法相比较,一般化的情理推断方法在事实认定中具有灵活性和有效性,可以克服印证证明方法的不足并作为其补充。
关键词:事实认定;情理推断;印证证明;合理可接受性
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5.02.10
情理推断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事实认定的基本方法。《淮南子·说山训》有言:“以小见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正是情理推断在生活中的运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裁判者的事实认定活动也遵循着日常生活中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律,不可能回避情理推断的具体运用。那么,事实认定者是如何具体运用情理推断的呢?情理推断在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中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传统的印证证明方法相比较,情理推断方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如何处理二者关系呢?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对刑事司法过程中情理推断的运用予以探讨,分析其作用的机理和特点,论证其在刑事司法中运用的合理可接受性,指出情理推断方法运用的现实路径,以服务于事实认定的准确和有效。
一、情理推断的解读及其在事实认定活动中的功能如何理解情理推断呢?笔者以为,情理推断也可谓合乎情理的推断或不违情理的推断,作为事实的判断方法,是以已知事实的存在,依据一定的情理性因素推断待证事实的存在或者成立。比如以瓶中水结冰的事实,依据天气寒冷后水才结冰的经验和规律做出天下寒的推断,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情理推断。除此之外,情理推断还有一种特殊的模式,即某一现象或者行为与情理不符,这足以引起事实认定者的合理怀疑,进而做出合乎情理的推断,情理推断的这一特殊模式在司法证明活动中被广为运用。比如,因为证人在陈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态、语气等不符合一个诚实者的自然状态,进而做出证人陈述不可信的推断。
对情理推断的理解应该把握住两点:一为推断,二为情理。首先,情理推断之推断是由基础事实的存在,而做出待证事实的存在或者成立的判断推理过程,从哲学认识论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是对知识的判断过程或者知识的证实(justification)过程,其推理活动是以推论(inference)的方式进行的。推论证实(inferential justification)按其本质而言应该是而且主要是直线性的。这一过程就是信念的单一层面的延伸系列,它由组成认识过程中各个项所具有的先后的关系组成的。(参见:张军.知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8.)与法律推定(assumption)不同,推论是一种综合判断过程,事实裁判者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基础事实存在并不必然推导出待证事实,而法律推定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拟制,一旦基础事实成立,也就意味着待证事实的存在。
其次,情理推断所做出的推论之判断依据在于情理因素。那么,何谓情理呢?简言之,情理就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必须予以说明的是,本文所述之情理因素在本质上与陈忠林教授所提出的“常识、常理、常情”相类,然陈忠林教授“三常理论”的提出旨在为我们理解法律规定提供帮助,并不涉及情理因素在事实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关于“三常理论”,资料来源于:[2014-09-20] http://chenzhonglin.fyfz.cn.孟子曾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人之常情。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静芝在对《诗经·邶风·雄雉》的通释中也讲到,“言济水之满,野稚之鸣,此两事皆平常事也。但由水之满,可知车由水中渡过则必湿其车轴;由雌稚之鸣,则知在求其雄雉也,此固事之常理,亦见人之常情”。[1]由此可见,情理可以粗略地划分为“情理”与“事理”。前者多源于人之普遍的内心情感,乃“人情枢机”,“推情原意,能适其变”,以俗语言之,就是“通人情”,“富人情味”[2]。后者则多指社会普遍认同的经验、道理。可见,“情理”和“事理”有其一般化和普遍性的特点,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经验和认识,可作为推断的依据。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李滨:论情理推断方法在刑事司法事实认定中的运用事实认定者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运用情理推断呢?笔者拟以以下几则案例说明,并借此说明情理推断在事实认定中的功能分类。
案例一:冯梦龙《智囊》所载张潮杀人案。湖州赵三与周生友善,约同往南都贸易,赵妻孙不欲夫行,已闹数日矣。及期黎明,赵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张潮利其金,潜移舟僻所沉赵,而复诈为熟睡,周生至,谓赵未来,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赵门,呼,“三娘子”。因问:“三官何久不来?”孙氏惊曰:“彼出门久矣,岂尚未登舟耶?”潮复周,周甚惊异,与孙分路遍寻,三日无踪,周惧累,因具牍呈县。县尹疑孙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杨评事者阅其牍,曰:“叩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在此案中,杨评事断案的主要依据是“叩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夫也”。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情理推断,以A事实的存在,推论出B事实的存在,而推论的依据涨潮叩门便叫三娘子于情理不合。在此案中,情理推断表现出事实认定的启发性功能,即帮助裁判者形成事实成因的假设,或者说建立起案件事实的初步成像,这就如同福尔摩斯式的断案技巧,从案件各种零碎的事实出发推测出案件事实真相。事实上,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圣经中所记载的所罗门智断亲子案,我国民间流传的寇准智审铜钱案等,皆由情理推断事实真相以决断疑难案件。
案例二:赵某等涉嫌抢劫案。在一起抢劫案件中,被告人赵某等人趁被害人行车变道之机故意与被害人车辆擦挂,以此索要钱财。事故发生后,被告人二至三人强行将被害人拉下车,或以言语威胁或以手势威胁向被害人索要巨额赔偿。控方指控成立抢劫罪,但是辩护人认为只能成立敲诈勒索罪,并阐述理由:被告人以车辆擦挂相要挟,被害人在此要挟下赔给钱财符合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检察官在辩论中反驳道:任何一个身处这一场合的被害人都会感受到被告人所施加的威胁,而且很清楚这种威胁不是车辆擦挂的威胁,而是不合作就施加暴力的威胁,如果认为仅仅是以车辆擦挂为要挟的把柄,那就太不符合常理了。本案系笔者2012年于广东省D市第一人民法院所承办案件。在这则案例中,检察官以被告人客观所表现出的行为,推断其主观具备抢劫的故意,而非敲诈勒索的故意,并以辩护律师所论主观故意显与情理不符而反驳之,可谓有理有据。该案即折射出情理推断的另外一个功能,即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一般来说,犯罪主观方面的事实往往是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如故意、过失、目的等,其本身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在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只能经由裁判者依据社会经验之一般规律,从被告人外在表现出的各种行为事实中予以推断,可以说情理推断在犯罪之主观方面的事实认定活动中往往承担着证明性的作用。
案例三:Neil v. Biggers案。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衡量目击证人辨认可靠性应当考虑五个因素:(1)证人在案发当时有机会观察到作案者;(2)案发时证人的关注程度;(3)证人对作案者先前描述的准确性;(4)证人在对质时识别出作案者的确信度;(5)犯罪发生及对质的时间间隔。Neil v. Biggers,409 U.S.188 (1972).那么,法官具体又如何从这五个方面衡量辨认的可靠性呢?证人是否有机会观察到作案者,证人的关注程度如何,证人对作案者的描述准确与否,证人在对质时识别作案者是否确信以及犯罪发生及对质的时间间隔多久才不影响证人的辨认准确性等问题基本都属于经验判断的范畴,法官在做出具体判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个人和社会经验这些情理性的因素,从而以情理推断的形式对辨认证据的可靠性做出最终认定。据此可见,情理推断在案件证据材料的可靠性判断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国古代司法以“五声听狱讼”: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其本质上也是以情理因素推断两造双方言辞之真实性,而现代刑事司法普遍要求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维护被告人对质诘问权之外,同样起到辅助判断证人陈述真实性的作用。
以上三则案例均反映出情理推断在刑事司法事实认定活动中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此我们可以形成情理推断在事实认定中作用的初步结论。首先,情理推断是事实认定者在推理过程中,借助于常情常理等一般经验和规律,在A事实存在的前提下推断出B事实的存在或者成立,并为案件事实的构建和认定提供依据。其次,情理推断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为案件事实认定的启发性功能;二为案件事实的证明性功能;三为对案件证据材料可靠性的评判功能。
二、情理推断在刑事司法中运用的正当性基础(一)遵循认识过程中的基本推理方法
“判断为知识之根本”[3],人们在对知识的判断或者证实的过程中必须依靠一定的推理方法,否则无法达至知识的真正认知。在这一过程中,基本的推理包括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情理推断的运用主要就是遵循着这两种推理方法。首先,情理推断所依据的人之常情和事之常理是人们经验观察和归纳推理的结果,比如案例一所示,事实认定者首先是建立起来了这样的经验和规律:“人们在上门寻人的时候通常的作法是呼叫所寻之人”,尤其是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并以此信念作为进一步演绎推理的大前提,而这一信念的形成和建立正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归纳推理的结果。其次,杨评事以此信念为推理之大前提,以张潮“叩门便叫三娘子”为小前提,从而做出张潮知道被害人赵三不在家中的推论。可见,情理推断的推理过程事实上正是遵循了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普遍使用的推理方法。
西方最近的法律论证理论认为除了上述两种推理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推理方法:溯因推理( presumptive reasoning/plausible reasoning),又被称为推定推理或合情推理[4]。尽管对其名称学界还没有统一认识,但其基本的推理方法如下:根据已知事实结果和有关规律性知识,推断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或者说是“为现象寻找最佳解释方案的推理过程”。美国哲学家N·汉森在总结亚里士多德与皮尔斯等人的观点基础上,将溯因推理的形式总结为:(1)某一令人惊异的现象P被观察到;(2)若H是真的,则P理所当然的是可解释的;(3)因此有理由认为H是真的[5]。由于溯因推理是为现象提供最佳的原因解释的过程,其并不能否定其他现象原因的存在,故依据溯因推理所得出的原因结论只是具备较大可能性,其作用更类似于情理推断中的事实启发性功能。仍以案例一为例,现象P为张潮“叩门便叫三娘子”,这一现象引起了杨评事的怀疑,而如果H张潮先杀人后来寻人是真的,那么现象P就得到合理解释了。因此有理由认为H张潮杀人是真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溯因推理只是建构了事实的初步成像,认定张潮杀人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证实。因为如果将现象P的原因归结为H赵三系不慎溺水身亡,张潮为贪墨其金而隐藏尸体,那么现象P仍然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二)情理的一般性与普遍性特征
前文对情理的解读论及情理可以粗略分为情理和事理,前者是一般的人之情感,后者是普遍的事之规律,是人们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若干经验的总结,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人类认识,在本质上有着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作为情理推断依据的常情和常理等认知并不是个人所独有的、个别的认知和经验,更不是主观臆测性信念和偏见。关于偏见下事实认定的错误可以一则故事说明:一个人遗失了他的斧子,怀疑他邻居的儿子。他因此暗中监视他:每一步都暴露出是偷斧子的嫌疑犯,他的眼神表达,他的每一个词和话、动作、举止、行为和行动也是这样。这个人偶尔在沟壑附近挖掘,发现了斧子。第二天看见邻居的儿子时,他不再发觉后者的动作、行动、举止和行为像偷斧子的人了。(参见:恩斯特·马赫.认识与谬误[M].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0:139.)
对于情理的一般性与普遍性特征的理解应注意三个方面。其一,情理的一般性与普遍性特征并不是说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些常情常理等一般经验和规律是归纳推理而来的结果,始终无法排除反常之经验的存在,正如17世纪以前人们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但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这一经验就不再有效,故而情理推断之逻辑严谨性存在固有缺陷,其结论之确定性依据不足,这是情理推断作为事实认定方法的固有特点。其二,情理的一般性与普遍性特征也不意味着所有常情常理的一般性品质相同,而是程度有异,比如情理推断A由一叶落而知天下秋,B由雌稚之鸣,知其在求雄雉,C由瓶中之冰而知天下寒,这三个情理推断所依据情理之规律性程度依次递增,故其事实推论的结果之盖然性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三,作为推断依据的情理虽具备一般性和普遍性特征,但其前提是以个体的认知和接受为基础的。如果某一情理规律虽然表现出群体的可接受性,但作为推断主体的个人对此并不赞同,那么这一情理也是无法作为推断依据的,这也就意味着情理推断的结果必然会存在个体的差异。比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一起通奸案件的认定中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争议:男女双方共处一室,但没有二人通奸的直接证据。该案年老法官以“若非奸淫,男女岂会共处一室?”的情理推断认定通奸罪应当成立,但年轻法官却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和认知规律,对这样的情理显然不予赞同,故而认为应当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此案例系笔者从与我国台湾地区来访学者卢映洁教授的座谈交流中获悉。
(三)情理推断的合理可接受性
情理推断是日常生活中事实认定的基本方法,其遵循认识过程中的基本推理方法,以及情理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特征构成了这一事实认定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不过,刑事司法中的事实认定活动所要求之事实认知的确定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之事实认定,这与情理推断的事实结论之确定性依据不足之间存在显著矛盾,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一矛盾是裁判者在刑事司法案件事实认定中运用情理推断的前提。
在此,笔者尝试借用合理可接受性的概念进行分析。“合理的可接受性”是美国学者希拉里·普特南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如果一个陈述被人们认为是合理的,那么这个陈述就是有合理的可接受性。普特南在对真理的符合性和相对主义两种真理观的批判基础上提出真理就是合理可接受性的中间路线[6]。在诉讼认识论领域,“真理性问题和正当性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理想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获得绝对真理,那么正当性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绝对的真理就有绝对的正当性。但是在一个具体的条件下,我们无法获知绝对的真理,那么,相对真理的接受性就表现为它可以正当地被接受,即普特南所说的合理的可接受性”。[7]因此,情理推断下事实推论是否可以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础就在于其是否具备合理可接受性。
笔者以为,情理推断之事实推论在刑事案件事实认定活动中是合理可接受的,可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础。具体理由有三:第一,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为情理推断的合理可接受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哲学的批评和经验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十六至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和科学界尝试着经由实验、直接观察和陈述的方式检验普通现象,并且相信依靠所获得证据的质量和数量,通过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能够充分并真实地作为人类开展各项事务的基础[8]。正像休谟所说的,“如果有人问我们对于事实所作的一切推论的本性是什么?适当的答复似乎是:这些推论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上。如果再问,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一切理论和结论的基础是什么?就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经验”。[9]
第二,自由心证制度与情理推断的契合为其合理可接受性提供了制度基础。情理推断从其推论做出的过程来看是一个内心确信的问题,因为裁判者推论所依据之情理是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认识规律,并不是法律规范强制要求的一般性规则,裁判者既可以选择这些认识规律,也可以弃之不用,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在这些认识规律下对事实推论形成了内心确信。因此情理推断的事实认定方式内在地契合了自由心证制度的基本内涵,其合理可接受性在自由心证制度下也就不存在障碍。
第三,从工具主义合理观来看,情理推断下事实认定的有效性为情理推断的合理可接受性提供了事实基础。工具主义合理观认为合理性就在于有效地(effectively)、有效率地(efficiently)实现各种目标、目的和欲望。(参见:罗伯特·诺奇克.合理性的本质[M].葛四友,陈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4-65.)尽管在情理推断下事实推论的确定性依据不足,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案件事实认定中的有效性。具体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一,情理推断在事实认定中的功能是不同的,事实认定的启发性功能并不需要情理推断结论的确定性为条件;其二,情理推断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控方起诉事实的证明,在被告方所提出的辩护意见中也会运用到情理推断的方法,从诉讼证明的视角来看,只要被告方所提出的情理推断对待证事实的存在能够提出合理的疑点即可,并不需要以确定性的情理推断结论来证实待证事实的不存在;其三,在情理推断承担主要证明功能和证据可靠性评判功能的场合,情理推断之确定性依据不足也不妨碍其结论作为事实认定的基础,这是因为情理推断的确定性依据不足并不是认为其不具有确定性,只是无法对其确定性提供更多的论证依据,而作为推理前提的情理之一般性品质在不同情境下是有程度区分的,在高度盖然性的情理推断下之事实推论,在自由心证制度下裁判者排除内心的合理疑问并建立事实的内心确信后,是可以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的。如前文案例二所示,检察官以被告人客观所表现出的行为,论证其主观具备抢劫的故意,是高度盖然性的推论,裁判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只要排除了合理的疑点,内心形成确信后是可以做出相应的事实认定的。
三、印证证明方法与情理推断方法印证证明也是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基本方法,它是以证据材料之间的相互符合性或者一致性,从而认定待证事实的真实性。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判断就是坚持印证的方法,即要求以这一类言词性证据本身是否矛盾,有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来判断其可靠性。不过,言词性证据可靠性的判断从事实调查的基本方法来看,其常态化应当是一种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并充满情理推断在其中的判断,比如观察证人陈述时的表情、语气、神色、目光等,特别是其面对被告人质问过程中显现出坦荡或者畏缩的神情等,这些都有助于裁判者对陈述者所述内容是否可靠进行判断。但是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极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盛行,试图经由交叉询问而对证人直接观察并对其陈述可靠性的判断就无从谈起,一般化的情理推断方法适用的现实空间有限。而且,相对于证人、被害人、被告人的法庭陈述,法官更青睐于从言词性证据的庭前书面笔录中寻找其可靠性的依据,在此情境中情理推断的证据可靠性判断也就难以常态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其结果往往是把生动丰满的言词证据可信性的判断活动转变为冷静且抽象化的书面笔录是否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判断,这种印证性判断与Neil v. Biggers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证人辨认可靠性的方法迥异,事实认定者注重的是各类证据所表现出来的相互一致性并以此而形成确信,却忽视从证据本身所蕴含的合理因素中寻找内心确信的源泉。由此也可见,印证证明与一般的情理推断方法是不同的。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以印证证明方法做出事实认定的心证形成过程,不难发现,印证证明与情理推断并不矛盾。笔者以为,对于印证证明,严格来说也是一种经验的判断:证据材料之间的相互一致性越高,其可信性则越强。比如素未谋面也未相互影响的证人之间,关于待证事实的描述是一致的,假如这样的证人越多或者一致性程度越高,那么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证言就越是可信。可见,这一判断过程也是典型的经验判断,而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故其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真理。《战国策》所讲“三人成虎”的故事就是例证。因此,从本质上来看,印证证明与情理推断的方法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和冲突,相反二者是紧密关联的,也可以说印证证明是一种典型的情理推断方法。
印证证明方法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案件事实证明的“硬性”要求。关于印证证明,龙宗智教授指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是以何种方式使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从而做出事实判定的,我认为,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即‘印证,如果要作模式界定,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可以简略地概括为‘印证证明模式”[10]。进而,龙宗智教授还称其为“中国刑事证据法的‘铁则”。[11]而实践中作为实务共识的孤证不能定案也为此做了最好的脚注。由此可见印证证明方法在我国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为何我国刑事实务中如此推崇印证证明,并以证据相印证作为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则呢?这一方面原因来自于印证证明本身的特点,即方法的易把握性与可检验性,结果的高度盖然性或者说更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则在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即非直接与非言词的审理方法,审理与判定的分离,诉讼认识论上的客观真实观等。正是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印证证明与刑事司法的实践理性相互依托与契合,以致印证证明方法之树在实务中常青。
不过,印证证明方法并非完美,而是有着相当的局限性。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实践中并不总是能够找到可资相互支撑与印证的证据材料,如果恪守证据相印证的“铁则”,那么即使法官基于某一证据对案件事实排除了合理怀疑,形成了内心的确信,那么也很难在实务中对被告人定罪,这就容易导致印证证明方法的僵化。其二,实践中可资相互支撑与印证的证据材料并不都是可靠的,有的甚至于是为了印证而“创造”的,那么以这样的证据相互印证而认定案件事实则陷入了表象印证甚至虚假印证的陷阱之中,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比如,在一起抢劫案中,被告人供述了抢劫的事实,被害人做出了相一致的陈述并进行了辨认,而且双方还达成了对被抢劫的摩托车进行赔偿和谅解的协议,可谓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法官在审查中发现被告人作案时间是晚上10点左右,地点在一条没有路灯的崎岖小路,故而对被害人的辨认笔录产生了怀疑。后法官为进一步核实证据,向被害人了解情况。被害人坦诚地说并没有辨认出被告人,而是警察在辨认中作了指示,这就是一起典型的虚假印证。该案例是笔者在广东省D市第一人民法院所承办案件。其三,实务中裁判说理制度的不完善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表面印证和虚假印证的危险性,因为概括化和固定化的“证据相互印证”之裁判说理,掩盖了法官心证形成的真实过程,难以为外界所监督和制约,只是在形式上具备了事实认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不是提高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了。
与印证证明方法相比较,一般的情理推断方法则可以避免印证证明的弊端。这可以从印证证明的三个方面局限性来分析:其一,一般的情理推断方法不以证据相互支撑为事实认定的基础,孤证不能定案不是一般性的要求,只要事实认定者根据一般之情理规律对待证事实形成了内心之确信,那么就可以做出事实的认定,从方法上来看是灵活的,从事实认定的结果上来看,在具备合理可接受性的前提下也是有效的。如此即避免了印证证明方法容易陷入僵化的弊端。其二,也是由于一般的情理推断方法并不以证据相互印证为事实认定的前提,故而为印证而千方百计寻找印证资料,甚至于“创造”证据资料就没有必要了,表象印证和虚假印证的问题就不会突出。其三,相对于印证证明方法,一般的情理推断方法所形成之内心确信会掩饰内在的心证过程吗?笔者认为这是很难发生的。因为在实务中,印证证明虽然是典型的或者说特别的情理推断方法,但是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识性,以其为方法做出的事实认定是为实务界和理论界所接受的,故而在裁判说理中并不需要予以特别地分析和说明,概括化和固定化的“证据相互印证”之裁判说理本身就具有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但是,一般性的情理推断方法,其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不是普遍的,而是具体的和个别的,法官在裁判说理中是无法以概括化和固定化的用语而回避其心证形成过程的,也就是说,在一般性的情理推断方法下,裁判者必须对其做出事实认定的推理过程予以公开说明,以此建立起裁判结果之正当性基础,并体现其合理可接受性。
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注重一般性情理推断方法的合理适用,以之辅助印证证明方法,作为其补充,可合理促进事实认定活动的灵活和有效。不过仍需指出的是,一般性的情理推断方法在当前的司法环境并不能够普遍运用,这既不适宜,也不现实。但是,相信随着刑事程序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庭审中心主义和直接言词原则逐步得以确立,自由心证制度在实践中取得普遍认同,一般性的情理推断方法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功用。JS
参考文献:
[1] 黄忠慎.诗经选注[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121.
[2]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M].台北:联经出版社, 2003:12.
[3] 张东荪.认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
[4] 卞建林,王佳.西方司法证明科学的新发展[J].证据科学,2008,(2):132.
[5] 樊传明.司法证明中的经验推论与错误风险[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6):117.
[6] 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
[7]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244.
[8] Barbara J. Shapiro. To A Moral Certainty: Theories of Knowledge and Anglo-American Juries[J]. Hastings Law Journal, 1986,(38):156-157.
[9]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23.
[10]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J].法学研究,2004,(2):104.
[11] 龙宗智.薄熙来案审判中的若干证据法问题[J].法学,201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