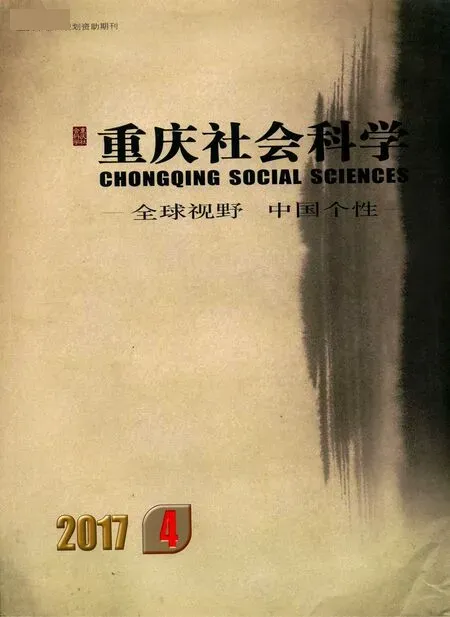公权力与私权力界限析*
李天昊
公权力与私权力界限析*
李天昊
权力是基于特定身份的主体对他人享有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其要素包括权力主体、作用范围和来源形式,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力的标准是权力主体要素。权力存在应然享有和实际行使两个主体,政权机关应然享有是判断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具体标准。公权力是政权机关应然享有的权力,即政权应然权力,两者在内部结构上高度一致,为旨在实现国民安全和幸福的必要国家管理权。公权力源于全体国民直接或间接授予,授权对象数量上的确定性是公权力的直观表现。
公权力 私权力 政府行为
2004年以来,学界围绕公权力的边界以及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但较少涉及权力系统内部公与私的界限。实践中,绝大多数权力为公权力,部分权力为私权力,还有少数权力兼具公属性和私属性,公权力与私权力同属权力,明确二者的界限首先要明确权力的内涵。
一、权力含义解析
权力,英文表述为power,被用于表达多种含义。权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权力包括对人的权力和对物的权力,罗素将其概括为“对人的权力和对事物或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权力”[1]。博尔丁则将其抽象为“得我所欲的能力”[2]。在广义权力的世界中,打死蚊帐中的蚊子被视为一项人类的权力。狭义的权力是指涉及、影响到他人的权力,即“我们为取得所欲之物而支配他人做事的能力”[3]。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应当以人类社会为出发点和归宿,鉴于此,权力的狭义概念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偏爱。这里取权力的狭义内涵。
(一)权力的手段:支配和影响
美国学者卢克斯对权力概念的解析非常深入,他归纳总结出三个维度的权力:一维权力观的基本观点是,A拥有支配B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能够使B去做某些B不会去做的事情,这就要客观存在某项议题,并且围绕议题可以观察到显而易见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权力方通过决策改变了另一方的初衷。二维权力观对一维权力观作出三点修正:一是议题不必客观存在,也可能是潜在的;二是冲突不必显而易见,也可能是隐蔽的;三是实现权力的方式不必一定是决策,也可能是不作为。三维权力观从源头上对前两种权力观进行了修正,认为A可以通过使B去做不想做的事情的方式运用权力控制B,也可以通过影响、塑造或确定B真实需要的方式运用权力影响B就范。换言之,三维权力观强调权力不一定表现为强制、操纵,也可能是出于劝导、激励等,使权力对象心甘情愿地改变初衷。[4]无独有偶,博尔丁将权力的来源概括为威胁、交换和爱,基于爱的权力就属于卢克斯所概括的第三维权力观,因为爱而受其支配是心甘情愿的,其间的权力关系如领袖与追随者、宪制君主与臣民等。[5]罗素则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强制与劝导的区别:一头拦腰捆绑的猪嚎叫着被拖上船,是基于对身体的直接强制;谚语中驴跟着胡萝卜向前走,则是在用胡萝卜引诱驴子按照人们的愿望去做,并使它相信这样做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劝导、激励。[6]
在此,不妨引用卓泽渊的观点进行总结:“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因为拥有一定的资源或优势而具有的支配他人或影响他人的力量。”[7]该定义紧紧围绕社会科学的主题,落脚点限定为“人”,作用于人的方式有二:一是支配,就是我们所说的强制、操作;二是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劝导、激励。如果暂不考虑权力的主体要素,权力就是对他人的支配和影响。
(二)权力的主体:非对等身份
权力和权利两者不仅发音相同,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一致性。例如甲借给乙1000元,乙不还钱,甲以诚信大义劝说乙还钱是“影响”,甲以起诉为手段要求乙还钱则是“强制”,这种影响和支配属于权力还是权利?按照权力的“影响与支配”标准,甲要求乙还钱属于权力,可事实上,甲要求乙还钱是行使债务求偿权的行为,债务求偿权无疑属于一项民事权利。因此,权力和权利都有“影响和支配”的内涵。那么权力和权利的界限是什么,这就要论及权利与权力的起源。
人的生存、发展必有所需,这种需要就是利益。随着人类聚居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个人获取利益能力的差异性,利益无法被平均分配,甚至剥夺他人利益成为个人牟利的重要手段,这种不公平和取之无道的行为势必受到社会的谴责。然而,何为不公,何为无道?这就必须对利益进行权衡和协调,规定出正当、应然的利益,对利益进行权衡的结果就是权利,权利的构词就是权衡利益的简称。而利益的权衡、协调、确认、保障需要某种力的作用,这种对利益的权衡之力即为权力。权力者,权衡、确认和保障实现权利之力也。[8]这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主体作出限定,平等主体之间不可能具有权力,因为无论由谁来权衡利益都会出现对另一方的不公,甚至回到剥夺他人利益以满足自身利益的原始状态。因此,权力主体与权力对象必须具有身份上的差别,基于非对等的特定身份关系间的“支配和影响”才是权力。
权力和权利在正当性基础上也存在差异。权利具有正当性,平等主体间正当的“支配和影响”为权利,不具有正当性的“支配和影响”为不当甚至不法行为,如强盗以利刃相威胁对他人强加的支配力不是权利,是犯罪行为。权力则不必具有正当性,权力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中被滥用的权力不会因为缺乏正当性而失去权力的属性。
综上,权力是基于特定身份关系的主体对他人享有的支配力和影响力。
二、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划分标准
基于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权力作出多种分类。英国学者迈克尔·曼从社会领域的角度,将权力划分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四种。[9]约瑟夫·奈以权力外在表现为标准将其分为软权力和硬权力。[10]最著名的权力分类莫过于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将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执法权)、司法权、外交权等。根据权力的公私属性,可将权力划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公权力在权力体系中无疑占据着绝大部分权重,以至于人们运用权力一词时,如未加说明都是在表达公权力的含义。实践中存在个人基于特定身份关系对他人的支配力和影响力,这些特殊身份关系包括血亲姻亲关系中的领导关系等,这些关系中尊者享有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为私权力。
明确公权力和私权力划分标准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公”与“私”修饰权力的何种要素。权力有三项要素:一是权力作用范围,二是权力来源形式,三是权力主体。首先,以权力作用范围的“公”与“私”界定权力的“公”与“私”显然不妥。“公”指公共,“私”指私人,作用于公共范围的权力不都是公权力,也有私权力,如私营企业要求员工八点前到岗否则扣工资,这种支配和影响范围遍及全体员工,属于公共的范围,但在我们的习惯性认知中私营企业对员工的权力不属于公权力,而是私权力;作用于私人的权力也不都是私权力,如政府对社会个体进行行政处罚,尽管权力作用对象为私人,但这种权力属于公权力。
其次,以权力来源形式界定权力的“公”与“私”也不甚准确。如果以此法进行界定,公权力是基于公众让与的权力,私权力是来源于个人意志的权力。但在实践当中,有的基于公众让与的权力属于私权力,如家族会议推选管理者管理家族事务,家族事务管理权来源于家族范围内的公众让与,但这种权力在习惯性认知中属于私权力。有的来源于个人意志的权力为公权力,如君主专制下的君权及其衍生权力,君权基于对臣民的事实控制由君王个人恣意掌控,不是基于臣民让与,然而君权代表政权,属于公权力,否则在世界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史中便无公权力可言,包拯、海瑞等官员都是在行使私权力为民作主,这是说不通的。
无论权力作用范围也好,权力来源形式也罢,虽不能准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力,但可以提供一种思路,即权力作用的“公共”或授权形式的“公共”究竟范围几何,也就是说何种形式的组织体属于“公共”,一个家族、一个公司、一个社团?抑或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家族、公司、社团的权力不是公权力,在整个地区甚至国家范围内的权力才是公权力。而享有国家范围内管辖权的只有国家政权机关,地方政权是国家政权机关在该地的代表。在此用权力主体要素的公与私界定权力的公与私便水到渠成,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划分标准为权力主体是否为政权机关,其主体为政权机关的权力为公权力,反之为私权力。政权机关包括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主体为中央政权机关的权力为中央公权力,主体为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为地方公权力。
政权机关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机关。政权机关的设立先于国家机关,如我国三皇五帝时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国家机关,但存在政权。国家产生后对内享有管辖权、对外享有代表权,政权机关就是行使这些权力的组织体。政权机关具有实然性,国家产生之初只有国家机关可以代表政权,但出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各国各异的国情,在一些国家的特定时期,教会、军事组织和政党在一定范围内实际履行了政权职能,是为非国家机关的政权机关,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等。
应当指出,根据权力的含义,并非政权机关对他人的支配力和影响力都是公权力,如政府在采购中因产品质量问题向供应商主张退货,任何主体在相同情况下都可以对供应商施加这种影响力,这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权利而非公权力,政权机关只有基于其政权机关的特定身份对他人施加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才是公权力。
三、公权力与私权力划分标准的具体判断
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划分标准是权力的主体要素。权力存在两个层面的主体:一是实际行使权力的主体,二是应然享有权力的主体。在具体判断公权力与私权力时应当以权力的实际行使主体为标准还是以应然享有主体为标准呢?这需要对二者进行取舍。
(一)实际行使和应然享有两个标准的取舍
首先来看实际行使主体标准。根据权力实际行使主体的不同,权力可分为政权权力、社会权力、国际权力和私人权力。政权权力是国家政权机关行使的权力,社会权力是非政权组织直接行使的国内权力,国际权力是国际组织行使的权力,私人权力是自然人行使的权力。政权权力是统治国家的力量,是最传统的公权力,两者间可以划上等号,至少是约等号,那么由非政权机关行使的社会权力、国际权力和私人权力都是私权力吗?
社会权力的主体包括一切社会组织体,如社会团体、基金会、企业、事业单位、中介组织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被打破,政府的权力与能力已难以及时全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求和参与政治、监控政权权力的权利要求,政权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力量,人类社会出现权力社会化趋势。[11]社会权力都是私权力吗?答案是否定的。姜明安在分析公权力的构成时指出:“在现代社会,公权力主要指国家权力。除国家权力外,公权力也包括社会公权力。”[12]社会权力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社会组织对其成员行使的权力,如某市汉服协会要求其会员参加汉服展示活动,此为私权力;二是社会组织依法律授权或国家机关委托对外部相对人行使的权力,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根据律师法的授权依法享有对全国律师的管理权,此为公权力。
国际权力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产物,随着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通过协商建立国际政府组织并赋予其一定国际公共事务和各国国内事务的管辖权,最典型的国际政府组织就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国际政府组织的国际权力来源于成员国授权,是政权权力在国际社会的延伸,为公权力。行使国际权力的主体除国际政府组织外还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无主权国家授权的情况下可单凭其特殊身份引发舆论声援对各国政府和每一个世界个体施加影响力,但这些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具备权力主体的政权性,为私权力。如绿色和平组织多年来在禁止输出有毒物质到发展中国家、禁止核子武器试验、促进国际环保公约制定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但基于权力主体的民间性,绿色和平组织的影响力为私权力。综上,国际权力包括国际公权力和国际私权力。
政权权力、国际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享有和实施者都是组织体,作为权力实施者的自然人只能以组织的名义行使权力。私人权力则是权力主体纯粹基于自然身份、以个人的名义享有和实施的权力,如恋爱中姑娘要求小伙子去为自己买荔枝。私人权力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概括地讲是历史形成的社会观念得到民众认可而具备了实效。私人权力都不具备政权属性,都是私权力。几种权力的公私属性如图一所示。

图一 政权权力、社会权力、国际权力、私人权力之间的关系
可见,由政权机关行使的权力都是公权力;由自然人行使的权力都是私权力;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行使的权力可以是公权力,也可以是私权力。政权机关实际行使的权力是公权力的充分条件,但无法囊括社会权力和国际权力中的公权力。
以政权机关实际行使为标准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力错误地将社会公权力和国际公权力划入私权力,那么政权机关应然享有权力标准是否可以担此重任呢?答案是肯定的。通过前文分析可知,社会权力、国际权力的公与私区分标准为是否由政权机关授权,社会公权力由政权机关将权力授权(下放)社会组织行使,国际公权力由政权机关将权力授权(上交)国际政府组织行使,政权授权的前提是政权机关本身应然享有这些权力。公权力包括政权权力、社会公权力和国际公权力三项,社会公权力、国际公权力都是政权机关应然享有的权力,政权权力是政权机关应然享有并实际行使的权力。三项公权力均为政权机关应然享有的权力,而私人权力、社会私权力、国际私权力等私权力均不由政权机关应然享有。因此,政权机关应然享有是判断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具体标准,公权力是政权机关应然享有的权力,即政权应然权力。
(二)政权应然权力的内涵
政权应然权力是公权力的本质属性,是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力的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因过于抽象以致难为所用,判断权力的公与私必须先明确政权应然权力的内涵。
应然是一个哲学范畴,英文表述为 “ought to be”,是对某种事件原因、结果或事物属性的肯定性逻辑判断,这种判断的作出受判断主体意志和利益的支配,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13]政权应然权力是根据法学、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共性的逻辑判断归纳出的应当由国家机关行使的权力,具体包括立法权、行政权(执法权)、司法权、人事权、监察权、外交权等。由于授权现象的存在,政权机关实际行使的权力范围小于应然享有的权力,政权应然权力包括政权实然权力以及政权向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授予的权力。
政权实然权力即前文所述的政权权力,出于用语习惯,在不加区分某一概念应然和实然状态时,该概念所表达的含义一般指其实然含义。根据权力的实际行使主体,政权实然权力又可分为国家机关实际行使的权力和非国家机关的政权机关实际行使的权力,即前文所述的在某些国家特定时期中教会、军事组织和政党实际行使的公权力。政权应然权力的构成及与公权力对应关系如图二所示。
关于公权力即政权应然权力的结构已基本厘清,那么政权应然权力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诸如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权力被认为是政权机关应当享有的权力?这就要从政权权力的起源说起。根据社会契约论,国家政权出于结束社会野蛮状态而产生,在野蛮状态下人们的基本安全得不到保障,“每个人都可以据此合法地攻击其他人,而其他人也可以合法地反击”[14],于是大家把“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15],这个人或集体对内享有管理权、对外享有代表权,这就是最初形式的国家政权。对内管理权是公权力的核心,旨在维护社会秩序,防止私权力对他人的侵害。久而久之,政权权力本身开始膨胀并侵害到大家的利益,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兴起并要求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作为政权应然权力的国家管理权不再仅仅要求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而是更多地要求保障人的自由、幸福和发展。换句话说,不是所有有利于保障社会秩序与安全的国家权力都是国家政权应当享有的权力,政权应然权力只是其中不得不由政权机关行使的必要部分。政权应然权力就是旨在实现国民安全和幸福的必要国家管理权。

图二 政权应然权力构成以及与公权力的对应关系
由于应然性的主观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政权应然权力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如在古代盐铁专卖权属于政府是社会共识,但当代没有人认为盐铁专卖权是政权应当享有的权力,再如军工、邮政、电信、水电、公共交通等行业的经营在一些国家是政权应然权力,但在另外一些国家则不是政权权力,或者过去曾经是,现在正在放开,未来很可能不再是。
(三)公权力的直观表现
探究政权应然权力的内涵可从深层次界分公权力与私权力,但因标准过于主观而缺乏操作性,与其说是实际的方法,不如说是理想的概念。结合上文论述,可根据公权力的外在表象划定其范围。
公权力都源于授权,政权权力源于政权范围内所有国民的授权,全体国民通过制定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契约授予国家政权机关公权力。社会公权力和国际公权力源于国家政权的授权,国家政权通过立法等方式将政权机关应然享有的权力授予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国家政权对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授权也是政权应然权力的一种,三项公权力追根溯源都源于国民的授权,政权权力为国民直接授权,社会公权力和国际公权力为国民间接授权。虽然各国各时期对公权力的应然认识不尽一致,但就我国当代而言公权力有相对明确的标准——授权对象数量上的确定性。公权力授权对象数量上的确定性要求国民授予公权力时,授权对象必须是一个确数,哪怕数以十计、百计,但必须可以被精确统计。
首先来看政权权力。国民授权建设国家政权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权力主体多元化造成相互的掠夺,因此只能将政权权力授予一个主体,被授予政权权力的主体即为中央政权,中央政权数量唯一。中央政权将政权权力分类,分别授予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中央政权机关,因各国政体不同,各国中央政权机关数量各异,但一定都是确数。以立法权为例,每个人可以就立法提出建议,甚至独立撰写一份法律草案,但只有国家立法机关可以使法律草案上升为法律,立法权的授权对象是确数,因此立法权属于典型的公权力。再如政党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议会议员的提名权,在一些国家中,各政党有权推举候选人,无党派人士也可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提名权的授权对象不确定,这种提名权不是公权力;在另一些国家,只有一个或几个确定主体享有重要公职候选人提名权,享有权力的主体是确数,这种提名权属于公权力。在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地方政权权力分别来源于中央政权授权和地方人民授权,各国地方政权机关也一定是与行政区划数相等的确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各级人大和政府权力,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府总有一个与行政区划相关的确数。
社会公权力、国际公权力是国家政权授予的,授权行为具有针对性甚至双边性,授权次数为确数,那么授权对象也是确数。运用授权对象数量上的确定性区分社会权力的公与私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如公司法赋予了公司及其内设机构一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教育法赋予了学校等教育机构一定的办学权,但公司法和教育法没有针对特定机构授权,公司和教育机构可由个人依法设立,其数量在授权时不确定,公司和学校享有的权力不是公权力,而是私权力。再如我国法律授予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职权,只要符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设立条件,任何主体均可依法设立商业银行,银行享有的权力不是公权力,国务院独家授权银监会对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统一监管权,银监会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
最后,运用授权对象数量上的确定性分析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公私属性。由于特许的缘故,特许经营权的授权对象即使不唯一,也一定是确数,如国家授权移动、联通、电信三家公司共同享有电信领域的经营权,授权对象为确数,移动、联通、电信三家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是公权力。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发展成熟,特许经营权的必要性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2010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等领域建设,公用企业的特许经营权正从公权力转变为私权力甚至权利。
四、结论
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划分标准为权力主体要素,应当由政权机关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其他权力主体基于主体身份对他人享有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为私权力。权力被授予时,授予对象数量上的确定性是判断公权力的最直观表现。
明确公权力与私权力的界限可以为公权力和私权力的既定认识提供理论支撑,特别是对兼具公私二重性的权力进行公与私的类型划分提供直接方法。在我国实践中,群团组织、公用企业等主体的权力兼具公属性和私属性,对这些权力应采取何种态度?国家是以公权力的标准严格规范之,还是以私权力的标准充当“守夜人”,甚至直接将权力放归民间?这都取决于如何对这些权力进行“公”与“私”的正名,对其中属于公权力的部分进行正名可以使这些权力的行使具备更加充足的理论依据,并严格规范、限制、监督之,对其中属于私权力的部分进行正名可以为政府简政放权提供决策支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6](英)伯兰特·罗素:《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靳建国译,东方出版社,第23~24页
[2][3][5](英)肯尼思·E.博尔丁:《权力的三张面孔》,张岩译,经济科学出版社,第 2、6、16~20 页
[4](美)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26 页
[7]卓泽渊:《法政治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
[8]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19~20页
[9](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 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10]Joseph S.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Inc.,1990.
[11]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法学研究》2001年第 1期,第 3~4页
[12]姜明安:《论公法与政治文明》,《法商研究》2003年第 3期,第 32~38页
[13]莫纪宏:《审视应然性——一种宪法逻辑学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87~88页
[14]霍布斯:《论公民》,应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
[15]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 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1页
Analysis on the Limits of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Power
Li Tianhao
Power is the domination and influence which the particular subject exercise over others.It has three elements which are the subject,the scope and the form of the source.The subject is the standard for the division of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power.There are two types of the subject of the power which are the should-be subject and the actual subject,and the former is boundary of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power.The public power is equivalent to the should-be power of regime,which are highly consistent in their internal structure and both designed to achieve national security and happiness.The public power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granted by all citizens.The number of authorized objects is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public power.
public power,private power,government action
国家检察官学院理论教研部 北京 102206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论公权力与私权力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