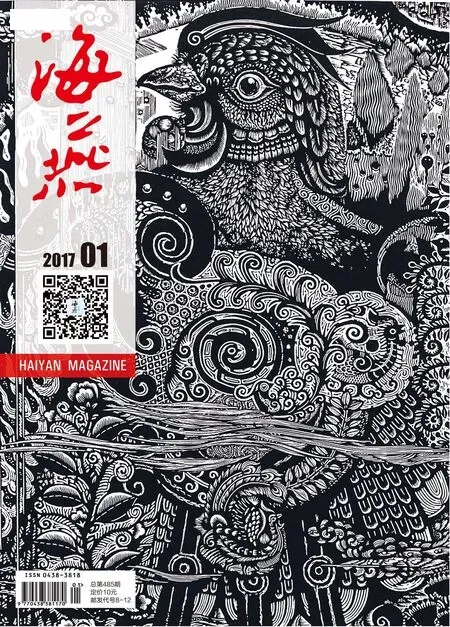苍茫虚空
□张瑜娟
苍茫虚空
□张瑜娟
我落寞得太长久了,以至于不记得已有多久。我有时听见从我身旁经过的人说落寞这个词,我想笑,除了我,这个世界还有谁更了解落寞?我究竟落寞了多久我已记不清了,是五千年?还是八千年?甚至是万年?头痛,真的记不清了。
我究竟是个什么生物一直很难界定。自从女娲造人起,那天她把我拿在手里,捏了又捏,团了又团,可就是没有捏成人形。那时她不知是怎么了,似有想不完的心事,以及作为一个女人的瞬间的莫名与虚空。于是,她许是忘了捏我,只是团我、揉我。从我之后她不再捏人了,而是改用柳树枝去甩,一甩便有许多的人活了。我既没被捏成,也不属于甩成,仅被她拿在手里,被她手心的汗所湿,被她瞬间的落寞情绪所感染,令我虽无人形,却有了丰富的内心和思想。我有别于那些在我之前捏成的人,因她仅赋予他们形,于是他们很少去想、去思考,想的仅是活着的本质与方式:狩猎或捕鱼、饥饿或寒冷。之后用树枝甩出的人更粗糙,没有了精准的外形,一切全凭无意而成,凡事很少过心,偶然地有了生命,便偶然地活着,只言存在,没有更深的意义。
女娲可能是忘了我,置我于阴阳河之畔,她只须稍一凝神或甩出手我便能活了,有形地活着,有着她的落寞以及片刻的思想,天与地、宇宙洪荒,甚至于补天那样的大事。然而她确是忘了我,我因此在阴阳河之畔的那块巨石之侧、那棵杂树之下,身旁有杂草,可厌的杂草,阻挡了她的视线,让她真的,永远地忘了我。我知道其实她最终用自己的身体去填补天上那个漏洞时其实想起了我,她那时后悔了,也许觉得对不住我,或者对不住她自己。她一直在思索为什么没有创造出一个令她内心愉悦的人,她似乎明白了那人也许是我。于是她奋力地望向我,想去找寻我,可是那是她最后的一瞬,她隐没在无形的苍穹里了,隐没了她的遗憾,明晰了我的遗憾,她融化在天的无形巨洞里,带走了她的遗憾,留下了遗憾的我,和那点关于我的难解的宿命。可是那一刻我分明看到她的笑意,那笑意使我明白了,也许正因瞬间的差池我才能永远存在,于是我和她一起创造了一个词叫做“永存”。
我存在了多久,我确已算不清了。我昏睡、我寂寞、我被夹在洪流里流走、我被搁浅在沙砾中暴晒、我阅尽岁月中的沧海桑田、我看着星月变大又变小、变近又变远……在太长的时间里我的身边几乎无人驻足,我错乱了时间,我只能感受空间。我太知道寂寞是什么,虚空是什么,我仅是一块泥土,却有泥土不该有的思与想,这思与想令我时痛时忧,却说不清。我面对空渺宇宙、大风与旷野、荣枯与衰败,醒着与梦着常没有界定,我被洪荒掏空又填满,填满了仍仅是空、长久的空。因没有形,我不知道自己的模样。
不知从何时起,我由怕孤单变成习惯孤单,我由点状的思考变为线的、面的思考,却仍没想明白我该如何改变这无边的荒凉。奇怪的是我竟一日比一日更习惯了、一日比一日接受了自己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物种,我于是恬淡了,像植物、动物般不再失眠,醒或睡了多久早也忘了。渐渐地我阅尽了人间太多事:喜悦、战争、饥饿、贫富、贵贱、得失、欺骗……我的心里仍然虚空与落寞,但我宁肯虚空落寞着也把人间许多越来越复杂的事看得淡远。我翻转身体,不再看那许多争斗与不堪,渐渐地入了梦的佳境。一日梦中女娲告诉我那日她使我空有了思想,却没有人形,她担心有形有思时我会更苦,但现在她决定还是要赋予我形体,于是用她最后的神思与游丝之气。可让我成为一个人,拥有人的身体,我本该会被捏成一个美丽的女子,可是如今她的气已微,我只能是个男子,且无法解决我与生俱来的落寞,而且不同于常人的是,我的人生是“永存”的人生,说不清究竟何时我的生命才会终结,因为我有她的情绪以及作为不明物时天地给我的磨砺,因为我的耐磨,我自当“永存”。最初我为“永存”这两个字狂喜,而今我却莫名地怕这两个字,怕它们所代表的永久之外的意义。
一觉醒来我是了一位白衣飘飘的男子,英姿飒爽、体态风流。只是我的身旁没有了阴阳河,我在一片无边的荒漠之上,周围没有人,只有我,我渴望见到人,他们都该是我的兄弟姐妹。
正当我陶醉在新生的喜悦中时,远远地来了许多人,浩浩荡荡、烟尘漫漫。那个骑着高头大马的长得很难看的人掳走了我,我于是成了一名军人,明代的军人。我不知明代是何代,此时的人不再像兄弟姐妹,时时相残,令人心惊。
我们的军队在经过几次战争后剩下了不到百余人,生死在此处是个简单的问题,由瞬间决定。我们的军队在一片沙漠里与另一支军队相遇、厮杀。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厮杀,我问我近旁的兵士,他也不知道,反正来了,就得厮杀。这场战争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战死了,包括那个骑高头大马长得很难看的掳走我的人。遍地都是尸体,活着的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士兵,一个是负了重伤的忧郁少年,另一个黝黑而瘦弱,有张断不清年龄的模糊的脸。于是我们三人结伴而行,欲走出这无边的沙漠。缺少食物、没有水,我们苦苦挣扎,气息衰微。我们判断着方位而行,却总是望不到边,那个伤痕累累的忧郁少年终因体力不支倒在途中再也没有起来。那个黝黑而断不清年龄的人建议我同他一起食了这个少年的血肉再走。我抛下他,发誓宁肯饿死也绝不会如此,于是我抱着我萎缩的干粮——半块南瓜,独自而去。我不敢想象身后发生了什么,我不明白人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也许像最初懂得捕鱼与狩猎就足够了。
沙漠的白昼烁热无比,夜晚却是奇冷的,我甚至怀疑我将永远困在这里,直至死去,那个叫做“永存”的词看来敌不过生命中的偶然。走了多少天我已忘记了,恍惚前行的时候,我常以为此时是那个泥土之我的梦。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便啃上几口南瓜,太阳的暴晒与夜的寒冷几乎消耗掉我全部的体力甚至意志。当我的南瓜完全耗尽后的第某日,我竟开始想起那个黝黑而断不清年龄的兵士对我的建议,这个想起让我鄙视自己。
当我的气力即将枯竭的某时,我看见了远处的城池,像飘摇在荒漠中央的仙山楼阁,但却是虚幻的,与荒漠的无边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可是它此时是去处,唯一的。尽管渺小飘摇,却是奇迹,假象般真实地存在着,却不同于我的梦境,不同于我一路看到的那许多个假象,永远也走不近的假象。我甚至要为人的伟大落泪了,人竟在无边的荒漠创造了奇迹!显现几分荒诞,却仍是奇迹。
城里到处都是人,城里的人到处都是,然而不再让我想起“兄弟姐妹”。我明白,此时已不是人之初了,我感到行走的艰难,然而更艰难的是我的心不在此时,我是个古人,却已不纯粹。城市里到处都是建筑:有高大巍峨的宫殿、有雕梁画栋的房子、有密集的楼阁、有厚厚的城墙、有曲折的小巷……我头晕而目眩,我得弄懂这一切方可存在。然而我弄不懂,这不知是谁的思想生出的形象,高深莫测,铁铮铮地存在。
我在明代的街上行走,人们称这里为京城,我在京城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繁华。我成了一名测字先生,虽然之前什么是字我并不清楚,然而当我看见字的那一刻便明白那仅是符号,类似我很久以前看见的那些最初之人在石上、岩壁上刻画的那些,它们的形体浅显,却有隐秘的力量,譬如阴阳、譬如风火雷电、譬如金木水土、譬如天象、星月、譬如生死轮回……我似乎对这种隐秘的力量有着及其敏感的感知,甚至于熟稔,从一个人写出的符号,便可预知他的现在与未来。文字像我的旧识,让我参出它的意味,虽然我从来不曾写过字。
我像个仙人般白衣飘飘在明朝的京城,显得深不可测。人们从各处聚拢而来,让我测不同或相同的符号,相同的符号在不同的人手里便有不同的宿命,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便可测出不同的因或果。人们叹服我的预测,却又疑心我怎会如此之“神”?我亦解释不了。他们在别人身上信服,在自己身上疑惑。但市井中的普通人其实亦没什么可测的,末了无非是想知道自已是否可享荣华富贵,但荣华与富贵大多在前世已定了,今生已生在平凡巷口,便没有太多的可能。于是测字仅是测字,改变不了什么,苦的人还是苦的,劳心劳力,却多是力不从心,直至生命衰微也还是没能富或贵,但奇怪的是人们依旧对测算乐此不疲,似乎测一下、算一次就能改变命运。我甚至恨自己无力替他们改变什么。直至我倦了此事,每日仍有络绎不绝的人群拥挤在我的周围,拥挤在我新有的种满芭蕉的小小庭院。
我能测出别人的命运与未来,可是却测不出自己的,其实我知道这并不奇怪,就像一个人永远无法整体地直观自己。我知道不是所有表象都能找到其对应的因果,譬如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仍会感到长久的孤单,我想,这或许便是与生俱来。
我在为一位所谓的贵人测字时第一次邂逅了让我震撼的木器,那是用某人从西洋掠回的木料制作而成的家具:床、榻、桌、椅、几、案、插屏、鼓 ……那木种大约叫做紫檀及花梨,第一眼我便被其所撼,极简的造型与精良的工艺,深沉的色泽、幽远的香,光滑如婴孩的肌肤。看着它们,我竟有了欲泪的感觉,我被深深地吸引、深深地打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我成了一个木匠,和一帮木匠一起为这个贵人打造木器。我怀疑我除了测字更有做木匠的天赋。我成为一个木匠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师自通,完全沉迷在其中。紫檀的深沉、厚重、幽暗与光洁,花梨的舒展、沉静、纹理与疏密,我都给予其最大限度地绽放、极致地生发,看着它们在我的手中生出了新的生命,有了意境,成了诗,我忽然想起“思想”这个词,想起我初见建筑时的情境,瞬间我理解了建筑,理解了形式是思想的体现,理解了没有无缘无故的形,理解了许多无缘无故或许是瞬间对于思想的超越。可我却无法言说自己对于木器的感动,亦如我永远无法测算自己的未来。
我能为木器的一根直线条倾注全部心力,使其不止是直的,更是生动的直、有情感的直。我在直线条里找直中暗含的曲,找曲直间最微妙的变化,让呈现在眼前的直有了更深层的含义。我知道直到极致时是必然的曲,我忽然明白了相生,我赋予木料曲直之外的思索,让其犹如乐理般生出具象里的抽象,它们无言矗立,却如诗般凝重,亦如奇迹。我不断地生出激情与灵感,我在思维圆时更赋予方的刚健,我让一把圈椅圆得饱满而有气韵,让观者联想天圆地方,联想无限与无极。我在穿插变化里找疏密,一丝一毫的不同便会出现不一样的气息。我拿捏紫檀的韧性使其出现深思的意味,一张画桌因点线面的变化、刻镂雕饰的意趣,遒劲方直间仿佛一泻千里、痛快淋漓。我最喜作书架时的感觉:严丝合缝、整体的素工,却可以包容太多内容:曲直、遒劲、疏密、深浅、大刀阔斧、细致入微……变化仅在微妙间,却可出现完全不同的气质,只见它楚楚地立着,晨光中玲珑剔透,亦如美人,暮色中不知像谁的心,无言却高远,令我莫名泪如雨。难以相信那竟出自我自己之手,已然成形,令我敬畏。即便一件花梨笔筒,也在看似简单的圆里幻化出张力,圆成圆满、满成苍穹,圆满便暗合了宇宙与时空,无由悲壮。我为花梨的纹理感动,我想那是它的思考以及一棵木无言的心思,我讨厌别人称之为“鬼脸”,那是它的诗、它的画,是它凝结万象因思想变换出的形式,怎能谓之“鬼脸”?虽鬼脸意在言说变幻,但我不喜,它太表面。可是该称作什么,仍未想好,但我从不称它“鬼脸”。
我创意出了一系列直线条的木器:禅床、禅椅,以及云案、修几、文堆、八部、北棱、海窗……没几年,我的木器名扬四海,我结识了:陈洪绶、唐寅,甚至于倪瓒,他们不远万里只求一唔。我与陈洪绶合作了件罗汉床,他理解了我的方直变幻,他目光莹润,握着手中的泪竹扇良久无言,他说我要是作画一定会是个不朽的艺术家,即使我不作画也应如此,我的木器包含了情感乃至天地。他描画了一方熏炉,极富装饰性,由我来制作,我在一线一隔、一方一孔中提炼取舍、写实写意……我们在熏炉前如歌如舞,我看到了他目光的深处,那是心灵的恣肆与感动。
倪瓒是在某日黄昏抵京的,他的目像他画中的远水:悠远、清明。我们一见如故,他没有让我刻意去做任何一件木器,而是要了一张已完成的书架,他告诉我他知道我的心,我们在瞬间变得没有距离。周围的人永远也猜不透。他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南方?在那一处:有山、有水、有书、有竹。我笑了,问他要不要留下来和我一起面对紫檀和花梨,还有我种满芭蕉的小小庭院?他笑了。我们似乎相拥而泣,我开始遗憾女娲为什么让我成为一个男人,而不是那个美丽的女人。
我心里渐生莫名的滞,凝不住气,愈面对木器时愈如此,甚至于哀伤。我不知这是何故,却在清冷的晨或是长长地夜时心思不宁。
倪瓒车马的烟尘早已消逝在视线里,我注定了是一个男人,而无法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于是冥冥之中有女人向我走来,她便是楚,楚有美丽的貌以及清逸的文思,她不用她的文思也呈现灵性与意韵,初见时我竟比见到倪瓒的那一刻还要迷幻。可是楚不单是楚,她更是那个知遇我的贵人的女人,于是我们的爱情里充满了悲情,要么苟且地偷情、要么在月夜私奔、要么别再爱情。于是我们终日在纠结、思念、悲伤的情绪里。最终决定私奔。可是我却想做完那几件未完的木器。楚无语,开始静静地等。
我的木器里呈现出另一种气质,多了一丝本性之外的情感,却也多了忧郁,更出现一种无言的绮丽,我终日被这绮丽所抑,我有点理不清生命之外的扑朔迷离,于是在那次疯狂爱欲之后我试图放弃我的爱情,回归我内心的神圣,自然地去爱那些木。因为它们仿佛大于爱情。我那灵性的爱人,却在我还未显形的意态变化里仿佛早已洞悉,她从此卧床不起、气息奄奄。我追悔莫及,却于事无补。她终在某个秋日的黄昏香消玉殒。
我开始无限度地鄙视自己。我不敢、不忍想起楚离开时的样子,可是我无法不去想起。我知道我失去了什么,任谁再央求我也不肯再做木器。
我从此没有情绪再去对那些木,瞬间我失去了所有。
我匆匆回归我满是芭蕉的小院,芭蕉已枯黄了,它们在秋里日渐萧条,我不知生命里何为意义,爱似乎太厚重,远比我的想象,又太绮丽,不尽绮丽。我再也不碰木器,木器成了我的痛。其实我知道木仅是表面,有一个更深的痛无言无形的存在,它在我的内中,却不知在何处。
我著了一本《木理》来缅怀我的爱情,通篇在说木与结构,却其实只有我知道说的其实是我的爱情。奇怪此时我不再觉得孤独与虚空,却变得如沉睡般不会思考。我终日伺弄我的芭蕉,那仿佛是我的全部,密密重重在方形的院里,是一块方形的石绿。
有个叫紫的女人来找我,问我是否能帮她做张琴桌,奇怪我不知为什么竟答应了她,我想许是因为内心深处对于楚的愧疚和遗憾。她惊异我的芭蕉怎么可以长得如此的高大、浓密,好像院子里没有房子,只有芭蕉。楚未看见过我的芭蕉,但她知道那些芭蕉,她曾说担心那大片大片的浓绿挤满我的心,担心它们会随着时间逝去,担心它们萧瑟枯黄,担心冬日时我如何去承受那长久的清冷……那时她欲泪。她总是想让我带她来看那些芭蕉,可是我们却一次也没能来。如今紫站在芭蕉前,我竟疑心她就是楚,她有酷似楚的眉目,长而淡的眉,灵而秀的目,但我知道那不是楚。
我在紫的家中为她制作琴桌,他的父亲是京城有名的显贵,紫的琴技被奉为城中之首,她家有许多张琴桌,不乏名木,更出自名家之手,可是紫却不满,并说没有我的琴桌她就不抚琴了。她的双目一本正经,我发现它们澄澈明净,像极了楚,可是那不是楚,因这双眼目里没有那丝意味深长的忧郁。我不受控的对紫好,想要做一张最好的琴桌,可让我想起楚的琴声,虽然我一次也未闻过。遗憾的是我竟从未为楚做过琴桌。
紫是兴奋地,她在我工作时偷窥我,她爱上了我。她是个任性的孩童样的女子。我无心说爱,我如何还能爱得起来?我满心是对楚的思念与歉疚。经过这件事我重新认识了女人,女人纤弱的是外表,坚韧的是内心,她们可以不惜一切而去维护爱情,这让我无端的想起花梨。男人的目标不仅是爱情,却不像紫檀。
我根本不去回应紫的痴心,任她在那片繁花之外的春日阳光下站上一天、一月、甚至于一年。琴桌做好的时候紫便带着琴桌嫁了,我发现她凝望琴桌的样子仿佛在说她要伴着它一生一世,我发现她那双澄澈的眼睛生出了忧郁,那一刻像极了楚。爱一个没有回应的人该是何等之苦?我的心也开始苦,但仅是苦,不是爱。
我知道其实紫爱的也许是我的琴桌,而不是我,或者是我以及琴桌,可是这个事是需要两个人来进行的,紫要一个人来,便一定是苦的。我是个生命没有期限的人,我像是又背负了一份债,并要在她苦完之后继续替她苦下去。
我再次回归我种满芭蕉的小院。我没有朋友,我常是孤单的,我像那本古书上描述的虫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背负的愈来愈负重,却从不知把重物卸下去,愈来愈重,直至生命终结。我常回忆我是一块泥土时所经历过的日子,那时与此时似乎没有太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此时重负,那时我是个不明的物体,或者就是一块泥土,旁观世间的沧海桑田,以及人间的冷暖。而今我是一个人,却像在人间之外,体会为人的过程时却怕了为人,将自己与人间隔开,我甚至怀疑除了测字与做一个木匠,我不具备做人的其他能力。
我知道折磨我的并非仅是楚,或者更有与生俱来的深藏着的那些莫名与悲情。
我像个女人,有时竟伴着雨打芭蕉的萧萧之音落泪。我疑心女娲弄错了我的性别,可一切都已如此,仿佛自然。我知道我的猜想是错的,男人如何就不能哭?我于是放声我的伤悲,竟被自己的声音惊吓了,像忽然惊醒,忽然想把自己不管多长的人生过得好些,从我拥有了一个人的形体到我从战争中幸存、到我走出了沙漠、到我是了个测字先生、到我成为一个木匠、到我会了倪瓒、爱了楚、爱了木器、弃了木器,仿佛已过了许多年。许多年是多长?在我那所谓“永存”的人生里到底代表了多少?却如此之重。我不知活着的本质是什么,但活着也许大多数时候形同草木,也许只有激情与感知的那些许时间里算是真正的活着,也许有那些许已很幸运了。但活着一定不尽是活着、不尽是芭蕉、不尽是倪瓒、不尽是楚、不尽是木理、不尽是做木器或不做木器、不尽是死亡或永生……只是,我竟参不透。只是,我竟不痛。我想起打猎或捕鱼,我想起饥饿或寒冷。
我走出了我种满芭蕉的小院,室外的阳光是秋的,淡而轻,风也是轻的,透着即将的冷,街上的人如同戏里,各有各的角色,老人、孩童、女子、男子、少年、壮年、美的、不美的……有的着绫罗、有的穿布衣,发如乌云、翩翩而来,他们在秋日的轻淡阳光下做着自己,演活了。笑语、苦闷、白胖、瘦弱。此时我不觉得自己像个仙子,尽管我仍是一袭白衣,除了白我未尝试过其它颜色,但我也不太像是一个人,显然我已不是一块泥土,却仍是难以界定。我从每个角色旁走过,我疑心戏里根本没有我,我的存在有点尴尬,我仿佛不属于现实,当我不再测字、不再去当一个木匠时,我便失去了拥挤在人群中的人气,与一块石、一块泥土没有太多的区别。我忽然想把我不管多长的人生过得好些。可是我不知怎样方能过得好,怎样就算好。
显然我在人群中是不适的,可是我却不愿就此回到我种满芭蕉的小院,我在人群中如同寻觅,寻觅一个属于我的角色,我在人群中如同漂移,没有目的随处而去。
某日我在街上漂移,我清楚地看到紫正掀起帘子的马车从我身边驶过,我疑心那是楚,或者楚就是紫、紫就是楚。她正用眼睛深深地看我,却是冷的。我莫名地对她笑,直至她的车子跑远了,我仍在笑,当她的车子即将消失时,我忽然跑起来,跑着、追着、奋力地跑、奋力地追。她的车子合情理地消失了,我仍跑着。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看不见他们,我不停地跑着、跑着,我忘了我为什么要跑,我想,也许我只是想要跑。
转眼秋已逝,我的芭蕉日渐萧条,大片的叶垂下来,变成枯萎之色,成为最可视的衰败,有时却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透明的样子,显得奇异。我是这片衰败、奇异里唯一的活物,我开始尽责让自己的活气贯穿在这里,否则,将是可想像的死气。芭蕉成了干的草色,这样的衰败之气里很难会去产生太多希望。
我不知我在这里究竟是为了思念谁还是因为我无处可去,究竟是我不知我该做什么,还是这是我关于楚的方式。芭蕉枯黄了还会再绿、再枯黄、再绿,那不过是个简单的更替,而这个简单的形式却会一直如此下去,抑或像我般“永存”。永存的究竟是生命,还是生命里的荒芜?亦如此时写实的满园荒芜。我一直在为楚的逝去而苦,可是她不逝去我就不苦吗?我不知自己怎么会这样想,原来我是如此的不纯粹,又是如此的纯粹。楚是何等的空灵与智慧,难道她早就看穿了这些?或者她亦如我,亦为本质之外而苦?我知道许多事无非是个过程,看似繁华,却如这芭蕉般转换着枯黄与青绿,没有永久的如一,也没有永久的不如一,更替的是存在,连绵的是虚无。
我被自己的思路所吓,我在冬日无色的阳光下看自己的发如荒草般生发,在风里如奔流般起舞。我凝神窗外笑自己,笑楚,笑人间。
那么紫呢,她凝视那张琴桌的眼神可曾因为长久的凝视早已了悟?简单更替与变幻中她还是她吗?她或者不是楚。
那么陈洪绶、倪瓒呢?陈洪绶热情洋溢地描绘着他的绝色美人,描绘着他的美人坐在青绿的蕉叶之上,描绘着他的美人纨扇、轻叹、拈花、焚香、低吟、筝簧、古琴、忧伤……那么他该是愉悦的,但也许愉悦的是画,是画中人,那么他自己呢?他在长久的午后与无尽的冬夜从来不思考画之外吗?还有倪瓒,倪瓒在他的山水、林梢、河畔、孤舟、老树、修竹、与藏书间会深长地思索些什么?他的山水尽了,到了修为的尽头,满是思想与思想的荒凉,却是终了,也许他在水畔林梢的淡然里早已成佛了,因为他的笔端从来不轻言哀愁。那么他在更替与往复里,在他仗义疏财之后,远眺水畔与近旁的老树时,可曾有那日别时的泪?
或许谁都是孤寂的,谁也无法摆脱宿命里的虚空,虚空或许便是世界的本质,这个物的世界唯有思想没被物化时可以不称为物,只剩下了物还有什么?只剩下了思想岂不是空了?
关外的士兵终于攻破了城,人人都在战事的恐慌中,许多人横尸街头,不再如女娲造人之初时的自然与欢愉。许多房子着了火,许多人在街上哭泣,其实他们仍是我的兄弟姐妹,人这时表现出的是自然的本能,此时的本能弱化了往日非自然态里的某些放大,仅剩下了本能,于是变得纯粹而有力。我此刻想起了楚,仿佛回归至我最初倾慕她的时刻,还有我的木器,在清晨的淡淡日光下已然成诗。奇怪楚竟渐渐融进了木里,和那些木融在一起,再也分不清。
城里到处都是火光,我的小院也起火了,红黄的火苗蔓延至我的芭蕉,芭蕉像一棵棵火的花,奋力而奄奄一息地燃烧。火花与当空随处的灰烬与尘埃犹如漫天飞雪,漫天而来。我的芭蕉的火与花燃成绝美的模样,闪烁着让我想起了亘古的星空,我疑惑这是个梦,我仍是那块不成人形的泥土,伏于阴阳河之畔,长久的思量,长久的不思量,长久的梦着,长久的醒着,长久的忘了思量,长久的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瞬间,仿佛大雪嘶嘶,我忘了,此事时是存在,还是虚无。
责任编辑 孙俊志
实习生 李 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