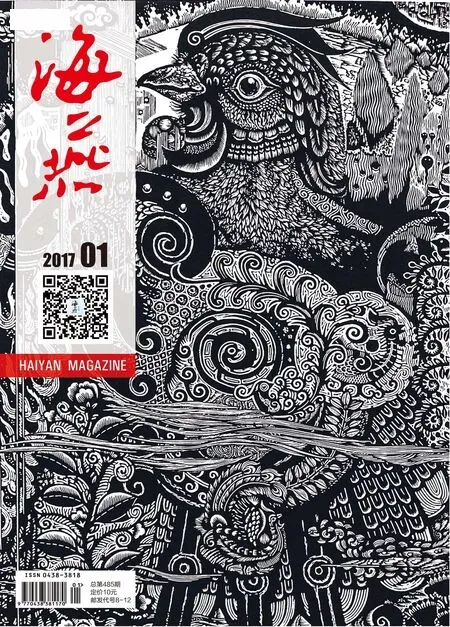剩女是个水疗师
□杨玉祥
剩女是个水疗师
□杨玉祥
一
北京街头,大小饭馆星罗棋布。民以食为天嘛!排老二的是各类按摩店。不信,你到街头溜溜,足疗店、美容美发店、养生会所、洗浴中心。说白了,餐厅是吃;称谓繁多的按摩店,本质上大同小异都是“摸”。
摸是简化了,全名称按摩。更准确地说应加上女子按摩。都是赚男人的钱。让男人心甘情愿地掏银子,当然得靠小女子也!如果按摩师都是男人,这些五花八门的店百分之九十都得关张大吉了!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不便把话说透,说透就没意思了。
店分三个层次。最次一等是路边小店,服务员大多是老板同乡,女老板亲自拿小姑娘操练一番,第二天就拿顾客当靶子,边学边干,干学结合。再说客人压根没期望服务多么到位,钱有所值,而是为了和小姑娘聊聊天,逗逗闷子。
再上一档,是一些连锁店。公司设有培训部,隔三差五把按摩师集中在一起,请老师授课,认识人身体上的穴位、经络。这些店一般冠以绿色店,严禁黄、赌、毒。不能因为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如果有涉黄情况被人举报,整个店铺被查封,几百万的投资就打了水漂。至于哪位按摩师被客人约出去吃饭、幽会,老板是不管的。这属个人隐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最高的一档是会所。客人都是办卡的,花现金的很少。这些店都设水疗室,不外乎先泡木桶浴,桶里撒满了五彩缤纷的花瓣,客人穿着一次性短裤,由女按摩师助洗、洁面、搓背,灯光昏暗,室内响着轻音乐。
沐浴完,客人躺在大床上,按摩师要做全身精油按摩。从后背开始,再到下肢、肚子、双臂、头部。按摩师都经过专业培训,模样高挑靓丽,小嘴柔柔地,不管是六十多岁老翁,还是二十出头小伙,一律“大——哥!”叫得你心里甜甜的、酥酥的、痒痒的。当然,客人得付出高昂的费用才可享用!
人有三六九等,树有花梨紫檀。按摩师更有高下之分。最差的是不知道脚下有啥穴位,只是抱着客人的脚瞎使劲;客人疼得龇牙咧嘴,按摩小姐累得满头大汗。
中等的按摩师都是上过培训班,拿到了毕业的小本本。明白人体有十三条经络,知道环跳穴、合谷穴、足三里穴、百会穴,偶尔还能查出客人那里不适,令客人赞叹不已。虽然按的都是穴位,但稍有偏移不准,客人就喊疼。按摩师就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客人便会附和说:“痛,并快乐着!”
最高一类的按摩师,只要一上手,你就能感触到与众不同。手法重而不滞,轻而不浮,刚中带柔,令客人如痴如醉,舒服感遍布全身。
邓华就是京城推拿行业小宇宙中名声如雷灌耳的女按摩师。
按摩行业收入差别是最大的,底薪一千元,剩下的靠自己了。给公司创的利润越高,收入也最高,上不封顶。一般情况下,谁收入越高,大家越佩服。凭手艺吃饭嘛,这是能耐。
邓华每月按摩提成3万多元,年收入40万元。
她出生在四川一个偏僻的小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地区一所中医学校,毕业在村里的小诊所当医生,也就是给村民治个头疼脑热。可是有的村民看病,还是拿不出现钱,讲究赊着,赊来赊去,连进药的钱都没有了。小卫生所只好关门大吉了。
人生一开始就为钱所困,所以邓华出来闯世界,就想多赚钱。问经多见广的人:“哪里挣钱多?”
“那还用说,北京呀!北京是皇都!”
“那我去北京。”
到了北京,应聘一家足疗养生连锁店。店里员工分两个组:足疗组、水疗养生组。她问经理:“哪个组挣钱多?”
“当然是水疗。”
“那我去挣钱多的组。”
有好心的姐妹告诉她:“水疗师多多少少沾点色情在里面。你一个小姑娘吼不住!”
“小心呀!别钱没赚到,就让人家给埋了。”
邓华咬着下嘴唇不吭声,仿佛前面是悬崖也要往下跳。
一切并不像姐妹们说得那么可怕。客人都是老老实实地享受服务,很少有图谋不轨的。感谢三年中医学校的学习,她深谙解剖学、经络学、针灸学,手法灵活、准确,客人不约而同地点她的钟。第一个月,她就领了七千元工资。点着厚厚的一沓百元大钞,她兴奋得满面通红,两眼放光。
二
口口相传是人世间最好的广告。一天,慕名而来一位客人,自称是位诗人。按摩完,诗人啧啧称奇,当即从书包里抽出一本自己的诗集,大笔一挥,在扉页上题了一句话:“妙不可言!你是一位用手做爱的人!”站起身,恭恭敬敬地送给她。
出于礼节,邓华双手接过这本装帧精美的诗集,羞红着脸,不知道说啥好。她还是个姑娘,可她毕竟二十岁了,知道诗人指的是中医推拿之术,是仅次于两性之爱,而又高于两性之爱的肉体享受。这本诗集,她一直藏在箱子底,别说炫耀,从来她都不敢给外人看。偶尔宿舍没人时,拿出来翻看一下。她知道这句激情四溢的话,是对她按摩技术的至高赞美。
这天,来了一位喝得醉醺醺、浑身散发酒气的壮汉。进入盛满水的木桶里,可邓华发现一次性短裤还放在床上,就问:“您咋不穿短裤?”
“别扭。还是不穿舒服!”
“不行。店里要求必须穿。”
“这里毛病怎么那么多。下次不来了!”
“下次来不来是您的事,短裤不穿我拒绝服务。”
客人只好无奈地穿上了一次性短裤,可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邓华。突然把她推倒在床上,手粗鲁地伸进红色裙子里扒掉她的粉色短裤。邓华为防不测,短裤里面还穿着一件粉色泳衣。壮汉傻了眼,他不知道如何下手才能脱下泳衣。
邓华慌张地问:“你要干啥?”
“我要强奸你!”
“啪——”邓华抬手一巴掌。她从小跟父亲练过武术。父亲曾获得省农民武术比赛冠军。
壮汉一下子被从床上打到床下,并在地下滚了两滚,窝在墙角。他捂着被打得留有五个清晰指印的脸,感到邓华那双纤纤细手,一瞬间变成小铁铲。他被打醒了,醉意顿消,不敢吭声,捂着被打疼的脸,傻傻地望着邓华,像一个办了错事,面对强悍的父亲吓得浑身发抖的孩子。
“姑奶奶靠手艺吃饭,不是鸡!找鸡到别处去!——滚!”邓华手指外面,瞪着眼睛,压低声音说。她那小脸已经气得刷白刷白。
壮汉一瞬间变得可怜兮兮地说:“姑奶奶,我错了!我是喝了点猫尿就昏了头了!”
“错了,就老老实实地给我趴上来。”
客人哆哆嗦嗦爬起来,像猫一样趴在床上,隔了许久才说:“没想到你不仅是按摩师,还是个武林高手。”
“没有点真本事,也不敢在水疗组混。”
推拿手法的发力方法与武术动作的发功方法是一致的。练过气功的人,手下的感觉会更加灵敏,准确地找出病变之所在,手法更加柔和、渗透,内气也会不由自主地发泄出来,手指所到之处,会有一股发热的气流在涌动。
会所里的女水疗师,刚开始是编成几号几号,叫八号,八号邓华就进房间服务。邓华讨厌叫号,理由是水疗师是人,不是监狱的犯人,或者部队的战马,按号排序。老板采纳了她的建议,她就给每个按摩师起了个响亮的诗情画意的名字:满天星、白月亮、紫罗兰。邓华喜欢满天星这个名字。在家乡,夜里抬头望天,星星是一堆一堆的,哪里像喧嚣的北京城,天气好时只能看见寥寥数颗星,那一堆堆的星星都淹没在污浊的空气中了。
客人来了,大堂的女服务员总是问:“贵宾您找谁服务?”
“满天星!”
有两个常来北京做生意的澳洲人,中国话几乎不会说,只会操着半生半熟的国语说:“满——天——醒(星)。”这二位只要来北京,几乎天天来找邓华捏。邓华反反复复跟这哥俩说:“按摩每周两次为宜,天天捏对身体无益反而有害。”说归说,这二位还是天天来。后来才知道,按摩这玩意,在澳洲属贵族消费,一般小商人消费不起。可到了北京,澳元换成人民币,那价码在澳洲人眼里,几乎跟不要钱一样。再加上邓华按摩的手艺,非澳洲一般按摩师可比,每次捏完神清气爽。
这天澳洲商人回国,北京的客户老板请客为他俩饯行,为了热闹,特意请来几个中国朋友作陪。菜一上桌,两人也不知道应酬两句,或为客人敬一杯酒,而是耷拉脑袋狼吞虎咽地吃饭,估计还没吃饱,就站起身对一桌陪客说:“你们吃吧,我们先行一步!”还没容客人反过神来,他俩就离席而去,把一桌客人晾在一边。
北京老板不好意思解释说:“他们捏去了!”
众人纷纷捂着嘴意味深长地笑。
北京老板说:“你们可别想歪了。这女水疗师的确捏得不错。客人几乎排得满满的。我有一位哈尔滨的朋友,让这女孩子捏了一次后,从此着了魔,特意带着老父亲到北京玩,住在会所旁的一个酒店,父子俩一前一后让女孩捏,乐此不疲。据说这女水疗师的收入,比她的经理高多了。
邓华每月收入是女经理的五倍。可一天工作下来,累得往床上一歪,一身毛孔汗透,四肢百骸都散了架,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沾床就呼呼大睡,呼之不应,睡得死死的。
女经理是养生会所闫总经理的干女儿。月初发工资时,她见邓华点着一沓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就生气,总觉得邓华是沾了她店的光。她的店开在各大部委之间,有钱人多。没有邓华还不是照样赚钱。
她蛮有心计,给邓华安排了一个徒弟,是自己亲侄女,天天跟着邓华学。半年过去了,估计学得也差不多了,就开始找邓华的麻烦。
邓华也看不惯女经理那张脸,仿佛欠她三百吊似的。她找到闫总经理,要求把自己调到郊区大兴店。大兴店是一个偏僻的小店,月月赔钱。
邓华走后,老板的干女儿乐得心花怒放,她亲自给邓华的老客户打电话,说邓华虽然走了,可邓华教出来一个徒弟,比邓华年轻、漂亮、按摩手艺超棒。
客人一个接一个来了,可又一个个叹着气走了,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女经理拉住一个客人问缘由,客人答:“如果邓华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空缺,此徒弟充其量算个老四了!”
女经理傻了眼,往常热闹的店前,人流空荡车马稀。她拿全店的效益工资,效益高则高,效益低则低。过去每月七千元算是拿不到了,勉勉强强给她开三千元。这还是看在干爹的份上。干爹责怪说:“有些人才,是可遇不可求。也不是想培养就能培养出来的。就像同样认识三千个汉字,有人写不出一篇语句通顺的文章,有人却用三千个汉字写出一本一本畅销书,年收入几千万元。这中间的差距可是千倍、万倍呀!”
她想厚着脸皮,把邓华请回来。可一打听,自从邓华一走,老客人不辞辛苦地驾着宝马、奔驰,穿越大半个城,找她去做按摩。公司业绩老末店,几个月后,一跃成为业绩最好的店。董事会隆重颁布:任命邓华为该店经理。按照邓华要求,她是全连锁店唯一不脱岗的经理。客人来了,仍然亲自操刀上阵为客人服务。
女经理肠子都悔青了。
三
邓华在京城一口气干了九年。由一个眼睛纯似一汪春水的女孩,变得动作沉稳,说话不紧不慢的靓丽女子。仿佛一个苹果,由青涩渐渐变红晕。母亲常来电话,催她找对象,并说城里没有合适的,就回家乡,随便找一个嫁了。
邓华这九年里见过各色人等,有追求她的,但语调很是轻飘,似乎是随随便便一说。店里有个男技师,见面总是说:“靓妹!我好想你!”“妹子,咱俩好吧!”邓华没有拒绝也没有说同意,只是淡淡地笑笑。
一天上午,邓华和男技师一起在房间打扫卫生。男技师趁她不备,一下子将她抱住,抱得紧紧的,嘴巴紧紧贴上去。那是她27岁的大姑娘第一次和异性接吻,全身一下子酥了,歪倒在床上。那技师上来就摸她的奶子,解她的裤子。她感觉一切来得太突然,就推开他说:“你要干吗!”
男技师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多好的机会,店里就咱俩人!”
“不行。没结婚之前不准干那事!”
“现在都啥年代了。你还挺封建!”
她把男技师推到一边说:“别人行,我不行。不办婚宴,不领证,不能干那事。”
男技师整整衣襟,鄙夷地说:“干咱们这行的,还假正经。”说完就往外走。
邓华一听急了,大喝一声:“站住。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假正经呗!”
“告诉你,我邓华不是假正经。我……还是处女!”她红了脸,埋下头。
“谁信呀!我还说我是处男呢。可在这屋子里,我和那些找我按摩的富婆,偶尔也风骚一下,谁知道呀!”
邓华气得瞪大眼说:“就你这样的,还想和我结婚,滚球去吧!”
“对不起,我说喜欢你,可从没说要娶你当老婆。干咱这行的,玩玩还可以,结婚白给也不要!谁知道她被多少男人睡过了!”
老父有个绝活或撒手锏,小时候每天早晨都跟着父亲抬腿猛击树桩。她能在一秒钟之内,抬脚踢对方脸颊;速度之快,对方都察觉不到脚在动;等脸被重重击中,倒在地上,都分不清是被啥击倒。内气蕴藏在脚丫上,击打在脸上有几百斤重量。
邓华今天只用一半的力量,一脚下去,男技师就横着飞了出去。不说是满地找牙,也是口吐鲜血,牙床都活动了。那小子咧咧嘴,想哭,可没有哭出来。他见邓华平静地站在一边,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男技师双手捂着脸,一声都没敢吭,跌跌撞撞地推开门,跑了。
屋里剩下邓华一人,她顿感满腹委屈,流下了泪!
九年来,有几个大款跟她说:“你赚钱太辛苦了。跟我好两年吧,当我的专职按摩师,一个星期给我捏一次,我一年给你一百万。咋样?”
邓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说:“不咋样!”
还有一个温州老板,开一辆七系宝马。白色宝马在会所门前一停,是鹤立鸡群。邓华送他出门,随口说:“你的车真漂亮!”
“喜欢吗?”老板问。
“喜欢!可买不起。肯定不少钱吧?”
“150万吧。”
邓华装作夸张地张大嘴巴。
老板把嘴凑到她耳朵边说:“当我的情人吧?一年,就一年。我就白送你一辆。怎么样?”
邓华仿佛没听见,笑而不语。
她曾把这一切偷偷跟闺密说了,她们几乎都说她太痴了,有这好事干吗不上。并指出小燕、小娜、小玲,被某某那个老板包了。邓华一琢磨,也是。这些小姑娘每月收入一千来元,可浑身上下穿的都是名牌。速递公司隔三差五来给她们送网上订的高档化妆品、法国香水、进口面膜,每一件都是几百元。收到了也不珍惜,随便往宿舍一扔,仿佛那钱是大风刮来的。
邓华淡淡地一笑,对这几个女孩赚钱方式不屑一顾。她平静地说:“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
“劳动赚钱最光荣!”这是邓华父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四
邓华悄悄地去了婚介所,交了八百元登了记。在职业一栏里,她写下按摩师;收入一栏里,如实填写“月入三万元”。
女工作人员看完填写的内容,犹豫了一下说:“我建议职业填美容师,收入写八千元就行了。”
邓华固执地摇摇头说:“我没有干过美容师,我只会按摩。干吗要说假话?”
工作人员欲言又止,把邓华的照片和资料收下后,就让她回去等消息了。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消息。邓华沉不住气了,来到婚介所打探消息。
女工作人员说:“我们重点推荐过你。条件好的男士,对你的模样感兴趣,拿着你的照片反复看,可一看你的职业都叹口气,摇摇头。条件差的,对你的收入感兴趣,可一看你的职业都放弃了。
”为啥?“邓华懵懂地问。
”社会上对按摩师这个职业还是有偏见,我还是劝你职业写美容师,收入也别写那么高。”
“为啥?我的确收入那么多。”
女工作人员优雅地笑着说:“没办法,你要面对现实。美容师一般服务顾客是女人,男人都喜欢。”她想说,那天她走后,几个工作人员拿着她的资料议论,都不相信她年收入这么高。大家一致判定,她除了给客人按摩,还顺便提供其他服务。直到一位五十来岁的光棍大叔翻看资料,看见她的照片说:“这可是名震京城的女按摩大师,找她按摩要预约,不然你大老远去了,她在上钟,后面还有几个在等。”
她还想告诉邓华,婚介所里鱼龙混杂,有一个专找富婆的男人,既骗钱又骗色。已经有几个女人来婚介所告他的黑状。他曾拿着邓华的资料,眼光在年收入四十万一栏上转了几转说:“这位肯定是专门吃男人饭的。像我这样的,还不是白骨精遇上孙大圣!”
工作人员说:“看来你也有怕的。”
“同行是冤家嘛!”
工作人员想把这一切告诉她,又怕引起有点偏执的邓华愤怒。好心办坏事。
邓华想起父亲常说的话:“咱们练武之人,为人一定要有浩然正气。像当年武松杀了狗官,可以一逃了之,可他还要在白墙壁上,蘸着仇人的血迹,写下‘杀人者,武松也!’”
邓华眼前常常闪现武松挥动手臂写字的英姿。如果问邓华姑娘最崇拜的男人是谁,武松当数第一。
她坚定地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我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我压根就是一个水疗按摩师,为了找对象,就说自己是美容师,这违背我的道德底线。”然后转过头,走出了婚介所的大门。
邓华父亲去世了。母亲孤身一人,无奈她写了辞职报告,说要回到四川老家。闫总经理说要给他几天时间考虑。
周末,总经理把她请到一家餐厅,特意点了几个川菜,一瓶剑南春,邓华不会喝,他就自斟自饮。
闫总经理有着一双细长的眼睛,线条纤细的挺直的鼻梁,闭上嘴,薄薄的嘴唇绷成平直的一线。怎么看,也不像拥有千万资产的老板,倒像个教师或者医生。
“酒后说真话。”总经理喝得脸通红,有点结巴地说:“你在北京待了十年,还没长大,骨子里还是个农民。”
“怎么讲?”邓华懵懂地问。
“眼睛里就是一亩三分地。我要有一双你这样的金手指,早就自己开店了,哪里轮上我足足剥削了你十年。”
“我这人就知道干活吃饭,没啥野心!”
“所以我是舍不得你走。你辞职报告一递上来,我就派我干女儿去你老家调查。你的家乡在山区,手机信号都没有。她是按照老乡指点,爬到高高的树上才跟我通了个电话。不就是村里答应还让你当村卫生所医生吗?每月工资才五百。够啥?我都为你屈得慌!”
邓华一听说闫总经理秘密调查她,事先也没有和自己打个招呼,一下子有点生气地说“村医也是医生,而且比女水疗师好听多了!”
总经理微笑着说:“我知道当医生一直是你的理想。你枕边放着一大本厚厚的《乡村医生手册》,十年间都被你翻烂了。”
邓华不吭声了。看来总经理早就通过宿舍姐妹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一瞬间,她脸微微发热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现在是剩女,城里找不到对象,只好回村找了。”
“回村找你只能找个农民。”
“我也是农民。我父母也是农民。农民有啥不好?”
“人往高走,鸟栖高枝。”
邓华愣怔了半响,垂下头。
闫总经理挥挥手,直来直去地说:“我想再开一个店,一家中老年养生店。我投资二百万,你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同时任经理兼技术总监,你只需要培养几十个水疗师。你这双能赚钱的手也该歇歇了!”
邓华不动声色地静静地说“我拿不出一百万。”
“不用你拿一分钱,你这双手就值几百万。店名我都想好了,就叫金手指。”
邓华没有吭声。换别人,早高兴得跳起来了,她却陷入思考、沉默之中。
总经理给自己又斟了一杯酒,凝望着邓华说:“还记得找过你按摩,并送过你一本诗集的诗人吗?”
邓华点点头。
“他死了!从十多层的楼顶跳下来了。”
邓华瞪大了眼睛。
总经理叹息了一声说:“我们俩是发小,从上初中我俩就迷上了写诗,都幻想着当一名诗人。可写到三十岁了,彼此仅在报屁股上发了几首短诗。编辑说我们有才气,再努力几年,就是顾城和北岛了。他欣喜若狂,辞了工作,一天到晚在家里写。写得昏天黑地。我是写着写着发现苗头不对,大家都忙着挣钱了,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店关门倒闭的越来越多。我觉得人们有钱了,就忙着追求享受了。我东拼西凑开了个足疗店。我那位诗人发小指责我堕落!钻钱眼里了。可后来我当了老板,买了房子和车子,还娶了一位在大学里教书的漂亮老婆。可他连自己都养不起,伸手跟父母要钱花。更别说结婚、生子。人都四十了,除了会写诗,干啥都不会,他也不屑干。”
“那也不应该自杀呀?”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总经理喃喃地朗诵着这首古诗。
彼此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俩人都泪流满面。
过了许久,邓华说:“我答应村支书了,不能诓人家呀!”
总经理点点头说:“你先回去。我相信不出半年,你会回来找我!”
邓华耸耸肩,不置可否。
五
邓华家的宅子曾是村里的标志性建筑,设计图纸是邓华当年客人中一个留过洋的建筑师无偿提供的。客厅、厨房、卫生间,都是21世纪最新潮,尤其是二层房顶,有个移动天窗,阴雨天不动,晴天一摁遥控器,铺着红泥瓦的屋顶,缓缓错开,露出十多米宽的玻璃,阳光瀑布般地倾泻下来,硕大的屋子洒满阳光。
邓华是开着一辆奥迪车回的家。在京城是一般的,可在偏僻的乡村,可是公认的豪车了。乡里乡亲好奇地问:“干啥营生,赚这么多钱?”
“按摩。”
村民们摇头。
“水疗按摩!”邓华笑着说。
男人们不吭声了,女人们仍然问:“那能赚多少钱?”
“一月三万元吧。”
女人张大了嘴巴,也不吭声了。
邓华母亲忙着给女儿张罗对象,她找来几个媒婆,怪的是一个个答应得挺好,可都迟迟没有消息。终于一个媒婆给介绍了一个,邓华去见面,不一会就跑回来了,脸气得铁青,气哼哼地冲母亲说:“你是给我找对象还是给你找对象!”从此连续几天不和母亲说话。原来媒婆介绍的对象五十来岁,死了老婆,还有一个仅比邓华小三岁的儿子。头顶都秃了,像一片开阔的原野。
母亲呐呐说:“过去村里几个年轻的,托媒婆到咱家提亲,像苍蝇见了血,赶都赶不走。你一回来,不知咋地,都不提这档子事了。”
邓华心中咯噔一下,她想起婚介所工作人员一再提醒,职业一栏上,要写美容师,不要说自己是按摩师。可她觉得都是父老乡亲,没必要说瞎话。
她叮嘱母亲说:“我是找对象,不是找大叔。也不想一进门,就当后妈。那样,我宁可当一辈子剩女。”
“啥叫剩女?”母亲瞪大眼睛狐疑地问。
“就是女光棍!”邓华的语调有点凄凉。
母亲眼圈红了,自言自语道:“自古只有剩男,没有剩女。啥时有了女光棍了呢?”
这天晚上邓华母亲上楼睡觉去了,她一人在客厅看书。忽然听见一阵断断续续的轻声呼唤声,她站起身走到门口,见门底的缝隙中塞进一张50元人民币。同时一个粗重的男中音说:“听说你是京城头牌水疗师,城里人能享受,咱是同乡,也想沾沾洋荤。”
她想把伸进的50元踢回去,可又一想,老乡们说得也不无道理,城里人自己能给服务,老乡们就拒绝服务了。
“不行,你这钱太少,不够。我在北京做一个活是五百元呢!水疗属于高消费。”
“咱是老乡,你就给咱优惠优惠。再说在咱宜宾市做水疗,也就50元嘛!”
一句“老乡”让邓华的心软了一下,再说几个月没有给客人做水疗了,一种职业习惯,使她浑身上下似乎憋足了劲,也正好在乡亲们面前展示一下。
她拉开门,见是本村上学和她同年级绰号叫“二愣子”的同学。她笑了一下,指着卫生间的门说:“你先进去准备准备,准备好喊我。这钱你收起来吧,今天免费。下次要揣着五百元来,本姑娘按摩从来不打折。”
“二愣子”嘻嘻笑着从地上捡起钱,装进兜,进了客厅旁的卫生间。卫生间是邓华设计的,喷水头下放着大大的紫红色木桶。
一阵“哗哗”的放水声停止了。里面有人喊:“水放好了!”
邓华进了屋,淡淡的水蒸汽中,只见“二愣子”躺在木桶里说:“皇帝浴!俺也享受一下!”
邓华取来一袋干花瓣,想放进木桶里,愕然看见二愣子光光的身子泡在木桶里,立刻怒了,抬手就打了他后脑勺一下说:“咋不穿短裤?耍流氓呀你!”
这一巴掌力度很大,打得“二愣子”眼冒金星,疼得龇牙咧嘴,好半天才喘口气说:“我在宜宾市也洗过一次水疗,就是不穿短裤的嘛!”
“甭骗我。我在北京严禁不穿短裤洗。八成你去的是鸡窝。”
“是正规水疗嘛!不信你进城看看嘛?打啥子人嘛!”“二愣子”满脸委屈。
第二天邓华开着车进了宜宾市,来到一家金水族水疗养生馆应聘水疗师。这个计划让她兴奋,有点像皇帝微服私访。
她把自己说成是啥也不懂的山里妹,老板安排一个叫阿芳的水疗师带她。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点了阿芳的钟,阿芳带着徒弟进去服务。水疗室是一间屋隔成里外间,里间靠窗户处摆个大木桶,木桶对面摆个牛皮水床,外间屋是一张大按摩床。
阿芳帮助客人脱衣,像一个玉米棒子,剥下一层一层的皮,露出光秃秃的白色玉米。白晃晃地大男人似乎对哧溜身子习以为常,躺进木桶里,舒服地闭上眼睛。阿芳为他洗头、洁面,她那双纤纤细手划过客人身体每个角落,当划摸到客人双腿中间,男人敞开双腿,脸上出现迷醉的神情。阿芳心领神会地把手在那个神秘的地方多停留了一会,然后才示意他从木桶里出来,自己爬到旁边的水床上。
怕客人冷,阿芳打开浴霸,水疗室被照得贼亮。她给客人搓澡、打肥皂,上下抹几下后,用喷头冲洗干净,再用毛巾擦干。令邓华惊愕的是,阿芳像女仆人一条腿跪在地上,悄声说让客人微微抬下脚,亲手给他穿上一次性短裤。客人眯起眼睛说:“花钱当回爷,——值!”
阿芳搀着客人走出洗浴室,躺在外屋大床上,开始精油按摩。
阿芳忙着干活,没有注意到旁边的邓华,看得是心惊肉跳,满面桃花。她休息时告诉邓华,“刚干水疗师时,觉得别扭极了,操作几次,就放开了手脚。洗了这么多‘鸟儿’,今后什么样的男人咱都能够对付。”
邓华听完也抿着嘴微笑。阿芳却得意地哈哈大笑。
邓华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男人们一听她是水疗按摩师,都像避瘟疫,躲之不及。店家为了打通客人享受的神经,啥都敢干。这店要在北京早查封了。这里天高皇帝远,只要没有“打炮”,就美名曰:绿色店。
邓华问阿芳:“你结婚了吗?”
“没有。一直忙着赚钱,按说,25岁了,也该了。我妈常来电话,说在村里帮我寻了一个,让回去见面呢!”
“天天见这么多的‘鸟儿’,哪个男人知道了,也不敢娶你呀!”邓华故意这么问。
“我傻呀!我才不说我在市里干这营生。我会说我干美容师或者在商场卖货。”
“那你说瞎话。跟你父母也说瞎话吗?”
“那当然,亲娘老子也不能说呀!说了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
仿佛一声炸雷在空中炸响,邓华目瞪口呆了。
邓华回了村,从此再没有说过自己在京城干过水疗师。村里哪家孕妇临产,她穿着白大褂,忙着接生。孩子呱呱落地,她满脸汗水,用衣袖擦汗。产妇婆婆、丈夫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谢谢邓医生!”听到医生的称谓,邓华甜甜地笑了。
晚上从卫生所回到家,吃着母亲做的饭,她给母亲讲一天的见闻,那位大伯吃了她开的中药,病痊愈。堂屋的小饭桌,母女碰膝而坐,娓娓而谈,听者不厌,讲者不倦,时而嬉笑,时而捧腹。
邓华家门前有塘,屋后有林。大门两旁还挂着父亲生前写的对联:青山一居室,碧池一老翁。
令村民们敬佩的是,乡长和乡党委书记都晓得她医术高明。一般领导们只需要一个电话,村卫生所的医生就会颠颠地跑上门服务。邓华一接电话,对方说:“我是乡长,找你们邓华医生看病。”邓华说:“她出诊了。不在!”啪,挂断了电话。
三年过去了,卫生所门口忽然响起汽车喇叭声。闫总经理和那个男水疗师下了车,见到邓华闫总就叹一口气说:“真难走!下了高速走柏油路,下了柏油路走石子路,下了石子路走坑坑洼洼的土路。”
邓华忙着沏茶倒水,总经理迫不及待地说:“我们是来接你的,连你母亲也和我们一起走。北京那边的房子我都准备好了。”
邓华平平静静地说:“这里的乡亲们已经离不开我了。我也觉得住在山里空气好、水好,吃得菜呀米呀都是自家地里产的,绝对绿色。”
这话让闫总经理一脸兴奋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站在旁边的男水疗师蔫蔫地说:“小邓,你回了家,我才从闫总那里得知你的一切。是我错看你了。我其实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姑娘。你要同意,咱俩现在就领证结婚。”说完他跪下一条腿,从兜里掏出一个精美盒子,打开,举到邓华面前,那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
闫总经理指着小伙子说:“他现在是我们彩虹城店的经理了。在北京有房有车。店里许多女孩追他,可他这两年一直想着你。他说:‘就想娶一个面对豪车和百万巨款不动心的姑娘。’”
邓华垂下头,望着那大钻戒,红着脸说:“你要想和我结婚,就留在大山里吧。我已经舍不得离开这荷塘,这竹山了!”
男水疗师听到这句话,木讷地望望邓华,又望望总经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邓华取过那钻戒盒,扶男水疗师起来,说:“谢谢你的好意。”她把盒子放进男水疗师兜里说:“女人不嫁,而内心安宁,是一种特殊的福分!”
他们失望地无功而返了。一路上默默无语。男水疗师呐呐地说:“我真想不通了。放着大把大把钞票不要,宁可回村小敲小打。”闫总经理若有所思地说:“这叫各有各的活法。咱们在德国有个分店,招聘当地技师。其中一个应聘者,是当地大学教授,他把工作辞了,干按摩师。就两个字——‘喜欢’。”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乡村女医生邓华依然单身一人……
责任编辑 孙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