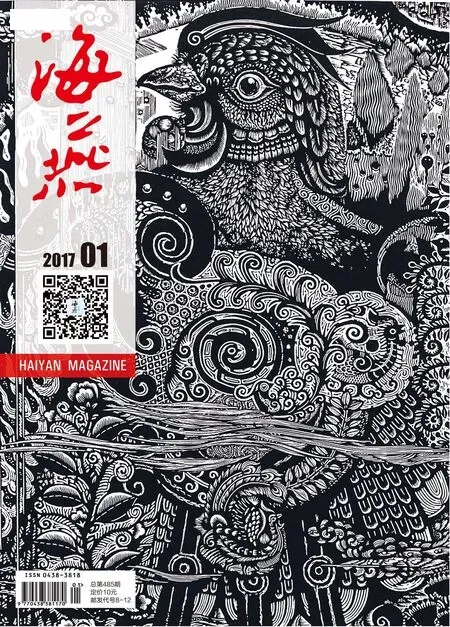唐诗境界辨说
——读《唐诗选注》
□徐牧心
唐诗境界辨说
——读《唐诗选注》
□徐牧心
读诗大概最艳羡的是盛唐诗人,有风作陪,逐日而行。有时阅读也是在安顿自己,找一种寄托,尤其当现实的种种压迫逼仄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则更喜欢寄情于盛世人语,人人得意饮酒并自留其名,如此也可梦回盛唐,迷失在飞甍鳞次的长安街上。
可到底身处世间种种樊笼之中身不由己,才做了一两的梦就有八斤现实等着啮人入腹,于是我们看到那个盛世的诗歌同样可以悲伤而深刻,宏大又不失细腻,话至沧桑处似乎拨开盛世铺就的一层薄纱,透露出思想的光华。
一.源水
历数唐诗中震撼过我的大场景,发现大多与明月有关。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挥毫泼墨间,似乎看到诗人独自铺张苍天,奔跑,以仰望星辰为生。
是夜中秋,月圆之时众星隐曜,致电好友,想询问他是否也跟我一样,仰观着同一轮圆月,竟隐隐有“天涯共此时”的气象。我想了想又咽了回去,总觉得有什么不够,这种不够不仅是情绪不够,没有足够激荡的情绪可以让心胸容纳下整个天涯,也没有一个让人自信满溢到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大背景,因此这句话做不到脱口而出。此间万钧气势,文人与豪杰的界线已然模糊,短短五个字竟如平地惊雷般突兀炸裂开来。
对于一个经典的诗句,我们常常会把它从几千年前的背景中抽离开来,可这半句诗中的气势何其恢宏,让我欲援引前人的句子时都感到无比心虚。
然而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盛世的平庸”一节中说:“诗歌最辉煌的盛唐,恰是思想最平庸的时代,思想的深沉多以社会危机为代价。” (葛兆光《唐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版 ,新序 第5页)
恰如韩愈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盛唐的豪气是声震寰宇的巨响,因他们总有“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太平富庶做底气。但是吼出来了,人们震撼完了也就完了,余韵绕梁是绕不过三日的,中晚唐诗歌虽总被人诟病绮靡,但同是写繁华,未知身死处的诗人看到的是当下的繁华在版图动荡后会怎样满目疮痍,正如同他们看过当年开元的盛世景象,又曾是宫廷歌宴的宾客,亲眼所见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读个中人诗,只感觉繁华如同过眼云烟,而悲凉才历久弥新。
“当那八个醉的一个醒的诗人随着繁荣时代的结束走进了历史,唐诗也渐渐变得沉思和深刻。”(葛兆光《唐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同是明月,北归无望的杜甫流寓江汉,疲惫不堪中仰望苍穹,不禁悲从中来。年过半百,月亮也似乎老了一轮,竟不似顽童年代那个随人行走的白玉圆盘。此时他说“永夜月同孤”,似乎人已久立成树,永远地在绝壁断崖之上与月亮两厢对望。
可他到底困顿落魄之际还能有明月同行,他们不是瞻仰与被瞻仰的关系,它无言安慰,只同苦同悲。不得不承认,毕竟是大唐诗人,即使有孤独也凛然大气让人不敢生起同情之意。毕竟是大唐之音,尾音处竟隐隐有当年盛世的金玉之声。
诗圣写诗,宅心仁厚,兵吏老妪尽可入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旁观者却也同是流亡颠簸人的最深沉的同情。所谓圣人,即使在自己都衣不蔽体的情况下心之所系的还是天下寒士。人们年轻时期大概总喜欢李白多于杜甫,总觉得杜诗措词过于严谨工整,即使有澎湃的情绪也被拘于一处,理性和“致君尧舜上”的使命感完全禁锢了中国式的酒神精神。读杜诗似乎感觉他从来不会喝醉,沉重的沧桑感坠在手腕上拿不起酒杯,因此心尖上的悲苦隐没在字里行间不见踪迹。
于是相比之下则更爱中晚唐诗,好像他们喝的永远是那几两浊酒,说的永远是醉中人清狂之语,只是读至沧桑处,也觉其呕心沥血、字字啼血。
金陵乃六朝旧都,至唐只余枯堞寒垣,自古路经此地之人,莫不感于疮痍,留下吊古之作无数。刘禹锡来时看到人事已成历史,亘古不变的只有潮打空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便恍若天成,竟使“后人无复措词矣。”李白写《苏台览古》有云:“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而刘禹锡不加“只今唯有”,一切沉痛都被包含在“旧时月”中,境界尤显浑厚深远。刘禹锡一生人事波折,而这苦难于他磨合成了什么,大概也都包含在一句“旧时月”中。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只怕我配不上我所承受的苦难。”
同是金陵吊古,杜牧来时已是朝代的尾声,盛唐被虫蠹的消瘦骨架瘫坐在昔时王座上。大概也是感觉到这个式微王朝已经衰落到了谷底,杜牧才会把《玉树后庭花》写进诗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是夜,秦淮河上寒气侵骨却蓦然听到这亡国之音,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在这漫漫寒江之上,寒彻骨髓之后的情绪沉淀下来,此时自省,思想开始变得深刻。这无限沉默的悲伤,无限悲伤的沉默,读来仿佛已身在舟头,在这靡靡之音中,望见一个金玉王朝最终的轰塌。
我之认为历史写到的永远只是真相而不是真实。写一场朝代更迭也不过寥寥数字“哀鸿遍野,饿殍在路”,轻描淡写如同小说家言。唯有读诗,感同身受之中才能知道真正身处其间的人们遭遇的到底是怎样一场动乱,其间令人绝望的悲苦,让几千年之后的读者共同震颤。
繁华可以没有极限,没有边界,递减下来的任何一种程度只能反映出这时的不繁华或者不够繁华,不由悲从中来。因此悲痛是文学永恒的话题,生命永垂不朽的主题。
二.绝顶
“孤独是指在个体生命过程中,所毅然持守的特立独行并具有出色价值理想的精神状态。”
作为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人最高贵的状态是孤独。
先秦诗古拙,总觉得到陈子昂一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境界始大。后人通常解释此诗为怀才不遇之作,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皆解释为贤君明主之意。后人奉陈子昂为诗骨,这支撑起词句的奇伟风骨又怎能是怨怼自伤的软绵绵的情绪;这气势如巍巍高山的一句又岂是人间君王的赏识所拘束得住的。这一句不加修饰,茫茫天地纳入他胸怀,这幽州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夹在水晶句中闷声叩我额头。
孤独不是缠绵悱恻的情绪,相反,孤独的思想者在心游万仞之中,恍然间灵魂可站在肉体攀登不到的天阶之上。千年之前独上高台的陈子昂会不会突然似灵魂脱离肉体,俯视人事代谢之中,它独自站在中点无人问津无人同行,这巨大的孤独中同时也有巨大的自负——他是这历史上不可替代且独一无二的逗号。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我们常常会得出一个让人心酸的结论。即很多时候天才的作品在后世才能成就他的价值。杜甫在他的《不见》中说李白虽自命楚狂人,实则却是佯狂,他说他实则可哀,“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这样对挚友的同情读来让人心酸,这友情坚固而不可摧毁,二人就像结伴亡迹天涯的放逐者,诗是最本质的内因,而“世人皆欲杀”的境遇让二人不可分离。
佯狂毕竟也是狂,李白在写“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时绝不消沉低迷,但我仍觉得那首诗如在皑皑冰原上挥笔写就,漫漫风雪仗剑独立。所谓孤独,它可以不凄迷,尽可以昂扬。无论他哭或笑,呼朋唤友或千里独行,孤独是一种心里的状态而不是身边的状态。
李白温了一壶酒,对酌苍天,与日月星辰为伴,尽管他说自己是月下独酌。因此我一直反对有赏析解这首诗为凄凉,一个孤独的诗人,他的孤独中尽可糅杂进悲伤,但他从不凄凉。他从不凄凉,当世人对日月行叩拜之礼时,他正在月上醉酒。每舞时便有影作陪,每歌时便有月唱和,他一夜行乐,与月亮结的是无情之游,所谓无情之游,蒋勋在《说唐诗》中给出了解释:“这种无情之游就好像是月亮与影子的关系,星辰与星辰的关系,彼此不过是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转,如果碰到了是一个意外,不碰到,那它本来就是如此。”(蒋勋《说唐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 页)孤独是灵魂的一次出走,而无情之游,使行者没有行囊,也就没有背负,尽可以使心游万仞,使盛唐十分醉意酿成七分月光,却来往匆忙不留牵挂。
此间,在人心里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命个体,他不依赖天地,他与天地结伴并行。
如若以情致来论,则首推柳宗元的《江雪》,其绝妙之处不仅是千山万径中隔绝一切的冰雪之境与孤翁独钓的如画之景。诗句字里行间中的寒气冻结,所有个人的情绪如佛家入定般“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这一瞬间竟忘声忘形,忘物忘我,其间气势威压如大音希声般的静谧天地,使人忘记苍茫中渺小的自身。这一种莫可名状、莫可理喻的孤寂只能浸在短短二十字犹如佛家偈语的白描中,言深而意远。
然而物极必反,当末句“独钓寒江雪”把孤独感推演至极致时,所描摹的已经成了个人的超脱。人把自身超脱出尘,恍然凌于绝顶之上,俯视云烟里的芸芸众生。
孤是王者,独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王者必须永远接受孤独,他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认同,更加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王者可以在很平静的环境下独行。
正如悲痛让思想变得深沉,孤独同样把思想淬炼得深刻,在孤独者创造出的与外隔绝的世界里,思想得以不受干扰地行驶。其实有些植物不是向这个世界要求阳光和雨露,它要求的是根茎生长的空间。
在人类上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正是思想让人有别于天地诸多生灵。终有一日,人类将会在独自求索中登上绝顶,即使宇宙欲将其毁灭,他们仍是万物灵长,只因为知道自己行将死亡。正如帕斯卡尔所说:“我们的所有尊严就在于思想。”
三.长空
《人间词话》首句就是“词以境界为上”。
而境界又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徐调孚.《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华书局,2009.)在物我两忘这一古代美学概念中,我所观的客体与我之主体浑然两忘,在这恍惚失神中已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了。
后人推崇王维为诗佛,说王诗无情,一字一句都不食人间烟火。王维爱用“空”字,尤爱空山,如“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空山不是空无生物的山谷,只是朦胧山色在有无之中的山景。而这空字也并非了无情绪,就像人生的最后一重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大概当很多情绪、阅历、思想还有在山水中找到的归属感趋于饱和的时候,就是一种“空”的感觉,恰似当所有颜色的光重叠在一起时,最后显现出来的竟然是白光。
王维一生并未有过太高的官职,甲子年做尚书右丞也不过正四品下。我想这在古代也算是种极好的人生了,他既不是位高权重,要处心积虑步步为营,也不过于人微言轻,生活上啼饥号寒,比起李白与杜甫半生多舛也算少有波折。人说人生三境界用佛家偈语来说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王维总算从变节伪朝的波折中全身而退,命运给了他安稳的晚年,让他可以寓情山水参悟人生最后一重圆满之境。
苏轼评王诗“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在短短二十个字限制之内,句有尽而意无穷。在不读王诗很长时间之后我还能记得他写《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自落。”后人以李杜为大家,高岑为傍户,然而李白诗大气潇洒,诗里时有瑶台仙境而非凡间景色。杜甫七律精致整饬,通篇严肃低沉。而王维只写清泉、空翠、一只山鸟、一株红萼,大概其中自有圆润的穷通之理修饰,虽直白却从不粗糙。如此身在画面之外,像是个背包过客偶然驻足,望见这一谷红翠,不由失神忘返,他此时只感觉心中愉悦,这愉悦中不掺杂任何复杂的情绪,这种愉悦只缘于人生于自然、长于自然,与之骨血相依血脉相连,与这样静谧而动人心魄的景色浑然为一。这种愉悦无法用语言形容,任何格律与韵脚都变成脚镣手铐,因此他只用笔画了幅水墨,什么多余的笔触都不要有,只不过是这个无人的空山,一枝红萼正独自开落罢了。
宋代禅宗将修行分为三个境界,与后人王国维整合的人生三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一境界是韦苏州的“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二重境界“空山无人,流水花开”,及至第三重“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一朝风月是万古长空的一点一段,然而在一瞬间悠然心会,这一株小小红萼也在瞬间拉伸成万古长空,何其壮大却无言的心境。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这妙处难与君说,妙处不可言说,这是一种不可描述的实在,法空中存在物的妙有。似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的乐道境界中,人已把悲伤与孤独摒弃在身后。当人已忘记有自身的存在时,他便已与眼前的此山此水融为一体,与此花此木同开同落。
此间,人即永恒。
责任编辑 孙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