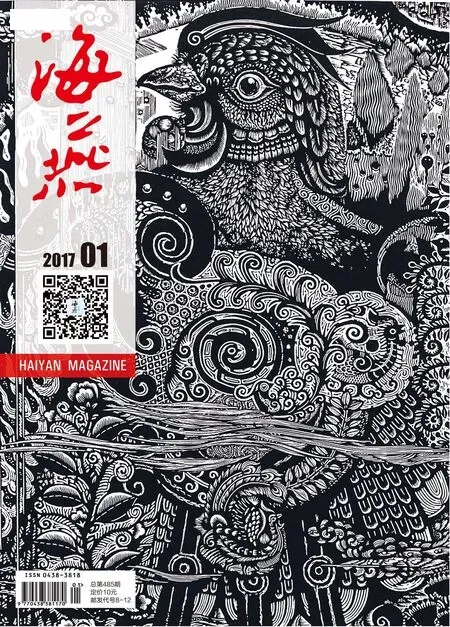异托邦少女运动史
——评王秀云中篇小说《我们的围栏》
□李屹
异托邦少女运动史
——评王秀云中篇小说《我们的围栏》
□李屹
对我而言,读当代小说时总有一种隐秘的期待,我期待它能显出我三点一线生活的另一面,如港片中“牛眼泪”的神奇功效,给予我多重世界的透视能力,在影像的叠加中寻找时空的裂隙。然后,以语言之“无厚”入人情的“有间”,依天理,批大 ,见血肉风流,见天地众生,一切因缘喜恶最终返诸己身。一睁眼一闭眼,几番穿梭轮回。小说合上,带着泪或笑,重新回到三点一线的生活。文字的鬼神之力,在当下还有另一种意味,凡现实世界不可言说的,都可以千百倍丰富的姿态出现在纸墨之中,所谓“幽情”,莫过于此。
近来读王秀云的中篇《我们的围栏》,我“隐秘的期待”似乎遇到了一个幽密的时空,围栏内三代人的对话和两代青年的“运动”,已不仅仅是“动物庄园”式的寓言世界所能笼罩的。王秀云在这个中篇中以反省的姿态道出种种忧虑,第一人称“我”的对话、心理告白和行动,凝练了两代青年“走向十字街头”和冲破“围栏”的欲望。饶有趣味的是,这篇小说既不是动物庄园式的“寓言”体又不是“一地鸡毛”式的现实体。女儿“三婴”发现小镇一直在“围栏”之中,虽然从未见过,但执拗地要去拆围栏。“我”忍不住一笑,通往围栏的叙述之路由此一分为二,当年“我”是受名为《小镇去围栏化的构想与宣言》的宣传册影响,和日后丈夫“开尔”走上了“拆围栏运动”之路;如此“我”看着喜欢韩剧的女儿三婴也开始思考围栏之存在,在网上秘密组织拆围栏活动。母女两代,都在少女时代要闯一闯小镇禁忌。
小说里当年之“我”颇有英雄气质,然而少女英雄不敌复杂人世——拆围栏运动因筹款而遭遇广告赞助,因而落入商业谋算的陷阱;因声势浩大遭遇所以求诸组织运营,最终却以团体内部的腐败和权谋自我解体。浩浩荡荡之人群造出轰轰烈烈之表象,几人能够从一而终地坚持理想信念?小说在虚构的故事里埋了多少历史陈故我们不得而知,小说以虚构之力钩沉历史教训,用心最多之处,还在于“少年男女”和“运动”相结合时的种种矛盾——天真烂漫之赤子,何以行千难百险之“运动”(革命)伟业? 而领导权遇到财务和人事这两项切实的问题时,关于革命组织的一切,都将在信念之中制造裂隙,引入人情欲望,此时信念的作用又究竟有多大?
王秀云在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时,有种双手互博、自我辩诘的张力在其中。但是小说的声音不是复调的,从头到尾都是“我”的自言自语,时而冷漠时而天真烂漫,理想主义的一面与悲观主义的一面俱在,其间思想的复杂性便生发了出来。然而,不要以为作者迷茫无措,文中的对话不是无意义的狡辩,革命虚无论在小说中实际上是被批评的——虽然“那条通向围栏的路走失过很多孩子”,中年的我还是要陪着女儿三婴去拆围栏。最终,理想主义的一面始终是被赞同的,其中暗藏着对反抗绝望的认同和对“行动”的赞美,这是九九归一后的箴言。小说写到最后我们连“围栏”都没有看到,发誓要拆围栏的女儿连家门都没有走出去。“我”参与和领导“拆围栏运动”的失败史,是警示,是教训,是否定性思维对历史的自觉反省。“我”和爱人开尔最终以极其讽刺的姿态“拒绝活在当下”,睡在那张“几乎花掉所有积蓄的硬床”上,成为如今理想主义一代的现实写照。一个有趣的对读是:在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中,主人公小林“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那柔软舒服的“床”,恐怕是围栏内的另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刘震云用“变馊的豆腐”砸醒做着甜蜜美梦的鸡崽似的人们,那“醉酒当歌”的隐喻精神是与契科夫遥相呼应。那么,王秀云在小说中开头以“三斤金莲”丈量活动空间,结尾处铺上一张传统精美的“雕花红木罗汉床”硌得心怀旧梦的老少男女们不得安眠,其间无声的悲怆总能让人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我们的围栏》最为可贵的地方正在于此:两代人的拆围栏行动都在途中自我解体、无“疾”而终,“我”忍受着硬板床未曾做过在鸡毛中安眠的甜蜜美梦,“我”和丈夫也过着普通的生活,却没有遗忘围栏的存在,“我们决定共同承受这种羞辱”。
小说最后,“我”亲自为女儿准备好卫生巾,这是“我”在运动最高涨时的身体经验。王秀云的这一笔前后照应、意味无穷:少女运动前后两代重叠之处,正在于运动热情高涨时身体流血而运动流产,前者有鉴,后代何如?结尾处,女儿一代的拆围墙运动难抵“起床气”,“小宇宙”的梦想和“萌萌哒”拆围栏行动在零食与被窝里消失无影,“我”重燃的赤诚热情戛然而止。小说最后一段,“我”和丈夫终于决定要换上一张“喜临门”床垫好好睡一觉。从此以后,柴米油盐馊豆腐,无英雄,亦无少年。——恐怕这也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承受羞辱。小说里,理想主义气息浓郁高涨时,总会有锥心的反省之痛提示着深渊存在;理想和英雄退散远去时,隐喻和讽刺力透纸背,剑在匣中鸣。
围绕“围栏”,“我”和母亲、和运动同志与爱人“开尔”、和女儿三婴有过多次对话。这些对话都是理解小说内部种种张力的关键所在——这些形而上的疑问,恰恰是现实界不可言说之事投射在天空中上的诡谲云影。
母亲对“我”说:“宝贝,对许多人来说,不需要知道围栏在哪里。”“因为那是危险的。而大部分人不需要冒险。你看见动物园的锦鸡吗?那么矮小的栏杆就可以让它老老实实待着,狮子,你看见了吧?就需要更结实更高大的围栏,还有很多动物,根本不需要,就会待在一个地方不动,比如霍英家里的猪。”
“我”对女儿三婴说不能拆围墙,“拆掉世界就乱了。”“杯子就是奶茶的围栏,如果拆掉了,会是什么后果?”
如果围栏根本不存在,“我”的一切坚守都会成为虚妄之执念,如同迫害妄想症患者一样需要被另一种方式对待。然而,上面这个想法是对的吗?围栏存在与否,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围栏》对虚妄之念和强大意识形态的反思。“围栏”所隐喻的究竟是什么?“拆掉围栏”的信念到底从何而来?
如果把“我”一开始就视为迫害妄想症患者,围栏如果不存在,那么,“我”所参与的运动史其实更明确地指出小镇在另一重思考下的样子:一个“另类空间”(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一个巨大的异托邦(heterotopia)。无论围栏存在与否,小镇的生活和生产发展都按照自己的历史前进着,可是只要有人想要“冲出围栏”或者“拆掉围栏”,真实生活如同被颠倒翻转,呈现出另一个关于权力关系、欲望投射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多维空间。“围栏”在小说中的功能与福柯所言“异托邦”之镜子相同,提示着小镇青年与其周遭世界的多重关系,提示着哪怕是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只有人思考到“围栏”,一切都将进入另一个时空。——王秀云的这篇小说,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有着奇妙的对话。
小说起笔,便是讨价还价之生活,然而“我”与丈夫的种种行为和对话,都似伪装,“我们必须坐这样一把漆皮剥落的硬木椅子。对外说是一种格调,而我们自己清楚,这只是一种仪式。在那件事之后,我们只好选择这样生活。”小镇少女参与“拆围栏运动”后,异托邦大门便被开启,“围栏”不拆,另一种生活便不会来到。另一种生活到底是什么?没有围栏的小镇是怎样的世界?二战后,德国哲学家布洛赫有过这样的思考:“积极的乌托邦就是对绝对美好的期待”,“思想就意味着超越”,人们的思想和乌托邦的存在就是要发现“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和“尚未形成的东西”(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围栏拆除后的小镇,恐怕正是那个乌托邦世界。
异托邦少女“我”竟与那个美好世界只有一围栏之隔。恰恰是这一围栏之隔,成就了这篇小说内部丰富的思想能量。《我们的围栏》里,浓缩了4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学生运动的经验与反思,传奇的革命热情与戏谑的后革命欲望如何转化为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和实践?这都是小说结束后未尽的笔墨。王秀云的“小镇”,恐怕还会有更多故事。
责任编辑 董晓奎
青春行
主持人: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