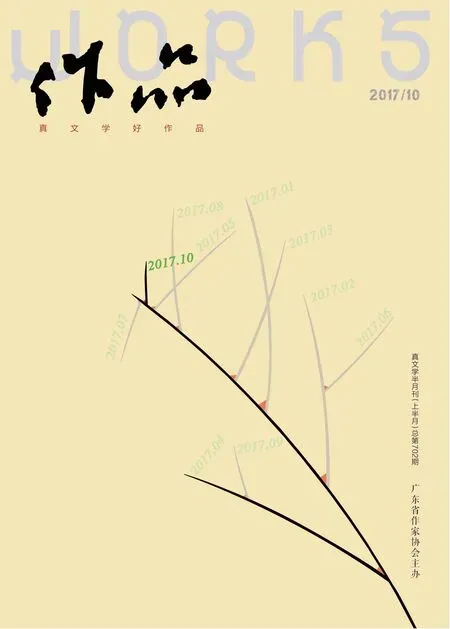史尼逛
文/张万康
史尼逛
文/张万康
起先,我以为我走在蛇的肚子里,后来我发现我是在鲸鱼的肚子里。这里不阴毒黑暗,这里广阔浩大。
“坐。”史尼逛说。“喝什么?”
“都好。有白水吗?”
“有的。”史尼逛微微一笑。或许如传说一般,他的调子很冷。但我觉得他的简短,更让我感到不做作的和蔼客气。或许这是事后我在美化他,但是谁说邪气的人就不能客气呢?想当然尔,当时我对他一直保持着警戒。羚羊在怡然吃草或嬉戏的时候,看不见的血液中,会对看不见的狮子怀有警戒。
看他的样子是亲自去为我倒水。他一边走过去,一边保持笑容:
“我好奇你这年纪,怎会用‘白水’这名词。”
没错,白水是大陆的用法,台湾都用白开水、开水或水。
“我爸是大陆台商,他跟我讲他们那边都这么说,我觉得很好玩。”
“其实很贴切。虽然水不是白的,但是加上这个字挺美。不是吗?”
“有吗?我只想到白山黑水。”
“‘黑水’也很有意思。你想,自然界的黑与白,其实跟化学颜料的黑与白,是有差异的,但你还是会这么形容物质现象。”他说话有点慢,但不会令我昏闷而性急起来。他的慢,好像使我感觉有人在推我。“你是校刊社的总编,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应该了解我说的‘形容’。我问你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他在茶几前,背对着我。“为什么用不正确的字眼去形容一件事物,却令人感到更贴切?譬如你用白水形容开水。”他边说边倒了两杯饮料走回来,一杯是白水,一杯是黑水。前者装在长方体的玻璃杯,后者装在高脚杯。
我突然有点烦躁,我不是来接受测试的;相反,我是来采访他的。
“你喝的黑水不是可乐吧?”
“枇杷膏。”他说。“只有枇杷膏才能唤醒我。我每天要喝一大罐。”他手指头托着侧视呈三角形的杯体展示着。“你好奇我为什么要倒在高脚杯吗?”
“你想说就说呗!”我向他露出拆穿的笑。这个人虽然是著名的社会大败类,但以他的聪明而言,这样就足以接收到我发出的不耐烦信号。
“我先回答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他坐下。“答案是,巴拉巴拉我也不知道。”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这可能要你来告诉我。你可以用一辈子的思考来答复我,如果你忘了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就是不必要的,至少对你而言。而我的想法是,‘白’与‘水’两者可以产生一种连结。这个世界上充满各种莫名其妙的连结,有些是莫名其妙,有些是莫名其烂。比方说你如果用‘白漆’当然没错,‘白水’也成立,但你用‘漆水’那就烂了。白可以逗上漆,也可以安在水上头,但漆和水搭在一块儿就不伦不类。虽然这两种液体可能可以混合,但‘漆水’这个字眼在科学上不值存在,对民间百姓来说也指示不出什么,甚至向来低级惯了的文学家或诗人也不会青睐它。另外在字面上,光是漆水二字听不出是漆是水、白漆或黑漆、白水或黑水。讯息开始不明确,漆水可以是任何鬼东西。讲到这里,我再给你一个例子,当你听到‘云’一个字,通常你想到‘白云’,而不是‘乌云’。约定俗成,云和白,彼此有连结的关系,云和白可以互通,但是你可以接受‘白水’这字眼,却不可能说:‘嘿!老板,来杯云水。’”
我实在想赶快进行访问的主题──你为什么成立杂交俱乐部。
史尼逛接着说:
“还有,‘云水’,有的台湾人会发音成‘淫水’,这就天下大乱了。”
他呵呵笑了两声,我不知道笑点在哪。
“请慢用,”他得意地说:“我看这大乱是个大爽。”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该与淫水为敌。喝口水,请慢用。”
“……”
他继续讲:
“或许你说‘白’是形容词,可以安在任何名词上,而‘水’和‘云’是名词,两个名词怎么能重迭。但是中文的特性是啥?就是可以自由恣意的排列组合。在中文的用法里面,‘白’一样可以是名词,‘水’和‘云’一样可以是形容词。这些词性的区分是现代人搞出来的,现代人不见得聪明,只是喜欢使用聪明。这就是现代人愚昧之处吧。”他说话时,脸部的肌肉没有什么牵动。不过他看着我。
“你奇怪我为什么跟一个国小六年级的校刊总编辑、一个小女生的你,谈这么深奥或无聊的问题吗?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听得懂,所以我才说。”
虽然我觉得他好像还是把我当成一个小女孩而不是滋味,但是他的话在我听来还是挺受用。我一直不认为我是小孩子,我不喜欢别人用“早慧”这个字眼说我,那好像说我虽然提早长大,但也仍然长不大,还是说我本来就应该很笨吗?不过我还是感受到他对我的尊重,远超过其他大人对我的尊重。
“就像我把枇杷膏倒入高脚杯。”他说。“这也是一种连结,土气和精致的连结,表示我重视枇杷膏,赋予它尊贵的地位。我今年三十八岁,从很小的时候,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我多小,一想起这些往事,我觉得我像是婴儿拥有的第一个玩偶或玩具,被他握在手里,或躺在他的小船般的小床上。那小船停在树梢上。很温馨吧。我曾经无法忍受这种回忆的镜头,它让我冷。让我走在路上有一种和世界彼此排斥的感觉,所以我不断的参加杂交派对,我告诉我自己我什么也不要,而绝非我要什么。有一天我想通了,我开始知道黑暗和光明并非彼此隔阂与为敌的,黑暗应该与光明握手,这时谁也分不出来谁是黑暗、谁是光明。这不是同归于尽,这是一起升天。此后我不去参加杂交派对,我自行创立杂交俱乐部。此后,当我离开俱乐部办公室,走在路上,每一只流浪狗都跟着我,每一栋建筑物都对我微笑。以前我怕巨型而恶相的狗,现在我一点也不怕。它们把我当成朋友,朝我走过来,希望我摸摸它们的头毛或脖子。玻璃帷幕在烈日下的闪光令我安煦。我不必戴墨镜,我的肉眼裸露,一双裸眼。我不回避这光。原先它是刺眼的,有时候是个残暴的刑求。摩天高楼不再把我压在山谷底下。楼前的风剪,不再是山谷间诡异的妖风。明明白白是无比的凉风。”他喝了一口枇杷膏,让它缓缓的入喉后,说:
“小时候,我常生病,我妈就喂我喝它,直到我能自己捧着喝它。四舍五入,这将近是四十年前的事,所以我说枇杷膏是旧式的东西。而高脚杯给人精致而华贵的质感,那是新式的东西。错!高脚杯的历史恐怕比枇杷膏久,枇杷膏在清朝时才被叶天士大夫萃炼出。对我而言,这根本是两种旧式产物的重迭混搭,这么一想,我的热汽球般的智能又比你膨胀了几分。原先我和你一样,认为它们是新旧的连结,因为高脚杯是舶来品,很少有中国家庭从小就让你以稀松平常的心情接触它。第一次接触高脚杯时,大部分的人和我一样,会有点新鲜感,如同西方人第一次拿筷子。现在你看到的我,其实是个旧式的人物,你却误认我是新派人物。我创立的杂交俱乐部,也是无比怀旧、充分溯源的行动。这好比文艺复兴。而你受传媒的影响,把这个俱乐部当成新玩意儿,所以引起你的好奇,使你在这里。你要知道,人类在史前时代,不但不是一夫一妻,也是彼此杂交的。的确原始人也会有占有欲,我的俱乐部的宗旨既是要恢复性交的自由,也是要进化人性,要去除贪婪,去除占有欲、权力欲。我敬佩的人物是孔子,为天下苍生,周游列国。不同的是,我不必周游列国了,而是列国的男女来寻访我的国度。我等待每个访客,包括前来交媾的消费者、警察、黑道、毒枭、记者、议员、官员、厂商、愤怒的家长,也包括前来寻找父母的少男少女,他们认为他们的父母被我诱拐来此,他们失去父爱母爱,而赖在我头上。殊不知他们的父母来过这里后,可能才开始懂得爱自己的孩子。还有中年男女,也来这里寻找他们年迈的父母,他们妒忌自己的父母已经老年却比他们有活力,他们认为你把我教育成你要的样子,怎么你却堕落了。他们的道德信仰产生危机。当然他们也妒忌自己的孩子于此地得到自己年轻时代无法得到的快乐,同时因为无法再度控制他们而感到挫败。你父母知道你要来吗?”
“他们很信任我。可以说我是在爱的教育下长大。”我盯着白水,说:“他们一直给我很大的自主性,这也是我不容易被你蛊惑的原因。”抬起脸我忍不住瞅着他笑。“当然也是有保险措施啦,我和他们的手机都在满格状态,如果你侵犯我,我可以随时呼叫他们。不过我发现你是个绅士,尽管我不赞同你的论点。”
“你有来月经了吗?”
我早就知道他迟早会问。
“那又如何?”我轻巧的带过。
“所以你选择不说。”
“有分别吗?”
“目前还不知道,我不会预设立场,那会让我连枇杷膏和高脚杯的关系都搞不懂。”
“私人问题就不必问了,而且是我在采访你哟!”
“那又如何?执政党的官员也可以对反对党的议员反唇相讥,而我只是反问罢了。”
“我没说你不能反问,只是我不想答。”
“那我告诉你,我根本不该反问。我在这世界上,看似在寻找促起人类进步的可变价值,但不要忽略我一直坚信和依循许多不变的信条。如果是接受访问,或是议场质询,大致上我就该保持着充分配合或唯唯诺诺,反问是个忌讳,只会带来挑衅,因为我的角色是受访者和被质询者。”
“那你还问。”
“所以你该断然阻止我反问你任何问题,何况我问你的私密。”
“我的妈啊!那也不是什么私密好吗?我四年级下学期就来月经了。”
“由此你对你的身体已经充分认知了。”
“是怎样!”
我不由得防卫起自己。
“有一天你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来到客厅对着镜子,当你看到新生长的部分,是恐惧还是兴奋,是迷惑还是骄傲?”
“没那么复杂的情绪,我只跟她们说:‘嗨,你好,你们来了啊,欢迎光临。’”“你一定会是便利商店最可爱的店员。”“无聊。”
这时他不动声色,又喝了口枇杷膏。我也喝水。他说:
“我发现你成长的部分,令我感到愉悦的悸动。可惜你自己不知道,你最迷人的地方是你的肩部的线条,和你的锁骨。”
“噢……是吗?”起初我以为他问我长阴毛的感想。
“锁骨是种温柔的自我宰制。切割你,也呈现你。统一你,而形成你。你的锁骨是你的美的枢纽,往上是颈部柔嫩的肤质和滑动的线条……”
“你怎么线条个没完?”
“往下是你的细长的手臂,延伸到你的指尖,古代的人说这是笋子的尖端,不仅如此,也像一碗巧达浓汤的味道。”
“很烂的形容。你实在很难勾引我耶!”
“因为我刚喝巧达浓汤。简餐店叫来的料理包做的汤。”
我把录音笔按停,因为实在不想理会他的离题。不过他之前已经把我想问的问题自行答复了。很快我想到别的,于是启动录音。
“史尼逛,是你的本名吗?”
“不。”
我等着他说下去。
“从前台东的都历这个小地方,有一个阿美族人,叫史尼旺,也有人翻译苏尼温。我向往这个名字,但不想犯他的讳,所以改叫史尼逛。都历在阿美族语是‘熊出没的地方’。我至今没去过台东,但某种程度上,我是一头熊。我在深山纵谷中,可能我不知道转过头来就是人类所称的太平洋,可能我甚至没见过海,但不表示海没对我起一定的作用。海风和水气可能就在我的四周。史尼旺出生在一九一八年,中文名字是李光辉,日文名字是中村辉夫。台湾在作为日本殖民地时期,日军征调台湾原住民去南洋作战,这批原住民蛮犷豪兴,骁勇善战,在南洋的原始丛林行如飞猿,立如熊姿。史尼旺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远离家乡的史尼旺不想再被操控了。他想脱离战争,于是独自深入印度尼西亚摩罗泰岛一片原始透了的丛林,过着遗世生涯。他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一待就是二十九年。对他而言或许二十九年如一日,对以前年轻的我而言则是一日如二十九年,我对生活诸项不满,曾是个失意者。史尼旺在一九七四年年底被发现时,一丝不挂。当时他选择了远走,二十九年来他付出孤绝的代价吗?他长期饱受寂寞之苦吗?是的,但也或许之中饱含着乐天知命。他肯定自己,他勇敢坚持,当人在做出一个决定时,是伟大的,当下是自信自觉的,至于以后,那是另一回事,那种被称之为命运的状态就不是凡人所能尺量的。从另一层意义来看,史尼旺在丛林待得越久,就越是对战争的永生控诉。他的孤单反映出人性的尊严,以及对和平光辉的信仰,别忘了他有个名字叫光辉。也有人说,史尼旺没有逃兵,他只是不知道战争结束,所以仍在原地‘鬼混’,甚至有人说他是唯恐向盟军投降遭不测,所以执意在原地驻守。这些对我而言不那么重要,‘魅力点’是他消失远走二十九年。就在一九七五年元月,史尼旺回抵台东都历,当他搭乘的公交车接近故乡时,发现族人为了迎接他,围成一个圆圈跳舞。他跳下公交车,立刻加入圆圈,载歌载舞。二十九年以来,他没忘记阿美族的舞步。他以为他忘了。歌声一来,他肯定自己没忘记过。远古的舞蹈仍然偷偷的与他相连结。”
“好想看他跳舞的镜头。”我为这个故事感到震动。
“‘白水’这字眼为什么好?”这时他冒出这句,而且不给我时间反应就往下说,“‘白’表示不足、表示欠缺,表示不是汤、茶、咖啡、果汁、汽水这些掺了各种东西的水。它乍看欠缺什么,却是个‘本相’、‘原型’。你用‘本水’可以吗?可以,但是有毒,听起来好像长了一个‘草’字头的‘苯’,那还不如长个‘竹’字头。用‘原水’好吗?如果不会想到原子弹,应该还算适合。‘素水’好吗?可以,但‘素’好像给美容业用滥了。‘清水’呢?可以,但是你可能不想喝,习惯用来洗碗。‘纯水’呢?还不错,可是好像嫌别的水都不纯,不礼貌。总结起来,我舒舒服服的说,‘白水’是最合适不过的。如果偏不用‘白水’,那就用‘逊水’或‘酷水’好了。所谓谦逊,因为逊所以酷。因为酷所以看起来逊。这是什么极限主义、后现代主义吗?这是简约风吗?这素景素意是个小平凡,也是个大气派。我只想喝一杯呆呆的水。这跟想看一个美美的女生露出痴痴的眼神是个殊途同归。我管它什么极限、后现代、后设,男人当然不能先射。简不简、约不约、新潮、旧潮、思潮、人潮、前卫、后卫、卫生、卫浴,艺术和设计的书籍到处都是,流行少女谁不会穿。到底我想找的是什么?水是一面镜子,明镜儿似的。尽管我喝下小小一杯水的时候,我可没想到啥镜水的哲理,我也没想到我要感恩这杯解渴的水使我活着好端端,但没关系,因为我平时想的够多了。我没事每次喝水都在感动、都在照镜子,那我是个神经病。就像正常人不会每次做爱都演内心戏。实际上我没用水杯照过镜子。何况枇杷膏只能照出个黑。但正因为我理解水,所以我能够热爱枇杷膏。因为我懂简单,所以我也热爱复方、幽深、丰富、黯黑、浓稠的枇杷膏。你问我什么叫‘活在当下’,是他妈的哪一个当下?你问我该通往何方,那该是个安全的地方。斗争?一个养尊处优的年轻人入伍后,自己用针线缝个名条都是个斗争。姑不谈人间各种型态的斗争,在那个瞬间,身上盗热汗,老兵威胁的讪笑,这是和老兵的斗争,也是和自己的手斗争,还来不及想到这是场历练。一个对人际关系怯弱的少女,当她被放进一个社交场子,一言一行都格格不入,这个窘态正和欢笑在斗争,是她放不开还是没必要放开自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如果告诉她世界上有很多挨饿受冻的人比你痛苦,这绝不可能使她在那一刻舒坦一点。或许有的人可以把自己连结到满世界多重的苦难,而使自己心境和胸怀更宽广,但这种圣明的人显然很少。明摆着的是,眼下我们这关该怎么过。当我喝一口枇杷膏时,我乐于我看起来走火入魔。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火、什么是魔,对你我充满宽容。当枇杷膏润过我的喉头到胸口,在黑色的清凉间,我已用一口枇杷膏席卷世界、润泽周遭,这时我已感觉你想帮我吹箫。我知道说‘哈棒’才可爱,但这一次我脑海中跳出的是‘吹箫’。我创办杂交俱乐部,正是在提供另一个世界,就像史尼旺的丛林世界,远远的离开恶质的斗争。是逃避吗?是愚昧吗?是冥顽不灵吗?是集体催眠吗?这是过程?还是终点?我想这是个起点,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终了,就像一出电影必须收尾,但没有结局。为了维系俱乐部的生存,我和我的员工周旋在黑白两道和各种人面所施加的骚扰或打击,我天天在付出、在作战,但历史不会记上我一笔。这又何妨?我是在默默行善,我的善行回馈我许多真理的花香,这弥足珍贵。”
想不到他跟我发起牢骚。我想,我来安慰他一下好了。
“大家都在享乐,不知道你的理念和辛苦。昨天还有一群人在俱乐部前举牌抗议,说消费金额太高。”
“他们都是大学生,诉求的是凭学生证打折。但我不同意。如果有人带他们偷混进来,那我不管。公开要我给优惠,我还要付水电费哩!”
“听说你最近企划‘小学生淑女之夜’?”
“是啊,现在的小学生都被媒体的色情传播污染了,不如我来端正感觉。”
“你能给小学生一句话吗?”
“对我而言,大学生连学校都无法击败,何况是击败我。至于小学生,可以击败我,却无法击败学校。小学生的智慧比任何人高,我无法建议。我很羡慕小学男生和女生写交换日记。建议,或许我也可以和你交……”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你妈在催你吗?”
“不,校长在催稿。”
“他同意你来。不错。”
“那个死猪头当然不同意,但是我得过全校‘简讯第一快手’的冠军,连续两年在全校考第一名,又代表全校得到全国四百公尺接力赛跑的冠军,我跑第四棒,逆转获胜,所以他拿我没办法,只好让我来。”
“真是感人的奋斗史。”
“还好啦!谁叫我兴趣广泛。”
“你会来参加‘小学生淑女之夜’吗?”
“应该不会,因为我喜欢比我大好几岁的男生。”
“那天各种年龄的人都会来啦,但是只有小学女生完全免费,包括饮料无限畅饮。”
“我跟我妈沟通看看好了。如果她那天也想来玩,我就不来了,不然总是有点尴尬。”
“母女第一次在这样的场上相遇,难免。总要踏出第一步,或许这个有趣的经验可以让你们日后津津乐道,更增母女感情。”
“随缘吧!我走啰!”我喝完杯子里的白水,起身。
“等等我。”他说完走到办公室里面的房间,过了一分钟才出来。他拿了一个透明夹给我,里面夹放一迭俱乐部的简介和DM。“回去参考。好下笔。”
史尼逛帮我推开玻璃门。我走的时候瞟他一眼,觉得他人不错,不禁对他二十九岁时发生什么故事,而感到好奇。我突然有点依依不舍。我以为他会上我,当然我不是因为他没上我,才依依不舍。再说我也不会让他得逞,而且我也对他没感觉。我不是说要多有感觉,反正没有那种想做的感觉就对了。
我走出俱乐部大门,发现大学生又在准备集结抗议了。大布条上的文字对他做人身攻击。我看了很气。
搭公交车回学校时,我在车上把他递给我的透明夹打开,发现一张卡片。上面有我的名字,是他的字迹;尽管我没看过他的字迹。他写:“我对你一见钟情这种感觉挺好的”后面是签名、日期,和一颗爱心。流利的文字是以黑色钢珠笔写的,爱心则是用粉腊笔画的。
我想我笑得很甜。
隔天我去我阿姨的化学实验室,请她用精密的仪器帮我化验卡片上的墨水字迹。化验后确定,那两句,是在我到访的前一天写的。至于史尼逛所画的爱心,时间点就无法推算。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