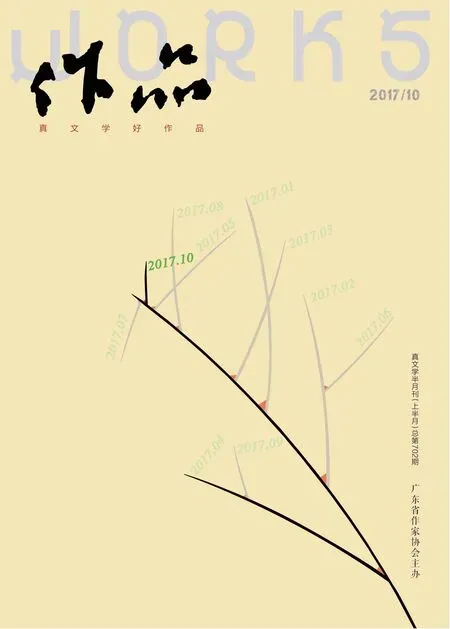来历不明的人
文 /毕 亮
来历不明的人
文 /毕 亮
毕 亮男,1981年生,湖南安乡县人,现居深圳。已发表中短篇小说60余万字,作品多次入选年度小说选本,出版短篇小说集《在深圳》 《地图上的城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曾获2008年度长江文艺文学奖、第十届(2010年度)作品文学奖、第十届丁玲文学奖、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另有小说改编成电影。
一
从中科数码公交站到龙塘新村租屋,走路大约抽半支烟的工夫。
租屋楼下是一条窄街,天擦黑时,道路两旁便密布各色商贩,有人卖臭豆腐,有人卖热干面,也有人就地摆个衣摊,卖十元一件的山寨阿玛尼T恤、四十元两件的廉价花格衬衣。半夜,人迹消散,硕大的灰鼠从地沟蹿出觅食,也有满身疮疤的流浪狗,趴伏暗处沉睡,而没睡的矮脚土狗,则站在昏暗的路灯下啃食来历不明的食物,或是眼望墙角模糊的黑影,恹恹地吐舌头。
相比白天红尘滚滚的喧闹,我更钟意龙塘新村的夜晚,它幽暗、暧昧,仿若坐落村东头,霓虹灯招牌闪烁的温州松骨城。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天冷或是天热,那里总有一帮穿短衣短裤露胳膊露腿的姑娘,她们肉挨肉挤坐在略显陈旧的人造革沙发上,要么嗑洽洽五香瓜子,要么嘴里叼一支女士烟,无光的眼神盯看泛黄墙壁张贴的年历女郎,吞云吐雾。每次我和小谢路经此地,都会默契地慢下脚步,假装漫不经心,朝店里头瞟两眼、三眼。我喜欢她们身体每个毛孔都似乎厌倦了一切,颓废的样子,但我没告诉小谢。
他跟我不是一路人。
小谢自称来自广西柳州,讲话却不带半点乡音。他习惯紧锁眉头,工作送快递的时候,端饭盒吃快餐的时候,手捧《读者》杂志阅读的时候,他的眉头从没舒展过。偶尔,我脑壳里会冒出一个念头,想问问他,是不是从娘肚子爬出来时,就一直愁眉不展,仿佛全世界人都欠他的。
我在龙塘新村快住满半年,小谢租住时间稍短,大概四个多月。小谢是我快递公司同事,也是我的合租室友。他平常爱读书。每月初,他会买两本杂志,一本《读者》,一本《知音》。他一字一句认真读完的杂志,有时我会顺手捡起翻一翻,里头故事五花八门,俄罗斯姑娘爱上河南男保安、网红拜金女豪门梦碎。某次,我在杂志里读到雪莱的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多数人会说,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
但我不是,我感觉自己一直生活在冬天,漫长的、寒冷的冬天,看不到尽头。我跟小谢谈起“冬天”的话题,他若有所思瞅着我,很认真地说,小马,你是个悲观主义者,这样好,也不好。好的是,不抱希望,就不会失望。不好的是,人活着,总要给自己一点盼头,一点念想。你说是不是小马?
对小谢这番言辞,我能说什么呢,他对我过去的生活一无所知。
很多事,我和小谢达不成共识,唯有一点,我俩是一致的——我们都十二分讨厌夏天,在炎炎烈日下送快递,热得人难受,特别是午后,感觉身体像雪糕一样慢慢融化。尽管厌恶夏天,它还是来了。我跟小谢送完一天快递,携裹一身臭汗返回租屋,站在六楼逼仄的阳台,边喝啤酒边谈论英国诗人雪莱。没有盐焗鸡爪,没有过油花生,雪莱就是我俩的下酒菜。
雪莱是个骗子。
一遍不够,我又强调一遍——雪莱是个骗子。
小谢盯着我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他说,小马,你不懂。又说,其实你不懂也正常,你才读过几本书,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恐怕你以为是教人炼钢的科普书吧。可能是担心我下不来台,他又补充,小马,你喝多了,不能再喝了你!
确实,我不爱读书,也不认识奥斯特洛夫斯基。
念中学时,只要眼睛一碰书页密密麻麻的铅字,瞌睡虫就会爬到我身上来。那时父母远在东莞打工,一年打不了一回照面,奶奶更管不了我,白天我经常逃课四处游荡,到桌球室看镇上染黄头发的混混打台球,看手杵拐棍满脸老年斑的老头在树荫下走象棋……现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我喜欢在城中村游荡,就像是一条流浪狗,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再从北走到南,从西走到东打发时间。我知道龙塘新村这片城中村哪里有常德牛肉米粉店,哪里有沙县小吃,哪里有重庆万州烤鱼馆,按摩店,哪一家是正经做生意,哪一家能“打飞机”。我像熟悉身体的器官一样,熟悉那些店面在龙塘新村的位置。
除了闲荡,我会在半夜睡醒时,梦游般掀开窗帘边角,瞟一眼斜对面租屋五楼的窗口,那里有时亮着灯,能目测到灯光下静默的影子,似一棵草,纤瘦而安静。若对面没亮灯,我眼里则是一片苍茫的黑暗,但也能瞅见那道黑影。
是我想象的幻影。
就算世界上所有的灯都熄了,五楼的女孩在我心里,依然散发着光芒。她长得像我过去在烧腊店当送餐员时认识的一个湖南女孩,名叫——玛丽。我搞不懂世界上为什么有长得这么像的人,就像我搞不懂小谢,为何他嘴里总是不停地嚼着口香糖。
仿佛口香糖是他的鸦片。
二
那个女孩,我在沙县小吃店遇到过一回。她点了一笼煎饺、一盅乌鸡汤。汤盅旁摆只装满辣椒酱的瓷碟。女孩伸出竹筷,夹起煎饺,放入酱碟,裹一层酱汁。再把煎饺夹进嘴里,抿嘴嚼。女孩嚼得慢条斯理。
我想象自己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拢过去,一屁股坐到女孩对面,找她搭讪,问她要手机号码。女孩爽快答应了。
我沉浸在愉快的想象中。
直到女孩离开,她的汤盅空了,她的座位也空了,我始终坐在另一张油腻的桌台,似尊雕塑,岿然不动。女孩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她穿的是一条碎花连衣裙。女孩长得不算漂亮,也不丑。她太瘦了,像一只营养不良的驯鹿。若我成她男朋友,我要把她当宠物养,帮她长点肉。
我猜女孩应该是在某个高档写字楼的公司当文员。我想哪天再跟她遇上就好了,若有下次,我一定鼓起勇气,跟她要电话号码,或者加她微信,再向她表白。退一万步,实在不行,我就直接去她租屋,敲她房门,告诉她我要泡她,要把她养成一只肉嘟嘟的驯鹿……走到租屋楼下,心中那团勇气伴随迈动的步伐泄得一干二净。我打了退堂鼓,心想就算女孩马上站我面前,我也不敢开口讲半个字,肯定早就变成一个涨红脸的哑巴。有些事,我在梦里才敢干,现实中,我不敢。
抬头,眼望六楼,租屋客厅亮着灯。我想起小谢,沮丧的心情好了不少,至少我比他要好些,小谢是个遇见蟑螂、蜈蚣都会躲路走的人。他是个怂人,比我更怂。
回到租屋,心脏仍在不同寻常快速地跳。我突然很想说话,想跟小谢聊一聊,一人开一瓶青岛啤酒,聊一聊那个营养不良的驯鹿女孩。但目视小谢嚼口香糖,草率地扫我一眼打招呼,然后目光又转回《读者》杂志潦草的表情。我迅速斩断了跟他聊天的念头。
洗完澡,我从浴室出来,厅灯熄了。小谢已回他的卧房。房门紧闭。他闷在房间干什么,可能是继续看书,也可能是躺床榻发呆或者睡觉。我也关紧房门,将门反锁。打开墙角行李箱密码锁,拿出存钱的铁盒,我将铁盒摆床上,揭开盒盖。
盒内有一沓钱。
有时无聊,无事可干,我会数钱玩,并且故意数错,好再数一遍、两遍,借此打发时间。这次点钞,数额是四千块。我又数了一遍,不多不少,四千块。本来我已经存满五千,前段时间手机坏了,我拿出一千,买了台“小米”。奶奶一直独自生活在四川老家,马上六十岁生日,我计划奶奶生日前给她寄五千块钱,让她拿这笔钱去县城医院做白内障手术。
将那叠钞票放回铁盒,码整齐。闭眼,我伸出手,拣起那叠钱。睁开眼,我又数了一遍,我很想把四十张纸数成五十张。结果,数额依然没有变化。我决定找小谢帮忙,开口找他借钱,借一千块。
敲响房门。
敲到第三下,门先是开了一条缝,一道光照我身上。他说,有事?我说,想找你借点钱。他说,多少?我说,一千,只要一千。我把奶奶患白内障,寄钱给奶奶做手术的事告诉了小谢。我没告诉他更多关于我家的事,估计他可能也不想听。然后房门打开了,室内的灯光全洒我身上。他说,没问题。他从折叠的黑色钱包数了一千给我,他的钱包立马瘪了。
我没料到,找小谢借钱如此顺利,之前想好的一大堆恭维、讨好的话没讲出口,钱就到手了。第二天,我揣着五千块钱跑了趟邮局,填好汇款单,我仔细地核对,默念一遍地址,确认没有错,才小心翼翼签名字,把手术费汇给远在乐山的奶奶。
走出邮局大门,小谢递钱给我时讲的那句话反复在我耳畔回响——小马,没想到你还是个孝子。
三
天气愈来愈热。
我希望这个漫长的夏天快点过去,可越是盼着时间快点走,时间走得越慢。度日如年。我想若是能刮一场台风就好了,将深圳的酷暑赶走。台风却迟迟不来。
租屋没装空调,只有两台电风扇,我和小谢房间各一台。电风扇是我俩从二手家具店淘来的。启动电源开关,塑胶扇片便呼呼转动,像是肥胖症患者沉睡后,发出的巨大鼾声。
半夜,我被热醒,身上糊一层黏稠的汗液。起身,我掀起窗帘,对面五楼女孩的窗口一片漆黑。我脑壳突然冒出一个古怪的想法,若我跟孙悟空一样会七十二变就好了,我愿意变成一台电风扇,守候女孩身旁,天长地久地帮她吹凉风。
一想到女孩,加上电风扇扇片搅出聒噪的声音,我越发感到气闷,热,皮肤像燃起烈火,心里也似有团火在燃烧。我从阳台取下毛巾,打了盆凉水,将毛巾浸湿揩热汗,再把双脚泡冷水里。身上的温度总算降下来、燃烧的火总算灭了。
小谢卧房传来响动。
我猜他可能也被热醒了。随后他携带一身热气,从卧房走出来。那个夜晚,我终于跟小谢谈起对面租屋五楼的驯鹿女孩。我说,要是我能变成电风扇该多好,可以帮女孩吹风。小谢说,小马,变成空调岂不更好,更制冷。我说,如果是电风扇,肯定摆的位置离女孩更近,我能闻到女孩身上的肉香。小谢说,肉香,是汗臭吧。我很想告诉小谢他这个人除了爱读书,没一点情趣,最后看在他借过我一千块钱的份上,我忍住没说,没打击他。
聊完女孩,喉咙发痒,我伸出舌头,添了两下干燥的嘴唇。我说,小谢,之前我们应该添台冰箱,那样的话,咱俩现在就可以边喝冰镇啤酒边聊天。说完我感到喉咙更痒了,一阵发干。小谢走到阳台,往楼下望,他说,下面黑灯瞎火,便利店都关门了。
返回客厅,小谢说,小马,想喝冰镇啤酒,是么?
我说,真热,这是我长到二十岁,过得最热的一个夏天。不过,我马上就要过二十一岁生日。
小谢说,以前我读过一本书,有一家人没饭吃,肚子饿得慌,书里的男人告诉他家人,他可以用嘴巴帮他们煮饭,帮他们炒菜,还专门煲了一锅猪蹄汤。书的名字我忘了,但我记得用嘴巴做饭这件事。
我说,这不就是做白日梦么,有意思,跟我想变成电风扇一样。
又说,小谢,想干嘛你?
小谢说,你说呢小马!
我说,来一瓶冻的,青岛还是金威?
小谢说,青岛啤酒,一人来一瓶。
于是,那个燥热的夜晚,除了谈比牙签更瘦的驯鹿女孩,我和小谢还装模作样地喝起冰镇青岛啤酒。当然,都是小谢用嘴巴买来的。后来,热情的小谢做了丰盛的下酒菜,白切鸡、卤水拼盘、烧鹅。小谢想再添两个菜。我说,够了,两人够吃了,吃不完浪费,等吃完再加。
喝完一瓶啤酒,我们又要了第二瓶、第三瓶。
估计是喝醉了,或者酒不醉人人自醉,我把家里烂七八糟的事倒豆子似的,全倒了出来。比如我爸妈在东莞打工,一场大火夺走他们的生命;我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害癌症死了,多年来我跟奶奶相依为命……
跟小谢边喝啤酒边聊天,基本上是我讲,他听。他安安静静坐我对面,假装喝酒、吃菜,关于他自己,他一个字也没提。对于我这种嘴巴一张,讲话就像打机关枪的人,小谢算是个合格甚至优秀的听众吧。
酒喝到最后,我记得小谢冷不丁张开嘴,冲我呵了一口气。他说,小马,闻到了啥你?
我说,一股子酒味。
他说,还有啥?
我说,一股子菜味。
他说,还有呢?
我说,没了。
他说,你没闻到口臭么?
又说,小马,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人。
我弄不清小谢讲这些话是啥意思,大概他真“醉”了吧。
不知小谢从哪里摸出盒装的益达口香糖,打开盒盖,倒出两粒搁左手手掌心,抛进张成○型的嘴里。对面传来牙齿打架的磕碰声。小谢咀嚼口香糖的模样,真他妈粗鲁。
四
自从在沙县小吃店见过一次驯鹿女孩后,我再没遇到过她。白天或夜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不送快递,我便跑下楼,野狗似的在龙塘新村闲逛。我想遇到她,不讲一句话,近距离看她一眼也行,我也会感到满足。
但老天爷似乎连这样的机会也不给我。
我想过,去敲她租屋的门。楼上楼下跑过多少次,我忘了,站在五楼钢质防盗门前,郑重地抬起手,默念一二三,那只手始终不敢往下落,仿佛落下去就是刀山火海。我发现自己敲门的手在抖,腿也在抖,只好找个借口,心说下次再来,下次一定敲。然后我转身咚咚咚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仿佛身后有个凶残的猎人端着猎枪。
轮到下一回,我再次失去勇气,把敲门的机会又留给下一次。三番五次,如此循环往复,我的手指始终未能触碰到那扇钢质防盗门。
夜里,我一脸沮丧回到租屋。小谢说,小马,还没恋爱,你倒先失恋了。
有段时间,小谢老是拿我临阵脱逃这件事取笑我,直到某天半夜,隔壁房间传来诡异的惊叫,我抓住小谢的七寸,他的胆子比蚂蚁还小。事后,我俩总算打成平手,他便没再笑话我。
说小谢胆子比蚂蚁小,一点也没诋毁他。半夜听到怪异的叫声,我敲他房门,门打开后,我目睹脸色惨白的小谢,额头汗珠比黄豆还大。我说,小谢,咋了?
他说,房里有蟑螂。
我说,蟑螂呢?
他说,跑了。
我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看见,蟑螂能把一个二十三岁的男人吓成这样。他说,小马,莫把这事告诉别人!
我说,就你这怂样,还怕丢人。放心,放一百二十个心,我会替你保密小马。
后来小马又在半夜惊叫过,不是遇到蟑螂,就是遇到蜈蚣,或者其他竹节爬虫。他似乎没睡好,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一天到晚哈欠连天。粗看上去,他像个失眠病人,又像是吸了毒品,戒毒,却硬是戒不掉的人。
天气越来越热,租屋里像燃烧着火球,安静地坐塑料凳上,汗水也会从毛孔冒出来,刷刷往下流。每天夜里,我和小谢都会喝一瓶啤酒。小谢酒量不好。我眼里,他除了是个怂人,还是个相当节制的人。他说,小马,我只陪你喝一瓶,顶多一瓶。
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沃尔玛超市雪花啤酒做推销活动,买五瓶送一瓶。于是,我拎了六支雪花啤酒回租屋,顺带买了熟食,一只烧鸡、一盒鸭翅,再加两块钱油炸花生。天热,我和小谢都把长衣长裤脱了,穿条裤衩坐塑料凳上喝啤酒。
我干完两瓶,小谢干完一瓶。他说,不能再喝了。
我说,小谢,今天我满二十一岁。
他说,要不,我去把她找来,让她陪你喝。
我说,谁?
他说,杨桃。
我说,谁是杨桃?
扭头,小谢瞥了眼黢黑的夜空,又把目光收回来。默默地抓起一瓶啤酒,拿筷子撬开瓶盖,他似笑非笑说,我陪你喝。
我说,到底谁是杨桃?
他说,我一老乡,不说了,喝酒。
我也撬开一瓶酒,握住圆柱型瓶身,跟小谢的酒瓶轻碰。我说,干。
小谢越喝越猛、越喝越快。我估计,他起码喝了三瓶,跟我一样。他大概喝多了,目光望向我时,眼神空洞、迷离。像是考虑很久,他说,小马,我实在憋不住了,我不是怕蟑螂、怕蜈蚣。
我说,小谢,到底怕什么你?
他说,我经常梦到杀人。
我说,杀人,是人家杀人,还是你杀人家?
目光聚焦成一只箭,射向我。我成了他的目标靶心。他说,废话,当然是我杀人。
我说,小谢,你喝多了吧,开始讲酒话、讲醉话了。不能再喝了,我们不能再喝了。
其实就算我们想喝,也没有酒,六支啤酒瓶都已见底。
小谢说,再不讲出来,我会疯掉。好多天,我整夜整夜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又接二连三做噩梦,那人死了,流一地血。血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洗澡时,莲蓬头流出来的也是血,红彤彤的血。
头晕沉沉的,抬手捶了两下脑壳,我说,小谢,有个事本来我打算烂肚子里,不告诉任何人。
他说,啥事?
我说,其实,我也杀过人。
五
后来我无数次回想起那个跟小谢喝酒的夜晚,首先想到的是乌漆墨黑的天空,似刷了一层黑漆,没半点星光。我和小谢一前一后上了趟洗手间屙尿,回来坐定,我便絮絮叨叨讲起曾经在罗湖区烧腊店当送餐员的经历:
估计那女孩跟鹅有仇,每次她都是点烧鹅饭外卖。送餐次数多了,我知道了她的名字——玛丽。有天夜里我吃嗦螺吃坏肠胃,拉肚子。碰巧第二天中午送餐,送到玛丽住处,依旧是烧鹅饭。站门口,她接过外卖,见我不走,问我还有事么?我说想借她家洗手间方便。我以为她会拒绝,没想到她同意了。若换作其他人,肯定不会答应我请求。玛丽应该算是个善良的人吧,看她一直只点烧鹅饭,我猜她应该也是个专情的人。有时,我送外卖去她家,会遇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瘦得跟麻杆似的。看得出来,男人不是玛丽老公,但他打过她,还在她家摔过东西,打得她鼻青脸肿,摔得她家里像是发生过八级大地震。男人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出现时感觉也不会有太多好事,直到有一天,我目睹玛丽头上包了圈白纱布。我知道,男人又对她动粗了,下手肯定不轻。我再送烧鹅饭时,就跟玛丽说,你得离开他。玛丽说,我要是走,他找到我,会把我杀了。盯着墙面纹丝不动的一只断尾壁虎看,想了三秒,我说,等着,我替你收拾他。
伸手,我抓起一支啤酒瓶,在眼前晃了晃,酒瓶空了,我又抓一支,再晃。我把所有啤酒瓶检查一遍,全是空的。我说,小谢,你大概猜到结果了吧!男人死了,玛丽再也没打过电话叫外卖。等我找过去,人去楼空,他妈的,玛丽不知跑哪里去了。
推倒一支啤酒瓶,哐当一声响,小谢的目光变成一潭深水,望不见底。他神秘兮兮地说,小马,你真不认识我?
我说,我当然认识你,你是小谢,爱看《读者》《知音》杂志的小谢。
扬起手,小谢轻拍我脸颊,拍了两下。他说,小马你看清楚,看清楚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脸。
我说,我没喝多,小谢,我认识你。
小谢说,别再惦记五楼那个女孩,她叫杨桃,两百块一次。你跟她去谈谈,指不定花五百,五百就能包夜,爽一晚。
我说,小谢,喝多了你。
小谢突然张开嘴,朝我呵气,呵了一口,又一口。他说,我有口臭么?
我说,除了酒味,没别的味。
小谢说,以前我在罗湖区一家物流公司上班,送货时,听到收快递的男人对屋里的女人讲,那小子有口臭,一张嘴讲话一屋子怪味。声音从门缝传到我耳朵。你知道后来么,我蹲守一个星期,男人从来不坐电梯上楼。结果你肯定猜不到,我在楼梯间把他杀了,连捅八刀,没想到那么瘦一个人,得捅八刀,才能要他的命。
双手捂脸,我感觉瞌睡虫来了,眼皮快撑不开。我说,小谢,你真会编故事,《知音》看多了吧!
小谢说,小马,雪莱不是骗子,你才是。
我分明看见,小谢眼里有个东西亮了一下,仿佛除夕燃放的烟花,刹那间,眼眸又黯淡下来。
六
就在夏天快要结束秋天将要来到时,小谢领完薪水,突然人间蒸发。他那间房摆的二手电风扇、组合衣柜,还有床上用品,他一样都没带走。当然,没带走的,还有客厅墙角那堆杂志。过去,他视它们为珍宝。
小谢走后,空出一间房,我想把奶奶从乐山接到深圳来,跟我一起住。我想带一辈子住山里的奶奶去大梅沙看海,看无边无际的大海。电话里,我跟奶奶好话歹话讲老半天,奶奶就是不愿来。我只好一个一个问同事,看是否有人愿意跟我一起住,好分摊房租。很快,我找到合租伙伴,是新来的同事小谭。
小谭搬来前,我收拾小谢房间,从组合衣柜摸出一个4A纸尺寸的白信封,打开,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刀刃、刀身沾满血迹。衣柜边角有一顶黄色太阳帽。我猛然想起罗湖区命案发生当天,我在玛丽居住小区的楼道口见过一个头戴黄帽子的背影。后来我辞职离开烧腊店,进了物流公司当快递员。小谢寻着味找来做我同事,他到底想搞啥子。我想起曾经许多个夜晚,躺床上,房门外响起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会不会是小谢手握匕首,趴木门上,打探我这边动静。那个经常神秘叵测对我笑的小谢,是不是在心里说,小马,若不是看你每个月要给你奶奶汇钱,我早对你下手了。我还想起那晚喝酒,小谢讲过的那些话,脊背一阵发凉,仿佛一阵寒风吹过,钻入脊髓,冷飕飕的。
其实我没杀过人。
大概玛丽以为瘦男人是我杀的吧。
小谭跟我合住后,有天庆祝他乔迁,喝完三支青岛啤酒,我便不省人事。小谭说,小马,你顶多三瓶的量,以后少喝点,得控制。我再次想起小谢,他说,小马,我喝一瓶,顶多喝一瓶。小谢酒量应在我之上。
漫长的夏天总算过去。
深秋某个夜晚,我在龙塘新村窄街游荡,偶遇五楼的驯鹿女孩。城中村商铺节能灯白色灯光洒女孩脸上、身上。她依旧是老样子,瘦,脸色惨白,瞧上去营养不良。我喊了一声——杨桃。眼角余光瞟向她,她扭头看我,目光空洞、茫然。
我没理她,低头继续朝前走,走进了浓重的夜色里。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