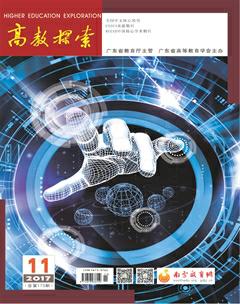美国批判性服务学习与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改进
收稿日期:2017-05-28
作者简介:李菲,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西安/710062)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关怀伦理视阈中大学生责任意识培养研究”(DLA160293)的研究成果。
摘要:批判性服务学习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它的出现与美国社会问题的凸显和批判教育学密不可分。相比于传统服务学习,批判性服务学习强调服务学习社会政治意义的实现,致力于通过社会变革推进社会正义。为此,它以权力再分配为着眼点,强调在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建立真正的关系,倡导批判性反思。志愿服务是我国大学德育的一种实践形式,批判性服务学习对于改进志愿服务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批判性服务学习;社会正义;权力再分配;批判性反思;志愿服务
服务学习是美国公民教育的重要实践模式之一,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今天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推行公民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服务学习在公民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地推动学生公民参与意识、公民技能和公民责任感等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服务学习发生新的转向,批判性服务学习(critical service learning)出现,它被称为“革命性教学”(revolutionary pedagogy)。这不仅是服务学习的深化,而且预示了美国公民教育的新走向。
一、批判性服务学习的兴起
批判性服务学习的出现与批判教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批判教育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被看作创始人,他的《被压迫者教育学》被认为是20世纪批判教育学的“圣经”。批判教育学是一种具有鲜明政治性的教育理论。它认为教育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社会意识形态下的一种文化霸权形式。统治阶级通过设计教育制度、教育目的和课程等实现对教育的控制,并通过“储存式”(banking)教学方式将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等灌输给其他阶层学生,既实现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也实现对被压迫者的控制和社会不平等秩序的延续。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正是通过教育再生产文化霸权实现的。对教育政治性的关注决定了批判教育学的基本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美国批判教育学的主要代表米歇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指出:“教育研究者要站到那些遭受经济、文化和政治霸权和压迫的人一边,站在那些因为保守主义的复活而失去了他们多年来所追求的人一边,即妇女、劳工、有色人种等的一边。”[1]只有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才能洞悉社会不平等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才能启蒙他们生发“批判意识”,即“人作为知识的主体,而不是被动受体,对于形成他的生活的社会文化现实及其改变现实之能力的深刻意识”[2],进而成为变革的主体,实现“解放”的目标,包括个体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
服务学习出现的时间与批判教育学大致相近,但兴起之初的服务学习主要是针对战后美国青少年政治热情减弱、不良社会行为激增等问题提出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公民责任感。进入20世纪90年代,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憎恶同性恋、无家可归者等问题在美国日益凸显。2009年美国全国无家可归家庭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Family Homelessness)指出,新自由全球化给美国青少年造成了很大影响,每5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无家可归儿童,一半适龄儿童有过无家可归经历,为此他们出现了焦虑、沮丧,20%的无家可归儿童出现了需要接受专业化照料的情感问题。[3]面对这些问题,服务学习能做什么,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受批判教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开始反思早期服务学习的性质、价值定位、目的等问题,并意识到一些不足。如阿曼達·摩尔·麦克布赖德(Amanda Moore McBride)等人分析指出,现有的公民服务研究忽略了对权力关系的审视,忽略了对公民服务在志愿者和社区群体之间造成的不平等关系的审视。他们认为关注权力机制将引发新的思考,比如谁有权力参与服务项目?谁将从中获益?参与服务项目的社区和人员是否有机会发挥他们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中的作用?[4]学者们逐渐发现,“尽管批判教育学与服务学习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二者可以联手合作共同推进学校和更大范围内的个人和社会的变革”[5]。服务学习的政治意义开始受到关注。
1997年,罗伯特·罗兹(Robert Rhoads)在著作《社区服务与高等教育:关怀型自我的探索》(Community Service and Higher Learning : Explorations of the Caring Self)中首次提出“批判性社区服务”(Critical Community Service)的概念。他认为服务学习是这样一种体验,它“将学生带入一种与他人的直接且重要的关系中,挑战学生思考各种有关自我的重要问题如生存密码”[6]。受这一概念的启发,赖斯(Rice)和波拉克(Pollack)、辛西娅·罗森伯格(Cynthia Rosenberger)等人在强调服务学习的社会取向时均提出了“批判性服务学习”的概念。由此,服务学习出现了传统服务学习和批判性服务学习两个分支,目前批判性服务学习正成为服务学习研究的重点,实践中批判性服务学习的项目也在逐渐增多。
二、社会正义:批判性服务学习的价值诉求
传统服务学习重在提高学生的公民参与性,但在批判性服务学习看来,这种目标只关心学生的个体化和社会化发展,忽视了社区的改变,甚至将学生发展与社区改变看作是相互排斥的[7],这对社区而言是不公平的。因此,它主张在学生个体发展和社区改变之间做出平衡,但并不止于提升社区的利益,而是希望实现社会变革。“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是批判性服务学习的价值立足点,它将服务学习从个体层面引向社会层面,致力于实现服务学习的政治意义。辛西娅·罗森伯格在批评传统服务学习时指出了这一取向。他说:“服务学习是在长期的社区服务中发展起来的,志愿服务指向的是个人或社区,这被认为仅仅是满足个体的需要而不是作为一种旨在转变结构性不平等的政治行动。”[8]可见,社会变革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将服务学习看作社会和政治变革问题的解决工具”[9]。endprint
进一步来说,实现怎样的社会变革?或者说社会变革的目标是什么?批判性服务学习给出的答案是“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在美国,很多社区及其群体面临的问题如不充足的教育资源、人员和资金匮乏的医疗、不平等的就业机会、性别主义、无家可归等,都与肤色、文化历史、种族、阶层、身份等有关。在批判性服务学习看来,这是不公正社会体制的体现,也是造成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服务学习必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探问背后的根源及其影响,鼓励学生思考不平等或被压迫的本质,努力“创建能推动平等、自治、合作和持久发展的社会结构或条件”[10],最终实现一个更加民主、平等、正义的社会。社会正义是社会变革的目标,是批判性服务学习的最终诉求。对于“社会正义”的理解,普遍的观点集中在权力问题上,因为权力分配的不平衡被认为直接导致了社会缺乏正义。如玛利亚·何塞·博特略(Maria Jose Botelho)和玛莎·路德曼(Masha Rudman)认为,“社会正义是指在性别、种族、民族,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审查权力的使用”[11]。批判性服务学习旨在引导学生关注权力问题,发展社会正义感,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主体。
社会层面的权力不平衡、不公正现象其实也体现在服务学习中。在服务学习中,社区成员与学生之间存在各种差异,这些差异来自双方的处境、年龄、能力、教育水平、文化背景、种族、阶层等。但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身份和角色却使这些“差异”制造出不平衡的权力地位与关系。学生摆出“服务提供者”的姿态,社区成员默认自己是“被服务者”,被动接受来自服务者的帮助。在二者之间,服务者明显享有更多的权力。洛莉·庞帕(Lori Pompa)对此的分析形象且耐人寻味,“如果我‘帮助(do for)你,‘服务(serve)你,‘给予(give to)你——这就构成了一种关系:我有资源,有能力,有权力,而你就是接受的一方”[12]。这是一种“有”与“无”范式下的权力不平衡现象。传统服务学习没有认识到这种差异和权力的不平衡,甚至将差异错误地等同于多元。但是,批判性服务学习认为,无视这种权力不平衡关系会导致被服务者的权力被消解,更多的权力涌向服务者,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继续维持,优势群体对权力的垄断将持久化,这实际上是在复制社会的不公正体制。所以,批判性服务学习极力主张推进“社会正义”。
从个体到社会,从社会变革到社会正义,批判性服务学习完成了对传统服务学习的改造。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使批判性服务学习突破了传统服务学习仅关注学生个体发展的局限,向社会体制发起挑战,促使学生对“社会正义”问题产生思考,并发展那些能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公正的行动。因此,它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正义取向的学术服务学习经历”[13]。
三、批判性服务学习的基本特征
与传统服务学习一样,批判性服务学习也是一种将社区服务与课程学习整合起来的实践形式,但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使其呈现出完全独特的一面。
(一)权力再分配:批判性服务学习的着眼点
批判性服务学习认为:“如果在决定谁接受服务和接受什么服务的问题上,不能看到通往社会权力和权力地位的道路的话,批判性服务学习就会丧失自身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走向正义的教学形式的潜力。”[14]“权力不平衡”是批判性服务学习的关注点之一,扭转权力不平衡关系,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首先需要在服务关系中进行权力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是批判性服务学习的着眼点,是实现社会变革取向的起点。
如何实现权力的再分配?学者们认为,根本原则是轉变“服务”的性质。在传统服务学习中,“服务”是学生给予社区帮助、援助,这是一种服务者对被服务者的单方“慈善”,甚至是一种“‘强迫式志愿主义的慈善”[15]。这种服务观将服务者推向优势地位,使其享有更多的权力和主动性,同时给被服务者带来疏离感和接受服务时的羞愧感。此外,服务的“慈善”性质使服务者总是抱着“聚焦自己”的心理,他们关心的是为自己找到更好地完成服务工作的机会,被服务者的主体身份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换句话说,服务者与被服务者是分离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服务者被当成满足服务者需要的“工具”。正如一位职前老师在反思他和同学在一个低收入社区的服务经历时所说的:“当20个小时结束了,我们离开了他们。这感觉像在剥削孩子,我们来了,然后我们走了,留给他们的疑问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再回来。”[16]这样的服务实则是保罗·弗莱雷所言的“虚假的慷慨”,就是“试图在不改变被压迫者软弱的情况下”,“为了不断有机会表示他们的‘慷慨,压迫者必须永远保持不公正的局面”[17]。如此,服务学习便在复制权力的不平衡,继续不对等关系。因此,实现权力的再分配,必须要超越服务的“慈善”性质。
超越服务的“慈善”性质,批判性服务学习主张用“共同体”(community)的观念取代服务的观念。在共同体观念中,所有人都懂得和接受彼此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这将避免服务者总是摆出“服务提供者”的姿态,避免被服务者陷入被动状态。这意味着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一种新的关系的建立。
(二)建立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真正关系
具体而言,用“共同体”观念取代服务观念,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即学生与社区成员之间要建立一种基于“联结”(connection)的关系。“联结意味着质疑自我—他人之间的二元化,强调互惠与相互依存”[18]。这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关系”(authentic relationship)。
首先,承认差异,实现相互理解。“差异”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一种现实表征,只有承认“差异”,才能理解权力问题。承认差异,一方面学生不能无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问题,相反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并探问背后的根源,以及分析权力及其重新配置问题。另一方面,学生不能人为地同质化自己与被服务者,回避差异,应该正确辨识彼此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并且了解它们是如何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的。endprint
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双方要实现相互理解,也就是“促使学生面对来自不同背景中的个体,建立起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意识,加强对差异的接受性,以及提高学生在社会问题上聆听他人观点的意愿”[19]。对话是实现相互理解的重要方式。学生和社区成员可以分享经历和认识,交流、讨论话题,评价伙伴关系等。对话还要以加强彼此的了解为前提。在服务开始之前学生要了解社区成员的情况,社区成员也要对学生的背景、经历,以及服务学习本身有所了解。在笔者参加的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荣誉学院的一门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服务学习课程中,授课教师邀请教会人士、非政府组织人员(亚特兰大无家可归者关心联盟 Atlanta Homeless Continuum-of-Care、亚特兰大拓展服务与支持中心Central Outreach & Advocacy Center、亚特兰大希望组织 HOPE Atlanta)、公职人员如警察等进入课堂,介绍他们接触到的无家可归者的处境、面临的问题,分享他们的感受,也介绍各自机构为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所做的工作,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增加对无家可归者的了解、认识,也引导学生对服务宗旨、服务态度等形成合理的认识、理解。
其次,发挥被服务者的参与性,实现互惠。保罗·弗莱雷说:“真正的解放教育学要能贴近被压迫者,不能把被压迫者看作是不幸的人,也不能从压迫者中推出被压迫者的效仿榜样。被压迫者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必须以身作则。”[20]批判性服务学习反对将被服务者看作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认为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应该实现服务给予与接受的交换,也就是二者应该互相学习,共同合作。这就是“互惠”关系。为此,要积极调动社区成员的参与性,让其与学生相互协作、共同参与服务实践,也可以让社区成员向学生分享他们的处境、体验、感受等,鼓励他们提出想法,给学生提供帮助,对服务活动给予评价、反馈等。
可见,批判性服务学习致力实现的“真正关系”,实际上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平等地参与服务学习的关系,是一种互动、互惠的关系,也是一种真正的尊重、信任、关心的关系,在最终形态上是一种“团结”的关系。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团结关系能遏制权力的垄断,迈向权力的再分配。“团结意味着超越服务关系,进入更广泛的对社会正义的承诺或献身中。它反映了服务学习最可能的目的。”[21]
(三)强调批判性反思
服务学习是基于课程学习的社区服务,课程学习包括公民知识、技能的学习,还包括一个重要的环节——反思。反思建立起了公民实践与理论学习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传统服务学习中,反思主要是“反思服务与其所学课程内容之间的联系”[22],重在引导学生发现自己学到了什么,服务学习之前、之中和之后有哪些行为表现,目的是推动学生公民意识、情感和行为的提升。与之不同,批判性服務学习认为,“如果学生对贫穷、文盲、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的解释仅仅指向个体品质的缺陷或弱点,那么他们就非常可能完全失去从社会正义角度对问题的审视”[23]。因此,它主张批判性反思(critical thinking)。在批判教育学中,“批判”是一种方法论,意指对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相关分析、意识形态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批判性反思就是从“批判”的视角,以“批判”的方法论对服务学习进行反思,归根结底是解构、揭露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包括反思“社会政策和条件、政治参与技能的掌握和社会纽带的形成”[24]等。批判性反思是对批判性服务学习的推进。
批判性反思仍然使用传统服务学习倡导的反思方法,如问题解决、阅读、写作、讨论、对话等,但是非常强调反思的批判性。为了使反思具有批判性,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将服务经历放置到更广大的社会结构系统、权力关系等背景中展开思考,也就是“对服务学习关系中的权力和特权问题具有批判意识”[25]。在开展阅读方面,教师应注意提供的阅读材料中要有对各种相关概念的介绍,以帮助学生围绕“身份和压迫、特权和权力、社会正义和社会变革”等话题展开讨论和对话。同时,材料要能帮助学生审视固有的一些理论视角,帮助他们评估自己所做的反思。
此外,教师要鼓励学生质疑惯常的思维方式、假设、价值观等,引导学生从对比的角度思考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比如在一项美国大学生到墨西哥蒂华纳市为低收入者搭建房屋的服务学习项目中,在每天晚上的反思环节中,指导教师都会给出一些问题引导学生进入批判性反思。如,你为什么选择来蒂华纳?来到这里,你希望蒂华纳是什么样子?你看到了哪些与美国不同的东西?通过这个项目,你对自己有了哪些认识?你对所工作的社区及其成员有了哪些了解?活动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你认为这个项目给你和你所服务的社区带来了哪些影响?[26]
四、对改进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启示
在美国大学中,服务学习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模式,它不仅被应用于德育,也被教师教育、医学等专业用于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志愿服务是我国大学的一种德育实践形式,它与服务学习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差异,相比于批判性服务学习,差异更加扩大。改进我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提升大学德育的实效,批判性服务学习是有积极借鉴意义的。
(一)提升志愿服务的价值定位,深化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发展
有调查显示,增加社会阅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增加社会交往是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主要目的。此外,增加就业竞争力、消磨时间、让生活更充实、为了获取各种荣誉等需求也有少量存在[27]。虽然这是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但也暴露了志愿服务在目标导向上存在一定的欠缺——个体化倾向突出,社会共同体意识关注不足。在这种目标取向下,志愿服务的价值往往被窄化为向学生提供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于是大学生参与的志愿活动多是“环境保护与美化”、“大型活动志愿者”等公益劳动,志愿服务所强化的社会责任感也多是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加快,不良社会问题的显露,人们对社会正义、良善发展的诉求日益增长,大学生仅仅具有参与社会的公民责任意识已不足以担负起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之责。社会的发展依赖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公民不仅能参与社会,服务社会,更应该关心社会发展,对社会共同体利益充满关切之心,具有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的意识。美国批判性服务学习的出现即是例证。它将公民教育从注重发展个体的公民品质层面提升至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推进社会正义层面,也推动了公民责任感内涵的深化——从公民的社会参与性提升至社会正义感和社会改造能力。endprint
因此,我们需要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的价值定位,使其突破仅仅提供参与社会机会的局限,应该成为激励学生关心社会发展、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平台。为此,志愿服务应该确立新的目标,即不仅引导学生具有社会参与性,而且发展他们的共同体意识、批判精神和社会正义感,为积极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努力践行公民责任。随之,志愿服务在活动设计上应该注重结合社会问题,注意活动要能满足社区的真实需要;在活动过程中注意引导大学生透视社会问题,跨越志愿服务的边界,思考、关心更大意义上的社会发展问题。
(二)推行志愿服务的课程化,强化道德学习
我国高校在志愿服务中多发挥联络、组织和监督的作用,但在活动目标和内容、活动实施等方面都欠缺系统的设计、指导。这使志愿服务本身缺乏道德学习的要素或成分,就是说活动本身并未有目的、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发展社会责任感,学生只是参与活动。社会责任感的强化主要依靠学生个体对活动的自发体验和感悟。这在很大意义上削减了志愿服务的教育意义。相比而言,美国的服务学习是一种将社区服务和课程学习整合起来的实践模式,课程化是其核心特点。课程化体现为服务学习有明确的公民目标和完整的模式流程,尤其在模式中设有反思环节。这使服务学习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社区服务活动,具备了明确的“学习”成分,成为一种“通过服务进行学习的方法”[28]。批判性服务学习同样遵循课程化形式,而且为了社会正义价值目标的实现,它从主张权力的再分配,倡导建立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真正关系,以及开展批判性反思方面,对传统服务学习进行了改造,强化了道德学习成分。注重道德学习是服务学习具有良好效果的根源所在。
借鉴美国服务学习模式,我国高校应推行志愿活动的课程化,增强道德学习成分。为此,高校应该在活动目标上制定明确具体的要求,在活动实施上参照服务学习落实完整的实践环节,包括调查确定问题,学习相关知识技能进行准备,制定服务方案,实施服务活动和开展反思。高校还要为志愿服务选配相应的教师,负责完整活动环节的展开和指导。总之,课程化形式将能确保公民实践与公民学习的有机结合。
(三)倡导批判性反思,推动大学生批判精神的发展
当今现代化、全球化、多元化的迅猛发展使个体的价值选择面临诸多困惑、冲突和挑战,一些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出现功利化、平庸化倾向,轻信、盲从、摇摆、迷茫,甚至堕落等行为也显露出来。如何辨别良莠,如何确立并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念,选择积极的行为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昭示一种重要的道德素养——批判精神的出现。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念、态度、观点,对于个体而言它能促使人不断自省,不断克服纷繁信息的干扰,克服自身的局限,不断追求人之为人的本有存在方式。社会的进步也需要人具有批判精神,为社会揭露问题、澄明观念、指明方向。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大学生应该具有批判精神,大学应该担负起培养学生批判精神的责任。这对大学批判精神的信守也具有积极的意义。美国的批判性服务学习在这一点上已经做出了努力。一方面,它引导学生关注权力、不平等问题,树立追求社会正义的理想;另一方面,它运用批判性反思鼓励学生思考社会问题及其根源,探索推进社会正义的方式。这都有助于批判精神的形成。正如彼得·法乔恩(Peter Facione)所说,批判性反思不仅是分析、推演、解释、说明等认知技能,也体现了批判精神、求知欲、锐利的思维、对理性的热情、对可靠信息的渴求等品质。[29]
相比之下,我国的志愿服务不仅缺乏系统的设计,而且较少注重激发学生进行问题探究,志愿服务之后多是类似观后感的总结,且总结欠缺教师的深入指导。这不仅影响了志愿服务的效果,更不利于学生批判精神的发展。因此,在提升志愿服务价值定位的同时,大学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和批判性反思。为此,在志愿服务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捕捉自己的疑惑、情感体验,鼓励提出问题,并结合社会背景、文化、体制等展开讨论;引导学生学会对一个主题或问题从多元角度如性别、阶层、人际结构、历史等进行思考、分析,聆听他人的看法,形成开放的认识,并鼓励学生从自我理解的角度对不同认识进行选择、协调。此外,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反思一些社会传统认识,反思自身的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思维和行为模式等,深化探究和反思,也确保其客观性。批判性反思鼓励小组合作的问题解决方式,也鼓励个人写作、阅读学习的方式。当然,在进行批判性反思时,教师也要注意把握学生的反思和认识变化,引导积极取向的发展,及时指导可能出现的偏激、消极甚至是负面的认识与情感,确保批判精神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Michael W.Apple.Education and Power[M].New York:Routledge,1985:133.
[2]轉引自:Peter Jarvis Paulo Freire.Twentieth Century Thinkers in Adult Education[M].London:Croom Helm Ltd.,1987:270.
[3][5]Brad J.Porfilio & Heather Hichman.Critical Service-Learning as Revolutionary Pedagogy:A Project of Student Agency in Action[M].Charlotte,North Carolina: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2011:ix-x,5.
[4]Amanda Moore McBride,Jenny Brav,Natasha Menon & Michael Sherraden.Limitations of Civic Service:Critical Perspectives[J].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2006,41(3):307-320.endprint
[6]Rhoads R A.Community Service and Higher Learning:Explorations of the Caring Self.Albany[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36.
[7][13][14][15][18][21]Tania D Mitchell.Traditional vs.Critical Service-Learning:Engaging the Literature to Differentiate Two Models[J].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2008,14(2):50-65.
[8][25]Rosenberger Cynthia.Beyond Empathy: Developing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M].//Carolyn R.OGrady (Ed.).Integrating Service Learning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0:29,34.
[9]Tara J Fenwick.Experiential Learning:A Theoretical Critique From Five Perspectives[R].Columbus,OH:ERIC Clearing-house on Adult,Career,and Vocational Education,2001:6.
[10]Langseth M & Troppe M.So What? Does Service-Learning Really Foster Social Change?[J].Expanding Boundaries,1997(2):37-42.
[11]转引自:Leisa Martin,Lynn Smolen.Using Citizenship Education,Adolescent Literature,and Service Learning to Promote Social Justice[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2010,17 (9):425-432.
[12]Pompa L.Service-Learning as Crucible:Reflections on Immersion,Context,Power,and Transformation[J].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2002(1):67-76.
[16][22][26]John T King.Service Learning as a Site for Critical Pedagogy:A Case of Collaboration,Caring and Defamiliarization Across Borders[J].Journa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2004,26(3):121-137.
[17][20][巴西]保羅·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10.
[19][24]转引自:Trae Stewart,Nicole Webster.Exploring Cultural Dynamics & Tensions within Service-Learning[M].Charlotte,North Carolina: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2011:84,85.
[23]Marullo S & Edwards B.From Charity to Justice:The Potential of University-Community Collaboration for Social Change[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0,43(5):895-912.
[27]王泓,邓清华.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状况与长效机制的构建——基于全国性大型问卷调查的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2012(8):46-50.
[28]转引自:Timothy K Stanton,Dwight E Giles Jr ,Nadinne I Cruz.服务学习:先驱们对起源、实践与未来的反思[M].童小军,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5.
[29]Facione Peter A.Critical Thinking: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M].Millbrae:Th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1990:11.
(责任编辑陈志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