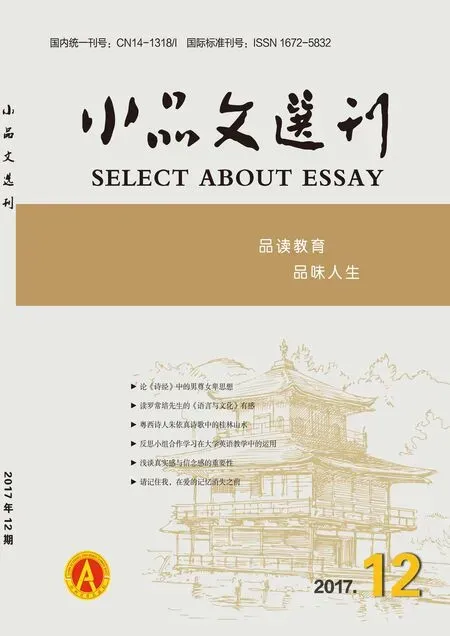商谈论视角下的法治国原则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解读
周 钰 包晓娟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商谈论视角下的法治国原则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解读
周 钰 包晓娟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哈贝马斯认为,经济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存在,但是它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危机了。因为国家应用行政手段过多的干预私人领域,所以促使其行政决策的合法性也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哈贝马斯从商谈论的视角出发,重新定义法律合法性的来源。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提出的商谈论应用于法治国和社会运行治理的诸方面,本文试图通过讨论商谈论视域下的社会运行与治理,反思其不足之处,分析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商谈论;法治国
哈贝马斯作为一名成长于纳粹德国时期的思想家,他与同时期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对纳粹德国的统治心有余悸。并且他们对产生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莱辛、席勒、歌德等思想大家的民族竟然出现了纳粹的残暴统治这一怪异现象深感诧异。[1]这些都自然而然的影响到这些思想家的理论思考,哈贝马斯当然也不例外。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从商谈论的视角出发,结合自身感悟理解和当代学术思想对法治国原则的内涵提出新的界定:人民主权原则、确保每个个人都能的到全面的法律保护原则、行政合法规性原则、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原则。
1 商谈论视野中的人民主权原则
二战之后,人们反思战争,对人本身给与了更多关注,对人的价值给与更多重视。人民主权原则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认可,无论实行什么制度的国家纷纷将人民主权原则写进自己的宪法中,以体现对其重视。人民主权原则的含义是一切国家权利来自人民。起初,人民主权原则是对君主特权的限制,它的性质是人民与君主或者政府之间的契约。
在哈贝马斯对法治国原则的内涵体系中,人民主权原则居于基础地位。哈贝马斯没有从社会契约角度对人民主权原则进行讨论,而是从商谈论角度对人民主权进行了定义。哈贝马斯认为:“根据其商谈论理解,人民主权原则的意义是一切政治权利都来自公民的交往权利”。[2]哈贝马斯从交互主体性的立场出发,认为没有人能真正占有这种交往权力。他认为交往权利并不能直接产生产生政治权利,通过交往权利的行使只能产生法律。法律进而对政治权利产生影响,政治权利依靠法律获得其合法性。这些法律是公民通过商谈得出的商谈性意见的形成过程中制定的。
哈贝马斯从商谈论的角度出发,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新的探索,使人民主权的法治原则不仅可以为法律和权力提供合法化论证,而且还为人民主权的真正实现规定了具体的方式与步骤,为交往权力的形成并进而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3]
2 商谈论视野中的全面保护个人权利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即要求每个公民可以平等的参与公共决策,同时也要求每个公民参与决策多表现出的意志上升为法律的可能性。因此,法治原则不但要求人民主权,还要求确保每个个人全面的法律保护。商谈论的角度来讨论确保每个个人全面的法律保护原则,哈贝马斯采取的思路是:从公民这边来看,公民的权利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得到诠释和展开;从国家这边来看,有组织的国家权力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得到控制。[4]确保每个个人全面的法律保护原则是哈贝马斯商谈理论必然到处的结果。
交往形式可以分为论证性商谈和运用性商谈。法律的运用性商谈是指法律具体运用到具体案例的过程,即针对特定具体的案例运用合适具体的法律规范。强调各个参与人积极公平参与,法官居中裁判,其他诉讼主体可以针对案件,发表各种争议性的意见,以此展开对话与商谈,并且法官要给出自己的裁判理由。论证性商谈中,原则上只存在参与者,没有裁决者,这是与运用性商谈的主要区别。这两种类型的商谈也是立法与司法的划分。立法对应于法治原则中的人民主权原则,着眼于运用性商谈的司法职能则要求确保每个个人全面的法律保护的原则。
3 商谈论视野中的行政合法原则
在商谈论中,行政过程是法律具体运用得过程,行政活动必须遵循法律。行政合法原则反映的是权力分立。行政过程遵循的法律是每个公民参与决策多表现出的意志上升为的法律,这样就确保了行政权力产生于公民共同地形成的交往权力。
这样就使行政行为有了一个大前提——法规。这样的话,任何违背这个前提的行政行为都是无效的,所以说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都是可以被撤销的。另一层不言而喻的意思是:行政行为绝不可干涉立法和司法行为。
4 从商谈理论看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原则
从商谈理论的角度来看,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防止国家权利或者社会权利不经商谈,不经交往权利的转换,而直接转化为行政权利。
哈贝马斯并不认同国家仅仅作为守夜人,把其他事物交给与政府无关的、自我调控的经济社会。他认为国家不是一种中立的政治力量,那种认为国家可以作为一种中立力量超越其他社会力量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5 结语
上述法治原则总结起来,就构成了一个体系。哈贝马斯认为,在这个体系的背后,是这样一个单一观念:法治国家的目的,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民联合体,通过权利体系而构成的共同体或政治上自主的自我组织。法治国家的各种制度,应当确保具有社会自主的公民可以有效地运用其政治自主:一方面,法治国家的制度,必须使一种合理形成意志所具有的交往权力能够存在,并在法律中获得有约束力的表达;另一方面,它们必须允许这种交往权力通过对法律的合理运用和实施而在整个社会中流通,从而通过稳定相互预期和实现集体目标而发挥出社会整合力量。“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法治国赋予交往自由之公共运用以建制形式,另一方面,法治国给与交往权力向行政权力之转化以规范指导。”[5]
[1] 陆玉胜.商谈、法律和社会公正[D].复旦大学,2012.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
[3]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4.
[4] 喻中.商谈理论视野中的法治国原则[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
[5]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6]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DF01
A
1672-5832(2017)12-015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