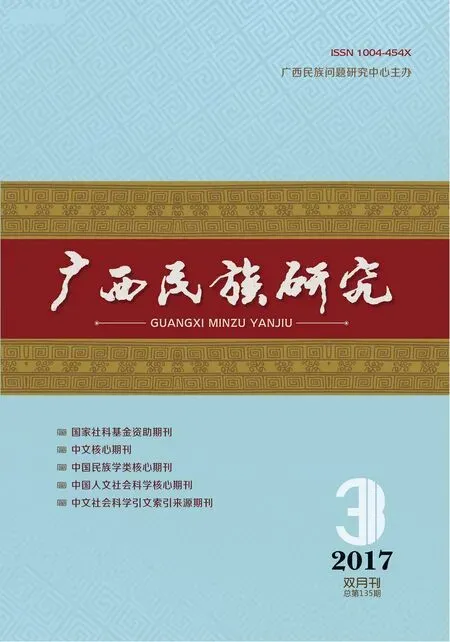多元共生视野下的藏彝走廊族群关系*
——以大理邓川坝为例
李红春 马 滔
多元共生视野下的藏彝走廊族群关系*
——以大理邓川坝为例
李红春 马 滔
位于藏彝走廊云南段的大理邓川坝,汉、白、回等族群共同生息繁衍,和睦共处,演化至今成为区域民族团结的典范。文化调试与族际互动构成了邓川坝族群关系的历史与变迁的两条主线,并显现出环境共居、文化共享、经济互联及社会互嵌的共生特点。
多元文化;共生;互嵌
人类学历来注重族群关系研究,从“经典进化论”把族际关系诠释为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到“传播学派”开始考虑族际间的互动影响;从研究文化调适,提出“互惠”原则,再到功能学派提出族际互动关系概念;人类学对族际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大量的族群关系研究纷纷指明了族群关系是一个交织着博弈、竞争和融合多维的、历史的、连续性的、动态的互动过程。社会学族群关系理论强调定量统计与指标分析,①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戈登在研究《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第一次从社会学角度提出衡量族际关系的7个因素:文化或行为的同化、社会结构的同化、婚姻的同化、身份认同的同化、族群偏见的消除、族群间歧视的消除、公共事务的同化(转自马戎,1997)。马戎(2004)教授在戈登提出7个因素基础上,结合研究中国族际关系获取资料的可能性,提出了8个影响因素: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人口迁移、居住格局、交友情况、族群分层、族际通婚、族群意识。政治视角指导下的族群关系理论则突出族际紧张与族际分离,②由此形成了社会民族学研究族群关系的种族主义族群关系理论、社会学族群关系同化范式、权力—冲突范式。认同理论过于强调族群意识的工具性功能。现实生活中,族群关系事实更多的是一个彼此消解陌生,共存互融,不断适应,创造共识与熟悉的演化过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族群关系研究对文化调试与族际互动越来越青睐。在主张族群文化的族际价值效应与互动的诸多族群关系理论中,多元文化主义、嵌入性、共生理论是较为重要的几种理论。分别从族群文化的互动关系,强调不同文化载体之间的平等与共存;剖析族群社会与文化的互融关系,探索融合背后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因素;梳理族群共生体系的内容与功能,解释族际共生互补的真实性。族群共生关系是一种多层面的民族共同体适应、共同发展的优化路径,要求诸民族志在合作竞争机制的驱动下,互惠共生,协同共进。[1]费孝通倡导的“美美与共”与“多元一体”理论可以追溯为中国族群关系中较早强调多元共生关系的重要论点。
自古以来,藏彝走廊这个多民族聚居区内各民族基于自我生存发展的需要,形成了长期持续不绝的文化互动与族际共生联系。但是目前学界对于藏彝走廊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化多样性、宗教互尊、族群认同、经济互动等领域,对文化调试与族际互动的研究则相对较为薄弱。位于藏彝走廊南段的大理邓川坝,其族群关系的历史变迁、文化调试与族际互动成为藏彝走廊族群关系的一个典范,显现出环境共居、文化共享、经济互联及社会互嵌的共生特点。
一、差序格局:邓川坝族群的共生环境
作为藏彝走廊区域内一个多种文化与族群频繁迁徙交往的重要地带,邓川坝的社会结构与族群关系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因文化差异与族群边界的持续影响,进而触发了邓川坝族群意识中融合与共生的本能,族群差序格局的存在催生出跨越边界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实践。
地缘纽带邓川坝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东南部近弥苴河入洱海口的一段被山岭让开的“坝子”,是洱源县的南大门,这里是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的交汇区域,东部为马鞍山、西部为覆钟山,因此呈现南北走向。亚热带季风气候及云南西部广阔的高原平坝的自然优势使得邓川坝自古以来地理位置就极其重要。此区域位于云南西北的咽喉要塞,国道214线纵穿南北,成为云南通往滇西丽江、迪庆的必经要道,继续向北则可以通往川藏,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历史上邓川坝是重要的马帮贸易中转站。处于“藏彝走廊”和“茶马古道”核心地带的邓川坝,历史至今人口流动频繁,多元文化与宗教交汇不断,使其成为文化与族际多元共生的理想之地。
历史沿革邓川坝所属的洱源县境内共有28个民族,其中世居民族有白、汉、彝、回、傈僳、纳西、藏、傣等8个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县总人口287833人,其中白族179550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62.4%,汉族87431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30.4%,彝族11642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0.04%,回族6584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0.02%。[2]22-23各民族分布具有因族而居形成村落的“小聚居”特点,邓川坝中部,沿弥苴河及214国道沿线主要为汉族居住,有中所、左所、右所、刘官营、郭官营等村;邓川坝西线主要为白族居住,有西湖、旧州、温水、城西、包头、包中、包尾等村;邓川坝东线为回族居住,有士庞、鸡鸣、三枚村。邓川坝也是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一个重要场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本主崇拜几种信仰并存,并显现出同一民族同时信仰佛教、道教、本主等宗教,同一宗教被不同民族信仰的特点。
共生与差序的并存是邓川坝族群关系的一个核心,差序的客观存在不断呼唤共生的文化实践与族群互动,共生的终及目的在于巩固自我族群的文化自信与认同。在巩固地缘关系紧密性的基础上,却又保持着各自的族群边界,形成族群的差序格局。尽管邓川坝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不断强化族群间亲密的地缘关系,但是在漫长的族际交往过程中,因传统文化和社会差异的差序格局并未消失。但在异族间得到了尊重、承认与包容,而且也会被看作承载族群的一项“光荣使命”而必须做到世代延续。[3]67世居于邓川坝的各族群在地缘基础上获得族际交往的共生环境,进而实现文化分享、生活互助、情感通融的更为宽广和深入的共生关系。
二、文化共享:邓川坝族群的共生文化
文化传播是族群交往中最直观的一种反应,人类学提出“文化传播”与“文化圈”的观点,为理解多民族地区因族际互动而形成的“文化潜移”现象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在邓川坝的族群互动中,区域文化共享的跨族际传播成为族群关系的重要表象,主要表现为“白化”过程,语言、服饰、建筑、习俗的白族文化转化借用,兼有汉、回、彝族群文化贡献的整合。
语言语言的共通,是评定族群关系的一个重要参考量。一个社会对其他社会群体语言文字的吸收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态势与融合程度。[4]151白语是各族群之间最为畅通的交流语言,并成为“共通语”。在普及义务教育之前,邓川坝是一个完全白语的世界,族际交流以白语为通用语。①邓川坝的回族内部以白族话为主,少量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汉族、彝族的白语使用情况主要为对外交流,内部以汉语、土语(彝语)为主。白语不仅是族际交流的共通语言,还成为当地回族的母语。在回族聚居的士庞、鸡鸣、三枚几个村子,回族男女老幼都以白语为主要的交流语言,不仅仅是与白族,民族内部仍以白语为主。白语的族际流行与频繁使用,一方面使得族际交流毫无障碍,另一方面使非“白”族群对白语的认同感得以强化。①以白语为母语的回族在评价白语与汉语的差异时,对白语群体认为白语“好听,语调委婉,通人意”。相比而言,邓川坝周围的汉族、彝族对白语的熟悉程度虽不及白族、回族,但也“会听”(听得懂),日常简单的白语用词也“会说”。南士庞村汉族老人均能够精通白族话,内部也主要讲白族话,大约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内部逐渐以汉语来交流,白语使用逐渐消失。但是,上学的孩子与邻村白族、回族长期接触,他们“会听”,重新掌握白语。
服饰在邓川坝汉、白、回几个族群的服饰文化里,同样表现出对白族服饰的亲近借用。从服饰外观来看几个族群的地方服饰是相同的,却依然存在细微之处的族属差异。回族与白族头巾重点区别是前额的黑纱巾,俗称回族妇女二蝶和白族妇女的一蝶,回族的包头为有尖角形的两层,白族的包头为单层。白族服饰主要由领褂、围裙、飘带和头巾组成。[5]邓川坝的部分汉族老年妇女至今仍然保持着白族服装,白、回老年妇女则一直传承白族服饰。在现代生活中,年轻人不再穿白族服饰,只穿现代时装。时髦的年轻人与守旧的老年人在服饰上显现了邓川坝服饰的两种文化方向。
建筑白族民间建筑深受中原传统建筑风格的影响,采用四合院式。较为典型的白族建筑风格多为四合五天井大院和三坊一照壁。邓川坝一部分家庭建四合院,大多数家庭建一主屋一耳房。邓川坝白式建筑的特点主要表现于屋顶的“斗拱飞檐”设计与墙面的古朴书画临摹。这一建筑特点主要显现在房屋顶端和大门之上,屋顶及正门采取顶部双层“飞檐”的立式结构,上下八个边角均仰望朝天,房屋上房头为鳄鱼,房柱正面檐口为龙凤狮兔四层雕刻,格子门为麒麟,正屋中堂为公鸡图案。[6]26房屋或大门飞檐之下的墙体设计一般为白底方形格子,每一个格子都画或写着精美的绘画与书法。古式为上下两层三间组合的木质房屋,主体色调为木黄色或红色,楼门窗雕刻有精美绝伦且色彩艳丽的精美图案,内容多为花鸟鱼虫之景,其精妙之处还在于雕刻样式的镂空与半镂空。[3]51现代式的房屋主体样貌为形似别墅的三层复式结构,但因屋顶的“飞檐”与色彩等方面“白化”的异常浓厚,亦使这种“复式别墅”的“地方性”特色依然十分明显。汉、白、回几个主体族群的房屋建筑整体一致,外观上没有族群差异。其中,汉、白两族的房屋建筑完全一致,而回族房屋在装修上常常表现为阿拉伯语或伊斯兰教信仰图案,与其他几个族群有所差别。或许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同,回族对白族建筑的模仿更胜一筹,传统的白族房屋建筑大量显现于回族村落。回族家庭房屋直接移植白族建筑风格,甚至清真寺的大殿和唤礼楼(门楼)分别为殿堂和亭楼式,当地人称三转五或五转七,屋面四周翘角飞檐,鳌鱼跃式,屋脊中间莲花台上面有葫芦顶。
习俗除去语言、服饰和建筑的日渐白族化,邓川坝汉、白、回、彝等族群的节庆、婚姻、饮食、情趣等日常习俗在交往中也逐渐融入不同族群生活之中。火把节是大理地区白族和彝族共同的民族节日,如今,邓川坝的不同族群都参与火把节狂欢娱乐,淡化原有节庆的宗教寓意,转换为地方性的一次跨族际的欢庆盛会。另外,流行于小范围区域性的传统“鱼塘会”(商品展会)也是邓川坝的一大地方节庆盛典,受到各族的追捧。受白族婚俗影响,回族婚姻习俗上所传承的整套习俗与仪式,包括仪式习俗的称谓都具有白族文化的地方特色。
在白化的过程中,汉、回、彝多元文化的互动也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许多习俗与文化的踪影难以辨别为何族特有,而往往演化成为一个地方性的共享与发明。如始发明于邓川坝的“乳扇”(奶制品),不仅成为邓川坝白、回两个族群的一项重要经济收入来源,而且对于乳扇的喜好没有丝毫族际差别。乳扇这一地方特产的技艺一直是邓川坝所有族群一个值得炫耀的文化遗产。另外,在日常饮食中,对老少皆宜的酸木瓜、酸梅调味以及冻鱼、乳腐、泡椒泡蒜等地方美食的喜爱更加突显出邓川坝的地方文化特征。邓川坝向来注重庭院美化,大部分家院环境布置中少不了花卉栽培,对山茶、杜鹃和兰草尤其喜爱,这在邓川坝的各个族群中演化为一种地方性文化特征,家家养花,养鸟,户户庭院种兰草、山茶、杜鹃,鲜花盛开、绿树成荫。伴随长期的接触互动,不同族群将自身族群文化因子不断播化到其他族群社会生活中,成为区域性的文化要素,实现了“文化贡献”。
缘于洱海区域白族政治文化的势力与影响,使得邓川坝地方文化显现出“白化”的地方特质,这一地方性的尝试是通过构筑“同质”文化而实现的。在多元文化的差序格局中不断找寻“同质地带”,形成另一“共序格局”的存在(张晗,2014)。语言的客观差异对语言使用者的族群认同来说并不重要。[7]151因服饰、建筑乃至习俗的白族化和地方化,不断建构起彼此的同质地带,并没有对差序格局的存在产生消解作用。可见,共序与差序,同质与差异是同时存在于邓川坝族群社会的两个特质,同质地带与共序格局存在于族群文化和族群意识中,呈现出族群关系中的文化共享结果,族群差异和差序格局则表明族群认同中族际边界的清晰界限。
三、社会关系:邓川坝族群的共生网络
地缘、文化、经济层面的共生是对等的族际互动,社会关系的共生则呈现出交错网络化的特点。伴随族际关系的网络模型的建立,逐渐明晰了族际关系是一种复杂网状关系的实质。邓川坝族群整体以“白化”为核心的文化共享仅是社会共生的一个面向,而在日常的族际交往中,社会层面的交融互动,共生社会网络的运行才是族群共生关系的主要内容。
聚丙烯短纤维混凝土可以很好地改善常规混凝土的脆性,使其的韧性增强,劈裂抗拉强度与抗冲磨性能增强。本文对掺聚丙烯短纤维的水工混凝土进行多数据平行对比分析,在满足试验设计要求的情况下,掺聚丙烯短纤维的水工混凝土抗裂性能与抗冲磨性能都有显著提高。另外,聚丙烯短纤维掺入水工混凝土试验时,混凝土拌和工艺、试件的成型过程、养护方法也很关键,只有这样在实际水利工程施工中才能保证质量。本次研究还有一些不足,如掺入纤维后水工混凝土的抗渗性能、抗冻性能变化情况等需后续继续研究。
政治互信族际交往中政治关系是考量族际关系的重要依据,政治关系直接决定着族际关系的性质与发展。平等互信是族际交往的首要前提,邓川坝历史上没有存在族际政治上的不平等的情况。虽然历史至今白族存在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和文化的强势作用,但是并没有形成民族分化。邓川坝历史上没有土司,不存在民族隔离,历史上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族际冲突。汉、白、回几个族群都生活在共同的地理环境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文化差异较小,族际之间相对熟悉,甚至历史上有过族际结盟互保事件。清咸丰、同治年间,大理杜文秀率领的“回民起义”失败后,云南全境回族遭到灭绝性杀戮,邓川坝也不例外。据当地回族老人介绍,当时一部分白族、汉族挺身而出,不畏风险收留庇护回族妇女、儿童和老人,或掩藏保护在自家,或收为“义子女”,待成人后还宗(宗教)归族(民族),这一患难之恩一直被回族铭记感激。据回族告知,杜文秀起义前邓川坝没有南士庞村,也没有汉族居住。杜文秀失败后受清政府委托监视回民的王、杨、何三家汉族迁来士庞村,形成南士庞村。一段时期里回汉内心存有芥蒂。岁月冲蚀,回汉和睦相处,芥蒂逐渐消解。
经济互嵌交通闭塞的西南边疆,历史上族际之间的物物交换和经济交往使得族际交往变得持久、深入和频繁。由于族群生产自给的局限性,使得建立一个经济关系的统一体成为必然。经济上优势与劣势的双向互动推动了族际经济往来,形成经济交往的互嵌互依。邓川坝的汉族、白族适于耕种的田地多于后来迁入的回族,擅长农作物栽培,粮食蔬菜多有盈余,临近西湖、绿玉池的白族还经营捕鱼养鸭。回族擅长饲养奶牛,贩卖牛马,是制作乳扇、干巴及屠宰牛羊的主要群体。彝族则居住于山区半山区,山地多,适于放养牲畜,且药材山货丰足。
历史上的云南马帮贸易极为兴盛,其中尤以回族马帮的规模最大,其经营活动的范围最广,资金最雄厚,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巨。[8]民国时期邓川坝马帮贸易极为兴盛,约有千余马匹规模,大部分为回族马队。马帮成员主要为回族,也有少部分的汉族、白族被雇为马夫加入马帮。近年来,政府推广种蒜产业,在种蒜、采蒜苔和挖蒜的几个农忙之时,邻村不同的民族都会成为临时劳动力。新兴的现代运输业中,回族占得先机,形成客运、旅游和货运的现代运输产业。回族运输业的成功经验带动了周围的汉族、白族,部分汉族和白族群众也加入到地方运输产业中,有的成为回族运输车队和运输公司的合伙人,有的受雇为司机,与回族兄弟共同致富。
流行于邓川坝的“打賨”是民间传统信贷方式,在市场经济时期则成为强化族群经济联系的一个主要途径。霍曼斯在《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一书中指出:“社会行为也是一种商品交换,这不仅是物质商品的交换,而且是诸如赞许或声望符号之类的非物质商品的互换。”[9]148在资金汇集与个人利益实现过程中,打賨强化了地方族群的经济联系。打賨的跨族际经济参与,通过资金的流动与交换,表明了新时期邓川坝族群经济的整合与互嵌,并获得族群信任与互助的关系效果。以洱源右所镇团结村委会为例,在以士庞、鸡鸣和三枚村回族为主的打賨团体中,在同学、熟人、亲戚等关系下接纳了一部分周边城西(白族)、绿玉池(白族)、南士庞(白族)等村民加入打賨。[10]
宗教互尊宗教的普世性使跨越族际边界成为可能,整合或独立性的宗教生活不约而同地成为推动族际交往的重要契机。汉族主要以祖先崇拜为主,还信仰土地神、灶神、道教和佛教。白、汉、彝几个民族信仰本主,本主庙众多,大湾子彝族“湖南大王”本主庙、绿玉池白族西山本主庙、南士庞汉族本主庙。回族仅信仰伊斯兰教,日常的宗教节庆活动为不同宗教和族群创造了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平台,回族开斋节时邀请其他民族朋友和老人参加宴席,送“油香”(甜点),其他民族的亲友则会送些糖茶回赠回族。春节时,汉、白等族的耍龙队会专门到部分回族亲友家祝福拜年,对回族的饮食禁忌极为尊重,婚丧嫁娶的宴席都会专门制作清真饭菜招待回族亲友。汉、白族每逢接本主、死人送葬时需经过清真寺,出于尊重后绕道举行仪式。
情感互通通过各种密切的个人关系,邓川坝族群之间形成了拟血缘的亲属关系和熟人圈,族群情感互通无阻。地方传统的“拜干爹”“打老友”习俗让文化区隔的汉、回、白、彝等族群之间形成“关系的人们”,成为“熟人”。很多白、汉、彝族与回族结成亲家,拜回族为自己儿女的干爹,或与回族“打老友”成为兄弟姐妹。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邓川坝汉、回、白、彝族都沿袭地方传统,男女老幼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位异族干爹或是老友。
生活交往场景是族群关系最丰富和鲜活的内容,族群关系研究历来重视社会结构及其各种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在拟血缘“熟人圈”及地缘“地方人”的双重影响下,邓川坝的各族群紧密的生活往来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一直传承着互助传统。这一互助传统存在于农事之时,婚丧嫁娶之际,节庆欢庆时刻,以及个人危难之际。南士庞村曾经有一户汉族残疾的夫妻家遭遇火灾,周围回族、白族全村齐力帮助救援,事后回族全村集资3万元帮其建新房。2004-2014年期间,洱源县伊斯兰教协会捐资救助委员会共对邓川坝为主体的各民族240人进行资助,共计资金6万余元。
共居于邓川坝的诸多族群历经频繁、深入、持久的社会生活,不断构建族群文化、社会、经济、心理的“同质地带”,通过拓展社会网络,维系了族群之间的归属感与亲密性。由此,邓川坝族群间社会生活的亲密产生了政治互信、经济互依、宗教互尊、生活互助、情感互通的关系效应。
四、共生互补:邓川坝族群的共生策略
通过经济互补、文化互补、宗教互补一系列的文化实践和族群动员,在共生的社会空间中实现了熟悉与亲密。某一族群对于其他族群的生存而言,在共生社会文化构建的过程中起到媒介作用。汉族的文化体系深受邓川坝各族群的向往,教育资源与文化的辐射作用实现了汉族与其他族群的交往;白族的语言、服饰、建筑文化成为汉、回乃至彝、纳西等族群竞相模仿的文化典范;回族的经济成就与清真美食在族际交往中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成为迈向现代的一个鲜活范例;火把节、端午节等节庆娱乐弥补了汉族、回族娱乐生活的真空。
强调族际共生,并不是不存在摩擦和冲突。邓川坝的族群关系呈现出族群之间融合、竞争、共生等多维场景。①在邓川坝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族际个体间的族际摩擦,以及“一截骂一截”的族际心理隔阂。然而,邓川坝族群关系的历史主线一直是将竞争的生存本能不断转换为族群融合与共生的文化实践与族群互动。共生互补、彼此互依始终成为推动邓川坝族群经济互嵌、文化共享、社会互动的强大动力。
共生互补是生存策略的重要表现,显现出族群面对异文化、非传统抉择的一种行为意识与文化心性。族群关系常表现为两种态势,或因“排斥”而发生“冲突”,或因“互补”而谋求“共生”。众多实例证明,不同社会的“差异”不是“冲突”的根源,关键在于文化主体间对待“差异”的态度,相反,“社会共生”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与众望所归,在“差异”中谋求互补共存的“共生格局”不仅是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基础,更是文化承载者利用“共生”为武器,在有限的资源中合理分享资源的生存智慧。[3]66可以看到,共生意识消弭了资源争夺、族群边界、意识差异等负向解构社会要素的凝聚,整合为生存发展的智慧,强化地方性的文化建构与认同意识。
五、结 语
在众多藏彝走廊研究视角中,差序格局、多元文化与社会共生显得尤为重要。差序是现实,多元是过程,共生是结果。处于多元文化交汇之中,各族群的主观意愿都是希望在社会生活的每个画面中能够找寻到自身的族群性(ethnicity)踪影。面对多元利益关联与生存压力的现实,族群社会总是在谋求与其他群体的共同之处来跨越边界。在文化藩篱的微观视野里,更多的是通过构筑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经济纽带、社会网络等方式的族际互动,转换为族群间的熟悉和亲密。
多元与共生是藏彝走廊的两个特征,多元是事实,共生是机制。藏彝走廊中族群文化和族群关系蕴藏着丰富的理论知识与经验探讨,透过族群多元文化构建与社会共生整合的观察,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也是探索相互嵌入式民族关系的重要捷径。
[1]袁年兴.共生理论: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视角[J].理论与现代化,2009(3).
[2]洱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洱源年鉴2011[M].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12.
[3]张晗.共生于文化碰撞的中间地带:大理邓川坝“白回”的族群认同实践[D].云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4]马戎.民族社会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赵卫东.族群服饰与族群认同——对“白回”族群的人类学分析[J].民族艺术研究,2004(5).
[6]王亮斗.回乡文集[Z].内部资料.
[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姚继德.云南回族马帮的组织与分布[J].回族研究,2002(2).
[9]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0]李红春.藏彝走廊邓川坝“打賨”的经济人类学解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11]张丽剑.从族际接触、多元一体到共生互补——对湖南桑植白族“连理会”文本的解读[J].铜仁学院学报,2012(6).
[12]袁年兴.从多元走向一体:民族关系演变中的共生学取向[J].学术月刊,2010(9).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ZANG AND YI CORRIDOR IN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A CASE STUDY OF DENGCHUAN IN DALI
Li Hongchun,Ma Tao
Located in Zang and Yi corridor,Dengchuan in Dali,Yunnan province,a place of Han,Bai and Hui ethnic groups living together in harmony,has been evolving into a model of regional ethnic unity.Cultural adjustment and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have become the two main threads of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history and changes of Dengchuan,showing symbiotic features of environmentally cohabitation,shared culture,economic linkage and mutual-embededness in society.
cultural diversity;mutual-embededness;symbiosis
C912.4【文献识别码】A
1004-454X(2017)03-0085-006
﹝责任编辑:袁丽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研究创新团队”。
【作 者】李红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滔,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员。昆明,65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