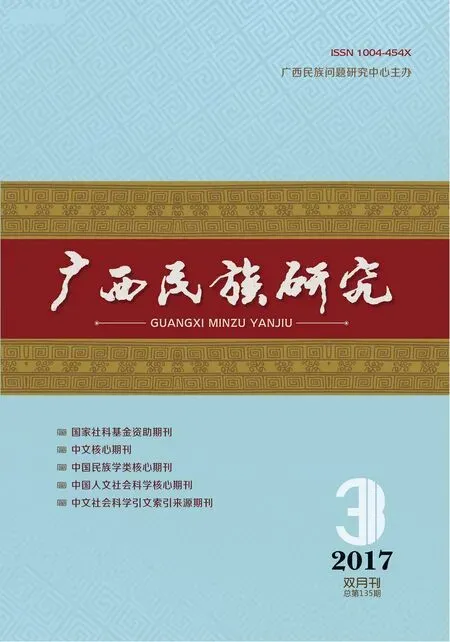民族政策对族群关系现实的偏离与纠正
卢小平 种航飞
民族政策对族群关系现实的偏离与纠正
卢小平 种航飞
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机构识别和建构的民族政策问题,与社会现实的族群关系问题之间,存在一定的偏离。这种偏离使得民族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受到了较大影响,其政策目标也相应地出现了偏离。在社会多元化环境下,民族政策中存在的这些情况,若不能得到调整和改变,将会对我国族群团结、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为了克服民族政策存在的这些问题,需要纠正对民族问题的泛化理解,将涉及族群因素的政策更多建立在市场、公共服务基础上,在族群间建构多维联系纽带。
民族政策;族群关系;公民导向
近几年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陆续发生了一些极端事件,在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的同时,更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民主政治不断推进、公共事业日益完善的形势下,边疆民族地区部分人群的极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仍然发酵,值得我们深入反思。本文认为,在影响当前民族地区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发酵,进而引发一系列极端行为的诸多因素中,我国现行民族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一方面在解决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人权等现实问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另一方面它在内容设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偏差,也对边疆民族地区部分人群思想、行动发生偏差起了一定催化作用。而民族政策的这种复杂影响,从根本上来说,与民族政策设计思路,特别是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政策问题的建构有关。
一、中国社会族群间存在的现实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族群间的关系纷繁复杂,总体来说,族群间关系以交流—融合为主流,但也伴随着不时发生的矛盾、冲突甚至激烈斗争。正是不同族群长期以来的激荡融合,奠定了中国社会族群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难以清晰区分,难以割裂、分离的格局,形成了自在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以及维系这一共同体凝聚力的中华文化。
在近代社会,当中国遭遇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并引入西方民族—民主国家理念之后,中国古代形成的自在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日益觉醒为一个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然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的过程中,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在自觉的进程上出现了不一致,部分在中国社会相对处于边缘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发生了偏差。在中国推翻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并建立现代国家之后,导致中华民族分支成员认同偏差的内外因素并未消失,因而族群间关系问题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融合到了一起,便成为现在我们所认识到的“民族问题”。
近代以来,部分边缘化社会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发生偏差的内外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发展不均衡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不同区域间、不同族群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这种发展差距在传统中国由于政治—社会管理模式的局限,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缩减,反而不断扩大,进而使得部分边缘化社会成员,特别是边疆地区少数族群中部分成员,与主流社会之间经济、文化、心理裂痕不断扩大。传统中国“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模式,固然在边疆地区以低成本维持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却也使得这些地方的权贵阶层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利益,同时在民间形成了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绝的政治治理方式与文化、生活方式。因而,当整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进程启动后,民族地方特权阶级面对民主政治可能带来的利益消亡威胁,极力反对现代化;而民众由于对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缺乏了解,对整个国家缺乏认同,也缺少参与现代国家建构的主动性。这使得边疆社会特权阶层很容易利用歪曲的民族主义思想,渲染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以抵制现代国家建构工作在民族地区的开展。
(二)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对民族主义工具的误读误用
西方早期发展起来的现代国家,无一例外地借用了民族主义这一社会动员工具,以整合社会成员,发动反对传统国家统治阶层或境外侵略势力的社会革命。英、法、美等早期建立的现代国家开展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实质,是在既有国家疆域内,通过思想文化运动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的宣传和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应、市场主导的经济资源重新配置,将一盘散沙状的国民凝聚成具有高度政治共识、拥护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价值和革命号召的政治共同体,是公民导向的民族主义。或者可以说,现代国家建构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服务和服从于现代国家政治价值普及和政治制度建设的。然而,民族主义运动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却发生了变质,从整合传统国家国民的工具,转变成了部分社会精英以族群意识、情绪为依托,瓦解既有国家,实现部分社会精英特殊政治、社会利益的族裔民族主义。而中国近代部分社会精英在开展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却未能正确区分这两类民族主义,使族裔民族主义这一偏离现代国家建构宗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过度传播,进而使得中国现代国家革命和建设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和某些地方社会精英借助族裔民族主义分裂中国的企图。
(三)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分化策略
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一直发挥着极其恶劣的影响,想方设法延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分化中国甚至肢解中国。体现在族群关系方面,则主要采取分化、瓦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分裂中国,以降低其侵略、奴役中国成本的策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采取典型的双重标准,极力否定、贬损中国公民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现代国家建构工作,而支持中国境内部分边疆社会精英的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如中国“本藩”两分论、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权”而非“主权”论、中国对新疆“殖民”论等。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这种侵略策略,与中国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使中国近代早期族群间关系一度恶化,族群团结、边疆稳定、国家统一局面遭受空前挑战。
基于这三大因素,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并非西方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政治共同体问题,而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面临的内部政治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工作完成不彻底,由地方分离主义势力和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借助被歪曲的民族主义工具制造出来的问题。
二、我国民族政策问题的识别与建构
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民族问题,比较合适的解决办法,是遵从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规律,将整合国民的公民民族主义运动,与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开放性的现代国家政治价值、公共服务、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卓有成效的现代国家建构工作,消除由于历史因素形成的区域间、群体间差异,进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在以共同政治价值为核心的多维纽带作用下,凝聚成牢固的政治—社会共同体。“建构起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强化其爱国主义情感和凝聚力,是现代国家治理社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内在的本质要求。”[1]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就坚持了这一方向。我国当前民族政策体系虽然庞大而复杂,但如果从逻辑上去解剖,其问题识别、建构并不复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的民族政策问题建构:
(一)在坚持中华民族一体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存在族群、区域间差异性,并将之作为公共政策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
我国民族政策的起点,是对中国社会存在族群间、区域间差异性的承认和尊重,并将之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去对待。在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工作中,解决族群间、区域间差异性问题,是一项重要任务。
(二)以维护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与统一作为涉及族群间、区域间差异性的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
即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唯一政治—社会基础,[2]其他族群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分支成员和文化共同体,不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对等的政治共同体。这与苏联和其他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双重民族、双重主权有着重要的区别。
(三)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矛盾主要是族群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在中华民族一体的前提下,由于族群间、区域间差异性而引发的矛盾,虽然表现形式多样,但其核心问题,是族群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涉及族群因素的公共政策,基本上都围绕着如何消除族群间、区域间发展不平等来设计。
(四)国家赋予特定区域、群体以特殊权利,以更好地解决族群间、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其关键内容都是赋予特定区域和人群以特殊的权利,进而使之在发展过程中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可以获得更多资源,以缩小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导致的发展差距。
三、民族政策实施过程中与现实族群问题的偏离及其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设计的民族政策,出现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受当时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被歪曲解读的族裔分离导向的族裔民族主义的痕迹还比较重。因而使得我国民族政策在政策问题识别和建构过程中,虽然总体上遵循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规律,但却未能将公共政策完全建立在公民身份基础上,而是掺杂了较多族裔民族主义因素。虽然这些族裔民族主义因素并非我国民族政策的主流,但其影响却深远而危险,特别是在我国社会整体走向开放、多元的环境下,民族政策中族裔民族主义因素成为引发地方狭隘族群意识,激化区域、族群间矛盾冲突的重要诱因。狭隘族裔民族主义的因素的渗入,已经使得民族政策所要达到的整合、凝聚国民,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目标发生了偏离。
我国民族政策在识别和建构政策问题时,之所以会掺入较多族裔民族主义因素,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晚清以来内外交困的局面使部分区域基于族裔民族主义的分离倾向非常明显,族群间和谐共处出现障碍至中共民族政策构建时已经是既存事实
鸦片战争后,由英国人用“宗主权”理论包装的西藏与中央矛盾;由英、俄两国支持,建立在经过精心杜撰的突厥历史、被歪曲的伊斯兰宗教思想体系基础上的新疆与中央矛盾;由于狭隘族裔民族主义思想的介入,已经从传统社会单纯的封建王朝内部矛盾,均变成了具有族裔民族主义性质的分离运动。这类矛盾在此后随着殖民侵略势力的深入,在中国不断扩展、恶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恰恰形成于中国边疆危机最为深重的时期,当时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精英普遍认为,一般的政治手段包括西方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已经难以维持中国国家的统一和族群的团结,因此试图通过承认文化族群特殊政治权利,以避免边疆地方采取激进分裂措施。
(二)苏联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思路的深刻影响
由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与苏联这个“老大哥”关系紧密,因而苏联建立在“民族自决”基础上的民族治理理论、政策和工作方法,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思考。这使得苏联处理民族问题过程中形成的混同文化族群与政治民族;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赋予特定族群以特别的权利或利益;行政区划不完全按照行政管理技术需要,而主要考虑不同族群人口分布特点,并在少数族群占主导地位的行政区域推行特别的行政管理制度、政策措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自成体系的维护少数族群权利的组织机构等经验与方法,几乎被完全照搬到中国来。
民族政策中族裔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使得其中部分内容在设计、实施过程中,过度地将族裔身份与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这对于在社会整体发展中处于后发位置的区域、族群获取更多发展资源有利,但这些措施的实施却在心理与现实两个层面,制造或扩大了社会成员间的裂痕,使得族群间本来模糊的界限因为政治权利、经济利益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分配的介入而变得清晰。更为严重的是,族裔身份、行政区划与特殊政治权利的结合,在某些人心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特定族群是特定区域的主人,是在这片区域具有特别政治权利,甚至是应该独立行使政治权利乃至主权的群体,是中国社会的特殊公民。这种观念非常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以制造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社会骚乱。“藏独”势力、新疆“三股势力”,它们在其分裂国家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宣传中,都有将“族群—行政区域—特殊政治权利”捆绑的内容。在内地,虽然公然鼓动民族分离的思想缺乏现实基础,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歪曲理解国家的政策,将自己特殊的族群身份,用作否定当地政府、社会正常的行政管理、市场管理规则的工具。而来自边疆的分离主义活动和内地部分群体的特殊公民意识,又反过来导致其他群体的响应。这使得我国本来相对淡薄的族群意识出现激化的趋势,族群间关系张力不断收紧,进而累积了巨大的风险。
四、民族政策内容的现实回归
民族政策中族裔民族主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会变得尤其危险。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对社会的管制将会不断放松,社会多元化趋势将日益明显,国家政治权力重心将会不断下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族裔民族主义情绪得不到及时消除,那么它必然会成为一些社会成员争取市场竞争优势、特殊政治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工具。而在一个思想、利益及权力日益多元的社会,民众由于现实利益的影响,辨别和抵制族裔民族主义思想的困难将大大增加。由于族裔民族主义是以其他族群和国家为对象,以族群在政治上的完全独立为最终目标,以排他性极强的敌对情绪渲染为主要内容行动策略,这种思潮一旦扩散开来,国家将永无宁日。有鉴于此,我国的民族工作理论和民族政策体系,有必要结合我国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淡化族裔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使民族政策真正成为服务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服务于中华民族建构的政策工具,而不是引发族裔裂痕的因素。
(一)纠正将一切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等同于民族问题的思维惯性
首先我们需要纠正那种将一切涉及少数民族成员、少数民族居住地方的问题都等同于民族问题的思维惯性,将少数民族身份、居住区位与公共政策设计与实施、公共资源分配分开来思考;将涉及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一般问题与民族问题分开来思考。特别是各级公共管理主体,要对什么是民族问题,什么是非民族问题保持足够的政治敏感性,不能过度屈从于狭隘族裔民族主义势力的压力。例如笔者在北京、广东、浙江等省市调研过程中就发现,当地部分市、县政府工作人员在面对大量涌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时,极度缺乏这种敏感性。少数民族商贩在部分城市,公然违背城市管理、市场经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但由于其少数民族身份,当地政府管理部门不敢管、不想管、不去管。或者在管理之后,遭遇少数民族商贩基于狭隘民族利益观提出的不合理诉求,便一味妥协、纵容。这种公共管理方式,无疑会更加强化部分少数民族成员“特殊公民”“特殊市民”身份感,若不彻底改变将会使得更多的少数民族成员效仿,进而使所有涉及少数民族的一般公共管理问题被泛化理解为民族问题。
(二)纠正区域发展、帮扶政策过度掺杂族群因素的做法
由于我国大部分后发地区都处在中西部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恰恰是少数民族聚居程度较高的区域,因而使得我国从政策决策层到普通社会成员都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我国整体上存在民族地区与一般地区的划分,民族地区是我国的后发地区,民族政策主要就是解决后发地区问题的政策,为了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必须从民族、地区两个特殊性出发来考虑政策设计。但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科学。
在我国人口总量中,少数民族(文化族群)人口直到现在只占全部人口的8.49%,少数民族人口总量1.1亿。即使不考虑中国的少数民族身份真实性(因为民族政策,我国存在大量虚报民族身份的人群),就以当前统计数据来看,在人口超过1亿的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并不算高。例如美国主要人口是英国移民后代,占60%~70%,其他族群人口占30-40%;印度则有数百个族群,人口最多的印度斯坦族只占总人口的46%左右;俄罗斯、印尼等人口大国,少数族群人口比例也高于我国。我国人口分布现实也难以真正区分出一般地区与民族地区。我国内地省级区域中,除了西藏自治区外,其他省区没有一个少数族群人口过半,每个省级区域族群成份至少都超过30个,在每个县级以上区域都至少有2-3个族群成份。在我国正式认定的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人口总体只占47.7%,绝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主体民族人口比例低于50%。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我国各地族群结构将变得更加多元,各族大杂居的态势越发明显。
同时,我国后发地区当前面临经济社会问题,主要是一般性的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这些问题基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或社会管理方法、技术就可以应对,而不必也不应强调其中的民族因素。从世界范围应对民族问题的经验来看,解决民族问题较为成功、境内族群关系较为融洽的几个国家,都没有将国土分成非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进而在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公共服务与这种划分相结合的例子,如美国、巴西等。而将国土按族群分布划分的国家,或者出现了强烈的族群分离运动,或者已经开始转向否定民族与非民族地区的区分,否定基于民族身份、民族区域的特殊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安排。如苏联已经分裂,其后继者俄罗斯则对苏联时期民族政策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中非国家卢旺达在经历严重族群屠杀后,在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区划、公共服务供应等许多方面,都刻意淡化族群因素的影响。
为此,重新思考如何应对我国存在的区域间、群体间发展差距问题,在设计后发地区扶助、发展政策时,逐步弱化族群因素影响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三)以市场机制、公共服务的手段代替民族身份作为资源分配的工具
在我国民族政策体系中,基于民族身份进行的资源分配是关键性内容,这种分配模式所基于的前提假设是我国社会成员发展的不平等,与族群人口结构具有高度重叠性,而族群人口又是可以清晰认定的。
然而,这两个前提假设本身却存在问题,甚至是错误的。首先,中国社会成员发展的不平等是多元化的,并不仅仅与族群因素关联。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区域、城乡、行业、性别、族群等多种不平等,即使同一片区域、同一个族群内部,不同成员之间发展差距也非常显著。其次,中国社会的族群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根本无法准确认定哪些人属于哪个族群,因而基于民族身份所做的资源分配,在识别民族身份的阶段,就必然会出现偏差和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高考、干部竞聘、就业机会等现实需要而修改民族身份的现象屡禁不止,正是民族身份模糊性的体现。而基于民族身份分配社会资源的更为深层次的影响,会在部分社会成员中造成特殊公民观念,使民族意识凌驾于公民意识之上,使现代国家普遍性、平等性的政治价值、公民精神、市民精神,在被特殊对待的人群中无法生成。
为此,在未来国家针对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后发区域的发展政策设计过程中,应该逐渐弱化民族身份在各类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作用,采取现代国家的普遍性做法,将社会资源分成应该由市场配置的和应该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配置的两大类型。对于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国家除了依据市场管理法规进行间接的调控和管制之外,不应过多干预,以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对于应该由政府公共服务配置的资源,则应该基于现代国家民主、平等的要求,均等化地向国民提供。对于弱势群体,国家应该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性标准去认定,并出台相应的扶助措施,而不应该过度依赖于相对抽象的价值、文化标准去认定,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帮扶政策。
(四)建构多维纽带促进社会成员进一步融合
西方国家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处理族群间关系问题时,过度强调族群的特殊性,或者过度忽视族群的特殊性,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合适选择。过度强调族群的特殊性,进而在政策上设计一系列特殊措施以维持族群的特殊利益,会使族群间界限清晰化,进而使得公共政策无形中成为推动族裔民族主义运动的帮手;但过度忽视族群利益,则无疑会使得国内部分文化群体现实存在的特殊困难得不到有效化解,进而使之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出现日益扩大的裂痕,最终也会导致族裔民族主义情绪滋长。[3]
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格局,相关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而不是采取最容易做到的所谓‘一刀切’”[4]。对待境内族群间各方面差异,特别是发展差距的时候,采取综合性措施,在不突出族群特殊性的前提下,为不同族群成员的交流、融合提供多种渠道,进而在不同族群间建立多维联系纽带,在推动族群相互交往与融合的过程中弥合其客观存在的差距,是多元族群国家比较合适的选择。“要使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同时成为加快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及干部的对流的过程,成为促进各民族团结交融的过程,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过程。”[5]要在实现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目标导向下综合思考政策内容和实施方式,而不能让相关政策和措施滋生或者强化族群间分离意识。
目前我国一些地方之所以有少部分人对狭隘族裔民族主义思潮缺乏免疫力,其原因恰恰就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渠道去了解、融入主流社会和参与主流社会的发展,分享主流社会的进步成果,进而使之难以形成对现代国家、现代政治价值以及作为现代国家载体的政治民族的认同。“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共同文化与观念,在族群层面上的不同文化就难免会彼此冲突,无法和谐相处。”[6]例如在西藏不少地方,由于交通、通讯、广播等基础设施的欠缺,居民在经济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在心理与文化上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很难接触到来自内地的文化信息,很难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优质公共服务,导致了国家、政治、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等观念对于他们而言都是非常陌生的东西。所以,就这些地方的族群来说,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不是民族身份与民族权利保护的问题,而是通过哪些渠道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和分享主流社会利益、价值的问题。
[1]胡鞍钢.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3]王建娥.民族冲突治理的理念、方法和范式[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4]郝时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理论性与实践性[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5]朱维群.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N].学习时报,2012-02-13.
[6]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
〔责任编辑:黄仲盈〕
THE DEVIATION OF ETHNIC POLICY TO THE REALITY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CORRECTIVE
Lu Xiaoping,Zhong Hangfei
There exists certain deviation between the issue of ethnic policy that identified and constructed by the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 of public polic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ethnic relations in social reality.Such deviations create great impacts on the plan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hnic policy,and so as to the deviation of its policy objectives.In a pluralistic society,if such problems existed in ethnic policy cannot be adjusted or changed in time,China’s ethnic unity,social stability would be affected negatively.In order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we need to correct the generalized understanding of ethnic issues,to establish the policies involving ethnic factors more on the basis of market and public services,to construct multi-dimensional bonds among ethnic groups.
ethnic policy;ethnic relation;orientation of citizenship
D633.0【文献识别码】A
1004-454X(2017)03-0041-007
【作 者】卢小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种航飞,中央民族大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