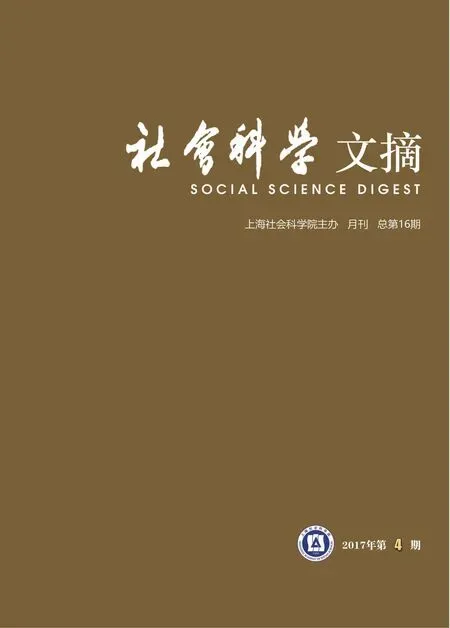简论意境与禅境之别及其绞缠
文/顾祖钊
简论意境与禅境之别及其绞缠
文/顾祖钊
1992年,拙作《艺术至境论》出版,书中意境论的主要观点写入了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沿用至今;后来《文学意境的特征》一节,又被编入上海市高中《语文》教材,使用多年,算是有了一些学术影响。可是,杨矗先生在《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发表的《王维的禅境与意境》一文对我的意境研究提出批评,认为“对禅境的遮蔽是我们当代意境理论的重大缺陷”,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禅境与意境的绞缠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难题之一。近年来我留意了佛经和禅宗,并认真拜读了李壮鹰先生的《禅与诗》,蒋述卓先生的《佛教与中国古典美学》和张节末先生的《禅宗美学》等大作,终于可对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了。
意境的主要特征及其与境界的区别
旧时文人多不分意境与境界,这是中国古代文论家模糊性思维的表现,王国维也受过这种模糊思维的影响,一度在“境界”与“意境”两个概念之间摇摆。《人间词话》开篇便倡导“境界”论:“词以境界为最上。”然而一篇未了,又冒出了“意境”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从这里强调的“最上”和“第一流”看,文中涉及的“境界”和“意境”实为可以互换的概念。如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诗词皆然。”这是想对“境界”有所界定。而在《宋元戏曲史》中,他却用几乎同样的话界定了“意境”。其云:“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这说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多次的采用“境界”概念,实际上说的是诗词中的审美境界或艺术境界,即“意境”。虽说《人间词话》使用的主要是“境界”,但就其一生倾向而言,主要还在“意境”上。《人间词话》定稿的前一年,即1907年,他还在《人间词乙稿·序》中三用“意境”概念。而在成书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史》中,他又郑重其事地采用了“意境”范畴,并连用“意境”概念评鉴诗词、元曲凡五次,却一次也没有再使用“境界”。这说明王国维在“境界”与“意境”之间,已经有了更为理性的选择。
王国维最终选择“意境”论诗词大有深意。首先,“境界”是一个使用普泛的模糊性概念,只要是说事物所处的某种境地,都可以称“境界”。例如,东汉郑玄在解释《诗经·江汉》之“于疆于理”时,将“境界”理解为国家的“疆界”。而出现于当时新译佛经中的“境界”,已被虚化。东汉支娄迦谶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另译名《无量寿经》)有云:“比丘白佛,斯义宏深,非我境界。”“境界”以虚化的形态首次出现在这部佛经中,支娄迦谶如此翻译,必有所本。《庄子》中虽说没有“境界”的概念,但有着明显的境界论的思想。《秋水》中,河伯在北海若面前深愧自己心中的境界“见笑于大方之家”,井底之蛙在东海之鳖面前“规规然自失”,都觉得自己心中的境界不如人家的境界宏大。而支娄迦谶对境界概念的翻译和运用,正与此在思路和逻辑相同。自从境界概念进入佛经,佛学便把它变成了一个有特定涵义的佛学用语。由于“境界”一词在佛学中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历经东汉、六朝、隋唐至北宋千余年间,人们都不以境界论诗。南宋之后,境界概念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的确频繁起来,但仍较少在意境论的意义上使用,而是被泛用在文学牵涉的各种元素和领域内,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有十余种涵义之多。此外,它还可以广泛应用于思想境界、道德境界、人格境界、学养境界、哲学境界、宗教境界以及武术和体育等活动。总之,它是一个宽泛无边的模糊概念。虽然文学作品中的意境,也是一种境界,但“意境”是一种指称明确的专指性概念。若用涵义模糊的“境界”概念取代它,不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很不恰当的。王国维最终放弃以“境界”论诗词,而选取了“意境”范畴,是逐步克服模糊思维,趋向现代学术规范的做法。
其次,王国维对意境称谓选取的同时,也对它作了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现代转换工作”,特别是对抒情和“情真景真”的特点的强调,为意境划定了一个适应的范围,不像“境界”那样没边没沿。这会让那些企图让意境论统辖整个文学世界的现代学者无地自容。由此看来,王国维对“意境”称谓的最终选择,是一种理性自觉的表现。
再次,“意境”是“用直觉”,靠“某种直接的领悟”得到的概念,所以,意境的范畴史几乎与中国古典文学史一样长久。在前范畴阶段,意境的典范形态已经出现,如《诗经·蒹葭》已把民族审美理想中的意境美完美地呈现出来;“庄周梦蝶”的故事已经把意境美形成的双向交流、主客共鸣的模式揭示出来。所以意境论发源于中国文化艺术,而不是佛教、佛经等什么外来的东西。在意境论萌发的阶段,以“境”论诗可以说自刘勰始。《隐秀》中论述的“蕴藉”和“蓄隐”,这就涉及诗歌意境。“境玄思淡”准确地概括了阮籍诗的意境美。《隐秀》几乎成了意境论的专章。盛唐以后,便进入了意境论成熟和称谓的选择期。王昌龄的《诗格》以“诗有三境”说影响天下并远播东瀛。中唐之后,“诗境”被广泛接受。白居易就有“闲中得诗境”“诗境忽来还自得”的诗句。皎然提出“缘境不尽曰情”,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司空图提出“思与境偕”,权德舆提出“意与境会”等已包含着对意境非常深入的认识。不想,五代人孙光宪(?~968)却给诗境提出了一个“境意”的新称谓。北宋南宋基本上都以“境意”论诗,除叶梦得重提“意与境会”,“意境”的概念始终没有破唇而出。元人赵汸(1319~1369)在评杜甫《江汉》诗时说:“东坡诗‘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亦同此意境也。”此后,就再也没有人以“境意”的论诗了。明清以后,多数学者基本上以意境论诗,意境范畴史才算进入了称谓的确立阶段。而王国维的选择,正符合这一历史的逻辑。
综上所述,中国抒情诗论为什么弃“境界”而取“意境”,这里有几点值得明确。第一,意境是民族理论智慧长期孕育的并确定的针对诗境和审美的专业术语,而境界只是一个用处广泛的模糊概念,在佛教中还有其特出涵义。第二,意境范畴具有审美性和理想性,符合审美活动和艺术至境的要求;境界却是一个地道的中性范畴,具有理想性和审美性的境界仅是境界使用领域的极小部分,混淆二者,在学理上是不通的。第三,中国意境论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一切关于意境的言说首先应该尊重这种历史,不应把华夏民族的东西硬说成外民族的东西。
禅境为什么不能与意境相混?
意境论的历史和专业性告诉我们,并不是随便什么概念、什么境界能够取代的。但学界有人却硬说“禅境乃中国意境之魂”,说我的意境研究抹杀了“禅境”。要弄清这样的问题,还必须从弄清禅境的特殊内涵说起。然而要正确理解“禅境”,必须有个前提。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具正法眼者,是谓第一义。”他意思是说在讨论禅宗时应以“正宗”“正道”为标准。这个说法虽然连他自己也没有做到,但就这个主张本身而言,还是正确的。谈论禅宗问题,首先应确定以何宗何派的说法为标准。佛教门派的复杂性,这里暂不去管它,仅就禅宗而言,中唐之后历史便有了结论。由于六祖禅师慧能的理论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所以,南宗很快地取得了禅宗的正统地位,在全国传播,而由神秀开山的北宗,日趋式微,以至消亡。柳宗元撰写的《大鉴禅师碑》中说:“天下言禅者皆本曹溪”,应当是历史的真实。
慧能《坛经》中将南宗“法门”概括为三个要点:“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其中的“无相”最为关键。他说:“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诸相,则体清净”,才能做到“无住”,不执著、不牵挂于外物,才能实现心无杂念的“无念”的目的。关于“坐禅”与“禅定”的定义,也在这个意义上展开。其云:“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又云:“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禅宗(南)修练的主要方式是坐禅,而坐禅的目的便是要达到一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而“心念不起”的无牵无挂、唯见“自性”的境界,这便是禅境。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通过“禅定”来解决。而实现禅定的关键是“外离相”,即坐禅时要努力排除一切外在形象,因为,“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坐禅的一切目的都无法实现,所以又有“般若无形相”“离一切相即佛”之说。《金刚经》中也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看来,禅境第一的、或绝对的特征,便是“离相”或是“无相”。
其次,禅定的目的是心的“不动”“不乱”,“外于一切善恶境界”。而要外于“善恶境界”,除了“离相”,还须“离情”,即排除一切情感的因素,“心不乱”,即不被外界一切善恶是非感染而生情,“心不动”,即禅心不为外界的善恶、是非之情所动。慧能认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以便“內见自性不动”,以达“禅定”而入禅境。于是,禅境便有了第二个特征即“离情”,离开世间的情感纷扰或“无情”。因此,蒋述卓先生说:“在佛教那里”,“情是需要排除的对象”。李壮鹰先生也说:“禅宗则是排斥感情的,在他们看来,感情是人们执着于有限事物的表现,如果超离了有限事物,回复到空明寂静的本来心,那是不会发生感情活动的。”
论述至此,禅境与意境的区别已经泾渭分明。意境讲究“情真景真”,而禅境则追求情、相全无!禅境的这两个特征便使一切所谓“禅宗美学”,“佛教美学”的罗织,成了“皇帝的新衣”。试问,无情无相(“相”,换一种说法就是“景”)哪来的美?
其实,意境与禅境在思维的性质、方式和结果上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就思维的性质而言,对意境欣赏是一种本能式自发性思维,它的发生是由人的爱美天性使然,自发地、自由地产生的,基本不需要对象之外的条件;而禅宗的思维则是一种目的性思维,要进行这样的思维必须有一种自觉的目的性追求的冲动,并不能随时随地自由发生。就思维的方式而言,意境的思维是一种审美互动的双向思维,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刘勰从理论上概括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我在2003年就揭示了审美思维的双向性,蒋述卓先生也发现了这一点。在这种双向运动过程中,人的生命和思维一直处在愉悦的积极的活跃状态,其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美感享受。而禅境思维却是一种不断地回归内心、寻求解脱的单向的运作过程。李壮鹰先生认为禅宗采用的思维方式是“减法”,即要把客观世界存在的一切,乃至主观的经验和思维,都从脑中减去,“减之又减,最后我们脑子里剩下一片虚空”,只有一个“自我”,“再也取消不了了”,这才是“实在的本体”“禅家的‘心’、亦即佛性”和“永恒的真相本身”。蒋述卓先生则进一步指出:禅境思维“最后的目的却是要‘息心’,要‘泊然若死’”,“使生命力进入到宗教幻想中去得到解脱”,“它只能使现实的生命力萎缩”,所以艺术意境与禅境在思维的“最后的归宿(也)是截然不同的”。李、蒋二先生的概括都很精辟。禅境的最高追求是佛教的“涅槃”,即生命的“不生不灭”之境,此时心无一念,“泊然若死”而归于冥寂。质言之,禅境是一种宗教境界,并不以审美为追求,故不能以审美言说之;意境则是一个鸢飞鱼跃,活泼飞动的生命境界、审美境界。因这些不同,更使禅境与意境界判天渊。若要理清诗与禅的关系,理应从这一角度出发。
怎样理性看待诗与禅绞缠与误解?
既然意境与禅境不同,于是对待文学史上诗与禅的绞缠与误解,便有了区分原则和标准。可将这一复杂纷乱的文学现象分为四个方面来梳理。
其一,应当肯定那些比较合理的理论和现象。对于诗境与禅境的不同,第一位明白人是刘勰。他本人深通佛学经义,所以特别不敢以佛学混乱诗学,所著《文心雕龙》,其“原道”“征圣”“宗经”“辨骚”“明诗”各篇,特别着重阐释中国诗学传统,几乎连一丝佛光禅影也没有出现,不仅首次以“境”论诗,而且明确提出“覩物兴情”“为情造文”,这就为诗境与禅境设置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第二位是唐代诗僧皎然。除了文化学养、知识结构与刘勰相似外,历史语境却为他预备的十分混乱的理论前提:隋唐以来儒道释三元混一已成一股思想潮流;盛唐时甚至出现了像寒山、拾得那样的似儒非儒、似道非道、似僧非僧、亦僧亦俗的诗僧;在北宗的影响下,出现了像王维、孟浩然等追求所谓“禅趣”的诗人;总之思维的模糊性已成一种社会习惯。在这样的条件下,皎然依然不以禅境说诗,仍以文学理论家的理性眼光,深化意境论的一系列建构。深知诗境与禅境不同,他常为自己流连于诗而苦恼自责:“贫道隳名之人,万虑都尽,强留诗道以乐性情,盖由瞥起余尘未泯。”第三位是禅宗宋代诗僧文珦。他明确认为诗有害于禅。其云:“平生清净禅,犹嫌被诗污!”又云:“吾本学经论……书生习未忘,有时或吟诗。聊以识吾过,吾道不在兹。”第四位是南宋刘克庄。有人要为他的诗室起名“诗禅方丈”,他反对说:“诗家以少陵为祖,其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刘克庄将诗、禅视如水火。他所说的实际是诗境与禅境的第四个重要区别。第五个明白人是明末的学者陈宏绪。他说:“诗以道性情,而禅则期于见性而忘情。”“诗之所谓性者……悉征之于情。而禅岂有是哉?一切感触等于空华阳焰,漠然不置于怀……既已出尘垢而学禅,其又安以诗为?”他从抒情的角度判定诗境与禅境不能混淆。看来,反对以禅境论诗的,大有人在,应当得到今天文学理论家更多地尊重和肯定。
其二,应认清北宗的误导和王、孟“禅趣”的道境实质。盛唐人多视神秀的北宗为真禅。而稍后王维、孟浩然等理解的禅境,也与炙手可热的北宗有关。慧能的《坛经》曾客观记录了神秀的一首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此偈不过是老子“涤除玄鉴”和庄子“至人用心若镜”观念的翻版。这样解禅,与其说是禅家,不如说是道家!所以,慧能的师傅弘仁当面批评神秀说:“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这彻底否定了北宗的正统性。神秀虽悟性很差,但谋权有术,北宗很快取得了皇家的认可。统治者的思想往往会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思想,而对于本来就习惯于老庄思想的盛唐诗人来说,谁能看透北宗还“未入门”的实质呢?于是,一些源于老庄,追求归隐、闲适和静寂之美的诗人,便以追求“禅趣”的新名号出现了。其中的佼佼者,便是王维和孟浩然。王维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这里的“空山”“深林”“人语”“长啸”,皆在“六尘”之内,没有“忘相”;“独坐”与“弹琴”,“不见人”与“人不知”,显然是在排解什么,寻觅什么,心念已动,亦没“离情”。这仍然是华夏自古就有的澄怀味象、目击道存的审美模式。这里的诗境依然是中国的意境,其中的哲理意味依然是道境。显然,王、孟诗境是一个有声有色的艺术世界,直接与佛学对立。像这样只能用道家美学眼光来概括的意境型诗歌,为什么一定要用“禅境”来概括呢?今天,当北宗因其“未入门”而被埋葬在历史深处时,中国文学史还应该因袭这样的误读与误导吗?
其三,意象诗与禅宗思维过程是有某一小段的相似之处。汉代王充根据我国巫术文化传统和儒家象征文艺观,取《易传》“表意之象”的意思,首创了“意象”范畴,用以专指那些象征着哲理的有艺术意味的形象。南梁和尚慧皎在《高僧传·义解论》中说:“夫至理无言,亥致幽寂。幽寂故心行处断,无言故言语路绝。言语路绝,则有言伤其旨。心行处断,则作意失其真。”意象似乎也能达到这种程度。它可以引起人们一种求解的冲动,在有所解又不能全解,有所悟又不能全悟的情况下,了悟的兴奋和求解的冲动,便使审美的情感上升为崇高,达到一种审美思维的峰巅状态。叶燮描述此境说:“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例如我们对李商隐《锦瑟》的审美求解与猜测,便能达到“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的状态。许多人以为这就是“禅境”,其实不然。慧皎所言的“心行处断”是便是“无念”,“幽寂”之境,已“无相”可观,其中的“至理”处于言语无法表述状态。而对《锦瑟》的审美求解进入“言语道断、思维路绝”之后,其意象世界仍处于“鸢飞鱼跃”的“昭著”状态,而“灼然”于“心目之间”,一点也不“幽寂”,并以审美为目的。因此,也不能将意象世界混同于禅境。
其四,对于“以禅喻诗”的现象,应审慎甄别。唐代以来名士们谈禅说诗、以禅喻诗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不能一概否定。一方面应注意到:在整个北宗尚在禅宗“门外”的情况下,诗人名士所说的“禅意”,多不是真禅!例如,苏轼在《次韵僧潜见赠》一诗中说:“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婉转诗人情”。这仍是庄子的思路:“至人用心若镜”。“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实际说的不是参禅,而是细细“品味”。“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说的不是什么禅境,而是老庄的“虚静”,即主张通过虚静进行艺术构思。又如“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这是主张文学艺术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哪里是佛门禅宗的思想!
虽说诗境与禅境不是一回事,可是,若从比喻的意义上,还是可以“以禅喻诗”的。例如,虽说诗道与禅道不同,但是它们都是那种的“不传之道”,只有通过个人体验和修练才能获得。因此,严羽提出“妙悟”说,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依此看来,以禅喻诗,用得好的,可以加深人们对诗学理论的理解,并非全无好处。
几点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意境与禅境的误解与绞缠到如此地步,是什么原因呢?显然,有几个问题值得深思:(一)全是“境界”惹的“祸”。由于中国学者长期习惯于模糊思维,以为有境界的地方便可以汇通混解,意境与禅境等的绞缠便是由此引起。但模糊思维是与日趋精密化的现代学科思维背道而驰的。如果不注重概念的界定和基于这种概念之上的逻辑推理,便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也很难称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二)由于习惯于模糊思维和不注意概念的界定,一些著作显得缺乏基本的常识。比如审美和美学概念,它的构成应是有基本条件的,不能将“审美”和“美学”变成“膏药”到处贴。(三)研究者常常缺乏历史意识,不知道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即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谈禅,首先要弄清楚在哪个历史阶段的禅宗才是正宗。由于没有历史意识,他们对各种佛学文献没有鉴别意识。比如,他们把庄子的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混在一起说,不知它们是不同的境界;把佛经与禅宗混在一起说,不知它们的文化阐释模式是不同的;又把北宗与南宗混在一起说,而不知它们的思维尖锐对立而又属于不同历史时期。只有尊重了历史,才能找到可靠的学术标准。有的人故意抬高禅境的地位和作用,浑说什么“意境的本质本色就是禅境”。不知他这样浑说时是否考虑过意境与禅境孰先孰后;是谁依靠谁才得以在中国立足;为什么一定要将中华民族文化长期孕育和独创的审美范畴“意境”,让一个只有宗教境界和外来文化基因的宗教概念来冒充,来取代?这种种做法也太缺乏民族文化历史的自尊和自信了。(四)本文特意考察了意境论形成的历史,并没有发现它是“一个不断禅化的历史”。敏泽先生说过一个很好的意见:“正如佛教的输入只能影响、不能代替传统的思想文化一样”。同样,禅宗思想也“只能丰富、补充我国的传统美学思想,而不能代替或改变它”。杨矗先生将禅境说成是意境的“命根子”,岂不是想“代替或改变”“我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意境论吗?当然,禅宗对我国诗歌创作还是有某些影响的,这主要表现在对诗人的世界观和美学风格的改变上;而对于我国源远流长的意境理论,可以说影响甚微。
(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摘自《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原题为《简论意境与禅境之别及其绞缠——兼答杨矗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