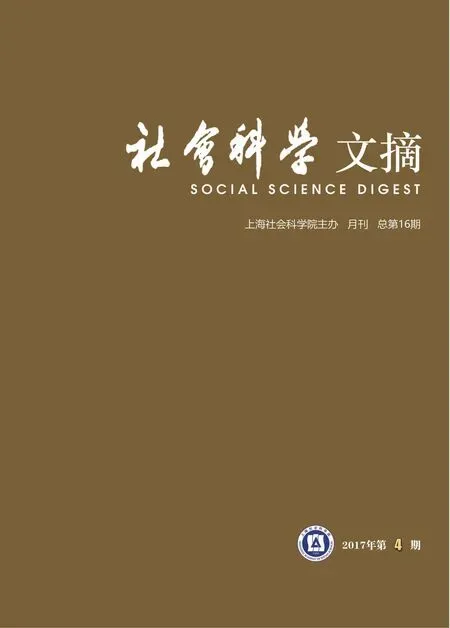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与大学传统的扬弃
文/邓云清
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与大学传统的扬弃
文/邓云清
牛津、剑桥大学是19世纪以前英格兰仅有的两所大学,建于十二、十三世纪,因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故称“英格兰古典大学”。在19世纪英国改革浪潮中,英格兰古典大学进行了自建校以来规模最大的改革。这场改革尽管只涉及牛津、剑桥大学,但两校是当时英国的超级机构,其改革不仅仅是单纯的教育改革,而且牵涉到甚为复杂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竞争,牵涉到教会、政府与大学的棘手关系。在一个传统浓厚甚至根深蒂固的国度,如何突破重重阻力、打破改革的僵局?又如何保留既有优势、实现传统的扬弃?这需要改革者找到改革的支持力量和有效途径,并妥善处理改革与传统的关系。
古典大学制度及其问题
16世纪中叶以来,牛津、剑桥大学推行古典绅士教育,课程以古典文学与新教伦理为中心,注重绅士身份和品质的养成。英格兰国教会是两所大学的主导者,对其拥有极大影响力。书院是两所大学实质上的组织者,在教学和管理中发挥实质性作用。但是,这种教育难以适应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新形势,无法为平民社会培养充足的专业技术人才与工商实业人才。
19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大学改革时期。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脱离不了欧洲大学改革的总趋势。为了因应自由和民主、工业和技术、科学和研究的快速发展,欧洲大学发展出现三个新趋势:一是世俗教育的兴起,教育与宗教分离;二是专业教育的兴起,并与职业相对口;三是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兴起。19世纪早期欧洲大学主要有三种制度模式:一是英格兰古典大学由书院主导的导师制,世俗政府不直接介入,大学和书院高度自治,注重古典人文教育和理智训练;二是法国由帝国大学控制的联邦型大学制度,大学体系高度统一,关注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三是德国普鲁士由大学主导的教授制,大学由世俗政府开办,关注自然科学教育。英格兰大学难以适应19世纪上半叶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在与世俗政府和大学机构居于中心地位的法、德高等教育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如何突破自由和自治传统、古典绅士教育传统,实现世俗教育、专业教育、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大发展,就成为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的基本任务。
19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改革时期,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绕不开英国改革的总体趋势。19世纪英国改革涵盖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宗教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调整和转换,而且涉及社会各阶层权利和财富的再分配。改革如此广泛而持久,得益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思想先导。边沁以苏格兰启蒙思想为主要基础,对自由主义理论加以创造性发展,提出自由主义大系居中偏激进的学说——功利主义,试图用功利原则(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根本上清除神学原则等支撑贵族和绅士特权的理论。功利主义具有强烈平民主义和世俗主义色彩,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和主流。功利主义和边沁学说直接启迪了英国改革。改革首先在天主教解放和议会改革领土取得突破,这些宪制缺口的打开为国教会从公共教育中分离出去与大学治理的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不过,古典大学改革的难度不亚于天主教解放与议会改革,主要因为古典大学特别是牛津大学是国教会的基地,是宗教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堡垒,不易击破,而且具有强大的抵抗甚至反弹能力。因此,古典大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改革者的持续努力。
改革的力量和途径
改革力量的生成和聚合是改革的头等大事。以边沁功利主义为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倡导世俗化和平民化,为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论和思想体系。苏格兰爱丁堡评论派的汉密尔顿等人是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的急先锋,是他们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舆论宣导将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英格兰的边沁主义者密尔等人另起炉灶,通过外围突破的方式创立宗教无甄别、课程讲实用的新式高校伦敦大学。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古典绅士教育家阿诺德在拉格比公学进行改革,成功实现实用知识与古典知识的兼容,实现功利原则与神学原则的兼容,为改革超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提供了范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教育界前辈汉密尔顿、密尔、阿诺德等人的宣导和探索,最终在古典大学内部形成了一支以斯坦利、乔伊特、沃恩、帕蒂森等人为核心的致力于改革的基本力量。他们对课程、宗教等核心问题持兼容立场,认为大学可以兼设实用和现代课程,可以兼收非国教徒入学,还提出外部介入改革、加强教授席位建设、削弱书院地位等主张。不过,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不仅仅是教育思想之争,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且是权力或权利之争;不仅仅涉及古典绅士教育理念的修正,也不仅仅涉及作为保守主义基石之传统的扬弃,而且牵涉到国教会垄断权、书院自治权等法律难题。要想突破这些争议和难题,改革还需寻求来自政界的同盟者,需要找到行之有效的途径。
改革途径的探索和选择关乎改革的成败。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探索过程中出现过两条改革途径。一是内部力量主导,由大学当局及其背后的国教会进行内部改革;二是外部力量主导,由世俗政府介入推动改革。英国自古以来就有教育归于民间的传统,世俗政府对教育既无直接干预之权力又无扶助之责任。而且,古典大学及其书院还受到王室特许状的法律保护,具有高度自治权。因此,内部改革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不过,实践表明,依靠国教会和院长寡头控制的大学当局去大幅削弱国教会和书院的影响力,逐渐让有识之士认识到“我们无法改革我们自己”。改革需要新思维,这一新思维就是政府介入。对于谨守自由传统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要自由和自治,还是要改革和发展?能不能在改革的同时保住自由?法治框架成为上佳选择。对于大学来说,法治框架可以防止世俗政府的过度介入。对于世俗政府来说,法治框架可以为其介入提供一个减少阻力的理由。大学自治权受法律保护,只有新的立法才能加以撼动。为了积聚共识、减少争议,改革者还为议会立法设置了一个前置条件即皇家调查。它由一个独立委员会对某争议事项进行特别调查,为议会立法工作提供详实信息和可行建议。
外部介入改革从1834年开始进入实践阶段,但十余年间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转变出现在1850年。此年,经议会较充分的辩论,女王应内阁的请求签发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皇家调查委员会委任状,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得以成功启动。至此,改革人士成功探索出一条外部介入改革的途径,就是以“自愿性皇家调查”为突破口的议会立法。1852年,长篇皇家调查报告发布,对大学机构的权力分布、教授制的推广及书院财务加以协助等议题已有较为明确的态度和成熟的方案。随后,改革进入议会立法指导和大学修章落实的实质阶段,直到1882年修完章程才结束。其间通过的法案包括“1854年牛津大学法”、“1856年剑桥大学法”、“1871年大学考查法”与“1877年牛津和剑桥大学法”,大学机构的重组、宗教考查的取消、教授制的推广是这场改革最主要的成果。从改革自启动至落实的过程来看,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之路分三步走。先是皇家调查委员会进行非强制性调查,再是议会进行立法,最后是大学和书院在执行委员会监督下修订规章。这是一条以外部介入为主、以立法为核心的改革途径:“皇家调查——议会立法——大学修章”。在这一改革途径中,皇家调查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非强制性调查的效力可能不足,但它披荆斩棘,最终描绘出一幅甚至令反对者叹服的改革蓝图,成为改革启动的关键环节。议会发挥了主导作用,不仅为争议双方提供了制度性的竞争和辩论空间,而且为改革阵营提供了一批资深议员,包括如格莱斯顿这样中途转向改革的人士,最终将改革蓝图化为多数认可的改革法案。不过,改革法案相当多的内容是原则性的,这为大学及其书院修章提供了弹性空间。通过这条改革途径,可以看出世俗政府权力的上升,也可以看到国教会、大学及其书院的自主性,改革结束后的大学及其书院仍然高度自治。世俗政府对大学改革的介入主要是立法主导式介入,而不是行政主导式介入,主要是授权性介入,而不是控制性介入。通过这条改革路径,还可以看到英国人对法律、程序和规则的倚重,无论是改革方还是反对方,均在法律框架下采取行动。整个改革过程就是一个论法的过程,就是法律、程序和规则不断被引证、被解释的过程。
改革与传统的关系
英格兰古典大学具有两个深厚的传统。一是自由和自治传统,大学及其书院享有从事学术活动、自我管理、持有财产等自由权利,不仅教学和研究自主,而且人事和财务自主,并受到古老法律的有力保障。书院制就是这种自由和自治传统的集中体现。二是古典绅士教育传统,注重古典人文教育和理智训练,注重绅士身份和品质的养成,适合精英教育与通才教育。导师制就是实现这种教育理念的基本教学方式。在英格兰古典大学制度模式下,大学更像知识上的“世外桃源”,容易与外部形成隔离,在知识上自给自足,维持纯粹知识的发展。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当外部的介入有害时,可以起到防火墙的作用,知识的纯粹性不易受到污染;当外部的介入有益时,容易陷入故步自封,难以反映社会的需求,实现知识的快速发展。十八、十九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城市化提出大力培养实用专业人才、发展科学研究等新要求。英格兰古典大学以古典绅士教育为中心,更适合教学的发展与通才的培养,反应速度明显偏慢。内部自主改革难成气候,外力介入改革成为历史选择。这场改革既有大学内外治理结构的重组,又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调整。
在学校治理上,两校对内外治理结构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和调整。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这场改革恢复和重塑了评议会的立法和选举功能,加强了理事会的代表性和民意基础,削弱了书院在大学行政和财政体系中的影响力,从而建立起具有英格兰古典大学特色的内部治理结构。这种内部治理结构可以称为双平衡结构。一是作为大学中央政府机构的理事会与评议会之间的均势结构。评议会拥有大学立法、人事、财务等事务的主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最高权力机构。在英国议会主权确立一个半世纪后,牛津、剑桥大学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近代宪制。二是作为自治实体的大学与书院之间的联邦结构。通过理事会中大学方代表的增设,以及大学对书院资金的部分调拨,书院实力畸重的局面显著改善,校院行政和财政关系趋于平衡。第二个结构值得深入探讨。尽管书院自治权有所削弱,但并没有剥夺书院的自治权,书院自治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考虑到其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特殊使命更是如此。作为基层教育组织,书院融教学、科研、人事、财务管理于一体。但是,书院绝不仅仅是大学的基层教育组织,更是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使命的专业人员的主要载体,是大学教学和科研职能的核心承担者,其自治精神可以有效抵御来自大学甚至校外力量的过度干预,为探究性学习和创新性研究提供有效保护。如果说大学更多的是以行政管理(包括对学术的管理)为己任、以管理创新为追求的行政力量的话,那么书院则是以教学科研为己任、以学术创新为追求的学术力量。因此,校院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利的关系。培育有自治精神的书院才是学术治校的根本。在外部治理结构方面,新的宗教考查法取消了国教会对师生招聘和录取资格的宗教审查权,也在事实上将宗教课程从必修课降为选修课,从而宣告国教会垄断权与宗教意识形态灌输不复存在。当然,国教会及其意识形态作为可选项之一,仍在古典大学发挥影响力。在国教会退却的过程中,世俗政府并没有乘机入驻大学,只是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与大学建立间接的联系。总体而言,牛津、剑桥大学及其书院的自由权利和自治精神仍通过教学科研专业人员即学者而得以延续,这种治理结构我们可以称为“学者自治”。
在教学上,两校对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进行了有效修正和调整。改革的主要目标指向专业教育与学术研究。教授制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有效方法,这正是德国大学制度的核心。通过这场改革,英格兰古典大学向欧陆有所靠拢,在专业人才培养和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通过这场改革,古典绅士教育传统为实用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所部分平衡。不过,英格兰古典大学并没有放弃古典学、数学等传统优势学科,也没有放弃通识教育和理智训练的既有优势。时至今日,牛津、剑桥大学在教学结构上仍保持着通识性教学型书院与专业性学术型系部交叉的结构,在教学方式上仍保持着导师制与教授制并行的格局。导师制值得深入讨论。作为手段的制度,需要从大学目的的高度进行把握。大学的根本目的是知识生产和思想供给,学术创新是大学的本义。导师制教学确实在专业性上不足,但它注重师生互动和言传身教,师生组成一个个小型知识共同体,共同致力于知识和思想的进步,这在探索精神和学术品格的塑造上非常有效,因而适合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在形式上,英格兰古典大学模式与德国全然相反,一个以导师为核心,一个以教授为核心;但在价值上,二者差异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英格兰古典大学的制度改革,特别是导师制的扬弃,用一个典型而生动的案例提示着制度改革的困惑与可能的出路: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更好的制度;制度侧重于形式和手段的意义,还需要价值和目的的支持。
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是19世纪英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调整,而且包括大学内外治理结构的重组,因涉国教会垄断权、书院自治权而成为19世纪英国改革的难点。功利主义的思想先导、知识界的舆论宣导和外围试验起到了凝聚改革人心、汇聚改革共识的重要作用。同情大学改革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与非国教徒政治家是改革的同盟者,正是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联手,古典大学改革才得以成功启动。这场改革打破教育归于民间的传统思维,成功探索出一条以授权性介入为特征的大学改革新途径:“皇家调查——议会立法——大学修章”。这条途径也具象地反映出19世纪英国学权、教权与政权各自力量的消长与角色定位。这场改革在引入专业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保留了大学的既有优势,其自由和自治传统、绅士教育传统通过书院制和导师制得以大部分延存,在知识创新的背景下持续展现出传统的魅力。大学传统的扬弃过程也清晰地反映出目的与手段的差别,作为手段的大学制度需要以知识的生产和思想的供给为归依。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摘自《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