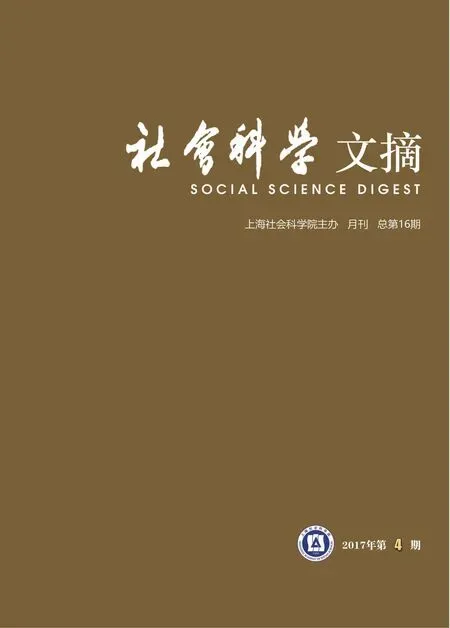何谓世界文学?
文/方维规
何谓世界文学?
文/方维规
“世界文学”难题,或众说纷纭的“世界文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世界文学”观念展开了一场深入的理论探讨;并且,“世界文学”概念成为新近关于“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国际论争的焦点。打上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烙印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曾被持久而广泛地接受。最迟自20世纪60年代起,这个概念逐渐遭到批评,原因是其思考文学时的(常被误认为源自歌德的)精英意识,以及世界文学设想虽然超越了民族框架,却只能基于这个框架才可想象。“一般来说,所谓普世性,只要不仅是抽象,只能存在于地方性之中。”如今,不少人喜于“世界的文学”(Literatures of the World)之说;这个概念虽然还勾连着世界文学的“经典性”,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想象或纲领。
新近的世界文学论争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欧美关于这个概念的论争,似乎还未终结。本文试图反复追寻歌德论说,旨在厘清相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当今。
“世界文学”概念的“版权”及其历史背景
论说“世界文学”概念,总要追溯至文豪歌德。歌德曾长期被看作“世界文学”一词的创造者。另外,不少学者论述歌德“世界文学”概念时,不愿或不忍心看到其时代局限,他们主要强调这一“歌德概念”的全球视野。
无疑,“世界文学”概念不能只从歌德说起,还得往前追溯。约在30年前,魏茨(Hans-J. Weitz)发现维兰德(Christoph M. Wieland)早在歌德之前就已用过这个词,见之于他的贺拉斯(Horace)书简翻译修订手稿(1790)。维兰德用这个词指称贺拉斯时代的修身养成,也就是“世界见识和世界文学之着色”(“feine Tinktur von Weltkenntniß u. Weltlitteratur”)。此处“文学”乃见多识广的“世界人士”(homme du monde)之雅兴;此处“世界”也与歌德的用法完全不同,指的是“大千世界”的教养文化。无论如何,已经没有理由仍然把“世界文学”一词看作歌德之创,也不能略加限定地把它看作歌德所造新词。
其实,“世界文学”这个有口皆碑的所谓“歌德概念”,在歌德起用之前54年就已出现!施勒策尔(August L. Schlözer)早在1773年就提出这个概念,将之引入欧洲思想。他于论著《冰岛文学与历史》中写道:“对于整个世界文学(Weltlitteratur)来说,中世纪的冰岛文学同样重要,可是其大部分内容除了北方以外还鲜为人知,不像那个昏暗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爱尔兰文学、俄国文学、拜赞庭文学、希伯来文学、阿拉伯文学和中国文学那样。”事实是,“世界文学”概念及与之相关的普世主义,已在1773年出现,早于歌德半个世纪。
毋庸置疑,歌德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确立和流传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说这个概念最初并不源自歌德,还有更深层的思想根源。这里不只涉及这一词语本身,而是孕育和生发世界文学思想的思潮。一个重要贡献来自赫尔德(Johann G. Herder)。1773年,赫尔德与歌德、弗里西(Paolo Frisi)、莫泽尔(Justus Möser)一起主编出版《论德意志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其中不仅载有狂飙突进运动的宣言,亦鼓吹民族文学或人民文学。
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其《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指出,民族文学思想主要由赫尔德倡导并产生重大影响,从德语区传遍欧洲并走向世界,此乃所谓“赫尔德效应”(“Herder-effect”)。“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两个概念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没有后者,前者只能是地方的;没有比照对象,民族文学也就失去了与世界上重要作品的媲美可能性。赫尔德也是世界文学的精神先驱之一,他的著述明显体现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歌德《诗与真》(1811~1812)中的一段话,讲述他于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与赫尔德的相遇。
他(赫尔德)在其先行者洛斯(Robert Lowth)之后对希伯来诗艺之极有见地的探讨,他激励我们在阿尔萨斯收集世代相传的民歌,这些诗歌形式的最古老的文献能够证明,诗艺全然是世界天资和人民天分,绝非个别高雅之士的私人禀赋。
这段语录中的“世界”,常被歌德研究者看作其世界文学思想的序曲,这当然不无道理。可是,若无赫尔德,这个概念在歌德那里或许不会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
“世界文学”概念不只拘囿于自己的实际意义,它还连接着更宽阔的历史和体系语境,同其他一些近代以来与“世界”二字组合而成的重要概念密切相关。“世界-”概念旨在涵盖某种存在之整体。1770年至1830年有一股强劲的“世界”热,一些同属普遍主义的概念脱颖而出,其中有许多今天依然很重要的观念,以及一些今天还被看重的价值观与全球思维方式。也是自18世纪70年代起,歌德时常说及世界,“世界诗歌”(Weltpoesie)、“世界文化”(Weltkultur)以及“世界历史”“世界灵魂”“世界公民”“世界事件”等词语组合,常见于他的言说。就“世界文学”而言,歌德很早就认识到文学场的某些特有规律,使得交流过程成为特殊的文学景观,可是这要到很久以后亦即19世纪20年代末期才被他明确描述。而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奥尔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éans, 1801)的法文本译者德谢(Jean J. Derché),最先提出了欧洲文化网络意义上的“文学世界主义”。
最后,我们还须提及施特里希(Fritz Strich)在歌德研究的标志性著作《歌德与世界文学》(1946)中所强调的视角,即个人经历对歌德世界文学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歌德感到特别惊奇,自己那些隐居状态中创作的作品,完全是为了释放自己,为了自己更好的养成而写的,最后居然能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接连不断地传到他这个年迈文学家的耳里。这一世界反响有益于他的身心,让他感到幸福,从而成为他呼唤和促进世界文学的最重要的动机,要让所在都有他这种福祉。
莫衷一是,或歌德对“世界文学”的不同理解
自1827年初起,歌德开始并多次在书评、文章、信件和交谈中明确谈论“世界文学”。他在1827年1月15日的简短日记中,第一次写下“世界文学”字样:“让舒哈特(Johann Ch. Schuchardt)记下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他又在1月26日给哥达(Johann F. Cotta)的信中说:“我们现在必须特别关注外国文学,人家已经开始关注我们。”次日,他在给作家和翻译家施特赖克福斯(Adolph F. Streckfuß)的信中表达了他的信念:“我相信,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民族都对此感兴趣,因而都迈出了可喜的步子。”
也是在1827年初,歌德在《艺术与古代》杂志第6卷第1册转载了《塔索》译者迪瓦勒(Alexandre Duval)的两篇书评,一篇简介出自《商报》(Journal du Commerce),另一篇出自《全球报》,迪瓦勒盛赞歌德为楷模。歌德最后在评论这两篇书评时写下如下结语,第一次公开说及“世界文学”:“人们到处都可听到和读到,人类在阔步前进,还有世界关系以及人际关系更为广阔的前景。不管这在总体上会有何特性,[……]我仍想从我这方面提醒我的朋友们注意,我坚信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我们德意志人可在其中扮演光荣的角色。”
最后,歌德于1827年1月31日在与爱克曼(Johann Eckermann)的谈话中表达了后来闻名遐迩的观点:“我喜欢纵览域外民族,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做。民族文学现在已经算不了什么,轮到世界文学时代了;现在每个人都应出力,促成其尽快来临。”
法国《全球报》于当年11月1日援引歌德之说,但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替换成“西方文学或欧洲文学”(“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ou européenne”),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歌德“世界文学”的原意。换言之,他当初想象的世界文学是欧洲文学,如他主编的杂志《艺术与古代》第6卷第3册(1829)的题旨明确显示的那样:“欧洲文学,即世界文学”(“Europäische,d. h. Welt-Litteratur”)。
毫无疑问,歌德是一个极为开放的人,但他有着明确的等级观念。“中国、印度、埃及之古代,终究只是稀奇古怪之物”,他如此写道,“自己了解并让世界了解它们,总是一件好事;但它们不会给我们的品德和审美教育带来多少助益”。显然,歌德无法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
德意志文学家对古希腊的钟爱是众所周知的。这种认同感颇为强烈,甚至可被看作“民族”而非“跨民族”之感受。歌德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如此解释自己的思想:
[……]但在赏识外国事物时,我们不能固守有些奇特之物并视之为典范。我们不必认为来自中国或塞尔维亚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也不必这样看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而在需求典范之时,我们始终必须返回古希腊,那里的作品总是表现完美之人。其他一切事物,我们仅须历史地看待;如可能的话,从中汲取好东西。
偏偏是歌德这位“世界文学”旗手,固执于欧洲古典精神,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我们无须惊诧,那是时代的局限。我们不应忘记,歌德是在七十八岁高龄,也就是去世前五年,倡导“世界文学”思想;他更多地只是顺带提及,且不乏矛盾之处,并非后来的比较文学所要让人知道的系统设想,且把“世界文学”看作这个专业的基本概念。歌德所用的这个概念,绝非指称整个世界的文学。并且,他的世界文学理念,所指既非数量亦非品质,既不包括当时所知的所有文学,也不涉及各种民族文学的经典作品,基本上只顾及德意志、法兰西、大不列颠和意大利文学,间或稍带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民间文学,偶尔也会谈论几句欧洲以外事物。
“世界文学”vs.“全球文学”:何为经典?
当今对歌德之世界文学论说的讨论颇为活跃。可是,“没有一种世界文学定义获得普遍认同”。一方面,歌德的世界文学思考被当作理论,从而被过分拔高。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诘问,这个“歌德概念”究竟指什么?人们能用它做什么?歌德曾把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学看作历史快速发展的结果,而他所说的“这个高速时代和不断简便的交流”和由此而来的“自由的精神贸易”,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今天,达到了他无法想象和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世界文学观念,这也是“全球文学”观念的时代基础。
在不少人指出歌德式世界文学概念的欧洲中心主义蕴含之后或同时,人们又试图重新起用这个概念,为了在今天的意义上赓续世界主义传统,抵御全球化的连带弊端。当今世界许多地方所推崇的“世界文化”概念,不仅为了描述一个因全球化而改变的世界,亦体现出批判性介入。而介入的一个依据亦即中心观点,来自歌德所强调的世界文学成于差异而非同一。柯马丁(Martin Kern)在《世界文学的终结与开端》一文中,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对立”语境中,提出如下问题:“在不断交流、相互影响和文化、语言四处弥漫的同质化压力之下,地方的独特性如何幸存?”非常明确,他的理论依据已见于该文题词,即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所言“世界文学思想在实现之时即被毁灭”。奥尔巴赫哀叹世界上文学多样性的丧失,从而诘问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究竟还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交流的根源在于差别,已经占有则无需交流。不同文学之间的调适,使交流失去了丰腴的土壤。因此,人们必须更多挖掘不同文学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柯马丁诟病与歌德理念背道而驰的最新发展:“对歌德而言,世界文学作为文化实践保证了各种当代文学文化相互启发和影响,然而它在今天却面临变为全球文学的威胁。全球文学并不关心文学文化来自何处,而是屈从于全球化市场的压力。”因此,他认为“世界文学和全球文学的二分,已变得十分紧迫;如果世界文学成于他异性、不可通约性和非同一性,那么全球文学确实是其对立面:它在单一的、市场导向的霸权下强求一律,抹除差异,出于某种同一性而非他者性将他者据为己有”。
目前(西方)学界有一个共识,即世界文学概念不能理解为所有文学的整体,亦非世界上最佳作品之经典。世界文学是普遍的、超时代的、跨地域的文学;若要跻身于世界文学,必须是超越国族界线而在其他许多国族那里被人阅读的作品。施特里希在70年前提出的观点,“只有超越国族边界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世界文学,今天依然有效;或如达姆罗什广为人知的说法,将世界文学描写为“在原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可见,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视角问题:文学不再归于国族这一亚属体系,而首先要从国际文学场出发,以此划分不同文本和写作方法的属性和归属。跨语言、超国界现象亦见诸缘于政治关系的集团利益而生发的区域文学。
当代“世界文学”概念,首先不再强调国族归属。这对文学研究来说,也就意味着重点转移,告别按照语言划分的国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研究重心在于揭示诸多文学及其场域之间的关联和界线。弗莱泽(Matthias Freise)对“何谓世界文学?”的理解是:
其核心问题是普适性与地方性的关系。这一论题提示我们,可以用关系取代本质主义视角来观察作为现象的世界文学。我认为,世界文学必须作为一种网状关系,而非一组客观对象,比如一组文学文本来理解。这些关系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普世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我们把客观对象和诸关系按照不同系统鉴别分类,世界文学的不同理解首先就从这种差异中产生。理解作为关系的世界文学,提醒我们关注其过程性。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
我们再回到全球文学,其诉求是从全球视角出发,打破文学生产中的中心与边缘的界线,也就是一开始就应在跨国族的架构中思考文化生产的发生和形成。语言多样性和更换国家(居住地)对写作产生深刻影响;并且,由此产生的文学分布于世界上的不同语言、文化和地域。就文学生产而言,国族文学的界线尤其在西方国家不断被消解,新的文学形式不时出现,很难再用惯常的范畴来归纳。在欧美国家,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杂合文学,也就是不只属于一个国家的文学。
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常会给人带来时空上的重新定位,这在当代常与全球化和跨国发展紧密相连,即所谓走向世界。当代斯拉夫文学的转向,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而发生,许多文学文本不再拘囿于国族的单一文化和单一语言的文学传统。这些现象既会在文本内部也会在其所在的文学和文化场域造成“混乱”,但也释放出创新之潜能。当今世界的许多作家,不会感到自己只属于某个单一文化,他们有着全球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到处可见的现象,它与旅行和国际性相关。这些作家作品的明显特色是语言转换和多语言,以及对于世界各种文化的多元视角,从而带来社会及学术聚焦的移位,突破了以往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的三维组合。将作家团聚在一起的,不是他们的来源地、语言和肤色;团聚或分离作家的,是他们对世界的态度。
论述世界文学,不可能不谈“经典”或曰“正典”。那些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在世界人民眼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声望的作品,可被看作世界文学,这基本上依然是一个共识。歌德使用的“世界文学”,是指超越民族的世界主义精神所创作的文学。对歌德来说,不是每一部在世界传播的作品就必然属于世界文学。能够获此殊荣的关键是文本的艺术价值及其对世界上众多文学的影响。(在歌德那里,“超越民族的世界主义精神”中的“世界主义”,如前所述不完全是今人理解的世界主义,他的“世界”偏重“欧洲”。)
德国文学理论家从来就有神化歌德及其“世界文学”意义的倾向,这有其深层根由。人们时常谈论如何克服国族文学思维,旨在抛弃“往后看的‘老式德意志爱国主义’艺术”。格森斯(Peter Goßens)在其论著《世界文学:19世纪跨国族文学感受的各种模式》(2011)中,联系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他写道:
一件艺术作品的当代成就[……]不仅取决于创作者的技艺以及他对国族艺术的意义。靠技巧和文学作品的愉悦价值所赢得的声望是短暂的,这对世界文学思想没有多少意义。这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作家及其作品是否成功地破除了国族文化的界线并斥诸文学艺术实践。
这里或许可以见出本雅明关于作品通过翻译而“长存”(Fortleben)的说法。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什么作品可被列入世界文学行列,要在这方面获得普遍认可的范畴和看法是相当困难的,不同国族或人民因为文化差异而对文学的意义所见不同。在西方世界,“经典”一词从来就给人一种不言而喻的固定想象:它首先是指古代作家和艺术家的历史作品,这些作品及其作者被视为审美楷模,在“经典”(classicus)意义上被归入“上乘”。后来文学时代遵循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审美准则、效仿他们并创作出重要作品的作家,亦被称为经典作家。当然,世界文学还须经得住不同时代的考验并被看作重要作品。
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勒夫勒(Sigrid Löffler)的《新世界文学及其伟大叙事者》(2013)一书,呈现的完全是传统“经典”的对立模式,赋予世界文学新的含义。在她看来,今天的世界文学不是西方、欧美的文学,而是源自那些太长时间受到忽略、创造力和创造性都在爆发的地方。世界文学是全球文学,是当代真实可信、叙述真实故事、发出鲜活之声的文学,是游走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人、往昔殖民地后裔和冲突地区的难民所写的后国族文学、移民文学。“游牧”作家是不同世界之间的译者。新的世界文学取自文化混合、冲突和生存题材,如跨国迁徙、自我丧失、异地生活和缺乏认可。其实,她的“新世界文学”就是不少人新近倡导的“世界的文学”。
一般而言,“世界文学”和“世界的文学”这两个概念多半是在明确的不同语境中被运用:若说“世界文学”依然意味着作品之无可非议的重要性,那么,“世界的文学”则更多地指向世界上那些不怎么有名、却能展示新方向的文学;它们不同凡响、颇有魅力,却还未在读者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也就是说,“世界的文学”未必就是审美和经典意义的上乘之作,或得到广泛接受的作品。谈论世界的文学,人们面对的是浩繁的书卷、无数作品和文化传统、难以把握的界线以及挑选时的开放态度。
余论
歌德没有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这个概念的神秘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一个事实:它拒绝所有固定界说,就连歌德自己也回避言简意赅的界定。他的世界文学设想的中心意义,首先意味着文学的国际交流和相互接受。他曾强调说:“不能说各民族应当想法一致,他们只需相互知道,相互理解,还要——设若他们不愿相互热爱——至少学会相互容忍。”在诸多关于“世界文学”观念的著述中,我们一般能见到的是歌德的乐观态度及其相关言论,不了解或被遮蔽的是他最迟自1831年起的否定视角,至少是怀疑态度。歌德自己也告诫过,人们不能只看到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学的积极意义:“若随着交通越来越快而不可避免的世界文学逐渐形成,那我们对这样一种世界文学不能期待过多,只能看它能做到什么和做到什么。”
写作此文的目的,不仅旨在勾稽“世界文学”概念的——借用比较文学曾经喜用的说法——“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也在于呈现它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跨语言、超国界的文学走向,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认同、文学运行和经典化的生成条件,以及还未完成的概念化过程。在这一世界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口号和实践,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我不愿用不少人眼中的“民族主义焦虑”形容之,但要指出它违背文学之国际传播的一般规律。文学接受基本上是“拿来”,“接受”往往是主动行为,全世界都是如此。“输出”之一厢情愿,欲速则不达,本在意料之中。与此相伴的是一些学者切盼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我要问的是:何在?一些学者一味强调“中国性”的说法,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与新的“世界文学”理念格格不入,也与“全球文学”或“世界的文学”理念格格不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摘自《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