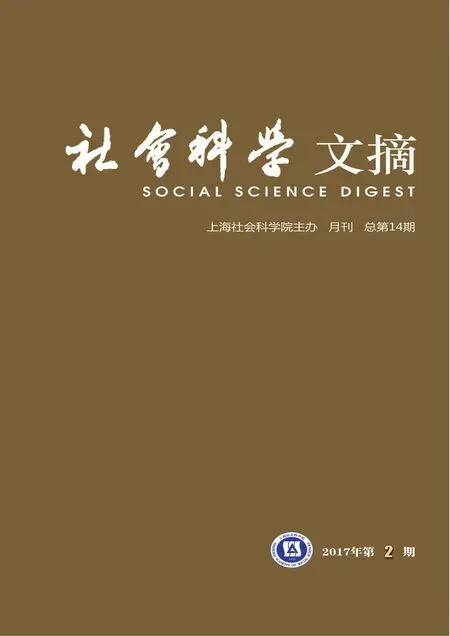再论中国美学史的发端问题
文/易冬冬
再论中国美学史的发端问题
文/易冬冬
2016年9月,《文艺争鸣》发表了洪永稳、顾祖钊《对张法主编本〈中国美学史〉的几点意见》一文。该文对“马工程”《中国美学史》教材提出的意见很多,要而言之,是关于中国美学史写作的逻辑起点问题,或者说中国美学的发生问题。该文作者认为中国美学发端于原始“巫术文化”而不是“农耕文明”。其所谈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历史观念以及方法论等诸多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澄清,不仅是对洪永稳、顾祖钊相关质疑的回应,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美学史写作范式的调整和进步。
对中国美学史发端认知方式的歧异
中国美学史的历史发端问题一直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近30年的中国美学史写作,不同的学者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判断。有的学者认同“魏晋起点论”,有的认同“春秋起点论”,更多的则将美学史的发端追溯到旧石器晚期的山顶洞人,即“石器时代起点论”。事实上,这一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基于考古学、文献资料和哲学的反思,张编本将中国美学的发端定位在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该文作者也认同这一判断。但是两者对于中国美学历史发端期的相同认定,却有着根本不同的哲学立场和文化取向。
张编本将中国美学的发端定位于山顶洞人时期,只是一个基于考古实物、文献资料和哲学反思的相对判断,是哲学和历史相妥协的结论。就美学史观而言,如果认为中国美学的历史发端是从审美意识开始,那么它虽然将发端期定位于石器时代,却并不意味着人的审美意识真的就是从这个时期萌生,而是可能更早。之所以姑且定位于旧石器晚期,是因为从现代考古学来看,这一时期留下了最早的可以确证其审美意识存在的人工印迹,如人体装饰品。然而,审美意识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张编本看来,这却是一个不可能单纯凭借考古学和文献资料就能获得的答案。它无意于一定要给审美意识找一个“绝对起点”,而只是要借对这一问题的有限界定提示给人一种更深广的历史感。事实上,就美学作为感性学而言,在人还不会制造器具之时,他就已经可以对周遭世界形成感知,也未必不能从这种感知中获得一种心理愉悦。甚至,如果基于生态学的研究,一些高级动物也有审美活动。如此一来,发端期的研究甚至要突破人学的界限,指向更遥远的时空。由此看出,人的审美历史要远远早于人制造器具的历史。易言之,张编本对于审美意识的发端期之确定是持开放态度的。
与张编本对中国美学发端问题所持的开放态度不同,该文作者对于中国美学发端期之确定尽管也有考古学的支持,但其认定更趋确定和保守,且与张编本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美学史观。该文作者认为,中国美学史的发端期之所以可以定位于山顶洞人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是原始“巫术文化”兴起的时期,且巫术文化“兴起于原始公社制社会后期”。而华夏先民的审美意识是审美文化的开端,审美文化又是包孕在“巫术文化”之中。那么审美意识的兴起就包孕在“巫术文化”中,在时间上一定是晚于巫术文化的兴起,或者至少与之同时。由此可以推论出,审美意识的起点至少不会早于“原始公社制社会后期”,即“巫术文化”起源时期。在时间上,作者对于中国美学的发端期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大大不同于张编本的确定性。
虽然张编本和此文作者,都将中国美学的发端期定位于山顶洞人时期,但一个是更富开放,一个更趋保守。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立足于考古器物、文献资料和哲学反思,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美的认识而下的判断。而后者则主要是基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这种历史认识和研究方法起于西方19世纪后期,代表人物有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列维·斯特劳斯等,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曾红极一时。但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学者对自身历史认识的深入,这种带有鲜明西方文明中心论色彩并对历史缺乏同情理解的研究方法已基本被抛弃。同时,就人类历史认知的有限性而言,审美意识的发端问题永远是一个待解的秘密,任何独断性的答案都必将面临新的历史发现的检验。
美的历史的先导性与农耕文明
基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该文作者认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发生,必须从原始“巫术文化”着手,是原始“巫术文化”最终决定着华夏先民审美意识的形成。在笔者看来,这是给中国美学发端的研究扣上了一顶原始“巫术文化”的帽子,似乎如果帽子没有戴好,中国美学史就不能迈出自己的脚步。
该文作者的一个致命失误,是将美学史研究泛化成了审美文化史乃至一般文化史的研究。该文章的开头这样写到:“美学史的研究必须回到人类文明的母体文化,在母体文化中寻找形成的根由。因此,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的逻辑原点应该从原始文化寻找,也就是从中华文化的根性入手,探讨中华美学何以如此的理论依据。”这段话首先折射出了作者的美学史观,即将美学史等同于审美文化史。此文的逻辑是,中国美学史是中华审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研究中国美学史要从当时的审美文化着手;而审美文化又是当时一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又应该从当时的一般文化入手。正是基于这种泛文化的美学史观,作者才会认为,当人们试图去探究审美意识的发生时,就应当从原始巫术文化中寻找根由。
这种方法,简单言之,就是不能“单刀直入”,不能将美学史本身的研究作为根本的立足点。这种泛化看似给美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调动了多种美学资源,但是也必将导致美学史的研究中心模糊化。而张编本的远古美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恰恰是“单刀直入”的。这种方法是“选取哲学和艺术的直接对话,即用哲学强化对美学历史的控制力,用艺术激发美学历史的活力”。易言之,美学史可以拓展成审美文化史,但审美文化概念的无边界性,意味着一部严肃的美学史著作,在向文化延伸时必须保持审慎。
张编本的中国美学史并不是不谈美的历史与审美文化史、乃至一般文化史的关联。但是它始终要让美的历史作为先导,让审美文化史和一般文化史紧密跟随。在谈及这个漫长的发端期的美学史的文化内涵时,它把远古美学的孕育和农耕文明联系起来。尽管在时间上原始农业的出现要晚于作者所谓的原始“巫术文化”时期,但是就与后世文明和文化的紧密关联来看,中国美学史的发端期的文化内涵仍然要定位于农业文明而非“巫术文化”。同时,中国美学史发端期的文化内涵并不是排斥当时的宗教、巫术的意义。然而,这种宗教、巫术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时期就已经不再成为文化的主导,不再与后世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有紧密关联。就此而言,即便巫术文化在中国人审美意识生成过程中产生过作用,但它也会因为对后世中国美学影响的弱化而缺乏其本应具有的美学史意义。
与此比较,农业文明,不仅仅对发端期的中国美学的形成有着孕育作用,且“这种生产方式所建构的人地关系影响了后世中国哲学、美学和艺术的方方面面”。如果一定要追寻中国美学发端期的文化内涵,同时注意这一发端期对后世中国美学传统形成的实际影响,就不能从“巫术文化”着眼,而应该从农耕文明,即这种生产方式所建立的人地关系着眼。农耕文明所奠定的人地关系对中国美学和文化的孕育具有更深的奠基性。这种更趋具体、更考虑到中国美学的历史连续性的判断也许仍存在问题,但总比将一切史前史问题都推给一个想象性的“巫术文化”更切近历史的实相。
“巫术文化”对中国美学史发端研究的非适应性
该文作者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直接搬运到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中,未能考虑这种理论的直接移植对于中国美学史是否依然有效。此文作者将原始文化理解成一种人类文明共有的“巫术文化”,而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华夏文化,在他看来,自然也就成了这种普适性的理论可以运用的一个东方案例。
研究中国美学史的确必须有世界眼光。中国美学,作为一种学科形态,本身就是在西方的学术视野下逐渐建构起来的一门学科,是现代世界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美学史写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世界美学的体系中,如何呈现中国美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而所谓世界美学的普遍性,首先取决于人们对于这个学科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理论共识,哪怕这仍然是一种永远处在不断形成中的理论共识。这意味着我们必然要运用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来考察中国美学,但对于任何一种普适性理论的运用我们又必须保持高度的审慎。否则,这种移植很容易遮蔽中国美学的历史真相,更无法确立中国美学的主体地位。该文作者的这种直接移植对于中国美学发端期研究的非适应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法深入阐述 “巫术文化”与审美意识发生之间的关系;二是没能认识到所谓的“巫术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过分拔高了其对于中国文化和美学传统的影响。
首先,此文作者以“巫术文化”介入中国美学的发端研究时,并不能有效论证“巫术文化”与华夏先民的审美意识发端的联系。此文作者在谈及原始“巫术文化”与华夏先民的审美意识之间的关系时,从三个方面为审美意识的发生找根据,但笔者认为,这三个方面均缺乏说服力。列述如下:
第一个方面是,巫术文化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催生了无功利的审美意识。似乎先民们的宗教礼仪活动在先,在此充满功利性和目的性的活动中,才逐渐诞生了无功利性的审美意识。这是缺乏历史依据的推论。既然说实用、审美(艺术)、宗教、礼仪在远古时期是一体的,有什么理由认定宗教和礼仪活动在先,在此基础上才催生了审美和艺术活动呢?当人们去考察先民的审美意识时,并不能单纯地做这种简单的推论,而必须从先民所留下来的器物中去探究审美意识是如何发生的。作为“远古美学”一章的作者刘成纪认为:“远古器物的图案、纹饰虽然包含宗教、礼仪内容,但有效地实现审美或艺术欣赏依然是制器者的核心关注点。”即便审美本身是无功利的活动,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是在其他功利活动的基础上催生出来。
第二个方面是,巫术文化的盲目自信催生了原始先民的主体意识,进而催生了审美意识。此文作者认为先民因为无法战胜外界灾难,借助 “巫术文化”中的神力,在一种神秘的幻想中实现对它的把握。幻想中的盲目自信精神竟可以催生华夏先民的主体意识,显然在哲学层面是说不通的。主体意识意味着先民们在认识和实践的哲学层面实现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稳靠的把握。而这种稳靠的把握是对决定其生存的事物,即对土地的把握。华夏先民正是在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中实现了对土地的把握,并实现了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农耕文明使得华夏先民的定居成为可能,不再因为不断地迁徙,而产生一种对自然的恐惧和自身命运漂移感。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土地由于其给予的稳定的支撑,使得先民们生活资料的获取能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劳动投入。这就使得他们对自身的力量逐渐形成一种相信,于是“祀鬼敬神”的原始宗教、巫术观念逐渐弱化,人道主义的曙光逐渐升起。
第三个方面是,此文作者还站在现代科学、理性的立场,认为“巫术文化”在内涵上是非理性的,而“巫师”为了“维护自己的虚假权威”,一定程度上对于科学和知识的利用,“为人类原始审美意识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上古时期的人们,的确经常地进行着某种图腾崇拜、礼仪宗教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上古时期的人们意识里,他们的文化就是愚昧的低级形态。把科学理性意识的抬头归于所谓的“巫术文化”本来就缺乏说服力,又把这种理性意识说成是审美意识诞生的历史契机,着实是牵强附会。似乎在作者眼中,我们现代所谓的理性、科学、审美、艺术等诸意识都是萌生于这个涵盖乾坤的“巫术文化”中。
其次,该文作者过分地拔高了原始“巫术文化”对后世中国美学和文化的影响。作者为了论证中国先民的原始巫术文化对中国美学史的发生的重要性,除了在横向维度上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直接挪移到中国美学研究中;在纵向维度上,认为原始巫术文化是华夏民族的“母体”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性”所在,决定后来的“礼乐文化”“诸子文化”的形成。在他看来,远古初民,他们所创造的“巫术文化”决定着后世中国文化的方向和特质。正是基于 “巫术文化”对后世华夏美学传统的形成有着如此重要的影响这一判断,他认为中国美学的发生应该从其所谓的原始先民的“巫术文化”中找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一种文化的精神特质和传统虽然与其源头处的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特质和传统的真正形成则是来源于这一种文化在其自觉时期所创造的。就中国而言,中国文化和美学特质主要奠定于西周时期。西周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其对远古乃至夏商文化的确有所继承。但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伴随着农耕文明的成熟,中国文化开始真正走向自觉,并且奠定了后世数千年风教和文化传统。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和美学走上了一条真正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国美学史的发端仍应以美和艺术为核心问题
事实上,张编本并非完全排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只是可以介入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一个视角而已。李泽厚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其《美的历程》中,曾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介入中国美学发端的研究。其主要观点认为,原始先民的审美和艺术是潜藏在巫术礼仪和图腾崇拜的活动中,尚未分化和独立。且原始器物上的“文饰”并不只是纯粹为了一种美的装饰,而是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而“远古美学”一章的作者对于远古时代器具文饰上的巫术、宗教的符号象征意义并没有忽略。只是,他发现原始人已经有了充分的审美意识的自觉,虽然这种意识和原始人的宗教、巫术意识是并存的。
在“远古美学”一章中,张编本认为无论远古器物的文饰承载着怎样的精神意蕴,其对人视觉的迎合,其所呈现出来的外观形式,首先是一个美学问题。而至于器物作为符号的象征意义,也同样是远古美学的基本问题。这里面关键是要认识到远古器物具有实用、审美、象征诸方面的价值。由此,美和艺术的问题永远是美学史的核心问题,其他的问题是朝着这个问题聚集,且由此而获得更深刻的说明。基于此,笔者认为在介入中国美学的发端时,让美的历史居于核心地位是重要的,审美文化史乃至一般文化史只是围绕着这一核心而呈现自己。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美学博士生;摘自《文艺争鸣》2016年第12期;原题为《再论中国美学史的发端问题——兼与洪永稳、顾祖钊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