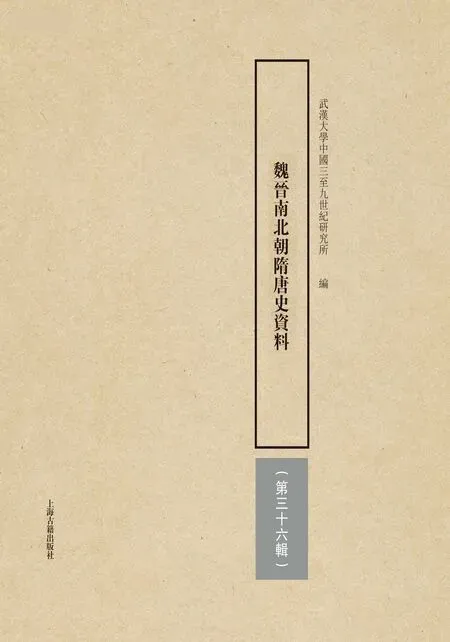關於《唐會要》流傳的考察
古畑徹 著 李雨豐 譯 劉安志 校
一、 前 言
成書於北宋建隆二年(961)的王溥《唐會要》一百卷,其如今的通行本,即武英殿聚珍版本(以下簡稱爲殿版)系統的諸本,[注]《唐會要》的通行本,包括殿版、鉛印了殿版的國學基本叢書本、中華書局本、世界書局本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存在着許多錯誤。若要利用該版本,必須參照東京静嘉堂文庫所藏明抄本(以下稱爲静嘉堂抄本),以及諸書所引的《唐會要》記事。最早指出這一問題的是平岡武夫氏。[注]贝冢茂树、平冈武夫: 《唐代史料の集成について》(《學術月報》七一六,1954)。平冈武夫编: 《唐代の行政地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5年),第19頁。其後,島田正郎氏介紹了藏於臺北圖書館的兩種舊抄本(以下稱爲臺北A抄本、臺北B抄本),并確認其中的臺北A抄本就是作爲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爲四庫本)底本的汪啓淑家藏本。[注]《在臺北“中央”図書館蔵 鈔本·唐會要について》(《律令制の諸問題》,汲古書院,1984年)。另外,島田氏還認爲殿版和四庫本是同樣的版本,他通過對校四庫本和臺北A抄本,指出四庫本是在四庫全書館,經過與唐代諸史料的綿密對校後成書的。
筆者曾基於上述觀點,對殿版、四庫本、静嘉堂抄本、臺北A抄本、臺北B抄本等五種版本進行調查研究,在1989年發表了題爲《〈唐會要〉的諸版本》(以下稱爲拙稿A[注]《東方學》七八,1989年。)的研究論文。筆者在文中明確了如下幾個觀點: 1. 静嘉堂抄本并非明抄本,而是清康熙抄本;2. 臺北B抄本是康熙以前的抄本,由此派生出静嘉堂抄本和臺北A抄本(康熙抄本);3. 殿版與四庫本是同樣底本的通行説法是錯誤的,兩者其實是不同系統的文本;4. 雖然已經推定四庫本基本上直接轉抄臺北A抄本,其缺損部分則由“别本”補入,但唯獨卷四十九後半段的五條并非源自“别本”,而是維持其缺失狀態;5. 殿版又名《御定重刻唐會要》,可以推定是以清初可能存在的某個刻本作爲底本(關於此點,本稿將進行若干修正),使用四庫本和《册府元龜》等唐代史料進行校訂和補入的,但其校訂仍存在問題。基於以上成果,可以對諸版本間的關係列圖,如圖1。這些事實將會大幅改變過去對《唐會要》版本的一般認識,也會再度確認平岡氏觀點的重要性。

圖分1 《唐會要》諸版本變遷圖
然而,拙稿A仍有兩個問題未及探討: 第一,抄本作爲史料的特點和價值。雖然拙稿A已經指出,根據殿版系統而成的通行本,明顯并非最佳版本。但抄本系統的版本是否就接近《唐會要》的原貌呢?像此類討論其特點和價值時最爲關鍵的問題,拙稿A并未展開探討。這樣一來,在利用抄本系統的版本時,前提就不充分了。
第二,在四庫本和殿版成書時所進行的校訂作業,是否利用了其他諸書所引用的《唐會要》内容?衆所周知,《四庫全書》編纂時大量利用了《永樂大典》,并從中復原了部分散佚的書籍。因此,若未經探討,就不能斷定四庫本校訂時没有利用過《永樂大典》。另外,雖然拙稿A已經明確,殿版成書時的校訂和補入工作,利用了《册府元龜》等史料,但那時是否也利用了諸書所引的殘存《唐會要》逸文呢?此點拙稿A仍未進行探討。若能確認校訂工作利用了逸文,那麽,這將大大影響到這些版本的特點和價值。
爲了解決上述兩個問題,就必須調查和研究諸書所引用的《唐會要》記事。而這些調查和研究工作,也能够推進如今并不充分的對諸書所引《唐會要》記事的利用工作,有着重要的意義。於是,我首先從《永樂大典》着手,發表了以《〈永樂大典〉所引〈唐會要〉記事一覽》爲題的研究成果(以下將稱爲拙稿B[注]《金澤大學教養部論集》人文科學篇二九—一,1991年。)。其後,則對《玉海》《事物紀原》《資治通鑒考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展開調查和研究,現已到了最終階段。本稿將介紹諸書所引《唐會要》記事情況,同時關照上面提出的兩個問題,并對其流傳過程提出一個假設。
在此過程中,中國學者發表了兩項研究《唐會要》版本的成果。我認爲,考察《唐會要》流傳過程問題,這些都是需要注目的成果。於是,我將首先檢討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并以此爲基礎,進而對諸書所引《唐會要》記事展開研究。
二、 關於中国的《唐會要》研究
(一) 中國現存《唐會要》諸抄本
中國學者的兩項研究成果,分别是1989年發表的鄭明《〈唐會要〉初探》(以下簡稱《初探》[注]《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和1991年刊行的《唐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是以殿版系的江蘇書局本(清同治年間刊)爲底本,以殿版、上海圖書館所藏四種抄本進行校訂,并利用《舊唐書》、《册府元龜》、《通典》等進行對校而成書的。《前言》(以下簡稱《前言》)。《前言》作者,是對本書進行點校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實際上這篇《前言》早在1986年6月就寫成了。
《初探》與本稿關聯較深的,是文中介紹和探討的中國現存的六種舊抄本。這六個抄本,分别是北京圖書館所藏三種(a、b、c本)和上海圖書館所藏三種(d、e、f本)。尤其是北京圖書館所藏三種抄本,在拙稿A的追記中,曾根據當時剛剛引進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中所介紹的册數、行格等,指出其與拙稿A所討論的三個抄本(下面稱呼這個系統的抄本爲臺北B抄本系抄本)之間存在屬於不同系統的可能性。故而,我將首先以《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和《初探》成果爲基礎,介紹北京圖書館所藏三種抄本的基本情況(以下,基於《初探》中的稱呼,將各個抄本稱爲北京a、b、c抄本),然後考察其與臺北B抄本系抄本的關係。
北京a抄本是全十二册的殘本,現存四十卷(卷一至三、十二至十五、二十至二十三、二十八至三十九、六十七至七十二、七十六至八十五)。行格爲十行二十字左右。據稱“字體粗劣,非出自一人之手。錯訛字不可勝數”。北京圖書館認爲是明抄本,鄭明氏也以其“陳舊殘破”的外觀爲根據,肯定這一觀點。鄭明氏還提及作爲一般看法的明抄本字體、體裁之拙劣特點,這也成爲其判斷該殘本爲明抄本的依據。筆者所要關注的,是其卷首目録也有殘缺,即從卷八到卷八十五稱“唐會要目録終”這一點。這暗示着此本在抄寫時已非完本,其目録和正文均不存在卷八十六以下的内容。但是,能够考察其與臺北B抄本系抄本之關係的材料基本没有。[注]根據《初探》,比較北京b抄本的目録與通行本目録,會發現少了卷四八《寺》、卷五八《户部侍郎》、卷六三《在外修史》,以及卷六四《崇元(玄)館》等標目。臺北B抄本系的目録也比通行本目録的標目要少。上述四項,除了《户部侍郎》,其他都已不存在。雖然從此也能産生聯想,但由於鄭明氏似乎并没有舉出所有缺失的標目,也就無法做進一步的探討了。
相對而言,北京b、c抄本則可以認爲是與臺北B抄本系抄本屬同一系統的。北京b抄本有二十四册一百卷,行格爲十行約二十字。《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認爲是清抄本,鄭明氏則根據未避康熙以下皇帝諱事例,且字體是清代使用的館閣體,認爲是順治年以前的清抄本。鄭明氏又指出,該抄本卷首目録前有《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玉海》之語的題解,卷七至十一有錯入,改“貞”爲“正”、不寫“構”而注爲“御名”等南宋高宗時代避諱例子,以這幾點作爲此抄本的特點。這些題解和錯入、避諱全都與臺北B抄本系抄本相同,因此可以認爲屬同一個系統。[注]根據《初探》,北京b抄本是翁之熹寄贈北京圖書館的。根據梁戰、郭群一編著《歷代藏書家辭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翁之熹是翁同龢(1830—1904)的侄孫翁斌孫之子。翁同龢的藏書由翁斌孫繼承,後者死後則由翁之熹繼承,解放後被寄贈北京圖書館。
另一方面,北京c抄本是二十册一百卷。鄭明氏稱“前十册有朱筆校文,而後十册無,書體也很拙劣”。關於行格,鄭明氏稱十行二十字,但《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則稱十行二十四字,不知孰是。《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認爲是清抄本,鄭明氏也根據其缺筆避康熙、乾隆之諱,且没有著録四庫全書提要,推定是四庫全書成書之前的清抄本。不過,并非所有四庫全書成書後的抄本都著録了四庫全書提要,鄭明氏的這一論證有點勉强,但這是乾隆以後的清抄本則是没有疑問的。而且,雖然没有題解,但卷七至十一的錯入,以及南宋高宗時代避諱的例子,這些都與北京b抄本一致。因此,筆者認爲,其與臺北B抄本系抄本也屬同一系統。
此外,關於北京c抄本,有一點值得注意。根據鄭明氏的介紹,北京c抄本上有“稽瑞樓”“鐵琴銅劍樓”之印。鐵琴銅劍樓即指常熟瞿氏的藏書,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二中有“唐會要一百卷舊鈔本”的記載,這條記事最後説:
此稽瑞樓(楊文蓀〈1782—1852〉的室名——筆者注)藏本。中有朱筆校過,較竹垞氏(朱彝尊〈1629—1707〉之號——筆者注)所見本尚多九十三、九十四兩卷。[注]朱彝尊所見本,即《曝書亭集》卷四五《唐會要跋》中所記常熟錢氏抄本: 今雕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近始借抄嘗熟錢氏寫本。惜乎,第七卷至第九卷失去,雜以他書,第十卷亦有錯雜文字。九十二卷闕第二翻以後,九十三、九十四二卷全闕。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書。姑識此以俟。據此,卷九三、卷九四確實全缺了。
據此,可以明確這就是北京c抄本。值得注意的是,這條史料提及該抄本存在卷九十三、九十四。鄭明氏也寫道“一百卷全”,即現在并無逸失的這一部分。[注]《初探》稱“一百卷全”,并未言及卷七至十内容是由其他史料補充的。因此,應該認爲其意是指包括後人增補在内,形式上的全卷齊全。相對而言,北京b抄本只記録爲“一百卷”,尚不明這種記述差别的含義。或許是卷數誤記,又或者是脱了“全”字,也或許意味着有某些卷存在較大缺失,這些都有待今後進一步的調查。與之相對的,拙稿A曾論及三種臺北B抄本系抄本中都不存在卷九十三、九十四這一問題。换言之,若認爲北京c抄本是臺北B抄本系之一的話,這兩卷就成爲嚴重的問題。但這也可以從北京c抄本前十册與後十册存在不同予以解釋。因爲有朱筆校文且字體也更秀美的前十册,與没有校文且字體較差的後十册差异明顯太大,據此可以判斷北京c抄本是由兩種不同的抄本拼合而成。也就是説,存在着可以認爲前十册屬臺北B抄本系,而後十册則否的可能性。筆者頗懷疑後十册乃後人的增補,當然這有待今後進一步的調查。
下面將檢討上海圖書館所藏的舊抄本。《初探》介紹了三種舊抄本,而《前言》則介紹了包括前者的四種。因此,這裏將依從《前言》,稱其爲上海甲、乙、丙、丁抄本,然後進行討論。而且,因《前言》已將這些抄本全部置於同一系統之中,故而,我對各抄本的介紹,不會着墨太多。
根據《前言》,上海甲抄本是舊抄本,十二册,卷首有傅增湘(1872—1950)等人的藏書印,與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六所記《唐會要》説明一致,應即傅增湘舊藏本。其特點如下: 1. 卷七至十全缺,由他書文字錯入;2. 卷九十二除了頭兩頁外皆缺,卷九十三、九十四全缺;3. 存在改“貞”爲“正”,“構”字缺筆,或注以“御名”等南宋高宗時代的避諱例子。因此,可以認爲,其與朱彝尊等人所見的常熟錢氏所藏抄本屬同一個系統,其源頭當來自南宋時期所成的某個版本。《初探》將其稱爲f本,藏書印情況也基本吻合。[注]可是,有關行格和缺卷的说明存在着矛盾。關于行格,《前言》所引《藏园群書经眼录》卷六稱是十二行二十五字,而《初探》f本是十二行二十三字。因爲一行的字数常有不同,根據调查的地方不同,得出不同的理解是常有之事。因此,筆者認爲,這个差异不足以成爲認爲上海甲抄本和f本是同一版本這一觀點的反證。關于缺卷,f本是卷九五全缺,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卷九五校勘記却使用了上海甲抄本進行校勘,這应该是鄭明氏的误記。另外,還追加了《前言》所無的四點特色説明:4. 卷十一有太宗、德宗、先秦時期的記事錯入;5. 卷首目録之前有《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玉海》之類的題辭;6. “玄”字有缺筆;7. 字體爲由多人所抄寫的館閣體。鄭明氏認爲這是明代到清初期的抄本,只是不能確定其具體時間。不過,從其6、7兩個特點看,上海甲抄本應該是清康熙抄本。
根據《前言》,上海乙抄本是清乾隆抄本,上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考中進士的彭元瑞“識語”。“識語”如下:
是書傳抄都無善本,舊曾有一部,雜取新舊《唐書》、《六典》、《開元禮》、《元和郡縣圖志》、《册府元龜》、《通典》、《通鑒》、《唐鑒》、《玉海》、《通考》及諸説部文集校改十餘年,頗覺爽豁。間爲友人借去,不戒於火,以是本見歸,脱誤與舊略等,就所記憶,少加訂改。俯仰二十年,手眼俱退,不能如向之精密也。芸楣。[注]《初探》也引用了這個識語,只是“新舊兩書”作“新舊唐書”,“脱誤與舊略相等”作“脱誤與舊略等”。
而且存在許多朱筆校改的地方,可以認爲這就是彭元瑞的手校本,而其錯雜缺失情況與上海甲抄本一樣。《初探》將其稱爲d本,行格爲十二行二十五字等,説明基本相同,但由於没有題辭,推斷有可能是明抄本,這與《前言》不同。[注]《初探》記爲“一百卷全”,卷九三、九四也存在,這也與《前言》不同。可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卷九三、九四校勘記中,并没有使用上海乙鈔本的痕迹,應該可以判斷爲是缺卷。恐怕鄭明氏只注意到了卷七至十一有他書錯入這點,而誤會爲包括增補在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全卷齊全。鄭明氏判斷其爲明抄本的理由,是不存在避清朝皇帝名諱的例子,且明抄本字體大多較爲粗劣。如果所言正確的話,其判斷爲明抄本的説法是妥當的。而《前言》有關乾隆抄本的説法,應該是因爲把彭元瑞的手校本誤解爲他不止校正,還全文抄寫了一次,又或者把“識語”中的内容理解爲其友人在原本被燒後抄寫他本歸還,這兩個原因之中的一個。
根據《前言》,上海丙抄本是清王宗炎(1755—1826)校本,開頭有朱彝尊的跋文,現存九十三卷,卷七至十、九十二至九十四全缺,文字與上海甲、乙抄本基本一樣。可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卷九十四的校勘記中,北突厥項開頭第一條的一個字,就是根據這個抄本校勘的。[注]校勘記中,《北突厥》第一條“送帝入關”中,記爲“‘關’原作‘闕’,據殿本、丙鈔本改”。因此,《前言》稱卷九十四全缺這一記述當有誤。但校勘者自己所寫的《前言》,不應無緣無故出現如此大的失誤。或許最爲穩妥的推論是,卷九十四應是存在大幅缺失的不完整的一卷,因而造成了這樣的誤記。[注]校勘記中有四處校勘存在,但除了前注這一處外,其餘都没有與丙鈔本進行對校,此足以支持這一推定。《初探》雖稱全九十四卷,卷九四也存在,但并未言及是否完整。另一方面,《初探》稱其爲e本,有行格,十二行二十四字,避康熙、乾隆之諱,且有缺筆,存在《玉海》等三書題辭,字體屬館閣體。鄭明氏據此判斷其爲清抄本。又因爲這是王宗炎的校本,因此,可以判定其爲乾隆、嘉慶時期的清抄本。
根據《前言》,上海丁抄本僅一册,殘存卷一至九,且卷七至九錯入情況,與其他諸本相同。《初探》并未提及這一抄本。
以上即是對上海圖書館所藏四個抄本的介紹。《前言》認爲這些抄本全部來自同一系統的抄本,筆者認爲這一觀點是妥當的。另外,《前言》認爲這些都屬常熟錢氏抄本的系統,并指出另有一個系統的抄本存在,即後來成爲四庫本底本的汪啓淑家藏本。關於這一説法的理由,《前言》指出後者卷九十二至九十四完備,稱四庫全書采用這一部分是“比較合理”的,并對其後殿本繼承這一做法表示理解。可是,正如拙稿A所明確指出的,汪啓淑家藏本,也即臺北A抄本,其卷九十二至九十四并不完備,四庫本是從“别本”補入的,而作爲殿版底本的刻本也没有這一部分,卷九十二、九十三是由其他史料,卷九十四則是從四庫本處增補而成的。也就是説,汪啓淑家藏本即臺北A抄本,其與常熟錢氏抄本也是同一個系統。换言之,臺北B抄本系的三個抄本,與上海圖書館所藏四種舊抄本是同一系統的版本。
以上就是對中國現存七種抄本所作的探討。其結果是,除了北京a抄本之外,可以判明其餘六種抄本都與臺北B抄本系的三抄本屬於同一個系統。也就是説,可以確認的現存十種舊抄本中,至少有九種屬於臺北B抄本系抄本。其次,除上海丁抄本外,其餘全部都屬從明到清初的抄本,而且可以確認乾隆時期存在的常熟錢氏抄本,也屬臺北B抄本系抄本。再次,彭元瑞最初所校訂的抄本,根據其“識語”,也可以認爲屬同一個系統。根據這些結論,可以推定,從明開始,到清初殿版出現之前,廣爲流傳、抄寫的《唐會要》,都屬臺北B抄本系抄本。而作爲其源頭的版本,根據大多數臺北B抄本系抄本都采用將南宋高宗的名諱寫爲“御名”的方法避諱情況看,應該是南宋高宗期(1127—1162)的抄本。
(二) 宋代《唐會要》的流傳
《前言》中,除上海圖書館所藏抄本以外,還有值得注意之處,那就是關於宋代《唐會要》流傳的兩個觀點: 其一是宋代已經存在刻本;其二是宋代已經存在好幾個异本。
《前言》認爲宋代就存在刻本的根據,是慶曆六年(1046)文彦博所撰《五代會要刻本題跋》中的記述:
本朝故相王公溥撰唐及五代會要,凡當時制度沿革,粲然條陳無遺。《唐會要》已鏤板於吴,而《五代會要》未甚傳。[注]筆者尚未確認這一題跋的出典,此處轉引自《前言》。
若這一記述無誤,則無异於發現了一條重要史料,證明《唐會要》在北宋仁宗的1046年時,就已經在蘇州被版刻了。
可是,關於這一刻本的記録,一直到清代都没有發現。因此,一般認爲,一直到殿版之前,只有抄本流傳,并不存在刻本。筆者過去在拙稿A中,以殿版一名《御定重刻唐會要》,以及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五《唐會要跋》中“今雕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認爲清初存在刻本,但不知其來歷。然而,根據《前言》,已經明確存在宋刻本,那麽若没有史料記載存在其他刊刻本的話,清初所存在的刻本是宋刻本的可能性就很高了。[注]《前言》中關於元、明時期流傳狀況的敍述,并未觸及刻本,但其後又説:“清代初期,《唐會要》刻本已非常罕見,著名學者和藏書家朱彝尊説:‘今雕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近始借钞常熟錢氏寫本’,就反映了這一情況。”關於刻本的存在,只在宋代流傳情況的敍述中有所提及,這裏所稱“《唐會要》刻本”,應該就是指宋刻本,但其文字表述并不明確。《前言》關於這一點到底如何考慮,尚不能確定。確實,與武英殿聚珍版一般都直接版刻四庫全書的通例不同,唯獨《唐會要》并未采用四庫本,而是以清初所存在的刻本爲底本這一特例,若是從發現了貴重的宋刻本因此采取例外做法方面去考慮,就會比較容易理解了。可是,只憑藉這個理由,就推定在清初存在的刻本就是宋刻本,仍有所不足。雖然現在尚未發現能直接證明宋刻本存在的史料,但與上述同樣具有异例性狀況的證據,還是有一個的。不過,要説明這一點,就有必要先對拙稿A中關於殿版底本的觀點進行修正。
拙稿A指出,殿版卷四十九後半段燃燈、病坊、僧籍、大秦寺、摩尼寺五條記事,是直接基於清初存在的刻本而來,但實際上,這五條都各只有二、三條記載而已。[注]卷四九後半的五專案中,只有兩條的是“病坊”、“大秦寺”,只有三條的是“燃燈”、“僧籍”、“摩尼寺”。不過,通過在拙稿B中所指出的僧籍逸文,[注]拙稿B中,確認是僧籍逸文的,是《永樂大典》卷八七○六《僧字·僧籍》以及卷八七○六《僧字·汰僧》所引用的《唐會要》記事,前者是天寶八載十一月十八日條,後者是會昌五年七月條。另外,認定是僧籍,或者是卷四九《雜録》逸文的,是《永樂大典》卷八七○六《僧字·度僧》所引記事的長慶元年三月、寶曆元年二月、大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條。以及《資治通鑒》胡注所引病坊的逸文[注]《資治通鑒》卷二五四廣明元年十一月乙亥條所附胡三省注引《唐會要》,有“至德二年,兩京市各置普救病坊”一條記事。這不見於殿版,根據内容推定其爲《病坊》的逸文。另外,《資治通鑒》卷二三七元和元年是歲條“摩尼教傳來”的記事中,胡三省注引用了“唐書會要十九卷”,記載有關於摩尼寺的大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和大曆六年正月兩條。很有可能并不是所謂《唐書會要》這樣的著作,而是《唐會要》的誤記。果如此,這兩條可以推定是《摩尼寺》的逸文。胡注也引用了許多《唐會要》的内容,但由於筆者整理尚未完成,本稿只好割愛這一部分的報告。等,可知除了各自的二、三條之外,原本《唐會要》還存在其他條文。清初所存在的刻本,這五條是不完整的。問題是爲什麽會不完整?僧籍缺落的形式,是較短的會昌五年條記事殘存下來,而其前後條文有所缺失,[注]會昌五年條應爲五年五月條,殿版脱落了五月。本頁注①所示的逸文,天寶八載十一月十八日、長慶元年三月、寶曆元年二月、大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諸條居其前,會昌五年七月條則位其後。另外,《病坊》的逸文應位於殿版所存兩條的中間位置。并非如同在流傳過程中掉了一頁這樣的文本缺損形式,而更像是特意取出這一條文的感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其他項目中也有少於三條記事的情況,但連續在三條記事之下的只有此處,唯獨這裏是异例。綜合這些情況看,可以推定清初所存在的刻本是抄録了部分記事的節本。
這一刻本即節本的推定,可以比拙稿A的觀點,更能整合性地説明殿版如何由清初所存在的刻本經過校訂而成的過程。比如説,拙稿A通過對殿版卷九十三《諸司諸色本錢上下》與《册府元龜》卷五〇五—五〇七《邦計部·俸禄》進行對照比較,發現包括文句在内的條文大半均一致,故得出結論認爲,刻本斷片式地殘存了寶應元年以前的《唐會要》原文,其後則主要據《册府元龜》的《邦計部·俸禄》加以補入。可是,那并非全部都是同文,尚存在殿版記事更爲節略的情況,以及雖然只有一條,但却比《册府元龜》多出四個字這樣的例外,推測應該是根據其他史料拼接而成的。[注]拙稿A中推定《諸司諸色本錢下》元和二年六月條,是由《册府元龜·俸禄》和其他史料接合而成。問題是,《册府元龜·俸禄》中并無“色役敕旨”這四個字,而記録了同樣内容的《唐會要》卷七十八《五坊宫苑使》元和二年六月條中有“敕”。同樣,《舊唐書》卷十四《憲宗本紀上》元和二年六月乙丑條記有“色役”,所以推定其是綜合了這些内容而補入的這一條文。但只有這一條經過了其他史料的綜合化處理,是不自然的。而且,這一條中,《册府元龜·俸禄》中,并不存在“伏以”、“近又”、“上副聖請,用弘至理”、“臣當司并不收管”等字句。若將其解釋爲節略,那麽就會變成一方面綜合了史料,另一方面卻對這些史料進行節略這樣不自然的解釋。或許應該認爲這一條文是殘留在清初所存在的刻本之中的。這一情況,若是考慮到卷九十三本來就存在於作爲殿版底本的刻本之中,只是因爲其爲節本,故而要從《册府元龜》進行增補,那麽就不需要假設一個例外也能説明了。在卷九十二第二項《内外官職田》中也是如此,除脱落了在四庫本中存在的條文,以及裏面的内容有兩條存在數字之异外,其他與《册府元龜》的《邦計部·俸禄》基本可以完全對應。這説明,該部分是與其他史料拼接而成,而無需作出例外之假設。[注]卷九二《内外官職田》中,四庫本有而殿版没有的,是景龍四年三月、長慶元年十月這兩條。《册府元龜·俸禄》的記事和殿版的記事,有部分不同的是開元十八年三月、十九年四月這兩條。拙稿A雖然并未明確斷定,但筆者現在的觀點是,《内外官職田》是從四庫本和《册府元龜·俸禄》編集而來的。可是,無論如何疏忽,也不應在編集時遺漏只有四條的四庫本條文中的一半。或許可以認爲,《内外官職田》原本存在於清初的刻本中,但因爲是節本,所以記事很少,故從《册府元龜·俸禄》進行增補,這樣説才比較合理。本來,由於作爲殿版底本的刻本也肯定缺失了卷七至十與卷九十四,筆者就輕易地認爲這與缺失了卷九十二第二項和卷九十三的朱彝尊所藏刻本是同一個刻本,并以此爲前提來進行討論。可是,在拙稿A的論述中,已經確認卷九十三中存在三條原始版本的原文,那麽其與卷九十三全缺的朱彝尊所藏刻本是不同的版本,就是很明顯的了。因此,應該排除前述的前提來進行立論。殿版脱落了明明還存在於四庫本的條文,這也可解釋爲是因其底本爲節本,最終不得不以四庫本來進行仔細的校訂和增補,但仍存在遺漏的疏誤。
如上所述,清初存在并成爲殿版底本的刻本,應該是節本。可是,以節本爲底本,這種行爲本身就是很奇怪的。事實上其也經過了大量的校訂、增補,基本上已經面目全非了。然而殿版既然有著《御定重刻唐會要》這一异名,那麽,這個刻本處於底本位置是不可動摇的事實了。我認爲,解釋這一异例性的方法,只能通過探尋該刻本的來歷進行。也就是説,現在能够得到的合理解釋,是因爲這個刻本是貴重的宋刻本,所以儘管是節本,但還是將其作爲底本。因此,雖然通過這兩個异例狀況給出了證據,但仍不能超出假設的範圍。不過,筆者現在還是如此理解,即“宋刻本=節本=清初存在的刻本”。再者,本稿至今爲止都是使用“作爲殿版底本的刻本”這樣的表述,爲了更加明瞭事實關係,以後將會用“置於殿版底本的位置的刻本”這樣的表述。
接下來將要檢討宋代就已存在异本這一觀點。持此種觀點的依據,是在大量引用《唐會要》的《玉海》一書中,引用《唐會要》异文的注有十處以上。根據筆者所見,在引用《唐會要》并注了异文的地方,至少有四十一處,注文中記爲“一本”或者“一本云”的,有十一處,“一作”有十二處,“一云”有十八處。[注]日期處没有明記出典,而用干支來注記的例子也有很多。現存《唐會要》所有文本的通例,都是用數字來表示日期,但也有數處記録了干支。有可能在原本《唐會要》中,數字和干支是一并記録的。若這個推測正確的話,那麽一并記録干支的注記,就有可能是從异本處引用的。另外,引用异文條目數字中,包括從卷二十八《藝文》之《唐前代君臣事迹·連屏·君臣事迹屏》中所引《續會要》的“一本云”一處,“一作”兩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玉海》卷一六四《宫室·宫》所附《勤政樓·花萼樓》中所引《唐會要》開元二十年六月條,其中注釋道“一本作天寶十三年六月,一本作開元二十六年。此是出處不同,非誤”。[注]這條記事屬於《唐會要》卷三〇《興慶宫》,臺北A抄本作“(開元)二十年六月”,殿版作“(開元)二十四年六月”。由此可知,南宋末期存在至少三種文本。從前面的考證中,我們知道,作爲臺北B抄本系抄本源頭的南宋高宗期抄本的系統,與可能是節本的宋刻本系統在當時是存在的,而在此之外還可能存在其他版本系統。
那麽,《玉海》所采用作爲基準的《唐會要》版本系統是什麽樣的呢?首先,把上述的四十一處异文注記記事,與臺北B抄本系抄本之一的臺北A抄本進行對校,可以發現臺北A抄本的字句與异文有八處基本一致,有三十二處與本文基本一致,還有一處没有對應的條文。由此可以判斷,《玉海》大多數時候所根據的版本,與作爲臺北B抄本系抄本源頭的南宋高宗期抄本屬同一系統,或者是非常接近的系統的版本。
在調查异文注記記事時,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它們全部都是崔鉉《續會要》所記大中六年(852)以前的記事。除三例之外,其餘全部是蘇冕《會要》所記德宗以前的記事。衆所周知,《唐會要》是把蘇冕《會要》四十卷和崔鉉《續會要》拼合,增補大中七年以後的記事,成全書一百卷的。但在宋代,蘇冕《會要》和崔鉉《續會要》也還各自獨立存在。我們可以確認這兩書的存在,如洪邁(1123—1202)在《容齋四筆》[注]卷一一《御史風聞》。其内容存在於《唐會要》卷六〇《御史臺》最初的故事條,字句也基本一樣。中就引用了蘇冕《會要》,而崔鉉的《續會要》最後可見引用的例子就是《玉海》,而且還有説法認爲蘇冕的《會要》,也曾被《玉海》所引用。[注]《前言》中,引用了谷霽光《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認爲《玉海》卷一三八《兵制》之《唐府兵、符契、折沖府、十二軍》所引《會要》有關府兵制度的記載,并非來自《唐會要》,而是來自蘇冕《會要》。可是,其根據僅僅是這條記事中有現行《唐會要》所無的内容,以及字句也有差异。這樣的例子在《玉海》中頻繁可見,并不限定在蘇冕《會要》所記唐德宗以前的記事中。因此,尚不能據此斷定這條記事就是引自蘇冕《會要》。
《玉海》雖然只在卷二十八《聖文·雜御制》之《唐前代君臣事迹·連屏·君臣事迹屏》中引用了《續會要》,但這裏也有异文的注記,有兩處是“一云”,一處是“一本云”。於是産生了兩個疑問: 其一,《續會要》的價值,在《唐會要》成書以後就下降了,而這時候仍有數種异本存在嗎?其二,《唐會要》與《續會要》當然會出現字句的不同,但爲何只有此處引用了《續會要》,而其他引用《唐會要》的記事,卻没有看到其與《續會要》進行對校工作呢?這裏需要注意的是,三處异文注記記事,全部都與《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的記事原文存在着字句的差异。[注]《玉海》卷二八《聖文》之《唐前代君臣事迹·連屏·君臣事迹屏》所引《續會要》記事,與《唐會要》卷三六《修撰》元和四年七月條同文。异文注記附於《續會要》“十一獎忠良”、“十三戎田獵”、“畫屏風六扇於中”下,分别寫作“一作忠直”、“一作簡田獵”、“一本云遣中使程文幹以事屏至中書”。將這些與《唐會要》臺北A抄本進行對校,前二者是“獎忠直”、“諫田獵”,“簡”通“諫”。因此,前二者的“一云”與臺北A抄本相同。最後一個,《續會要》和臺北A抄本相同。但這樣文意就不通了,推測應該是傳寫過程中存在脱落問題。現在的殿版作“書屏風六扇於中書”,筆者推測應該是校訂時根據文意補上“書”字。“一本”和現存《唐會要》字句并不一致,有可能该内容存在於當時的《唐會要》中。若是把這個异本理解爲《唐會要》,第一個疑問就可以解釋了。也就是説,筆者推測,《玉海》可能是把蘇冕《會要》和崔鉉《續會要》當作《唐會要》的异本來處理了。或許正因爲受到如此對待,蘇冕《會要》和崔鉉《續會要》都没能流傳到明代。
以上,通過對中國《唐會要》研究成果的介紹和探討,筆者盡可能闡明由明到清初的抄本傳寫及其在宋代的流傳狀況。下一章將以這些結果爲基礎,檢討諸書所引《唐會要》記事,考察其由宋到明的流傳狀況。
三、 關於諸書所引《唐會要》
(一) 《永樂大典》所引《唐會要》
對諸書所引《唐會要》記事的檢討,順着時代向上探索會更容易理解,所以首先就從《永樂大典》開始入手。《永樂大典》自永樂三年(1405)開始編纂,永樂六年(1408)完成,是中國最大的類書,完成時全書有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但現今僅存八百卷左右,其中有七百九十七卷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了。這七百九十七卷中,有九十七處引用了《唐會要》,拙稿B曾對此作了整理。[注]拙稿B中,以一覽表的形式記録了這97條所引記事。而筆者曾經解釋道,因爲其中一條,即《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二《人字·美人》中所謂“唐會要王珪傳”的記録,是《舊唐書·王珪傳》的誤記,所以實際引用記事爲96條(第3頁,第7頁)。然而,在寫作本稿時,筆者進行檢查,發現卷五二《忠諫》貞觀元年條存有這條記事。其原因恐怕是由於《永樂大典》的編者,見《唐會要》記事和《舊唐書·王珪傳》記事基本一致而産生混亂,從而出現這樣的誤記。因此,筆者在此修正拙稿B的觀點,將所引記事修改爲97條。因此,以下檢討將基於拙稿B整理成果而展開。
首先,前言曾提及《永樂大典》在四庫本、殿版成書時的校訂作業中是否被利用的問題,這裏將從此問題開始。通過對《永樂大典》所引《唐會要》和臺北B抄本系三種、四庫本、殿版進行對比,并没有發現被利用的痕迹,而否定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永樂大典》所引《唐會要》中,有上述五種《唐會要》都没有的記事。也就是説,存在着逸文。逸文總有十一條,在拙稿B中曾經推測這些條文原本的收録專案,包括卷三《内職》有一條,卷八《郊議》或卷九《雜郊議》有兩條,卷四十九《僧籍》兩條,卷四十九《雜録》兩條,卷四十九《僧籍》或《雜録》一條,卷五十《雜録》一條,卷五十九《兵部尚書·侍郎》或卷七十五《雜處置》一條,卷九十四《吐谷渾》一條。如前所述,卷八、九、四十九、九十四乃是四庫本和殿版校訂的重點。卷三《内職》條下,殿本也注云:“此條原本有闕”。由此可知,校訂者也很清楚存在着缺文。而這些有問題之處的逸文都能在《永樂大典》中見到,正説明《永樂大典》并没有在校訂作業中被使用。
第二,是文本間的對比結果。根據這個結果,《永樂大典》的文句、字詞常與殿版存在較大的差异。相較而言,抄本三種和四庫本的不同情況要比殿版少,基本没有巨大的差异。[注]《永樂大典》所引記事,與現存《唐會要》記載有巨大差异的例子,殿版有八例,三種抄本、四庫本則只有一例。詳細參照拙稿B。由此可以看出,殿版的校訂肯定没有使用過《永樂大典》。那麽四庫本又如何呢?要檢討這一點,比起較大的方面而言,感覺還是從較小的實例入手更好。試舉一例對比如下。
《永樂大典》卷六二三《農字·進農書》引用了《唐會要》卷二九《節日》貞元五年條,其中“士庶以刃尺相遺”的“刃尺”,三種抄本都空缺兩字,四庫本作“物”,殿版作“尺刀”。這條記事也見於《册府元龜》卷六○《帝王部·立制度》貞元五年正月乙卯條,作“刀尺”。《永樂大典》和殿版的字句在意義上更爲妥當,而四庫本的“物”則只能認爲是據文意理解而進行補充的。通過對比四庫本與作爲其底本的臺北A抄本,可以發現,像這樣推測是通過文意來補足臺北A抄本空缺的例子并不少。根據以上事實,可以判斷在四庫本和殿版成書時的校訂工作中,《永樂大典》完全没有被利用。
下面將檢討《永樂大典》所參照文本的具體情況。觀察《永樂大典》所引記事,都存在“民”作“人”、“治”作“理”這樣的唐代避諱,以及“貞”作“正”之類的宋代避諱。《永樂大典》并没有注意到避諱問題,而是直接從《唐會要》中引用了内容。卷一三三四五《諡字·諡法》“正”字條中,引用了《唐會要》卷七九《諡法上》的“貞”字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固然表明《永樂大典》編纂的粗雜,但也因此留下了其所引記事參照文本的原型。因此,《永樂大典》肯定參照了宋代文本,或者以其爲基礎另外抄寫的文本。
可是,宋代的文本也有數個系統。這其中可以從所引記事與現存諸文本的對校中,探明其與成爲臺北B抄本系抄本源流的南宋高宗期抄本系統的遠近關係。如前所述,《永樂大典》所引記事,與三種抄本、四庫本在文句、字詞上接近,與殿版則相差甚遠。爲了更加具體地展示這一點,筆者嘗試按照年號·年月日,把《永樂大典》所引記事、臺北A抄本、殿版三種文本的异同進行分類,用各自的頭一個字作爲略稱來展示的話,: 即: 1. 永=臺≠殿,17例(58.6%);2. 永=殿≠臺,4例(13.8%);3. 永≠臺=殿,6例(20.7%);4. 永≠臺≠殿,2例(6.9%)。《永樂大典》因在短時間編纂完成,故粗漏較多。基於這個原因,3應該是最多的,但實際上1占了壓倒性多數。也就是説,可以得出判斷,造成這種差异的主要原因,比起誤記所造成的不同而言,更可能是文本系統本身的不同。而《永樂大典》所參照的文本和臺北A抄本相當接近,這兩者與殿版則相差甚遠。由此可以認爲,《永樂大典》所參照的文本,即屬於高宗期抄本的系統。而且,由於其包含了卷三、八、九、四十九、九十四等逸文,可以推測應該是很接近原本的吧。
實際上,明朝廷有可能收藏了十分接近完本的《唐會要》。正統六年(1441)完成的有關明廷藏書目録《文淵閣書目》卷六中,有“唐會要 一部五册闕 唐會要 一部三十册闕 唐會要 一部二十五册闕”。這三種都是存在缺失的不完全本,但就筆者管見,并未見過諸書目中有三十册以上的《唐會要》,三十册本也已經是現在所知册數最多的文本了。因此,可以認爲,這個三十册本,是缺失較少且較爲接近完本的文本,或許就是《永樂大典》所參照的文本。
無論如何,明初存在着接近完本的高宗期抄本系統的文本,假若此文本因此留存到明末,那麽如現存諸抄本那樣大幅的缺失,也就不會出现了吧。不僅如此,在萬曆三十三年(1605)所作的《内閣藏書目録》中,明廷所藏《唐會要》三種都已經不存在了。也就是説,在15世紀中葉到17世紀初的一百六十年間,明廷失去了這些藏書。[注]有關明代官府藏書盛衰,可以參照來新夏等著《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5—267頁。因此,認爲卷三、八、九、四十九、九十四的缺失和缺損,就發生於明代,應該是没有什麽問題的。
(二)《玉海》所引《唐會要》
《玉海》是南宋末王應麟(1223—1296)修撰的類書,全二百卷。该書在宋元之交有所損佚,至元六年(1340)初刻時已非完本,此後也經過數次補修。平岡武夫氏已經指出,《玉海》大量引用了《唐會要》。[注]前揭平岡氏論文。實際上,檢索一下就會發現,其引用的形式有六種。以下將説明這六種形式以及各形式的引用數。
A. 本文首先寫上《唐會要》作爲引用書名,繼以引用文,而没有他書記事混入或者表示同文關係的注記。此類有659處。
B. 本文引用書名是《唐會要》,但混入了他書或者有表示同文關係的注記。進而言之,還存在三種形式: 引用書名下有“兼〇〇”、“又〇〇”這樣的割注;引用書名下有“〇〇同”之類的割注;本文末有“〇〇同”之類的注。此類有25處。
C. 本文引用書名是其他書,但混入《唐會要》記事,或者有表示與《唐會要》同文關係的注記。進而言之,還存在三種形式: 引用書名下有“兼會要”這樣的割注;本文末有“兼會要”的注;本文末有“會要同”的注。此類有30處。
D. 本文没有引用書名,而在本文末的注中説明引用自《唐會要》。根據注的表記法,有“會要”與“見會要”兩種形式。此類有5處。
E. 本文是他書的引用文,而在其注中引用了《唐會要》的文句、字詞。根據注的内容,存在三種形式: 與本文有一定關係的引用;爲了展示與本文引用書字句异同點的引用;在注裏進行考證的引用。此類有334處。
F. 在本文中的編者考證中,引用了《唐會要》。此類有7處。
以上合計檢索出1 060處引用事例。
首先,將檢討《玉海》在四庫本、殿版成書時的校訂工作中是否被利用這個問題。把《玉海》所引《唐會要》記事,與前述五種《唐會要》文本進行對比後,并没有看到被利用的痕迹。有很多逸文、缺文,可以作爲否定其利用的證據。殿版中没有確認到的記事有123條,而四庫本中没有確認到的記事則有119條。這裏面,作爲校訂核心的,可認爲是卷七—十的逸文有37條,[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卷末附録中,收録了《〈玉海〉中的〈唐會要〉逸文》,内有標校工作者推測本應存在的卷七—卷十的36條逸文。可是這個附録存在較大的問題,一方面,仍有被認爲是逸文的條文未被載入;另一方面,卷九《雜郊議》收録的天寶九載條、開元定禮條,卷十《雜録》收録的開元十二年條、卷十《籍田東郊議》收録的開元二十三年條,這四條分别見於《唐會要》卷二三《緣祀裁制》、卷二二《社稷》、卷二七《行幸》及卷三六《修撰》,并非卷七—十的逸文。另外,其他記事的歸類問題,也有很多與筆者觀點不一致之處。卷九十二的逸文有1條,卷九十四的逸文有4條。由此可見,《玉海》在四庫本、殿版成書時的校訂工作中并没有被利用,這一看法是妥當的。
接下來將檢討《玉海》所參照的《唐會要》文本與現存諸文本的關係。在前一章中,筆者已經推定,《玉海》作爲基準的文本,與成爲臺北B抄本系抄本源流的南宋高宗期抄本屬同一系統,或者是相近的文本。這也可以從《玉海》留下的《唐會要》逸文、缺文情況得到確認。雖然要確認殿版的哪一卷、哪一部分,是直接基於位於其底本位置的刻本,這種判斷十分困難,但如果存在於四庫本的記事被殿版遺漏的話,就可以知道這些被遺漏的記事肯定不存在於那個刻本上,可以認爲是校訂工作時未曾注意,就直接刊印了。也就是説,臺北B抄本系抄本、四庫本中存在而殿版没有的記事,就是在高宗期抄本系文本中存在,而位於殿版底本位置的刻本中没有的記事。前面已經指出,在殿版中確認不到,而能在四庫本中確認到的《玉海》所引記事有4條,[注]這四處分别是卷一○五《音樂·樂隊》之《唐鄉飲大射樂隊》(《唐會要》卷三三《太常樂章》皇帝射條)、卷一五三《朝貢·外夷來朝》之《唐日本遣使入朝·請授經》注記(《唐會要》卷九九《倭國》永貞元年條)、卷一六五《宫室·館》之《唐修文館·昭文館·弘文館》等等太和九年條的一部分(《唐會要》卷七七《弘文崇文生舉》太和九年條)、卷一六七《宫室·院》之《唐集賢殿書院·麗正殿書院》等等“華清宫集賢院”開元二十八年條(《唐會要》卷六四《集賢院》華清院條)。而反過來的記事則没有。這四條記事上文已有所提及,也就是《玉海》所依據文本更接近高宗期抄本系文本的一個證據。
另外,上節已經考證《永樂大典》所參照的是高宗期抄本系文本,然《玉海》中也有36處與《永樂大典》所引《唐會要》相同的記事。由於《玉海》多爲節引,因此調查《玉海》字句和《永樂大典》字句是否相同時,就會發現大多數是一樣的。[注]下面將以殿版《唐會要》卷二九《節日》開元十七年條爲例,用《玉海》卷五八《藝文·録》之《唐千秋金鑒録》所引記事與《永樂大典》卷一二○四三《酒字·獻萬壽酒》所引記事進行校勘: 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王公戚裏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絲結(1)承露囊,更相遺問(2),村社作壽酒宴樂(3),名賽白帝,報田神。(1) “絲結”,《玉海》《大典》作“結絲”。(2) “遺問”,《玉海》《大典》作“問遺”。(3) “酒宴樂”,《大典》無“宴”。另外,《永樂大典》卷六二三《農字·進農書》中,有一條屬於現存《唐會要》卷二九《節日》貞元五年條的佚文:“以中秋節代晦日。其月二十六日,中書侍郎李泌奏。”[注]《事物紀原》卷一《正朔暦數部·中和》也引用了這條《唐會要》記事,作“二十八日”,“二十六日”恐怕是《永樂大典》的誤寫。這條二十六日的記事,在《玉海》卷一七八《食貨》之《唐兆人本業記·中和節進農書》中,所引《唐會要》則記爲“二十八日,李泌奏”。這也應該可以表明《永樂大典》所參照的文本,與《玉海》所依據的文本是同一系統了吧。以上所言,可以補充前一章的推論。
由此可見,《玉海》所引《唐會要》記事是相當可信的,但問題卻并没有那麽簡單。因爲《玉海》所引乃是對原文的節略,而《玉海》現行文本也有不少謬誤。後者可以從其所引記事與現存諸文本進行對校得知。與上文對《永樂大典》所引記事進行檢討一樣,根據年號和年月日,對《玉海》所引記事、臺北A抄本、殿版三種文本之間共269例异同進行分類,以各自頭一個字爲略稱來表示的話,就是這樣: 1. 玉=臺≠殿,103例(38.3%);2. 玉=殿≠臺,34例(12.6%);3. 玉≠臺=殿,116例(43.1%);4. 玉≠臺≠殿,16例(5.9%)。這一檢討的特點,與《永樂大典》的情況相比就會很明顯,那就是《玉海》最有可能誤記的第3點是最多的。正如本節開頭所述,《玉海》在宋元之交有所損佚,初刻時已非完本,因此誤記較多也是理所當然的。故而在利用《玉海》所引《唐會要》時,有必要注意這一點。
根據這一檢討,還有一點值得注目,那就是1和2的差异。1和2的比率爲75對25,據此可以得出與迄今爲止的檢討結果相符合的結論,也就是《玉海》所參照的文本與臺北A抄本非常接近,而與殿版相差甚遠。而這裏1和2的比率,在《永樂大典》中是81對19,幾乎一致。1和2差异如此之大,其原因或許不止是因爲所依據的文本有所不同。
由此,筆者開始注目《玉海》所引《唐會要》形式E的第二形式——本文是他書的引用文,但爲了表明與本文引用書字句的异同,而在注記裏引用了《唐會要》的文句和字詞。這個注記中的《唐會要》字句,和殿版的同一處字句不同,這一方面的例子有16例,其中13例中殿版字句和他書引用字句相同。相對的注中《唐會要》的字句,與臺北A抄本、四庫本同一位置的字句不同的例子,只有3例。另注中《唐會要》字句與殿版同一處不一樣的16例中,與他書引用字句相同的,也只有1例。[注]這個例子是,《玉海》卷一八《地理·郡國》之《唐太宗并省州郡》所記“今考之《志》、《會要》,關内則泉稷……廢於元年,南夏……北連州廢於二年”,其中南夏州所附注中,記作“《會要》: 五年”。臺北A抄本、四庫本、殿版的卷七〇《州郡改置上》關内道夏州寧朔縣條中,所記都是“武德六年置南夏州,貞觀二年,廢州來屬”。筆者認爲,這個結果意味着殿版在參照他書進行校訂工作時,改變了本來的《唐會要》字句。换言之,1和2的巨大差异,不僅僅是因爲所據文本存在着差异,殿版在校訂時改變了原文的字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三) 《事物紀原》等書所引《唐會要》
在北宋的諸多史料中,引用《唐會要》較多的,是《事物紀原》《資治通鑒考异》《太平御覽》與《太平廣記》(以下將分别略稱《紀原》《考异》《御覽》《廣記》)。那麽,以下就對這些書所引用的《唐會要》記事進行一次大概的縱覽。
《紀原》是被認爲開封人的高承在元豐年間(1078—1085)編纂的一部類書。原本有十卷二百七十條專案,由於後人的增補,在南宋時已經有二十卷了。因此,不能斷定其所引《唐會要》就是北宋年代的版本,也不能説高承所見的文本,與後人所見文本就是一樣的。
雖然《紀原》也存在文本問題,但暫且還是用中華書局點校本(1989年刊)作爲基準文本,檢索其中引用《唐會要》的記事。[注]中華書局點校本的底本,是成化八年(1472)刊的李果刻本。該本雖然利用了一部分被移録到傅增湘校本中的宋本進行補入,但并未利用宋本本身。實際上,慶元三年(1197)建安余氏刊宋本二十卷就現存東京静嘉堂文庫,根據筆者所見,不止字句,就連記事的分配排列,都與中華書局本存在許多差异。雖然這是錯誤甚多的麻沙本,但要利用《紀原》,還是有必要進行參照。筆者現在仍未完成其對校作業。在《静嘉堂秘笈志》卷九中,記有其卷數二十六卷,刊行者爲全氏。通過檢索,發現總共有92條,其中有5條是現存諸文本中没有的逸文。這些逸文中,卷七《道釋科教部·僧賬》中引用有如下内容:
又(《唐會要》)曰: 舊制,僧尼簿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留州縣。又開元十七年八月十日,敕僧尼宜依十六年舊制。[注]這條記事,《永樂大典》卷八七○六《僧字·僧籍》引用了《紀原》,是完全的同文引用。
從内容看,這應該是卷四十九《僧籍》的逸文,而殿版中有與前半段條文内容一致的記載:“每三歲,州縣爲籍,一以留州縣,一以上祠部”。就引文而言,《紀原》應該是直接記録了本來的條文,而殿版則是摘引,僅取文意而已。如前所述,卷四九《僧籍》在現存《唐會要》中,只有殿版中還有記載,可以認爲這是依照位於底本位置的節本而來的。那麽,刻本是節本的這一推斷,可以由此得到進一步的支持,同時也可以推定《紀原》是從完本引用這一條記事的。然而,由於前述《紀原》的成書問題,這一推定并不能推廣到全書情況上。
《考异》是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的同時,整理其史實,考據其經緯,而得三十卷,與《資治通鑒》一同成書於元豐七年(1084)。今以縮印宋刊本的四部叢刊本(1919年刊)爲基準文本,對其所引記事進行檢索,檢出20條記事,其中5條是現存《唐會要》文本所没有的逸文,但并没有卷四十九的逸文。因此,不能據此考察司馬光所參照的文本是否爲完本,只有探尋其他推定方法了。不過,《資治通鑒》在設於崇文院的史局編纂這一點,成爲了提示。本來,《唐會要》就是進呈給宋太祖,收藏於史館的,[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建隆二年正月甲子條。此後也一直藏在位於崇文院的三館、秘閣裏。在慶曆元年(1041)成書的《崇文總目》卷三中,就記有“唐會要一百卷 王溥撰”,這當然就是完本。因此,認爲司馬光參照了這個完本,也不會有什麽問題。
《御覽》和《廣記》都是在宋初受敕命而編纂的宋朝四大類書之一,《御覽》成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全一千卷;《廣記》成於太平興國三年(978),全六百卷。兩書離《唐會要》編纂時間都很近,而且也是敕撰,可以推測它們都參照了《唐會要》的完本。
至於它們所引記事的概要,《御覽》擬以四部叢刊三編本(1935年刊)爲基準文本進行檢索,此本乃用另一宋本補充南宋慶元五年(1199)刊本而成。通過檢索,發現有32條記事,其中兩條不見於現存諸文本,應爲逸文。其特徵是,32條記事中有29條存在於卷五六六至五七四的《樂部五—十二》。相應的,其引用記事則集中於《唐會要》卷三十二到三十四與“樂”相關的標目,而逸文之一也是卷三十三《西戎五國樂》逸文。《廣記》則用中華書局點校本(1961年刊)爲基準文本,進行檢索,結果有31條記事。[注]這31條記事中,包括了寫作“出唐續會要”的卷一八六《銓選二》楊國忠條。《廣記》開頭的引用書目中并没有《續會要》,這應該是《唐會要》的誤記。另外,這條記事引自《唐會要》卷七四《掌選善惡》天寶十二載條。其中兩條不見於現存文本,應爲逸文。其特徵是,全部記事都集中在卷一九六《知人一》、卷一八五《銓選一》、卷一八六《銓選二》這三卷中,而能够確認出處的記事,又都引自《唐會要》卷七十四《掌選善惡》、卷七十五《選限》與《藻鑒》這三個標目。
以上對宋代諸書所引《唐會要》進行了探討。這裏還有一個迄今爲止都特地回避了的問題,那就是這些所引《唐會要》記事中,是否混入當時仍然流傳的蘇冕《會要》、崔鉉《續會要》?《紀原》在全書第一次引用,也就是在卷一《正朔歷數部·中和》[注]譯校者按:“中和”條在《事物紀原》卷一《天地生殖部》,而非卷二《正朔暦數部》,原文此處有誤。中,明記是“王溥唐會要”,故可判斷并没有兩書的混入。問題在於後面的三部書中。
首先從崔鉉《續會要》開始探討。由於《廣記》開頭引用書目裏没有《續會要》,因此可以不在討論範圍之内。而《考异》與《御覽》在引用《續會要》時會明確記録書名,可以判斷除非有文本誤寫,否則不會混入。
其次討論蘇冕《會要》。《御覽》和《廣記》開頭引用書目所列皆爲《唐會要》,并無《會要》,出典表記也是《唐會要》。也就是説,兩書應該都只引用了《唐會要》或《會要》二者之一。《御覽》卷五六九《樂部七·淫樂》中,先説“《唐會要》曰”,然後引用了卷三四《論樂》調露二年條,[注]《御覽》該條作“調露元年”,但就筆者所見《唐會要》現存諸文本,全部皆作“調露二年”。這應該是《御覽》的誤記,或者是誤刻。其後“又曰”,引用卷三四《雜録》咸通中條。咸通年間(860—874)的記事,在蘇冕《會要》中并不存在,因此,用“又曰”的形式,應該與調露元年條引用的是同一部書。所以,《御覽》所引《唐會要》,可以斷定就是王溥的《唐會要》。這個結論應該也可以推廣到《廣記》,但因爲《廣記》中全部都是唐德宗以前的記事,故這樣的斷定,恐怕還存在些許令人不安之處。最後是《考异》,因爲其引用書名有《唐會要》和《會要》兩種,因此判斷會有些困難。可是,不應該存在於蘇冕《會要》中的元和二年(807)記事,卻在《考异》中用《會要》的書名引用了,因此,可以確定這兩種引用書名,并不是指不同的兩種書。而憑藉元和二年這條記事,認爲兩種書名都是指王溥《唐會要》,應該是比較妥當的。
四、 結語——提出假設
最後,我將對到此爲止的考察進行總結,并對《唐會要》流傳相關問題,提出我的見解。在公元961年成書的王溥《唐會要》,從北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至少兩種异本存在: 其一爲後來以抄本流傳的完本,其二爲1046年以前就在蘇州刊行的刻本。從諸書引用情況看,前者在北宋與南宋被廣爲引用,相較而言,後者并未發現被引用的情況,看來宋刻本并未廣泛流布。一方面,被王溥《唐會要》基本直接吸收的蘇冕《會要》和崔鉉《續會要》,在北宋和南宋都曾作爲獨立的書籍流傳,可是到南宋末期,其獨立性逐漸減弱。在《玉海》編集之時,已經被當作王溥《唐會要》的异本來處理了。或許正是受此影響,這兩部著作在南宋末到元代期間就散佚了。
《唐會要》的抄本,在明初編纂《永樂大典》時,幾乎還是完本。在明代期間,這一抄本大幅地缺損了。其中殘留下來的,是繼承了南宋高宗期抄本系統的文本,内中卷七至卷十以及卷四十九後半等缺損,卷九十二第二項至卷九十四也缺損。這個版本被廣爲傳寫,成爲多數明抄本、清初抄本的基礎。其中,像此前判斷臺北A抄本和四庫本的聯繫那樣,將臺北B抄本系抄本和《永樂大典》進行對校,發現其字句相當接近,應該保留了明初文本的模樣。這當屬在前者完全缺損之前就被傳寫的抄本系統,推測其應是如今已經不完整的所謂“别本”,或者是保留了卷九四的上海丙抄本。
另一方面,我們已經很難確定宋刻本在之後的情況了。在本稿的推測中,若此宋刻本就是位於殿版底本位置的刻本,那麽這個刻本就是抄録了記事的節本,經過南宋、元、明時期已經有了大幅度的缺損,到清初則至少缺失了卷七到卷十以及卷九十四。姑且不論這到底是不是宋刻本,殿版把有缺損的節本置於底本的位置,利用四庫本和他書來校訂,補充其缺損和節略,最終在嘉慶初年刊行,這應該是無疑的。可是,由於没有利用到諸書所引的《唐會要》記事,而且利用他書進行校訂和補入,并混雜了兩種系統的文本,這使得殿版成爲與兩個系統都有巨大差异的文本。
以上就是本稿的結論,但終究也只是迄今爲止的假設。今後隨着對文本調查的推進,將會不斷進行修正,一定會成爲更加精細的假設,還請諸位讀者多加見諒。

圖2 本稿所推定的《唐會要》的流傳(現存的文本有下劃綫)
附記: 本文原載《東洋史研究》57—1,1998年,翻譯得到著者古畑徹教授的授權,羅亮博士對譯文提供了若干修改意見。謹在此向二位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