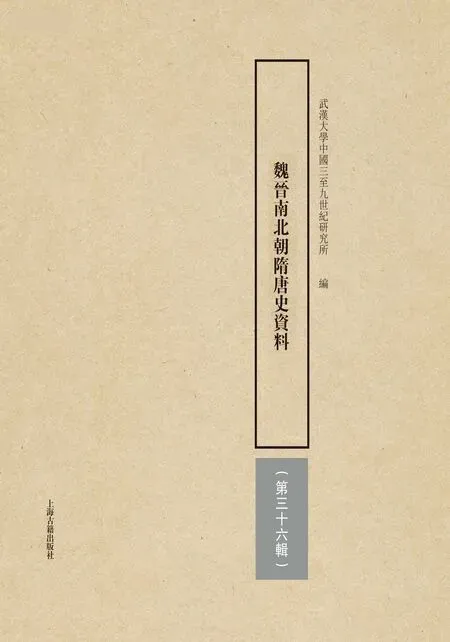服制、符命與星占: 中古“白衣”名號再研究
楊繼承
據《舊五代史·吐蕃傳》載:
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注]《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6年,第1840頁。
《新五代史·四夷附録》亦有相同記載。[注]《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録》,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915頁。由於史籍記録過於簡單,“金山白衣天子”這一名號長期不曾得到關注。[注]沈曾植最早對“天子”二字進行了解釋,他認爲:“夷虜豪酋多以夷語自稱,天子乃中國雅語,非彼所解也。疑此二記所謂天子者,正與元人之大石,明人之臺司臺什同,正華語太師之轉音耳。”(沈曾植著,錢仲聯輯: 《海日樓札叢》卷二,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第72頁)不過,金山國是一個漢族政權,張承奉并非“夷虜豪酋”,且“師”“子”兩字聲母懸隔,故此解釋難以成立,也不曾受到關注。1935年,王重民對金山國歷史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且率先注意到“白衣天子”這一問題。他利用敦煌星占文獻中的“白衣爲王”“白衣爲人王”等占辭,并結合唐代“白旗天子出東海”等開國謡讖,認爲“白衣天子”源自唐代謡讖,并在隋末時期的秦隴之地頗爲流行。[注]王重民: 《金山國墜事零拾》,《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9卷第6號,1935年,第10—13頁。對於王重民的研究,唐長孺認爲他并未對“此種謡讖之起於何時與其來源”加以説明,因此撰寫了《白衣天子試釋》一文,提出“白衣爲彌勒教之服色,起原當在元魏之世。而白衣天子亦爲彌勒教之謡讖”的論斷,[注]唐長孺: 《白衣天子試釋》,《燕京學報》第35期,1948年,第228、237頁。成爲有關“白衣天子”的通行觀點。
繼王重民、唐長孺之後,學者們或從“尚白”的服飾特徵、張承奉的信仰出發,將“白衣天子”視爲摩尼教、佛教(包括彌勒教、净土信仰)、道教等宗教信仰的産物;或從五行讖緯這一文化背景出發,探尋“白衣天子”謡讖的本土思想根源。
以“尚白”這一服飾特徵爲依據者,以西人哈密頓爲代表。他認爲,由於“白衣”是摩尼教聖徒們的服裝,且金山國境内有兩個州有回鶻居民,故而選擇“白衣”爲帝號,是想到了這些依附尚不太鞏固的回鶻州。[注]J.R.哈密頓著,耿昇·穆根來譯: 《五代回鶻史料》,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53頁。然而,張承奉祖孫三代曾與回鶻人有世仇,金山國最終也亡於甘州回鶻,金山國這一“歸義軍”性質的政權,似乎不可能在帝號這樣重要的事情上傾向於回鶻人所崇信的摩尼教。單純以服色尚白這一依據進行簡單的比附,得出的結論很難讓人信服。
因此,學者們多轉向張承奉的信仰層面尋求解決之道。在唐長孺所提出的“白衣”爲彌勒教謡讖的基礎上,魏静認爲:“張承奉的宗教信仰應該是以佛教信仰爲主”,故傾向於“白衣天子”出自佛教。[注]魏静: 《有關“白衣天子”札記》,《甘肅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45—47頁。姜望來則注意到了《北史·藝術傳》所載“齊當興,東海出天子”謡讖,認爲應當是隋末“白旗天子出東海”讖謡的淵源。由於這一謡讖出自沙門靈遠之口,因此被認爲具有佛教背景。[注]姜望來: 《讖謡與北朝政治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5—197頁。不過,對於張承奉的信仰歸屬問題,榮新江早就指出:“從宗教信仰來看,張承奉不能算是一位佛教徒,他大概更迷信於陰陽五行讖緯之説。”[注]榮新江: 《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4頁。而且,出於靈遠之口的謡讖,并不一定來自於佛教。據《北齊書·方伎傳》,沙門靈遠後來“罷道”還俗;在述及此事時,用的是其俗名荆次德,且述此人“有術數”。[注]《北齊書》卷四九《方伎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2年,第676頁。因此,這一謡讖是源自佛教,還是中國所固有的“數術”傳統,尚難以分辨。
此外,認爲“白衣天子”來自道教,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觀點。如日本學者宫川尚志、氣賀澤保規根據隋末出現的“白衣老父”事件,認爲隋末的“白衣”符命應該與道教有着密切的關係,并且是李唐王朝與當時的道教互相支持的一種表現。[注]氣賀澤保規: 《〈大唐創業起居注〉的性格特點》,劉俊文主編: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23—224頁。盧向前也認爲,“白衣天子”應該受道家影響,不過他也仍舊承認,“白衣”爲五涼讖緯、彌勒迷信,[注]盧向前: 《金山國立國之我見》,《敦煌學輯刊》1990年第2輯,第18頁。這無疑是將讖緯、佛教、道教三説雜糅在了一起,成爲一種調和之論。
從五行讖緯領域進行的探索,則是在王重民研究基礎上的繼續。李正宇在一定程度上認可王重民“白衣”出自唐代開國謡讖的意見,但又認爲其研究“囿於一時一地”,忽視了“白衣”有其“久遠而根深之傳統觀念”,主張“白衣天子”名號乃是“古代漢民族傳統的五行讖緯思想的産物”。他依據五行學説,西方爲金,色尚白,故將“白衣天子”釋爲“西方天子”。[注]李正宇: 《關於金山國和燉煌國建國的幾個問題》,《敦煌史地新論》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第207頁。在李正宇的基礎上,楊秀清也認爲:“金山國之‘白衣天子’也是與傳統五行之説相一致的。”[注]楊秀清: 《敦煌西漢金山國史》,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頁。昞麟認爲“白衣天子”的“白衣”與“敦煌爲金方色尚白相適,又符合白衣爲主之説”,也與此近似。[注]昞麟: 《金山國名稱來源》,《敦煌學輯刊》1993年第1期,第52頁。榮新江也認爲:“金山國建於開平四年七八月交,正好與西漢、金山、白衣的五行之説相符。”[注]榮新江: 《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第219—220頁。儘管從傳統的五行觀念來説,“白衣”確實與西漢金山國的地域、國名、建國時間相吻合,但這些研究卻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白衣”這一語詞的内涵及其相關文化背景。
據余欣介紹,法國漢學家茅甘(Carole Morgan)在《西北邊疆的動蕩》一文中,考察了P.2632、P.2941等5件占卜文書,并將“白衣”解釋爲“平民”(The Common Peple)。儘管這種解釋看似“簡單化”,但從占卜文書的角度出發,回歸“白衣”這一語詞的通用意義,可以説是我們重新理解“白衣天子”的新起點。余欣認爲,“白衣天子”的“確切來源還得到五行説、讖緯、道教符篆中去尋找”。[注]余欣: 《法國敦煌學的新進展——〈遠東亞洲叢刊〉“敦煌學專號新研”專號評介》,《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1期,第109—110頁。趙貞也以爲,要解決這一“中古經學以及思想史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很可能要從傳統的讖緯和星占理論中去切入”。[注]趙貞: 《敦煌遺書中的星占著作: 〈西秦五州占〉》,《文獻》2004年第1期,第64頁。
循此思路,我們對“白衣”、“白衣天子”及其相關文化現象的研究,既不能再局限於具體的語詞,[注]從語言學角度對於“白衣”的研究,可參見吴娟《也説“白衣”》,《語言研究》2008年第1期;王鳳、張世超《白衣溯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4年第3期。也不能只關注魏晉、隋唐五代或者金山國這一時一地。因此,本文的研究將進入到更爲廣闊的時代與文化背景中去,從漢代服制背景下産生的“白衣”身份符號出發,以作爲“服妖”的“白衣”及“白衣爲天子”觀念的流行爲切入點,對中古時期出現於災异祥瑞、星占系統的“白衣”符命與占辭做一系統的探究,從源流上對作爲謡讖、占辭、符命、名號的“白衣”現象做一清理。在此基礎上,我們不僅能獲得對於“白衣天子”名號的更爲合理的認識,也能够對“白衣”這一符命從産生到流傳,從迎合到模擬的整個過程得到更爲清晰的了解。
二、 身份符號與“服制”:“白衣”身份的再認識
“白衣”,本指白色衣物。《墨子·備梯》篇“以白衣爲服”,[注]孫詒讓撰,孫啓治點校: 《墨子閒詁》卷一四《備梯》,北京: 中華書局,2001年,第539頁。是目前有關“白衣”之最早記録,即用其本意。在明堂、迎氣、求雨等禮儀當中,爲順應秋天這一時節,依照五行配色之要求,“白衣”又多用作禮服。[注]關於明堂月令禮制中的白衣,參見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吕氏春秋集釋》卷七《孟秋紀》,北京: 中華書局,2009年,第155頁;關於求雨時服用白衣,參見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一六《求雨》,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第435頁;關於迎氣時服用白衣,參見《後漢書》志第八《祭祀中》,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第3182頁。自漢代以來,“白衣”逐漸成爲庶民的身份符號,頻繁地出現在傳世史籍中。如“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注]《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第3118頁。“文叔爲白衣時”[注]《後漢書》卷七七《酷吏列傳》,第2490頁。等語句中的“白衣”,即都指代未曾出仕、没有官職的庶民。[注]相關辭例極多,又可參見《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尚傳》,北京: 中華書局,1959年,第299頁;《三國志》卷一六《魏書·倉慈傳》,第515頁;《三國志》卷二三《魏書·常林傳》,第663頁。本來,有關這一語詞的意義并没有多少歧義,但顔師古的一條注文,卻使我們對“白衣”身份的確認産生了一些疑問。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載:
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
顔師古注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注]《漢書》卷七二《王貢兩龔鮑傳》,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第3082—3083頁。顔師古將“白衣”視爲官府驅使的雜役賤人,并與唐代的“諸司亭長掌固”相類比。所謂“亭長掌固”,《舊唐書·職官志》有載,屬“尚書都省”,亭長設六人,掌固設十四人,“檢校省門户倉庫廳事陳設之事”,[注]《舊唐書》卷四三《職官二》,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1818頁。爲尚書都省處理各項雜物之低級吏員。受顔師古之影響,後人有以“賤者之稱爲白衣”者,[注]焦廷琥: 《讀書小記》,稿本,不分卷。有以爲“漢白衣賤”者;[注]尚秉和著,母庚才、劉瑞玲點校: 《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卷五《身服》,北京: 中國書店,2001年,第59頁。亦有全襲用師古之説,以爲漢“給使賤役著白”者。[注]王楙撰,鄭明、王義耀校點: 《野客叢書》卷一八《漢臣僕衣皁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8頁。
由於顔師古的影響,對於一些出土文獻中的“白衣”語詞,也大都襲用了這一解釋。在走馬樓吴簡中的一些“私學名籍”中,“白衣”也被用來表示身份。曾磊曾對這些名籍有過較爲詳細的統計,[注]曾磊: 《文化史視角下的秦漢顔色研究——以白色的象徵意義爲中心》,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武漢大學,2013年,第90—91頁。由於形式與内容較爲一致,我們只揀選幾條:
(肆·3982)
□□長沙李俗年廿 狀俗白衣居臨湘東鄉茗上丘帥鄭各主 (肆·3991)
(肆·4009)
[注]
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 《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四〕》,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718頁。
在這些名籍中,“白衣”是作爲“私學”的“狀”,也就是身份出現的。王素以爲,這裏的“白衣”“常指賤役,也代指無功名、無官職之人”。[注]王素、宋少華: 《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的新材料與舊問題——以邸閣、許迪案、私學身份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第23頁。王素等人對私學名籍“白衣”的理解,即受到了顔師古的影響。
然而,將“白衣”理解爲“給官府趨走賤人”,在漢代文獻中僅此一見。因此,沈欽韓、曾國藩等人并不同意此説。沈欽韓以爲:“白衣謂庶人道路之言耳,何必以官府給使爲白衣?”[注]沈欽韓: 《漢書疏證》卷三一,《續修四庫全書》第2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68頁;王先謙亦引述其説,見《漢書補注》卷七二,北京: 中華書局影印本,1983年,第1348頁。曾國藩亦以爲:“白衣猶言布衣,即齊民也”。[注]曾國藩: 《求闕齋讀書録》卷二《經下》,上海新文化書社,1936年,第42—43頁。都將“白衣”視爲庶民,而與官府趨走者、賤人無涉。實際上,儘管顧炎武引述了顔師古的觀點,但卻以“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注]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 《日知録集釋》卷二四《白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82頁。來理解這裏的“白衣”,仍舊强調“白衣”作爲庶人的身份符號屬性,“在官”只是指出“白衣”所任之職務而已。而這,與簡牘文書中的“白衣”稱謂是相符的。如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所出《王杖詔書令》第廿六條:
亭長二人,鄉嗇二人,白衣民三人,皆坐毆辱王杖功,棄市。[注]武威縣博物館: 《武威新出土王杖詔令册》,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 《漢簡研究文集》,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頁。
在這裏,“白衣民”與小吏亭長、鄉嗇相區别,正表明其庶民身份。除“白衣民”外,這種“白衣+身份”的表達形式,還見於走馬樓吴簡中:
縣三年白衣衛士限米二百斛已入畢。(捌·3788)[注]走馬樓簡牘整理組: 《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八〕》,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743頁。
這枚簡是關於“白衣衛士”繳納“限米”的記録。“白衣衛士”屬於“衛士”這一身份,但平時也積穀屯田,所以需要繳納“限米”。[注]參見于振波《走馬樓吴簡中的限米與屯田》,《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第1期,第32頁。而這種在“衛士”前加上“白衣”的情形,與宋武帝時期的“白衣左右”相近。據《南齊書·幸臣傳》載:“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注]《南齊書》卷五六《幸臣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2年,第976頁。唐長孺以爲,“左右”是隨從的一種名號,這裏的“白衣左右”“是由富室有姿容少年充當的,他們不是兵,不隸軍籍,也還没有授官,所以仍像普通百姓一樣穿白衣”。[注]唐長孺: 《讀史釋詞》,《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262頁。走馬樓吴簡中的“白衣衛士”,與這裏的“白衣左右”,都有隨從、衛士之義,且都着白衣,當是特意標明其庶民身份。而“白衣左右”還多次見於《魏書》《南史》《北史》中,可見這種没有正式軍籍、官職的侍從、衛士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頗爲普遍。[注]按,在《居延新簡》中,又有“白衣騎”的稱謂,E.P.F22: 530號簡文:“獲望見第一白衣騎以爲大卿獲衣幘使吏張業下亭言小病叩頭”,這裏的“白衣騎”或即是服白衣而得此名稱,與“白衣衛士”、“白衣左右”相類。不過,“白衣”也可能是白色的盔甲。在E.P.T59: 183這件“被兵簿”中,即有“白玄甲十三領”的記載,此“白衣騎”或即穿著此類盔甲,而并非指代身份。而在職位前加以“白衣”這一身份符號的現象,則更多地表現爲“白衣領職”。以“白衣領職”的官員,實際上已經被罷官,着以“白衣”,即是爲了强調庶人身份。[注]關於“白衣領職”,可參見劉偉航、高茂兵《兩晉南北朝“白衣領職”初探》,《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徐沖《兩晉南朝“白衣領職”補論》,《早期中國史研究》第二卷第一期,2010年。
從語言學角度來看,以“白衣”指代庶民的語詞現象,與同樣作爲庶民稱謂的“布衣”相同,屬於語言學中的“借代”現象,即“通過某一事物内部較突出和較清晰的一部分來指稱和理解該事物的全部”。[注]藍純: 《認知語言學與隱喻研究》,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80頁。在漢迄唐的服飾制度下,“布衣”“白衣”爲庶民之常服,因此便直接用“布衣”與“白衣”這一庶民的衣服特徵來指代其整體。
漢代的“服制”,可以從董仲舒的一段文字中得到大致的了解。《春秋繁露·服制》篇云:
散民不敢服雜采,百賈工商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謂之服制。[注]蘇輿: 《春秋繁露義證》卷七《服制》,第224—225頁。
這一“服制”,應當是實際推行過的。如“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一條,就有後世的詔書可以印證。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建武二十二年(46)九月戊辰,地震。爲應對這一災异,光武帝下詔,其中規定:“徒皆弛解鉗,衣絲絮。”李賢注曰:“舊法,在徒吏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注]《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第74頁。這裏的舊法在光武之前,亦即西漢律法,其中當有徒吏或刑餘戮民不得衣絲絮的規定,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的規定相一致。“散民不敢服雜采”的“服制”,也應當是西漢律法的當然條目。沈從文“漢代農民照法律規定,只能穿本色麻布衣,不許穿彩色”[注]沈從文: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157頁。的論斷,當即本此而來。
到了東漢,對商人的服色仍有極爲嚴格的限制。據《續漢書·輿服志》載:
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絳黄紅緑。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紅緑。賈人,緗縹而已。[注]《後漢書》志第三〇《輿服下》,第3677頁。
從公主、貴人、妃以下,直到二百石以上的有秩官吏,在嫁娶中可以服用的色彩從十二色到四色不等。而作爲庶民的商人,只可以服“緗、縹”之色。緗,據劉昭注引《博物志》:“交州南有蟲,長減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視之無色,在陰地多緗色,則赤黄之色也。”而據《釋名·釋采帛》:“緗,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王先謙《釋名疏證補》曰:“《急就篇》‘鬱金半見緗白’,顔注:‘緗,淺黄也。’”[注]王先謙: 《釋名疏證補》卷四,北京: 中華書局,2008年,第148頁。則“緗”當爲偏黄的色彩。至於“縹”,《説文解字》曰:“縹,帛白青色也。”[注]段玉裁: 《説文解字注》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649頁。二者或偏白,或偏黄,與麻布的黄、白二色比較接近。[注]馬怡曾對先秦至漢代出土的麻織品做過全面的統計,麻布的顔色亦在統計之列,其中多呈土黄、黄褐、白等色,説明黄、白可以看作漢代麻布的本色,參見馬怡《漢代的麻布及相關問題探討》,邢義田,劉增貴主編《古代庶民社會》,臺北中研院,2013年,第174—176頁。至於二百石以上可以服用的青、緑色,應當不在其中。另外,由於《輿服志》所載爲嫁娶之時,要求當較平日爲寛,故一般民衆肯定是禁止服用青、緑以上諸色的。謝承《後漢書》曾記載了袁忠拜謁王郎時,“見朗左右僮從皆着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注]李賢注引謝承《後漢書》,見《後漢書》卷四五《袁安傳》,第1526頁。可見童僕衣青絳色的彩衣,不符合當時的服飾制度。
或許正是考慮到這套服飾制度早已破壞的情況,加之“倉廩無儲,世俗滋侈”,三國時期的華核乃向吴主上疏,提出了一系列杜絶奢靡的措施,其中就有“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注]《三國志》卷六五《吴書·華核傳》,第1469頁。的建議。華核認爲,應該放開對百姓衣物顔色的限制,只需要禁止“華采”與“文繡”等對服飾的過度裝飾。不過,華核的意見并没有得到吴帝的認同。在官方層面上,庶民仍舊只能服用白色,這從著名的“白衣渡江”故事中可以得到印證。據《三國志·吴書·吕蒙傳》載:“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中;使白衣摇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注]《三國志》卷五四《吴書·吕蒙傳》,第1278頁。吕思勉以爲,這足以説明當時的平民是不能服彩色的。[注]吕思勉: 《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79頁。按,據石冬梅的理解,這裏的“白衣”雖爲“庶民”稱謂,但并不代表白衣爲商人所常服,并認爲秦漢三國時期并没有文獻能够證明商人須着白色衣服,參見石冬梅《吕蒙“白衣渡江”辨》,《保定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1期,第88頁。然而,無論從此處的文意理解,還是孫吴時期所保留的服制考慮,這裏的白衣還是應當理解爲商人之服,才更爲妥當。
至於隋唐,庶人仍衣白衣。尚秉和曾引沈藩《夢遊録》“顯宦三十年,忽然夢覺,仍着白衣”爲證。[注]尚秉和著,母庚才、劉瑞玲點校: 《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卷五《身服》,第65—66頁。吕思勉亦注意到,平民不能服彩的情況,還延續到了隋唐時期。如《隋書·禮儀志》:“隱居道素之士,被召入謁見者,黑介幘,白單衣,革帶,烏皮履。”“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异等,雜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緋緑,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注]《隋書》卷一二《禮儀七》,北京: 中華書局,1973年,第259、279頁。《文獻通考》載唐天成三年詔:“今後庶人工商,只着白衣。”[注]馬端臨: 《文獻通考》卷一一三《王禮八》,北京: 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1020頁。可見,直至唐代,“白衣”還是庶人工商的專用服色。而對於這種現象,吕思勉解釋道:“蓋染色初起,非人人所能爲,故爲侈靡之事,惟王公貴人用之,後遂沿以分别等級也。”[注]吕思勉: 《中國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66頁。可謂揭示了這一等級制度之實質。
三、 作爲“服妖”的“白衣”與“白衣爲天子”觀念的流行
作爲等級制度的“服制”往往是雙向的,除了規定庶民只能服用白衣、布衣外,還對君主的服飾有着嚴格的限定;若服用庶民之服飾,則不合禮法。如在《治安策》中,賈誼就對漢文帝“身自衣皂綈”有所批判。[注]《漢書》卷四八《賈誼傳》,第2242頁。皂綈即弋綈,本爲黑色厚繒所制的粗制衣物,不加彩色。“身衣弋綈”本是漢文帝的節儉之舉,[注]事見《漢書》卷四《文帝紀》,第135頁。曾受到後世之讚揚;但在時人賈誼眼中,卻是不符合禮制的行爲。文中子所謂“衣弋綈傷乎禮”,[注]參見王應麟《玉海》卷八二《車服》,南京/上海: 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本,1987年,第1517頁。即是此意。而當漢代君主身着本爲庶民所服之“白衣”時,則被視爲“服妖”,會受到更爲激切的批評。在《漢書·五行志》的“服妖”部分,就記載了漢成帝服“白衣”之事: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爲微行出遊,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壄,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宫;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宫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别,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典門户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注]《漢書》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第1368頁。
成帝喜好微服出巡,爲了與民間穿着無异,乃與私奴客皆着“白衣”,且以平民所常用的幘爲頭飾。對成帝的這一行爲,當時的權臣王音、劉向曾極力勸諫。谷永則依據《易經》“損”卦的爻辭“得臣無家”,認爲“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故不可以爲私家之事。然而成帝“白衣坦幘”,與小民混同、“亂服共坐”的行徑,卻是以王者之尊而爲“庶人之事”。當年虢公無道,以諸侯身份夢見得土田,已經是亡國之兆了;成帝衣庶民之“白衣”,畜私田財物等不合禮制、身份的行徑,無疑也會招致失國之禍。
對於這次“服妖”及谷永的解説,有一點頗值得注意。關於虢公時期有神降於莘一事,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但原文并無“賜爾土田”之語,左氏所批判的,是虢公“聽於神”的舉動。[注]《春秋左傳正義》卷十《莊公三十二年》,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北京: 中華書局影印本,2009年,第3870頁。關於這次“服妖”的解説,也可參見蘇德昌的論述,見《〈漢書·五行志〉研究》,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第191頁。因此,從“賜爾土田”所得出的“將以庶人受土田”的解釋,無疑是谷永根據漢代的實際情形而新增的。與“庶人受土田”相類似的表述,則有“從匹夫爲天子”“白衣爲天子”。
《漢書·眭孟傳》曾載昭帝元鳳三年“枯柳復生”“大石自立”事: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説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爲郎。[注]《漢書》卷七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3153—3154頁。
根據《春秋》,眭孟認爲大石自立、枯柳復生非人力所能爲,“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根據蟲食木葉所成的“公孫病已立”的讖言,當立者爲“故廢之家公孫氏”。因此建議漢帝求索賢人,禪讓帝位,以承天命。班固以“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爲天子作爲這一災异的“事應”,其中深意,不難體會。
在《漢書·五行志》中,眭孟的言論被班固概括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注]《漢書》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第1400頁。“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并以“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爲此災异之事應。[注]參見《漢書》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第1412頁。除眭孟之外,班固還引用了《京房易傳》中關於“石立”的一段論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异姓。立於水,聖人;立於澤,小人。”[注]《漢書》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第1400頁。在京氏這一易學流派中,“大石自立”對應的是“庶士爲天下雄”。由於大石自立於泰山,故所立爲同姓,與漢宣帝這一劉氏宗親從民間受命爲天子相合。類似的表述又見於《晉書·五行志》:
吴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裏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説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异姓。”干寶以爲“孫晧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注]《晉書》卷二八《五行中》,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853頁。此事又見《宋書》卷三一《五行二》,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925頁。此外,又有學者將“石自立”所預示的“庶人爲天子之祥”視爲石勒以“石”爲姓的依據,參見David B. Honey,“Lineage as Legitimation in the Rise of Liu Yüan and Shi L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0, No. 4 (Oct. - Dec., 1990), p.620.中文譯本名爲《劉淵、石勒興起中的血統與合法化問題》,見童嶺主編,孫英剛、王安泰、小尾孝夫副主編: 《皇帝·單于·士人: 中古中國與周邊世界》,上海: 中西書局,2014年,第317—318頁。
則“庶士爲天下雄”,在《晉書》所引京房《易傳》又作“庶士爲天子之祥”,與谷永依據《春秋》得出的“當有庶人爲天子者”的觀點相一致,可見當時不同的災异派别,對“大石自立”這一災异有類似的理解。到了沈約所撰《宋書·符瑞志》,眭孟的占辭變成了“將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已,從白衣爲天子者”。沈約據此寫道:“及昭帝崩,昌邑王又廢,光立宣帝,武帝曾孫,本名病已,在民間白衣三世,如孟言焉。”[注]《宋書》卷二七《符瑞志上》,第768—769頁。《漢書》中的“匹夫”“庶士”,被同義詞“白衣”所取代,“枯柳復生”“公孫病已立”也成了在民間白衣三世的宣帝“從白衣爲天子”的符瑞。
不過,由“白衣”而“天子”的表述,至少在東漢末期就已經正式形成了。在應劭《風俗通義·皇霸》篇中,就有“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注]應劭撰,王利器校注: 《風俗通義校注》卷一《皇霸》,北京: 中華書局,1981年,第15頁。的句子。而庶民階層(無論在表達上是用匹夫、庶士還是白衣)可以突破“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注]《史記》卷四一《越王勾踐世家》,第1752頁。的等級限制成爲“天子”這一觀念,則建立在“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於一尊”,[注]趙翼著,王樹民校證: 《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第36頁。從而出現了第一個布衣天子的歷史事實之上。從此,作爲庶民的匹夫、布衣、白衣,便可以覬覦天子這一名號。除劉邦、漢宣帝之外,光武帝也處於從“白衣”升爲“天子”這一語境之下。從光武帝與胡陽公主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一身份轉换過程。據《後漢書·酷吏列傳》載:“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注]《後漢書》卷七七《酷吏列傳》,第2490頁。可見光武帝雖爲劉漢宗氏,但在民間已久,光武帝、胡陽公主都認可其“白衣”身份,只是升爲天子之後,二者的界限才需要嚴格加以區分。
雖然漢高祖、宣帝、光武是由“白衣”升爲“天子”,但當其建立政權之後,“白衣”能够成爲“天子”的觀念就是當權者最爲恐懼的异質資源了。眭孟因“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的言論,被當時的秉政者霍光下廷尉,以“涉祅言惑衆,大逆不道”之罪被誅殺,[注]吕宗力將此事視爲“讖言式妖言案”,參見吕宗力《漢代的謡言》,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1—53頁。可見當權者恐懼之一斑。不過,與眭孟相類似的觀點卻層出不窮,體現着漢儒對於天下歸屬問題的開放性。如谷永曾言:“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注]《漢書》卷八五《谷永杜鄴傳》,第3466—3467頁。即是此類觀點的理論化表達。[注]關於“國非人君所私有”的集中論述,可參見吕思勉有關秦漢“政體”的論述,見吕思勉《秦漢史》,第555—556頁。正是這種關於皇權的開放性觀念,成爲了易姓受命的理論基礎;而與“白衣”有關的兩種災祥,也成爲了中古中國頻繁出現的受命之符。
四、“白衣人”闖宫與“白衣老父”:受命君主的“白衣”符命
由“白衣”升爲“天子”,依照應劭的認識,舜、禹二帝是因爲“砥行顯名”而達成的。而在布衣天子劉邦眼中,則是“馬上得天下”“提三尺劍取天下”,在於武力。不過,當漢高祖以武力獲得天下,并建立漢家秩序之後,也逐漸接受了天命之説。[注]關於這一轉變,可參見侯旭東《逐鹿或天命: 漢人眼中的秦亡漢興》,《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劉邦有“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注]《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391頁。的言論,可見承認自己得天下也是天命有自的。[注]如他提到的“三尺斬蛇劍”,便逐漸成爲了其開創帝業的象徵,(參見王子今《“斬蛇劍”象徵與劉邦建國史的個性》,《史學集刊》2008年第6期)而其斬蛇故事也被後世視爲漢朝興起的符命(參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與歷史》,《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94頁)。關於受之於天命的“帝王之祚”,班彪《王命論》有着系統的論述: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絫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説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注]《漢書》卷一〇〇《敍傳》,第4208—4209頁。
因此,高祖雖然興自布衣,但卻是“神器有命”,并不僅僅是在遭值暴亂之時通過武力“逐鹿”而得。從“白衣”到“天子”,無疑是古代社會能够産生的最具革命性的階層流動,其天命之獲得,必然需要一些能够表現天命所歸的直觀形式,即各種符命、祥瑞。這些符命、祥瑞的出現,既是易姓受命能否成功的重要輿論因素,也是新政權建立合法性的必要保障。在中古時期的君主受命之際,就有大量以“白衣”作爲象徵符號的符命出現,這既包括災异祥瑞系統中的“白衣人”闖宫事件,也包括受命君主在建立王朝過程中獲得的來自“白衣老父”的神示。
這些有關受命之君的“白衣”符命,基本上都能够在正史的《五行志》《符瑞志》,或者《大唐創業起居注》這些詳細記載災异符瑞的專門書籍、篇章中找到。這種分布規律不僅爲我們尋找資料提供了便利,也爲我們將這些神秘、怪异事件界定爲“符命”提供了依據。也就是説,無論是“白衣人”闖宫事件,還是“白衣老父”,其之所以被視爲符命,并不是依據我們的判斷,而是得到了中古時期歷史書寫者的普遍認可的。
(一) 災异祥瑞系統中的“白衣人”闖宫事件
最早的“白衣人”闖宫事件,出現於王莽代漢之際。始建國元年(9)秋,王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除此四十二篇《符命》外,《漢書·王莽傳》又記載了另外一些祥瑞、圖讖,其中就有如下事件:
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冠小冠,立於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注]《漢書》卷九九《王莽傳中》,第4113頁。
“白布單衣”人來到王路殿前,對侍郎王盱説的這番話,耐人尋味。所謂“同色”,顔師古以爲:“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顔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衆,而與莽也。其義兩通。”[注]《漢書》卷九九《王莽傳中》,第4115頁。無論取何種解釋,這位神秘的白衣人已經宣告將天下人民屬予王莽了。類似的事件,又出現於東漢靈帝時期。據《續漢書·五行志》載: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黄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襃絳衣入宫,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异,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黄天作亂,竟破壞。[注]《後漢書》志第十七《五行五》,第3346頁。
在這裏,不知名姓卻身着“白衣”的神秘人想要進入德陽門,并説出了“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的悖亂之辭。對於這一事件,蔡邕認爲與西漢成帝時期男子王襃絳衣入宫的事件相似,[注]關於王褒事件,參見《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第1475頁。但“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程度稍輕,儘管有人想仿效王莽篡奪漢家政權,但最終會以失敗告終。因此,司馬彪在撰寫《續漢書·五行志》時,便將張角作亂作爲事應。不過,這一事件很快就被袁山松、劉昭等人視作“曹氏篡漢”的徵兆。[注]關於此次“白衣人”闖宫事件,《續漢書·五行志》、《後漢書》、《風俗通義》、《後漢紀》、劉昭注等文本有較大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史家的態度與書寫方式,具體參見楊繼承《空間比附與歷史書寫——東漢洛陽的建築災异》,待刊稿。
相似的事件,又出現在隋唐之際,《隋書·五行志》所載的一件“裸蟲之孽”事件如下: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伏誅。[注]《隋書》卷二三《五行下》,第662頁。又見《隋書》卷三《煬帝上》,第74頁,文字略有不同。
在大業六年(610)正月朔旦這一特殊的日子,衣白色裙襦的盜賊闖入建國門爲亂,并聲稱是“彌勒佛出世”,爲齊王暕斬殺,這被視作楊玄感作亂的徵兆。楊玄感之亂後,隋煬帝去世,隋朝實際已經滅亡,最後被唐朝取代。而在唐代,又發生了兩次“白衣人”闖宫事件。在《册府元龜》的“徵應”部分,記載了武德八年(625)一次與“素衣冠”相關的符命:
武德八年,拜中書令。嘗夜於嘉猷門側,見一神人,長數丈,素衣冠,呼太宗進而言曰:“我當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忽因不見。[注]王欽若等編撰,周勛初等校訂: 《册府元龜》卷二一《帝王部》,南京: 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211頁。
衣“素衣冠”的神人對唐太宗説出了“我當令汝作天子”的讖言,這無疑是唐太宗成爲受命之君的符命。而在《舊唐書·天文志》中,也發生了一次與“白衣”相關的災异事件:
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静,乘白馬,着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床坐,勘問比有何災异。太史令姚玄辯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長五尺,漸小,向東行,出天市,至河鼓右旗,十七日滅。[注]《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第1320—1321頁。
唐高宗永隆二年(681),萬年縣女子劉凝静衣“白衣”,闖入太史局,“勘問比有何災异”。《天文志》所安排的對應事件,是當夜“彗星見西方天市”。“彗星”見於“天市”的占例,多見於五行、天文等志書。如《晉書·天文志》載:
其十二月,彗星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號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坐在其中。”明年,趙王倫篡位,改元,尋爲大兵所滅。[注]《晉書》卷一三《天文志下》,第392頁。
又如《宋書·符瑞志》載:“義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掃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興,此除舊布新之徵。”[注]《宋書》卷一七《符瑞上》,第785頁。可見,由於“帝坐”在“天市”之中,故“彗星”出“天市”往往是政權更替的預示。而永隆二年的劉凝静事件,在《新唐書·五行志》中有着更爲明確的指向。《新唐書》的作者認爲:“太史司天文、曆候,王者所以奉若天道、恭授民時者,非女子所當問。”[注]《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第951頁。“女子”勘問天文、曆候,代表女子干涉王者之道,無疑象徵着女主臨朝,這自然是指武則天稱帝一事。所以,從武則天的立場來看,這次劉凝静衣“白衣”闖宫之事,即是武則天受命稱帝的符命。
在簡單地敍述完這些“白衣人”闖宫事件之後,我們把這些事件的基本要素提取出來,製成表1,會對這一書寫模式有更爲直觀的理解:

表1 中古“白衣人”闖宫事件一覽表
通過表1不難發現,這些和“白衣”有關的闖宫事件有着極大的相似性,并大體表現爲這樣一種書寫模式: 着“白衣”者闖入某一宫殿,并説出一段讖言,最後以某種神秘的方式失蹤不見,或者不幸被捕被殺。具體而言,又表現爲兩種不同的形式。第一類是着“白衣”者宣告自己將成爲受命者,這包括如光和元年、大業六年、永隆二年的闖宫事件。光和元年,白衣人明確表示爲欲登德陽殿而爲天子;大業六年,是着白練裙襦者自稱爲彌勒佛之轉世;永隆二年,則是着白衣的女子劉凝静勘問關涉天命歸屬的災异。不過,這些以白衣人爲受命主體的闖宫事件,都以失敗告終。白衣人自身雖没有完成易姓受命,但卻以秩序破壞者的角色,加速了新舊政權的更替。第二類則是作爲神人身份的“白衣人”説出讖言,宣告某人當爲天子,這包括始建國元年、武德八年的兩次事件。始建國元年穿白布單衣的人宣告將天下百姓屬予王莽,武德八年穿素衣冠的神人則告訴唐太宗,命其爲天子。在這裏,王莽、唐太宗是符命的承受者。與“白衣人”自己宣告受命不同的是,王莽、唐太宗都順利地登上帝位,承接了上天給予的天命。
通過對兩種不同類型的“白衣人”闖宫事件的分析,可以發現,白衣人既可以是秩序的動摇者,也可以是宣告天命歸屬的神人。作爲秩序動摇者的白衣人事件,被傳統史家編入《五行志》,因而被視爲“人屙”“裸蟲之孽”等災异。游自勇曾對唐代長安的闖宫事件有過專門的研究,并將這種事件視爲“下人逾上之妖”,象徵着唐政權秩序的動摇。[注]游自勇: 《唐代長安的非常事件——以兩〈唐書·五行志〉所見訛言、闖宫爲中心》,《唐研究》第十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30—241頁。而宣告天命歸屬,具有神人屬性的白衣人事件,則被收录在了帝王的本紀[注]按,《王莽傳》實際具有帝王本紀的性質。或類書的“徵應”之部,成爲傳統史家所認可的符命。不過,依照《宋書·符瑞志》“將來之休徵,當今之怪异”[注]《宋書》卷一七《符瑞上》,第781頁。的理論,這些發生在前朝的災异,正可以視作受命者的符命。從《五行志》作者所安排的事應中,即可以發現他們都是作爲政權交替、易姓受命的預兆而出現的。
(二) “白衣老父”: 源自“霍山神”信仰的“白衣”符命
除了“白衣人”闖宫這一形式外,中古的“白衣”符命又表現爲“白衣老父”。在這種形式下,“白衣老父”實際參與了君主創業歷程,并爲處於困境中的受命者指示了通往成功的路徑。這一“白衣”符命的初期形態,在《後漢書·光武帝紀》中有所表述。建武二年(26),王郎起兵,河北之地紛紛響應,光武帝只得南走信都:
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注]《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上》,第12頁。
光武率軍至滹沱河,得天之助,僥幸渡過結冰的滹沱河,進入了博城西,卻又迷失了方向。此時,有一“白衣老父”立於道旁,爲光武指明了信都的方向、里程,使光武得投信都太守任光。在《宋書·符瑞志》中,此事被正式看作光武帝的受命之符,“白衣老父”則作“白衣老公”,其文曰:
及在河北,爲王郎所逼,將南濟滹沱河。導吏還云:“河水流澌,無船可渡。”左右皆恐懼。帝更遣王霸視之。霸往視,如吏言。霸慮還以實對,驚動衆心,乃謬云:“冰堅可渡。”帝馳進。比至,而河冰皆合,其堅可乘。既渡,餘數乘車未畢而冰陷。前至下博城西,疑所之。有一白衣老公在道旁,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耳。”言畢,失所在。遂至信都,投太守任光。[注]《宋書》卷二七《符瑞上》,第770頁。
在《宋書·符瑞志》中,這一行軍過程更具神秘性。如在《後漢書》中,是剛好遇上滹沱河結冰,而《符瑞志》的敍述中,滹沱河本有流水,但光武帝至時,卻有堅冰可渡。此外,“白衣老公”爲光武帝指路之後,很快便神秘失蹤。杜篤在其所作《論都》一文中有“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的言辭,李賢注曰:“靈祇謂呼池冰及白衣老父等也。”[注]《後漢書》卷七〇上《文苑列傳上》,第2606頁。而在《光武帝紀》的相關部分,李賢也注道:“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因此,無論是將“白衣老父”理解爲神人,還是像《册府元龜》中所記載的武德八年衣“素衣冠”者直接寫作“神人”,都是將“白衣人”的神秘出現視爲符命的,這應當是中古時期的普遍認識。
在唐高祖李淵的創業歷程中,類似於光武帝遇“白衣老父”的符命,又再次出現。據《舊唐書·高祖紀》:
(大業十三年)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爲鎮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饋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注]《舊唐書》卷一《高祖紀》,第3頁。
當時,唐高祖李淵屯兵賈胡堡,而隋將宋老生屯兵霍邑,與高祖相拒。加之陰雨綿綿,補給不濟,一度使唐高祖起了退兵的念頭。此時,來了一位自稱爲霍山神使者的“白衣老父”,告訴他八月的時候雨會停,并爲唐軍指明了出兵路綫。到八月,果然雨停,高祖遂按照這位“白衣老父”的指示出霍邑,斬殺宋老生,得以順利進軍。
在温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中,“白衣老父”則作“白衣野老”,其情節較之《舊唐書》更爲詳細生動:
甲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山遣來,詣帝請謁。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此老乃伺帝行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得見?卿非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祠,山中聞語:‘遣語大唐皇帝云: 若往霍邑,宜東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當爲帝破之,可爲吾立祠廣也。’帝試遣案行,傍山向霍邑,道路雖峻,兵枉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去縣十里城上人即遥見兵來。”帝曰:“行逢滯雨,人多疲濕,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難爲之朽。山神示吾此路,可調指踨。兩霽有徵,吾從神也。然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顧左右笑以爲樂。[注]温大雅撰,李季平、李錫厚點校: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頁。
由於這裏的“白衣野老”是受霍太山所派遣,因此宫川尚志根據杜光庭的《歷代崇道記》所載“霍山神”,認爲這裏的“白衣野老”與道教有着密切的關係。不過,氣賀澤保規注意到,《歷代崇道記》所載的“霍山神”,并未與“白衣老父”或“白衣野老”記載在一起,因此認爲,“霍太山神(白衣野老)事件與其説是道教影響李淵的結果,不如説是唐方面出於自身的需要而安排的。其背後有宗教的、歷史悠久的山嶽信仰。”[注]參見氣賀澤保規: 《〈大唐創業起居注〉的性格特點》,劉俊文主編: 《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23—224頁。氣賀澤保規對“霍山神”有着“歷史悠久的山嶽信仰”的判斷,確實可以從更早的文獻中找到依據。《史記·趙世家》曾載,趙襄子四年(前454)出奔晉陽:
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恤,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别,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注]《史記》卷四三《趙世家》,第1794—1795頁。
原過在王澤遇見的三人,頗爲神秘: 腰帶以上的部分可見,腰帶以下則不可見。而從三人交給趙襄子(字無恤)的竹書可知,三神爲霍泰山之使者,預言趙襄子滅知氏、得林胡之地,以及趙國後世的領土擴張。《論衡·訂妖》篇亦録此事,曰:“是蓋趙襄子且勝之祥也”。[注]黄暉: 《論衡校釋》卷二二《訂妖》,北京: 中華書局,1990年,第920頁。應劭《風俗通義·皇霸》篇亦載有此事,并載録了趙襄子滅知氏後,“趙北有代,南并知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注]應劭撰,王利器校注: 《風俗通義校注》卷一,北京: 中華書局,1981年,第36頁。等應驗之辭。由此可見,此事被漢人視爲趙襄子之符命。《舊唐書》所謂“此神不欺趙無恤”,《大唐創業起居注》所謂“然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可知唐高祖李淵熟知這一典故,因有所本,所以自然視爲天意,故而有“顧左右笑以爲樂”的得意之態。
不過,從《史記》到《舊唐書》《大唐創業起居注》,這一符命還是發生了一些改變。就霍山神的使者而言,《史記》所載爲“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的三位神人,而後者則是“白衣老父”。前者顯示其神聖性的,是其帶以下不可見的超現實形象,故而當李淵見到白衣老父時,會有“神本不測,卿何得見”的疑問;而後者的神性則是通過“白衣”這一具有革命性的服飾特徵來顯示的,這無疑是承襲自光武帝所遇“白衣老父”,并且與作爲异質資源、帶有符命意味的“白衣”密切相關的,而不再只是單純的山嶽信仰。
五、 星占文獻中的“白衣”占辭及其“革命性”
從早期數術文獻到唐五代時期的星占文獻,我們可以看到“白衣受地名城”“白衣之聚”“白衣會”“白衣自立”等有關“白衣”的占辭。在這些不同形式的占辭中,“白衣”是作爲身份符號出現的,都表示庶民;而占辭本身則是一種普遍的具有“革命性”的預言。不過,與受命之君的“白衣”符命不一樣的是,這種預言并没有與特定的君主或政權建立聯繫。也就是説,星占文獻中的“白衣”占辭,只是爲受命之君提供了一種可供迎合、解釋的資源,任何個人或群體,都可以據爲己用。
(一) 馬王堆帛書《刑德》篇中的“白衣受地名城”
馬王堆帛書《刑德甲篇》的“日月占”部分載有這樣的占辭:
月交軍(暈),一黄一赤,其國白衣受地,名城【也】。[注]裘錫圭主編: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北京: 中華書局,2014年,第2頁。按,該占辭又見於《刑德乙篇》,但“其”作“亓”,見第44頁。
劉樂賢認爲,“月交暈,一黄一赤”指的是“月亮周圍有兩種不同的暈氣相交”,“白衣”則指“布衣,平民”,“名城”爲“大城”。[注]劉樂賢: 《馬王堆天文書考釋》,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68頁。將“白衣”理解爲布衣的觀點,又見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43頁。在《刑德甲篇》的“風雨雲氣占”部分,又有“雨而不雷,以白衣城。雨而雷,以甲者城”的占辭,[注]裘錫圭主編: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第9頁。按,《刑德乙篇》亦同,唯“城”字漏抄,以小字補抄在後文“冬”之上,見第45頁。也有“白衣”一詞。對於“以甲者城”的“甲者”,陳松長認爲“當指穿甲之人,即握有兵權的武士”,[注]陳松長: 《帛書刑德甲篇箋注(雲氣占部分)》,《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2期,長沙: 嶽麓書社,2005年,第75頁。由此更可以確定,這裏的“白衣”應當是與“甲者”相對應的一種身份,我們將其理解爲庶民,應該是不誤的。
關於“其國白衣受地,名城【也】”,陳松長的斷句與劉樂賢、《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稍有不同,他將“白衣受地名城”連讀,以爲“白衣”“猶後世所稱布衣、古未士者之稱”,“‘白衣受地名城’,猶言布衣百姓占地封侯,這對統治者來説,自非吉兆。”[注]陳松長: 《帛書刑德甲篇箋注(雲氣占部分)》,第67頁。“白衣受地名城”,與前文提到的谷永“以庶人受土田”的表述相類似,故而陳松長的理解應該是接近事實的,我們可以將之視爲一種“失國之祥”。據程少軒的研究,“馬王堆的這一系列兵占書,最初就是爲秦末亂世特製的”。[注]程少軒: 《馬王堆兵占書與軑侯利蒼》,《中華讀書報》2014年11月19日,第010版。秦末頗有戰國遺風,出現這種占辭,恰好適應群雄逐鹿的政治局面。
(二)平民聚衆:“白衣之聚”與“白衣會”
除“白衣受地名城”外,馬王堆帛書《五星占》中,又有所謂“白衣之聚”的占辭:
這裏的“白衣”,劉樂賢同樣理解爲平民,并且認爲:“‘白衣之遇’,古書或作‘白衣會’,指平民相聚,亦即‘聚衆’”。[注]劉樂賢: 《馬王堆天文書考釋》,第78頁。與馬王堆“白衣之聚”相類似的,則有周家臺秦簡《日書》中的“白衣之冣”:
甲子,其下有白衣之冣,黔首疢疾。丙子,其下有旱。戊子,其下有大敗。庚子,其下有興。壬子,其下有水。(二九八三)[注]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 《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 中華書局,2001年,第125頁。
“白衣之冣”的“冣”,整理小組引《説文》云:“冣,積也”,段玉裁注曰:“冣與聚音義皆同”。因此,“白衣之冣”即可以理解爲“白衣之聚”。而這裏的“白衣之冣”,陳偉結合傳世文獻中的“白衣會”,理解爲“帝王或其配偶的喪事”。[注]陳偉: 《讀沙市周家臺秦簡札記》,《燕説集》,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24頁。而將“白衣會”理解爲喪事,則是一種較爲傳統的解釋。如《後漢書·皇后紀》載:
董卓令帝出奉常亭舉哀,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也。合葬文昭陵。
李賢注曰:“有凶事素服而朝,謂之白衣會。”[注]《後漢書》卷一〇下《皇后紀下》,第450頁。即是最早將“白衣會”理解爲“凶事”的。而對於普遍出現於漢唐《天文志》等星占文獻中的“白衣會”“白衣之會”,傳統的注家也多理解爲喪事。如《史記·天官書》:“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注]《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第1305頁。王元啓認爲:“按《星經》,昴爲天之耳目,主獄事,又主喪,又主口舌奏對。按,主喪,故又爲白衣會。”[注]王元啓: 《史記三書正譌》卷三《天官書》,《二十五史補編》,北京: 中華書局影印本,1955年,第79頁。《史記疏證》以爲:“考要曰,昴爲天之耳目,主兵,故曰髦頭,主胡,故有胡兵,占主喪,故爲白衣”。[注]佚名: 《史記疏證》卷二一,清鈔本。按,關於佚名《史記疏證》的作者,董恩林考證爲杭世俊,參見董恩林《佚名〈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作者考——兼論杭世俊〈史記考證〉的性質》,《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著名漢學家沙畹也認爲,昴星團主管喪事。[注]沙畹這一觀點出自其《司馬遷〈史記〉譯注》一書,此據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0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p.274.又如《史記·天官書》:“木星與土合,爲内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注]《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第1320頁。王元啓以爲:“若猶及也,謂有喪及水。”[注]王元啓: 《史記三書正譌》卷三《天官書》,第89頁。瀧川資言認爲:“白衣會,又見咸池,言喪也。陳仁錫曰:‘若,及也。言木與火合,則爲旱;木與金合,則爲國家喪及水澇也。’”[注]瀧川資言: 《史記會注考證》卷二七《天官書》,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1843—1844頁。而據趙貞對漢唐《天文志》中“白衣會”的統計,“‘白衣會’的預言還見於‘日中見烏’、‘太白入氐’、‘太白犯填’、‘土與金合’、‘太白入房’等特定天象中,且多與‘内兵’、‘兵起’、‘政亂’、‘饑旱’、‘國亡地’和‘國易政’等相聯繫。”并認爲:“白衣會”“被附會爲帝王後宫駕崩後官員的舉哀活動,因而成爲國喪的重要象徵。”[注]趙貞: 《漢唐天文志中的“白衣會”小考》,第119、120頁。此外,陳槃將“月犯昴”相關的“白衣會”也理解爲喪事,參見陳槃《故讖緯研討及其書録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6頁。
傳統的觀點之所以將“白衣會”與喪事建立關係,主要根據的是長期以來“白衣”作爲喪服的文化背景,以及“白衣會”經常與帝王喪事同時出現於各種占辭中。然而,對於白衣爲喪服之説,清人杭世駿早有辯駁,認爲“白衣非必喪服”;[注]杭世駿撰,陳抗點校: 《訂訛類編》卷六《白衣非必喪服》,《訂訛類編·續補》,北京: 中華書局,1997年,第190頁。周壽昌也認爲,古人雖有忌諱白色者,但不忌諱之處亦多有之。[注]周寿昌撰,許逸民點校: 《思益堂日札》卷四《尚白》,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第78頁。因此,無論是以“白衣爲喪服”否定平民以白衣爲常服,還是不加區分地將凡是出現“白衣”的地方視爲喪事,都是過於絶對的做法。而在星占文獻中,雖然“白衣會”經常與喪事的占辭同時出現,但同時出現并不代表二者是直接相關的。我們看《續漢書·天文志》劉昭注的一段文字:
《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揚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衣之會。”[注]《後漢書》志第十一《天文中》,第3247頁。
在星占文獻中,“一曰”是表述兩種不同的占測觀點時常用的辭例。從劉昭注來看,對於“太白晝見”這一天象,《韓揚占》有兩種占辭,一爲“天下有喪”,一爲“白衣之會”,可見“白衣之會”與“天下有喪”表述的并不是同一種現象,故當與喪事無關。因此,對於“白衣會”,我們應當嘗試尋求另外的解釋。
由於數術文獻的特殊性質,在具體研究中,需要我們“注意搜求後世相關記載與出土文獻對讀”,[注]劉樂賢: 《簡帛數術文獻探論(增訂版)》,前言,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頁。藉以利用更爲清晰、系統的表述來解決早期數術研究中的某些疑難問題。而劉建民從《開元占經》中發現的一些占辭,可與早期星占文獻中的“白衣會”對讀,爲我們理解“白衣會”提供了另一種可能。《開元占經》卷八十四“客星占八”之“客星犯鼈星”曰:
《黄帝占》曰: 客星守鼈星,有白衣之會。石氏曰: 有星入鼈星,有水令。《海中占》曰: 客星出守鼈星,有白衣之衆聚,若天下有水,水物不成,期百八十日,遠一年。[注]瞿曇悉達: 《唐開元占經》卷八四《客星占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7册,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83頁。
又卷八十“客星占四”之“客星犯昴”曰:
《荆州占》曰:“客星犯守昴,讒諛賊臣在内,諸侯謀上;一曰: 有白衣徒聚謀慮。”[注]瞿曇悉達: 《唐開元占經》卷八〇《客星占四》,第754頁。
劉建民認爲:“比較上面的引文可知,‘白衣之會’即‘白衣之衆聚’,也就是‘白衣徒聚謀慮’的意思。”[注]裘錫圭主編: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第236頁。這一判斷應當是没有問題的。因爲《黄帝占》中的“客星守鼈星,有白衣之會”與《海中占》的“客星出守鼈星,有白衣之衆聚”,“石氏曰”中的“有星入鼈星,有水令”與《海中占》中的“若天下有水”,這兩處星占内容可以看作同義表達。而《海中占》的内容,則較《黄帝占》、石氏更爲具體、明白,也更容易讓人理解。此外,《史記·天官書》中的“金爲白衣會若水”,似乎也應該是《海中占》“有白衣之衆聚,若天下有水”的簡單表達。由此可以推斷,“白衣之會”即“白衣之衆聚”。而根據《玉篇》,“徒”即“衆也”,則“白衣徒”即是“白衣之衆”。此外,《開元占經》中還有多處相似的内容,如卷三一《熒惑占》中的“熒惑犯亢”:“赦東官候曰:‘熒惑守亢,國糴貴;芒角犯淩,有白衣之衆暴聚,麻麥載倍價。’”[注]瞿曇悉達: 《唐開元占經》卷三一《熒惑占三》,第409頁。又如卷四七《太白占》之“太白犯心”:“《海中占》曰: 太白入心,有白衣之衆,又爲。”[注]瞿曇悉達: 《唐開元占經》卷四七《太白占三》,第532頁。
這些“會聚”的“白衣”、“白衣之衆”,當表示一種身份,即指代庶民。而根據《荆州占》“諸侯謀上”這一占辭,“白衣徒聚謀慮”所表達的,應當是有别於諸侯謀上的平民聚衆叛逆。實際上,關於“聚衆”,睡虎地《日書》甲種《除》篇就有涉及。若在“害日”這天祭祀,將導致“最衆必亂者”。整理小組以爲:“最衆,即聚衆。”王子今以爲,“最”當作“冣”,表示“聚”。[注]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1—182頁;王子今: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頁。儘管睡虎地《日書》此處并未提及“聚衆”的主體,但“聚衆必亂”應當是一種很早的觀念,所以“白衣之衆”的“會聚”才會與“謀慮”發生關係。
由此,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馬王堆《刑德》、周家臺《日書》中的“白衣之聚”“白衣之冣”,正好説明在早期數術文獻中,“白衣會”很早就以“白衣聚”這一形式表現。而“白衣聚衆謀逆”這一占辭,則多少與前文提及的“白衣人”欲爲天子,或者是馬王堆《刑德》中的“白衣受地名城”有着一定的聯繫,他們都代表了處於下層的平民階層對於現有身份、秩序突破的一種努力,而這無疑是對舊有秩序的動摇,因而有着某種“革命”意味。
(三) 《開元占經》與《西秦五州占》中的“白衣自立”
在《開元占經》《西秦五州占中》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關於“白衣自立”“白衣爲王”“白衣自立爲王”的占辭,這種占辭無疑比“白衣聚衆謀逆”更進一步,象徵着“白衣”可以稱作王者,并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在《開元占經》中,“白衣爲王”“白衣自立”集中分布在“客星犯二十八宿”部分,涉及奎、婁、東井、張、軫五宿。其具體占辭爲:
客星犯奎:
甘氏曰: 客星入奎,强國奪地,變争兵起,白衣自立,擾中國。
巫咸曰: 客星出奎,邊兵大起,白衣立爲王。
《玄冥占》曰: 客星守奎,强國争起兵,有白衣自立動國。
客星犯婁:
郗萌曰: 客星守犯婁,天下欲分社稷者,白衣自立者,牛馬貴。一曰: 有白衣之聚。[注]瞿曇悉達: 《唐開元占經》卷八〇《客星占四》,第751、752頁。
客星犯東井:
黄帝曰: 客星出東井,宫中火起,大人爲亂,兵大起,將軍有憂,若白衣有自立者,其國必破,期三年。
甘氏曰: 客星守東井,有白衣自立者,其國破,不出年中。
巫咸曰: 客星出東井而守之,宫中火起,大人爲亂,王者以舟船爲急,河海溢,土功并起,人無食,白衣有自立者,其國破,期三年。
客星犯張:
《春秋圖》曰: 客星出張,白衣同姓有自立者,天下更令,有徙人,若使人於諸侯。
甘氏曰: 客星出張,若守之,白衣同姓自立者。
客星犯軫:
《文耀鈎》曰: 客星出軫,若有白衣自立者,大國多害,若有喪,兵革起,天下有逃主,近期不出一年,遠三年。[注]瞿曇悉達: 《唐開元占經》卷八一《客星占五》,第757、758、760、761—762頁。按,除《開元占經》外,李淳風《觀象玩占》也有類似的占辭,如卷一七引《天文録》與《開元占經》引《黄帝占》中的“客星出井”相似,卷一九有與《開元占經》所引《春秋圖》類似的記載,只是文字略有差异。此外,《乙巳占》中也有一些“白衣自立”的占辭,涉及客星犯婁、張、軫等宿。
這些出現“白衣自立”“白衣自立爲王”的客星占,都有一些相同的特徵,即都是伴隨着國家大亂、兵大起的背景,然後“白衣”作爲逐鹿者,也就是上引郗萌占中所謂“欲分社稷者”的姿態出現,自立爲王。由此可見,“白衣自立”的占辭,應當適用國家大亂和政權交替之際。而“白衣”作爲身份,也不同於占辭中出現的將軍、大人、諸侯,而當屬庶民無疑。實際上,在讖緯文獻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庶人王”這樣的文字。據《北齊書·方伎傳》所載宋景業之事云:
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注]《北齊書》卷四九《方伎傳》,第675頁。又見《北史》卷八九《藝術傳上》,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2934頁。按,又有“聖人”作“吴人”者,參見安香居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1頁。
宋景業“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曆數”,這裏即根據緯書《易稽覽圖》“鼎”卦中“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的辭例,預言出自渤海的高氏將得到天下。由此,“東北水中,庶人王”成爲北齊高氏代魏的符命。而這裏的“庶人王”,與《開元占經》所引的“白衣自立爲王”,在語意上是一致的。此外,同樣是易類文獻,前文所引《京氏易傳》中有:“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异姓。立於水,聖人;立於澤,小人。”其中“立於山,同姓”即代表“立於山,同姓庶士爲天下雄”,與《開元占經》所引《春秋圖》中“客星出張,白衣同姓有自立者”也是相同的表達,只是《春秋圖》的依據是星象,而《京房易傳》依據的是“石自立”這一災异。而從《開元占經》占辭的來源來看,分别出自甘氏、巫咸、郗萌、黄帝、《春秋圖》《文耀鈎》《玄冥占》,而《春秋圖》《文耀鈎》正是讖緯文獻。由此可見,無論甘氏、巫咸等專門的星占流派,還是在讖緯書中,“白衣自立爲王”“庶人王”的占辭已經有了較爲廣泛的分布,并且已經被方術之士用作符命。
而這種占辭與符命之傳播,又可以在晚唐五代的敦煌文獻中找到。在一部被稱爲《西秦五州占》的星占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白衣爲王”“白衣自立”的占辭。《西秦五州占》,鄧文寛題爲《玄象西秦五州占》,[注]鄧文寛: 《鄧文寛敦煌天文曆法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頁。趙貞則題爲《西秦五州占》,包括P.3288、P.2632、P.2941、P.3555、S.2729v、S.5614和Дх1366v等7件性質相近的文書。該書涉及武威、張掖、酒泉、晉昌、敦煌等五郡,故名爲“五州占”。據趙貞的研究,此書當流傳於中唐以後的河西地區。而據王晶波的判斷,該文獻“唐代安史之亂後到敦煌陷落之際,在吐蕃統治時期及歸義軍時期均有抄寫流傳”。[注]王晶波: 《敦煌占卜文獻與社會生活》,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87頁。從殘卷可知,該書至少包括了五星占、日暝占、日鬥占、日食占、色氣占、月光不明占以及五星符等九項星占内容。[注]參見趙貞《敦煌遺書中的星占著作: 〈西秦五州占〉》,第55—67頁。在P.2632、P.3288兩件文書所録的“占日鬥十二月十二日同占法”中,即出現了多次“白衣爲主”的占辭:
辰日鬥者,敦煌白衣自立爲主,千人亂,煞將亡土,不出其年春季月。
未日鬥者,酒泉崔氏欲立爲主,白衣爲主,城人相煞,及者二百人,不出其年春季月上旬。
申日鬥者,注,晉昌張氏、吕氏,白衣爲主,城人相煞,不出秋八月上旬,及者五百人死。
戊日鬥者,注,敦煌自立白衣人爲主,不歸帝位五年,死者萬人,不出其年夏季月。[注]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頁;《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頁。按,P.2632、P.3288文字基本相同,但P.2632較爲完整。P.2632篇題爲“占日鬥十二月十二日同占法”,P.3288則作“占月鬥法”,“月”當爲“日”字之誤。本處録文,則兼顧二者。録文有參考王重民之處,見《金山國墜事零拾》,第11—12頁。
從上引“占日鬥法”來看,這一星占術以十二辰發生的“日鬥”作爲占測依據,是一種極爲簡便、實用的星占方法。而根據占辭,在辰、未、申、戊四日發生日鬥時,便會在敦煌、酒泉、晉昌等郡出現“白衣爲主”的現象。對於這裏的“白衣”,法國漢學家茅甘(Carole Morgan)解釋爲“平民”(the Common Peple)。[注]這是茅甘考察了P.2632、P.2941等5件占卜文書之後的結論,見其所著《西北邊疆的動蕩》一文,本文則根據余欣之介紹,參見余欣《法國敦煌學的新進展——〈遠東亞洲叢刊〉“敦煌學專號新研”專號評介》,《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1期,第109—110頁。而這裏的“主”字,有的地方寫作“王”。在《西秦五州占》中,有一些占辭即寫作“白衣自立爲王”。如P.2632的“西秦日食占”部分,午日日食部分即有“白衣自立爲王”的占辭。在P.2632“日暈占”部分,有“旬正月,白虹關日,注: 酒泉白衣人自立其君”的占辭,也有八月日暈而導致“八月關,注: 武威、張掖二州,其君萬人,聚白衣,自立爲候王”的占辭。[注]圖版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册,第8頁。由此可見,這裏的“主”,應當就是“君主”的意思,或稱作“王”。[注]按,“王”字在漢魏六朝碑刻中也有寫作“主”字的情形,因此這裏的“主”字也有可能就是“王”字,具體參見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异體字典》,北京: 中華書局,2014年,第908頁。如此,我們便可以判定,無論是“日暈占”部分的“聚白衣,自立爲候王”,還是“日鬥占”部分的“敦煌白衣自立爲主”,都應當與《開元占經》中的“白衣徒聚謀慮”一樣,是作爲平民的白衣相聚謀反,稱作“候王”的意思。趙貞曾推斷:“《西秦五州占》中‘白衣’的出現,似乎更多地强調了改朝换代和除舊布新的‘革命’意義。”[注]趙貞: 《敦煌遺書中的星占著作: 〈西秦五州占〉》,第64頁。而從張守節對於《史記·天官書》“奎”宿的一段注釋中,我們似乎也能够感受到“白衣”的革命意味。張守節提到,當奎宿“開闔無常”時,“當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注]《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第1305頁。由此可見,與“白衣”相關的革命意味,無論是我們在討論受命君主的“白衣”符命時,還是在星占文獻中諸如“天下更令”“天下欲分社稷者”“白衣稱命”等占辭中,都能够得到切實的感受與直觀的了解。
此外,“占日鬥法”中“戊日鬥”提到的“不歸帝位”,又見於P.3288“占日食法”中:“子日食,秦四州自立白衣爲主,不歸帝吉,歸其位,即令萬人死,牛馬貴,粟帛,相煞。”[注]圖版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3册,第67頁。從“不歸帝位”“不歸帝吉”可以看出,《西秦五州占》中的“主”“王”,實際便是擁有帝位的天子,只不過這個“帝”的統治範圍只限於西秦五州而已。這種解釋不僅能够從《西秦五州占》的文本中得到證明,也能够從“占日鬥法”更早的淵源中獲得。
在《開元占經》卷六《日占》部分的“日以十二辰鬥”中,我們可以見到記載於《孝經雌雄圖》《魏氏圖》的兩種“占日鬥法”,以子、丑二日的占辭爲例:
《孝經雌雄圖》曰: 子日日鬥者,李氏欲爲天子。《魏氏圖》曰: 子日日鬥者,李氏、竇氏欲爲天子。《孝經雌雄圖》曰: 丑日日鬥者,趙氏欲爲天子。《魏氏圖》曰: 丑日日鬥者,趙氏欲爲天子。[注]瞿曇悉達: 《開元占經》卷六《日占二》,第226頁。
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占日鬥法,與《西秦五州占》的占日鬥法的占測原理都是十二辰。在占測結果上,《孝經雌雄圖》《魏氏圖》都是預言某一姓氏欲爲天子,這些姓氏包括李、趙、竇等等。而在《西秦五州占》中,則提到了酒泉崔氏、晉昌張氏、吕氏等姓氏將爲“主”;在其餘八辰中,也提到了趙、吕、劉、王等姓氏爲“主”。因此,我們可以將《孝經雌雄圖》《魏氏圖》以及《西秦五州占》看作是三種不同的“日以十二辰鬥”法,其十二辰日鬥與某氏爲天子、爲主的搭配,則如下表:

表2 十二辰占日鬥法
由此可見,《西秦五州占》“日鬥占”有關“白衣自立”的部分應當是借鑒了《開元占經》所引讖緯、星占文獻中的“白衣”占辭,而某氏爲王、爲主的占辭,則明顯來源於《孝經雌雄圖》、《魏氏圖》二書中的“十二辰占日鬥”法。不過,由於《西秦五州占》局限於“西秦五州”這一較爲封閉、獨立的區域,其占法以河西地區爲立足點,因此“天下”演變爲了“西秦五州”,而“天子”也轉變爲了“主”“王”。
而對於《西秦五州占》所提及的李、宋、劉等氏,王重民注意到:“蓋此數氏者,并是五涼鼎足,其勢力足以左右社會;而白衣在諸鼎足中,其聲勢尤大”。[注]王重民: 《金山國墜事零拾》,第13頁。陳餘柱也注意到,“文中自立爲王者,多爲河西漢族大姓”,[注]陳餘柱: 《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敦煌禄命書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64頁。這也是《西秦五州占》較之於《孝經雌雄圖》《魏氏圖》的特點。然而,王重民“白衣在諸鼎足中,其聲勢尤大”的説法,卻頗有問題。實際上,“白衣”只是一種身份象徵,某姓某族亦可以冠以“白衣”這一身份。如“日鬥占”部分就提到,“酒泉崔氏欲立爲主,白衣爲主”、“晉昌張氏、吕氏,白衣爲主”,這種占例是表示作爲“白衣”的崔氏、張氏、吕氏將自立爲主。而這種在姓氏前冠以“白衣”的做法,與《京氏易傳》中依據石立於山、平地,從而預言是“同姓庶士”還是“异姓庶士”“爲天下雄”中的表述一致;《春秋圖》中“客星出張,白衣同姓有自立者”,也與此相近。只是在《西秦五州占》中,將所謂的同姓、异姓具體爲敦煌地區的大姓,這也是《西秦五州占》這一星占文獻對舊有星占傳統的地方化改造。而這種改造,自然能够使星占文獻的預言更爲貼切敦煌地區之實際情形。蓋地方政權更替之際,本地大宗族可以更快地“聚白衣之徒”,稱作帝王。
六、 迎合與模擬: 從謡讖到名號的“白衣天子”
如前文所述,在“白衣”升爲“天子”這一觀念背景之下,“白衣”符命出現、行用的時間,必然是政權交替、君主受命之際;星占系統的“白衣”占辭,也與國家大亂、兵大起的背景密切相關。基於此,我們將重新考察隋唐之際以及金山國所流行的“白衣天子”謡讖與名號。
隋唐之際的“白衣天子”謡讖,出現於温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康鞘利將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軍矟旛皆放此。營壁城壘,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國。開皇初,太原童謡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於東海。常條律令,筆削不停,并以彩書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注]温大雅: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第11頁。
是年(617)六月己卯,[注]按,是月并無己卯,《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當有誤。裴寂等通過太子、秦王向李淵建議“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李淵接納這一建議後,便遣使突厥,突厥隨即派遣了柱國康鞘利等人至太原。而對於如何改易旗幟,有人以爲當建立“白旗”,以仿效周武王革命之故事。據《史記·殷本紀》:“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大白旗。”[注]《史記》卷三《殷本紀》,第108頁。又《史記·周本紀》載:“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注]《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24頁。可見牧野之戰正是甲子日,而周武王則是以“大白旗”指揮諸侯的。不過,李淵卻并没有直接采納建“白旗”的意見,他認爲武王所建白旗不過是“臨時所仗”,因此最終建立了雜絳白之旗。對於此絳白旗,胡三省以爲:“今用絳而雜之以白,以示若不純於隋。”[注]《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隋紀八》,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5864頁。不過,陳寅恪卻以爲胡三省的解釋“適得其反”。陳氏曾勾稽史料,對李淵稱臣於突厥一事,加以疏通證明。據陳氏之研究,由於突厥懸白旗,因此建立“白旗”之説,本爲“以示突厥”,即稱臣於突厥。而“唐高祖之不肯競改白旗而用調停之法兼以絳雜半續之者,蓋欲表示一部分獨立不純服從突厥之意。”[注]陳寅恪: 《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寒柳堂集》,北京: 三聯書店,2001年,第113頁。按,對於李淵所建絳白旗,有論者從五德終始説立論,以爲“其用旗幟絳白雜半,正是將土德隱藏在火德與金德中間,此即: 火(赤)—土(黄)—金(白)”。(見高明士《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第24頁)然而,至今未有朝代將自己的德運用這樣一種曖昧不明的方式表達出來,故此説難以成立。這一觀點,不僅使李淵稱臣於突厥一事得以大白,還敏鋭地把握了李淵起兵之初不得不暫時臣服於突厥,同時又努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微妙心態。基於此,陳氏對“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這一謡讖也有不一樣的看法,他寫道:“所可笑者,開皇初太原童謡本作白衣天子出東海,太宗等乃强改白衣爲白旗,可謂巧與傅會者矣。夫歌謡讖緯,自可臨時因事僞造,但不如因襲舊有之作稍事改换,更易取信於人。”[注]陳寅恪: 《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第113頁。
陳寅恪認爲,“白旗天子”不過是改造“白衣天子”而成。也就是説,這一謡讖在開皇初本做“白衣天子出東海”,改造的緣由則是李淵改易旗幟一事。而從隋主楊堅對於開皇初太原童謡的迎合、模擬來看,陳寅恪的判斷是正確的。如“隋主恒服白衣”,即是模擬原謡讖“白衣天子”;“每向江都,擬於東海”,則是希望借助江都這一地理位置來比擬謡讖中的“東海”;“常條律令,筆削不停,并以彩書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則明顯是模擬“法律存,道德在”,以製作律令。[注]按,由於有“以彩書五級木壇自隨以事道”的句子,因此也有論者以爲此一謡讖出自道士之手,具體參見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修訂本)》第2卷,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頁。不過,由於楊堅本人崇奉道教,有可能是楊堅結合自身信仰對這一讖謡的模擬,造作者并不一定是道士。由此可見,楊堅對於這一謡讖,是盡可能地去迎合與模仿,希望太原童謡的預言能够在自己身上實現。即便“江都”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東海”,但楊堅也試圖將其比擬爲“東海”。因此,如果原讖謡作“白旗天子”的話,楊堅的迎合與模擬多少也應當向“白旗”靠攏。而事實上,當隋建國之後,以爲得火德,乃決定“旗幟犧牲,盡令尚赤”了,[注]《隋書》卷一《高祖上》,第15頁。根本没有顧及“白旗天子”。而且,以“白衣天子”作爲太原童謡的早期版本,不僅更符合自漢代以來“白衣”升爲“天子”的政治文化背景,且能够與《開元占經》中不斷出現的“白衣”占辭相互對應。相反,作爲孤例出現的“白旗天子”,卻没有“白衣天子”所具有的影響力與説服力,難以取信於衆。
此外,如果我們再對太原的“白衣天子”謡讖進行一番溯源的話,還能够得到另外的佐證。前文曾提及,姜望來注意到了《北史·藝術傳》所載“齊當興,東海出天子”讖謡,他認爲,這與“白旗天子出東海”謡讖有“前後因襲模仿之痕迹”。[注]姜望來: 《讖謡與北朝政治研究》,第196頁。這一判斷應當是没有問題的。另外,他還注意到,“東海出天子”謡讖又與西晉末的“真人出東北”、魏末的“東北水中,庶人王”有着明顯的承襲關係。[注]姜望來: 《讖謡與北朝政治研究》,第148—150頁。按,“真人出東北”見《晉書》卷九五《藝術傳》,第2492頁;“東北水中,庶人王”見前引《北史·方伎傳》。因此,“白衣天子出東海”的“白衣天子”便極有可能來自魏末“庶人王”這一謡讖,只不過將“庶人”變爲“白衣”,“王”變换爲“天子”。而前文已經提到,“庶人王”與《開元占經》所引讖緯文獻中的“白衣王”有着密切的關係。而將“庶人”轉换爲“白衣”,無疑更具有象徵意義及革命意味。因此,“白衣天子出東海”讖謡的出現,即是對“東海出天子”等讖謡的模擬與改造,同時也受到了“白衣”爲天子這一政治文化背景及廣泛流傳於星占、讖緯文獻中的“白衣王”占辭的深刻影響。
與“白衣天子出東海”相類似,金山國的“白衣天子”名號,既可以看作是對隋唐“白衣天子”謡讖的模仿,也是對流傳於西秦五州的“白衣自立”、“白衣爲主”占辭的迎合。而這兩方面的内容,我們從張承奉所確立的幾種名號中,可以窺見一二。據蘇瑩輝之統計,張承奉稱王、稱帝的名號如下:[注]參見蘇瑩輝《從幾種敦煌資料論張承奉、曹議金之稱帝、稱王》,《敦煌文史藝術論叢》,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第250頁。
王號:
拓西金山王(P.4044)
聖文神武王(S.1563)
燉煌國天王(S.1563)
金山白衣王(P.432)
帝號:
金山白衣天子(新、舊《五代史·吐蕃傳》)
金山天子(P. 2594、P.2864)
金山明聖主(P.2684)
金山白衣帝(P.2633)
這些張承奉所采用的名號,大都可以確定承襲自唐代。如S.1563、P.2594,都以“聖文神武”爲號,這本是唐玄宗的尊號。據吕思勉之統計,唐玄宗於開元、天寶年間嘗六受尊號,分别爲開元神武皇帝、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從此加尊號被沿爲故事。[注]參見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59頁。此六次尊號,實爲後世生前受尊號之始,[注]王鳴盛認爲:“蓋生上尊號固起於唐,前世未有,即殁而上諡,前世亦用一字而已,無連累數字者”,見王鳴盛撰,黄曙輝校點《十七史商榷》卷七六《新舊唐書八·尊號諡法廟號陵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90頁。自然有極大之影響力。即在當時,因上尊號,玄宗曾數次下詔大赦,留下了《加開元聖文神武尊號大赦文》《加應道尊號大赦文》《加天地大寶尊號大赦文》《加證道孝德尊號大赦文》等文字。[注]四篇赦文見王欽若等撰,周勛初等校訂《册府元龜(校訂本)》卷八六《帝王部·赦宥》,第946—947、952—953、955—956頁。篇名爲後人所加,見《全唐文》卷三九、四。因此,儘管加尊號只是一種頌聖之舉,由於施行大赦,且大赦文中多有各種禮儀、制度之規定,當時的百姓必然會有着切身感受。而且,《加應道尊號大赦文》之殘卷尚見於敦煌遺書中,[注]此殘卷編號爲S.0446,具體録文及相關校讀,可參見王繼如《敦煌遺書斯0446號〈加應道尊號大赦文〉校讀記》,《文教資料》1997年第1期。可見在敦煌地區,有關唐玄宗受“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等各種尊號的事實,已經有着較爲廣泛的流傳,或已成爲敦煌地區的某種集體記憶。因此,張承奉因襲唐代故事,以唐玄宗的“聖文神武”尊號爲自己的帝王名號,自然比較容易得到敦煌各界之接納。[注]此外,“金山明聖主”之“明聖”,或取自唐懿宗之徽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參見《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第652頁。
除“聖文神武”這一尊號之外,“白衣天子”這一名號,也应当是承袭自“白衣天子出東海”這一唐朝謡讖。而這種做法,無疑是將唐王朝塑造政權合法性、神聖性的要素移植到了金山國,是“對構成權力正統的要素進行模仿和映射”。[注]余欣: 《符瑞與地方政權的合法性構建: 歸義軍時期敦煌瑞應考》,《中華文史論叢》2010年第4期,第377頁。這種模仿既包括“聖文神武”這一曾廣泛流傳的尊號,也包括“白衣天子出東海”這一謡讖中的“白衣天子”名號。更何況,當唐王朝覆亡之後,歸義軍長期奉爲正朔的中央王朝不復存在,歸義軍自身統治的合法性也受到威脅。在這一背景下,構建金山國本身的合法性就成爲金山國立國前後的重要事項。[注]據榮新江之意見,金山國建立的時間是在唐亡之後,具體參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第214—219頁。而對舊的讖謡、符命的迎合、改造或模仿,要比新造作的祥瑞、符命更加有説服力,無疑能够幫助張承奉樹立天命在己、繼唐而興的形象。
除“白衣天子”外,“白衣王”“白衣帝”的名號,則與星占文献中的“白衣”占辞密切相關。金山国立国之時,《西秦五州占》中“白衣自立”“白衣爲王”等占辭早已經流布於西秦地區。據陳餘柱的分析,“四州自立白衣爲主,不歸帝吉,歸其位,即令萬人死”的占辭,“清楚地表明吐蕃占領河西時期,該地區的國家意識與區域自治觀念在此落彼漲的趨勢。歸義軍政權建立之後,雖然多奉中原王朝爲正朔,但因晚唐五代中原内部藩鎮割據、王朝權威衰落無暇西顧以及河西部族政權的紛紛建立,歸義軍實際已經近似於一個獨立王國,統一王朝時期的民族—國家意識也愈加讓位於區域自治,張承奉金山國的建立,曹氏執政者在歸義軍轄區稱王等,即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注]陳餘柱: 《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敦煌禄命書研究》,第264—265頁。對於金山國的建立,余欣在王重民基礎上也有過這樣的判斷:“五涼一直流傳‘白衣自立爲主’踐祚稱帝的讖謡,流布極廣。張承奉得知唐已亡的消息後,即執此讖言爲天命在己,圖謀履九五之尊。”[注]余欣: 《符瑞與地方政權的合法性構建: 歸義軍時期敦煌瑞應考》,第346—347頁。也就是説,張承奉只需要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去迎合這些“白衣”占辭。以張承奉的帝王名號爲例,或稱爲“金山白衣王”,或稱爲“金山明聖主”,或稱爲“金山白衣帝”,這種同時以“王”、“主”、“帝”作爲名號的情形,正好與《西秦五州占》中“白衣自立爲主”、“聚白衣,自立爲候王”、“不歸帝位”等占辭相吻合。不過,從“王”“主”“帝”這些名號的同時出現,我們也可以看到金山國對自身政權性質的認識是較爲模糊的,他自然希望能够履九五之尊而成爲天子,但實質上仍舊是一個地方政權。
張承奉對於星占傳統中“白衣”占辭的迎合,以及在帝位名號上對於《西秦五州占》的模擬,都使我們相信,張承奉所確立的幾種“白衣”帝號或天子號,都不過是執舊讖以爲己用,以獲得敦煌百姓最大程度的支持。遺憾的是,即便迎合了敦煌地區自治的潮流,也獲得了敦煌地區各界的支援,但在沙洲回鶻的連續攻擊下,金山國很快就遭遇覆滅。無論是唐的舊讖,還是流布於河西的星占預言,都未能延續金山國的政治生命。
七、 結 語
通過本文的論證,可以知道,“白衣”在中古時期一直都是作爲庶民的身份符號出現的,這是建立在庶民以“白衣”爲常服這一服飾等級制度基礎上,且能够由傳世及出土文獻所證實的。因此,對於中古時期的“白衣”及相關謡讖、符命、星占的研究,都應該建立在這一語詞基礎之上。而自漢代以來,由於漢高祖、宣帝、光武帝等由庶民立爲天子的事實,“庶士爲天下雄”“庶人受土田”“從匹夫爲天子”等表述紛紛出現。由於“白衣”已經成了庶人之身份符號,因此從“白衣”升爲“天子”這種同義表述也出現在了《風俗通義·皇霸》《宋書·符瑞志》等文獻中。從《北齊書·方伎傳》“東北水中,庶人王”到隋唐時期“白衣天子出東海”謡讖的演變中,還可以看到“庶人”爲“白衣”所替换的情形。而從《皇霸》《符瑞志》的文獻性質來看,“白衣”爲“天子”的表述本就是與受命之君相關聯的。由此看見,隋唐之際的“白衣天子”謡讖或名號,至少在東漢晚期就已經有了一種較爲原始的表達。
而在中古時期,災异祥瑞、星占系統中也有大量關於“白衣”的符命、占辭在流行。在“白衣人”闖宫事件中,“白衣人”或以秩序破壞者的形象出現,宣告自己將上殿成爲天子;或稱作“神人”,被賦予神性,以謡讖的方式宣告某人將成爲受命天子。而“白衣老父”或“白衣野老”,實際上也是“神人”的一種。這些“白衣人”以不同的身份在易姓受命過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另一種方式詮釋了“白衣”如何升爲“天子”。
而在星占系統中,則有“白衣受地名城”“白衣之聚”(或“白衣會”)“白衣自立”“白衣爲王”等多種形式的占辭。這些占辭中的“白衣”都可以確定表示庶民,且大多出現在國家大亂、王朝更替的背景之下。尤其是“白衣徒聚謀逆”“白衣自立爲王”等占辭,則十分清晰地表現了庶民以“欲分社稷者”的姿態出現,聚衆反叛,自立爲王的情形。無疑,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白衣”爲“天子”。由於《開元占經》等星占文獻的“白衣”占辭有較多出自《春秋圖》《文耀鈎》等讖緯文獻,這些有關“白衣”的占辭也應當以讖語的形式廣泛流傳,“白衣天子”謡讖即是其一。
考慮到“白衣”爲“天子”的表述早在漢代就已經存在,而“白衣”爲“天子”也已經在災异祥瑞、星占系統中頗爲流行,隋唐之際的“白衣天子”謡讖又淵源自北朝“齊當興,東海出天子”“真人出東北”“東北水中,庶人王”等讖謡,因此,將“白衣天子”讖謡視爲對中古“白衣”符命、占辭、謡讖的模擬與迎合,當没有太大問題。而張承奉的“白衣天子”名號,也能够被納入到這一系統之中。一方面,金山國以繼唐而興的形象出現,爲了構建政權的合法性,在天子名號上充分模擬唐朝,因此他既襲用了“聖文神武”等尊號,也采納了謡讖中的“白衣天子”名號;另一方面,《西秦五州占》這一星占文獻已經對《開元占經》中的“白衣”占辭進行了地方化改造,“白衣自立爲王”“白衣自立爲主”已經成了西州的本土資源,張承奉采納“白衣王”“白衣帝”等天子名號,也十分合乎情理。
由於從“白衣”爲“天子”的表述起源於漢代,而無論是在創業君主歷史書寫中的“白衣”受命之符,還是流傳於各種星占文獻中帶有革命意味的“白衣”占辭,都可以視爲中古中國所固有的數術傳統,而并非源自佛教、摩尼教等外來宗教。此外,儘管數術與道教有着極爲密切的關係,但數術和道術仍舊是兩個流傳有序的傳統,因此早期的“白衣”符命,也不能説起源於道教。
不過,當佛教流行於中國之後,中國固有的符命思想與數術傳統,確實受到佛教的影響。本文所討論的“白衣”符命,至晚到隋唐便開始表現出了某種佛教意味。以流傳於史志災异系統的“白衣人”闖宫事件爲例,隋煬帝大業六年(61)群盜入建國門的事件,就明確記載着這些闖宫者“自稱彌勒佛出世”。而在此之前的“白衣人”闖宫事件,或稱“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或稱“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而無論是“天同色”還是“梁伯夏”,都可以在中國固有的傳統中找到;而自稱彌勒出世,無疑是受了佛教之影響。由此可見,讖言的改變才是我們判斷是否受到佛教影響的標準,而不是同樣作爲服飾特徵的“白衣”。在《隋書·五行志》“裸蟲之孽”部分,還有兩次類似的事件。大業九年(613),唐縣人宋子賢“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同年,又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注]《隋書》卷二三《五行下》,第662、663頁。這些事件雖是彌勒教衆的叛亂行爲,但卻并未有衣“白衣”,可見以“尚白”爲唯一的判斷依據,并不可靠。
當然,從大業六年建國門事件自稱“彌勒出世”可以看出,中國的五行災异敍述已經帶有明顯的佛教因素了。而事實上,傳統的災异符命之説,確實在佛教盛行之後發生着相應的轉變。嚴耀中認爲,佛教史料大量進入陰陽五行學説,正表明“佛教在隋代已經融入中國文化意識的主流”。[注]嚴耀中: 《試説〈隋書·五行志〉中的佛教史料》,《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輯,第256頁。游自勇的研究則表明,史家在某種程度上也承認了佛家讖語能够對王朝的興衰做出預測。[注]游自勇: 《天道人妖: 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博士學位論文,首都師範大學,2006年,第120頁。而孫英剛的研究則告訴我們,佛教因素還能够對傳統的陰陽災异學説進行化解。[注]孫英剛: 《佛教對陰陽災异説的化解: 以地震、火災與武周革命爲中心》,《神文時代: 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2—284頁。而在星占領域,敦煌文獻中的P.3055V、P.3571VB,就與“外來佛教文化,尤其是印度天文星占學關係密切”。[注]王晶波: 《敦煌占卜文獻與社會生活》,第192頁。不過,從我們所考察的星占文獻中的“白衣”占辭來看,似乎還看不到佛教因素的影響。
而更爲重要的是,無論“白衣”這一符命、占辭在後世受到佛教的影響幾何,以庶民身份符號爲基礎的中古“白衣”符命,仍是根植於漢代以來的災异符命與星占傳統這一土壤之上的。即便受到佛教之影響,但無論其采用的理論依據如何,或采取了何種具體的技術手段,其作爲符命、讖謡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其所表達的内涵,也仍舊不會超出傳統中國的易姓受命觀念。
附記: 本文的寫作、修改,曾得到中國人民大學王子今、孟憲實,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馬怡、曾磊,北京師範大學羅彧,復旦大學高中正等先生的幫助,并曾以《服制與符命: 中古“白衣天子”的再研究》爲題,提交人民大學中國古代史青年學術研討班第四期(2016年4月14日)討論,得到把夢陽、黄曉巍、李蘭芳等學友的寶貴意見,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