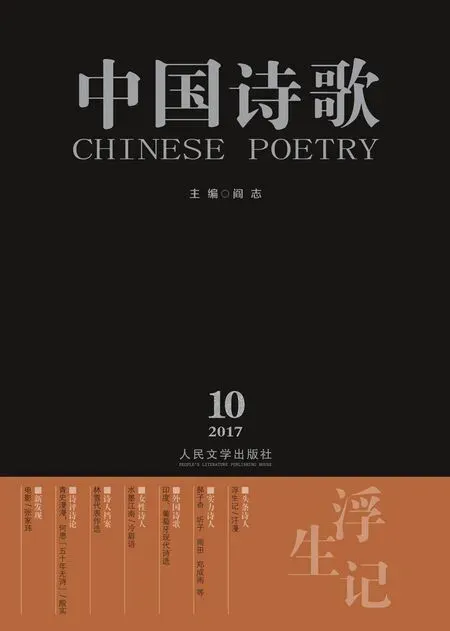诗学观点
□甘小盼/辑
诗学观点
□甘小盼/辑
●左存文认为,境界才是诗意的出发点,也是诗意的目的。诗意就是“境界”所呈现出的诗歌的艺术之美,是审美之所以产生的根本。而审美是不完善的生活在完整和谐的形式中的自救。所以,当下诗歌创作的重中之重就是重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支撑。诗歌所表达的真景物、真感情不但是“真切的一己之情,而且是诗人对宇宙实底、人生本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体悟”。当下诗歌的创作走入了一个误区,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语言迷宫,就是絮语式的无关痛痒的言说。不用说对于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就连心灵的宣泄共鸣也很少出现。或许,除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冲击之外,新诗本身的价值定位还有待酌。
(《“境界”说的当代阐释及对新诗创作的启示》,《北方文学》,2017年第5期)
●葛兆光认为,写诗要有理趣,有理趣的诗首先是不能直接写理,而要借景写理,写得含蓄蕴藉。有理趣的诗应该是浑然一体、自然轻松的,它要令人在不知不觉中领略到哲理,哲理在美的欣赏中自然而然沁入人的心灵。有理趣的诗还要写得新、写得巧,话说三遍,人人生厌,所以要有新意;平淡无奇,笨拙滞重,也引不起人喜爱,所以构思要巧。但最主要的还是上述的含蓄、自然、轻松。只有含蓄,才能耐人寻味;只有自然,才能富有情趣;只有轻松,才能使人不知不觉地领略哲理,领略艺术的美。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5月5日)
●张洁宇认为,寻找诗歌的独立性,划分诗与散文的界限,树立诗歌独特的审美原则,这是中国“纯诗”论者的初衷和思想基础。这是很重要的诗学观念,不能说只是某一种趣味。“纯诗”的“不纯”的问题,一方面确实与诗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有关,现代知识分子式的现实关怀对写作的题材、表达的方式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所谓“不纯”也是中西诗学互动实践的一种必然。不过,“纯诗”这个概念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美学理论,而在写作实践中,不断地有意识地将“不纯”的东西融入“纯诗”写作,不断以“纯诗”写作本身去容纳和解决“不纯”的问题,这可能才是更好的更有创造性的状态。
(《理想的新诗史应是一种“问题史”》,《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欧阳江河认为,诗歌需要有原创性,并要体现诗人的个性、独特性。这些和诗人的才气、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疼痛、他们对时代的看法、对命运的感受等等都有关。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才构成他们彼此之间完全不同的诗歌。但人工智能只是从已经写出的诗里进行模仿、重组。我们应该尊重诗歌的原创性,写的不是已有的诗的重新组合,写出的应该是诗歌史上还没有被写出来的东西。人工智能一定是根据已经写的诗进行重新的编排和整理。诗歌写作的背后还有更为广阔的东西,而面对日益发展的人工智能,诗歌或许是人类最后的“堡垒”。
(《人工智能将攻克诗歌?》,《深圳特区报》,2017年7月4日)
●九天认为,诗歌是内在精神的外在体现,一个精神明亮的读书人,终究会照亮人心的深处,使人性高尚。诗歌是人类精神最早的萌动与起源,这些近乎于宗教情绪的诗歌经典,都给人以神秘的情感抚慰和心灵净化,这种情感,是大自然与诗人个体精神的对接。意境与精神同步,诗魂和心情共舞,此为诗人之能事。诗人都有一个敏感的性情和不屈的心灵,而诗歌,就是人类的心灵史,其神之属性,让诗人具有一颗悲悯的心灵,诗歌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让人的心灵充满了梦想。
(《诗意星空下的精神光芒》,《山西日报》,2017年7月12日)
●杨四平认为,“新诗叙事”不是该不该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产生现代的中国的诗意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新诗叙事所提供的历史形象与现实影像的语境中,从它与新诗抒情、新诗议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境、“秘境”和事境的关系,来思考其自由与限度的问题,进而从宏观上构建新诗叙事理论,看看它们最终能否回应新诗发展的现实提问,并给未来新诗发展提供诗学动力。诗的“向内转”,诗注重自身的段位性,并不一定就脱离了社会,也不必然意味着是条诗歌窄路,更不等同于诗歌死路。面对此种诗歌险境,当下中国诗人不但没有放弃“向内转”,反而在挖空心思地考虑如何在诗的“叙事背后”、“叙事之外”大做文章,大有可为。
(《新诗叙事的诗意生成及其诗学反思》,《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
●薛述方认为,对诗意内核的思考,直接决定了诗歌在语言和观念上的外在呈现。只有金玉的外衣,却没有成熟的诗思和诗艺作为依托,依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饱满的诗意空间。只有基于诗人一定的基础经验认知,在积攒了足够的诗思基础上,通过多向度的观察和体悟达到诗歌内在的平衡,建立起诗人的自觉,才能达到经验、语言和观念的和谐,从而真正地借助于皮相的手段恰如其分地呈现诗意。对西方现代诗表达技巧的学习固然有助于写诗,但只有立足于个体经验以及对生活的理解,诗人的诗歌创作才会具有特色,也只有在一定艺术思考和人生经验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形式意味,才能达到诗思和诗艺的互动和谐,创造出有意味的诗歌。
(《痖弦:在日常状态中抵达诗艺与诗意的和谐》,《世界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温建生认为,写诗从古到今都是一件寂寞的事情,也可以说,诗歌从来就是小众和少数的。面对中国诗歌的时候,特别是面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水准和具体评定指标的时候,诗人和诗学家常常会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真正的中国当代好诗是什么样子的,能够呈现的标杆性的作品又有哪些呢?这些问题常常又会莫衷一是。优秀的诗歌首先是说人话的。高手出招,一刀致命。直接的表达永远是最好的表达,任何对诗歌表达造成障碍的东西都是非诗的东西。优秀的诗歌都有很自然的呼吸,这种呼吸来自诗歌本身的质地,和世俗物化的标准无关,和道德评判无关,是内心情绪最好的一次释放。优秀的诗歌必须是独特的,独特的诗歌视角和文本形式,这是支撑诗歌本身最重要的部分。
(《诗歌是一门关乎灵魂的技艺》,《太原日报》,2017年7月26日)
●闻礼萍认为,中国新诗和新文学一样,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它不再是旧式的士大夫阶级抒愤、怡情或言志的手段,新诗和新文学区别于旧诗和旧文学的最根本的要害,就在于二者都是不间断地把创作同追求中国社会的进步、变革和更新的历史运动、时代的整体情绪和时代的精神,相当自觉地结合起来。尽管目前中国新诗“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但无论是诗歌创作界还是诗歌批评界,对此却缺少反思,因而,目前在诗歌界流行的仍然是所谓的“新的美学原则”。现在也有不“边缘”的诗,但这些诗不仅不关心时代、不关心社会、不关心现实,也不关心人道、人心、人性,而是一味写感官、写欲望、写堕落、写性,成为消费主义的同谋。因此,要发挥诗歌批评的作用,驱诗歌浊音,扬诗歌正音。
(《中国新诗:应该行进在怎样的道路上》,《中国文化报》,2017年6月21日)
●吕进认为,网络的随意性,自由性,即时性,也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诗人不再被称为是诗人,诗人变成了“写手”,写诗很容易。网络诗歌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所以需要发出“重建写诗的难度”的呼声。而且,相当数量的诗人只生活在自己的网站、朋友圈、微博里,圈内的人相互模仿,对于圈外的人的作品不屑一顾,没有差异,自然就弱化了对独创的努力。百年新诗史上各种诗歌的“群”,当下诗歌新诗、旧体诗、网络诗、民间诗的“群”,都是诗歌发展的正途。多元带来丰富,竞争带来发展,只承认、推崇一种流派或门派,排除一切别的流派或门派,不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可成就的“霸业”。诗可以“群”,这也许是中国现代诗歌在下一个百年应当坚持的。
(《诗可以“群”》,《中国艺术报》,2017年7月5日)
●李少君认为,百年新诗成就如何,这个问题必须从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入手,百年新诗其实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相互关联又相互缠绕的问题。如何理解百年新诗,其实也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性。现代性问题解决不了,新诗的问题也就解决不好,新诗本身也是现代性的探索者和先行者。百年新诗万事俱备,现在最需要的是向上超越。在此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确立民族主体性和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具有典范性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为当代人提供新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只有在这样多维度的融域视野中,当代诗歌的高峰才会出现。
(《百年新诗:光荣与梦想》,《学习时报》,2017年7月14日)
●佛山五月花认为,诗词不是写出来的,写诗词一定先要有灵感,是诗人的生活感触与感悟的记录。诗词既然是诗人生活感悟的记录,就应该有真情实感,就应该接地气,没有真情实感、不接地气的东西不论平仄、对仗如何规范、工整,那最多也就是文字游戏,算不上诗词。诗词跟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是形象的艺术、语言的艺术。艺术,就是处理技巧。要让诗词的画面耐人品味,还需要将诗词的画面融入作者自己的感情,写诗不但要让读者通过阅读文字、通过形象思维还原成画面,而且还应该在欣赏画面的同时,感受到作者的“精气神”和高雅的个人情趣与格调。
(《诗词不是写出来的》,中华诗词网,2017年7月25日)
●巍微一笑认为,诗歌中,当今还没有人敢轻易站出来说自己是真正的高手,那些所谓的“高手”,或许是专业的文字鉴赏师,到底有无真才实学,无从得知,所以他们的点评也不一定就是圣旨,开的口也未必就是金口,没必要偏听偏信。诗歌是意象和情感的组合体,不能摘只言片语妄言定论。之所以评,之所以写,只起到一个相互交流、促进的作用,不能以一种评判标准而全盘否定自己,忘了诗写的初心。世界这么大,各人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写出来的东西是给大多数人看的,有人赞成,当然就有人反对,众口难调,这都在常理之中,关键是起到个人释怀的作用。
(《诗人也要有亮剑精神》,中国诗歌网,2017年8月5日)
●西川认为,有些人的诗歌写得如此之差,其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超常的思维,而仅仅把“超常”归结为超常的生活方式,这种“归结”本身恰恰太不“超常”了。超常的思维和超常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但超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超常的思维作基础,那必是学来的和做出来的,并且最终是不真实的,海德格尔有一句口号:“人的诗意的栖居”,然而在“诗意”的名下栖居着多少庸才和笨蛋!他们把自己装扮得比诗人还诗人。如果他们不来纠缠你,那就由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敲你的门,你就记住:凡是太像诗人的肯定不是诗人,至少不是好诗人。
(《太像诗人的诗人不是好诗人》,诗网刊微信公众号,2017年7月18日)
●星儿叶子认为,从现代禅诗来考量,诗中的“景”是有独立性的,具有自身独立的审美价值,并不完全是为主观抒情铺设的辅助工具或道具。现代禅诗主张万物平等,物我相融,那么现代禅诗的诗人们在观照万事万物的时候是没有分别心的,因而这些摄入诗中的景象多是客观的,生动的,千变万化的,也是自身具足灵性和生命的,它并不依附于诗人的主观情感而存在,它们可以依赖于自身的性情灵性特色优长而独立存在,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现代禅诗的艺术形式,直接融合了禅的直觉思维的活动形式。正是直觉思维观照抵达的悟境所呈现的诗歌灵感和灵性之光,使现代禅诗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生命温度和灿亮的精神光芒。
(《谈谈现代禅诗中的物情之美》,现代禅诗欣赏微信公众号,2017年7月22日)
●谭延桐认为,诗歌也是有气味的。生命有生命的气味,诗歌也有诗歌的气味。诗歌的气味就如同人体的气味一样,有清有浊。清新的诗歌人见人爱,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只因为它对得起“清新”二字。一颗正常的健全的心灵,是不可能不喜欢清新的。这样的诗歌,只要是嗅上一嗅,就会心旷神怡,甚至心醉神迷。这样的诗歌就像妙品或极品或神品一样,是很少见的。也正因为它像沉香木一样稀罕,才更容易让人产生非凡的兴趣和联想。精神的洁癖,首先应该是诗人的一种喜好,美的使者,更应该是诗人一生的向往。美好的气味都是从信实和执守等等生命的枝条上不断散发出来的。
(《诗歌也是有气味的》,诗评媒微信公众号,2017年8月4日)
●陈仲义认为,如果从诗歌写作根本目标,即从创新性出发,新诗跟文言诗的差别其实是越来越大的。二者已经发生很大的质地和属性的变化,包括语言觉醒、潜意识开发、本能直觉、抽象等等,现代诗已成为独立于古诗又在白话新诗基础上有所超越的升级版。诗歌的不同制式意味着在发生学、文本学和接受学上,在语言、功用上文言诗与现代诗都不太兼容。首先,文言诗是单音字为单位的字思维,而现代诗歌是词思维。其次,古典诗歌是无时语态,是没有时间引发的一种空间装置,现代诗歌已经进入特指时代过程。再一个是模式变化,一个是农耕田园的模式,一个是与高速喧嚣的都市化进程相关,还有就是古典诗歌的优雅精致跟现代诗歌的本能的物象也有区别。
(《为什么先锋诗歌没能成为新诗主流》,诗歌周刊微信公众号,2017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