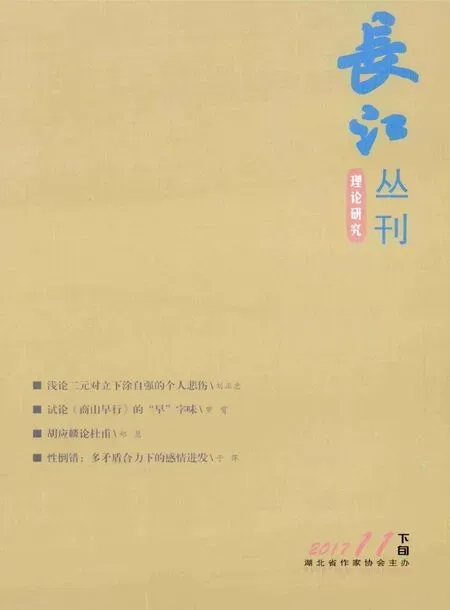性倒错:多矛盾合力下的感情迸发
——以严歌苓《白蛇》中孙丽坤形象为例
于 萍
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中依据性倒错人群不同的行为表现分为完全性倒错者、两栖性倒错者和偶然性倒错者。完全性倒错者是指性对象只能是同性的人群。两栖性倒错者,性心理上表现为雌雄同体,他们的性对象既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不具有排他性。偶然性倒错者则是指在特殊条件下,正常的性行为受到阻碍,才将同性作为性对,并在与同性的性行为中获得满足的一类人。
很显然《白蛇》中孙丽坤是个偶然性倒错者。被关押前,孙丽坤的性对象只是异性,她演“白蛇传”的那些年,“大城小城她走了十七个,个个城市都有男人跟着她”。“文革”时,孙丽坤被关押,两年里整个精神面貌如猪猡一般。“徐群山”的出现,照亮了孙丽坤的末日,带给了她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满足。在徐群山“调查”孙丽坤的最后一天,“她的手停在他英武的鬓角上,她都明白了”,但不能道破,道破“她就一无所有”,即便知道了“徐群山”是女性,孙丽坤还是坚持把梦做完,她将自己“三十四岁女人渴极了的身体任徐群山赏析、把玩、收藏”——这是她黑暗生活里的唯一希望。
当禁欲的大环境里性欲再次醒来时,孙丽坤把这份冲动寄托在忘我的舞蹈上来寻求解脱。这时“全须全尾的女孩子”珊珊出现了。珊珊也一点点褪去徐群山的影子,柔媚渐渐回到她的身上。“在停尸房附近的树林里,这年这月这天,她意识到自己开始爱珊珊了”,这时孙丽坤才成为了真正的同性恋,在欲望喷发与禁欲的冲突中,性倒错成为孙丽坤解脱的唯一选择。然而孙丽坤在与徐群珊在一起时,“她们之间从来就没能摆脱一种轻微的恶心,即使在她们最亲密的时候”。关押期间,孙丽坤与粗俗的建筑工人斗嘴时,并没有排斥过他们,即从始至终,她依旧是对同性之间的恋爱怀有排斥的。平反后,孙丽坤从“文革”的黑暗走出来,回到阳光下,需要找到一个“支持她的舞蹈事业”,生活上照顾她的正常男人做未婚夫。孙丽坤与徐群珊间的同性之爱只能存在于那个特殊的时期。
当性本能冲动无可遏止的产生时,将欲望投射于同性,便产生了性倒错。在严歌苓的《白蛇》中性倒错可以说是在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多重矛盾合力作用下产生的,当个体欲望不可遏制时,这种欲望就必然和他者、社会环境形成激烈的冲突,也必然面临着情感选择,性倒错无疑就是孙丽坤的情感选择。
孙丽坤是一个一直在追求欲望满足的人,当被关押后,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她欲望满足成为无稽之谈,无休止的关押与检讨彻底压抑了她的欲望的同时,也榨干了她的灵魂。孙丽坤与自身、与看管者、与整个禁欲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昔日的美女蛇孙丽坤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她和其他中年妇女没有什么区别……孙丽坤丢失了尊严、荣耀、一切好的东西,连自身都陷入了无尽的暗黑之中。昔日把孙丽坤看作“孙祖祖”的女娃们,现在得了看管她的权利,把昔日的恭敬演化成一股仇恨加倍奉还给她。孙丽坤俨然成为了逐鹿场上的困兽,坐以待毙。直到徐群山的出现,犹如末世里的一缕阳光,照亮了孙丽坤僵死的灵魂。当男性徐群山出场,孙丽坤仓皇地“退场”后,重新出现时已然换了个精神面貌,“她肌肤之下,形骸深部,那蛇似的柔软和缠绵,蛇一般的冷艳孤傲已复生”,可以说这一刻孙丽坤身上被压抑已久的欲望复活、喷发了。
在极度禁欲的年代,在自身欲望与现实环境、他者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孙丽坤选择做着自欺欺人的春梦,接受了珊珊的爱恋,尽管她始终觉得会有那么一点恶心,正如她自己反问的那样,不去爱珊珊,她又能去爱谁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丽坤的性倒错不是最终的感情目标,只是自身欲望在多重矛盾下的一种折中选择,只是特殊环境里的一种感情取舍与迸发。在这一点上,严歌苓《白蛇》中的性倒错与以往的同性恋爱是截然不同的。如陈染笔下的女性性倒错不具备偶然性、可逆性、暂时性,多是父权文化专制下的受害者在感受了父权社会与父权文化的专制后,自然地结成了女性同盟。比如《私人生活》中,“我”(倪拗拗)选择和母亲相依、与禾寡妇相恋,女性同盟似乎成为女性躲避外界窥探的城堡——当然陈染也相当清楚这个同盟本身的脆弱性。相比而言,《白蛇》中所呈现的同性恋爱就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临时性,它不是女性同盟的一种表现,更像是女性情感路程中的一个片段,一个随着时间流逝而丢弃或模糊的片段,它本身就是女性在与自身、与他者、与社会产生巨大矛盾冲突时的一种情感选择。
注释:
①严歌苓.白蛇[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6.
②严歌苓.白蛇[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48~49.
③严歌苓.白蛇[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54~55.
④严歌苓.白蛇[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19~20.
[1][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学三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
[2][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C].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