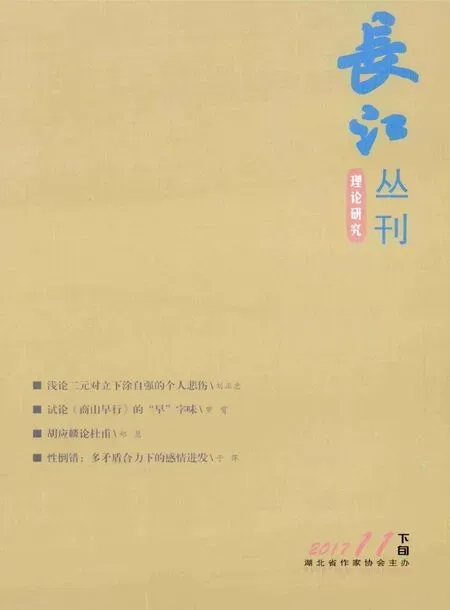天墀山
周凌云
雪化了。天晴了。蓝天盖在乐平里的山上。
屈原庙的后山是天墀山,天墀山也是兰花村的靠山。雪后的天墀山格外清晰。兰花村是一溜儿斜坡。天墀山从这溜斜坡上突然耸立而起,像天地间铸造的巨大的战国青铜器,上端蹲着一个天大的狮子,这个狮子咆哮无声,威严无语。昨晚,我在屈平河边散步时,一抬头,天墀山黑黑的,像个庞然大物压了下来,冷古丁吓出一身大汗。我对天墀山生了畏惧。
这座让我畏惧的山,我要攀登,要让黑暗中的庞然大物踩在我的脚下。这是我熟悉而又相当陌生的一座山。我从徐贪德的门前往天上看,它深入蓝天之中,看不清道路,只看到它的奇崛与险峻。徐贪德为我请来黄家刚作向导。他换了鞋戴上手套,握上一把锋利的镰刀,带我登山。
路,模糊可见,窄狭而险要,攀登如爬行。最险要最难走的,一处是眼皮子岩,一处是干柴老爷岩。过这两处,向下观望,感觉头晕目眩,神经触电一样格外麻木,行走小心翼翼,要绕开笔直陡峭的岩石,沿崎岖羊肠小路爬行。眼皮子岩上,有一溜凸起的岩石,极像人的上眼皮,村里人便称这岩为眼皮子岩。九十二岁去世的诗人徐正容写过一首诗:
岩生眼皮白云封
俯视河中水势汹
有人过此仰头看
削壁悬梁巅碧峰
这是村里唯一写过眼皮岩的诗人。
岩生眼皮白云封,从这里跌下去,不死即残。黄家刚指着岩皮子岩说:“我在岩上采过药”。我脸一下煞白。他说:岩上有一种药叫五灵脂,妇科良药,就在岩的洞穴里面,在里面采过很多次。老黄采这种药不是攀山爬岩,而是身系绳索从山巅吊下来,在半腰停住。山腰凹进去了,不能靠进山洞,老黄就手持长竿在岩上撑几下,借助惯力,让身子甩进山洞,采完五灵脂,老黄吹响哨子,山巅上的伙伴便用力拉绳,将他拉上山巅。老黄话语平淡,仿佛在叙说一件与已无关的往事,我看了看山,又看看黄家刚,觉得他在讲一个神话,形象像这山一样在我心中树立起来。山比人伟岸,有时,人又比山伟岸。他说,也有人为了采这药,从岩上摔下悬崖。采药最怕的是飞鼠嘶咬绳索,或者用翅膀去割锯,飞鼠翅膀的骨架像钢丝一样坚硬。它的飞行全靠滑翔,从高处向低处,从低处往高处就得靠爬行。五灵脂就是飞鼠的“粪便”,传说是飞鼠吃灵芝转化而成。黄家刚说,近来崖柏走俏,价值高,也有人吊下绳索在悬崖上挖,这是玩命的事,黄家刚现在不干了。
干柴老爷岩在眼皮子岩之上,另一侧,也险极。岩洞里置放着一块石头,模模糊糊,像个人形,人们把它当作石头神像,这就是干柴老爷。这就是村里人心中的神。人们通过这里都要供奉干柴,有的供一小捆,有的供几枝,再闭眼默念心中的愿望,保佑上山下山天不下雨,过往平安。下雨,不敢从这里过,脚下稍一滑溜,便坠山谷了。我爬过这里时,天阴,气象暗淡,也捡了几根枯柴供奉干柴老爷,以保我来回天不下雨。我是不信神不信鬼的,天不怕地不怕,不迷信什么也不崇拜什么,但人过中年以后,历经了许多事情,才明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天把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生存之中感觉到有一只无形的手拉你,或推你。我们对上天是要有敬畏之心才好。干柴老爷岩旁的路边堆了一人多高的干柴,像一段长城。这都是人们的敬畏。
天墀山居高临下。
屈原在这里问过天吗?
这时,我想朗诵《天问》。
乐平里全进入我的视野了。屈原庙很小了,像火柴盒。看到香炉坪了,屈原的老家,那几弯田,也像几把小梳子。房子都是意象,这里几点,那里几点。这时候,人比蚂蚁不会高大多少。人像坐在飞机上俯瞰大地。
走过最险要的两处,再翻过天墀山,是另外一片天地,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广阔的森林,风声犹如海啸,隐约可见颓废的房屋和荒芜的田亩。房屋有的拆了,有的朽了,人全下山搬走,曾经耕种的土地都长着丈余高的茅草,灰白如剑,覆盖了所有的耕地。茅草,也叫王草,是一种称王称霸的草,长得高,茂盛,粗糙,叶片就是锯齿,地下也盘根错节,长了这种草就不长别的草。这种草并不长在瘦土上,而是长在肥厚的土地里,营养全拔到自己的身上,田,一年不种,王草呈燎原之势,蔓延,覆盖,然后土地再也看不见了。草,农民厌恶,它是粮食的敌人。但是王草这里一片那里一片,成风景了也好看的,是画家的素材。跟我一同爬山的画家,后悔没有带上画笔,手痒痒的,我看见他的手比比划划,好像一幅画已有轮廓。虽然好看,但我觉得不适合画家画,它表现什么主题呢?是繁茂还是荒芜?
天墀山上有千亩森林、百亩耕地,曾经是一个小村落,建过林场,是兰花村的大片飞地。天墀山下的兰花村,户挨户、人挤人,土地少,只有翻山越岭在这里种些庄稼才能养家糊口,山上土厚,阳光充足,山上与山下同一天撒播的包谷种,收获时用同一升子(量器)来量,山上的要重三两,颗粒饱满,色如黄金。山上有大片的土地可供开垦和耕耘,可种黄豆、土豆和燕麦。兰花村人过得艰辛,不在耕耘,而在攀登天墀山的艰难,上下负重,是探险。有十四户人家索性搬至山上,造房,落户,耕耘自食,怡养天年,懒得下山。曾经办过学校,教室借用农户的,一个房间、一块黑板就足够了。五个年级,但只有八个学生、一个老师。老师叫谭家礼。是本地人。他每天从乐平里的另一座山上下山,然后又上天墀山,把一天的课讲完,又下天墀山回到另一座山上。天天如此,往返二十公里。八个学生,却有五个年级,有时一个一个教,像旧时的私塾,有时又围在一堆,一起讲,五个年级一起讲,这叫复式教学法。我读小学时,就有相同的经历,和其它的几个年级的同学坐在一个教室,老师一会儿讲一年级的内容,一会儿又讲二年级、三年级的知识,聪明的人,一节课能学几个年级的知识,低年级要学习高年级的困难,高年级学习低年级的等于又复习一遍。谭老师这种复式教育,我太熟悉了。当时我读一年级,老师讲一年级内容时,我们就抬起头,看着老师看着黑板,跟着老师读听老师讲,其它年级就默读自己的课本儿,老师讲二、三年级的东西时,我也盯着黑板,一位女老师持着教鞭点到我的头上,厉声说:默读自己的!教鞭是一节竹根,根结儿看起来一个连接一个,像串起来的珠子,教鞭点在黑板上,能发出咚咚的声响,看起来软软的,点在我的头上却生疼难受,不论教鞭点到哪个人头上,同学们都会条件反射,收颈缩头,双手去护。其实,教鞭真的点落在我们头上并不多,样子做得凶恶,教鞭一弹一跳的,像根弹簧,但我们还是怕,我们确实不听话,才会落到我们头上,教训一下,长点记性,踏实学习。小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位老师,喜欢用粉笔砸人,哪个同学走神儿,冷古丁地一颗粉笔头就飞过来,落到头上,让人傻傻地呆一阵子。一颗粉笔头也曾落到过我的头上,我委屈地淌了一节课的泪。谭家礼用过教鞭吗?粉笔头砸过人吗?他不会的。他慈眉善目,和和善善。我认识他,很久以前,镶着一颗银牙齿,一露笑,明净闪亮,好像月亮的光华照射大地呢。后来,我看到他又换了一嘴的新牙,玉一般光洁,银牙没有了,都整整齐齐,比真牙还要美。他写诗。活跃分子,是骚坛的一根柱子。骚坛的诗会,他没有丢过一场。老了,仍然支撑着上台。他很少走出过大山,一旦走出大山,就是治病,自己治病,家人治病。大山是他的根基,骚坛是他的舞台。谭家礼在天墀山上教学四年后,教学点要撒销,他要下山,山上的人不准走,黑板也不让搬走。直到山上人户陆续搬走,人烟全无,他才得以下山。
在山上种田,还有一大威胁是野猪。野猪是敌人,黄家刚和它们斗争过,乡亲们都和它们斗争过。
野猪像一条条野蛮的汉子,强行收获乡亲们的庄稼!比人类残忍,想吃的吃掉,不想吃的也要糟蹋掉。也比人类狡猾,尽掀高人一头的秆子,尽食个大饱满的包谷。将那些瘦弱的,掀倒、撕烂。
乡亲们心疼,愤怒。野猪从人口里夺食,人也得从野猪嘴里抢回来。
先在包谷林沿边打上桩,用藤或篾织上篱笆,栽上几个像土飞机一样的“野人”,给它们披上人类的破衣裳。野猪全然不理会这些,几脚就把它们踏烂了。乡亲们真是迂腐透了。土匪一样的野猪,篱笆和“野人”能够吓退吗?太把它们看得文明了。真人姑且不怕,还怕见风就抖得厉害的鸟野人?一眼就能识破人类的把戏。毫无顾忌地嚼食、奔跑,像是竞技场。乡亲们又买来爆竹,冷不丁放一个,管用。或者静寂的时候,突然打一阵铜锣,野猪懵懵懂懂云天雾海,急忙逃窜,回归山林歇脚。天天放爆竹,天天打铜锣,也失灵。人类的花招不能天天使用,野猪也是有些智慧的动物,不会被人类左右。过几个日子,野猪更加疯狂,怀着仇恨,像枪一样站立的包谷秆,也都悲壮倒下。
收获季节,持久战就这样拉开,野猪们夜间偷袭,乡亲们全力护卫。
家家户户在包谷地里搭起棚子,拉上电灯,打一阵瞌睡,偶尔对着包谷地吼上几句,向地里抛几块石头。有的把收音机放到地里去广播,有事没事去唱。有的拿来手电,左一下右一下地扫描。这已经是人民战争。世界是要讲究和谐的,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动物的和谐。在这里,人与野猪是不和谐的。野猪要掠夺,人们要抗争。这是针尖对麦芒的事儿?野猪是凶悍的动物,居于熊和老虎之前。人类不会轻易暴露他的凶悍,一旦惹火了,对不起,土铳、猎枪、陷阱都来对付你,三十六计统统用上。野猪是保护动物,是大自然的宠物,没有这条禁令,野猪!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乡亲们是讲和谐的,只求他们的包谷被少啃一点点。
争夺粮食的战争,常年展开。收获剩下的包谷,慢慢喂养温驯的家猪。这些包谷碾碎以后拌上饲料,一年半载就能喂养一头大猪,每家都要喂养好几头,留一两头自食,余下的抬下山卖钱,这就是零碎花销的长流水儿,所以乡亲们要和野猪计较。
持久或零星的战争,总是发生流血事件,把野猪逼疯了,它们也会孤注一掷,撵人咬人,如凶悍的土匪。人轻则伤残,重则亡命。一头野猪撵人,一位乡亲慌忙爬上树,野猪将树掀倒,狂撕乱咬,如果不是乡亲们合力营救,锄头、棍棒、石头一起上阵,这位乡亲就让野猪给咬死了。
黄家刚抓住过一头野猪,还不够壮大。野猪把他的衣裤撕烂了,咬了他一口。黄家刚死死抓住野猪脊上的鬃毛,掀倒在地,活活摁死了它。在生死面前,黄家刚只能选择打倒对方。黄家刚就凭他的拳头,暴发出他平生最大的力量。自己也没想到能把一头野猪打死。过后有种武松般的自豪。
天墀山有广阔的森林,野猪可以随便立足,进退自如,令人防不胜防。收成好,就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欠收,或者颗粒无收,就是乡亲们败下阵来。
后来,住在天墀山的人户,先后搬走,不全是因为山高路险,野猪猖獗、夺人口食,也是一个因素。
山上还有种田的人,是林场的人。天墀山林场都是兰花村里的人,一是防火护林,二是种田。场长是黄家兆。黄家兆天天着一身褪色黄衣,俨然一个转业军人,长身瘦脸,能言善辩,当场长时帅气十足,那时还没有写诗,现在是骚坛诗人。防火护林,看起来严肃,是天大的事儿,实际只要锁住重点,守护几棵成材大树,不让人偷,万事大吉。防火的事也简单,嘱咐住户和林场队员管好火种,就平安无事。黄家兆和他的队员精力都用在开垦种地上。都为自己种,收获的粮食背下山。林场是铁打的营盘,队员轮流上山,一年一换,刚好种两季。有一个人不种田,守树,叫黄相应,是黄家驹的儿子。黄家驹曾当过骚坛社长,读书多,脑子装满了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受《楚辞》影响深,擅写骚体诗。是个倔人。恃才放旷。诗的基因没有传给儿子,倔,却让他继承了,黄相应虎头虎脑,认死理儿。黄相应怕人砍那几棵成材的树,晚上睡在树旁,死心踏地。黄相应说:睡在树旁,看谁来砍!真的,山上的树没人来偷。住到天墀山上的十四户人家,都是聪明的人家。兰花村田挨田,人挤人,种田,发展,已没有空间,只有天墀山顶却有无限的地域,虽然偏居一隅,却能吃饱肚子,广种薄收,犹其在特殊的年代,真是天堂。接着天,隔着地,悠闲自在,是躲避“文化斗争”的好风水。
上山难,下山更难,从天墀山原途返回,又重复一次历险,要更加小心翼翼。
返还经过兰花村时,天晚,已近暮色,远观山梁,树木沿一道梁子参差而下,空中已没有一片树叶,树木枝干简洁,奇古憨拙,如书画家笔墨行走,这些树真是写生的好素材,线条生动,背景苍浑,能表达深刻的内容。走进时,才知是些椿树、榆树。有一棵椿树,主干高高细细,从根本拔地而起,冲向天上,看起来没有其它的椿树粗壮,但高于一切树,虽然风可以摇动,但柔韧有度,摇摆有节。喜鹊在上面做了个大窝。这个大窝十分显耀,在天墀山上观,是一颗大墨点,近处看,像个大笼子。这是喜鹊的房子,是它们从山上衔来的枝条草经搭建编织而成,喜鹊是优秀的建筑师。喜鹊选择这棵树做窝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它处在兰花村的最亮堂处,前后无遮拦,树挡不住,房子挡不住,是棵居高临下的树,飞往天墀山只需鼓十次翅膀,去屈原庙只要一个小小的俯冲,一声鸣叫,其它的喜鹊都能听清,也都明白,一枝独干,动物虫蛇窜上来,能做出迅速反应,如果树丛枝杈过多,会四面受敌。喜鹊把窝做在这棵树上觉得安全。喜鹊和人类一样,有些事不得不防,不作别人的敌人,不等于自己没有敌人。去屈原庙报喜,去乐平里家家户户报喜,也要构建好自己的安全体系,偷袭的事在自然史上和人类史上常常出现。其实这个季节最不安全,树叶全没了,窝巢成众矢之的,如果不是喜鹊的窝巢,早被冲毁了。喜鹊是鸟类的朋友,是人类喜讯的信使,它的窝巢看起来危险,实际上安全。一般来说,自然界法则是,你不威胁他人,他人自然不会威胁你。
路过兰花村,房子白白亮亮的,也有些房子颓废、剥落,人烟开始稀少,有些人搬走了。诗人徐宏章的房子也已朽坏,他到城里去了。我很想把他的房子买下来,修葺一下,来这里种兰、写诗,静下心来读读《楚辞》,好好感受屈原少年时代生活的味道。兰花村橘香仍存,如果把兰种好了,散失的馨香又会从远古飘逸而来。
又来到了徐正容的家。这是我第二次路过。他住在兰花村的边沿,在一条溪沟之畔。徐正容已作古了,去逝时九十四岁,他是骚坛诗人中活得最久长的一个人。不知道他是不是诗人中过得最惬意的一个。好多年前,村里的诗人郝大树去世,我去吊唁,回转时路过徐正容家,他正晒太阳,穿一身黄衣,坐在一把木椅上,宽大的身子把椅子挤得满满的,威武、臃肿,我的感觉,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只老虎。家里人说他年轻时高高大大,威威武武,就像房子后面的天墀山。一米九高,力大无比,是乐平里第一大汉。用徐宏章的话说,徐正容看起来像个蛮汉,是个将军身胚。我看到他时,他大概九十岁吧,神情已经木然,需大声和他说话,他方能猜测你说话的大意。当他明白我也写诗,是位文联干部,脸上有了温暖之色。人已老,但思想还在,诗歌的情怀还在。他还能走动,从屋内搬出自己线装的笔记本,是他写的诗,手工线装本儿,黄黄的纸,蓝蓝的线,全部用毛笔誊写,工整而隽永,诗集叫《归里作》,我清了清,共十八集,约两千首,这不是一个打仗的将军,是一个灵秀的诗人。我捧着他几十本诗集,一时无语,心情激荡,眼泪也淌了出来。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人,更没读过他的诗,他就一直默默生活在这里,劳动,写诗,毫无功利,不去发表,也从未在端午诗会上露面和朗读,就为了写,写自己的生活,是诗的日记,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看到哪儿写到哪儿。他的诗,悼屈原,思老伴儿,记端午、中秋和重阳,也吟月吟菊吟梅,写春日闲语,说野草碎花,诗中有自嘲自责,也有自尊自狂、自叹自慰。记的是历史的烟云,又是自己的浪花,既是经历的写照,又是社会的变化。哀怨的诗,如泣如诉,欢快的诗,又犹如歌舞,是他全部的心灵世界,也是沉甸甸的心灵史诗。他为徐正端写诗二十五首,诗中都以“端弟”相称,情真意切,可谓情同手足,我看他的诗后,一股暖流贯通我的全身:
端弟年华六十多,酸甜苦辣都尝过。
闷来月下三杯酒,愁向苍天一曲歌。
养性修身勤锻炼,延年益寿除邪魔。
乐观旷达庙堂隐,论定百旬超容哥。
老伴过逝多年了,他还在忆念她:
日出浮云散,烟消始见山。
江河依旧在,不见故人还。
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跃然纸上,也高高挺立在我的面前。他就是写身边的这些人和事,写真性情,写他的爱。写诗就是追忆往事,修炼个性,饱满人生。比起他来,我显得矮小,萎琐。我写诗,就是为发表。找编辑,找熟人,绞尽脑汁,兑些稿酬,换点名声,还为争取作品获奖煞费苦心。我也写得辛苦,却是名利的心态。看到他一尺多高的诗篇,感叹,他的心是多么纯净,而我们复杂得多,我们真的要反思,写诗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把诗集还给老人,让他好好保藏,我虽有为他整理成档案的心愿,但不能这样做,让诗集好好呆在他的身边,让诗永远活在他的心里吧,互为取暖,互为依存。这些诗,至到诗人仙逝,他的家人才送给我,我请人整成档案,将它永久传承。屈原的诗,是村子里的财富,徐正容的诗,也应当是。屈原的诗,我要读,徐正容的诗,我也要读。很多时候,我把徐正容的诗从档案室搬出来,细细品味,了解他,研究他,一个生动、性情的徐正容,一个高大的徐正容又鲜活在我面前,他就是我的父辈,让我时时忆起,让我时时想念,也常常叹息,认识他真是太晚了。
第二次路过徐正容家,只有他的孙女和孙女婿还住在这里。从他们口里,我了解了他的人生轮廓。读私塾十二年,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投诚又到解放军部队当过兵,一九五三年转业到人武部,因为他读书甚多,安排他教书。先教初中,后教小学,最后成了民办教师。别人是越混越好,他却是越混越窝囊。这都缘于他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在政治气候敏感的时代,一个人要受到公正对待很难,尤其是一个外乡人。他默默忍受一切。在自己的家乡,也遭受了一场劫难。他家里藏书甚丰,徐宏章说有八箱子书,八百斤。除“四旧”时代,工作队把他的书烧了,精装的,线装的,全烧,烧了一天。徐正容哭了一天。这都是“四旧”,是“腐蚀”人精神的坏东西。有一套康熙字典,是他用二十五担包谷换来的,工具书,也烧。徐宏章看自己的叔伯爷爷哭,也哭,看过焰火中的书,感到可惜,真想把康熙字典刨出来。
他心中从不滋生怨恨,因为他把人生格外看得透彻。既不伤春,也不悲秋。他以陶渊明为榜样,总铭记着陶渊明的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行走在世俗的大道上,又超越了世俗,一个人到了晚景,金钱富贵真的就是浮云了。一个人的一生,要懂得取舍,得失也全在取舍之间。要活得快活,就要舍去一些。“得失荣枯总在天,机关算尽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徐正容是这样想的,所以他的心里亮堂得很,不索取,不算计,顺其自然,坦然处世,给别人的爱多一点,笑靥就多一点,笑靥就是山花,会还给你芬芳。徐正容,字宽夫。宽,心宽也,宽人也。这就是徐正容。宽,就是他人生的信条。
天已模糊了,不便久坐。徐正容孙女送我到溪沟边,望着我走上“思乡桥”。他们说,“思乡桥”是爷爷捐款为乡亲们修的。一九九二年,徐正容七十七岁,他拿出积攒的六千元,又在银行贷款八百元,修了这座桥。当年,这笔钱应当是他三年的退休工资。徐正容没有请工程师,自己设计,自己督导施工,让每一分钱都发挥了最大的能量。因为他再拿不出更多的钱,能节省的尽量节省吧。这并不是很小的桥,二十来米长,八米高,我走在上面,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这座桥修得太有必要了,如果下雨,山洪瀑发,人有天大的本事,动物有飞天的功夫,也难以逾越这个山沟。桥修起后,先取名“七七”桥,以纪念自己七十七岁生日,但觉得这不好,修桥不是为表功,也不是为纪念自己,是为了方便乡亲,让人们来往自如,出行安全。便又改为“思乡桥”。修桥补路舒心事,舍己为人可树勋。乡干部徐宏章为徐正容的义举所感动,不容徐正容反对,犟着要为徐正容立一块纪念碑,亲自写了碑文,碑刚立起来,便遭人暗算,状告徐宏章,大概竖碑花的钱是公家的。徐宏章站在桥上大声向山下喊道:这碑是公家出的钱,我立定了!哪个龟孙子把我告倒了,我就回家做农民!有点骂街的气势。徐宏章破天荒骂了一次娘。
我搜遍了徐正容的诗,没有一首写到桥。我感到诧异。修桥,是他人生重要的一件事儿,应当有记述,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更没有诗体的日记,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只有徐青海的一首诗提到一句:“惠民桥畔仰高名。”徐青海的这首诗叫《徐正容先生赞》,写一个晚辈对长者的仰慕。可能是徐正容死后,徐青海写了这首动情的诗。如果在生前,徐正容不会让他写的,更不准让他提到“思乡桥”。
晚上我在“屈乡人家”小餐馆邀诗人黄家兆喝酒,请他讲讲天墀山林场的故事,他喝着啤酒,两瓶下肚,只写了一首诗:
墀山耸立天,奇险路云间。
菩萨面前过,眼皮角上旋。
看今森绿茂,问昔草荒田。
明月青松照,夕阳红艳巅。
诗人只想抒情,不愿叙事,别勉强别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