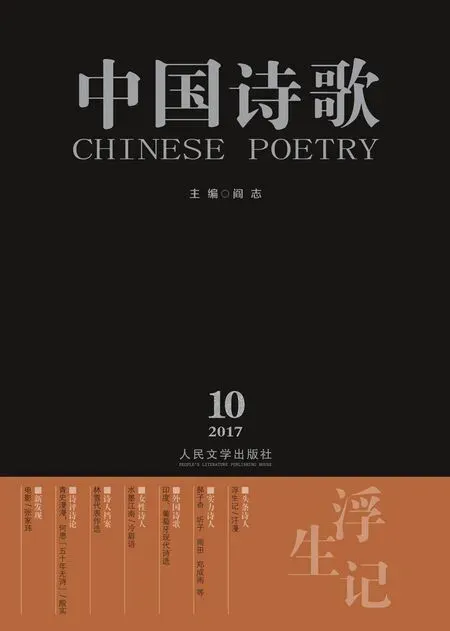羞耻与失败
□汗 漫
羞耻与失败
□汗 漫
“一个作家的源头,正是他的羞耻。”“生活失败了,就这样进入诗歌——无需天赋的支持。”罗马尼亚作家齐奥朗的观点,惊心动魄。
自少年时代开始,诗就同行同在,赐予我友情、爱、思辨力、人格、视野……而我对诗、对汉语的贡献微乎其微,因为我的“羞耻与失败”还不够卓越?中年以后,羞耻感和失败感渐渐强烈,或许有助于一个诗人形象的完成?
组诗《浮生记》是我近两年来的作品,记出游、访友、还乡、独步……是中年况味,是下午的自画像、黄昏的练习曲——浮萍流水般的人生,短暂、微弱、不安,需要以写作加固存在、抵抗流逝。
这些年,我在诗与散文之间跨界,试图使散文与诗歌这两种文体双向地滋养与纠正:“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布罗茨基),而“诗歌必须写得像散文一样好”(庞德)。
在《浮生记》这一组诗中,散文的日常性、驳杂性、及物性得以进入:意象与细节,书面语与口语,沉思与抒情,正融合为一。而日常生活入诗,对诗人是一个考验——“坐在椅子上,安静得如同一根导火线。”像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那样,必须对自己所引发的毁灭或绚烂,充满不安、不凡的预感。
当下,不少诗人仅仅是写着“导火线”字样的湿绳子,坐在论坛上、沙龙里,姿态别致而又安全,但无效。有效的写作,就是辨认出那伪装得如同礼盒一样的火药、那修饰得如同眉笔一样的火柴,去防止或者加速夜色的毁灭——让焰火在一瞬间绚烂。
有效的写作,也必须是充满差异化的、异质性的写作,才有存在价值。克服时间的单向性流逝——史蒂文斯说:“一切诗歌都是试验诗歌。”反对既定的范式,在差异化、异质性的写作中显现实验性、先锋性。当下,“实验诗”“先锋诗”似乎被特指为“某一类型”的写作,而一旦进入“某一类型”,还存在实验性、先锋性吗?实验、先锋,从来都不是个别人的标签和专利,而应是基本的写作伦理:脱胎换骨,蝉蜕蝶化,从少年写到中年、老年,越写越好——像一生不断嬗变的叶芝,像经历过蓝色时期、红色时期的毕加索。
与其他文体相比,诗歌天然具有孤身奔赴的姿态和气质。扯旗立派、呼朋唤友的“先锋”“实验”阵容,是一支可疑的军队。一个人暗夜独行、无人喝彩,方能在寂静处感知自我、辨认晨星。
“诗坛上无法浮现出令人颤抖的圣洁共识。微妙的、遥遥领悟的默契,率领不了全局。中国现代诗的此种失律现象,造成了它内部的投机、虚伪、急功近利的艺术欺骗……越过了边界的小型罪恶,积日累月,历久经年……”评论家徐敬亚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沮丧和焦虑。但我相信,诗歌拥有纠正、修复、拒斥、消毒、淘洗等等能力。相信真正的写作者之间,依然存在隐秘的“令人颤抖的圣洁共识”、“微妙的遥遥领悟的默契”,那就是:真诚与独到。
即便我的“羞耻与失败”还不够卓越,我起码可以做到拒绝投机、虚伪、急功近利,对母语保持赤子之心,而不要成为制造“小型罪恶”的人。
喜欢北宋黄庭坚的一对好句子:“谢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儿孙。”——戴虎头帽子、穿豹纹裤子,能假装成一个遗传了前贤血液的英俊后生?我把黄庭坚和李白的两个句子集在一起:“桃李春风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以汉语为酒,越代同欢,可销尽春风万古愁——一个笨拙的人,倘若能够以笔为盏,干杯,就是幸福的人了。
李白、黄庭坚之后,陆游出现了:“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历代写作者的书桌,都是停泊于书房里的船,以写作一一记取新雁的振翅、鸣叫声,对于正在加速降温的生活,有暖意,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