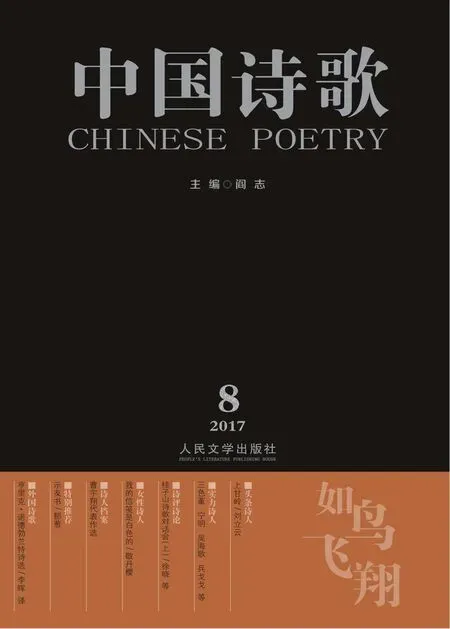语言就是思中之在
◎索耳
语言就是思中之在
◎索耳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第一次来华师参加桂子山诗歌对话会,觉得非常荣幸,也有些紧张。因为我对今天对话会的这两个命题“当下诗坛现状问题和当代大学生写作”都不甚了解,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就不敢贻笑方家了,我就跟各位分享一点个人在诗歌创作上的思考吧。
因为我受语言本体论的影响很深,所以我在语言这个问题上有比较深的聚焦点,语言就是思中之在,就是把思想所思想的存在说出来。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并不是表达知识的工具,也不是逻辑和语法结构,而是对存在的意义的直接的显现和解蔽。虽然他承认思想和语言是人的思想和语言,但是他又试图去排除人的主体性意义,从而把思想看作纯粹的思想存在的活动,从而使语言作为存在的直接显现。排除了人的主体性,将存在本身直接显现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让语言自行说话,而不是人说话。在他那里,人退居到了工具性的地位。
我觉得他的观念有部分的合理性吧,在我看来,当下的诗歌创作应该有一种AI即人工智能的精神。诗人应该破碎旧有的语言体系,从而用一种新型的更接近混沌体的本质的语言去创作。创作应该就是肢解自己,分裂自身,蹂躏语言,而不是被套路化的语言秩序所统率,沦为语言的工具,因此,我们不妨用一种机器人的眼光去重新看待我们的诗歌本态,用一种笨拙,混沌,而又充满潜质性的观念去对我们的创作进行重构。所以,我愿意写完一首诗以后,大家可以这样认为,这首诗肯定是机器人写的,那样就是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了。
无论是固化的修辞也好,翻译腔的语言和能指也好,我都不希望自己的写作会给别人一种既有的安定感。如果这样安定感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审美观感的话,那我更想走到它的反面去,和它对抗。语言的游戏应该是不安定的炸裂的,哪怕是随意,就像赫塔·米勒的拼贴诗一样,那至少也是一种尝试。不过当然,这不是鼓励随意性,任何无道理的随意的自洽性都是应该摒弃的。写作应该是挖掘和突破自身的最大可能,而不是轻易的取悦自身。语言游戏应该是像维特根斯坦说的那样,“……它们是比我们使用我们的高度复杂的日常语言的符号的方式更为简单的使用符号的方式。语言游戏是一个小孩借以开始使用语词的那些语言形式”。在他看来,语言游戏就是某种简单而初级的原生态的使用语言的方式,就是每个人小时候所采用的语言符号形式,通过观察日常语言的使用来反馈语言的本义和修缮理想语言,而不是用后天习得的语言秩序、用理想语言去统摄世界本质。这样才能使得诗歌的语言保持着陌异性和永动性。
这就是我对诗歌创作的一点微薄的想法,请各位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