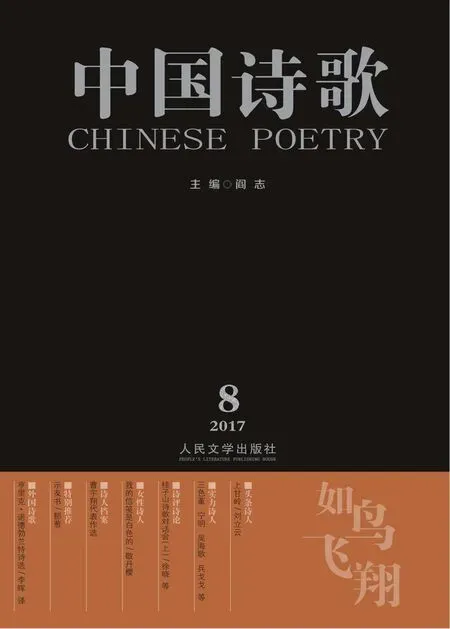诗学观点
□甘小盼/辑
诗学观点
□甘小盼/辑
●刘频认为,当下有的文本和传统的抒情诗区别不大,依然顽固地依赖隐喻、象征、暗示,不习惯脱掉这些外衣,不习惯更直接地呈现现实生活。而不少作品在叙述中让读者看到的只是鸡零狗碎、一地鸡毛,简单肤浅的书写,缺乏一种诗性的强大内核,这种平面化的写作肯定是无效的。有些诗从当下现实出发,深入人性柔软之处,这样的构架与一个人的文化视野和人文关怀有关,然而数量上令人堪忧。好的叙事,就是在文字中你不知道他是在叙事。但是,不少作品,从抒情诗向叙事性写作转身的过程中痕迹太重,喜欢饶舌,总是要从叙事中跳出来作一些抒情、议论式的旁白,缺乏客观冷静的呈现,这是一种低级的硬伤。
(《广西诗歌:从叙事中缓慢转身》,《文艺报》,2017年1月8日)
●吕进认为,诗具有公共性,诗一经公开发表,自然就成了社会产品。公共性是诗在公众社会的生存理由,也是诗的生命底线。诗一旦背对公众,公众肯定就会背对诗。从诗歌发生学来讲,从诞生起,诗就具有公共性这一特质,这是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遗传。从诗歌传统来讲,公共性是中国诗歌的民族标志。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的首要表现就是诗的公共性,就是诗人要充当时代的代言人。诗无非表达两种关怀: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两种关怀就是两种代言。对于优秀诗歌,生命关怀永远是与社会关怀相通的。诗要表达意义重大的感情,诗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个人身世中。诗人要做时代的吹号者,写出有温度、有高度的不愧于时代的篇章。
(《诗人要做时代的吹号者》,《中国艺术报》,2017年1月6日)
●海岸认为,纵观我国百年的中西诗歌译学理论,中西诗歌翻译实践基本围绕“直译”或“意译”、“格律体”或“散体”等几个方面展开,试图解决“语言形式与内容关系”这一诗歌翻译本体论主题。与其他各种翻译相比,诗歌翻译实践有其特殊性,由于诗歌语言精练繁复,比之其他形式的翻译更能集中地体现对语言技巧的理解、把握与处理。中西诗歌翻译的关键最终要落实到语言技巧处理问题上来,亦即形式与内容的协调问题;本体诗歌翻译实践讨论的焦点也集中在特定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客观地看,我国至今在诗歌语言形式技巧与内容的协调关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翻译家各人的分歧已然存在。当代诗歌翻译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分歧,都难逾越翻译者个性的制约。
(《译家之言言之凿凿——读飞白先生的〈译诗漫笔〉》,《中华读书报》,2017年1月18日)
●胡中行认为,“现代新名词和俗语俚语入古典诗词的写作,该如何把握其中的度”涉及今人写古典诗词的一个核心问题。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一味地在古典的意境和名物词汇中打转,显然是一种没出息的表现。为了保持古典诗词创作的传承性,保持古典诗词特有的韵致,对现代词语入诗词还是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如果大量使用白话系统的词汇,势必会与本属文言系统的诗词意境发生冲突,从而破坏语词和诗境的协调性。现代词语局部有序地融入古典诗词的创作,是有利于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的,但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体裁上也要有个区别对待。(
《新词俚语入诗词须有“度”》,《文汇报》,2017年3月6日)
●杜学文认为,中华传统美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审美追求。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审美方式,特别是其天人合一、和谐协调、含蓄简约、各美其美、注重内心体验、善用赋比兴手法等影响深远。首先要从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汲取滋养;其次是要从中国人的方法论中汲取滋养;最后要从中国传统审美中汲取滋养:一是艺术层面,二是生活层面,三是终极价值的艺术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方法论、审美观有着丰富的滋养,对今天的文学、诗歌等艺术创作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重建中华审美:文艺创作要更好地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太原日报》,2017年3月15日)
●横舟认为,徜徉于古典诗词营造的艺术世界,毋庸置疑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情趣和家国情怀。对酒当歌,曲水流觞,这样的审美崇尚,是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品质。古典诗词中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揭示,同样反映了古代诗人追求正义的迫切愿望。诗言志,无论是关注现实的家国情怀,还是审视内心的内心修为,古人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表达。白话文兴起以后的新诗写作,承继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方式并融合了西方自由诗的率性表达,但中国卓越的诗歌文化传统却总在人们心中荡起涟漪,掀起波澜。诗心不灭,情怀依然。
(《不灭的诗心不忘的情怀》,《检察日报》,2017年2月10日)
●孙晓娅认为,网络与微信在诗歌生产与传播方面功不可没:它们牵引诗歌走出象牙塔,拓展了诗歌的发展空间,及时解决了大众文化语境下诗歌传播、互动、反馈等问题。此外,它们面临着诸多共性问题——大众文化的渗透力强大,牵涉了艺术品质的走向,干扰诗歌的自我定位,在大众视域中,诗歌创作的精义难免随之流转,并充斥着喧嚣的游戏精神和娱乐趣味。物质与精神的垃圾是现代社会进程的必然产物,在新媒介的更迭之中这更是无可躲避的问题。那么在必然性面前,当代汉语诗歌建设最大的挑战在哪里?作为诗歌研究者,需要我们着力反思的是什么?诚然,诗歌终归要靠文本自身去说话,文本自身的操纵力胜过任何外界因素。
(《新媒介与中国新诗的发展空间》,《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
●蒋林欣认为,针对当下诗歌的主要症候,诗人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宁静致远的文学理想。高远的文学理想与宁静致远的心态决定了艺术的生命,理想的缺失与心态的浮躁正是当下诗歌弊病的根源。二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当下喧哗与骚动的时代,一切追求短、平、快,文艺创作也不例外,粗制滥造,生产大量伪劣产品。三是温润如玉的人文情怀。在诗歌写什么的问题上,很多人既不关心历史,也不关注当下社会,而是将个人感觉神圣化,切断个人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一切联系,使诗歌通向极端的梦呓和欲望宣泄,沉溺于世俗化的日常琐碎,创作态度游戏化,作品平面化。四是勇于创新的现代体验。
(《文化诗学视阈里的现代抒情长诗——龚学敏的诗学实践及当下意义》,《当代文坛》,2017年第1期)
●陈世明认为,诗有空灵之美,能显示出空间的无限和时间的无极,同时意蕴深邃浑厚,衔旨遥远无定。研究诗的空灵美,有两点尤须注意。一是诗人气质,二是艺术处理。当代的诗歌创作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太实,一是太空。一派主张写生活,却只是罗列一些生活表象,给人一种淤塞感。一派主张强化人的主体精神,主张写摆脱群体意识的个人的纯主观感念和自我心灵的开掘。面对时下诗坛这一“实”一“空”之流弊,两派诸君应结合起来,相互拿来一点。客体派诗人,要空灵一点,少写一点;主体派诗人,应实在一点,多写一点。基于此,“太似则泥实,不似则欺世”,当视为诗之空灵的审美原则。
(《论空灵与诗美》,《写作》,2017年第1期)
●张翼认为,中国现代散文诗是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影响而在新文学土壤里诞生并发展起来的新生文体,但它在百年发展进程中始终摆脱不了面孔“模糊”的命运。对文类的划分或定义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和创作,在应用上不至为不同的称呼或定义而争论不休。我们不必急于为“散文诗”文体划定清晰的类型边界线,也无需贴上固定的本质化的文类标签,而是要深入到丰富的文本中去感受散文诗“混血”的魅力,领略它在不同文类边界间自由游走的活力,享受这个新文体包含不同文类特性而给予的新奇而熟知的阅读感受。各文体间相互渗透、融合,同时也互相竞争,使其在演进中不断有来自各方面的源头活水乃至挑战,才能推动一代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历史文体学视域中散文诗的文类归属与界说》,《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1期)
●马冬莉认为,四川卫视《诗歌之王》的成功,走出了一条以流行歌曲拯救诗歌之路。具体表现为:1.追本溯源的诗歌创作之路。首先,追本溯源的诗歌创作是指诗歌创作所需要的题材均来自于现实的生活;其次,还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对传统诗歌创作技巧的继承上。2.返璞归真的诗歌传播之途——诗歌与音乐、舞蹈的结合。3.文化精髓的诗歌再现之旅。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担负着传承传统文化精髓的重任,既包括对传统价值观的形象再现,也包括对传统语言词汇的继承。4.继承创新的文化之轨。在诗歌这种文体里,古今的继承与创新可以表现在多个层面。
(《〈诗歌之王〉:对流行歌曲拯救诗歌的解析》,《当代电视》,2017年第1期)
●洛夫认为,一个重要诗人(或所谓的大诗人)必须具备三个层次的境界,一是美学层次,二是哲学层次,三是宗教层次。美学层次是基础,哲学层次是思想内核,宗教层次是峰顶,是对前二者的超越。然而,一个优秀的诗人不甘于停滞在某个单一层面上,而且也不只会突出某个向度,他创作的应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构成,既非只有哲学,也不是只有宗教,而是一个浑成的艺术品。对于诗歌创作与书法写作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以书法写新诗是一项新的艺术追求,一种诗歌的新表现形式的探索,可称之为“由书法过渡到诗歌的另类形式”。希望通过书法把诗提升到水墨艺术的层次,使两种不同形式的美作有机的结合而化为一个更丰富的二元融合的宇宙。
(《作家声音》,《文学教育》,2017年第2期)
●唐珂认为,“诗性”的语言除了因为经常被限制在固定的形态之中而为人所识之外,它的特征从根本上说还是言说本身的话语行为重于言说的信息,诗语言更侧重于指涉自身而非指引外部现实世界,诗的属性在于特定文类/语用场所的话语所凸显的修辞功能和修辞效果。旧体诗的意象、用典、意境,归根结底源自文本在千百年传统积淀中形成的、承载于语词的文化类属性和特殊性,借助认知空间的整合,使词典义背后的深层复义及语用意义得以表达。
(《语言符号学视域下的“诗性”与“散文性”——以中国诗歌古今演变之际的苏曼殊创作为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沙鸥认为,与上世纪五十年代诗歌批评精神相承的是,强调诗歌的时代政治性:诗人的主体“不能不留下时代的、社会的烙印”。然而现在诗不能作为“照像机、素描画”,诗要真实地表现诗人“主体的丰富性复杂性”。问题是诗人如何处理“时代的、社会的烙印”和“诗人主体的丰富性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当写作的天平倾向于“时代的和社会的”时候,诗歌的面貌往往成了时代和社会的注脚;而倾向于“主体的丰富性复杂性”时,诗歌的质性往往显为内心和感觉的凝结。不但一部中国诗歌史,甚至整部世界诗歌史,也许都是在这个矛盾中跌宕前行。“好诗应具有七个要素:立意深,构思巧,形象美,感情真,意境浓,语言新,手法奇。”
(《主体的消失与政治的霸权——沙鸥的诗歌批评》,《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2月)
●郑立峰认为,新诗在新世纪发展“民间化”倾向加剧。新诗民间化发展,是极具寓言意味的形式。民间诗人们就是在生活中发现诗意,为生活谱写诗歌。“生活即是诗”这就确定了他们的创作的诗歌的基本走向——用日常口语来谱写生活的诗歌。而且他们似乎对“口语化”诗歌有着某些天然接近。因而诗歌要回归,回归生活,回归本土,回到原生的状态。并且,诗歌是诗人生命熔炉的瞬间的显示,并达到包容人类整体生存的高度。生命的担待与命运关怀意味着生命尽管纯粹,其血缘依旧维系在当下深刻的矛盾根部。
(《〈漆〉:夜空亮丽无比》,《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2月)
●冯骥才认为,诗的小众化在世界上已是共同面临的问题。许多曾经产生过诗神诗圣的国家,诗也在被公众淡漠。有人说,诗的消退是因为这种文学方式不适于当代人的需要,还说这种文学体裁早已度过盛年,走向衰老,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其实,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心灵上——在市场时代里,消费方式异化着消费者,商业文化也在把我们商业化、浅薄化、粗鄙化。这样,诗一定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在所有文学样式中,诗是最不具有消费价值的。因为诗首先是精神的,精神愈纯粹,诗愈响亮。诗是情感的,情感愈真纯,诗愈打动人。诗还是敏感的、沉静的、深邃的、唯美的、才情的。如果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一定会失掉与它相关的那些东西。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没有诗》,诗评媒微信公众号,2017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