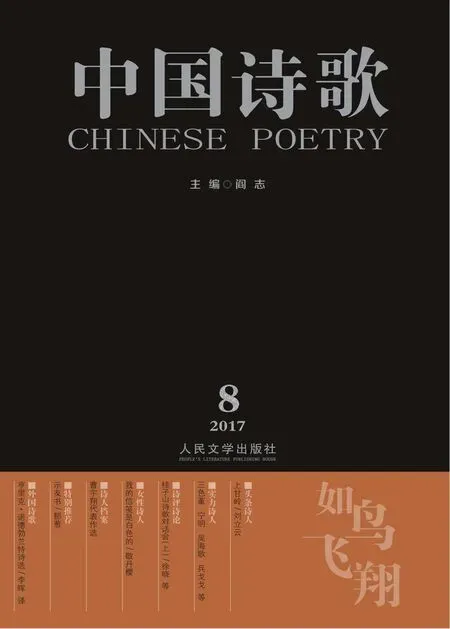诗歌、多元化与重新发现生活
——一句话的分行所引发的思考
◎敖 翔
诗歌、多元化与重新发现生活——一句话的分行所引发的思考
◎敖 翔
在正式进入话题之前,我想先引用好友向尧描绘武汉白沙洲的一句话:“以为是对岸。其实是/江中小岛”。向尧写诗,但这句话却只是他发布在微信朋友圈里的一小段描写,似乎没有用到任何修辞,看似平淡无奇。不过,他没有将这句话以日常语句的线性模式展现,而采用了分行手法;同时,他也没有按照常规语法将两个分句分列两行,而是将第二个分句切开,将第一个分句和第二个分句的前三个字“其实是”并列一行,第二个分句的“江中小岛”则另起一行:
以为是对岸。其实是
江中小岛
如此,原本普通的一句话便获得了诗的效果,稍后我也会专门谈论分行。言归正传,这次演讲会的主题与大学生诗歌创作有关,但我想暂且将写作放到一边,先谈谈阅读。一首诗惟有被读者阅读才算真正被完成,且这种“完成”一直是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因此,诗歌阅读的意义丝毫不亚于诗歌创作的意义。甚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阅读可能更为重要:几乎所有文体的写作技艺都来自于阅读经验(写作内容则来自于生活经验),而文学作品写作的目的也大抵是为了被阅读。但据我对周围人群阅读状况的粗浅了解来看,大学生的诗歌阅读在总体上可能存在单一化的问题:首先,不少同学的诗歌阅读仍以中国旧体诗词为主;其次,就新诗阅读而言,也往往局限于文学史上名声显赫的几位“代表性”诗人,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穆旦、北岛、顾城、舒婷、海子等;其三,对“代表性”诗人作品的阅读,也常停留在几首代表性作品(往往是中学课文和大学文学史教材中出现过的作品)上,如《凤凰涅 》之于郭沫若,《再别康桥》之于徐志摩,《雨巷》之于戴望舒,《赞美》之于穆旦,《回答》之于北岛,《一代人》之于顾城,《致橡树》之于舒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于海子等。此外,更多人可能根本不读诗。
第一个问题想必大家都深有体会。无论是大学生群体,还是其他读者,谈到中国诗,多数人可能更容易联想到旧体诗词,而非新诗。固然,相比数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新诗的百年历史实在太过短暂,也自然可能因此稍显稚嫩。但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人们往往容易以旧体诗词的标准来看待新诗。根据旧体诗词尤其是近体诗的标准,有些读者大概会认为,诗歌虽然不必严格讲究平仄,但必须押韵,必须具有较为整饬的句式。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诗观,但可能失之于机械。诗歌作为一门艺术,自然需要以特殊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习惯旧体诗词的读者经常将新诗戏称为“分行的散文”,但他们大概忽略了,“分行”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如果按照常规语法将一句话的两个分句分为两行,的确与散文的分段类似,难以获得诗意;但倘若打破语法规则进行分行,或许就完成了一次对日常语言的反叛,同时也是一次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反叛”。回到演讲开头所引用的两句话,友人反语法的分行,正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他让“江中小岛”独列一行,使之成为了一个内涵丰富的独立意象,从而激发着读者的无限遐想。也许我们会联想到一个画面:放眼望去,仿佛望到了江对岸,仔细观察后,却发现其实只是江中小岛;也许我们会思索到一种哲理:当我们以为已经认识到彼岸世界的真理时,其实仍然行走在探索真理的途中。但无论是感性联想还是理性思索,都来自于一个体验性的意象——“江中小岛”,这意味着诗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直觉式体验,而非理智式认知,这也许正是诗歌与散文的根本区别所在。而相比旧体诗词的“格律”,作为新诗形式的“分行”也更为多样化,往往没有确定、统一的规范,不同诗人可以选择不同处理方式。
除去分行外,新诗的其他修辞方式(如隐喻、通感、比拟、陌生化等)也同样具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当然,旧体诗词也不乏个性化的艺术手法,但从总体上看,旧体诗词尤其是传统格律诗(如近体诗和词),往往具有一种标准化、规约性的艺术形式(当然,古代卓越的诗人通常可以突破格律的束缚,如李白、苏轼等,再如“拗体诗”也是一种对既有格律的反叛),相较而言,新诗的艺术形式则具有更为鲜明的个性化和反叛性的特征。而就古典诗歌本身而言,它也具有多种传统,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南朝永明体、唐朝近体诗再到宋词元曲,其发展历程便充满变化;五言、七言、杂言,“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太康诗风”,“盛唐之音”,“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宋诗),其文体特征和美学追求本来便具有多元化趋向。将古典诗歌和诗歌本身机械理解为一种格律化文学体裁,本就是对文学多元化事实的违背。上述其他两个问题,其弊病也同样在于单一化:对新诗和诗人的认识单一化、平面化,缺乏更为丰富、深入的理解。故而,我们需要更为多样的诗歌创作和更为广博的诗歌阅读,从而创造一个丰富多姿的诗歌世界。
实际上,诗歌创作必将趋向多元化,甚至同一诗歌流派,都会有多种不同倾向。德国学者胡戈·弗里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里总结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两个不同倾向:一为兰波,其抒情诗形式自由,非逻辑;一为马拉美,其抒情诗形式严整,讲究智性。他们也由此开创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两大传统,而后又衍生出无数小传统。就我校学生创作情况来看,阿海、白天伟、向尧、张朗、北北等亦各自有其独特的美学追求。不同诗人有不同的美学追求,其中,卓越的诗人往往敢于尝试不同风格,而优秀的读者也会懂得欣赏不同风格的诗歌。不同类型的诗歌也具有相应的各类不同欣赏方式。有些诗歌富于音乐性,适合“听”,如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等,这类诗往往由于适合朗诵而广为流传(相较《雨巷》,戴望舒另一首杰作《我的记忆》则可能因其音乐性较弱,不适于传诵,故而不为一般读者熟知);有些诗歌则颇具画面感,适合“观”,古代山水诗多是如此,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谢灵运《过始宁墅》),“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谢 《游东田》),“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王维《送邢桂州》),“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等,新诗中亦不乏如画之诗,如顾城的《初夏》,描绘初夏宁静的村庄,“所有早起的小女孩/都会到田野上去/去采春天留下的/红樱桃/并且微笑”,再如李元胜的《青龙湖的黄昏》,“空气是波浪形的,山在奔涌/树的碎片砸来,我们站立的阳台/仿佛大海中的礁石/衣服成了翅膀”;还有些诗歌尽管可能缺乏音乐美和绘画美,却敏锐捕捉到了生活的微妙,适合“思”,如韩东《细节》,不经意间,一个路人的个子和动作被诗人记住,“那个路过的人出现在你的谈话中/那么的无关、无辜/毫不知情/却被我们记住了”,再如宇向《圣洁的一面》,一些想飞进飞出的苍蝇撞在玻璃上,诗人由此联想到“我的生活和这些苍蝇的生活没有多大区别/我一直幻想朝向圣洁的一面”。
方才我强调诗歌创作和诗歌阅读都应趋向“多元化”,但“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杂乱无章。目前似乎并不缺乏诗歌创作者,但似乎也因而导致“诗人”严重贬值,甚至在某些语境中“诗人”之称沦为了贬义的谑称。究其原因,或是因为不少创作者写诗太过随意,不经精心构思,便下笔作“诗”,然而所作往往是肤浅粗糙的“打油诗”。作为一种怡情遣兴的手段,这类“随性”的创作无可厚非,但对于真正的诗歌爱好者而言,却无疑需要通过广泛阅读优秀诗歌来建立健康的审美观,从而提高艺术感悟力与创作能力。所谓“健康”的审美观并无统一标准,它也应是多元的,但必须体现着创作者对语言文字的敬畏,并必须显现着诗人细腻、敏感而热忱的诗心。这里,需要说明“权威”与“多元”的关系。“权威”并不都坏,相反,人的成长与事物的发展都需要良性权威的引导,诗歌亦不例外。美籍德裔犹太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将“权威”分为两种,一种为“合理性权威”,以引导为目的,即尊重他者个性并引导其全面发展,最终使“权威”自然而然地消解,趋向多元;另一种为“抑制性权威”,以压抑为目的,即压抑他者个性并阻碍其全面发展,最终导致一元绝对主导,陷入自我膨胀和自我封闭的危险境地。读者需要“合理性权威”的引导,需要诗歌批评家或文学教育者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优秀的诗歌。在坚持多元化的前提下,引导读者从浩瀚诗海中辨别真正优秀的诗作,进而从中汲取营养,逐步发展出个人风格,大概正是诗歌批评家和文学教育者的责任所在。同时,也需要警惕“抑制性权威”——任何优秀作品的意义都在于引导后辈写作出更为优秀的作品,而不应束缚后辈的想象力,使他们在模仿中止步不前。
最后,我想简要谈论个人对于诗歌的认识。还要回到开始时那两句描写的分行,在这种“反语法”的分行中,我们重新发现了语言,也重新发现了生活。在我看来,诗歌不是艺术性的发明,而是对生活的重新发现,且往往是瞬间性的发现。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在于可以在庸常生活中发现不凡诗意:他们往往在一瞬之间,借助直觉顿悟,从而与诗歌邂逅。因此,写诗绝非刻意捏造,而是诗人与诗的自然相遇。旅行归来,我们回到书桌,展开一张白纸,或打开电脑的word文档,准备动笔写游记,却久久不知从何下手,这是我们生活中容易遇到的寻常情境。但在诗人韩东笔下,白纸和雪亮的显示屏却被比作“积雪覆盖在高山之上/等待霞光的映染”,随后诗人又写“他就那么宁静/压抑着下面的荒草/怪石”。这正如我们写作前感触满腹又难以道明的感觉。写诗自然少不了语言,但诗歌的语言应该是开启生活之门的钥匙,而不应是锁闭自我之门的锁。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在《三个最奇怪的词》中展现了语言的神奇:
当我说“未来”这个词,
第一音方出即成过去。
当我说“寂静”这个词,
我打破了它。
当我说“无”这个词,
我在无中生有。
(陈黎、张芬龄译)
这里,“未来”、“寂静”和“无”这三个词语已与生活本身发生联系,趋向充实,而不再是虚空能指。作者所描写的其实也已非三个词语的能指本身,而是说出三次词语的行为。言说本身,本就是一种生活体验。
诗歌通过语言重新发现了生活,也通过语言重新发现了自我。“重新发现”正是诗歌特有的思维方式——通过直觉体验生活,获得顿悟,又将这种顿悟交还给生活,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言:“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语言,则是沟通自我和生活的桥梁。因而,“重新发现”实际上也是自我与生活不断交流的过程。当诗歌重新发现了生活以后,自我不仅仅是孤立的自我,生活也不仅仅是原本的生活,这时,生活与自我已水乳交融、物我为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诗歌很小又很大——小巧如一株野花,又博大如整个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