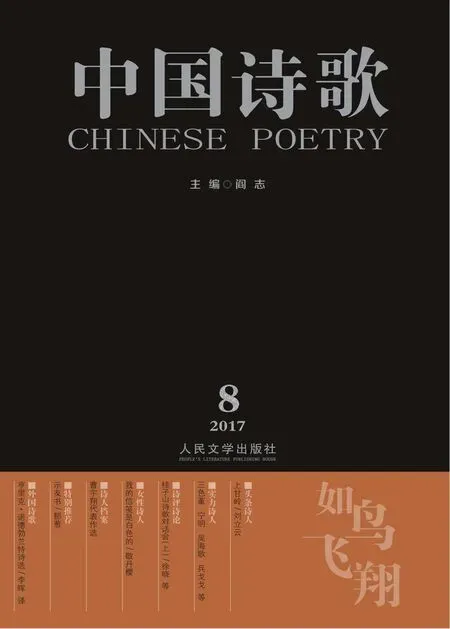结束处往往意味着新的开始
◎苏宥时
结束处往往意味着新的开始
◎苏宥时
为新诗正名的时机在过程中潜伏
1918年《新青年》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九首新诗,正式宣告新诗乘着时代潮流的东风应运而生。但因其白话文的体式,从诞生之初便被置于同正统地位的古典诗歌几乎二元对立的一边。换言之,新诗的初始面貌是被“抛掷”到了汉语语境中而“横空出世”,这样的情形就像一介匹夫试图跟皇子分庭抗礼,家世显赫又养尊处优的皇子当然不会成全这样的野心,于是便造成了此后延续不变的尴尬局面。事实上新诗也确然存在让人诟病的话柄,比如我最近着手深入研究徐志摩诗歌的前后分期,就发现奉行英美自由主义的徐志摩也难逃这样的窘境:典型如《再别康桥》这样的代表作,追根究底也仅有最后一句足以让人叹其绝妙;其他不太知名的诗作,可圈可点之处就更为匮乏。更严重的怀疑在于,他的诗中有许多从西方诗歌“搬运”过来的意象或写法,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把西方诗歌中成功的例子以汉语书写的方式“复制粘贴”了一次。其实这也算不得“不光彩”的事情,因为借鉴是实现提升的一个有效途径,尤其是在新诗起步的当时。然而新诗要想独立地存在、健康地发展,面临的处境便不会那么简单。
在这百年的进程中,有一个时间点非常有见证意义,那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诗歌与中国诗人曾处于舆论和社会关注的中心。但紧随其后的,消费转型与欲望扩张,对国人造成价值选择上的消解,严肃文学受到强烈冲击,诗歌与诗人的地位,从被众星捧月般地环绕在舞台的中央,一下子又为众星所排挤、抛掷到舞台的边缘。柏拉图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预言一语成谶,现实中的诗人们被主流社会“放逐”,日渐与“底层化”、“边缘化”这样的词汇相伴为伍——这样一个“边缘化”的进程却是使动的、被迫的,充满无奈。然而两方抗衡,实力悬殊,社会的大多数结成一股强大的异己力量,诗人便沦为孤独而可怜的少数,在黄昏时、在黑夜里,数着自己的星星,把呼声肢解为沉默。
谈到新诗诞生的原因和使命,概括性的表述便是“对时代新精神的响应”。施蛰存在三十年代就说过,新诗是现代人的新诗,免不了也包含了现代文明的一切在内,但这还不是它的本质上的新。在本质上,新诗之新是其情绪之新。它应该是“道前人之所未道,步前人之所未步”。忙迫、变化、速率、噪音、丑恶、恐怖、不安定、不宁静,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的经验不同于前一二个世纪,生活愈加复杂,情绪就愈更微妙。可见新诗的诞生和发展,都是历史的客观助产。存在即合理,尽管有着不少悬而未决的疑问,但没有一种文学体式是绝对完美的,同样也没人能够推翻新诗存在的根基。当代人要有自己的情绪载体,而新诗正是合乎时宜的一个得力工具。
不论新诗诗人如何自信自足,新诗至今仍是副产品般谦卑地存在,或被视为非主流文类。新诗的边缘化一方面归根于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自身建设也难逃其咎,这一点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中会交叉讨论。新诗不遵格律、门槛过低、鱼龙混杂,大概也会被视作先天缺陷。而最近北岛等诗人在豆瓣上推出了《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课》,以及“为你读诗”、“朗读者”等节目的热播,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手段,新诗脱下礼帽和衬衫,换上平易近人的T恤,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这似乎表明:沉默已久的新诗终于肯为自己发声。新诗曾一度想要争夺文学殿堂的圣杯,如今又换了种姿态,这一自上而下的路径也许是好的;在理想贫血的当下,也许是一剂唤醒浪漫意识和人文春风的良药。
有比照就必须提供参照系。我们之所以能对古典诗歌盖棺定论,是因为时过境迁,今人再难制造出当时语境、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我们不需要用试图在古诗词上超越古人来证明自己的不服输精神,因为新诗是我们的语言,即使它目前还没有古诗词的积淀或所谓成就。作为新诗的写作者,我当然希望为新诗正名的那天尽早来到,但理性告诉我:为新诗正名,可能永远是个进行时的过程。
新诗的审美尺度:私人话语的上升空间
凭我自身的写作经验,我有个习惯就是经常回头看自己以前写的诗,做自己的头一号读者,这时就会发现先前的诗歌良莠不齐,有的耐读,回顾两三次也觉得还不错,有些则不然,回顾第一次就觉得烂。那么“好”与“坏”究竟处在怎样的分野呢?我自问评判高低优劣的标准,却无果。肇事者通常是用直觉,但这要求读者的审美修养到达了一定的水准,否则直觉会时常害人犯错。而培养大多数人的文学嗅觉,是另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如果说当年新诗发展尚不成熟,重要原因是白话文还没有“崛起”,我们的新汉语还处于婴孩期,那么在白话文运动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直至普通话在全国大规模普及的今日,已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要给新诗进行一次笼统的分期,我认为分为早期的“白话诗”和后来的“现代诗”就足以明了。当今的诗人们已然能将现代汉语应用自如。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被悄然置换成新诗审美尺度的选择。
按照尼采的说法,人是美的尺度,也确然如此。诗歌从笔下分娩之时诗人便已死去,我很赞同巴赫金的观点。我想以“美”的生产者为本体出发探讨新诗审美尺度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一条线索是:私人话语的膨胀增加了审美的困难。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新诗写作的私人化程度明显增强,被读懂、被接受的难易程度以及读者的反馈似乎已不列入诗人的考虑范围内,这就很容易造成“写作——传播——接受”链条的断裂。回顾曾经拥有大量读者的朦胧诗,经历了八十年代初期的黄金时代,之后因部分诗文本中意象系统过度密集庞杂,充斥虚假玄思,联想随意牵强,导致作品由朦胧走向晦涩,遭到读者的反感和拒绝。许多过去红极一时的朦胧诗人开始少写诗或不再写诗,朦胧诗写作群体逐渐走向解体。这或应当成为当代诗人进行选择之前需要思考的一个前车之鉴。
从去年下半年接触到余秀华的诗歌,就对她产生了较大的兴趣,这主要基于我对她印象的反转——从未读其诗先闻其名的些许“反感”,到细读其诗竟有点陪她一起大哭一起大笑的“冲动”。余秀华从文学的背面出发,用乡野、酒瓶和残缺构成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她练习着同生活的拉锯,用手中的笔试探生命的极限。她克制内心蛰伏的爱火喷薄欲出的强烈,又以淡淡的感伤回避着声泪俱下的低级诉苦。我关注她的时间也不久,读过两本诗集,平时有空逛一逛她的公众号,遗憾发现她近期的诗歌也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似乎有点不进则退的倾向……这些且先不论,我觉得从她身上还是得到启示更多,一是作为一个诗人,最大的幸福是直接面对诗说话,但现在我们和诗之间隔着太多的阻碍,时代、资本、评奖等等总是企图蒙蔽我们远眺的目光。故而不忘初心,是成为真正诗人、写出优质诗歌的首项必修课。二是一成不变的创作势必阻碍前进的脚步,新诗写作最好加入点游戏精神,或及时开始某些探索性的实验。反复言一种情,尤其以同样的声音、语调去表达内核相同的观点,只会给自己、给读者造成味同嚼蜡的没劲。
据一些批评家的看法,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在直线增强——诗人直面个体真实的生命体验,以接近口语的语言表达方式,综合运用各种叙事手法,复现人们的日常现实生活场景、具体生存状况和个人独特心理。这样的诗歌观念和写作方法固然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还可优化诗人心理结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新生代诗人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把叙事性引入作品,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李亚伟的《中文系》、《生活》等等,已经呈现出使用口语、讲述生活以及反讽的特点。随着时间之轴的不停转动,“真理”之曙光日益明晰,许多诗人加入反思讨论后毅然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幻觉下赞歌式的抒写,而走向了以叙事手法表现个人经验的道路。叙事性是一种形式,而个人经验的输入、私人话语的生成始终占据核心。私人话语的上升空间究竟有多大?是否存在一个屋顶式的阻碍,来预判私人化写作的价值?我联想到北岛的《迷途》一诗,直至近年才被人了解其中的真相是纪念妹妹的溺水事件。但假如当年人们知悉了这一事实,这首诗便会因视角的狭隘而轻易被宏大叙事的主流偏好所淘汰。如今的时代更开放、更自由,诗人也逐步从群体性创作中脱离出来,为自己言说,这是否意味着私人话语的上升空间直指无限呢?不然。诗人要有个性,但又不能过分自信。假如一首诗里全是自言自语的叨叨念,无法唤起共鸣,无法引发加斯东诗学理论中所提出的“回响”——这也是不尊重读者、蔑视他人的表现。更危险的是,在叙事性诗歌的私人话语中也出现了随意化、过度化的迹象,如恶叙事、身体叙事、简单叙事、口水叙事等的滥用,无疑偏离了诗歌的本质,以无辜的“新诗”之名为恶俗趣味的滋生提供土壤,进而破坏诗歌生态,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的影响绝对是弊大于利的。
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我也发现:消沉和声张都是语词的病态。无人为你的颓废埋单,也无人因你的跋扈喝彩。语言和文字并不负有将心绪精准传达的义务。过于简洁会显得浅白平庸,过于繁琐则又陷入奇淫巧技的旋涡,这是一个无定形的尺度,天平的任何一边倾斜太多无异于矫枉过正,都会引发危险。我想探求一个调和的写法。新诗的自由是补偿个性的缺席,但信马由缰会摧毁新诗的自塑之路。不论是追求自我抒写的目的,还是强调现实关照的渗透,都应意识到瞬间的审美愉悦是暂时的,价值诉求所传递的信息才是长久的。一旦新诗中没有注入价值关怀,无异于灵魂缺失的状态,形式再出众,也是经不起历史之海遴选而在岸边曝光而死的空壳。这也就是,不论一首诗的写作初衷如何,最好还是有智性的参与。我们要的是诗,不是分行的句子。私人话语本身并无有害的天性,如果诗人能够做到“以个人生活的点带出时代的面,寓意式地反映出了一个时代人们心灵的变迁,对现实生活的荒诞进行探寻,对个人生活中折射出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深度追问”,就是成功的。
不断地否定,不断地开创,才会产生螺旋上升的连锁反应。有些人认为,海子的死标志着新诗写作在农业文明审美意象的终结,而顾城则以更加残忍的方式结束了中国新诗的自然审美意象,然而这些“结束”并没有驱使新诗走向早夭的结局,相反,结束处往往意味着新的开始,如今新诗发展的态势更加多元化。“文学和诗歌永远不可能单纯,它们是文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我认为新诗的发展不需要立法者,只需要探索者。或许诗歌审美的无定态和多重性特质正是新诗趣味之所在,我们不要戴着镣铐跳舞。这是一项历史的任务,它的完成最好是交给时间。
加斯东·巴什拉的诗学著作里有一条我很喜欢的形容,他说“诗歌形象是心理形象中突然出现的异常”,尽管这一观点牵涉到现象学和心理学,但它的意旨是简明的。我认为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具创造性的,因为它强调字数的有限性,要求诗人具备水平较高的浓缩和炼字能力。而这一特点又恰好跟当今高速的生活节奏、碎片化的阅读习惯相契合。同样的还有意象的新奇性和情感的爆发性。诗歌在短短的篇幅里包藏着水一样的张力同时孕育着黑洞般的引力。最近在读张枣的诗,感慨于他的英年早逝无疑使当代诗坛痛失一枚精致而硕大的玉石。在写作工序上,他独特的技法令人叹为观止——把古典的、唯美主义的词汇巧妙而精准地降落在深受西洋眼光熏制过的语境中。因此他的诗不论在节奏上,还是弹性上,都极具匠人式高超的表现力。
武汉的空气很浮躁,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感觉静下心来写点深刻的东西,还是有难度的,也可能是自己尚年轻,感知力也有限,但是当我触碰到诗,诗便主动迎上来,为我打开一扇门,它说:这里有一片未知的世界,你是你自己的引路人。欢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