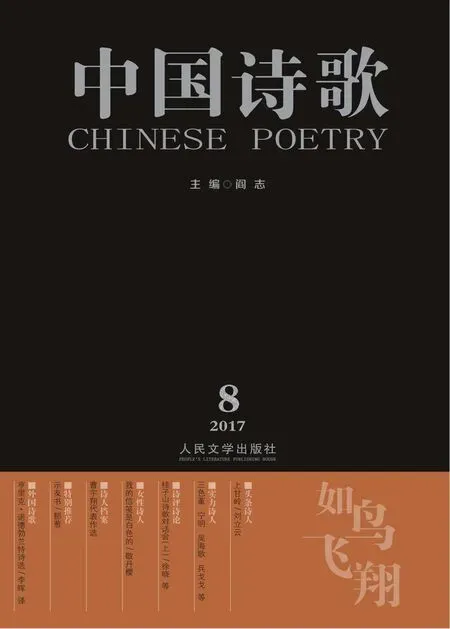关于诗歌的几个想法
◎庄 河
关于诗歌的几个想法
◎庄 河
存在的诗人
“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就这样掉进了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的一个漂亮的、几乎神奇的叫法‘对存在的遗忘’那样一种状态之中。”今天,当我们开始努力追寻,奋力为白话诗歌拟一条“再出发”的路径时,也许越是急迫,越是意味着我们开始慌张了。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在今天诗歌失落了。海子的时代成为了神圣殿堂遥不可及的梦幻。我们越是精准地了解诗歌,掌握的关于诗歌的知识越多,我们就越盲目。世界、自我与生活,诗歌在这些存在当中退场了,或者说诗歌遗忘了这些存在。诗歌的写作仍在继续,但诗人们不再仰望星空,而是闭着眼睛低头行走。
白话诗歌的写作自胡适先生开始,此后,关于诗歌的韵律、语言、修辞、形式等的论争,百年来此起彼伏。但似乎对一个近乎浅薄的问题,我们遗忘了。那就是为什么写作诗歌?昆德拉曾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据此也许对写作诗歌可以给出这样一个轮廓:发现惟有诗歌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诗歌惟一的存在理由。
因为有这样一种东西,是只有诗歌才能发现的,因此诗歌存在,因此我们写作诗歌。正是诗人,也只有诗人才能够实现这种发现。同时,正是这种实现确证了诗人作为个体的文学身份,而非社会身份。(个体的存在通过多重身份来完成,其中包含文学身份、伦理身份,法律身份、职业身份等。)
一种身份的确证,是一种可能性的确认,一种合理性的表达。百年前先辈们确证白话诗歌的合理性,是为白话这样一种语言形式的诗歌发生做一个辩争。今天我们确证诗人的文学身份,是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在不自觉的“对存在的遗忘”状态下,在诗歌与现实与自我的对抗之中开始的。每一种身份的发生,都是在排他性的限度中建立的,诗歌也不例外。
诗人的文学身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我只能就这一问题所延展的边缘来谈。在这种身份延展出的众多脉络中,以写作作为接近诗歌的触点。并且,最需要注意到的是,诗歌的发生绝不依靠谈论,而是具有的无限意义的写作。写作才是实现诗歌发现那惟一的,并只能由诗歌来发现的东西的惟一途径。以诗的方式接触自我、人生、世界,实现诗歌在各个方面的扩张,是今天的诗人们可能要做的。
变奏的艺术
在描述轻与重时,贡布罗维奇有一个既荒唐又天才的想法。他说,我们每个人自我的重量取决于地球上人口的数量。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轻与重的变化涉及诗歌的一种变奏。它也可以被称为节奏或者韵律,但变奏这一词汇不仅包括诗歌的诵读因素,同时也包含诵读这一再创造过程。这就好像是戏剧,剧作家的文本创作完成之后,必得有导演、演员、观众等的介入,戏剧才具有某种完成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完成是短暂的、不可复制的、持续更新的。与戏剧艺术相类似,诗歌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状况。
诗歌这一艺术形式自诞生以来,便与诵读存在着先天的联系。每一位诵读者对诗歌的理解都是不同的,侧重也有所不同,甚至诵读与诵读者的学识、修养、经历、情感、时代等因素都有直接的关系。这同样是不可复制的、短暂的、持续更新的。在舞台上或者交流中,诵读的发生都带有变奏的性质。变奏,是米兰·昆德拉在剧作《雅克和他的主人》中提出的。这是昆德拉以戏剧的形式,对狄德罗的小说《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这部小说进行的“变奏”。戏剧在内容、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了小说,但实现了昆德拉对小说提炼出的“理性”内核的再表达。
就诵读本身便是一种艺术形式而言,诵读是诵读者对诗歌的一种变奏。我曾隐约记得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轮船上为人们诵读,他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悱恻缠绵,感动了在场的听众们。事后人们才知他诵读的不过是一份菜谱,只因他使用的是在场人们不懂的一种语言,这一行为才得以实现。由此也许可以说,语言的陌生化在此完成了诵读对诗歌的变奏。
诵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表演,它是诗歌完成性的体现。诗歌不仅需要文本支撑,同时需要诵读支撑。或者从更为综合的角度而言,诗歌不仅需要形式上的视觉效果,同时需要诵读上的听觉效果。从这个角度,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浅略的判断:诗歌,是一种视听结合的产物。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认同,语言不仅是纯思维性的存在,也不仅是视觉观感或者抒情的存在,它还应是听觉上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讲,之于前两者而言,听觉于语言似乎更具基本意味。
在整个诵读发生的过程中,听众的艺术修养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这部分人与读者部分地重合,但又存在着对抗的性质。视与听两种进入艺术的角度,决定了他们对诗歌将会产生的不同认知。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当诵读行为在诗歌的接受中发生时,诗歌即转变成了一种集体行为,集体欣赏,甚至集体表演的形态。
诗人、诵读者、读者、听众这四个因素都是诗歌发生时不可模糊化的。从接受学的角度而言,文学作品只有在被接受后才真正完成。从这个角度而言,诗歌这种特殊的体裁,决定了它的无限性与永恒性。诗歌具有与时间并驾的包容性。回到本部分最初提到的轻与重的问题,我们发现似乎在诗歌的视听融合与对抗中,自我的轻与重成为了诗歌的核心。如何把握轻与重以及诵读这一艺术形式,也可能是今天青年诗人们需要注意的。
风格的味道
具有明晰意义的诗歌,语言晦涩、表达朦胧的诗歌,碎片化意识流动的诗歌等,每一种风格的形成,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世界方式的被发现。某种程度上说,风格的形成既要产生自我,又要突破自我。比如诗人——我在关于诗歌的想法表述中,不谈诗人应该如何,只谈他们可能如何,这种可能指向猜测也指向已发生——他们可能创造一个色调浓稠的小世界,也可能将生活引向抽象的表达,还可能关注到孤独、无聊以及艰涩的生活,但如果他们无法脱离性别的限制,无法在写作时拒斥自我,无法为自我谋划一条生路,在被修建好了的公路上,终有一天他们会挥霍掉自我的额度。
当写作建立了一种自我对世界的体验后,我们可能要做的不是加固它,而是放弃。如果手仍紧紧握住被占有的路口,路的尽头则很难是出口。我们不能贪心,但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对是否完成了自我构建的明确判断。这一点很难,因为自我这一词汇指向的存在本身,便是极端矛盾的。换句话说,对一种风格的建立其实是在假设的条件下完成的。我们必须把前提设置好,才能开始探究可能的结论。
一种风格的建立绝不是简化感觉,而是要释放感觉。阿奎那在谈到灵魂时曾做过这样的一个论断,大致是说当把灵魂从肉体当中分离出来,那么剩余的这部分不能被称为肉体,也不能被称为灵魂,分离出去的那部分也是。我想,对待感觉这种体验与想象世界的方式,我们不能切割、不能规训、也不能简化,能够怎么样,这很难说。或者其实可以这样说,诗人的风格只能是这样的一种形态:不是……;而不是这样一种形态:是……。在写作诗歌时我们可能要做的是去否认,而不是判断。这种建立风格的方式是将自我围困起来,让诗人犹豫起来,在生与死的两个端点之间。
我以海子跟顾城的自杀来明确我的想法。自杀这一行为本身极具反抗性——在谈论这一点时我避开了伦理的限制,不去考虑自杀的任何不可取性——因为它打破了一种秩序,即生命的产生与死亡被一种异己力量掌控,而非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子跟顾城为自己死亡了,不是为他人活着或者被支配结束活着这一行为。他们做的就是释放,当然,我不对这种释放的方式做任何的评论。总之,风格这一问题跟所有问题一样,都不适合高谈阔论。诗人们可能做的是写作,而不是发表长篇演说。
附件:
一个很机械的,被简化的方式是:如果是写作者,读诗的意义绝不仅仅是阅读,而应是研读。或者说,应该把作品通过拆解和组合的方式来读。关注诗人的切入点、意象、模式等,这种时候寻找问题往往比学习写法更重要。当然,这种方式似乎破坏了诗歌的整体性,在很多人的心里,诗歌是仅仅需要感悟而非分析的。这是我们的偏见,也许还是让我们长期无法脱离困境的原因之一。在读诗的过程中,偏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我们惯于寻找同类,同时消除异类。也许可以做这样一个判断,校园诗人在写作时似乎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读过诗,但并未研读,也并未深读,但是我们却动笔了。
作为诗人,我们必须写下去。能写多久,写作是否受到重视等问题不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些应该交给学者以及批评家们。多数时候,我们逾越了。以经验来谈,大多数人写作的时间都极为短暂,似乎热血澎湃之后,只有干涸在等待。坚持在今天写作诗歌的人之中,是胜过天赋的。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对待诗歌写作时把理性关在了门外,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比专制。所谓理性,即是不断地压制自己想要完成诗歌的冲动,这一点至关重要。源于抒情,指向想象。
本文所谈及的诗人指涉写作白话诗歌的写作者,诗歌以现代汉语写作为范围。(本文不以新与旧来作为划分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的准绳,而采用以诗歌语言样式的转变作为标准,因称白话诗歌而非新诗。)题目庞杂,拟就诗歌浅略谈谈自己的几个想法,未得展开,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