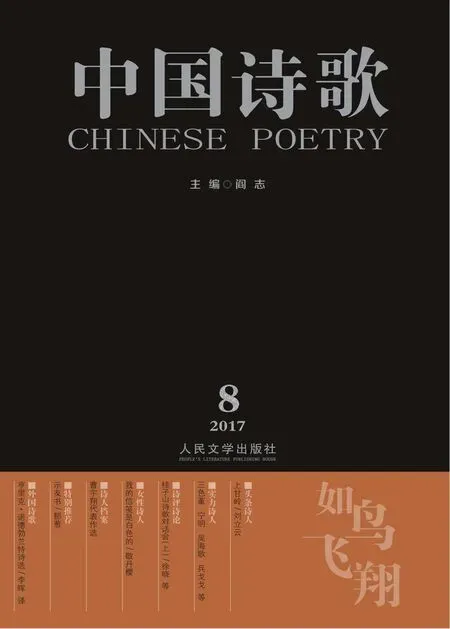军旅与日常的协奏曲
——张永枚新诗导读
□刘玉杰
军旅与日常的协奏曲——张永枚新诗导读
□刘玉杰
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四川省东部的张永枚,于新中国诞生的同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作为文艺战士,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其文学生涯也正式开端,并一直延续到世纪末。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出版诗集近三十部:《三勇士》 (1954)、《新春》(1954)、《海边的诗》 (1955)、《南海渔歌》(1957)、《骑马挂枪走天下》 (1957)、《神笔之歌》 (1957)、《椰树的歌》(1958)、《唱社会主义》(1959)、《将军柳》 (1959)、《英雄篇》 (1959)、《雪白的哈达》(1961)、《六连岭上现彩云》(1962)、《白马红仙女》(1962)、《螺号》 (1963)、《人民的儿子》 (1971)、 《西沙之战》 (1974)、 《前进集》(1975)、《椰岛少年》(1975)、《孙中山与宋庆龄》 (1984)、《宝马》 (1985)、《爱与忧》 (1988)、《画笔和六弦琴》 (1989)、《张永枚诗选》 (1991)、《梅语》 (1998)等。此外,还著有《金凤树开花》 (歌剧)、《红松店》 (歌剧)、《平原作战》 (京剧)等多部戏剧以及《红巾魂》、《省港奇雄》等多部小说。
“军旅”是人们认识张永枚及其诗歌作品的惟一标签。当然,它在恰如其分地彰显出张永枚诗歌艺术最鲜明印迹的同时,也遮蔽了张永枚在风景诗、童话诗等其他诗歌领域的耕耘。正如他在诗作《海颂》中所写的那样:“大海啊!你是最会唱歌的:/你的歌使无数白帆沉醉,/也能使钢铁的大船战栗,/你有英雄的歌,也有轻柔的歌。”(《海边的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张永枚的诗歌如同他笔端唱歌的大海,既有关于军旅英雄的刚勇,也有关于日常风景的轻柔。军旅与日常的互鸣交汇成一支协奏曲,显示出张永枚诗歌的思想与艺术全貌。
一、英雄主义的多重叙事
与军队在中国政治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密切相关,军旅文学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领域。在相当长时期内,军旅文学给人的印象都是单面性的宏大叙事,展现的是军人刚勇、热血、忠于党、爱国爱民、纪律性强等崇高的英雄主义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张永枚的军旅诗歌可看作是当代文学中英雄主义宏大叙事的一个范本。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张永枚,见证了抗美援朝战争、西藏平叛、西沙海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事,书写战争、战士不仅是其诗歌创作的起点,而且成为贯穿其整个文学生涯的红线。“我长大在革命部队里,我吸取她的乳汁而成人。我歌唱革命战士”,张永枚在诗集《将军柳》“后记”中如此写道,并明确提出“兵的共产主义品质”是其主要创作主题,“部队气派”是其追求的主要基调(《将军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军人的英雄主义固然是其诗歌主题的起点与核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英雄主义叙事的全部,还有平民百姓以及悠久民族历史中的英雄主义。
第一,军人的英雄主义叙事。张永枚前期诗歌多从正面刻画战士的英勇。长篇说唱诗《三勇士》,摹写志愿军机枪组吴有林、李正和、唐国藩三位战士,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阵地的英雄形象。长达35章的长诗《人民的儿子》,同样是朝鲜战争题材叙事诗,然而较之于《三勇士》的群像刻画,改用了更为细腻的单个英雄形象摹写。此外,除了像《三勇士》直接描写战场外,《人民的儿子》还注重对杨胜涛从孩子成长为战士的完整过程的叙写。《西沙之战》可谓诗人军旅诗所达到的巅峰,被誉为“中国当代最名噪一时的报告式长诗”(谢冕、李矗主编:《中国文学之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这部长诗曾出版多个语种的单行本,如蒙文版、藏文版等国内少数民族文字版,以及英文版、法文版、俄文版等外文版,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此诗塑造了西沙自卫反击战中钟海舰长、老渔民阿沙船长、黎族新战士李阿春等英雄形象。
进入八十年代,诗人描写英雄的题材与手法均有所拓展,无论是对战场军人还是和平军人,诗人更善于从侧面进行反衬,使得诗歌更有张力之美。《马樱花》中的马樱花,盛开于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成为美好生命的一种象征,战士用钢盔把它扣紧加以保护,“鲜花也不得不戴起钢盔,/为了结籽,就得抵抗侵凌。”(《画笔和六弦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整首诗脱离了浓厚的政治氛围,成为了一首生命的赞歌。《赶考》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小战士与灯下准备高考的儿子并置,形成了文与武、和平与战争、考场与战场之间的张力,“你选取的考场是战场,/以铁和血前去应考!”《情鸿》写在和平时代中战士所面临的爱情与爱国冲突,面对女友要“我”复员出国结婚的情鸿,“我”在矛盾挣扎之后选择了自己的祖国,“如若不爱祖国,/哪有崇高爱情?”
第二,平民的英雄主义叙事。平民百姓与战士具有同样的英雄主义品质。首先,创伤苦难中的觉醒过程。“人们一边英勇斗争,/一边医治创伤”,《杏树》的这句诗表现出诗人军旅诗写作的另一个面相,即对于战争带来的创伤、苦难的书写。《诺尔多江边》、《带路老人》、《抬起头来》、《乌拉尔牛淌下眼泪》等均可归于此类。它们都写到或战友或亲人或平民的死亡,目睹死亡的人们往往化悲痛为前进的力量。写西藏农奴制度下藏族同胞觉醒的《抬起头来》:“昨日的奴隶,/已经直起虎腰,/抬起头来,/把步子大大迈开!/雪山的主人是我们!”(《雪白的哈达》,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也是如此。其次,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也是其描写的重点。《雅鲁藏布江》中写道:“藏布江就是藏民,/藏布江就是英雄,/她的浪花是洁白的,/不准污黑只能染红!”雅鲁藏布江成为藏民英雄的象征,充满了抗争精神。《西沙之战》中的阿沙船长,面对敌舰时更是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胆量”(《西沙之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
第三,历史的英雄主义叙事。军旅诗歌多涉及当代军事、军人题材,历史诗歌可以说是军旅诗歌的自然延伸与扩展,关涉的是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总的来说,随着张永枚诗歌创作的线性时间推进,他笔端呈现的历史感也愈加浓厚,由当代到近现代进而扩展到中国古代。其历史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近现代革命历史,如长诗《孙中山与宋庆龄》、《椰岛少年》等,短诗《军旗》、《蹈海》等,刻画出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批近现代革命历史英雄;另一方面是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如《黄帝陵》、《轩辕柏》、《汉武仙台》、《黄土》、《唐魂》、《中华民族》等创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系列短诗,借书写黄帝、汉武帝等民族历史人物,表达出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感。《黄帝陵》中黄帝的崇高伟大:“人文的初祖啊!/伟大的黄帝啊!/头戴高冕,垂旒璀璨,/玄衣黄裳,立地顶天。”(《梅语》,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二、一种少有的边疆书写
如果说英雄主义叙事是“军”的自然反映的话,那么边疆书写则是对“旅”的集中体现。诗句“骑马挂枪走天下”确乎可以视为诗人的自我写照,由蜀山蜀水滋养大的诗人,笔端却难见对家乡的描绘。相反,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对异乡边疆山水人情的真实刻画。何以会产生这种较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呢?从人地关系来看原因大致有二:首先,与诗人的军人身份有关。诗人凭借自身军队文艺创作者的天然优势,得以在那个人员迁徙、流动不便的年代,遍走常人难以到达之地,并将其所见所感以诗歌形式留存下来。张永枚的诗歌所书写的边疆涵括了西藏、青海、广西、广东、海南等广袤的边疆地区。其次,地处内陆的静态的故乡更适合于诗人作精细化深度开掘,而边疆在政治地理学上属于独特的地理区域,暗含着的不稳定特性为诗人提供了动态叙事的写作资源,显然张永枚更青睐后者。政治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疆进入诗歌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边疆首先是新中国的边疆,对边疆的书写也首先是为新中国而写。在此意义上,边疆的边缘性得到稀释,在全局观念中反而获得了某种中心性,也即边疆不边。《骑马挂枪走天下》意气豪迈、直抒胸臆地唱出四海为家的豪言壮语:“东南西北千万里,/五湖四海是一家。/我为祖国走天下,/祖国到处都是我的家。”(《海边的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什么地方最好》则蜿蜒曲折地重述了这一四海为家的宣言,彰显出诗人的边疆之爱。边防战士心目中最好的两个地方是北京和故乡,前者是政治的、中心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圣地,后者是乡土的、地方的生养纽带。然而,在道尽了对北京的向往以及对故乡的依恋之情后,诗人将笔锋转向边疆,“这里的每一条小路,/都连接着北京的街道。/这里的每一座高山,/都和故乡相依相靠”。边疆成为“什么地方最好?”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祖国给我的岗位最好!/我守卫的边疆最好!”当然,边疆之爱不仅仅有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也有出于经济建设的缘由,比如在《我是青海人》中,立志开发大西北的上海姑娘和成都小伙,尽管乡音难改,却自称是青海人:“同志你别吃惊,/我们真是青海人!/我们虽生在上海、成都,/根儿却扎在西宁!”(《青海之春》,青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还乡曲》是张永枚诗歌中不多见的故乡题材诗歌,诗人用叙事手法详述了还乡的整个过程以及回到家乡的经历与感受,然而正如诗作开篇点明的这只是“探家”一样,在诗歌结尾处呈现的并不是还乡之乐,而是重返边疆的急切心情,“心儿飞过万重山,/心儿飞回国防线;/故乡啊故乡,/我要重返边疆,/保卫亲爱的祖国。/保卫你呵——/我们美好的家乡”(《解放军文艺》,1955年第4期)。
第二,彰显出深厚的领土领海意识。将《六连岭上现彩云》与《椰岛少年》对比阅读,会发现不少有趣的改动。《椰岛少年》借修订而增加了对南海领土的书写,这无疑与1974年的西沙海战有关。一方面,这自然可看作是诗人有意靠拢政治局势而做出的修改,毕竟诗歌的背景年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另一方面却也保存了珍贵的历史史料。“阿妈曾经告诉我:/海南不算是天涯,/远望有西沙中沙东沙,/还有南沙曾母暗沙。//阿妈曾去捕过鱼,/个个岛礁是宝地,/将来革命成功了,/咱也远航去那里。”(《椰岛少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领海歌》一方面显示出对领海的开放胸怀与心态:“碧蓝的疆土,/美丽的领海:/敞着大门,/袒开胸怀,/和平与友谊,/受到接待。”另一方面,面对外敌的侵略则显示出坚决打击的决心:“领海,领海,/神圣的海疆!/不让海盗旗,/垂在头上!/不准挑拨者,/玷污白浪!”
第三,关注边疆的地方性。一方面是地方的风物、人情,使得张永枚诗歌的色彩不再单一,有了尽管不多但倍显珍贵的鲜活感;另一方面是边疆的地方性风景,未能逃逸出政治、民族、历史等宏大话语的辖制。政治化的地方性风景,成为了衬托士兵英勇不屈形象的背景。这种情况下的风景往往失去了风景的本意,更多地是在隐喻意义上得到使用。《台风中的士兵》中台风被拟人化为敌人,“风像千万根凶狠的鞭子,/追赶着乌黑的云朵,/石蛋像树叶一样被卷走,/大树披头散发投入海中!”然而,台风的凶恶更突显了战士的英勇:“台风只能使战士更英勇;/台风像那挣扎的顽敌,/吓不倒守岛英雄。”另一种情形中,风景尽管不被拟人化,保留了风景的物质性,但仍旧被用来反衬士兵的优良品质。在《屋檐下》一诗中,诗人就用朝鲜的大雪来反衬志愿军战士不扰民的纪律性与憨厚品格。“呀!雪堆沙沙作响,/一下子垮了下来,/一块雨布顿时揭开,/露出三个志愿军战士!”(《新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因而中华文化中浸透着厚重的历史意识,历史遗迹往往能够激发诗人的民族意识。在《旅顺口祭》这首诗中,诗人借旅顺口与万忠墓来惊醒国人的民族意识:“噩梦醒——/海波荡翠,白鸥飘雪,/清风送给我:/两片红枫叶。”海波、白鸥、红枫叶等等在此是被高度历史化的风景,它们共同指向了“惨史一页”。
三、风景诗与童话诗
无论是英雄主义叙事还是边疆书写,都浸透着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这是张永枚诗歌的主要景观。然而,与此宏大叙事并行发展起来的,还有他的风景诗和童话诗。这一类的作品,不仅仅容易被接受者所忽视,即便在诗人本人那里,也是到晚年才有了清晰的自觉意识。1985年1月发表在《诗刊》的《椅子》,是诗人诗歌创作生涯中具有象征意味的并不多见的作品,用诗人自己的话讲《椅子》是“对‘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诗辩诗情”,其诗情是后来已古稀之年的诗人心中所思的“‘两个转变’:‘从军营转社会,从军官转百姓’。”(张永枚:《笔枪赞英雄——战争文学生涯回忆剪辑》,袁永生主编,《军礼·军威·军魂——老兵的故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创作者的思想认知自觉中,由特殊军人的军旅生活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转变,是到诗人晚年才发生、凸显的。而事实上,从诗人的创作实绩来看,从军旅题材中脱嵌出来而进入社会、百姓等日常性诗歌创作,要比这种自觉意识的诞生早上许多年。
在很大程度上,风景诗与边疆书写同属地方性写作,所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于地方的私人化的审美,后者则多与政治、历史发生关联。张永枚早期与中期的诗歌作品,尽管总体来讲是关于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也不能忽视其中浸透着的地方性审美目光,《南海渔歌》、《椰树的歌》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诗集。椰树、大海、岛屿等构成了诗集《椰树的歌》的核心意象。如《清澜港》:“一眼千里的椰子林,/长成两道翠绿的长堤。/装亿万顷清亮的海水,/照一面明镜似的青天。”(《椰树的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通过地方风景,诗人不仅看到了日常生活的甜美,如作为海边渔村日常生活图的《海边黄昏的山歌》、《渔汛三月三》等,也捕捉到了地方风景所蕴含的苦难的记忆,如《船形屋》中所写:“黎家的小屋像只船,/记下了往昔的苦难。”在诗人的后期诗作中,地方性往往较为普遍地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比如《渤海湾》、《正午的月亮——渤海奇观》、《午夜的太阳——渤海奇观》、《重新……》等一系列摹写渤海湾的诗歌。此类风景诗,往往会生发出诗人的点滴哲思,如《火炼的艺术——石林》一诗,全诗分为两个诗节,前一诗节是诗人对石林的艺术化想象,将石林想象成仙子起舞、水边浣纱、武士挥刀、士人卷书、工匠扬斧、孔雀开屏等等场景,后一诗节则尝试阐释石林之美源于火炼,“随着是春雨的洗涤,/雨后有熏风的吹化”,经过自然伟力的造化,“绝非炭余火渣,/成为真善美的雕塑”,最后诗歌以反问句作结,“啊!石林!/不因火炼,/哪得升华?”哲思的尾巴可以说成为此类风景诗的一大特点。
与风景诗旗鼓相当的是童话诗,张永枚创作的童话诗集有《神笔之歌》、《白马红仙女》等以及童话诗剧《檀香女》。在童话诗选集《宝马》“后记”中,诗人如此写到自己的童话诗追求:“我希望自己的童话诗,在形式上尽力做到:可读、可诵、可唱、可舞。内涵丰美而此四者皆备,必为孩子们喜闻乐见。”(《宝马》,新世纪出版社1985年版) 《神笔之歌》、《美酒井》两诗,均嘲讽了人们贪得无厌的心理,只不过两者的嘲讽对象不同而已,前者嘲讽官吏、后者嘲讽平常百姓。《射手》首先预设出一种苦难场景:万山之王派遣三座大山截断石花河,村庄的田园变得干涸,值得将五百童男童女献祭给万山之王。英雄杨弓的到来解救了这一困境,但他自己也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坏品质(如贪婪等)——受惩罚”、“困境——困境的解决”等构成张永枚童话诗的写作模式,体现了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教诲功能。
长篇诗剧《檀香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写给孩童的童话诗了,而是写给青年一代及其父辈的关于爱情的童话诗剧。檀香女原为木匠和画匠从檀香木中雕刻创造而出,被牧人赋予灵魂后,对牧人产生爱意。然而木匠和画匠,却不同意牧人将檀香女带到远方,最为要紧的是草原王爷又垂涎檀香女的美色,想将其霸为己有。最终,檀香女的反抗以及牧人的坚持使他们克服重重阻力,迎来他们的婚礼。当然,我们依旧能在《檀香女》中看到底层劳苦大众与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痕迹,但《檀香女》的重心在于爱情终究战胜霸权、父权、贫穷等诸多现实阻力。结尾处画匠表达出的纯真爱情的美好,即便在今日看来都感人至深:“结婚吧!孩子!/父亲虽然贫穷,/草原母亲已为你准备了嫁妆。/天上的彩霞是你新娘的衣裳,/明亮的河水是你梳妆的明镜,/柔软的草地是你的新床。/晨风已给你奏起了乐曲,/太阳已经升起在东方!/它是在催促你们,/不要错过了时辰!”(《檀香女》,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梅语》一诗以“长于南国温润之乡”的暖梅自况,但作为张永枚后期代表诗集的《梅语》却不能看作是诗人的小我抒写。诗人在《梅语》“后记”中特别强调“梅语非枚语”,“梅语,大中华各民族老百姓之语”。“梅”并非以“枚”的谐音来暗指诗人张永枚本人,而是中华民族老百姓的象征物。在此意义上,强调张永枚的风景诗与童话诗的诗歌创作,并不是说它们反映了诗人的小我抒写,只是说他笔端的大我从军旅转向了日常。
四、诗艺上的独特追求
首先,语言简朴无华,注重叙事与抒情结合。由于他诗歌的预设受众往往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或寻常百姓,张永枚的诗歌大多通俗易懂,避免单一的抒情,往往做到叙事与抒情的融合。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三勇士》就是以传统说唱艺术中常见的程式语“说的是”开端,诗节之间夹杂着散文段落,“嘿!那位同志说啦!你唱的是啥呀?半天还没个头脑儿呢!众位不要急,我唱的这段书,就是韩班长讲的那段故事,因为这段书是真人真事,我就得把来源交代一番”。可见听众对故事性的要求较高,而整篇长诗也以故事发生的线性时间顺序依次展开。除《孙中山与宋庆龄》这部诗人晚年创作的纯粹诗体长诗外,《三勇士》、《六连岭上现彩云》、《椰岛少年》、《人民的儿子》等叙事长诗,为了便于叙事,部分段落均用散文写成,形成以韵文为主的韵散结合的艺术特色。面对有人批评他的诗直白、通俗,张永枚认为:“直白不是苍白。贫血的朦胧不如饱满的直白。直白与含蓄,都是诗法,可依情、事、理的需要灵活运用。”可见,在张永枚的诗学理念里,直白终归是没有危险的占据第一位的诗法,相反,尽管他承认朦胧是美的一种,但朦胧却不可超过可以理解的界限,不能理解的“朦胧诗”应该叫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怪文诗”(《张永枚诗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其次,探索诗歌的多种样式。张永枚称自己追求的诗歌风格是“力求融汇:祖国古典诗词(包括曲艺、剧诗)、民歌、‘五四’以来的新诗、外国诗菁华”(《张永枚诗话》)。从张永枚的诗歌实践来看,尽管很难讲他将所有的诗歌样式融汇于一体,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但他的诗歌的确是多种样式的,诗人受民歌、古典诗词影响而创作的诗作也是多种多样的。如《退役马》:“长鬃烽火红亮,/双耳号角悲壮……/驮着一对新婚青年,/背上蜜月,/蹄下泥土香。”绵密的意象,短促有力的诗句,明显受到词这一文学样式的影响。再比如在中国古典曲艺、剧诗的影响下,诗人在诗体戏剧领域多有收获。他创作的歌剧《金凤树开花》、《红松店》以及京剧《平原作战》等一般归类于戏剧,但其中的唱词部分却是用诗歌形式而非散文形式写成的,如《红松店》中的这段唱词:“武功山上一棵松,/不怕血雨和腥风;/眼忘青松豪情生,/山上背炭回家中。”(《红松店》,广东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尽管诗文浅白,却在韵律上做到了押韵。
最后,诗歌的朗诵化与谱曲化。诗歌的朗诵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新诗的朗诵化则与抗战有着莫大关系,“诗歌‘朗诵化’的审美特点重建和发展,不仅符合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时代需要,而且也符合新诗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新中国军人的张永枚承袭了抗战新诗朗诵化的传统,比如应广东电视台之邀所作的《好朋友》一诗,就曾被广东朗诵艺术学会会长姚希娟所朗诵。此外,诗歌的音乐性也是诗人的诗学自觉,他的第一部诗集《三勇士》就是说唱诗,《新春》“后记”中则明言“由于战斗的环境,要求即时歌唱”,等到几年后的《将军柳》则明确提出“谱曲能唱,离曲可读”的诗学主张,《螺号》“后记”中诗人也重申了“音乐性”的重要。诗人的音乐性自觉意识与军队文艺制度的推力形成合力,使得诗人多首诗作被谱曲传唱,从军队传唱到社会而成为脍炙人口的歌曲,如《骑马挎枪走天下》 (原诗名为《骑马挂枪走天下》)、《人民军队忠于党》、《滚滚江河流不尽》 (歌剧《欧阳海》选曲)、《还乡曲》、《月儿代我把手招》等。
张永枚的诗歌放置于当今文化心理中来理解,无论是从诗歌形式美感还是诗歌的内涵上来讲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我们难以在他的诗歌中发现小我与大我、诗歌语言与社会语言之间的紧张与冲撞,相反,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情况下其诗歌呈现给我们的是宁静的和谐与一致性。他本人属于那个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年代,他的诗歌也毫不保留地献给他所生活的时代,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以及他的诗歌构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切的反映。然而比较吊诡的在于,尽管张永枚的诗歌内部并不存在诗学紧张,却与现今这一解构崇高的个人主义时代形成巨大的紧张关系。对今日而言最有教益之处的反思在于,张永枚诗歌所代表的时代与现时代之间的沟壑转化成的文学问题,即文学他律与文学自律之间的紧张。文学的自律尽管在现代以来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与珍视,但是无论如何文学终究处于文学场之中,必然会与政治、经济、历史等等发生不可断绝的联系。今人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共性大于个性、大我超于小我的诗歌写作,简单地予以否定或贬低并不是可以让人一劳永逸、高枕无忧的做法,背后所隐藏的文学自律与他律的问题,或许永远没有定论,而这种由于自身原因所产生的张力,或许可以看作是文学生命力众多源泉中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