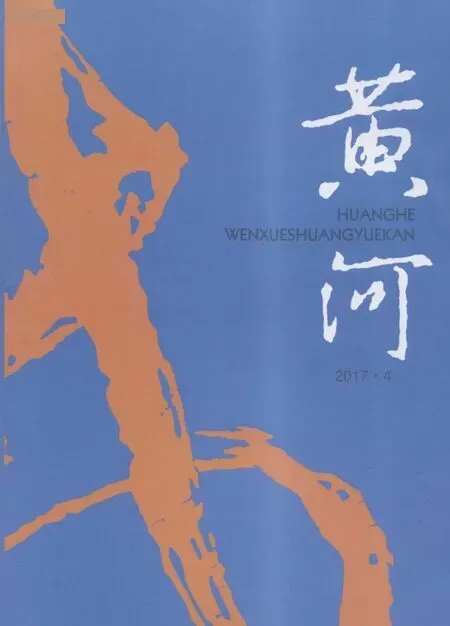一枕书梦
朱航满
我不是出生在书香门第,但祖父对于书却是极为敬重的,听说我们家中曾有一座二层阁楼,楼上有很多书,大约可以装小半卡车,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书都被我祖母私下里销毁了。祖父是老中医,没有上过什么学,认字是在村旁的一座小寺庙,被一个老和尚发了蒙,他自己后来信了一辈子的佛,也吃了一辈子的素斋。祖父对于书的敬重,一方面是他节衣缩食,买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书,另一方面,也有敬惜纸张的缘故,他对印有字的纸张都十分爱惜,对于书上的东西都很信服。曾有很多次,他把家中幸存下来的几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书,拿给我看,态度非常虔敬。祖父的藏书以中医、佛教和黄历之类的旧书为主,其中有一些也可能有版本价值,后来有书贩专门上家中来收购,但被他严词拒绝了。祖父生前总是在抄抄写写,但从未曾发表过东西,他自己研究了一个治疗某种常见皮肤病的偏方,被收录在《民间偏方秘方辞典》中,算是一种认可。
也许受祖父的这种影响,我很小就爱书。但家中的书实在是少得可怜。我父亲是种菜的农民,因为被“文革”耽误,没有读过什么书。我买的第一本书是由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改编的连环画,是在小学校门口的地摊上,印象很深,大约是五分钱。小学快毕业时,一位在西安上班的亲戚送我一堆《故事大王》旧杂志,我在田间地头逐页读完了。这是一种迟到的阅读,我以后的读书,大约都是这种补救般的节奏。我曾一度把村子里能借的书全都借来看看,当然其中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诸如通俗小说、相命占卜、《半月谈》杂志之类的东西。偶然在村中借到一册《中国民间故事集》,封面都被翻破了,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民间传说,大多故事曲折有趣,许多内容至今记忆尤深,令我爱不释手。后来我大哥考上了大学,偶尔会给我带一些他读过的书,印象很深的就有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和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尤其是后者,一度给我很大的激励。
我的阅读习惯大约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但在我们那个小镇,是无书可读也无书可买的。我读高中时,有次读到一篇文章,写列宁临终前曾让他的妻子给他朗读美国作家杰克·伦敦 (John Griffith London)的小说《热爱生命》,这让我极想读到这篇小说。后来一位出差到西安的老师替我买了一套《杰克伦敦文集》,这大约是我平生第一次买到一套像模像样的书。我第一次自己在书店里买书,还是到县城参加高考时,在县城的新华书店里买过一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散文全编》,记得是贾平凹曾在一篇散文中提及过,这本书我至今还留在身边。那时我也常常向同学借书,借到的主要是一些世界文学名著,记得借过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司汤达的《红与黑》之类小说名作,外国人的名字看着很吃力,但还是硬着头皮来读。有次我带了其中一本书回家,母亲看到了,对我说,你现在还有时间看这种东西,眼神是比较失望的,我从此未再敢将闲书带回家。
读书的高中在一个小镇上,有时会有一些卖盗版书的小摊贩出没于学校附近。我在书摊上买到过几本书,其中一本书是《古文观止》,一本是《鲁迅文集》,这两本书大约也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推荐,于是下决心买了。只是鲁迅的书当时读着颇为吃力,后来我带到大学才陆续读完,同时还读了一本王晓明的《鲁迅传》。王晓明写鲁迅“横站”的战斗姿态,深深地感染了我。年轻人读鲁迅,可以变得特立独行,但一定也会因此碰壁不少,这至少是我的一点感受。还有一本书摊上买来的书,其实本不值得一提的,但当时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此书名为《在北大等你》,大多是各地考上北大的状元谈自己的高考心得,使我间接地对北大充满崇拜。我后来自然没有考上北大,但这本书直接改变我的是,在距离高考还有不到半年的时候,我执意从理科转到文科,因为梦想读北大中文系,这种冲动现在看来也是一种头脑发热。不过后来我也有机会在北大中文系旁听过一阵子的课,也特别关注过不少北大学人的著作,算是这本书带来的一些影响吧。
一九九八年我到南京去读大学,临行前,去西安的六路看了看,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书的世界。六路是西安批发图书的一条街道,一家书店连着一家书店,我在其中流连了很久,最终只买了一本书,就是 《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由西安带着去了南京。贾平凹以《废都》名世,有“鬼才”之称,在陕西影响极大,祖父有次在广播上听了他的一篇散文《秦腔》,很是佩服,对我说,贾平凹这个人了不起,名字起得也很有水平。我后来很有一段时间都喜欢贾平凹的散文小说,直到他的长篇小说《秦腔》出版,我刚起头来读,便感到一种厌倦,后来很少读贾氏的作品了。现在想想,或许在我的思想深处,已渐渐对那些意淫传统的内容有了警惕。那年在西安,我还去了钟楼书店,它当时坐落在最繁华的城市中心。我买了一本魏明伦的杂文集《巴山鬼话》,薄薄的一个小册子。我拿着那本小书,坐在公交车上埋头翻读,悄然从这座千年古城中穿过。
在南京读书时,因为有国家补助,可以衣食无忧地读书。我走过的地方不多,但南京是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一座城市。有时读书到夜深人静之时,可以聆听从长江上传来的汽笛声,若隐若闻。校门口的法国梧桐,郁郁葱葱,遮盖着马路,也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如果留心的话,在南京街头则不时可以发现一些旧书店,其中有不少是大学教授的旧藏。记得从旧书店淘来一册《俄罗斯作家小传》,编著者已经忘记,墨绿色的封面,内容系介绍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作家生平,诸如托尔斯泰、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等人,真可谓星汉灿烂,一时为之心热。后来又接连读了别尔加耶夫(Nicolas Berdyaev)的《俄罗斯思想》和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俄罗斯思想家》,都是大受震撼。上世纪末大约是图书出版的一个短暂黄金期,我也跟读过不少流行的学人著作,诸如朱学勤的一册文集《书斋里的革命》。当时恰逢朱先生曾经任教的那所学校也与我就读的这所学校合并,令我深感到即使再不济的地方,或许也有藏龙卧虎之人。
大学毕业后,可以挣工资了。由于没有什么经济负担,常买一些自己想看的杂书。刚毕业时在石家庄郊县的一个小山沟里工作,进城是很困难的,但几乎每周都要进城去买书,就像采购粮食一样。经常买书的书店,先是一家连锁的席殊书屋,后来则常去友谊大街图书批发市场,还有河北日报社旁的嘟嘟知识书店。嘟嘟店面虽小,但品位颇不俗,后来才得知店主原来是学者邓正来的弟弟,我当时拟出版一册随笔集,他答应出版后可以在那里寄卖,但那本书一时没有印出来。“非典”肆虐的那一年,单位封闭管理了三个月。无聊之际,发现单位有个封闭已久的小图书室,其中大多藏书与我的兴趣无关,但其中竟然有一本加缪(Albert Camus)的小说《鼠疫》,于是便借来读了一遍。那种在社会危机中读书的感受,以后很少再有了。当时办公室有个已婚同事,因为“非典”,很久没有回家,疫情解除后,他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立即洗澡。而我则是将三个多月来记下的书单整理出来,立刻准备去城里的书店逐一买来阅读。
可以说,在此之前,我对于书的需求,基本上处于饥馑状态,要么之前根本没见过那么多的书,根本不知道该读哪本,又该买哪本,要么就是没有太多钱去买自己想要买的书。而自己对于书的需求,基本上也属于恶补的状态,毫无厌倦,从不满足,见什么书都可以读得津津有味。这样的状态直到自己读了研究生之后,才慢慢有了一定的偏好和趣味,并渐渐摸索出一些门道,也培养了一些分辨的能力。研究生是在北京一家艺术学院就读,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是我的师兄。我曾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翻到一册1983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聂鲁达诗选》,书后的借书卡上便有一个“管谟业”的签名,我悄悄地留藏了这张小卡片。研究生的课业相当的轻松,买书和读书算是常态。可惜那时虽是带薪读书,但工资毕竟不高,而想买的书又实在太多,常常有见好书而掉头的怅然。记得《鲁迅全集》新版刚出来时,售价近千元,故而只能一声叹息。我有位师兄,也极为爱书,但他有个办法,就是整本整本地复印,费资甚少,这个办法我也尝试过几回。
北京不愧是文化中心,虽然是穷书生,但不少文化场所反倒提供了读好书的可能。诸如距离学校很近的国家图书馆,那时新馆还没有建成,老馆在紫竹院公园旁边,可以借了书到公园里来看,也不失为一种特别的享受。有时在国图老馆的开架阅览室里看书,每到夜幕降临,工作人员会将很大的窗帘逐一轻轻从上拉下,此刻你会油然而生一种阅读的肃穆与神圣。还有坐落在圆明园旁的单向街书店,店名取自本雅明的著作 《单向街》,颇有些现代情调,书店几乎每周都会有讲座,听完讲座,有兴致的话,可以买本签名著作,然后再到圆明园遗址去看看风景,也不失人生的一种乐事。还有万圣书园、国林风、风入松、盛世情等书店都不太远,也常能在课余去看书。印象很深的是某次去鲁迅博物馆拜访馆长孙郁先生,在馆内的鲁博书屋里翻书,店主极力向我推荐刚刚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于是买了一套,这也是我后来研读知堂的开端。
我读研究生时,有一段时间也是好读奇书,这也是值得一记的事情。当时偶然读了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真是颇为震惊,于是逢人推荐。学校附近有一家很小的书店,名为“城市季风”,我常常在课业之余去那里翻书,但多看不买,后来和那家书店的店主也熟悉了。有次我推荐他这册《寻找家园》,后来再去,便见他果然进了不少册,当时真是颇为兴奋。因为攻读文艺学的研究生,一时立志要做文学评论家,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为偶像,也很喜欢英年早逝的学者胡河清。一直想买一册胡河清的评论集 《灵地的缅想》,但遍访不得,后来在国家图书馆复印了一册。还有一册奇书,便是我久闻捷克剧作家哈维尔(Vaclav Havel)的著作而不得,某次有幸拜访社科院的徐友渔先生,他得知我不曾读过此书,便送了一册崔卫平女士翻译的《哈维尔文集》。此书内部印刷,徐先生说他自费买了一些分赠师友,我则有幸得到一册。后来我在网上的读书论坛结识了一位书友,我们相约在万圣相见,他赠我了一册台版《哈维尔自传》复印本。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与钱锺书先生交好的陆文虎先生。但我迟钝,读书时并没有怎么钻研“钱学”,说实话,对于《管锥编》和《谈艺录》之类的著述,当时真是如对天书。直到离开学校之后,才磕磕绊绊地读了一些。但从读周作人和钱锺书开始,我逐渐喜欢上了这种“抄书体”著作,那种书山探幽的兴奋与新奇,影响了我的择书趣味。后来读到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 jamin)的论文集《启迪》,由苏姗·桑塔格编选,也是大为喜爱。不过,最受影响的还是周作人晚年所写的“抄书体”文章,令我感受到了中国文章的古朴与清明,并被一种特别的气息所慑服,我把这也看作一种“五四”遗风。我后来读书,几乎都是围绕这两位作家展开的,诸如由钱锺书而关注吴宓、杨绛、郑朝宗、鲲西、胡河清、谢泳等学人,由周作人则进而关注废名、丰子恺、张中行、黄裳、谷林、锺叔河、舒芜、扬之水、李长声、止庵等文人。对鲁迅的热情虽在慢慢降低,但与鲁迅有关的人与书,却也并没有失去关注的兴趣,诸如台静农、唐弢、王瑶、孙犁、邵燕祥、林贤治、钱理群、陈丹青等学人作家,也都曾集中读过不少。
以上大约是我的买书与读书琐忆,因为再后来,基本上便是网上购书了,也少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和感受。我对于书的梦想,之前是无书可读,再后来是无钱买书,都是颇为无奈的事情。前几天和一位也爱书的朋友谈起,乃是这十多年中国人的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了,但书的价格似乎涨得不太多。现在的书,大多是能够买得起的,但很多人反而不买书了。诸如那套曾经让我叹息定价太高的《鲁迅全集》,后来又过了近十年,网上书店竟以半价出售,我虽然已经有了多种关于鲁迅的著述,但还是毫不犹豫地购下一套。我甚至以豪举的行为,先后在网上购买了《胡适全集》《周作人散文全集》《周作人译文全集》《丰子恺全集》《沈从文别集》《汪曾祺全集》等不少大部头著作,但似乎没什么特别可说的。可以说,以前对于书的痴想现在都已经解决了,但新的问题似乎也产生了。工作之后,虽然好读书的习惯没有改变,但读书的时间却是少了,甚至变得愈来愈少。说来这是一件相当困扰我的事情,后来经过了许多的事情,也竟然慢慢地平复下来,并习惯利用业余来读点自己喜欢的书。由此也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爱好都应该是业余时间来完成的。
也或许正是这种缘故,我对于身处专业机构之外的作家和学者分外关注,诸如声名并不彰显的谷林先生,便是我所喜爱的一位。谷林的那本《书边杂写》我时常会找出来翻翻,这位一辈子从事会计工作的爱书人,好读知堂,善写文章,又能在细微之间阐发他人难以见识的滋味。更为难得的是老人淡泊宁静的修为,真是心向往之。我至今都遗憾没有与谷林先生有所接触,而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没有。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一册谷林先生的签名本《答客问》,才算了却一件心事。我在旧书网上买书的开端,就是收集黄裳和汪曾祺生前出版的各类版本的集子,后来基本上在这里收纳齐全了。曾在山西作家协会任职的谢泳先生也是我关注的一位作家,他的《杂书过眼录》三册均是我喜爱的,谢泳研究胡适、储安平、陈寅恪、钱锺书等学人,他利用自己搜罗和收藏的资料,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写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文章。而谢泳先生坚持独立研究的精神,便是很得前辈学人遗风,那也是我所向往的。谢先生曾给我的一册集子写序,我后来在孔网上买到一册郑朝宗的《海滨感旧集》,竟然还是谢先生的旧藏,也算是一件小小的书缘。
拉杂写了这么多,起因还是与书有关。去年春天,我在家中书房把这些年买到的书重新整理了一番,并借此机会陆续将一些感兴趣的旧书又重翻了一遍。有些书读后颇有感慨,就随手写了一些笔记。虽然这些文章大约并没有多少特别的见识,但其中一些自己读过的心得,或许对于还未读过这些书的朋友,会多少有一些启发,而我对于这些书的感情,或许也会引起一些朋友对于书的兴趣,我把这也看作是一种人生的书梦。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何客兄很有出版情怀,他热心出版了《胡河清文集》,很令我敬佩。几年前,他还为我出过一册随笔集《书与画像》,彼此都很愉快。这次承蒙他的青睐,又邀我加入他主持的“渡”书系文丛,我便将这些文字以时间为序,结为一集,作为一种纪念。倒是为这本小书取个名字,竟颇费了些心思。说真的,连黄裳先生要给书画集子取个好名字,都感到有些苦恼,他在《银鱼集》的序言中感慨好名字都被他人用过了。后来我忽然忆起这些年买书和读书的往事,竟也有了“一枕书梦”这样的感慨,于是不妨用作书名也好。祖父生前曾预言我将来会写书,如今我果然出了好几本书,可惜他一本也未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