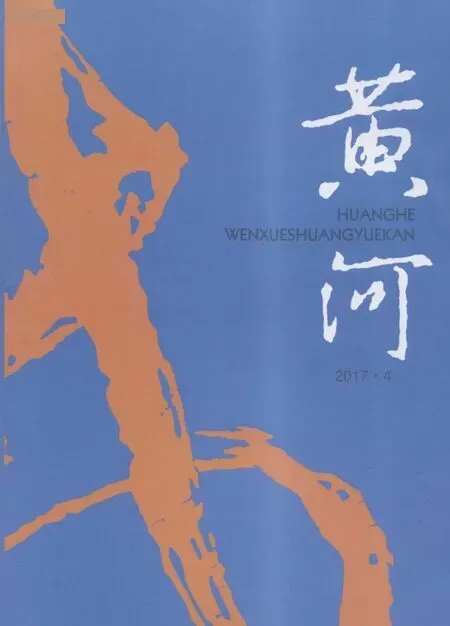女友夏兰兰
周子湘
一
这是一爿没有被拆掉的城中村。现在这样的地方不多了。能找到是宋小宝和夏兰兰的运气。
夏兰兰现在已经会化浓妆了,眼线从眼梢挑上去,口红浓重,色彩艳丽。只要不出汗,脖子上的金项链就不会掉色。
宋小宝用三轮摩托车驮着夏兰兰在城中村里转,一边开一边指给她看:“兰兰,就是这个村子,城里该拆的都拆完了,再不下手,就没咱们的份了。”
夏兰兰坐在三轮摩托车上,从身边滑过的理发店玻璃门里瞥见自己:宋小宝给她买的高跟鞋,小碎花的连衣裙,裙子里是白嫩修长的一双腿。腿上放着她的包,金色链子的人造革女士包。
这是为了取悦中介人专门打扮的。中介人见过多少乡下出来的漂亮女孩,不打扮一下,他能看得上?他看不上,这生意还怎么做?
夏兰兰看着打扮得像赛金花的自己,拉拉裙子,梳了梳头发。她的脸是小巧的圆脸,没动过刀子,没垫过下巴,不是锥子脸锋利妩媚那一路,却是温柔、恬淡的一朵小花,如果去了这身行头,是自然敦厚的健康美。白净的皮肤骗了城里人的眼睛,这姣好的肤色让很多城里女孩把夏兰兰归入自己的同类。
可她知道,她终究和她们不一样。她从山里走出来,要走多少路呢。先在路边搭摩托车,再坐汽车,再倒火车……从娘胎里爬出来的那一刻起,人的命就算是注定了。她和宋小宝是一样的,一路跌跌撞撞走进城里,他们都清楚来的目的,来了就是为了扎下根。再不回去走那么长的山路了。
八千块,老头不残疾不痴呆,可以了,兰兰,算公道了。宋小宝抱着夏兰兰劝她。
只要想到自己要去嫁给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头,夏兰兰就想哭。
“哭什么,兰兰?这又不是真嫁。假结婚。你知道中介人有多难找,现在查得紧,这条线不好搭。如果让他们村上知道了,打死也不会给咱们分房,你的户口也别想迁到他村上。分不到房子,指望咱俩,要在这座城里奋斗多少年?”
宋小宝搂着夏兰兰,一晚上就这样从背后紧紧抱着她,又叹口气翻过身去:“你以为我想让你和那老头演这出戏?只是走一个过场,你和他领个结婚证,一切结束——还是咱俩住。那老头敢碰你一根手指头,我饶不了他!他敢!其实我心里也难受,谁愿意自己的女朋友和别的男人‘结婚’?想想你要和他去领证,我都要疯。”
夏兰兰立刻扭头问:“那你为什么让我‘嫁’给他? ”
宋小宝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得夏兰兰几乎听不见:“不这样怎么办?咱俩在餐馆端盘子,干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他忽然没有了平时的虎劲,只觉得虚弱无力。他松开搂着夏兰兰的手,转了过去。
屋子里静得有点荒凉。她看不得他这个样子,他在夏兰兰最无助的时候来到她的身边,现在,她怎么能撇下他不管呢?她又从背后抱起他,吻着他脑后的短头发说:“小宝,我去。”
夏兰兰从山里走出来,并不是来找宋小宝的。那时候,她还不认识宋小宝。她来投奔的人,是早二十年走出大山,在城里工作的大姨。
夏兰兰站在厂区的家属楼前,放胆走上去叫了一声大姨。大姨提着一兜从超市买来的打折鸡蛋,茫然地看了一眼夏兰兰。大姨印象里,夏兰兰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猛然有一个成年姑娘站在面前叫她,她的第一反应不是亲热,是戒备。
“大姨,我是兰兰。”夏兰兰背着沉重的大包,自己报名道。
大姨愣了一分钟:“你怎么来了?你妈还好吗?”
“我妈我爸都好,他们可想你了。本来要给你打电话,可是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哦……手机号码换了。可你应该先给你姨夫打个电话啊,他手机号没换。你这不吭不哈地来了,家里还没收拾,怎么住得下?还有你这么大的包......家里地方小,往哪儿放呢?”
被大姨这么一说,夏兰兰觉得自己像个累赘,和自己身上的大包袱一样,给大姨家里添麻烦了。开在脸上浓浓的一脸笑花,瞬间冻在僵硬的嘴唇上。
大姨不冷不热地看了几眼陌生外甥女。夏兰兰背着大包,在太阳地里站着,打听了好几个街区,才找到大姨的家属院,她走得实在太累了。脸上晒得滚烫,小腿上也像着了火。
身上烫,可心里凉。临出门,爸妈往大包里塞了好几包菌子、木耳,都是父亲在山里采的。妈说,大姨做姑娘时,最喜欢上山采菌子、木耳吃,要多带点,她一定爱吃。
如今看来,大姨是不会稀罕的,城里到处是商店、超市,超市里什么东西没有?可愚笨的父亲冒雨在山里采了这么多,兰兰一想起父亲背着篓子进山的样子,不觉心酸起来。
大姨领着夏兰兰往家里走。这是一个普通的厂区家属院,大姨家是老房子,不大,走进屋,家里并没有什么高档家具,甚至那把凉椅,还是一把老式竹椅。大姨把排队买来的鸡蛋放进厨房,一屁股坐进老式竹椅里,竹椅突然受力,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
夏兰兰坐在大姨对面,她看到大姨的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白色的塑料拖鞋晃晃悠悠勾在脚尖上,随时可以啪地一声掉下来。大姨用一把塑料凉扇扇风,一下一下拍打在胳膊上,仿佛睡着了。
“你进城来有什么打算?”大姨从半睡里透出声音。
“我打算找一份工作,山里没有什么出路。我爸妈老了,他们在山里一辈子,不打算出来了,可他们说我还年轻,应该进城找一条出路。”夏兰兰看着大姨说。
“山里没有出路,进城就有好工作了?你们现在和我们那会儿不一样了,我那会儿,毕业了包分配,现在哪有上学包分配的。现在多少城里的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你连大学都没上过,怎么找工作啊?”
“可我能吃苦,我干活不怕累,我一定能找份工作养活自己的,大姨!”
塑料扇子一下一下拍打着胳膊,停了半晌,大姨起身进厨房去了。过了一会儿,从厨房飘来大姨淡淡的一句话。“你先住下吧。”
夏兰兰开始找工作,餐馆服务员是上岗最快的工作,她长得不差,被分配到包厢。可夏兰兰还没学会给酒精炉加火就上岗了。她在往酒精炉里加酒精时,没有先灭火,酒精一加进炉膛,炉里的酒精被瞬间点燃,喷出一条火舌,直冲女顾客的身上蹿去。
夏兰兰一把扔飞了酒精,女顾客尖叫着跳起来,她也尖叫着跳,包厢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两个女人惊恐的喊声。隔壁包厢的服务员宋小宝听到喊声,一把推开门,用一张台布蒙住酒精炉,迅速扑灭了火。
被吓蒙了的夏兰兰只知道哭。宋小宝却忙开了,忙着道歉,鞠躬,递凉毛巾,姐长姐短地叫着,替女顾客送果盘,给经理解释,收拾台面……一系列的活儿,宋小宝替夏兰兰全干完了。等夏兰兰哭完了,女顾客早就不喊叫了,又点了两道菜,还让经理免了对宋小宝和夏兰兰的责罚。
宋小宝真有本事,夏兰兰用感激又崇拜的目光看了看宋小宝。下了班,宋小宝拉着夏兰兰的胳膊一个劲吹气:“烫着了吗?以后做事小心点……”他要看,就给他看呗,她伸着胳膊没往回缩。谁让人家帮了自己这么大的忙呢,没有宋小宝,你夏兰兰明天能不能来上班都不一定呢。
“我要是被开除怎么办?”夏兰兰担心地问。
“傻瓜,有我在,你就不会被开除。以后有什么事,你就叫我。”宋小宝拍了拍胸脯,好像餐馆是他开的。这份仗义,让夏兰兰觉得踏实。
她做了他的跟屁虫。宋小宝最喜欢和她说话,他让她叫哥,她就叫哥。她愿意跟着他,跟着他学端菜,学点餐,学摆盘,有了这个“哥”,夏兰兰觉得自己不会被开除了。
她白天上一天班,晚上回去,大姨一家早就睡觉了,仿佛她是一个空气人。大姨和自己没话,姨夫也不常在家。躺在床上,她把头埋在臂弯里,静静地回想一天里他的影子,他和自己说的话。他跑在餐厅走廊上的样子,干练、麻利地传菜,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亮晶晶挂在脸上。她想伸手给他擦一擦,把他揉皱的衣领整一整,她不自觉地伸出手,停在半空中,心里有一股暖融融的感觉冒出来,流遍全身。
一年后,夏兰兰搬出了大姨家,她和宋小宝住在了一起。
一天,宋小宝神秘兮兮地说:“城中村快拆迁了,能分房!”
“分房?”
“你想不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想啊!”
“我也想。”
宋小宝真有这样的朋友,专门拉皮条,找女人“嫁”给城中村的穷光棍,宋小宝和夏兰兰花钱,老头卖人格,他们合起伙来糊弄城中村里多得住不完的房子。
荒凉的房间里,节能灯闪了一下。“小宝,我去。”夏兰兰抱着宋小宝说。宋小宝一下转过身来,在夏兰兰的脸上响亮地亲了一下。
二
夏兰兰和老头去民政局领证的时候,穿着一身红裙子,跟在老头身后,老头走到哪儿,她走到哪儿,工作人员问什么,她就答什么,像个乖巧的小媳妇。宋小宝和几个老乡冒充亲友团一起去了。宋小宝的喉头发紧,不时紧张地咽一下,他紧紧盯着老头的一举一动,看老头的手有没有碰夏兰兰。
宋小宝竖起耳朵听夏兰兰说的每句话,看老头和她走在一起时的距离。老头今天打扮得真像新郎,花白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竟然还穿了一套西装,虽然是一套廉价的西装,却配着皮鞋,挺像那么一回事。这更让宋小宝气不打一处来。还真把这场戏当真演了?
老头走得挺慢,每走几步,就回过头等等夏兰兰。民政局好几个办公室,楼上楼下地走,夏兰兰一直微微低着头,跟在后面。宋小宝在离得不远的地方一路跟着,像一头紧盯猎物的豹子,他冷眼看着前面两个人,越想越不是滋味,可只能咬牙忍着。
照相的时候,摄影师让老头和夏兰兰坐得近点。老头的目光闪烁了一下,嘴唇抿着,坐直了身子,向夏兰兰靠了靠。老头发出短促的呼吸声,他既庄重又紧张。
这让夏兰兰的心里突然很难过。他这么紧张,恐怕他这辈子都没有拍过结婚照。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一辈子没结婚?还是他也有过喜欢的女人,只是最终没走到一起?他这样的年纪,本应是含饴弄孙的生活,可他连儿子都没有。当初拉皮条的人指着老头的照片,像指着一头待价而沽的动物说,放心,绝对不会有人找你们麻烦,这老头干净——真是老光棍,连孩子都没有。
老头是一个人来民政局的,一个亲友团也没有,为了赚这八千块钱,老头也是豁出去了。
“看这儿,笑!”喀嚓一声,摄影师按下快门。老头紧张地笑着,夏兰兰似笑非笑。宋小宝瞪着一双豹子眼,狠狠咽了一下唾沫。
晚上回到出租屋,夏兰兰脱下那身红裙子,换上睡衣炒菜。把菜端上桌,宋小宝依旧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小宝,吃饭。”宋小宝根本不理夏兰兰。“小宝,吃饭。”再叫时,宋小宝从床上一跃而起,光着脚蹦到餐桌旁,端起一盘红烧鱼啪地摔在地上。红烧鱼的汤汁泼洒一片,溅到沙发上、床上、夏兰兰的睡衣上,艳丽的带血的桃花一样。
夏兰兰没有哭,宋小宝蹲在地上,大声哭起来。夏兰兰蹲下来,一把搂住他的头。
第三天,老头就来叫夏兰兰过去住。
城中村的村长和几个村干部都上门看望老头,他是村里有名的光棍,临老了娶上媳妇,还是这么年轻的媳妇,能不来看吗?头一天还能挡,说夏兰兰回娘家了,第二天怎么办?不但要看,还吵着要喝喜酒。
宋小宝用三轮摩托车拉着夏兰兰和行李,一路颠簸着,到了老头的房子。夏兰兰这才知道老头叫冯立本。当着人面,她什么也不叫,没人的时候,她叫他冯叔。可宋小宝坚持什么都不叫,白搭话。他只是在冯立本的屋子里转,检查老头的屋子,每间房子都看,尤其是厕所和浴室,看看里面的锁,他把夏兰兰关在里面,关上门,自己扭了半天门,打不开,他满意地笑了笑。
“你干嘛啊?”夏兰兰被关在厕所里,拍着门问。
“我看看老东西会不会使坏!”宋小宝隔着门说。
夏兰兰出来打了他一下说:“你怎么这么多心啊,他不会的。”
“不会?听见女孩洗澡,他什么都会了!”
宋小宝拉住夏兰兰,指着大门口说:“他要敢犯浑,你就喊人,门正对着街道,你一喊,他就不敢了。给我打电话,我立刻来收拾他!”
夏兰兰甩开宋小宝的手,阴沉着脸扔下一句:“当初不知道是谁出的馊主意,现在又防贼一样折腾我!”
夏兰兰心里竟然对老头有了点歉意。是因为宋小宝明打明的不信任,还是对老头一生孤苦的同情,夏兰兰自己也说不清。她只是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她和老头各睡一间屋子,起来的时候,老头屋里的灯还没亮。她悄悄起来做好早饭,自己吃完,把老头的那一份闷热在锅里,出门上班。
一天早上,天蒙蒙亮,夏兰兰听到厨房里有响动,她警惕地爬起来,伸出头往窗外望。窗外竟然是老头,他今天起得这么早?他手里提着一锅豆浆,一塑料袋油条,正在厨房里拿勺子拿碗。
夏兰兰急匆匆穿好衣服走出来。老头局促地看了一眼夏兰兰,磕巴着说:“起来了?快吃饭……早上第一锅新鲜的豆浆,油条也是第一锅,热乎乎的,快吃吧。”
夏兰兰的手里被塞进一根油条。
“冯叔,我还没刷牙,刷牙洗脸完再吃吧。”
“哦,对,对,你快去洗,油条先放下。”
老头抢过油条放在案板上,放得太猛,打翻了白糖罐。夏兰兰急忙上前扶,老头也扶,头凑到一起又赶紧分开了。哎,这不伦不类的生活!夏兰兰心里叹了一声,却又有一股暖流,顺着豆浆油条的气息飘过来,在清晨的薄雾里飘荡。
但老头吝啬,还贪小便宜。每天早上他去油条摊上买豆浆,都要缠着摊主多加一勺。摊主给他加一勺,他又把白糖狠狠舀两勺,洒进豆浆锅里。自从他发现摊位的餐桌上有免费自取的白糖,老头就不再用家里的白糖了。但他放得实在太多,每次夏兰兰都喝得齁嗓子。
夏兰兰是有一天提早出门时发现豆浆的秘密的。宋小宝突然有一天一大早来找她,为了监督她究竟睡在哪间屋子。夏兰兰被宋小宝催促着穿上衣服,坐上他的电瓶车一起上班。走到油条摊前,夏兰兰要给老头打招呼,正撞见老头拿着大铜勺往锅里加豆浆。
电瓶车穿梭在城中村低矮的巷道里,大门上“院内有空房”的粉笔字从夏兰兰眼前滑过。门口闲坐着吃早饭的女人和抽烟、发呆的男人。隔夜垃圾乱糟糟堆在墙角,一两只流浪狗在垃圾堆里刨食。大清早,盖楼的工匠已经开始干活。地上的沙子围起一堆水,工人正在搅拌水泥。很快,一层层在自家院子里加盖起的危楼会拔地而起。房主在尽最大努力加盖到极限,以求在城中村拆迁时多占些面积,多分几套房。
老头家里穷,没钱加盖楼房,他只能守着自己的一个院子,拆迁时能分几套就几套吧。想到这儿,夏兰兰有点失望。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老头富裕,他还会为了八千块钱和自己假结婚吗?
街边,闲散的男人们支起麻将桌,沏上一壶茶,开始打麻将。亮红灯的小旅馆,熄灭了亮了一夜的红灯。洗脚房的按摩西施露出雪白的大腿,她拿着小镜子往脸上抹粉,脸上刷白的,只是眼睛红得刺目。
这就是他生活的环境。夏兰兰鄙薄老头的那点心思升腾起来,又渐渐散去。今天回去该给他交伙食费了。除了八千块,夏兰兰住在老头家的这段时间,住免费,伙食费另算,直到村干部不再拜访老头,夏兰兰就可以搬走,这是事先商量好的。
晚上回来,老头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夏兰兰把钱放在桌子上:“冯叔,这个月的伙食费,你数数。”老头的眼睛一亮,伸手要去拿,可又看了一眼夏兰兰,顿了顿说:“啊……辛苦一天了吧,我把电视开小点。”
“不碍事,你也早点睡吧。”夏兰兰出了客厅,走进自己屋子,想起包忘了拿,又返回去,正看见老头用大拇指蘸着唾沫,一张张搓着纸币数钱。搓一下,举起来对着灯看看真假,看完了,再放在耳朵边揉一揉,听纸币的声音。夏兰兰刚站在门边上,又转身走了。她不想让老头尴尬。
三
老头还有一个儿子的事,连给夏兰兰拉皮条的中介人都不知道,老头瞒得真干净。夏兰兰若非这天晚上亲眼所见,也不会相信老头会有这样的儿子。老头年轻时和一个女人好过,但女人嫌老头太穷,带着孩子嫁了他人。女人和老头再无往来,可养出来的儿子不成器,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没工作,每日打牌为生。家里的钱被掏得干净,后来知道了自己竟还有一个亲爹,小伙子便隔三差五上门问老头要钱。
老头从没有承认自己有儿子,他不认。他也没钱给这个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儿子。可儿子不这样想,你二十多年没有养过我,现在花你点钱,怎么就不应该?
“我没你这个儿子,你走!”晚上,夏兰兰刚上床睡下,院子里传来老头的说话声。灯影里,老头和一个小伙子站在院子里。
“你不给我钱,当初为什么生我?我听说你又结婚了?你当初撇下我们母子不管,现在你多大年纪了,娶一个女孩?你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哩!”小伙子叫喊着,他用手愤怒地指着老头。
老头啪地打开他的手,“你给我走,当初是你妈嫌弃我,不和我过,不是我不要你们。我不欠你的,你给我走!”
“你还要抵赖?你就眼看着我输光了钱,你也见死不救?”
“我没你这样的儿子,我早就给你说过,不要打牌,你不听,今天这步是你自找的。”
小伙子眼看要不来钱,气急败坏,忽然看见客厅桌上夏兰兰给的伙食费,他冲进屋子就抓,“你明明有钱,你骗我说没有,你的心真狠啊!”
老头拉住儿子的衣服,去抢他手里的钱,“还给我!”哧啦一声,老头的短袖破了。
儿子紧紧攥住钱,猛地挣脱他,朝大门外走。老头浑身颤抖着,追上去,伸手去拽儿子的胳膊。可扑了一个空。
儿子一把甩开老头,快速朝大门外跑:“你见死不救,你老了我也不会给你送终!”
老头颤抖了一下,雷打般,手无力地垂下来,脚下一软,跌倒在院子里。儿子早已跑远,老头的破短袖从两边的手臂上跌落下来,像两块破抹布,披在老头肩上。老头深陷的眼窝里流出浑浊的泪水。
夏兰兰急忙穿好衣服,把老头从地上扶起来,坐进屋子。汗水混合着泪水,从老头的额头上、眉弓上、眼睛里流下来。夏兰兰一句话不说,她找出针线,默默缝补着老头那件破裂的短袖。
老头花白的头发一缕一缕挂在头皮上,他抖着嘴唇,费了好大力气不让自己发出哭声。夏兰兰不抬头看他,低头缝衣服,她找不出合适的话语劝他,也不想直视他的痛苦,让他自己慢慢平静一会儿吧。
“谢谢。”好一会儿,老头的嘴唇不抖了,“兰兰,你去睡吧,我没事。”夏兰兰收拾好针线,准备回房间:“好,冯叔,衣服补好了,你也早点睡吧。”
他忽然拉住她的手。她吓了一跳,准备挣脱,却看到他的眼睛很平静,静静地端坐着,没有一丝侵略性。“谢谢你给我缝好了衣服,谢谢你把这个家收拾得这么干净。谢谢你……今晚啥也没问……”
夏兰兰没有挣脱自己的手,她笑笑说:“这没啥。”
“你每天上班,路远吗?”老头问。
“不远,坐公交车五站路。”
“哦......这么久了,我竟然不知道。其实挺远的。”
“不远,你早点睡吧。”
“你在城里还有亲戚吗?”
“还有一个大姨,但我大姨……上班忙,我去得少。”
“伙食费,你以后不要给我了,你吃得太少,不要给我了。”
夏兰兰刚要反对,老头松开她的手,推了她一把,“去睡觉,去睡,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五站路,不近。”
夏兰兰躺在床上,心还在砰砰跳,老头不要伙食费了,怎么给宋小宝说呢?
果然,第二天,宋小宝把餐盘咚地蹾在理餐台上,瞪着眼睛问夏兰兰:“什么?他那么吝啬的人,为什么不要伙食费了?他把你怎么了?”
“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刚给你说了吗?”
“你给他补衣服,他还摸你的手?”
“宋小宝,你听得懂人话吗?我不是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你了?”
宋小宝根本不听夏兰兰的解释,他气呼呼地摔着托盘,“老东西,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这天晚上,宋小宝坚决没让夏兰兰回到老头那里,他把夏兰兰带回出租屋,扔在床上,趴在她的身上一边进入一边发火。她一声不吭,默默承受着。他紧紧搂着她:“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你非要把我折磨疯!”
平静下来后,他点燃一支烟,望着天花板发呆。她吻着他的短头发,他依然一句话也不说。算了,他一定心里难受。夏兰兰躺在宋小宝身边,陪着他发呆。窗外的野猫叫了一两声,夜深了,风紧一阵,又缓一阵。
四
那是一座沿着马路而建的农贸市场。市场正在修建中,顶棚用绿色的塑料遮阳板覆盖,里面绿森森一片。人在里面走动着,仿佛鱼在水草里游。
老头坐在一堆高高垒起的新砖前,用一只凉帽扇风,有人叫他,他就走过去帮忙抬水泥,推推车。这是他新找的工作,在建筑工地上看砖,拌水泥沙子。这是他这样的年纪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工作。
夏兰兰和宋小宝是在看到老头拿着水管子给砖堆浇水时,发现这个秘密的。老头浇砖的水流了一地,宋小宝的电瓶车一个刹车,准备绕道。绕道的一瞬间,夏兰兰看清了那个浇砖的人是老头。
他为什么到工地上打工了?是受到夏兰兰的感化,觉得自己游手好闲的生活太惭愧,还是一个人的生活实在太闷,在工地上能找人说说话?谁知道呢。夏兰兰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她猜不到答案,只看见老头矮胖的身影在砖堆前走动,砖堆几乎淹没了他。
“呀呵!老东西也上班了?不错啊,学会自食其力了!”宋小宝停下车,幸灾乐祸地看着老头。
夏兰兰没有理宋小宝,她忽然看见老头绊了一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倒。浇砖的水管子太长,奇形怪状蛇一样盘在地上,老头的一只脚缠在管子里,往前扑着,头上的凉帽跌落在水地上,他去追自己的帽子。
他的脚上套着水管子,像一头笨拙的老熊,手舞足蹈地抓扑着泥水里的帽子。
夏兰兰跳下电瓶车,帮老头去捉泥水里的帽子。宋小宝在身后大喊着:“你给我回来,不许去,你就那么身子轻!”夏兰兰根本不听宋小宝的喊声,她跑起来,跑向老头,帮他去捉那只帽子。
老头抹着手上的砖末和泥水,接过帽子时,他认出是夏兰兰。他半蹲在地上,这个姿势让矮胖的他显得更滑稽。他仰视着她,好像这帽子不是她帮他捡的,而是她赠给他的。
老头的儿子又来找过一次老头。上次抢走的伙食费很快输光了,多少钱,也顶不住赌博的花销。老头什么也没说,他带儿子到工地上呆了一下午。他让儿子看自己搬砖、浇水、抬水泥、拌沙子,让他也搭手。儿子从没有干过这样的粗活,他刚抬了一袋水泥,就嚷嚷着自己的手破了。
“破了你就走吧。”老头眼不抬地干活,闷着头说。
“可我没钱了!”儿子搓着自己的手依然不放弃,在做最后的挣扎。
“没钱了,你就搬水泥,你能比我搬得多。”老头背过身去,用毛巾擦了一把汗,他再没有回头看一眼儿子。儿子什么时候走的,他并不知道,他只是知道,他再也不会来了。
夏兰兰也再也没有去过大姨家。那不是她的家,大姨有大姨的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夏兰兰是宁静、知足的。
只有宋小宝很烦躁。“下个星期,你就给我搬回来住。村干部已经去老头家好几次了,不会怀疑了。你的户口已经迁到老头村里,只要一拆迁,就能分到房。一分到房,就离婚,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夏兰兰知道宋小宝在想什么,他想让夏兰兰尽快结束这不伦不类的“婚姻”。夏兰兰收拾东西,准备搬走。她打扫了院子,又把老头的几件脏衣服洗了,屋子里那些半旧的家具,她一一擦洗干净。擦到厨房时,夏兰兰看到了那个糖罐。糖罐的盖子上结着几块糖疙瘩,夏兰兰用抹布擦干净,她微微笑了笑,想起老头第一次买豆浆回来时,那慌里慌张的样子。
老头这一晚上,再没有回来。夏兰兰的手机尖锐地响起时,是晚上九点多。夏兰兰是老头唯一能联系到的“亲人”,工地的工头通知她赶快过来,今天下午运砖时,砖墙倒了,老头的腿被砸伤,现在正躺在医院里。
“你没毛病吧?他住院了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他什么人?”宋小宝听到夏兰兰说要去看望老头时,正在吃饭,将筷子摔在桌上。
“工头说他砸得不轻,现在正在医院输血。”夏兰兰急急地说。
“这究竟和你有什么关系!”
“小宝,咱们毕竟和他认识一场。”
“可我们已经给过他八千块,两清了!”
夏兰兰没再搭话,她拎起包,走入茫茫的夜色中。医院的病房里,白皑皑一片安静。只有氧气瓶咕噜咕噜的气泡声回荡在屋子里。夏兰兰坐在老头的床前,老头闭着眼睛,没有一点声音。
许久,老头也许感觉到了什么,他睁开了眼睛,“兰兰,你怎么来了?”
“工头打电话给我的。”
“哦,让你大晚上跑过来,对不住你……”
夏兰兰摇了摇头:“不,冯叔,我应该来的……”
夏兰兰的手机响了,宋小宝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地喊着:“我就在医院楼下,我在等你,你下来,跟我回去!”
老头听到了电话里的声音,他用力从被子里抽出一只手挥着说:“快回去,兰兰,我没事,快回去。”
夏兰兰犹豫着,她看见墙角放着一辆轮椅,她突然醒悟到,老头的下半生可能只能坐在轮椅上了。夏兰兰的心里打翻了各种调味瓶子,那些瓶瓶罐罐在心里乱成一团,五味杂陈。
夏兰兰拉住被子里那双又老又皱的手,她紧紧握着。两双瑟瑟的手,抖得无法停止。
老头忽然松开了她的手,一行浑浊的老泪滴落在被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