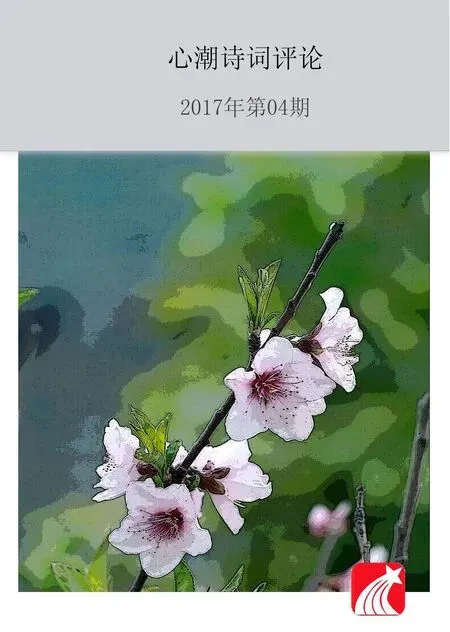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
——真意坦率、刚柔并济的达夫抗战诗词
常苗林
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真意坦率、刚柔并济的达夫抗战诗词
常苗林
新文学作家之中,爱写、擅写旧体诗者不在少数,在这其中,鲁迅和郁达夫历来被视为成就最为突出者而被反复提及。鲁迅旧体诗数量不多,但偶有佳作,即臻绝唱。达夫天性率直而好吟咏,有大量的旧体诗作留存。其中,或兴之所至,养性怡情;或感慨时事,寄托遥深。
“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自述诗·其六》),郁达夫不仅是天才型作家,更是天赋型诗人,九岁能题诗,十五岁读到吴梅村的诗集,“忽遇江南吴祭酒,梅花雪里学诗初”(《自述诗·其十二》),诗词的创作可谓贯穿其整个的文学生涯。他的旧体诗题材广泛,咏史怀古、感慨时事、写景记游、自述情思、赠别酬唱、题画题壁等不一而足,风格上或浪漫忧郁、凄婉感伤,或悲愤呐喊、气势磅礴。
郁达夫性格柔弱,敏感多情,心绪极易波动,相比于鲁迅的沉郁冷静,郭沫若的万丈豪情,徐志摩的飘逸空灵,他的感伤与愤激往往表达得最为明显和完整。达夫爱国并志报国,家国危亡的责任担当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始终是萦绕其诗词的最为明显的情愫,真意坦率、刚柔并济则成为其抗战期间诗词最为典型的美学风格。
抗战前: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
抗战爆发前夕,郁达夫的诗词还延续着一贯的婉约柔美风格,虽忧郁感伤,但绝无鲁迅所说的“夸耀颓唐、炫鬻才绪”的嫌疑,每一首歌泣有端而字字真情。幼年失爱于父母,青年所遇非人,中年流离困顿,未达天命之年即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郁达夫常称自己为“悲剧的出生”,这种忧郁感伤的心理也伴随了他的大半生。
“溪声摧梦中宵雨,灯影摇波隔岸楼。虫语凄清砧杵急,最难安置是乡愁”(《秋宿品川驿》)。留学日本时期的郁达夫,常常陷于思乡怀国的身世之感之中,祖国风雨飘摇而内乱频仍,远在日本的他自是有心无力,“南渡中流思祖逖,西风落日吊田横。何堪重说长安事,兄弟操戈议未平”(《王师罢北征》)。彼时,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远在日本的郁达夫痛切难忍又深知自己是柔弱无力的文人,于是希望能够出现祖逖、田横一般的爱国良将,能够救民族于危亡,挽国家之颓势。
“升沉莫问君平卜,襟上浪浪泪未干”(《晓发东京》)。由于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感慨、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国内局势的担忧相交织,抗战之前的郁达夫诗词往往读来凄切动人。“俊逸灵奇宰相才,卞和抱璞古今哀”(《杂感八首·其一》),“诸葛居长怀管乐,谢安才岂亚伊周”(《新秋偶成》),“亦有宏才难致用,可怜浊水不曾清”(《客感寄某》)。果然不出所料,一直自视甚高,自信有宰相、诸葛之才的郁达夫回国之后连连碰壁,生活困顿、情路坎坷、社会压迫、国家动乱,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郁达夫陷入忧郁、愤激、悲戚的无限循环之中,总体上形成凄婉感伤的美学风貌。
抗战中: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
抗战爆发后,哀婉柔弱的郁达夫也立刻投身于抗战洪流之中,国难当头,那些凄凄切切的低语吟唱和温情脉脉的思念感怀都化作高亢激昂的呐喊疾呼,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召唤和家庭破碎的失意痛苦之中充满了悲壮的意味。
“目今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侮,当系目今之天经地义。”早在全国性抗战未真正爆发之前,郁达夫就写信给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敦促其回国抗战,其自身也通过加入左联(不久即退出,单独抗战)、写文章大声疾呼、联系国内外同好等参与抗战。此时,其诗词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首先,语言多白描而少修饰。“马二先生真好汉,能屈能伸能苦干。昔从西北练精兵。今到中央弄笔杆。莫嗤丘八变诗人,杜甫伤时涕泪新。萁豆相煎何太急,英雄虽老岂轮囷。抗战今年将胜利,加强团结全民意。……”(《冯焕章先生今年六十,万里来书,乞诗为寿。戏效先生诗体》)虽是戏仿,语言上力求靠近冯玉祥“丘八诗”口语式的通俗浅近,但“国破家亡”“傀儡登场”等词语不断出现在其此时的诗作之中,“文人几个是男儿,古训宁忘革裹尸”,虽然被目为新文学作家,但是儒家忧患承担意识还是渗入骨髓,正如他自己所说“像我这样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只是在此时他褪去了以往的侬粉修饰,抛却了佯狂颓唐的外衣,融入了民族救亡的大合唱之中,真意坦率的情感以浅近通俗的语言流出,成为真正的“爱国诗人”。
其次,风格由温情脉脉的浅吟低唱转向毁家纾难的激越悲壮。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携妻儿远赴新加坡宣传抗战,同样是远离故土,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褪去当年赴日留学的青涩与感伤,当年的侬粉诗虽也出自青莲,但毕竟少年意气,叹弱嗟贫的字句也多少难脱诗歌撒娇的嫌疑。当年那个忧郁哀婉的诗人此时的作品已难掩“中年情调”,况且家中也遭逢不幸,其妻子被昔日的故交好友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徐绍棣诱奸,“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然而此时的他依然以民族大义为重,将屈辱与家丑暂且隐忍不发,高喊着“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贺新郎》)。在国家危亡和如火如荼的抗战中,诗人的爱国激情压倒了毁家的离伤和屈辱。“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毁家诗纪·其四》)。一语双关地将国与家情思与共、祸福相依的密切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唯有在这种“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毁家诗纪·其十三》)的激越豪情与悲壮之中,他才能获得些许的安慰吧。“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乱离杂诗·其十一》),“卷土重来应有日,俊豪子弟满江东”(《廿八年元旦因公赴槟榔屿,闻有汪电主和之谣,车中赋示友人》),“拼成焦土非无策,痛饮黄龙会有期”“怜他傀儡登场日,正是日斜欲坠时”(《闻鲁南捷报,晋边浙北迭有收获而南京傀儡登场》)。如此金刚怒目式豪迈与坚韧语句倾吐了诗人心中郁积愤懑与不甘,读来自是令人豪情满怀。正如刘海粟老师所评价的其后期诗歌风格“痛快沉着,托物明志,朗润含蓄,其信念之坚强,更在豪迈之外”。
最后,化用甚至是挪用前人诗句也是郁达夫此时诗词的重要特征。他非常推崇黄景仁,历来也有不少学者将其与黄氏相比较,坎坷的身世以及诗中绵延不绝的怅惘与悲凄是二人的共同特征,郁达夫也经常化用黄氏语句,如黄景仁在《绮怀》中有“茫茫来日愁如海”,郁达夫则在《乱离杂诗·其七》中则以“茫茫大难愁来日”来表达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担忧,再如其《金丝雀》中的“岂不怀归畏简书”与《诗经·小雅·出车》的“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如出一辙,而“寂寞人间五百年”与“此情可待成追忆”更是直接挪用。这自然没有邯郸学步与东施效颦的丑态,更非江郎才尽的尴尬,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之聪慧,是熔铸百家的气魄,当然那些情人间的旖旎情思,家国天下的忧患与担当意识,古今自有相通之处。化用与挪用,只是手法,无关才情与品格。
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
少年时天纵英才,九岁即能赋诗;青年时远渡重洋,敏感多情的岁月诉不尽的是对自身家国命运的无限怅惘;中年时再度远离故土,为挽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抗战前,他敏感多情,诗句哀婉柔美;抗战时,他刚毅坚忍,诗句悲壮激越,从温情脉脉到气势磅礴,改变的只是心境与风格,那颗拳拳爱国之心却未减分毫。
1936年,郁达夫在《赵龙文录于右任并己作诗题扇贻余,姑就原诗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诗》中写“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没想到一语成谶,1945年,他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任职《星洲日报》期间,他的第一篇文章是《估敌》,文中他不断地呐喊道:“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彼时,这些语句真正地起到惊破残梦、唤醒斗志的作用;此时,我们再次吟咏其《满江红》,共同祈愿英灵不灭,金瓯无缺:
福州于山戚武毅公祠新修落成,于社同人广征纪念文字,为填一阕,用岳武穆公原韵
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到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 会稽耻,终须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