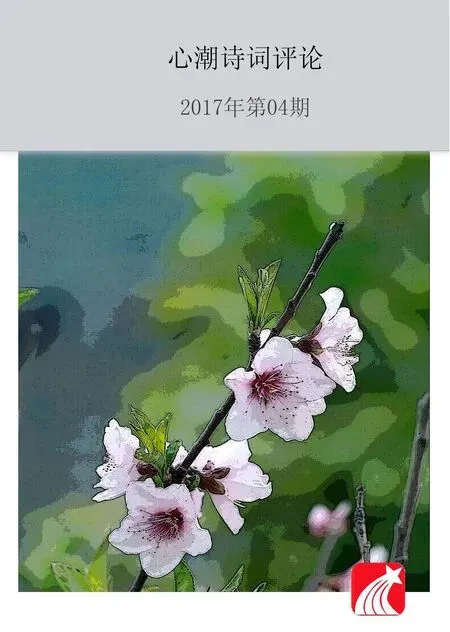放翁继响,老杜回声
——论钟敬文先生的“抗战诗”
归 仁
放翁继响,老杜回声——论钟敬文先生的“抗战诗”
归 仁
钟敬文先生不但是当代著名的民间文学学者,当代“民俗学之父”,还是著名的诗文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之一,他自己也很注重自己的诗名,尝云:死后能在墓碑刻上“诗人钟敬文”足矣。为此,我曾作过两首白话《如梦令》,其词曰:“常见校园清晓,一叟神扬步矫。借问‘是何人?如此神仙仪表?’‘知否,知否,此即敬文钟老。’”“‘我亦久闻钟老,早是一级国宝。提起民俗学,谁不倾心拜倒?’‘尚少,尚少,还有诗文更好。’”钟先生诗文佳作甚多,而最令人感佩莫过于他的“抗战诗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钟先生毅然辞去长期从事的大学教职,投笔从戎,到广州第四战区任视察专员,从事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以鼓舞群众。其间转战粤北湘南,亲赴战地,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抗战报告文学和抗战诗歌。
钟先生论诗特别强调诗歌创作要有饱满的激情,要紧密地贴近现实,要有“诗史”的价值。如云:“据说古代希腊人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这是诗人职能最好的象征。”“深沉的忧苦,是诗人献给‘真理’的特定礼物。”“由于心脏的搏动而咏唱出来的真理是诗。”(见《兰窗诗论集》)又说:“五四”之前自己只是个“旧式的士人的候补者”,“五四”之后虽开始写新诗,但还是把“自己关闭在学院里”,只有亲身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后,自己的“学艺(包括诗学)观点,特别是在它的实践上,才有了比较明确的改变”,“变得实际些、坚强些”(见《历史的公正》)。而钟先生诗歌创作的高潮即在这一时期,所留下的数十首作品,可谓首首精彩,确实是用心脏的搏动谱写出的战歌,是出征时响在前面的号角。正像他所总结的那样,“这些成果,本身未必有什么超越之处,但是它与当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哀乐连接在一起,也是与我这时期整个意识形态的变动和腾跃血肉相关的。战争真是一个洪炉,它烧毁了许多东西,也炼铸了许多东西”(见《历史的公正》)。
钟先生的“抗战诗”践行了他的诗论,这些创作最明显的特点是对陆游与杜甫的继承和发扬。
陆游最值得盛赞之处不外有二:一是他在强敌入侵前所表现出的高度的战斗精神和爱国情怀,二是他诗句中所迸发出的火热的激情和英雄的气概。钟先生最服膺、最称赞的正是这两点。他在抗战期间毅然投笔从戎时说:“抗战期间,我……行囊里的书籍只有一部《陆放翁诗集》。在粤北转徙无定的生活中,放翁那些燃烧着火热爱国情思的诗句,当时成为我精神的一根重要支柱。”“陆游生在南宋的时候,朝廷没有收拾旧山河的宏志,他一股忠勇的意气抑郁在胸里,一有机会便发泄出来,所以在他的诗集里,我们随处可以感觉到这点。‘和戎壮士废,忧国双泪滴。’这种境遇真太值得哀伤和同情了。他生平对于杜甫颇为致意,读杜诗结句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即咨嗟。’这正道破了自己的心事。数年前,住杭州乡间,曾做了一首题剑南集绝句:‘莫道孱迂不解兵,梦中往往夺松亭。骑驴细雨消魂事,终竟诗人了此生。’三四年来每回出行,总把剑南集放在皮箧里,因此前年冬在始兴所作诗中,就有这样的两句:‘激昂降未得,三读剑南诗’”(见《兰窗诗论集》)。
类似这样直接歌咏陆游、或直接书写陆游对自己创作影响的诗篇,在钟先生的诗集中比比皆是。如六十岁时所作的《六十回忆杂诗》其三十三还说:“抛却群书利转移,囊中留得剑南诗。清笳响断吟声歇,犹梦黄旗北渡师。”更重要的是,他能把这种放翁情怀自然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其实,早在1934—1936年钟先生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他的诗作已经有了这种陆游式的情调。如《过奈良故都》云:“冻云癯鹿助清寥,肃肃髡杉梦故朝。过客雄心未能死,百金欲买奈良刀。”(自注:时华北形势危机,奈良刀为此邦名产)这种情怀使我们不由得想起陆游《金错刀行》等借宝刀以抒豪情的作品。到抗战开始后这类陆游式的调子在钟先生的作品中更是大量出现。如《赠救亡青年》云:“森然背影如杉柏,雄劲歌声彻水云。揭却忧霾吾一笑,创新排难岂无人!”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陆游的“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的豪情。又如《别胥之同志》云:“日暮军笳动离席,豪情别意两难平。”使我们不禁想起了陆游描写的“笛里谁知壮士心”(《关山月》)的情景。再如《村居书感》云:“许国身宁计近遥,只灯山馆坐清宵。……斩敌剑愁三尺短,慰情山爱一痕娇。”《得秋帆桂林书诗以答之》云:“军行无定迹,宵梦亦相思。……匈奴尚骄悍,未许说归期。”使我们不禁想起了陆游的“直斩单于衅宝刀”(《雪中忽起》),“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等诗的意境。直到六十岁时,钟先生还念念不忘这一段诗缘:“磨崖勒语非虚愿,终见山河属汉家。”“平生诗稿怜飘散,最是难忘战地诗。”“最忆翁江严逻夜,高高霜月照戎装。”(均见《六十回忆杂诗》)这些描写仍能使我们想起陆游“抉眼终看此虏平”(《书愤》),“高城刁斗夜分明”(《醉中感怀》)等坚定的志向和执着的精神。
更可贵的是这种陆游式的情调不但出现在“战地诗”或回忆战地生活的诗中,还出现在以后其他题材中,这可视为这种风格的本色流露。如1979年所写的《北戴河》:“避暑名区傍海开,绿荫处处见楼台。中宵陡觉军声壮,无数惊涛捍梦来。”这自然令人联想到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又如《纪事》云:“八十高龄今过了,热情犹似少年时。”《黄果树观瀑》云:“白头结队观黔瀑,未觉疏狂减少年。”这种意气风发且老而弥坚的热情,不正和陆游八十二岁时所写的“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如出一辙吗?
杜甫是中国仁人志士型诗人的代表,可以说,杜甫之后,任何一个具有士精神的诗人无不受其影响,钟先生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这种影响已深入到骨髓之中。杜甫及杜诗对后代最具影响之处不外有四:一是深厚的忧国忧民情怀,一是责无旁贷的承担精神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一是博大浩瀚的史诗格局,一是精深的写作技巧。而这些境界在钟先生的诗论和诗作中都有深刻的体现。他除了称赞杜诗中某些诗句“意境卓特,词笔矫健,境象壮快”外,更特别强调:“从内容的深广看,从体式和风格的繁复看,……杜甫都是超过一般诗人的。……杜甫所以得到‘诗史’的赞词,是因为他具备着两种性质。第一是记载之实,……第二是‘抑扬褒贬之意灿烂’。……今天的诗人要能够真实地追上杜甫,或者超过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诚挚地学习他那以史笔做诗的伟大精神。在这个神与兽、光与暗巨斗着的时代,诗人们正应该用忠实的笔去刻画,用严厉的笔去批判。要跟杜甫一样竭诚地、勇敢地去担负史诗的责任!在这历史的转型期,有魄力、有良心的诗人,必须充当时代忠实而且严正的史官!别让《北征》《丽人行》等诗篇的作者嘲笑!别让文学史家永远把史诗作者的盛誉专归美那个杜陵人”(《兰窗诗论集》)!在诗作中钟先生也曾多次直接地称赞杜甫:“忧民肠内热,秉笔意高骞”(《杜甫川一律》)。“骚心杜魄关民物,何取雕金织绮。大世代,要求史诗”(《金缕曲》)。这都说明杜甫在他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正像钟先生称赞杜甫的诗“朝政的得失,边塞的动静,权贵的骄纵,军吏的横暴,战争的灾祸,民间的疾苦,乃至家人朋友的流徙存亡、山川草木虫鱼的声色性状”无不写入诗中,堪称“史诗”一样,钟先生的诗也是一部“史诗”。尤为可贵的是,这些“抗战诗”也确实体现了钟先生所推崇的老杜式的责无旁贷的承担责任、义无返顾的奉献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在这些诗中,他日记般地记录了自己的经历与行程,忠实叙写了出师、转徙、以至败退的真实场景,具体描写了操练、草檄、逻夜的军中生活,深切抒发了告别战友、思念亲人、坚定信念的情怀,更加增强了“史诗”的特色。如《得秋帆桂林书诗以答之》云:“三月断消息,书来慰饥渴。……柴米劳筹策,烽烟亘岁时。”这境界和老杜《春望》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何其相似。《秋怀》云:“孰使连城瘖鼓角,未妨遥夜望星辰。”这情调与老杜《秋兴八首》的“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异曲同工。又如《送秀侠之官恩平》:“林叶艳如火,山云冻不流。暂为千里别,长共万民忧。经世吾侪任,衡文气味投。他时应眷念,风雨达开楼。”不但精练浑厚的格调深似老杜的五律,而且沉郁顿挫的风格,以至“山云冻不留”(以及其它诗中的“冻云癯鹿”“风噬肤”“清话一烟篷”等)的锤炼也深得老杜的精髓;不但忧国忧民的精神似老杜,就连“衡文气味”、风雨怀人的举止也深具老杜的情趣,即使把它置于老杜集中,也难加分辨,但这确实是新时代的钟敬文的史诗!
更值得称赞的是,钟先生一直把这种精神发扬,贯穿其一生。如七十四岁所写的“算轮扶巨匠,稍殚微力;情牵大局,肯废吟篇?老境侵寻,壮心自许,力命争衡如激湍。迎新岁,要提精鼓勇,不计华颠”(《沁园春·岁暮感赋》)。八十四岁所写的“千古煌煌《出师表》,‘鞠躬尽瘁’是吾师”(《武侯祠》)。九十五岁所写的“世味深尝头尽白,事功未竟意难安。多情亲友劳相祝,斜日长途敢息鞭”(《九五生辰抒怀》之二)。读了这些诗句难道能不想起老杜那颗“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的“老臣心”吗?
总之钟敬文的“抗战诗”既深具放翁的爱国传统、老杜的史诗精神,又是自己写就的一段抗战传奇;我们从中即可看到钟老用心血谱写的抗战经历,又可听到放翁与老杜的继响与回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张旭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