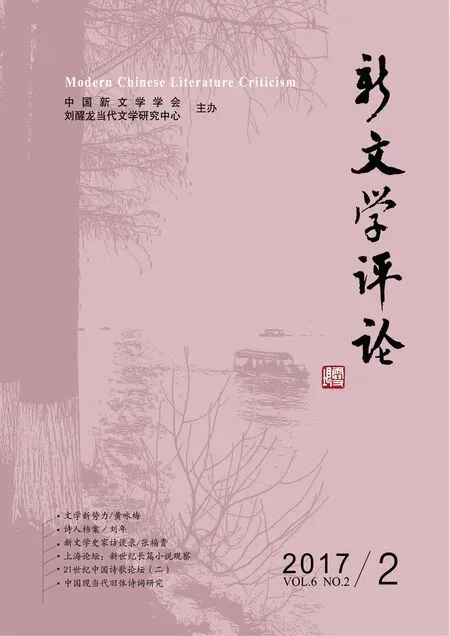论吴奔星诗歌的创作个性
◆ 李建明
论吴奔星诗歌的创作个性
◆ 李建明
吴奔星先生在《生命之歌》中这样唱道:
我哟,藐小得有如麻雀,
可也不高攀横绝云表的天鹅。
我的声音虽然嘶哑,
却要唱出自己的歌,
别坠落于瞒和骗的大泽,
别飘然于假大空的洪波。
作为一个著名诗人,他既谦卑又自信,他虽然不是大诗人,但要“唱出自己的歌”——他诗作有自己的艺术个性。本文以《都市是死海》为基础,旁及诗人1949年以前的其他诗作,拟从诗人创作题材、体验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方面,探讨诗人的艺术个性。
一、 人生的迷惘与希冀
上个世纪30年代崛起的现代主义诗群,如天空闪烁的星星,吴奔星是这片天空中一颗明亮闪烁而辛勤的星辰。
我们知道,现代派反复咏叹的是寂寞的幽居,空蒙的山色,飘零的落叶,迷惘的人生。现代派诗人的感知方式,注定了他们的诗歌视点主要偏向于个体心灵的隐秘之隅。同样,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吴奔星在诗作中也表现他内在的痛苦与迷茫。
诗人在《示丐女》中说:“行乞的女孩,别盯住我吧,/挂着两行清泪走来;/我,虽对你怜爱,/奈何,也早被驱逐在人生的华宴之外!”诗人劝她说:“你无须为寻求同情/而颤动你的瘦腮;/人间的同情啊,/都在大戈壁里深埋!”诗人诅咒这个冷漠的世界,其实内心深处燃烧着对人间温情的召唤。诗人在青年时期贫困得一无所有,完全靠借债度日,因此,他对人世的冷暖,比那些家境富足的诗人来说,体会自然更深刻。比如戴望舒在《我的素描》中说:“我是青春和衰老的结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自己“漂泊的孤身”“要与残月同沉”。或者如金克木感叹“生命是一粒白点儿,在悠悠碧落里,神秘地碾成云片了”(《生命》),叹息“年华像猪血样的暗紫了”,“静待宰割”(金克木《年华》)。他们的感伤无疑是真实的,在他们的心灵中,生命的欲望包裹在许多朦胧意识中,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找到目标,流露出对于人生的叹息。而吴奔星诗歌中的孤独则分明有现实内容,读者几乎可以触摸。类似这种诗歌还有《帽子》:“旧了的帽子戴在头上;/新来的尘土吻着/那发粘的帽沿,/里面藏着我过去的希望。”诗人由此感到在帽子的尘土和裂缝之间“有一曲无声的痛楚的歌”。诗人在人生的旅程中是辛苦的,他在《挥汗吟》中调侃道:“汗之味是臭而且咸的,/已遭世纪之唾弃,/而我是与之有深厚之缘的,/人世味对我太淡漠了,/正所以返求诸已啊!”而在《行云》中,则对自己的人生征程发出了较沉重的感慨:
是异邦的放逐者吧,
奔波于永恒之旅;
听日子在风声里喘息,
有感于家之需要了。
蹲踞于青色之山巅,
凝睇于牧子之鞭影,
疲倦的泪遂潸然下洒,
古刹里有老尼唏嘘呢。
天空的行云是诗人的写照,诗人流露出一种人生疲倦感。
不过,诗人并不总是孤独感伤的。他有真挚的友情与甜蜜的爱情。
诗人在困苦中,得到北师大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先生与系主任钱玄同先生的赏识,让他利用课余时间,为师大标点《二十四史》中魏晋南北朝及隋唐部分的史书,获得微薄报酬,贴补生活。1936年,他与李辛伯创办《小雅》时,柳无忌、李长之、林庚、吴兴华、李金发、路易士、韩北屏、戴望舒、吕亮耕等诗人纷纷来稿。师友的关心与支持,让诗人感到人间的温暖。所以,他写了好多关于告别友人的诗歌。
写于1934年的《别》有这样的动人场面:
默默地,在寂寞的氛围里,
你对着我,我对着你;
颤抖的桃色的眼泡皮,
眨一眨,凄然地又闭起!
在《送别》中,他殷勤地叮咛友人:“前面也许是崎岖的山道。/也许有澎湃的海潮。/珍重吧,如有意外,/千万长啸一声,/托狂风吹到这里。”写出难以割舍的友情。印度《五卷书·第二卷书》中说:“朋友是抵抗忧愁、不愉快和恐惧的保卫者。”诗人笔下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人。这是诗人对友谊的礼赞。
青春是最美丽的,青春的诗人心中也跃动着对美丽爱情的憧憬与期待。请看《秋祷》:“秋阳透过窗来/我感到南国的温馨了/愿万千金线/牵往两颗滚烫的心。”“你这时在幻想/钱塘江口八月的海潮吧/我呢,是倦旅的香客哪/梦在日观峰上开花了。”诗中的男女“心有灵犀一点通”。《走后》抒写别后相思:“雨夜的相思点点滴滴,/说不尽,数不完的,/而夜风之沙音,你知道不?/含蕴着独处之凄凉呢!”诗人似乎如顾夐《诉衷情》在对情人吟唱:“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诗人在恋爱中有过痛苦,诗人因对方的《爽约》,感到“心的悸动陨落了”诗人在《别辞》中为猜不透恋人的心思而苦恼:
你的脸:永远对我
是一个半透明的秘密,
或者是为恐引起感伤,
而不敢读的一部传记的封面:
那么苍白、清瘦,
嵌着黑灰色的眸子。
恋情有曲折,诗人还是怀抱希望,在《小札》中他梦想:“我们最好抿着嘴/让两颗心紧密地叠合/默默地听他们/和谐的跳动/过去——/现在——/——未来。”诗人的恋情总体是欢快的,不同于何其芳《预言》中对爱情透明忧伤,更不同于戴望舒爱情诗中那种怯弱、痛楚。
这样,诗人作品的感情基调虽是感伤的,但仍然闪烁着希望,所以诗人笔下有《晓望》、《颂歌》、《情书题辞》等色调欢快的作品,在《雨天小唱》中诗人相信:“只有在晦暝的雨日/希望才轻叩我的心扉。”
不妨这样说,青年诗人在人生中也有迷惘,但在迷惘中萌动着生机。诗人的人生咏叹调,可以用郭沫若《巫峡的回忆》来形容:
啊,人生行路真如这峡里行船一样,
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
我如今就好像囚在群峭环绕的峡中——
但只要我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
是的,诗人的迷惘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诗人的年岁渐长,随着抗战的烽火,诗人的孤独感伤渐渐隐去了,代之以人生的思索。诗人没有囿于自我,除了年龄和社会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对诗人的熏陶。诗人的父亲吴挹清、母亲张真荣与挪威的传教士,在家乡东坪镇所建福音堂附设的信义学教书。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自然会用基督教的一些文化影响幼小的诗人。基督教把人生的一切困苦磨难都当成上帝对人的一种试炼,人应该积极勇敢地面对这一切,才会成为上帝的选民。有了这种生活的态度,诗人在面对人生一切艰难困苦时,就能挺住,不至于被击倒。这是诗人在人生感叹中,有别于其他现代派诗人诗情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 历史的纠葛与时代的漩涡
现代派诗人的诗情世界主要集中在个人的哀伤与喜乐,不太关心周围世界。这种浊世的哀音也是一种时代病,不过,吴奔星并不完全这样。他的诗作有不少关注现实与时代的内容。即使他早期逃离现实、隐遁山林之作《山径》,也表现出一种身在山林心在现实的无奈之感:“不复闻林下的歌声,/小小的足印也模糊了。/夕阳置一只空花篮,/塞满了无边的幽怨。”而在《更夫》中:“拖着沉重的脚步,/拖着系在足端的弓形的影子,/土腥气时恐怖终于袭来了!”则分明有着时代的烙印。
诗人自己回忆说:“我的青春又是现代史上的一个最革命的时代度过的,是在那个革命与反革命、侵略与反侵略的搏斗中度过的。”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处在这样一个艰难岁月中,必然会表现出一种责任。1927年,他在东平镇滨资读高小时,就追随进步教师,集体参加共青团,率领一批青年学子,巡回于东平镇各个乡村,投入湖南农民运动。后来他成了大学教授,参加“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等相关活动,并第一个在高校课堂讲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被称为“提头教授”。这些都表明了诗人在当时有明确的政治理想。正是因为诗人有理想,诗人才会关注现实,诗人表示:“我要唱出历史的纠葛,我要唱出时代的漩涡。”
1937年全面抗战,吴奔星离开故都北平,辗转到广西。在救亡岁月里,他有一种新的生活体验,诗作也有更广阔的内容和境界。他的诗行中,跳动着爱国的赤心。
写于1939年的《过桂中》写道:“车子拉我更远了/,一座混合的山,/一种混合的鸟音,/钉住着我的记忆,/离奇而亲切的。/我愿各地的山,永在/亲切的鸟音,也永在;/我最怕听到耳熟的鸟音/,呼唤着我的流亡的步子。”诗人为什么害怕耳熟的鸟音,是因为它会触到诗人的故国之思。此诗与王维《晓行巴峡》“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人在流亡途中,并不总是如汉蔡琰在《胡笳十八拍》发出的哀叹:“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祖国的灾祸,对于诗人来说,像母亲感到她的怀着的孩子的痛苦,但是更像鹰那样爱辽阔的天空,对自己的祖国,充满豪情壮志。《涧之歌》便是这样一首佳作:
生来见弃于父母,/命定便是流亡。//我无心回首烟岚杳霭的家,/只低低地哼着流亡之歌。//每一刻银灰色的泡沫,/胆怯地说出了行旅的艰辛。//(我自知是藐小的行客,/但自信有伟大的前途!)//我提起永不疲倦的腿,/从石罅、从悬崖,蛇样的流亡。//我的歌喉永远是那么嘹亮,/羞愧了无数次的牧童樵子!//蓦地里,千万伙伴的吟哦,/组成了宇宙的合唱团。//我们玩弄着鲸鲵、海豹,/谁说不是横槊赋诗的英雄呢?//而高歌婉转中,插入了/“别忘了烟岚杳霭的家!”//于是,每一条银色的鲜花,/反射着伙伴们的欢喜。
流亡的途中是艰辛的,但没有“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的惆怅,诗人反而有一种横槊赋诗的豪迈,因为他坚信民族解放的胜利一定会来到。他在1939年的《答客问》也表达了这样的信念:
你我的视线是如此亲切,
虽包孕着几分痴憨,
却具有坚强的凝聚之力呀!
我们该以同一的眼色,
扫过各色各样的音区,
堆积起眼色来吧,
这该是入侵者所不能突破的长城!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诗人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投入保卫祖国的和平与庄严的伟大事业中来,这样,祖国就不受外侮,就一定能自立于地球之上。
诗人在《暴风雨之死》中,描述暴风雨过后,礼赞中华儿女不屈的斗志:
天仍是青的
地仍是绿的
中华的沃壤上
连一根芳草都是笔直的
1943年秋日寇由湖南入侵,妄想把广西省政府所在地的独秀峰炸平,枉费了许多重磅炸弹。诗人作《独秀峰》赞美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一峰独秀,/不受孤芳自赏,/而是以硬骨头精神/对居民和游人的人品的熏陶!”诗人同时还有一首旧诗《题桂林市独秀峰》,可以与新诗并读:“独秀峰长在,谁知几亿春。雷霆轰若旧,风雨洗尤新!立地腰难折,顶天势不群。浑身都是骨,何处近妖氛?”据说诗人在每天警报解除时就朗诵这首诗,闻者群起高呼,声震林木。
这种豪迈之气也体现在诗人的《题最新抗战地图》:
遭受劫掠与侮辱的土地上
磅礡着守卫者的呼啸
赋予山河以肺之张缩,
赋予山河以心之起伏。
于是,所有的山岳怒发冲天,
所有的江河放声狂啸,
它们不但庄严地存在,
并且英勇地活着。
诗人启示我们,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有英勇的人民在战斗。该诗写得明快而激越,是抗战诗歌中的名篇。
在民族解放的岁月里,诗人的友情融进了时代的风云。由于消息不通,误传诗人的好友路易士已经附逆,后来中央社发电为之申辩,原来路易士已经到香港机关报《国民日报》担任编辑。诗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了一首《致路易士诗笺并序》,诗中对坚守民族大义的路易士抒发了这样的深情:“呵,我满身天真的气息,/我狂喜得没有话说,拉长了嗓子,/拍案一声:岂止濯污泥而不染!/而想到他跋涉酸辛的旅程,/把险峻的关山丢在背后,/把汹涌的独流撇在旁边,/则又不胜其世态炎凉之叹了,/但我的心,终究是爽朗的,/因为我的周遭,/弥漫了青的绿的水。”
诗人在这流亡岁月中,感到自身也在不断成长,在《自诉》里,他写道:“跋涉——/千山万水/山/是独立不移的,/水/是自强不息的/于是/我有了山的性格/水的性格。”
诗人回忆说:“我的青春又是在官商不分,兵匪难明,灯红酒绿、腐朽堕落的所谓大后方度过的。我的心为悲愤所充塞。”当时的人们这样形容国统区:一面是严肃认真的工作,一面是荒淫无耻的生活。大后方的一些大城市,如重庆、昆明、桂林等,那里的人民不堪贫穷破产的痛苦,而上层社会却过着纸醉金迷,腐朽淫靡的生活。作为一个正直而又有抱负的诗人,怎能不表示出他的愤怒呢!
诗人笔下的《农夫》由“南风下碧绿的秧纹”和“秋风下金黄的稻纹”而想到“仓库旁的地主的笑纹”和“冷灶旁的妻儿的泪纹”,揭示了贫富的对立。《湘桂车中》则提醒坐在车中的人们不要忘记筑路工人的辛苦。而在《记所见》中,则对权贵表示了一种蔑视。“肥肚皮、双下巴的人,/是不惯于山居的!/他怕一泓清泉诅咒他那污秽的脚,/他怕一轮明月映入那黑色的心,/他怕数声村鸡嘲骂他那麻木的耳……”诗人用纯净来反衬权贵的龌龊。在名作《小鸟辞》中,则通过小鸟来鞭挞腐朽的人们:
当我展翅向天外扬长,
四条腿的人们,
塞满大街小巷
他们贪婪的像饥饿的豺狼,
争抢我消耗得剩下的空气,
争抢我消耗得剩下的阳光,
为了养肥豪华的梦想
而忘却自己的生命,
已涂满了剥蚀灵肉的风霜!
诗中的小鸟有着魏晋文人的洒脱风度,而贪婪的四条腿的人们则徒具生命空壳,没有灵魂。
对丑恶现象的抨击,最有力的是诗人的《都市是死海》。诗人把大后方的城市比作死海,尤其诗的后两节:
在恶臭的死海上/已有/正有/将有/“礼”的浮尸,/“义”的浮尸/“廉”的浮尸,/“耻”的浮尸,/以及一切“忠”、“孝”、“信”、“义”的/浮尸,/它们腐烂——/它们分解——/它们化合——/它们沉下去,/终于变成了沉淀。/多么美丽的/死海的底层呀!//都市,是海——/是死海!
读完这两节,喧嚣杂乱的都市,仿佛飘出恶臭,令人对腐朽的城市产生厌恶之情。诗人不仅揭露了城市的腐败、腐朽,还揭示了造成这现象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诅咒的同时,发现了一种新生的力量,《宣传》中写道:“星光与眼光垂直地结合着,/造成护卫大地的光明的藩篱。/尽管黑暗倾盆地倒泼墨汁,/他们仍然有力地锥子一般钻出头来,/把黑暗屈居于它们的胯下喘息!”预示光明必胜。在《小树》中,诗人发现:“泥土尽管是那样浇薄,/并且坚实地压迫住/而小树却挺直地生长着!//暴风雨尽管那样冷酷,/摇撼并且湿透其身心,/而小树却更幌动令人欣羡地新绿!”由此,诗人不禁感慨道:“在卑微的境遇中,/竟能勇于乐于/摧折残暴,以污秽为营养,/试想,小树会永远小下去吗?”结尾发人深省,新生力量是无法阻挡的。
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吴奔星在抗战期间,把时代风云纳入自己的视野,但仍然以自己的一颗心来感受时代生活,这使他的诗既有浓郁的现实情怀,又有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而没有如有的现代派诗人那样,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感受方式,抒发情感,流于空泛。
三、 虚实相生之美
上面我们分析了吴奔星对生活和时代的体验和理解。早在1935年,孙作云在《论“现代派”诗》中就指出:“在内容上,是横亘着一种悲观的虚无的思想,一种绝望的呻吟。他们所写的多绝望的欢情,失望的恐怖,过去的迷恋。他们写自然的美,写人情的悲欢离合,写往古的追怀,但他们不曾写到现社会。他们的眼睛,看到天堂,看到地狱,但莫有瞥到现实,现实对他们是一种恐怖,威胁。”这是现代派诗人的一个通病,而吴奔星恰恰在这一点做得很好,诗作有社会现实的内容。这是诗人的一个显著的个性。
仅仅就这样认定吴奔星的创作个性是不够的,因为创作个性不但表现在写什么上面,还表现在怎么写上面。艺术表现上面往往更深刻地表现作家的创作个性。
现代诗派不是把情绪赤裸裸地宣泄出来,而是借助巧妙的笔触描出来,使诗的情绪外化、物态化。还如孙作云在《论现代派诗》所说:“现代派诗的特点便是诗人们欲抛弃诗的文字之美,或忽视文字之美,而求诗的意象之美。”
用意象来抒情,使诗歌含蓄。但这仍然构不成吴奔星的创新性,我们必须分析吴奔星选择什么意象系列来抒情。意象的选择,不仅与作家独特的生活有关,而且也与作家艺术素养不可分。意象的特点体现作家把生活和情感变成艺术时所具备的特有才力和技巧。
翻开《都市是死海》,我们会发现,吴奔星对春天、七夕、秋午、早晨和雨夜等时间较敏感;他的视觉爱捕捉烈日、大戈壁、狂涛浊浪、天涯海角、行云、山径、山林、荆棘、山洞、山涧、鲸鲵、海豹、贝壳、珍珠、庭院、丛林、市镇、原野、小树、红叶、落叶、更夫、丐女、苗女、肺病女、支那女儿、模糊的倩影等形象;他的听觉对于北国驼铃、长空的秋雁、鼾声、林下的歌声、知了的叫声、嗓子的嘶哑声、秋雨点点滴滴的声音、燕子的呢喃、痛苦的粗哑的歌声特别敏感。这些形象很难用一个单一的特点来概括,它们是明朗与灰暗、纤细与壮大、忧伤与欢乐的统一体。这与诗人迷惘而又追求、关注现实的诗情相吻合。与现代派大多数诗人相比,吴奔星绝不是逃离现实的诗人,但是与那些大勇者相比,诗人又不免显得有些灰色。不妨把诗人的意象系列与其他诗人比较一下。戴望舒喜爱在暮春残冬、枯枝死叶、苦雨孤灯、古井夕阳等凄凉、飘渺的物象上寻找诗情,这与诗人孤独、虚无的心理气质相合拍。而艾青诗中的土地、太阳则表现了诗人忧郁的情绪,而这种忧郁则是一种力量。从比较中,可以看出诗人吴奔星意象系列的独到性。
意象是一个具有主客体内含的情感生命体,当诗人创作冲动产生,便获取内心对应物,通过意象组合形成诗篇。而在组合过程中,可以看出诗人的联想和想象习惯,体现诗人的独特艺术构思。
《晓望》就表现了诗人的创造性。
你凌乱的发束是相思的脉搏吗?
晨风的梳齿轻而且轻
乱云里映出一抹鲜红
妆点你清瘦的脸呢
当一层薄雾爬上你的眉峰
远的,近的,云山的风景都失色了
我乃祝福我流浪的眼
开始它的隐逸的新生
这首诗比较晦涩、朦胧,借助意象曲折地甚至怪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带有早期象征派的色彩。不妨作一些解读。“你”由于辗转反侧而头发凌乱,诗人就把凌乱的发束比喻为相思的脉搏,这是联想。当“你”起床后推开窗户,晨风轻轻地吹着“你”的头发,诗人又把无形的晨风想象成有形的梳齿。晨光初照,朝霞就成了你“抹鲜红”的脂粉,来“妆点你清瘦的脸”。尚未褪尽的薄雾“爬上你的眉峰”,好显出“你”的风韵之美。接着诗人又虚写一笔,想象那远远近近的云山风景在“你”面前相形见绌。最后诗人把专注的恋情喻为“流浪的眼”开始了“隐逸的新生”,极富独创性。诗人在对意象组合时,交替运用了联想和想象,全诗有一种虚实相生之美。诗人说:“在创作实践上,想象与联想虽可独立成篇,但由于二者毕竟都是想象力的产儿,在抒情诗中仍须互相生发,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以保持诗意的虚实搭配,气氛协调,以及韵律和谐。”正是诗人丰富的创作经验,才道出联想与想象相结合的这种奥秘。
吴奔星在创作新诗之前写了不少古典诗歌,由于旧学基础好,他在意象组合时,能对古典诗词进行点化。这时,诗人多用联想。
《十四行》中有这样一节:
长空的秋雁,叫的分外哀怨,
可是,我像不曾听见一般;
火辣的情感已成死灰,
再也扬不起熊熊的烈焰!
“长空的秋雁”是古典意象,反衬我心灰意冷。《走后》中:“雨夜的相思点点滴滴,说不尽,数不完的。”明显化用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吴奔星化用古典诗句,语言更精练。
仅仅是化用古典诗词,还不足以表现诗人的创造性。吴奔星更善于融化古典诗词表现现代诗情。如《我沿山涧以彳亍》
我沿山涧以彳亍
倒影启示了我的伶仃;
而风尘的脚步,
更启示我不该慕此清高!
遂将污浊之心
濯清流而伴以痛哭。
(古人云:一片冰心在玉壶,
我亦喜斯境之将至!)
熏以山花之芬芳,
藉易红尘之腥气,
但恐浣衣的山女,
闻臭味以先逃:
何能免于流水之诅咒呢?
我跪祷青松古柏旁:
明月照之,
清风拂之。
隐遁山林是古代文人的一种传统,也为30年代现代派诗人所向往,他们也希望在自然中追求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忘却尘世的烦恼。如玲君的《山居》、刘振典的《伐山人》等。而吴奔星在这首诗歌中清醒地认识到无法逃离现实,自己身上的红尘之气和污浊之心会吓走浣衣女,招来流水的诅咒。这是现代人在都市物质化环境下的一种精神痛苦,是反“异化”的现代性主题。古典意象与现代意识融合无间。类似这种诗歌还有《赠甘云衡夫妇》、《秋雨》等。
吴奔星诗歌中更多的是生活中的写实意象。这些意象往往有象征意义,诗歌具有暗示性。《帽子》:“新来的尘土吻着/那发粘的帽沿,/里面藏着我过去的希望。”用尘土吞没了自己的希望这一生活物象,象征地抒发青春渐渐远去的感伤。又比如《脚印》中的第二节:
有鲜血的残痕,
有绿叶的遗迹,
渐次泯灭,拖着
老年人的太息!
这简直是一个人人生的总结,有着沉重的感喟。
吴奔星有些诗作有一个中心意象。他用中心意象贯串其他意象。中心意象的内涵既显得丰满,又富于变化,而诗歌的意蕴也得到饱满的体现。诗人的名作《都市是死海》便是如此。
这首诗的中心意象是:
都市,是海——
是死海!
然后用意象群来丰富“死海”这一中心意象:
广袤的死海呀——
有被桎梏者的自由的沉淀,
有被侮辱者的人格的沉淀,
有被剥削者的法益的沉淀,
有被谋害者的安全的沉淀,
有被离间者的友谊的沉淀,
有被打击者的清高的沉淀,
有被奸污者的贞操的沉淀,
有妻离子散者的天伦的沉淀,
有转徙沟壑者的乡愁的沉淀,
有失业者的希望的沉淀,
有失学者的希望的沉淀,
一层——又一层,
固结的海底啊!
用大量的排比,表现广阔繁复的生活内容,简直是一幅都市地狱图。这种意象群是生活的浓缩与提炼,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容量。
接着诗人又用意象群分别描述了暗礁、暗礁间的水族、死海中的洪峰,从而全方位地描述了“死海”的狰狞和可恶。
这种以中心意象贯串其他意象的组合方式,在诗人作品中比比皆是,比如《示丐女》、《落叶》、《模糊的倩影》、《涧之歌》、《我裸睡在青草地上》、《万人桥》、《暴风雨之死》、《小鸟辞》、《小树》等。
这些诗歌意象的组合方式是一种联想,但是诗人善于把联想虚化为想象。比如《小鸟辞》具有象征意蕴,诗歌具有暗示性。这些诗歌具有虚实相生之美。

福建省高等学校科研创新平台“两岸语言应用与叙事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项目编号LAYY2016003
注释
:①孙玉石:《吴奔星与1930—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②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③吴心海编:《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页。
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
⑤吴奔星:《都市是死海》,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⑥吴奔星:《都市是死海》,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⑦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⑧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
⑨吴奔星:《虚实美学新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⑩别林斯基著,满涛、辛未艾译:《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页。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