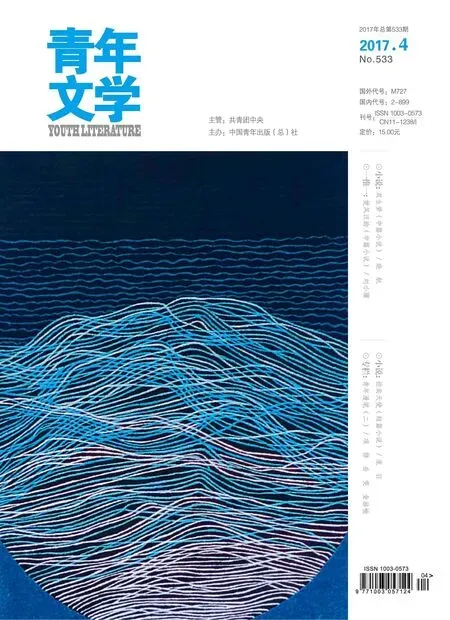然后说到李潘
⊙ 文 / 高 君
然后说到李潘
⊙ 文 / 高 君
高 君:吉林蛟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钟山》《作家》《山花》《人民文学》等刊。有小说被《小说选刊》《作家文摘》等转载,并入选多种选本。小说集《段落》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
那年春天,闹起了非典,到种地时,这座城市已经成了全省的重灾区。我先坐大客车把大猫送到妹妹四粉家,然后自己乘火车回了老家。
火车已开始明令禁止携带任何小动物,尤其是猫狗。据说正是动物导致和引发了这场人间灾难。街上随处可见被遗弃的它们,有的还是珍稀品种,穿着鲜艳的肚兜和小鞋子。我只是心情复杂地看上一会儿,并没打算施舍一点多余的爱心。它们不是我养的,我爱不上来。
我虽然来自疫情重灾区,逃难也好、躲灾也罢,但那是我老家,所以并没遭即刻遣返,更没遭老家人厌弃。只是例行公事,回去第二天,乡派出所一早来了两辆摩托车,带我到乡卫生院分别做了血检和胸透,然后按规定在未来十五天的潜伏期内,我只能在一家出入,不许四处串门,更不许做任何出行,包括折返。
但话说回来,若我带上大猫回老家,那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轻点儿说是我不明事理,重点儿说就是给脸不要脸,弄不好连二姐都要人前人后跟着犯难。所以,幸好没有带大猫回来。没有带它回来,对于我,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男人,居然还养了一只猫玩儿,在家偷着养也就罢了,带回老家就不大合适了。尤其是在这节骨眼儿上。
至于非典,我则一点儿都没害怕。摊到头上又能怎样?
那一年,我最不怕的就是死,最羡慕的则是农民。不光我自己羡慕,我还替四粉羡慕。换句话说,我巴不得去哪儿重新做回农民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甚至都没法儿跟他们比,他们有土地、宅基地、新农合医疗保险、大病救助和补助。据说马上就要有养老金了。而我只有一本一文不值的、写着出生年月日的城市户口簿。
我连一个下岗工人都不如。
时光流转,农村还是那个农村,农民却已不是原来的农民了。他们真成了土地的主人。一年春秋各忙一个月。因为有除草剂,锄镐都用不着了。夏天上山放放牲口,秋收完毕卖了粮食囤够烧柴,整个一冬天就闲了下来。东北农村跟南方不同之处,是地多,一家三四垧算少的,一般家里都有七八垧地,所以根本用不着外出打工,守着田园就已丰衣足食了。关键是没有温饱之虞,因此也就没了大焦虑。还有比温饱更重要的问题吗?有那么多的地,只要把种子播下去,即便是大灾之年,也能换回足够吃的来。何况灾年十年九不遇,又有良种和粮农补贴、大量的化肥和农药、节节攀升的粮价做后盾。
你从他们吆喝耕地牲口的嗓门儿,隔着百八丈远距离还能跟你搭话的劲头儿,就知道他们的底气有多足!
——放假啦?这活儿还能干吗?还会干吗?
——现在在哪儿上班呢?
——这回多待两天吧,好好体验体验,光念书了!
四月乡村,生机盎然。隐约在树缝间的松花江水,湛蓝如洗,光亮似镜。
家家锁头把门,除了老迈动弹不了的,几乎是倾巢而出。大地上春光无限。大姑娘小媳妇怕春风打黑了脸,用纱巾遮着脸。色彩却极其丰富艳丽。她们是有备而来的,甚至把这当成一顶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比如,在前一年冬天的某次进城或赶集时就已买好了,而且是精挑细选,包括太阳帽和太阳镜,迷彩服和防雨服。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在消费观念上,一点儿也不比城里人落后。好衣服留着出门穿、下地干活儿时破衣喽嗖的时代早就见鬼去了!
四月,是农村人展示自己的重要时刻。年轻人都在家闲了一冬天了,现在好了,春天来了,大地生机勃勃,他们也跟这大地似的,青春勃发,意气盎然。
地与地之间大多隔着一片荒格、一条毛道、一两棵柳树榆树梨树或者杏树,远看基本上就是连着的,这家与那家,此屯与彼屯。如此一来,就不光是邻里之间,而是屯与屯之间的姑娘媳妇在争芳斗艳了。小伙子们当然不会自甘示弱,他们憋了一冬天的劲儿,正愁没处使呢,所以看上去有点儿不大像劳作,而是像撒欢儿,还有竞技和炫技的味道。相互间隔着八百丈远,扯着喉咙叫号儿,手下的扎眼板(播种大豆的一种农具)、大轱辘播种器都抡飞了。他们往往好在速度上做文章,这时连质量也不顾了,惹得旁边的父母直骂。
歇气儿时,我卷了一支旱烟,和二姐坐在地头。
二姐说,明儿个我让人去小卖部给你买两条烟卷儿,这烟你能抽吗,齁辣的。
一样儿。
我没跟别人说你现在没工作了。
无所谓。
让他们知道啥用?不连心不扯肺,干赚闲话。
……
等你走时,我多给你拿鸡蛋和苞米面儿。
不用啊,供一饥也顶不了百饱。
顶一阵儿是一阵儿,等你走了我再给四粉攒。
那一年,乡村在我眼里的确变成了天堂。我甚至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选择读书而离开它。我还在梦里看见自己又变了回去,金玉满仓,鸡鸭成群,肥猪满圈。奇怪的是我还跟我的大猫在一块儿,而身边并没有其他的人;更奇怪的是,我还在焦虑,不是为吃饭,而是为小说。醒来时我明白了,老家再好,跟我也没多大关系了,它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它。
城市跟我也没有关系,在那儿,只有那间在产权期内的小房子暂时是我的。还有大猫,前提是它不丢不逃不死。它是小牲口,自己打不出食儿来,我得对它负责。
半个月过去,地一种完,我便火速赶往四粉家,包儿都没撂,取了大猫,即刻打道回府。我灰头黑脸,不光城里邻居,连大猫都快要认不出我来了。
时间又过了一年,农历七月中旬,大姐忙完自家的两亩水田、一亩旱田,要去二姐家住几天。大姐打电话问我能回去不?我说我刚上完坟回来。想想又说,大客车和火车都不让带猫。其实这也就是一个借口。大姐说,我就想你,惦记你,别人隔两年还能见上一面,你都好几年没看着了。我一时就没话了。后来大姐就决定中途先到我这儿来。
其实不是我不想她,也不是心疼路费;说白了,就是我不愿回去。人境况不好时,最想和最不愿见的恐怕就是故乡和故乡人。
大姐就不同了。自从十年前随姐夫迁回辽宁普兰店邹屯,每隔一两年大姐都要回吉林老家住上一阵儿。嫁鸡随鸡,但故土难离。而且除了小儿子,她另外一儿两女都在这边成了家。可每次大姐在儿女家基本都不长待,各住一两宿之后,立即到二姐家驻寨。然后召集我们都回去。那里是我们共同的老家。
大姐说人亲土也亲,看哪儿都好,年年盼“挂锄”,哪怕就回来瞅一眼。要不啥也干不下去,天天抓心挠肝的,坐不稳站不牢。大姐又说,人家是想儿女,我是想姊妹,想老家人,岁数越大越厉害。要不是离得远,我一年都能跑回来两趟。
我们知道,远不是问题,大姐最愿意坐车,不论大客车还是火车。她心疼的是路费。尽管来回两宿的硬板火车票价并不贵。俗话说,搬一回家穷三年,大姐在老家时是一等的富裕户,那时种地虽然不赚钱,但大姐家副业搞得好,打鱼、养牛、养猪,所以一直坚持不走。用她的话说,辽宁普兰店邹屯,那是丈夫的家,不是我的。直到当年和大姐夫一同挨饿跑过来的辽宁同乡都陆续回去了,且回去后都说日子过得好,大姐这才决定回去。中间,大姐还几次要搬回来,直到小儿子回到辽宁在服装厂上班,结了婚,小孙子出生,她才作罢。
大姐打我电话前,我确实回老家上过坟。我只住了一宿。头天晚上到,第二天起大早上坟烧完纸就走了。二姐挽留我半天,然后拎着一个装满鸡蛋的大纸壳箱,一直跟我走到了另一个屯子。
在两片黑压压的玉米地之间的毛道上,我抢过来她手里的纸壳箱,制止她再送我一程。这时她就哭了,哭着往我兜里塞了三百块钱,说,啥用不顶,留着买烟抽,我自己攒的,谁也不知道。——我没把钱推让回去,因为确实够我抽大半年烟了。
二姐家的年景才刚刚好,但前些年盖房子、儿子娶媳妇拉了很多饥荒,且多半都是借的,利滚利。虽不缺吃喝,但在钱上一直都是紧绷紧。而且二姐在家不管钱。
那我不送了,二姐说,离大客车开还早着呢,这么早这块儿碰不着咱屯里的人,咱俩说一会儿话吧。我说嗯,然后点着一支烟。
二姐用手背擦了擦眼睛,说,好时候净借你光了,难时就可你一个人扛着。咱现在姊妹六个,就你二哥有钱,多了不敢说,七八十万是有,可那是铁公鸡,这辈子就长了一颗疼老婆孩儿的心。剩下这几个是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个不如一个。我在家天天干瞪眼儿干着急。离得又远,给你送仨瓜俩枣还不值来回路费呢。我跟小要账的四粉说了,让她别向你要钱花了,你黑白不睡觉,写写写的,挣那俩稿费那么容易?还得求人搭人情,哪还有闲钱供她吃药啊?再说要是吃药能好也行,就是让我借钱我也认。说白了就是个武大郎服毒,吃也完不吃也完,咋整都是个死。干脆就让她上我这来吃偏方,兴许还能瞎猫碰上个死耗子。我跟徐万灵说了,他专门会治疑难杂症,还敢下狠手,治好算活捡着,治死也不用他偿命。你腾出点时间,去跟她说说。
我说行,但千万别说漏嘴她得的是绝症,那样还不如不管她呢。
知道,说是这么说,疼还疼不过来呢,谁的姊妹不连心?自打她确诊后,我黑白就更没睡好觉了,这一年揪心揪得头发都白了,想起来还恨。二姐说着,突然咬起牙根儿来:就稀罕城市,死活都得奔城市,这下好,小命儿眼瞅着就要没了。当初要是嫁农村能这样吗?再穷也能有口饭吃,再说咋整也不能死啊。你看这十里八屯跟她一茬儿的那些小老娘们,个个养得翻肥,都跟活驴似的。还都当家,自个说了算。哪有一个出外挣钱回头倒贴养老爷们的呀?什么命呢?损命!贱命!一想起来我就恨得牙根儿直!
我说,别翻八百年的旧账了,人都没长前后眼,知道尿炕都不睡觉了。
二姐说,关键是她没睁开眼睛嫁着好人。
晚上八点多,在火车站出站口接到大包小裹的大姐,然后我们打车直奔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酒水全免的自助火锅店。我算计好了,我们都能吃肉,而且都饿了一天了,多吃几盘肉来回打车的钱就都出来了。
到了火锅店门口,大姐才反应过来,直说吃喝都带了,回家热一下就行了,下什么馆子呀!不过待一推开门,她立即就被热气腾腾的麻辣香气和唰唰的一片吃声所虏获了。大姐说,我就得意肉。我说我也是,咱俩今晚放开量吃!
吃这一顿你得写多少字儿能换回来呀?
不能这么算。
我拎了一瓶饮料和一提溜啤酒,落座,把饮料拧开,递给大姐,掏出自备的酒起子,砰砰连开两瓶啤酒,自满后,仰脖干了一杯!大姐乐了,说就愿意看你这样儿,从小到大都没看够。人能吃能喝就有福,钱越花越有,瞎子不点灯也没看省下灯油钱。
我说对,嘴头子能省下几吊,能吃能喝不得病,少吃点儿药啥都有了。
大姐说,这些年让一帮药篓子把你给拖累了。
我说没那么严重。为了不继续这个话题,我扬手叫来服务生,先点了两大盘羊肉,加赠送共四盘。又点了一盘鸭血、毛肚,刚要点青菜,立即被大姐制止:够了够了,不要了。
服务生一走,大姐立即说,破青菜稀烂贱的,一块钱能买一堆,上这儿吃什么?死贵的。
我说,这是自助餐,吃啥吃多少都花一般多的钱。
大姐“妈呀”一声,说是吗,我光听说你二姐夫他们一帮老爷们卖完粮,去蛟河把好几家火锅店都给吃黄铺了,你这里还有开自助啊?那就更不能要青菜了,饮料我也不喝了,你也少喝两瓶啤酒,想喝回家喝,我给你买。
我说,那咱俩来点儿白酒?解乏又不占胃。
那天晚上,我和大姐喝了一斤散白干儿。我喝了有七两。借着酒劲儿,我彻底翻了一把旧账,陈芝麻烂谷子一股脑儿倒了出来。需要强调的是,那些话我原本打算永远压在肚子里,起码不能跟大姐说,她都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自己还得靠儿子养呢。因为酒,我当时只想到她是家中老大,尽管是姐,那也是老大。而作为家中老小,委屈也好,抱怨也罢,都是关于这个家的,不跟她说,跟谁说呢?
四粉的事自然首当其冲。
那时,四粉肚子里的脾已经肿大得用衣服遮不住了,看上去就像身怀六甲的孕妇。
可当时我没管这些,只为一吐为快。因此听上去不光像抱怨,而且就像在告状。我当时真的感觉累了,够了,烦了。烦死了。
那是四粉、大姐和我,我们仨最后一次相聚。
那是中午时分,我强打起精神领她俩乘公交车去了趟离家不远的南湖公园。所以去,一是三个人心里都不痛快,再在家待着,气氛实在压抑;二是不去那儿,实在找不着可去的地方。在公园里,我们仨离得很近,却一直没说什么话。四粉一定是有话要说的,她病成那样,而且有三四年没见着大姐了。可是她的话还没等说出口就被怼了回去。对于我和大姐,话都在那个晚上说尽了。
四粉苍白着脸,中间去一处售货亭买了一小纸杯爆米花,怯怯地递给大姐,大姐问完价,“妈呀”一下立即推了回去:我可不要,这么贵,都这样了,还显啥大包儿(大款)呀?
我悄悄递给四粉一个眼色,意思是她不吃你吃。四粉一直用手心捧着,没吃一颗。后来我们照了张相就回家了。三天后取相时我才发现,我们身后的一池荷花全败了。
下午,我去火车站买了两张火车票,回来时在恒客隆超市给大姐买了两箱鲜牛奶。当晚,大姐就领着四粉去二姐家吃偏方去了。
两天前,我跟四粉在电话里说大姐要来,所以,她就起大早背着药包坐大客车来了。敲门时天才刚亮。一开门,她“哇”的一声就哭了。这让大姐和我都十分意外和反感。我们还沉浸在昨晚的酒意和情绪里。
妈呀,咋的啦?赶紧进来,大早晨的,别人家还睡觉呢,你哭什么呀?红口白牙的!大姐说。
我说,她就那样,多少年了,见着我就哭。我点着一支烟,转身回了里屋。
老娘们家的,整天咧咧啥呀,哭也哭出丧来了!小时候就是个哭白精!赶紧进屋,让邻居听见笑话死了,还以为咋的了呢。大姐又说。
四粉止住哭,抽抽搭搭地说,我一看见我小哥就心难受。
妈呀,奇怪死了,这不是整反了吗?你小哥没病没灾的,你看见他难受啥呀?净看你难受了。怪不得这些年你小哥没得好呢,都是让你给妨的。怎么跟崔四女一样呢?硌硬死了,妨完婆家妨娘家。你没看见你小哥现在都啥样了?班儿都没了,你不给增光道喜就罢了,这下还哭上了呢!白活了!
四粉说,我也心疼我小哥,可我没着儿。
大姐就教训起她来了——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心疼,咋心疼的?没着儿,没着儿找婆家去!从十六岁开始,你小哥就开始管你,现在你多大了?三十二了,怎么就管不出头儿来了?你还赖上、讹上谁了?该你的还是该你婆家的?我这次来,就想好好问问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凭啥养你呀?结婚前也就算了,现在你儿子都八岁了,怎么有事儿还来找啊?这不是讹人吗?结婚前足足养了你八年,你说那八年你哪天消停过?光对象就处了一箩筐,处一个黄一个,圆了不行扁了也不行,为这,你小哥脑瓜子好悬没让人给削开瓢儿。他花钱让你学手艺,学完手艺给你买户口,买完户口再求爷爷告奶奶给你赖个银行家属,再安排你进银行招待所。好歹算遇到一个你愿意嫁的,我告诉你小哥,快刀斩乱麻,赶紧打发了,去它一块大心病。哪想到啊,就消停了不到半年,一怀孕你就把班儿给辞了,你说你胆儿有多大!连你小哥都不知道。你以为你是谁呢?你小哥还一身能耐呢,还念过大学呢,结果咋样,辞了班儿不也照样在家里蹲着吗?你想当阔太太不上班?做梦呢你,没看看这是啥年头,没看看自己是块啥材料,没看看嫁的是啥家庭,全家守着一个破烟摊儿,说白了也就癞蛤蟆打苍蝇——将供嘴儿!说句到家话,当初你要是没班儿上,人家还不一定能要你呢!咋样,没了班儿全家人的脸立刻就都变了吧?你说你到底是精还是傻,想当太太,找有钱的呀,天生穷命鬼一个,小姐身子丫鬟命!在银行招待所上班那两年,酱牛肉都不吃了。这下好,白菜汤都喝不足兴。
孩子刚满月就让老婆婆给抱走了,留着你干啥?出外给人家挣钱去!再说就你那样的能做买卖吗?武大郎卖棉花人熊货囊,再加上心慈面软,拿谁都当八百辈儿老姑舅亲,送你两句好话给钱都不要了。咋样,蒸饺馆开黄了吧?不服气,八珍熟食店也黄了吧?有的是外人不雇,非得拽着自己的死老爷们,就让他卖他的烟去呗,烟棚子小伸不开腿,以前咋干的?嫌憋屈?活该,谁叫他没能耐的。你心好可怜他,他可怜你了吗?处处跟你较劲唱反调,提溜个大长脸,八杠子压不出半个屁来,你能指使了他吗?他能当服务员吗?懒得腚帮骨都带不动,说话比放屁都冲,来人也得给吓跑了。还一门儿往兜里掖钱,你说你让他把钱当掌柜的,结果赔个老底儿朝天,连冰箱、黄金首饰都搭了进去。难怪后来人家啥也不干,再说就他那样的除了卖烟还能干啥?
现在好,眼瞅着小命就要搭上了,店都黄了俩了,咋还张罗开呢?我就纳闷了,这是啥意思呢?开也行,让他家给拿底垫儿呀,管娘家要什么呀?你说你这不是成心祸害娘家吗?还哭喊着不给拿不走!借,说得好听,拿啥还?谁还?还是你二嫂有心眼儿,你就是哭死人家也不吐一分,我看那就对了!得,我儿子那两千我给做主不要了,就当孝敬你了,活该,谁叫他是当外甥的;可你怎么还管老叔家的小艳借呢?五百块钱让人家可哪叨咕,整得亲戚都不亲了,见着我都爱答不理的。你也真能耐,谁的电话都知道。再说你三姐,她自己还吃人家下眼食呢,从哪儿给你弄的两千呢?这回瞧好受气吧,说不定得多挨多少揍呢;你二姐跟我说,她那两千是二分五的利现借的,她自己还有一屁眼子饥荒没堵上呢,难道你不知道?还有你小哥,起五更爬半夜,点灯熬油,写俩月才挣了一千块稿费,还没等用手焐热乎呢,就让你给抠去了。你在这儿吃三服汤药顶多能拿出一服药的钱,完了死吃死嚼,饭钱呢?再说了,你总在这儿吃药,店让他和他妈管,这不是还得给搂黄铺吗?你说你这个实心眼儿的大傻狍子,让我说你啥好呢?怎么专门坑娘家人呢?
恨死了,白长一副漂亮壳子。好时候一点儿俏钱不知道挣,就知道死啃娘家人,这眼瞅都死到脖颈了还使劲儿祸害一把……
大姐的话说得确实够难听。
对于四粉这最后一次开店,我、二姐、三姐事先都已心知肚明。我们拿钱与其说是帮她完成最后一次心愿,不如说就是买个自己将来心里的不后悔。因为四粉她不甘、不愿、不想死,还想好起来,还想自食其力,甚至想供我在家写小说。
我心烦起来,并走出里屋,说,大外甥和小艳的电话是我让打的,那钱当时准备做手术用,跟开店无关。打酒问提瓶子的要钱,以后她还不上我还。等下次回去我找小艳,那几个钱,至于吗?行了行了,你别哭了,你也别说了,赶紧做饭,都饿了!
四粉拎着药包和一大兜“八珍熟食”一直在门口站着。不知什么时候,大猫凑了过去,在距四粉脚边不到一尺远的地方,正一边翻滚一边斜眼看着她。它在四粉家住过两回,一回是几年前我去长白山写电视剧本,另外就是非典时回老家的那次。
四粉抱起它,立刻又哭了。
小说到这里应该结束了。
四粉是第二年夏天死的,比医生说的多活了大半年。
最后大半年,她果然变成了孤家寡人。我和大猫驻寨,二姐三姐轮流打替班,最后又雇了一个陪护。四粉的房子早被她租出去吃了汤药了,后来的一切费用三姐出得最多,剩下的靠我在报社的一个哥们给募集的捐助。
这些年,我一直保持着和姐姐们的来往。走得最近的是二姐,我年年回老家上坟,她年年往我这儿倒腾蛋呀、杂粮呀、山菜呀,以及产自自家园子里没上化肥的干菜。我所做的是尽力帮她还为她儿女借高利贷。她一儿一女都在城里,没工作,做点小买卖,却总赔。二姐两口子就不停地给他们寄钱。每年春秋两季,农活最累时,我都会接到二姐跟我哭诉的电话。大前年秋天雪下得早,割倒的苞米还没等扒就被捂大雪里了,我在电话这头除了听到二姐的哭骂,还听见盘旋在山尖上西北风的啾啾声。自非典那年后,我再也没回老家帮她种过地。都是各过各的,帮一时救不了一世。这是二姐说的。
自打大姐的大儿子帮着盖了二层楼,小儿子结婚,另外因公家占地按月拿补偿款后,大姐心就稳了,加之年龄也大了,就不经常往老家折腾了。她大儿子和我同在一个城市,常年在外包盖电厂,和我几乎不联系。四粉借的那两千块钱,再附上我的一份,被我以红包形式,分别在她过六十六、六十八大寿时汇了过去。去年秋天她想大孙女特意来我住的城市住了一星期,晚上住儿子家,白天在我这儿。一天,吃过午饭,我俩搬两只小板凳坐在走廊,一时没话,就望着厨房白花花的光线发呆——
这时候,我又起来了那年,四粉、大姐和我,我们仨最后一次相聚。
那天,我们仨吃完饭,四粉挺着肚子在厨房洗碗,我和大姐搬了两只小板凳就坐在这里。厨房连着阳台,亮得晃眼,让穿着一身浅粉色睡衣的四粉就像要化了似的。光柱从厨房半敞的拉门投过来,在我和大姐脚边,形成了一个好看的平行四边形。
因为吃得太饱——四粉从家里带来两只大“八珍”猪肘和五斤大棒骨,把我们撑着了——刚坐下让人感觉有点儿不适,我们就看着白花花的厨房,边发呆边没话找话。不知不觉就由阳光说到天气,由天气说到季节,由季节说到收成,由收成一下子就跳到眼下的吃喝和钱上。
然后就说到李潘。
她是当年四粉在红林宾馆时期的姐妹,那时,四粉做白案师傅,李潘在舞厅当领班,我则在她们开户的工商银行驻红林办事处做会计出纳员。大姐搬家之前去住女儿家,顺脚来看我和四粉,在宾馆餐厅吃饭时见过李潘。
大姐说,吃饭时我就想,到现在也没想起来,就那个大高个儿、大屁股水蛇腰、在舞厅上班的女的,叫啥的呢?
李潘。四粉在厨房答道。
妈呀,是叫李潘,她现在在哪儿呢?
我愣了一下,说,早来这儿了。
前天还来看我的呢,说过两天再来给我小哥洗被。四粉又说。
刷你的碗吧。我回了四粉一句。
妈呀怪好的呢,现在啥样了?
还那样。
那样人不显老,现在干啥呢?
不清楚,没问。
都不用问,咋整都错不了,你瞅那个精劲儿,一眨巴眼睛一个道儿,一点儿亏不吃。结婚没有?
没听说。
那是挑呢。你看着吧,末了谁也没她找得好。你说我就纳闷儿,也就有个个头儿,模样儿多一般哪,可人家咋就那么能呢?听说当年把林业局头头脑脑,还有那帮倒腾木材的老客玩儿得滴溜转。估计钱早就挣足了,现在就是啥也不干也够过了。满家子还都跟着借光。听说那几年就在县城买了大楼,把爹妈和小弟接走了,还给哥姐在下边林场都安排了好活儿。你瞅瞅,完了屁股一扑搂,扭身进了大城市,照样当大姑娘。你说多能。哪像这——大姐压低声音,突然眼锋一刁,冲厨房一撇嘴,回头又咬了咬牙——混来混去,连小命儿都要丢了!
你说那几年形势多好啊,林业局富得流油,南来北往倒腾木材的老客赶着趟儿,就跟蚂蚁泛蛋似的,随便摸一个就是身家百万,都不止。只要人家手指一松,就够你花两辈子的了。别说长李潘那样,就是长得像猪八戒他老姨那样,跟他们勾搭上都照样赚得盆满钵满。钱就跟大风刮来的似的,都不用弯腰去捡。你说你也是,那时候咋不把班儿给扔了?那时候要是把班儿扔了去倒腾木材,就凭你的聪明,说不定早就发达了。发了之后再捣鼓小说呗。说来说去,都没抓住好时候。
还有——那个李潘,你别怪我多嘴,看样儿现在对你还没死心,当年我和你二姐、你三姐就怕你跟她搞对象,现在看,你要是娶了她还逮着了呢,在家爱咋写咋写,光老底儿就够花了。省得我们没黑没白替你担心。人得想开,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儿,刺啦一下就过去,能享受千万可别找罪遭。你瞅瞅这——大姐又把声音压低,冲厨房撇了撇嘴——有钱能混到这份儿上吗?啥叫正经?正经啥用?当饭吃还是当钱花?你好好琢磨琢磨,再不抓住机会,不抓住李潘,就更啥都晚山秋了。
……
大姐还要往下说。我打断了她。
我说,行了行了,咱不提这茬儿了。
大姐说,可有件事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你说打小穷得恨不得连裤子都穿不上,咋就不知道稀罕钱呢?啥时让钱给吓着了?见着有钱的望烟逃,专门儿冲穷鬼使劲儿。说人家有钱的没有好玩意。啥意思呢?怕被人坑还是怕被人骗?这下好,找个穷鬼,可是好玩意儿,混了一身的病。再说在宾馆那会儿。都一样在舞厅陪人跳舞,人家恨不得上男的裤兜里掏去,可咱家人,这给都不要,到底是咋想的呢?不想要,就别跟人跳了呗,干赚闲话不说,还干赚着费鞋底儿,你说这是哪股劲头呢?我听说你一个月给她买了三双鞋,不怪我说!
我忍不住说,不光是跳舞,餐厅本来就费鞋。
大姐说,瞅瞅,一说她你就不高兴。得了,我算看明白了,你就是上辈子该她的!
我说,什么叫我该她的呀?凭啥我该她的呀?谁不知道把钱留着给自己得劲儿花呀?
大姐说,所以我就纳闷儿嘛,找不找有钱的先不说,可咋就不知道在外面挣,然后反过来给你呢?你看人家李潘,咱家这个可倒好,到现在还是张嘴伸手——
我突然气愤起来。
然后和大姐一应一和,就像声讨,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