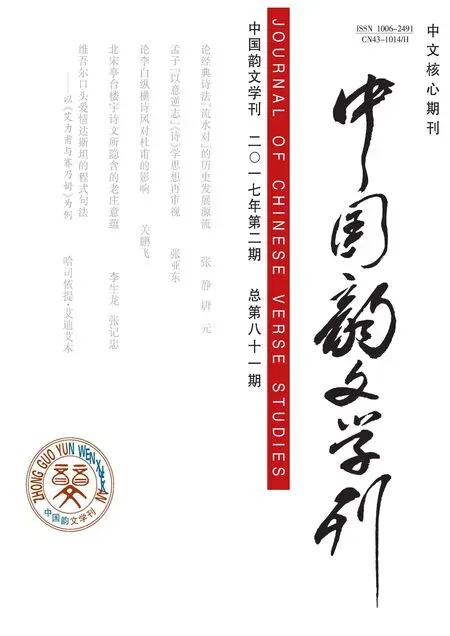陈三立自辩说考论
张 宁
(湖南城市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晚清民国文学研究所,湖南 益阳 413000)
陈三立自辩说考论
张 宁
(湖南城市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晚清民国文学研究所,湖南 益阳 413000)
陈三立是民国诗坛的领袖,评论者通常视其为江西诗派。他虽没公开表示异议,但却曾私下进行辩解,以阶段性的创作特征来回应诗坛上流行的整体性评价。这反映出他想淡化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却又无法完全否认的矛盾心理。他的遭遇也说明当读者所谓的某种知、不知、解、不解成为一种共识的时候,原本最具话语权的作者既很难在公众视野中还原自我的理想形象、诗学取向和审美趣味,亦无法摆脱世人贴在身上的标签。诗派林立、风格多样的诗歌江湖表面上看是诗人技艺、诗歌高下之争,实际上也是读者审美、好恶、话语的角逐。
陈三立;江西诗派;自辩说
“同光体”诗派在清末民初诗坛上居于主流地位,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等人。其中,陈三立的创作成就最引人瞩目。张慧剑在《辰子说林》中说:“诗人陈散原先生,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杨声昭称:“光宣诗坛,首称陈郑,海藏简淡劲峭,自是高手。若论奥博精深,伟大结实,要以散原为最也。”汪辟疆云:“至陈散原先生,则万口推为今之苏黄也。其诗流布最广,工力最深,散原一集,有井水处多能诵之。”一些评论者认为陈三立之诗法源自宋代江西诗派。如李详谓:“陈君诗宗西江。”李之鼎云:“义宁陈伯严吏部三立,天下久震矜其诗,以为足绍西江诗派。”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评价说:“双井风流谁得似,西江一脉此传薪。”这里的“西江派”即江西诗派之意。陈三立七十寿辰之际,友人纷纷以诗相赠,不少人直言其为江西诗派。冯煦诗云:“西江诗派续黄陈。”姚华称:“少陵诗句几山谷,永叔文章亦退之。”罗惇曧谓:“西江诗派黄双井,南宋遗民谢叠山。”陈三立对这些评论虽没有表示异议,但他却不喜人称 “西江派”。他私下对胡翔冬说:“人皆言我诗为西江派诗,其实我四十岁前,于涪翁、后山诗且未尝有一日之雅,而众论如此,岂不冤哉?”显然,诗坛上流行的说法与陈三立本人的自我定位有所出入。王培军在《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中指出:“尤足诧怪者,则其夫子自道,亦明确否认,不自承学涪翁。”陈三立的“冤屈”是否属实?又缘何有这种矛盾的说法呢?本文试加以探讨。
一 四十岁前未尝雅好涪翁之说不可信
涪翁、后山分别指黄庭坚和陈师道。陈三立所称雅好涪翁、后山诗云云,实针对所涉及“江西诗派”的笼统说法。宋代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将黄、陈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命名为“江西诗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江西诗派的“三宗”,称:“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三人中,黄庭坚对后世影响最大。陈三立生于咸丰三年(1853)农历九月廿一日,到光绪十八年(1892)刚好40岁。事实上,他在40岁前已对黄山谷存有好感。
1877年,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为隆观易《罘罳草堂诗集》作序:
既而取阅其《罘罳草堂诗卷》,则逢源杜与韩,语言之妙类大苏,而似归宿于吾乡山谷老人,世之号为能诗者未易而有也。无誉(指隆观易)自言:“向读朱文公《中庸注》,至‘静深而有本’之语,恍然悟诗教之宗。”故其诗淡简以温,志深而味隐,充充乎若不可穷。往尝论今之为诗者,大抵气矜而辞费,否则病为貌袭焉。而窃喜子瞻称山谷“御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之言,谓为得其诗之真,而颇怪世少知之而为之者,盖乡先辈声响歇绝,殆千数百年于兹矣。读无誉诗,其庶几遇之也。无誉将行,予与笙陔以其诗无副本,虑亡阙于道里之险艰,相与尼留其稿,而略为择录若干首,付之剞劂,兼以质无誉塞外云。
陈宝箴对隆观易极为称赏,认为其诗源于杜甫、韩愈,语言妙如苏轼,旨趣似黄庭坚,甚至将其视为黄庭坚的接续者。这样的评价自然也反映出陈宝箴对黄庭坚的推崇。傅熊湘称:“此序可谓能发作诗之诣者,不独深知无誉也。无誉诗以七律为最工,散原盖亦承其流者。”傅熊湘的话似乎隐含着这样的逻辑:陈宝箴深知并认可隆观易的诗歌,加之隆氏的七律成就较高,因而陈三立受其影响。他在《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一文中进一步指出:“(陈三立)诗出于黄山谷,而与稍前之遵义郑珍极相近。珍字子尹,所著有《巢经巢诗集》。又宁乡隆观易,著《罘罳草堂诗集》,三立之父宝箴,时官于湘,为之刊行,疑亦散原诗所从出,其气味亦相近也。”傅熊湘认为隆观易诗似山谷,陈三立诗出隆观易。傅氏此说不知依据为何。钱锺书质疑说:“隆氏宁乡人,向于傅钝安遗著中见其姓名,极推其七律,谓散原诗所从出,心窃怪之,今虽未睹全集,已断知傅氏之为谰语。”同时,钱锺书指出《销食录》中曾载有一些传闻:“陈右铭观察亟为欣赏,命伯严公子抄录以为把玩,后集中有《留别右铭伯严》《怀伯严》诸诗,足徵文字因缘而已。”钱氏对此不以为然。
傅熊湘的臆断和《消食录》的记载应当事出有因。王闿运《隆观易小传》云:“义宁陈宝箴,好奇士也,得见观易,特以为诗人之穷者,又隐阨不自拔耳。然尤喜其诗,为之刊行,间以示人,人亦未之问也。”陈宝箴出于欣赏,为其刊印诗集,还极力推广。在这种情况下,“命伯严公子抄录以为把玩”当然合乎逻辑。
而且,陈三立本人与隆观易交情颇深。1879年正月下旬,陈三立得知隆观易去世的消息后,深感痛心。他在给廖树蘅的信中说:
无誉凶耗,正月下旬已得宁夏喻太守书及所寄讣函,闻之怛悼伤怀,雪涕无已。以无誉之才之学而止于此,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昔人有言,诗人多穷而多夭,是耶非耶?而三立所为疚心者,所代为校刊诗篇,以字画讹舛,辗转迁延,未能早日告成,使无誉以一见为快。
这里陈三立提及的代为校刊诗篇一事或许就是《销食录》所谓陈宝箴“命伯严公子抄录以为把玩”之讹。陈三立为隆观易作传,谓其“敝精力呕血为诗歌,自废斗室空山,憔悴枯槁。其志深,故其道隐;其怨长,故其辞约而多端”。这说明陈三立对隆观易生平所历相当熟悉,对其诗领悟很深。既然陈三立嘉许诗风类似山谷的友人,这至少表明他对黄庭坚是认可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对山谷持有好感,故认可隆观易之诗)。后来,他推崇范当世的诗歌,也与范氏诗风类似黄庭坚有关。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明确指出:“三立之诗,晚与郑孝胥齐名,而蚤从通州范当世游,极推其诗,以当世亦学黄庭坚也。”据龚敏《范当世与陈三立的文学交往》一文所云,“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范当世离开天津李鸿章幕府赴江夏湖北按察使署省亲嫁女,也就是从这年开始。我们看到《范伯子诗集》中有了与陈三立的赠答之作”。陈三立此时刚刚42岁,他对范当世的欣赏,自是此前喜爱黄庭坚诗歌顺理成章的结果。陈三立看到范当世的《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诗后,即作《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诵之叹绝苏黄而下无此奇矣用前韵奉报》(1902年)。他认为范当世的诗可以比肩苏东坡、黄庭坚,并在诗中感叹说:“吾生恨晚数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这些话语既表现出他对友人诗作的欣赏,同时也表明陈三立对苏、黄的敬仰和歆羡。
而且陈三立在评价友人诗作时,常将之与黄庭坚进行比较,甚至将其拟为“黄庭坚”。这说明在陈三立看来,黄庭坚的作品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参照标准。如1879年,陈三立在信中评价廖树蘅的诗说:“大诗浑雅之中复有雄直之气行乎其间,大似苏黄。”
此后,陈三立对黄庭坚的称许之意一再表露。1889年10月,陈三立游览黄庭坚故居,赋诗相赞。其中《长沙还义宁杂诗》第十五首云:“双井涪翁宅,松萝相向青。千年今怅望,一代汝精灵。乌影沿溪灭,茶烟散雨冥。神州清啸罢,来拂旧镌铭。”从“千年今怅望,一代汝精灵”一语,可以看出他对黄庭坚十分推崇。
陈三立刊刻《山谷诗集》,应是他对黄庭坚有所属意的结果。1893年,陈三立41岁。他在杨守敬的藏书楼中见到从日本得来的宋椠本黄山谷内外集,马上想到“念余与山谷同里闬,余父又嗜山谷诗”,这既可反映出陈三立对黄庭坚的敬仰,又表明其父陈宝箴嗜好山谷诗对陈三立的影响。陈三立《山谷诗集注题辞》云:
光绪十九年,方侍余父官湖北提刑。其秋,携友游黄州诸山,遂过杨惺吾广文书楼,遍览所藏金石秘籍,中有日本所得宋椠本黄山谷内外集,为任渊、史容注。据称,不独中国未经见,于日本亦孤行本也。念余与山谷同里闬,余父又嗜山谷诗,尝憾无精刻,颇欲广其流传,显于世。当是时,广文意亦良厚,以为然。乃从假至江夏,解资授刊人。
另外,就诗歌创作而言,陈三立早年诗歌有明显的避熟避俗的痕迹,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黄庭坚的诗学观念和创作风格。如一些字词的使用,其《武陟官廨赠杜俞》(1881年)诗首句云:“山城飒凉飚,微霖歇喧浊。”“飒”一般用作形容词,且常以词组“飒飒”的形式出现,或表清凉之意,或拟作风声。然而,陈三立却将其用作动词,表起风之意。同时,以“飚”字代替常用的“风”,以“霖”字取代“雨”,这显然是诗人的有意安排。《游隆中诗》(1882年)云:“氛雾列缤纷,岫堮攀翱翔。”“缤纷”有繁多而杂乱之意,又引申为颜色多而绚丽,用之修饰“氛雾”并不常见。陈三立将“岫堮”连用,并用“攀”字来表现山势直逼天空、几欲挣脱地面的情状,颇有新奇之感。又如“澶漫廛闾隐,杏霭林峦晚”(《从献冲越嘉义岭遂至长寿司》,1887年),“夙驾及回途,轻装翼流飚”(《还长沙发龙谷市向山口》,1887年)等皆属此类。
同时,一些意象的使用当亦出于此种考虑,如“烟外乌啼冷”(《长沙还义宁杂诗》,1889年),“千甍日暖乌啼暮”(《东坡生日饮集待石园西轩》,1889年),“暮鸦朝雁日相期”(《湘上录别一首》,1891年),“饥乌飘雁各在眼”(《和答南皮尚书凌霄阁置酒用原韵一首》,1892年)。“乌”的意象冷僻而落寞,它的反复出现当是诗人有意为之。陈衍在评价陈三立的诗时,就将“乌”看作三立避熟避俗的一个例证。他说:“为散原体者,有一捷径,所谓避熟避俗是也。言草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鸟不言紫燕黄莺,而曰乌鸦鸱枭;言兽切忌虎豹熊罴,并马牛亦说不得,只好请教犬豕耳。”后来,陈三立秘不示人换字秘本当是这种求新求僻的用字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云:“闻其作诗,手摘新奇生崭之字,录为一册,每成一篇,辄以所为词句,就册中易置之,或数易乃已,故有时至极奥衍不可读。”这一传闻后来得到刘成禺的证实,他在《世载堂杂忆》中称:“陈散原老作诗,有换字秘本,新诗作成,必取秘本中相等相似之字,择其合格最新颖者,评量而出之,故其诗多有他家所未发之言。予与鹤亭在庐山松门别墅久坐,散老他去,而秘本未检,视之,则易字秘本也,如‘骑’字下,缕列‘驾’、‘乘’等字类,予等亟掩卷而出,惧其见也。”
由此看来,陈三立40岁前已对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黄庭坚持认可态度。他自称40岁前于涪翁诗且未尝有一日之雅的说法并不可靠。
二 自辩说的委曲之意
从上文中,我们不难看出陈三立以阶段性的诗歌创作特征来回应诗坛上流行的整体性评价。这反映出他既想淡化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却又无法完全否认的矛盾心理。
众人评价陈三立为西江一派,是就其总体创作而言的,有合理性。比如陈三立自己也曾直言对江西诗派的认同。1904年,他所作《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其三云:“驼坐虫语窗,私我涪翁诗。镵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在这里,陈三立自认“私我涪翁诗”,毫不掩饰对黄庭坚诗歌的师法。此外,陈三立与张之洞有关诗句理解的分歧也颇能说明其诗学取向。1905年重阳节,陈三立受张之洞邀请登高,作《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饯送梁节庵兵备》。诗中的“作健逢辰领元老”一句引起张之洞的不满。这件事屡屡被时人提及。陈衍《石遗室诗话》认为“此在伯严最为清切之作,广雅不解其第七句,疑元老不宜见领于人”。张之洞不满这句诗,或因其中有尊卑无序之意。但更可能是因为这句诗不够“清切”。如陈曾寿解释说:“逢辰二字甚生,此二字后山、朱子常用,公偶未忆及耳。”“甚生”反映出一般人对于“逢辰”二字的感受,尤其是为陈师道、朱熹所常用,陈三立此处与陈师道恰恰相合,这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者对前者的亦步亦趋。张之洞未必没有想到出处,或许恰恰是因为他知道出处,才会不满。正如钱基博云:“(张之洞)生平宗旨,取平正坦直,最不喜黄庭坚,题其集曰:‘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如佩玉琼琚,舍车徒荆棘。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子瞻与齐名,坦荡殊雕饰。’几于征声发色,不啻微言讽刺,而见诗体稍僻涩者,则斥为江西魔派,不当意也。”从句法上看,“作健逢辰领元老”意在表现“元老领众士”,然语序的调整使意思的表达变得曲折,“逢辰”又颇有生僻的嫌疑。张之洞向来注重“平正坦直”。因而,才会心生嫌恶。陈三立最“清切”的作品却让主张“清切”的张之洞觉得不满。说到底,这是两种诗学旨趣的分歧。
陈三立奇崛奥衍的诗歌语言、曲折隐晦的表达方式以及避俗避熟的诗学趣味都与江西诗派相契合。因此,世人视其为江西诗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陈三立为何不肯明言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呢?
人所共知,江西诗派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对初学者颇有助益。不少诗人即由此得其门而入。陈三立早年对黄庭坚诗歌的态度就有问途于江西诗派的意味。这与一般学诗者从江西诗派入门的经历相吻合。
然而,江西诗派技法上的弊病招致不少人的批评。如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李调元在《雨村诗话》中指出:“西江派诗,余素不喜,以其空硬生凑,如贫人捉襟见肘,寒酸气太重也。然黄山谷七言古歌行,如歌马、歌阮,雄深浑厚,自不可没,与大苏并称,殆以是乎?后山诗,则味如嚼蜡,读之令人气短。如‘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二句,系集中五律起笔,竟成何语?真谓之不解诗可也。拥被呻吟,直是枯肠无处搜耳。”陈三立本人的创作甚至遭受时人的非议。如1914年,柳亚子作《论诗六绝句》,抨击陈三立、郑孝胥等人,如其二云:“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1916年7月24日,任鸿隽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三立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同年10月,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亦有类似描述:“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盦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文学云乎哉。”1917年南社主任柳亚子与社友姚鹓雏、闻野鹤、朱鸳雏、成舍我等人因唐宋诗之争引发激烈的争执,在这场论辩中,柳亚子直言对江西诗派不满,称:“意者野鹤又用其作西江派诗之惯技,移而作文,故钩章棘句,使吾辈读之甚感不快耳”,“仆向西江派宣战,于兹十年,功罪自任之”。陈三立对于这样的批评之声应该是了解的,他不愿直言与江西诗派的关系也就容易理解了。
事实上,陈三立不认可世人的评价,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即创作和诗学取向的转变。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父子皆被革职,参与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则横尸刀下,陈三立悲不自胜。1899年,陈宝箴致信俞明震说:“立儿自经此家国巨变,痛急万状,虽病不肯服药。日前进药,竟将药碗咬碎,誓不贪生复活。”1900年,陈三立写信给廖树蘅书,称:“别来又已几载,沧桑之变既已至此,复骤值先公大敌,通天之罪,万死何辞!”1901年,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国变家难,萃于一时,集于一身。”陈三立自觉地将国变家难的悲剧加诸己身,他看到的是表象背后人世之劫难、生命之痛楚、岁月之荒谬。故其诗境为之一变,深感“片念微茫千劫换,一椽人海阅枯禅”(《移居》),“残生余血泪”(《闵灾》),“转恸江湖容后死,独飘残鬓看中原”(《哭孟乐大令》),“况今世变幻苍狗,屡闻窃国如分瓜”(《同叔澥筱珊登扫叶楼归访薛庐顾石公遂携石公及梁公约过随园故址用前韵》)。吴宗慈对此做了很好的概括:
先生既罢官,侍父归南昌,筑室西山下以居,益切忧时爱国之心,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欷歔,不能自已。越一年,先生移家江宁,右铭中丞暂留西山埥庐,旋以微疾逝,先生于此,家国之痛益深矣。西山者,《水经注》作散原山,先生晚年自号散原,所以识隐痛也。其后僦居金陵,凡数载。庚子后,离开复原官,终韬晦不复出,但以文章自娱,以气节自砥砺。其幽忧郁愤,与激昂磊落慷慨之情,无所发泄,则悉寄之于诗。
这种以一己之情感寓诗的方式已经与江西诗派讲求文字、技巧和表达的诗法取向有了明显差异。
进入民国,陈三立虽然选择平静地以遗民身份终老,实际上内心郁积着深深的兴亡之感,他屡次提及的“国变”一词即是这种感伤的影射。或许基于此,陈三立民国以后的诗风明显向杜诗靠近。如《三月七日抵南昌铁路局谢蔚如同年招朋辈会饮入夜风雨中走谒欧阳丈》(1914年)云:“越江犯重湖,了了见乡国。严城殷鼓鼙,几变旌旗色。……客归迷所向,人群依典则。宵阑声震瓦,愧对面黧黑。”樊增祥称:“此诗乃少陵《北征》缩本也。”杨声昭《读散原诗漫记》云:“散原诗五古似韩似杜,亦似大谢。五律则专意于杜。吾最爱其《对雨》及《别俞氏女往柏灵》诸篇,意境高敻,字句矜慎,曾涤生氏谓下笔迟重绝伦者,此类足也。”吴宓在《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中对陈三立诗与杜甫相似之处有不少分析。如其谓:“《散原集》中诗,以五古为最多,且最胜。写景述意,真切深细,实得力于杜诗者。”他也对孤篇进行分析,称:“《雪中楼望》因小思大,有杜工部之怀抱及格调。”同时,吴宓还指出:“凡先生所为挽诗、寿诗,皆从历史、政治、国局、世运大处落墨,持论精严,可为其人之最好评传。此是杜工部《八哀诗》之义法。”这些评论敏锐地捕捉到陈三立诗风的移易。
陈三立的诗歌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并不奇怪。早在1895年,友人黄遵宪就曾为陈三立指出两位楷模——杜甫和韩愈,并殷切地希望陈三立变通而自立。他在《陈三立诗题识》中说:
唐宋以来,一切名士才人之集所作之语,此集扫除不少。然尚当自辟境界,自撑门户,以我之力量,洗人之尘腐。古今诗人,工部最善变格,昌黎最工造语,故知诗至今日,不变不创,不足与彼二子并驾而齐躯。义理无穷,探索靡尽,公有此才识,而勉力为之,遵宪当率后世文人百拜敬谢也。
陈三立对黄遵宪的见解应该是赞成的。这可以从他们之间彼此的认可程度推测出来。就在黄遵宪做出上述分析的前一日,陈三立也在《人境庐诗草跋》中对黄遵宪给予充分的肯定:“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不久之后,黄遵宪在写给陈三立的信中诚恳地说:“无论何等文字,究欲得伯严评数字以为快。”那么,遭逢家国巨变后陈三立诗中流露的沉哀巨痛及其呈现出的奇崛风格,当与黄遵宪这次对话中为其指出的这两位楷模有关联。至清末,陈宝琛就曾指出陈三立深得杜甫、韩愈之妙。1908年,其《题伯严诗卷》一诗谓:“老于文者必能诗,此道只今亦少衰。生世相怜骚雅近,赋才独得杜韩遗。”这说明陈三立在靠拢山谷的同时,亦对杜甫、韩愈等人有所倾心。
当然,这种取向的转移并不意味着陈三立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由于他人生际遇的变化,情感思想在某一时期与某一诗家更为契合,并或隐或显地通过创作加以呈现。陈三立对杜甫的认同,并不表示否定黄庭坚。他在民国时期的创作就颇能说明这一问题,陈三立有的诗近杜诗风格,有的则似山谷诗风。甚至,同一首诗也会给人似杜似黄之感,樊增祥评价《九江铁路局楼闲眺》(1914年)“前六句纯乎杜陵,收句乃入山谷”。又认为《崝庐三首》“三诗亦杜亦黄,实非杜非黄,自成为散原一派”。陈衍也注意到这种变化,故其谓:“辛亥乱后,则诗体一变,参错于杜、梅、黄、陈间矣。”这样的创作反映出陈三立诗学观的通达和包容。
再者,陈三立晚年极为看重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其创作本身亦自成一家。吴宗慈《陈三立传略》载有他的创作心得,其云:“应存己。吾摹乎唐,则为唐囿;吾仿夫宋,则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故吴宗慈称其“所为文诗,一句一字,皆经千锤百炼而出,斯能精魂相接,冥与神会焉”。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云:“伯严乃以余为后世之相知,可以定其文者耶?大抵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奡之意态,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李渔叔亦谓:“散原精舍诗,其得力固在昌黎山谷,而成诗后,特自具一种格法,精健沉深,摆落凡庸,转于古人,全无似处。”或许因为陈三立晚年感觉个人的创作已经超越前人藩篱,自成一家,因而不认可仅将其归为一家一派。因此,他才会在私底下表示不满。
三 结语
诗人所处之诗坛,如侠客所行之江湖。行处其间,诗人自重其名誉与位次。
初涉诗坛的籍籍无名者通常借助前辈名家的推介,以求捷足先登,扬名立万。如民国诗坛,渴望与陈三立交接的晚辈甚多,钱仲联称:“少年后生,得其一言褒赞为荣。”然而,由于诗学取向、审美趣味、亲疏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他人品评与褒贬的结果可能与作者预期存在一定差距。如自诩“天罡”的陈衍在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仅被拟为“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据汪辟疆云:“甲戌来金陵,一日与石遗登豁蒙楼煮茗,因从容询曰:‘君于有清一代学人位置可方谁氏?’石遗曰:‘其金风亭长乎?’时黄曾樾亦在座,因问余:‘君撰《光宣点将录》,以陈先生配何头领?’石遗不待余置答,遽曰:‘当为天罡耳!’余笑。石遗岂不知列彼为地煞星首座耶!殆恐余一口道破耳。”陈衍的抢答显然有自我标举,以示不满的意味。夏承焘曾亲闻其抱怨。1934年11月30日,夏氏赴金天羽之邀,席间陈衍“谈点将录以散原为宋江,谓散原何足为宋江,几人学散原诗云云。言下有不满意”。陈衍对汪辟疆的不满,属于作者对某一特定对象的抗议,自是人之常情。
陈三立的情况要复杂的多。他面对的是诗坛上流行已久且近乎一致的集体性评价。正如王培军所云:“散原诗学山谷,在当时盖为公论。”而这一公众认知虽不完全准确,却又有其合理性。这既已成人所共知的旧闻,自然难以公开辩驳。陈三立既为诗坛巨擘,褒贬与否皆无损其声誉。况其处世泰然,如其自云:“故余丁扰攘污浊之世,往往杜门偃仰,累月不复出,为得淑人相师友,养德性永天趣,犹有以坚其志而自适其适也。”陈三立在文学革命的语境中下尚能“杜门偃仰”,“以坚其志而自适其适”,当然也就无意纠缠于诗友们善意却不完善的评论。
诗坛评判与陈三立私下的辩解本质上反映的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知与不知、解与不解的矛盾。当读者所谓的某种知、不知、解、不解成为一种共识的时候,原本最具话语权的作者既很难在公众视野中还原自我的理想形象、诗学取向和审美趣味,亦无法摆脱世人贴在身上的标签。而这种舆论所形成的判断和认知无形之中也将被评论者归类,划分派别。诗派林立、风格多样的诗歌江湖表面上看是诗人技艺、诗歌高下之争,实际上也是读者审美、好恶、话语的角逐。陈三立身为诗坛领袖,虽有不满,却不得不在公众视野中保持沉默的姿态,他的遭遇实为行走诗歌江湖之人的缩影。
[1]张慧剑.辰子说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2]杨声昭.读散原诗漫记[J].青鹤,1937,5(14).
[3]汪辟疆.汪辟疆诗学论集:上册[M].张亚权,编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李详.药裹慵谈[M].李稚甫,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5]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M].李开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上册[M].王培军,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
[7]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J].学衡,1923(13).
[8](元)方回.瀛奎律髓汇评:中册[M].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汪叔子,张求会.陈宝箴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傅熊湘.傅熊湘集[M].颜建华,编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1]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徐一士.一士类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4]龚敏.范当世与陈三立的文学交往[J].古典文学知识,2009(3).
[15]钱锺书.石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6]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M]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17]刘成禹.世载堂杂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8]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1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9]苍虬.读广雅堂诗随笔:续[J].东方杂志,1918,5(4).
[20](清)李调元.詹杭伦,沈时蓉,校正.雨村诗话校正[M].成都:巴蜀书社,2007.
[21]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册[M].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2]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M].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3]胡适.胡适文集:第2册[M].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4]中国革命博物馆.磨剑室文录:上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5]杨声昭.读散原诗漫记[J].青鹤,1937,5(14).
[26]吴宓.吴宓诗话[M].吴学昭,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7]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M].潘益民,李开军,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28]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9]钱仲联.梦苕盦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0]汪辟疆.汪辟疆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1]夏承涛.天风阁学词日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李剑波
2016-06-22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大事编年”(项目编号:14BZW094);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传播学视域中的民国旧体诗大事研究”(项目编号:16C0312)
张宁(1986— ),男,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文学。
I226.7
A
1006-2491(2017)02-0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