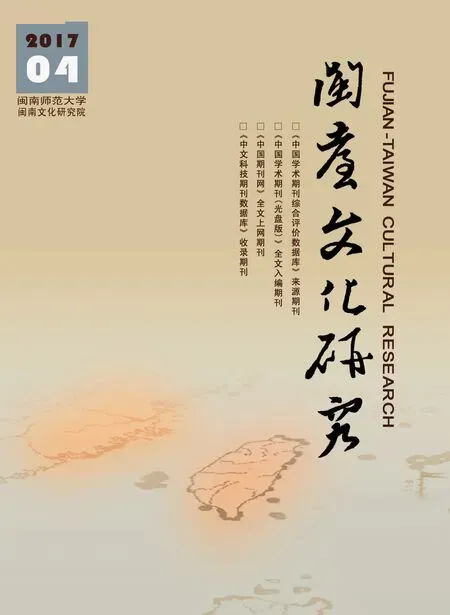农事·礼乐·会计
——黄道周《月令明义》思想研究
蔡 杰
黄道周(1585~1646),福建漳浦人,字幼玄,号石斋。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历任崇祯朝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少詹事,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隆武朝内阁首辅等职,后募兵抗清,被俘不屈,于隆武二年(1646)就义于南京。乾隆四十一年(1776)谕文以品行称他为“一代完人”;道光五年(1825)清廷将黄道周请入孔庙从祀。
黄道周是明末大儒,著名的易学家、理学家和书法家,时人徐霞客盘数天下名流时,称:“至人唯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所谓学问直追周孔,即指黄道周以六经救世,重拾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特别是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兼容并跨越汉宋,回归六经,直追周孔,《礼记》五解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明朝中后期阳明后学蛊惑天下,黄道周痛心疾首,他主张以六经救世,上疏以六经授太子,并“在长安中,闭门深于幽谷,今复作小书生,再翻传注”,亲撰《洪范明义》《月令明义》《儒行集传》《缁衣集传》《表记集传》《坊记集传》《孝经集传》等,此中即包括了著名的《礼记》五解。黄道周的《月令明义》立足于传统社会制度,其思想与《月令》原旨保持一致,主要可分为农政思想与王道思想两个方面。
一、传统视域下的月令旨归
《月令》是《礼记》的第六篇,此篇被编入《礼记》以及作者年代问题,在历代饱受争议。经学大师郑玄即对其发难,认为此篇摘自《吕氏春秋》,而非传统的说法为周公所作,“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尽管受到质疑,但是《月令》式的“时政”颁行,却是历代政令的一项重要内容,最典型的是唐代玄宗御定“月令”,“更附益时事,名御删定,月令改置《礼记·第一》”(《旧唐书·礼仪志四》),于是至今仍有《唐月令》的文本流行。再如宋代也重视“月令”的颁行,“真宗时,贾昌朝撰国朝时令;景祐中,丁度等承诏约唐时令为国朝时令,以备宣读”。可见《礼记》中的《月令》文本虽受到质疑,但是“月令”作为一种传统时代的政治制度,却有其重要地位。
月令的哲学是一种唯时观,体现出古人对“时”的敬畏。所谓“月令”,“月”即是时间,“令”为政令,也就是因时布政。“时”是政令(甚至人类活动)的最高依据,四时变化可以指导人类生活生产、万物休养生息以及政治社会的治理。“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荀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时而作,以天地为法。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月令是一种不同于唯物论或唯心论的“唯时论”,是有其道理的。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决定了古人的生产活动必须依靠天时,于是古人对天时十分顺从与崇拜。倘若有不顺从,也就是出现违时行为,那么将会受到惩罚,比如《月令》中明确记载“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月令的思维不在空间差异上的因地制宜,而是因时制宜,所有的因时制令、因时为政都是以“时”为最高依据而展开的。所以断不必勉强强调《月令》中的时空结合或时空一体,单是“因时制宜”的思想放在今天,就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月令》出于“时”,归于民。“月令”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性特点,其所有律令最终都落实到形而下层面,为了天地万物和谐,为了人民生存与社会安定,体现出儒家极强的目的论。尽管《月令》中条令广涉天文、气象、草木、鱼鸟等与自然环境相关的事物,今人也颇以此阐发《月令》的生态哲学或生态智慧,但生态问题绝非《月令》的思想旨归。《月令》指向的是人民与社会,“用以课农时,驻物候,上可以资钦若,下可以训作息”,非在自然本身,更不在动物植物,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保护环境。即使每月最末一条的违时惩罚,最终影响的也是人事,而不在自然环境或动物植物,如“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竟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惰,师兴不居”。所以今人大谈《月令》的生态哲学,这本无可厚非,但实不是《月令》的主旨。在儒家视域中,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论语》中有“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月令》中所体现的“天人和谐”思想观念,若要细细分析,则为“以人适天,天为人用”。
《月令》的出于时而归于民,若以传统哲学术语表述,则为出于天,归于人。单有出于天,而不落实到人,则中国哲学将无有归宿,将失去现实意义;单有人事主张,而没有对天的敬畏与信仰,则中国哲学将走向堕落,将失去道德价值。汉儒如董仲舒,对四时五行是持敬畏与信仰之心的。到唐代柳宗元开始对四时五行相配提出质疑,“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以远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使古之为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养幼少,省囹圄,赐贫穷,礼贤者?”至宋儒虽对四时五行相配较少阐发,但对天地化生仍持有敬畏之心,“凭着这份敬仰敬畏之心得以把人的价值追求往上提升”。尽管后来清儒支离破碎的训诂考据,预示着对天的敬畏与信仰消失,儒学由信仰走向俗世化,但此前《月令》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发展到明代仍是有的,并且特别为黄道周《月令明义》所突出强调。
二、《月令明义》所体现的农政思想
《月令明义》的核心思想是农政王道。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人民百姓基本以农为业,所以农政理应是政治的基础,也应居于政事首位。因此《月令明义》反复强调以农为本,“《月令》之义,以农时为本”,“是书专为农政”,再如孟春月引汉文帝二年正月诏书“农,天下之本,民所恃以生也”,又引其十三年诏书“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黄道周认为历代如汉文帝,可谓知道为政之本,也就是务农。
“农事者,先王之首务也”,那么这就决定了所有与农事不相干的,都需让位;所有对农事有所妨害的,都需制止。《明义》引汉景帝二年四月诏书“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说明农事、女红作为防范饥寒的保障,是人民百姓生存的根本,不可妨害,不可耽误。于是像商贾贸易一类,则由此被视为末端,这可以说是儒家“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源,如果百姓人民不务农而奔走于商贾,那么小农生产的社会结构将受到冲击,最根本的生存条件得不到保障,百姓则无法安居,国家则无法安治,于是黄道周提及“文帝时称极治,粟红贯朽,犹云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以当时一意务本抑末,市籍之家称为最贱”,这就是农本商末的体现。除了抑商,军事也不能妨害农务,“至武帝时擿发七科,犹以三世有市籍者分为三等。然自是兵之妨农百倍于商,又无论酒醪之糜谷、六畜之众食矣。军兴而后始竞言屯,大率行之,未有实效”,以历史史实说明了军事之妨害农务,要比商贾严重得多,并且认为农业应置于军事之前。除此种种,强调大凡政事都以农事为本为先,还如“聚大众置城郭,则游民长而农时失”,兹不复再举。
于是《月令明义》对神农、后稷十分推崇,二者作为农神,是古代农业的象征。以神农为例,《明义》说道“农神养气,不宜摇之;农神持功,不宜败之”,此处“农神”即是农业的象征,意思是说即将进入秋天,但还没到秋天,仍不得提前动摇农事,可见凡政事皆应以农为本。由于浓厚的农本思想,《月令明义》对非关农事者,则多不予阐发,甚至常往农政农事的角度以发明,比如今人颇以为生态思想的“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的《月令》经文,《明义》仍将其阐发为为了农事,而非与生态相关,“毋作大事,毋动林薮,盖皆为农事也”。再如在《月令》孟秋月经文“鹰乃祭鸟,用始行戮”下,《明义》阐释道“鹰不祭鸟,师旅无功;天地不肃,君臣乃懈;农不登谷,暖气为灾”,对“行戮”并无多少发挥,反倒又提及农事。所以整本《月令明义》,以农为本的思想几乎是贯穿始终的。
农本必然导出民本。在传统时代的中国,普通人民百姓一般以农为业,“农”是就职业身份说的,“民”是对社会地位说的,二者在古代可以说几乎吻合,所以《月令明义》引汉文帝十二年诏书“道民之路在于务本”,这里所谓“本”即指农。可以看出《月令明义》同时体现了较强的民本思想。
上文主要阐述了在政治律令的层面,农政农事应置于首位。而自政治伦理关系角度看,人民应置于君主、神灵之前。黄道周引春秋时期季梁关于民神关系的著名观点“夫民,神之主也。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认为在国家社会居于主宰地位的是人民,而不是神灵,所以应以民为本,将人民之事置于神灵之前,只有人民百姓安定和谐,神灵才肯降赐福祉。黄道周引用这一观点,仍对神灵持敬畏之心,但可以看出他的民本思想,一切当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出于这一点,在祭祀神灵、宗庙、山川时,实质乃是“为民祈福”,黄道周说道“天子为百姓以祀山林名川、社稷寝庙、皇天上帝,故先皇天而后上帝,先上帝而后社稷,先社稷而后寝庙,先寝庙而后山林名川,故古之为仁孝者,非自身致也,达其大本而后合举之,以天下奉其天亲,犹以肤发奉其心志也”,意思是说大凡天子祭祀,多是为民而祀,人民是国家社稷之大本,而所谓仁孝不仅仅是用心致力于父母亲人,而更应是用心致力于天下百姓,以天下百姓为“天亲”。所以说“甚矣,圣人之爱民也,甚于父母之爱其子也”,就是将仁孝一涵推广至“大本”“天亲”,如此才是国家社会意义层面的大写的仁孝。
按照季梁的思想逻辑顺序,是人民为先,鬼神次之,君为再次,亦即所谓“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也就是民心混乱不一,则鬼神无主,那么人君一人独丰独厚,国家也无法安治统一。整个国家社稷是一个整体,人民是这一整体的基本。由此看来,孟子著名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是有其源头活水的,而黄道周至明朝末年仍对民本十分重视,可谓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脉相承。
如果将民本上升到哲学层面,则必然导出人本,其实就是中国哲学一个重要命题:天人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天人关系是民神关系的抽象与升华。当然,我们不好说人为天之主或者人在天之前,因为“天”的范畴总要比“神”大一些,天不仅具有主宰的身份,而且还是最大的合理性与人世万物的最高根据。所以《月令》中每月之末都有一段违时的惩罚报应,正是体现了“天”的主宰地位。古人一向对天持敬畏之心,人于天的关系为“以人适天”,在《月令》表现为顺时。但是天作为最高依据,并不是说人就没有主体性。人之能顺时适天,就说明了人本身具有自我把控的主体性,所以在人的层面,是可以通过操控政令以顺时,从而得到天的回馈赐福,比如:春季“五政苟时,春雨乃来”;夏季“五政苟时,夏雨乃来”;秋季“五政苟时,则五谷皆入”;冬季“五政苟时,冬事不过,所求必得,所恶必伏”。从这一层面上讲,天反而处于有求乃应、有恶乃伏的被动地位,而人本身则具有极大的主动性,这种被动与主动的关系就决定了“天为人用”的结果。所以人并不是天的附庸,人于天是平等的。结合人民作为国家社稷的基础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民因为有其自身主体性就成为国家社稷的“天”。归根结底,仍是民本人本的思想。
《月令明义》体现的天人关系是“以人适天,天为人用”,人处于主体地位,所以一切政令实是出于天而归于人,最终都将落实到人的层面,包括人民本身以及国家社会。总而言之,《月令明义》十分突出农政思想,可以简单构建为“农本—民本—人本”的政治思想模式,从政治律令的角度看,一切政令当以农为先、以农为本;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君主、人民、鬼神当以民为先、以民为本;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在天人关系中当以人为本。中国哲学具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本源决定生存,譬如“一年之计在于春”,注重春的首位与本位能够决定一年的生计;再如天命之性往往在人的一生中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再极端者如宿命论。所以说无论是农、民或是人,将其置于首位与本位,在中国传统视域中于政治、于社会、于国家社稷都具有决定性。
三、《月令明义》所体现的王道思想
在天人关系上,强调人拥有主动性以适天,从而得到天的恩宠福祉,亦即天能被动地反过来作用于人,国家社会得以安定,其最终目的就在于一个“治”字。而达到“治”的理论方法本有多种,《月令明义》所阐发的农政民本主张,体现了深刻的王道思想。王霸之辩是先秦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逸周书·文传解》记载了文王的遗嘱“诸横生尽以养从,从生尽以养一丈夫。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材,无堕四时。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可以看出就国家得以长治久安而言,王道要优于霸道。所以王道思想作为儒学学说的重要来源,受到历代儒者的重视。黄道周在《月令明义》中阐发农政主张,自然而然流露出了王道思想,他提倡君主应推行仁政德政,由此民心才能统一归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居于此,《月令明义》意不在发明性理微旨,而是阐发外王之道。就仁孝一涵而言,上文提到仁孝不仅是用心于父母,更是致力于百姓,这就是王道的体现。兹就此一涵再举一例,养老是孝道的重要内容,但《月令明义》阐发养老思想,非在事亲本身,而是着眼于国家制度的政治层面。《月令明义》引《礼记·王制》以历数诸朝养老体制,“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西郊”以及“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说明上古三代的养老制度十分完备。黄道周认为养老制度是章服礼仪、庆赏刑威的根本,应置于最前,“章服以庆君子,刑戮以威小人,养老以教孝弟,孝弟立而后庆威行,庆威行而君子、小人各得其序,然后神明可得而享也”,提出了一套政治手段以治人的顺序,为先重养老,而后庆赏刑威能行,也就是养老是其根本。高举仁孝作为施政宗旨,正是王道政治的体现,传统社会的养老制度在当代制度中极具借鉴意义。
若要探求所以注重王道政治的原因,那么则在于为了维护传统礼制,寻求民定国治之道。“养老之礼废,则子弟易其父兄,庶姓慢其长上,骄奢洊出而叛乱滋起,章服不足以劝,刑戮不足以威,而天下乃乱矣”,可以看出王道的精髓在于制定与维护伦理秩序的礼治,如果处于根本地位的礼制受到破坏,社会等级秩序、伦常规范失序失位,那么章服礼仪、刑威杀戮都无法治理社会动乱的根源。所以要对《月令》精神的总体把握,就是从“时”到“治”,这也是《月令》“出于天而归于人”的思维模式的另一种表述。
所以《月令明义》提倡的政治是仁政德政,“古今治法皆以赏罚并言,惟《月令》详于庆赏而略于刑威,秋令云斩刈必当,亦不过一言而已”,这就是仁政的体现。因而黄道周论《月令》的宗旨用了一句话概括,为“本于农事,中于礼乐,终于会计,而皆曰是民之力也”,这里“会计”指的是天子大会群臣,计功行赏,也就是重庆赏的表现。凡以农为本、以礼行政及重于庆赏,都是王道的体现,故可以“农事—礼乐—会计”作为《月令明义》所涵王道思想的总纲。居于此,《明义》对《月令》经文中行戮惩罚的条文少有阐释,以《月令》每月末经文的违时惩罚报应为例,在《月令》每月末违时惩罚的条文下,《明义》除了对季春、季夏、季秋、季冬记载布施五政以及孟春、孟秋解释何为四季之令,基本对违时惩罚的条文不置一词。这样的空白在整本《月令明义》中是少见的,这可以说是轻于刑威的体现,也是王道思想的应有之义。
施行仁政德政,亦即外王之道对于人君的要求是内圣。“《月令》每言庆赏,不言诛罚,每言举贤遂良,不言逐谗放佞,其意只存于礼乐农,宽慈惠下”,这里说的不是内圣开出外王,而是外王的前提条件是内圣。《礼记·大学》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也就是说治天下的前提是治国,治国的前提是齐家,齐家的前提是修身,修身的前提是正心,正心的前提是诚意,诚意的前提是致知。那么反过来,致知不一定能达到诚意,诚意不一定能达到正心,正心不一定能达到修身,修身不一定能达到齐家,齐家不一定能达到治国,也就是说内圣不一定就能开出外王。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而后”一词仅表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不是推衍生化的必然结果,例如“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再如“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老子》)。用逻辑学推理分析,内圣是外王的必要条件,欲达到外王须有内圣作支撑;但内圣不是外王的充分条件,内圣不一定能开出外王。反观《月令明义》,外王之道必然向内要求君主须达到内圣的高度,于是有“人主宽大、敬慎、爱人”,有“敬以治之,和以养之,静以居之,诚以行之,仁以宣之”等诸多说法,都是从外王的角度向君主提出内圣修养的要求,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
总而言之,作为《月令》诠释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黄道周的《月令明义》基本与《月令》宗旨保持着一致。其中农本民本的思想贯穿整本《月令明义》,特别是春夏两季,《月令明义》还突出以礼为政与详庆赏而略刑威的特点,如此种种都是突出了传统月令思想中外王的特点。若将整本《月令明义》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以“农事—礼乐—会计”作为总纲,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中倡导仁政德政的思想主张。
注释:
[1]徐霞客:《滇游日记七》,《徐霞客游记》(卷七下),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710页。
[2]黄道周:《答魏秉德书》,《黄道周集》(卷十九),翟奎凤,郑晨寅,蔡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70页。
[3]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2页。
[4]袁褧:《枫窗小牍》,(卷下),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籍本。
[5]傅道彬:《(月令)模式的时间意义与思想意义》,《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
[6]例如乔清举《儒家生态哲学的基本原则与理论维度》(《哲学研究》2013年第6期)、张自慧《礼文化中的人与自然之和谐观》(《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郭刚《〈礼记〉和谐生态哲学》(《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8年第5期)等均对《月令》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有所涉及,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农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徐长波《〈礼记·月令〉生态哲学思想探析》(《中州学刊》2014年第9期)等更是正面阐发《月令》的生态哲学。
[7]李光地:《御定月令辑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柳宗元:《时令论上》,《河东先生集》,(卷三论),宋刻本。
[9]冯达文:《儒家系统中的宇宙论及其变迁——董仲舒、张载、戴震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0期。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2][33][34][35][36][37][39][40][41][42]黄道周:《月令明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孔晁:《逸周书》,《汲冡周书卷》(第三),四部丛刊景明嘉靖二十二年本。
[38]《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第7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