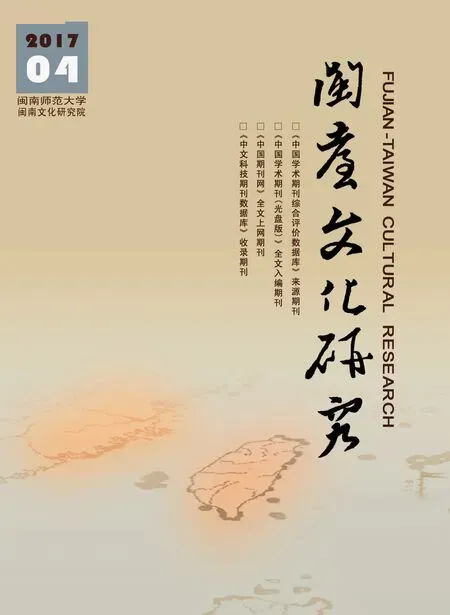闽南王爷在南洋:跨国信仰的国际性、历史感与在地化
王琛发
从航海地图寻找各地闽南代天巡狩信仰,17世纪以后的诸府王爷香火,不但分布在闽台各地,同时间是一路直奔明清两代的南海诸国。南洋各地主祀或附祀各姓王爷香火的庙宇,散布亚洲多国领土,整体上呈现跨海跨境的传播态势。各地诸府王爷香火,也是各有落地生根的渊源,不见得一定都是直接源自中国本土。其中,有很多王爷宫庙的香火原先是供奉在船上,或来自其他港口,通过信众商贸或开拓新土地,跨海跨境。因此,讨论诸府王爷信仰文化的历史渊源,固然追溯闽南,但现下各国王爷信仰已然演变成国际性质的在地信仰,互有渊源而各自精彩,若称“闽南王爷信仰”,或称“闽台王爷信仰”,正如称“台湾王爷信仰”或“缅甸王爷信仰”,都只能是指称信仰文化本源于闽南地区,由此说明它长期交融于各地的地方历史文化脉络,却不足以描绘此一信仰源于闽南而跨海跨境的整体文化景观。世界各国的王爷信仰落地生根,不受时间政治障碍而跨海跨界联系各国信众,是历史事实,也是当下的期许。
一、王爷信仰的开拓精神
诸府王爷香火落地生根在不同国家,由各姓王爷分散各地组成其整体分布之形势,其实也体现着信众与神明香火播迁的自家本色。其不同于其他闽南神明香火传播的特征在于:它印证闽南人传统上强调王爷“巡狩”之职权,也印证此类王爷信仰文化拥有过的“王爷不入永春”谚语;其“巡狩”范围不是从闽南向中国北部驱进,也不是西进或南向走入两粤地区,而是向东出海,沿台湾海峡一路南下,走入昔日漳州张燮《东西洋考》以文莱分界的所谓“南海”东、西两洋;至迟在南明诸政权更迭之际,不论位处“西洋”的越南,或位处“东洋”的菲律宾到马来西亚沙捞越,都出现诸府王爷的分香。数百年来,王爷信仰是沿明清两代的西洋航线,从越南一路沿海南下,分布在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在绕入马六甲海峡以后又沿海道北至泰国与缅甸。正如马来亚北海船仔头天福宫赵府王爷1888年碑文所说:“我同人自寄居西洋槟城亦成百年矣”。这说明过去谚语常说王爷的“代天巡狩”特征在于“过州吃州,过府吃府”,现实中显然真有其事——既在内陆的州府之间翻山越岭,尚且在东西洋航路上漂洋过海。
如此香火分布态势,正好重叠着昔日南海丝路。这大片历史上的南海—西洋航路所及,郑成功为主的前明部队曾经长期沿用,以维续南明政治的国际贸易,其航路远至缅甸,联系着永历残部势力;再后来天地会洪门部众延续“反清复明”,也是在同片海域的沿岸各处开拓许多垦殖区。王爷“过州吃州,过府吃府”,表面是说神灵,其实何尝不是反映人群与文化播迁?当群体侍奉着神灵香火落脚新地头,民众咸感此地也是祖辈世代供奉的神灵佑护之地,特别是以庙宇体现聚落空间的信仰中心兼文化特征,又以王爷的“五营”军马展现此地天命的神圣势力范围即信众日常势力所到的“本境”,由此也就转化出大众当地无殊故乡的土地认同。王爷“过州吃州,过府吃府”因此也是处处可以开疆拓土落地生根的开拓精神。“我们的”神灵凝聚了集体理想的道德价值,尚且在新土地实现,脚下土地就不再是没有意义的外在空间,而是与“我们”实践生命意义融为一体的“场所”。其实,这样的土地观,表现在王爷信仰,抑或其他神明香火到此,都是基于认同“德”是神圣体现,彰显着《大学》所谓“有德此有土,有土此有人,有人此有财”。
南洋诸府王爷香火当中,有的仅仅奉祀一位王爷,也有共祀多位王爷。而共祀一位以上王爷,很多时候又是反映着不同原乡群体下南洋如何在地结合。马来西亚吉兰丹州华人人口最稀少,1909年以前原是暹罗属国,居民以马来人居多,后来由暹罗割让给英属马来亚;在该州巴西吗(Pasir Mas)县,华人便是根据人间的结义关系,把Aur Duri村的苏府王爷称为大王爷,把隔河对面彭家兰巴西村的镇府宫杨府千岁称为二王爷,还称江沙村池府王爷为三王爷。超过百年之后,地方信众对几位王爷如何分出辈份,也是不了了之。这其中,镇府宫的杨府千岁本由一位名叫王寿的开拓父老从原乡带来,1940年建庙前后已经形成邻近甘榜古丹、登笼、纱卡、十三行等十几地区信众联系;另外,江沙村则至今保持最早组织形态,依靠各家各户每年掷筊选出值年炉主,由值年炉主义务将池王爷神像带回家设案供奉,以服务公众祭拜的需要。巴西吗当地华人,通过集体轮办三位王爷诞会,也让各村村民年年互相前往邻村赴会,促进来往。而大众在请神仪式,又尊称池府王爷“祖王爷”,希望其神威遍显境内,驱邪除恶。
再如越南会安市福建会馆,在当地是香火最鼎盛而庙貌最辉煌。会馆自乾隆丁丑年(1757)至1974年屡有重修碑文,说明越南华人在1690年代最初是搭建草屋供奉妈祖,命名 “金山寺”;直到1757年由福建帮出资改建瓦庙,改称“闽商会馆”。再到1849年会馆增建后殿,方才从别处移入张姓、黄姓、钦姓、十三姓,舜姓与朱姓的“六姓王爷公”。现在会馆成员每年把2月16日祭拜六姓王爷,2月1日拜金花娘娘及3月23日“妈祖生”,视为三大活动,其中祭拜六姓王爷最热闹、参与人数最多。但若观察所谓“六姓”王爷,其中“十三姓”不可能是一个姓,“舜”姓还可能包括其他舜裔分派的诸多姓氏。因此“六”应当带有图谋数字吉祥的意义,用以形容多姓;很可能当地最初有六个长期祀奉王爷香火的群体,其中有“十三姓”的结合,这些群体到19世纪时候已经融合为一,当地闽人社区便将六处香火结合。由此推测,当前“六姓”亦不代表中国原来六个村落王爷,已经推广至反映着全体越南闽裔老百姓的历史与真实存在。
而缅甸澳报市区,玉庵殿可为另一案例。据笔者询问当地父老,这是间主祀玉皇大帝的公庙,又盛行着邢府王爷与哪咤香火。其中,邢府王爷香火,是1913年陈奕培、陈奕俊领创本庙,由中国福建省南安县山后乡引进的。从那时的缅甸华人以“仰光埠”对称“澳报坡”,可见此地不似仰光繁华,但因着位于仰光通往卑谬之间,以必经之道成为商镇。以邢府王爷香火来自南安乡村,建庙时方被引进,受到地方上接受,或相关当地建庙群体的原乡渊源。当地近期报导提到,玉庵殿初创时,地方居民只有七八十户华人,大多数靠经商维生。这足以说各地最初的信仰群体不见得会人数众多,但开创共同体往往需要以彰显神道维护互相间的伦理,原乡神明落地也就代表了贯通天命人心的人格道德到社会秩序降临到地方社会,为大众做主。
再把缅甸仰光郊外的顶淡汶埠跨境对照马来西亚吉兰丹巴西吗,则会发现,不论前者在马六甲海峡出印度洋东面,后者在南中国海西面,正当地方人口较少,经济开发之初,两地信仰群体处理香火风俗相当一致。缅甸顶淡汶青龙宫在19世纪80年代从中国大陆迎来徐府王爷、恒府王爷、日府王爷,最初也如吉兰丹巴西吗江沙村池王爷,是轮流供奉在诸善信家中,到1956年乃由善信捐款建宫。而顶淡汶另有安福宫供奉的潘府王爷,是福建南安静安宫分香,与青龙宫三王府到缅时间相近。可是青龙宫与安福馆同在一地,甚至1950~1960年代都由当地苏姓为主的闽人供奉,但最初祀奉两庙神灵群体看来可能是不同聚落或渊源,所以各分组织。
另外,南洋各地多处王爷香火,更是被当地同宗信众视为祖辈,以祖先崇拜姿态入主族人当地重建的宗族村落,或者被供奉宗祠正中神龛。各姓华人对这类同姓王爷,往往不称“某府千岁”或“某府王爷”以免生疏,而是尊敬昵称“祖佛”或“叔伯大人”。正如槟榔屿东北角面海浮罗池滑(Pulau Tikus),当地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尚未开发市镇,来自闽南不同宗族村落的先民也在当地形成犬牙交错的宗族聚落,互相连接为据守海岸的地方势力。根据辛、柯、蔡济阳堂宗祠“水美宫”碑文,宗祠自1814年以来再而重修,数次沿用庙宇旧称,或改名宗祠,都不改对原乡蔡忠烈、忠惠二位王爷祖神崇拜。其宣统元年(1909)重修碑记即说“水美宫者,始自福建海澄县之三都钟山社,乃系蔡姓之家庙”,其中最早有同治壬戌年(1862)《水美宫碑记》则称:“槟屿之域有王府之庙,乃中华福漳之澄邑于钟山社之水美宫所自始也,溯自前人经商抵此,供带灵光香火。……是于我蔡家诸人云集重修”。至今,宗祠殿堂正中二位蔡王爷,还有柯、辛两王爷,依旧逢年过节接受子孙膜拜,咸认祖圣威灵显赫。
若论“代天巡狩”的原意,《孟子·告子》有说“天子适诸侯,曰巡狩”,是指天子巡察本朝展示的权势与教化,及于天下诸藩属国;而《幼学琼林》所谓“代天巡狩,赞称巡按”,则是皇亲或大臣奉令代理天子视察地区,或负责权衡、斡旋、改变、决断当地事务。民间信仰心理以为朝野事务反映天命伦常,人间体制不外顺仿天界体制;诸府王爷身份既尊称“千岁”,神圣巡游也以“代天巡狩”旗号开道,王爷当然拥有代理天帝燮理阴阳之权柄,巡察人间、赏善罚恶、施福降祸,驱瘟斩邪。依据这样一种逻辑,一般老百姓惊怕天灾人祸缠身,只能求老天做主;神灵如有“代天巡狩”的权威,则不论处在信众原乡或者新开垦土地,势必能超越一般鬼神,为百姓主持公道。何况,有的王爷原本就是大众原乡祖辈亲近的神明,有些王爷与信众之间又是同姓亲情,甚至是血缘先辈,或带领过大众祖辈的“祖佛”。老百姓求老天爷做主,有具体而亲近的祈求对象,大众漂洋过海的决心更安定,就更有信心抱团出门闯天下,有魄力异地群居,形成新家园。
以上述源自海澄县钟山社蔡姓人的槟榔屿“水美宫”为例,其群体又是经历过分分合合。先是蔡姓曾经联合其他邻近闽南开拓先民,一度形成共祀辛、柯、蔡、朱、池、李六姓王爷;以后其他信众把朱、池、李位三王爷迁移到湾岛另建“水美宫”,原地水美宫则由钟山社后人做主,依据祖先同源的立场,继续祀奉留在原址二位蔡王爷,以及辛、柯王爷为祖神,演变为联合“辛、柯、蔡”三姓宗祠。但从槟榔屿国际海港演变的视角看群体建庙一分为二,朱、池、李王爷香火后来是据守槟榔屿北面湾岛(Tanjong Tokong)码头市镇,而辛、柯、蔡则是继续坚守东北角沿海;这足以反映大众心目中源于神灵感召的分家,客观上推动了开枝散叶、开疆拓土。当地又有传说,说朱池李三府王爷北上湾岛期间信众互相纷纭,结果神明指示兵马令旗去湾岛镇守新开拓区,朱府王爷香炉则留在原区,安置在福寿宫,离“辛柯蔡”宗祠不远,恰好在分开的两处“水美宫”路程之间。湾岛水美宫光绪八年(1882)《重建水美宫碑记》有云“尝谓神以民为依照,民以神为保障,是知神民有维系而不已者”,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二、王爷信仰的国际视野
湾岛水美宫庙前石头柱子上对联写着“水陆兼权怜赤子,美灵特赫慰苍生”,这证实早期信众“过州吃州,过府吃府”,日常上下海港祭拜尊神,不外期待诸府王爷以“水陆兼权”保障善信跨山越海。由此进一步认知,诸府王爷既然远在南海以南保护信众开山辟地、海贸交易,则王爷信仰文化固然远溯闽南,也不可能在南海任何地方停止传播。旧时闽南沿海村落信众本就盛行佩戴王爷香包或带着圣像出海,祈求下海上岸一路平安;而南海各地延续相同风俗,王爷香火就不止常见于港口邻近,甚至也供奉在海商的商船。当商船停泊在各地,王爷香火或留在船上,或在港口岸边暂驻,接受当地华裔与地方原住民信众晨昏膜拜。其实,正因为有了商船海路传播,才能进一步推动王爷信仰跨海跨国的格局。
杨国桢曾引证大英图书馆藏乾隆乙丑(1769)《送船科仪》,并根据这份海澄道士专为海船人员禳祭用的文本指出,渔村举行“送船”目的和内地农业社会驱病除灾的心理本质相同,是由王爷把瘟神押送出境;然而海商和航海人沿用“送船”习俗,则是赋予王爷押送瘟神以外的护航海神功能,使得传统上的送瘟神仪式转带出海洋社会的特色。这种情形,在南洋海商社会体现更明显。原来,国际商贸依靠各港口互通有无,将产品从价格廉宜的生产地运往需要供货的地点,就能产生价值。可这也容易把各地细菌传染船上或传染其他港口,如此造成商船损失或导致合港伤亡,后果难以估计。因此,许多镇守河海港口的王爷庙也如镇守河海港口的其他神庙,往往会挂上“合港平安”横幅。对照19世纪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各地祈请王爷咒语,或能更清楚其目标在祈求河海平安。在马来亚半岛,吉兰丹位处南中国海西面航道南边,其巴西吗杨府二王爷咒语说“游遍天下河海港,过州府县鬼神惊。”“过州吃州,过府吃府”首先要“过港吃港”。而当地另有请求朱府王爷降坛咒语,开首诗句“谨请本坛十八庄,被水漂流见龙王”,表示大众崇拜朱府王爷威灵显赫,因其能调度江海龙王拯救各村庄成员在海上漂流等灾难。
而19世纪槟城海峡两岸的诸府王爷香火,或能提供较显著范例。自英国殖民者1786年占据槟城,英国东印度公司根据马六甲海峡水势,善用槟榔屿东北部东面内侧港湾改造马六甲海峡当中的槟榔屿,善用这个岛屿东面相对马来亚半岛大陆西岸的小海峡建立亚洲首个适合西方轮船进出的深水自由港。一直到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国际贸易主要依赖航运,槟城是亚洲唯一连接着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交界的国际自由港口,也是本海域的最大港。槟榔屿的不少王爷宫庙,其实就是守卫着各群体在港口岛屿各处岸边创建的码头,迎接各国上下人员和货物。槟榔屿东岸便有闽南宗姓村落后裔在当地重建靠海宗姓社区,包括建立俗称“桥”的木构渡头社区。随着海岸线历史以来不断随着填海向前伸延,这些“桥”也不断抢占策略性位置。到19世纪末,在这个港湾内,李府王爷香火,先是随同安兑山李姓族人落户最早的海边舢板巷公屋,后迁往族人直接对接外船的“姓李桥”;同安丙州社陈姓族人也如“姓李桥”一样,把他们的开漳圣王香火和陈府王爷祀奉在“姓陈桥”人们上下的岸边。沿着这条东面海岸线北上,就是浮罗池滑辛、柯、蔡三府王爷,还有留守福寿宫福德正神庙的朱王爷,再北上则是湾岛朱、池、李三府千岁。沿着同一东面海岸线南下,又会在日落洞区遇见几间孙、佘、池王爷,祖庙都是南安仑苍镇蔡西村寮洋宫。再南绕到槟屿东南部,则会在峇六拜“过山”遇上孙、刘二王爷。
而隔着海峡,槟榔屿对岸马来亚半岛的威省,行政上属槟城州政府;沿岸也有些王爷庙座落在靠海或者靠河港的地区,庙宇成员又是多有从事相关槟屿港口贸易的对接工作,包括经营大小货船接驳,在本埠小港上下供求产品。这些庙宇之间,如拉惹乌达(Raja Uda)灵应社,碑记记载是1846年间建庙,内置同治十三年(1874)“代天巡狩”匾额,本与日落洞的三王府同源。又如船仔头地带,过去原本即槟城闽商来往内陆码头,也是造船工坊集中区域,其“天福宫”现存最早匾额与香炉作同治辛未年(1871),门前放置尊奉顺平侯赵子龙“代天巡狩”的仪仗器具与牌匾;宫中光绪十四年(1888)碑文,主要捐款人是来自槟城的闽商兼会党领袖邱天德与胡泰兴,上边提到“我同人自寄居西洋槟城亦成百年矣”。
在威省更北面的日落斗哇(Teluk Air Tawar),其中天地堂三保宫供奉着缅甸商船传播进来的七府王爷香火。其香火既证实南海各地王爷信仰不尽然都传播自中国本土,又反证缅甸当地曾经有过七府王爷的信仰。更重要是,正如上述吉兰丹巴西吗镇府宫流传咒语,涉及马来亚半岛东岸南中国海的航海与港口,天地堂三保宫则在马来亚半岛西岸见证了马六甲海峡王爷信仰的海上特色——王爷在这带海域正如在南中国海,亦被视为镇海护航神明,曾经供奉在各国商船之上,包括接受缅甸船员膜拜。
除了缅甸传播马来亚,也有从马来亚传播缅甸的。像仰光华人朱府王爷信仰,与九皇大帝信仰结合,便是一例。据说,仰光的朱府王爷与哪咤元师神像,最早由马来西亚海商1896年以前带来,本是供奉在仰光码头桥边咖啡店后头,后来有位善信陈承波将朱府王爷和九皇大帝都供奉在二十条街42号,以后再由陈水闹、曾金汝、陈水来、杜拉拉敏代代传承;一直到1916年举办九皇大帝盛典,陈金淡传给施金章,再传施福德,才安置在只荷坦路32号。按照仰光地图,二十条街位置靠近仰光江边那条称为“海滨街”的大马路。此处朱府王爷供奉格式,神龛主位是朱府王爷,附祀中坛元帅哪咤,上方却是九皇大帝。如按规制,从二十条街发展到只荷坦路的九皇大帝,可谓分香,但当地人却以先人忠义关系代入香火关系,称前者为兄,后者为弟。虽然不知仰光朱府王爷从马来西亚何处传入,但在航海地图上,此地来往马来亚与印尼,都是依靠槟榔屿港口。而旅缅叶氏南阳堂1950年代也同样位于二十条街,叶氏宗亲以惠泽尊王叶森为祖神,并有同治朝追封“代天巡狩”之说,还说明先辈遍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可见其时各地诸姓称“王爷”或者“代天巡狩”的信仰群体,声气相同,多有靠港立祀,跨海往来。
槟榔屿和泰国之间,海贸带动跨海王爷信仰传播,亦有迹可循。湾岛水美宫庙同治六年(1867)的“惟德是依”匾额,署名“特授暹罗国丕阿暽啷、福建府龙溪县霞屿社许泗漳”。许泗漳本是海澄籍农、矿商兼船主,自1822年起在槟榔屿租借帆船,沿暹罗西岸各岛屿贸易,经营各种生意遍马六甲海峡以北,后开辟泰南暽啷,获封“丕阿”勋衔。查阅地图,浮罗池滑或湾岛码头,相比槟榔屿其他闽人码头,最接近许泗漳率众开拓的暽啷矿区;1882年《重建水美宫碑记》说“我唐人虽在夷地,服贾营生”,碑文上包括许多商号。由此看,由许泗漳到其子许心美,许心美历任董里府府尹、普吉省省长等职,闽人陆续居留当地,包括普吉岛网寮斗母宫内奉池府王爷香火,泰南各处王爷香火延续至今,岂无槟城渊源?只惜当下缺乏史料与重新联系。
然而,也当注意某些地区的王爷信仰传播,并非源于商贸,只是其群体因着商贸市镇变迁,发生迁移、重建与演变。例如,印尼的峇眼亚比亚比(Bagansi Aip Api)位处苏门答腊东北岸,是洛江溪支流下的交会点,在马六甲西南对岸,在新加坡斜南岸;根据洪士明《峇眼亚比开拓文献》记载,本地开埠实源于暹罗管辖之思思(地名)地方在1878年二月间发生土著策动排华,洪尔魁等18位洪姓同安籍渔民闻讯后,连夜带着2位金门籍许姓妇人驾驶渔船南逃新加坡;他们在转航马六甲海峡以后沿途捕鱼交换伙食,并于对面大山脚镇暂住,听闻苏门答腊的利巴咸地区有捕鱼,方才决议前往,后便落脚邻近的峇眼亚比亚比,设虾寮维生,招呼同乡前来。至今,这18人姓名俱全。以此说,当地洪姓开埠设立“永福宫”供奉福德正神,附祀纪府王爷,后把当地演变为同安语聚落,先是经历屠乡、逃亡、易地而居过程,后是依赖马六甲和新加坡等邻近商埠逐渐发展海产渔港,最终成为世界第五大渔场。印尼21世纪政策转向,地方政府自2003年起重新看待纪府王爷“烧彩船”,定位“廖省最重要民俗文化节”;这样一来,排华疑虑有机会成为历史,长期下去必然发生地方文化遗产与国际旅游商业结合的趋势,当地人民又不得不考虑如何权衡其中矛盾了。
事实上,1950年代之前,本海域各民族国家尚未对华人收紧政策,王爷信仰在今东盟诸国各地跨境传播相当普遍。只是20世纪东盟各国屡经政治动乱,包括日本侵略、反殖民战争、内战、排华,华人庙宇有的消失,有的多年后方才重建。如缅甸板庭梧当地记载,福护宫供奉金府王爷,是由缅甸华侨陈缨赏发起创建,1912年始建于板庭梧埠东郊。1940年,陈明屋、薛芳史感觉原庙地处偏僻,遂于河滨街购地建新宫;不料1949年遭遇缅甸内战,神庙毁于战火,陈天乞携带神像逃难仰光6年,1954年春,陈永竹、周宝来、陈水奔等人发起重建,翌年从仰光奉迎王爷返回板庭梧,1956举行落成庆典。当地近年报导,本庙历经缅甸内乱、重建,经历办学,以及地产被收归国有,到2015年再度重建落成,并举行103周年庆典。这一来,这类庙宇和祖庙的联系,或与其香火分支的来往,多是陷入失去联系、有待考证的处境。
无论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各国王爷信仰文化翻山越海,跨海分流态势维续至今,其历史以来精神面貌总离不开先人虔诚,信仰诸府王爷的“水陆兼权”,敢以实践“过州吃州,过府吃府”,乐观开拓脚下土地,乐观对待未来前路。如此开拓进取的精神境界,本当构成王爷信仰的基本共识。
三、王爷信仰的历史印象
从中国历史去追溯闽南王爷信仰的传播,只能发生在陈政、陈元光父子奉诏率领“八十七姓”军士与眷属入闽以后。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地开疆辟土、开枝散叶之前,闽南地区人口稀少,文教建设尚未起步,各姓后人未曾入闽居住,确实难以发展汉族传统的祖先/先贤崇拜,逢年过节祭祀各姓王爷。何况按信仰的说法,360位诸府王爷大多不是闽南人,而是来自长江以北,又是唐初陈元光入闽到五代王潮开闽国所带领的各姓先人;而如“赵府王爷”赵子龙、张巡、许远等一些历史上可考其源的“王爷公”,以及其他各位至今无从就史书细查身份的王爷,其正史上或传说中的生卒年代也都在唐宋以前。闽南的信众对待这些王爷,除了把他们视为历史人物,又是崇功报德、慎终追远,显是自认情怀传承自历代入闽先人。而“正统”的“中原入闽”说法往往是接着王爷信仰当中相关王爷来历,叙述闽南王爷信仰源自河洛地区南下福建先辈,其后裔长期演变出后来的闽南人,闽南文化还是继承着入闽祖辈从中原延续到当地的祖先/先贤崇拜,如此代代传承,或者亦是闽南宗族村落常见供奉同姓王爷,并尊称为“祖佛”的渊源。
这里头的尴尬就在许多王爷固然被信众供奉为开发南洋地方的集体祖神,甚至由中国宗族村落播迁南洋各国宗祠,可是难以在各种历史文献找到王爷们生平事迹。从这个角度,也许可勇敢下结论,认为某些王爷本不存在,或原型是瘟神或其他鬼神。可是从较保守角度,还得关注每位先人不可能都在正史有传,有些人物可能在野史、方志、家乘不乏记载,却因为这样或那样原因导致正史无名。而有些人物即使在野史、方志、家乘有记载,遇上中华文化屡遭天灾人祸,也可能遭受文献散佚之憾。这其中最典型例子包括开漳圣王陈元光,宋代漳浦县令吕玷寿《谒将军祠》边提及“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因此,某些王爷生平事迹固然只见于宗族村落,查诸其他史书无法对证,或者只是各地历经香火演变的庙方辗转记述,或居然只剩下宫庙香火供奉其名其像,建议后人还得谨慎处理,未必要骤下历史真伪结论。或应考虑,本无原型人物,为何香火流传?又或应考虑,有关英烈叙事,是否有幸依托先人保留残缺记忆,甚至后人基于崇德报功为往事添花加叶,方能在闽南留传,演变成某地某府王爷传说。
而信众立场,则不论整体历史或细节真伪,其心目的王爷都是有故事,有香火,有祭祀,有仪式,有扶乩/乩童等活动去“证实”,由此构成其信仰。这其实是借助信仰神圣在历史上存在,证实信众群体到个人存在当地合情合理。
正因为人们相信诸府王爷生为英、死为神,视王爷为自己先辈,善信更是从自己所经过去水陆平安,信仰冥冥中有神圣一路保障顺利。各地送王船活动,因此不只是祈求王爷显灵,替自己驱赶妖魔鬼怪或送走瘟神,而且是一种演练;人们参与社会大众共同集体演练,从中一再建构自身与王爷关系、王爷与社会关系、自身与社会关系。人们以如此演练,周而复始一起筹备、练习、完成送王船,证明王爷神圣与自己同在,继续是所在社会的神圣保障,也控制着整个地区水陆平安。当信仰群体在送王船过程聚合了许多源自自己原乡的文化元素,使得“我的”认知集合体现于活动,他们对待脚下土地的认知也在感觉中转化,无殊于原乡。
若论南洋各地王爷信仰,也许太多人忽略,19世纪50年代的南洋华人社会,沙捞越古晋市曾是华人最频密举行全市“送王船”的海港城市。此地每十年举行一次全市送王船活动,一直到1928年最后一次。以其十年为一周期,时间相隔短而经验频密,足以让市民每十年感觉到神圣时段到来,与日常不同;如此也能让参与者抱着虔诚,全身心融入整个信仰活动集合的各种传统文化元素,受其潜移默化,凝聚人心,陶冶人格。
据古晋本土的记载,当时活动是由统称“福建帮”的闽南人发起,期间福州人、诏安人与兴化人也热烈回应。大众往往要花两个月筹备与练习,组织长达一英里游行队伍。除了乩童化身神明参与游行队伍,主要有负责念“采莲”诗谣的儿童,敲锣打鼓的青少年,抬着神像小椅轿子出行的轿手,以及负责拖拉“帆船”的大队;此外又有送王船数百面旗帜的旗手,各种乐队,花车上妆艺活动的少女,以及数百个化装成各种奇形怪状动物形态的人。市区中心各处还有好些戏台,表演着各种舞剧或传统戏剧。而游行队伍经过每家神庙或转过一间店,手执圣旗的人都会将圣旗摇转两下,表示把盘旋空中的魔鬼驱赶入帆船,等午夜到达目的地,就从水路送它们出境。
记录也说,当时古晋有许多“王爷”神像,出游时各有四个人挑小轿担,一路负责收罗妖魔鬼怪,押送船中。古晋初期做法,原是把船放海流,后来则把船拖到浮罗岸与打铁街交界的小河,连同祭品烧掉,免得帆船被海浪推向邻近地区,魔怪得以离船上岸,肆虐当地。现在这些神像流落四方,庙宇或私人供奉,已难寻觅。
可是,古晋市闽人这种全体共同演练,毕竟是借助个体无助,人人冀望共生共存,根据“瘟难—信仰—平安”三段式思考,从而以“难题—方案—圆满”解释必要,成全众人齐心出钱出力的合理。组织一次又一次游行,成本却是相当昂贵。20世纪初,一家四五口丰富一餐也不到五分钱。只是当时霍乱传染常在古晋爆发,市民缺乏医药也缺乏清洁自来水,大众反复惊恐不安,往往会激发信仰者求神做主,1898年那场“送王船”花掉二万元,到1928年成本则抬高到三万元。等到城市建设和卫生设施较齐备,“瘟疫”不再频频出现,社会稳定下来,地方华人群体就不一定再需要以成本昂贵的演练凝聚彼此认同。尤其1930年代末,中华民族经历各种政治灾难已到高潮,整个社会不论对内对外,日渐醒觉殖民压迫,从自觉踊跃办学兴教自救,再到集中力量抗日救华,珍惜有限人力动员与经济资源,重点就不再是举市“送王船”。
在槟城,同样情况发生于1919年霍乱症横行之际。正当死亡者众多,殖民政府束手无策,日落洞青龙宫保生大帝降乩指示对抗瘟疫,建议大众以荸荠泡水服用,同时又召集孙、佘、池三府王爷一道巡境。对比古晋与槟城上世纪初王爷应对瘟疫出巡,槟城也如古晋,活动形成地方上闽人群体的社会动员,借助神灵保佑大众反抗瘟疫,无形在确认游行范围属于闽人日常区域,也集体展现闽人文化元素。其细节在于古晋活动以漳泉人为主,由闽中、闽西先民附和,负责造王船的兴化人在工作的二个月期间必须吃斋,充分展现出齐心合力。槟城活动只是以槟屿东部地区漳泉人公庙的名义,发动沿海主祀三位王爷的南安人聚落。不过,在瘟疫停止了以后,同类活动逐渐稀少。除波罗池滑辛柯蔡宗祠可见到王爷身边有木构的帆船模型,昔日湾岛水美宫留下民初某次放王船存照,现在当地大部份王爷宫庙都不见定期烧送王船。可见,“瘟难—信仰—平安”的三段式思考,一旦缺少压力引发群众集体动机,就很难从“难题—方案—圆满”解释确实必要。那时马来亚北部许多庙宇和宗祠也正和南洋各地一致,都把有限群体资源集中在办学、救国捐,更从抵抗日货到筹赈抗日。
既然20世纪上半叶结束以前,南洋各地区王爷信仰不见得都是为着对抗瘟疫“放王船”,重点也不一定要每隔一段时间放王船,而且有些宗祠/宫庙活动长久未涉“王船”或者“游街”,那么,认识当地王爷信仰,焦点可能更应回归庙宇或宗祠日常常态,重视大众如何在日常生活认识与沟通崇拜对象。
正如上述孙、佘、池三王爷。虽说三位王爷在1919年瘟疫时期被信徒抬出巡境,可是当瘟疫不再泛滥,神明主要任务毕竟是待在村子,保护“子孙”好好过活。由此,南洋民间王爷印象,首先就在信众藉由王爷生平事迹推崇其价值观,塑造诸府王爷各自文武造型;其次在信众认可其崇拜之王爷,认为王爷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行谊可作地方大众为人处世的模范。又或者,神庙或信仰组织也会通过各种信仰实践,包括灵乩或扶鸾,传达诸府王爷对人间教诲,更具体表述王爷关心信众从物质到心灵安身立命。
如此,诸府王爷的日常状态及其回应大众日常生活的职能,显然更多表现为信众生活秩序的护佑者。如湾岛水美宫,1952年曾在马来亚北部大量派发传单呼吁大众戒赌,指出沉迷赌博者是“日日求神,以致破坏神的安宁”,朱池李三府责问赌徒“神若不得安宁,怎能保佑人民”。而槟榔屿西日落洞香蕉芭灵应堂,延续三王府昔日香火,1989年曾把庙内辑录的“孙佘池千岁济世经验所集”乩文印成小册子分送善信,表露三府王爷的凡尘使命是解说儒家伦理、道教数术。而日落洞巡按庙位于邻近村子,2016年出版宫庙主席尤源隆撰写庙史彩色画册封面内页首要介绍三府王爷事迹,第一页则翻印17世纪闽南人海洋地图,标明王爷香火由南中国海绕入马六甲海峡航线。该庙有系统传播教义,鼓励信徒学经解经,2016年又联合马来西亚道教学院,邀请台湾史贻辉道长与青玄宗坛陈文洲道长弟子李建德,到马来西亚校点出版《代天巡狩说治心消劫妙经》,并开坛主持讲授该经,在南洋王爷庙之间首开以道教仪式主办传经盛典。
由此或应重视,南洋信众信仰虔诚,固然建立在相信王爷神圣与灵验,却不一定是凭着距离个体经验遥远的烧放王船记忆。信众的王爷印象,其实建构自他们认识的王爷历史/传说/神话,结合所在地的王爷信仰事迹。如斯历史印象,首先重视诸府王爷各有姓氏,同姓王爷各有来历,把每位王爷尊神各自生平表达在性格、行谊与教诲。其次又实现在信仰“祖佛”至今和大众一起“生活”,不离不弃,保佑信众所在具体地区历史发展,也随时聆听个人的苦难。
四、王爷信仰的在地实践
诸府王爷事迹在闽南本来就笼罩着汉文化色彩。以王爷具有汉化朝廷命官身份特征,还有王爷生平在实践儒学内涵,成就其在闽南无碍传播的基础。反过来,这当然也说明闽南王爷信仰确立,只能在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甚至是王审知开闽国,汉文化逐渐丰富地方生活资源而成为主流。就闽南人下南洋过程,王爷信仰承载着充满闽南地方色彩的当地汉文化演变,又是通过“神圣”作出自述,表达所认可的文化元素与价值观处在放诸四海皆准的状态;当王爷香火和相应的活动出现南洋各地,等如化约闽南古今往来历史文化符号。在南洋闽人乃至所有华人而言,他们心目的王爷历史印象就是信仰的基础,安身立命的凭据。各地的闽南王爷香火即是闽南文化的载体,由家家户户轮番祀奉王爷香火一直到建庙扩展,即是落地生根到开枝散叶。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关注在地演变的必然性。王爷信仰文化不论过台海、下南洋,不论在闽台或南洋各国都会走入各地历史文化脉络,生化出各种演变,在在说明王爷信仰在各地传播经历着由原乡而当地的进程,其跨国跨海传播既然经已表现出国际信仰跨越地域的态势,必然就在具体时空的地方人群呈现出在地演变特征。而考察王爷信仰在地演变,最具体莫如观察那些联系着历史上村镇创建过程的神庙,其具体“境”内的庙宇风格、神灵关系、仪式形式,往往就表现神明信仰文化的在地演变事例。王爷信仰是如此,其他神灵也如此。
就神道设教乃至神庙活动而言,“合境平安”之所谓 “境”,是庙宇影响所及的地区,一般即包括信众较集中聚居的范围,信众的集体意识也是寄望神明保护他们在周遭土地日常活动“合境平安”。“境”不一定拥有固定而明显地理边界,而且其边界在时间中演变,会随着信众分布范围不断扩大、缩小或改变。神明游行在本身庙宇势力或信仰认同影响所及范围,就叫“巡境”;祖庙香火或者神像到其他地方其分香,也一样叫做“巡境”。反之,神明一路出游非属本“境”的友好地区,和友好地区庙宇互相致意,则叫“绕境”。某种意义,神明的“境”也即是其信仰群体认同与认识自身环境的范围。人们通过神明“巡境”或“绕境”表达出对于本“境”的认知,把地区上的庙宇视为当地民众共同意识的载体,也承认属于他者的外“境”,可说通过神圣崇拜强化民众共同体,由此建构结合着地理范围的自我环境认知与版图概念。这样的情况,通用于解释各路神灵,也适合解说南洋各地百年王爷老庙信仰。
马来西亚华人由于未曾经历严峻的全盘同化政策,各村镇华人文化相对保持完整,这些地方的王爷宫庙也因此维持较完全的闽南宫庙文化色彩,但王爷庙的神灵布局也如其他神庙,会把他们对地方族群关系的认知,表态在如何认识土地神与于本庙诸主神的从属关系。所以,庙外附设小祠供奉本境土地,就不是南方村落传统土地公婆的造型,而是引进和包容原住民盛行伊斯兰教法以前的土地守护灵信仰,尊称为“拿督公”。不论诸府王爷日常祭祀、神诞节庆,抑或是需要请神指示,信众除祈求主神灵应,拿督公也成为大众希冀香火感应的兼及对象。华人先辈有缘开荒地区,以原住民尊称长辈“拿督”的敬意尊称原住先灵,以立祠表达互相承认,也是表述着拿督公先灵属意保佑先辈拥有脚下土地。
另外,南洋各地神庙都如家居,主神神龛脚下有“地主公”牌位。马来西亚和印尼、泰国一样,是作“五方五土龙神,唐番地主财神”,越南则如香港,将后句改称“前后地主财神”。南洋华人不论“唐番地主”皆拜,证明先辈更主动注意大家长期出入“唐”山与“番”地的处境,而“唐番地主”皆被视为“财神”,也证实先民主动意识本土环境变迁,积极落地生根;只是“唐番地主”“前后地主”两种截然不同提法足以反映那时来往两地群体的心态,对两处土地原来归属有不同认识。
若回首明末遗民自17世纪经营越南会安地区,对照着缅甸仰光华人社会自清代成形而在二战以后屡经变化,两地王爷信仰现有的在地化情况,显是两国历史变迁不同,表达为各自地方华人信仰的写照。前者可说明,在地发展若离开原乡越来越远,长期缺乏交往,而大众努力保存旧有记忆,实践的变迁足以演变出在地版本的说法,甚至也可能在地发展出在当地成神的新“王爷”。而后者例子则表述着,当信仰文化处在族群关系风口,交融着政策变迁压力,可能会互相结合当地其他信仰或文化活动,维续本身在大环境氛围的可现身空间。
越南福建会馆天后宫的案例,当地王爷信仰可说目前有史可据的南洋最早闽南王爷香火,17世纪中叶,明朝遗民求助越南王朝,王爷信仰可能是打那时跟着先辈垦荒和开发商贸市镇,从海路抵达当地。1650年左右,当地已经有全体南明遗民形成的 “明香社”,康熙三十八年(1699)刊行《海外纪事》曾记载:“盖会安各国客货码头,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仍先朝服饰”。可是正是有过如此历史背景,等到19世纪不同群体在福建会馆合祀诸府王爷,当地老百姓早已把神灵传说附合在先辈祀奉王爷香火“反清复明”的老故事,在会馆正门后的右侧墙壁绘画六位骑马将军,都在战场上手拿武器冲杀清军。依照这幅画面,无疑当地保存过当初集体记忆,又很不完整,于是群众便把各地群体供奉的王爷概括为一,把先辈视为集体祖先的“六姓”王爷象征所有明代撤入越南的闽南先辈义士。福建人天后宫以外,后来留越明朝遗民相互通婚、与当地民族通婚,形成延续反清复明理念的“明乡人”群体,在当地作为结社祖堂的明香萃先堂,也配祀带领反清大众抵达会安的魏、庄、吴、邵、许、伍等六姓先人,也称“六姓王爷”。这就是记忆的再生产,由于当初到达义民很大部份人是福建会馆先辈,同时属于明香萃先堂,他们因此影响着“本境”明乡人社会,让大家延续“六姓王爷”概念,把配祀萃先堂的六位先人也说成王爷。
又应注意,阮玉诗撰写的《越南福建人王爷信仰》,他除了提到当地“王爷”已是转化为全体先民的代号,也提到在越南南部地区,即使天地会曾经在这些传播“反清复明”福建人未见王爷香火和类似王爷传说;可见,会安(Hoi An)的王爷信仰是构筑在“本境”福建人原来历史脉络,离开会安,其历史到传说就不一定和反清复明相干涉。
再若从仰光是缅甸首府去说,当地华人在此地从事信仰活动,比起其他地方更需要谨慎,注意和谐影响。杜温《“朱府王爷”下南洋再到仰光》提到,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当地华人为着适应环境,使用中缅双语文去巧妙运用缅甸寺庙佛像、佛经等宗教符码,把朱府王爷神灵与北斗九皇信仰包装,结合着缅甸盛行民间水神“信乌巴谷”信仰,让祭祀乃至巡游可以公开举行。如此,有了宣称诸神结义又结盟的名堂,大众便能在仰光江聚合,用华人方式祭拜民间水神信乌巴谷,兼且拜祭朱府王爷与九皇大帝,并为神灵举行“流放香炉”送神仪式,以取代送王船等旧俗。当地华人节庆期间主办缅甸民间文艺展演,尚且由闽南建德育德社等文艺社团展示华人文化,无疑是以神缘织网,支撑着中缅文化和谐,降低我群与他群的区别。如此,以华缅诸神结义的王爷节日,在华族内部,是以活动推动行为规范,以文化展演内化族群认知,推动人群聚集与语文交流,实质便能维持族群整体互相联谊与认同,并以宗教仪式纽带吸引“乐善好施”商业人士举办各种布施,强化华人社会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很多时候,在地化的演变融入当地其他族群的元素,也未必是被逼,而是出于入乡随俗,或希望招引他人善意,接受/交流乃至参加。如泰国当地,当地1992年落成“暹罗代天宫”,历史不同于南洋地区二战前的诸府王爷宫庙,乃是台湾南鲲鯓代天府五府千岁现代分灵,作为南鲲鯓代天府香火流传泰国的开基庙,并且分香出董里府的泰南代天宫。然而,此中就像马来西亚、印尼诸府王爷统领各自“本境”地主尊神,也是入乡随俗,按照泰国传统地主崇拜,金炉前设有一座白色塔。其神灵活动也反映着天地间的人事人情——除了在泰国,各地其他王爷就不一定替泰皇生日祝寿,更不可能以此为由在曼谷出巡游行。
或者也应把“在地化”视为本境居民的记忆与沟通方式。随着时光前进卷动着事物的演变/流失,个人、集体通过信仰文化,足以把一切可言语、无从言语的知识与体验重构排列,展现为当前想要告诉自己和他人的具体情境事象。
五、余 说
简言之,诸府王爷信仰文化到了任何地方,首先都表现为历史上的王爷信仰落实在当地的国际传播,其“国际性”“历史感”与“在地化”内涵是同时俱现。由此也就使得各地王爷信仰文化的实践层面多姿多彩。无可否认,王爷信仰的在地演变不见得会影响大众继续认识到眼前还是“王爷”信仰。但又不得不承认,往往是在地增添了当地文化元素才有益维持王爷信仰在各地的生命力,成就人们在当地的王爷历史感受,不是陌生而遥远的闽南印象,而是紧密连接闽南渊源与在地乡野记忆的亲切感觉。
进一步解释,《礼记·王制》对于礼仪为何非得通俗不可,原有具体论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左传·隐公十一年》谈到如何才是落实“礼”的内涵,更有说明:“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由此而言,在华人世界,信仰不见得定必要和各地官方观念对立,信仰文化要做到既能国际性又是本土化,成全教化而非图存形式,即真正做到摄礼归义、摄义归仁,还得落实在地方上“度德而处,量力而行,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完成或谓“本土化”或谓“民俗”的过程,确保其内涵符合民情脉络,深入人心。如是,全球各地华人庙宇在历史、血缘、语言等等方面可能共通的传承渊源,而所有国家地区的共同经验是:一旦中华神明香火落实在具体地方环境,其演变必然是相对于落实在其他国境而成就国际化,而又由在地民众融入地方资源维护信仰、历史、文化等多重认同,构建出地方的本土缘分。神明信仰因此就结合到当地生活经验,庙宇沿革也会经过参与当地历史,成为地方文化景观。
沿着相同思路,不论探讨诸府王爷信仰的历史与文化渊源,或者是探讨王爷信仰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共同精神面貌,讨论闽南王爷信仰的国际性与历史感,问题当不在它散播多少个国家,而在于它到达当地,是否能继续内涵的儒道传统观念,同时还能保持原来就具备的“过州吃州,过府吃府”记忆,而非秉持着狭隘地方观念。否则,跨海跨国的诸府王爷信仰版图,一旦是脱节于原来信仰价值观,宫庙主持者再多庙会新花样,若果无从较完整去反映当地王爷信仰自历代以来走向国际、落地生根、在地发展,也是徒具其形,不够完美。毕竟,一旦无从继承过去以来整体社会的王爷历史印象,反而就可能引导着未来者的视角偏差,教人有所遗憾。
注释:
[1](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十六页,载《钦定四库全书(史部)》。
[2]荷兰海牙国立档案馆《热兰遮城日志》,其中“1655年2月27日至11月9日”档,记载着3月9日在台湾得到郑成功二十四艘贸易船出发的消息,是有七艘开到巴达维亚,两艘去东京,十艘去暹罗,一艘去马尼拉,还有一艘到安南的广南。Copie-daghregister des Casteels Zeelandiaop Tayean sedert 27 Febr.Tot 9 Nov.1655.[Kol.Archief.No1103]fol。571v.
[3]连横:《台湾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21~28 页。
[4]王琛发:《17-19世纪南海华人社会与南洋的开拓——华人南洋开拓史另类视角的解读》,《福州大学学报》2016第4期。
[5][42]王琛发:《台湾与南洋华人的民间神道信仰:同源、在地分流与互动》,《闽台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
[6]马来西亚吉兰丹《镇府宫杨府二王爷庙史》,庙方根据地方口述历史记录整理的手抄藏件。
[7]《巴西吗镇府宫发起人之一林朝板手抄咒簿》,1962年。
[8][38]蒋为文:《越南会安古城当代明香人、华人及越南人之互动关系与文化接触》,《亚太研究论坛》2015年第61期。
[9]《澳报举行玉庵建庙一百周年庆典》,缅甸《金凤凰报》,2013年9月26日。
[10]王琛发:《“代天巡狩”下南洋——马六甲与槟榔屿闽南先民印象中的王爷信仰》,《宗教人类学》第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291~294 页。
[11]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50~151页。
[12][13]《巴西吗镇府宫黄天兴手抄咒簿》,1970年。这些咒语,是1950年代以前庙中继续流传咒语记录,现由马来西亚吉兰丹巴西吗镇府宫庙方收藏。同样的咒语在吉兰丹当地至今还有流传使用着。
[14]王琛发:《闽南王爷信仰流传马来西亚的历史意义》,《闽台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
[15]《九皇大帝盛典》,缅甸《金凤凰报》,2015年12月4日。
[16]《缅华网——旅缅叶氏南阳堂简史》,http://www.mhwmm.com/ch/NewsView.asp?ID=4887,查阅时间:2017年9月10日。
[17]王重阳:《泰国邻廊郡侯许泗漳开拓史》,《南洋文摘》,第6卷第9期(总第69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5年9月20日,第47页。
[18]许经立:《印尼峇眼亚比——海外的同安城》,厦门同安区《同声报》,2014年2月21日。
[19]《廖省峇眼亚比永福宫前举行一年一度规模浩大的传统文化节》,印尼棉兰《好报》,2014年6月15日。
[20]《汇感百科——板庭梧福护宫》,http://www.hgzz.net/baike/97855.html,查阅时间:2017年9月10日。
[21]《板庭梧福护宫举行重建落成庆典缅甸》,缅甸《金凤凰报》。
[22][23][24][25][27]耶素:《三十六年前古晋祭神大游行纪实》,《南洋文摘》第5卷第5期(总第53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4年5月1日,第38页,第38~39页,第38页,第38页,第38页。
[26]大路:《槟城日落洞这个地方》,《南洋文摘》第5卷第7期(总第55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4年7月1日,第45页。
[28][29]金榜居士:《神发怒了》,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52年5月19日,“商余”版。
[30]孙、佘、池王爷乩文:《道教点滴》,槟城:西日落洞香蕉芭灵应堂,1989年,第1~16页。
[31][32]尤源隆撰文:《荫坛巡按庙三王府孙佘池大人》,槟城:巡按庙,2016年,封面底,第1页。
[33]《槟霹雳冷孙佘池三王府巡按庙720开坛传经仪式》,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16年7月5日。
[34]胡兆茵:《先辈感恩拜拿督公,后代求财初心改》,马来西亚槟城《光华日报》,2016年7月21日。
[35]王琛发:《再演变与再诠释:从周代中霤信仰到华南土地龙神在马来西亚的变迁》,《世界宗教学刊》21期,台湾: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2013年6月,第144页。
[36](清)大汕和尚:《海外纪事》,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80 页。
[37][39](越)阮玉诗:《越南福建人王爷信仰》,载于王琛发:《灵显与传播:闽台与南洋的王爷信仰》,吉隆坡:马来西亚道教学院、槟城巡按庙孙佘池三王府,2016年,第156~157页,第157页。
[40](缅)杜温:《“朱府王爷”下南洋再到仰光》,载于王琛发:《灵显与传播:闽台与南洋的王爷信仰》,吉隆坡:马来西亚道教学院、槟城巡按庙孙佘池三王府,2016年,第131~139页。
[41]谢玲玉:《向泰皇祝寿代天府王爷起程将出巡曼谷市区为民间信仰外交添一笔》,台湾《联合报》,2000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