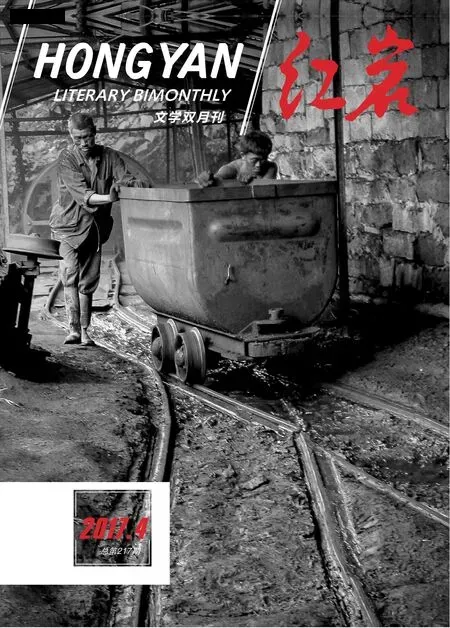致寂静
许俊文
致寂静
许俊文
许俊文,安徽定远县豆村人,种过地,教过书、当过兵,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出版有散文集《留在生命里的细节》、《俯向大地的身影》和《回到草中间》。
看大自然的花草树木如何在寂静中生长;看日月星辰如何在寂静中移动……我们需要寂静,以触碰灵魂。
——特蕾莎
一
想象那个叫特雷莎的修女,在书写这段文字时,想必是在宁静的早晨,或是安谧的黄昏,要么是在阒寂的午夜。此时此刻的修道院,想必空寂无人,管风琴沉默不语,唱诗班的声音已经遁去,那些祈祷的灵魂分散在各处,像一棵棵安静的植物潜生暗长……
那个叫特雷莎的修女,想必她已不再年轻,甚或生命已进入了深秋,像一支风中残烛,摇曳着清幽的光。如此看来,她定是经历了许多尘事,曾在内心起起落落,纷纷扰扰,喧哗与骚动都在所难免。现在的她,一切都归于平静了,平静得犹如寂静、庄严的建筑,轻轻合上纸张泛黄的《圣经》,独享着属于自己生命的那份宁馨。那一行行从笔尖缓缓流下的文字,带着女主人丝丝的体温,表达对自然与上苍的感恩之情。
我却没有特雷莎修女的那份幸运,至今还在尘嚣中扑腾与挣扎。譬如写作这篇小文时,在我寄居的楼下,几家装潢店铺正在切割金属材料,切割机发出的尖厉声,喷吐火焰的电焊枪与焊条合谋制造的刺刺声,以及金属的碰撞和断裂声,像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破窗而入,不管不顾地在我的耳膜上戳出一个个不见血的孔洞;而我能够做的,除了忍耐,还是忍耐。
我知道,寂静就像那逝去的青春,它已经回不来了。
二
对寂静的重估与追认,是以我生命的部分死亡为代价才得以实现的。其诱因则源于听觉的一次背叛。
时间回溯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个夏天。
在一场盛大的雷雨过后,我从人声嘈杂的购物商场内走出来,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万箭穿耳,头颅欲裂。我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中,用被子将头严严实实地蒙起来,可是那些讨厌的家伙却像一群寻衅滋事又不肯善罢甘休的流氓恶棍,一路穷追猛打跟踪而至,它们的武器便是无形的噪音:隔壁人家的收录机声,电视声,马路上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楼下食堂里炒菜的铲子与铁锅的摩擦声,关门和开门声,洗锅刷碗声,电台滴滴哒哒的发报声,鞭炮声,广场舞的喧闹声,施工场地上机器空空的打桩声,还有屋后学校篮球场上裁判的哨子声与喊叫声……这些平时听起来已经习以为常的声音,此刻竟然发生哗变,且被数倍的放大,它们在我猝不及防时,像一颗颗呼啸而至的子弹,硬生生地往我的脑袋里钻,我不得不用棉球将耳孔塞起来,然而还是于事无补。于是,我开始眩晕、恶心、呕吐。先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吐,接着大口大口地吐。也许是我的身体在做本能的抵抗,它要把那些杂音从身躯里清除出去,还生命一个安静。
或许是我的身体内部潜伏着叛徒,或许是各种声音过于强悍,我听觉的防御体系形同虚设,不堪一击,只能听任着它们在我的身体里横冲直撞,恣意妄为,而我却束手无策。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抬上担架的,只觉得大地在旋转,天空是不是旋转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敢睁开眼睛。要死的救护车一路呜哇、呜哇地尖叫着,每一声都像切割刀在耳膜上划过,我双手紧紧抱着欲裂的头颅,并将两根手指插在耳孔里,然而于事无补。
看来我是被狗日的噪音绑架了。
此后几个月里,医生一次又一次修改着诊断结果,颈椎病、美尼尔综合征、神经官能症,然而,一瓶瓶五颜六色的液体输入体内,可就是赶不走那些负隅顽抗的音魔,它们在我的痛苦中狞笑,在我的挣扎里狂欢。在那些难捱的日子里,我像一个稻草人被从一座医院搬到另一座医院。尽管我像一个惶恐不安的逃犯,不停地变换着藏匿的地点,但声音却如影随形,始终无法将它们甩掉。
熬过漫长的夏和同样漫长的秋,我的生命也随着季节一起进入了寒冬。医生出于善意,把我安顿在远离地面的十三层病房里,可是暖气管发出的嗞啦声,锅炉燃烧的嗡嗡声,被风从楼下抬升的人语喧哗声,都无一遗漏地往我的耳朵里灌。不瞒你说,那时的我,真的渴望安静的天国。
上苍也许出于眷顾和怜悯,在一个深夜送来了一场大雪。久违的雪啊!那雪飘落得虽悄无声息,但它把世界上所有的杂音都过滤掉了。此时躺在病榻上的我,聆听着窗外雪花窸窸窣窣地浅唱低吟,犹如神曲般沁入心脾,数月来被各种浊音浮声搅乱的听觉,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清静。那个夜晚,也是数月来我得以平静睡眠的一个良宵。
我纳闷,为什么同样是声音,落雪的声音听起来却如此的温柔和销魂呢?还有鸟鸣声。一天傍晚,一只麻脊长尾小鸟落在窗台上,它的叫声并不动听,吱啯,吱啯,吱啯啯,然而在我听来却不亚于天籁。我多么渴望它能够留下来陪伴着我,无奈却挽留不住它。
后来,医生第四次借助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和手术器械,将藏匿于我身体里“叛徒”缉拿归案,那原来是一颗体积只有蚕豆般大小的听神经肿瘤。其实,那颗肿瘤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它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我,每月每日每时每分每秒都要受到各种声音的蛊惑、刺激和怂恿,它在自己受到迫害的同时,却充当着声音的共谋。手术后,当我从深度的麻醉中醒来,医生询问我接触过什么高分贝声音,我只得如实相告,曾当过高射机枪手。
当然,这不是唯一。
三
我的听觉史的开篇曾经写满了鸟声、星辉、月色、风语、云姿以及大自然所赋予的一切,(鄙人以为包括听觉在内,人体的各个部位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比如胃,它会记录自己主人的饮食习惯,一生消耗掉多少粮食;我们的双脚则像汽车的计程器,它会知道你走了多少路程;嗅觉说不准会将我们经历的各种气味,分门别类地建档立案保存起来。)就像敏感的特雷莎修女在寂静的修道院里,体味大自然赐予的那份高贵的奢侈。
那时候,特雷莎修女的寂静,在我的故乡皖东豆村就像地里的庄稼和荒原上的野草,一眼望不到边,任你怎么割也割不尽,根本就用不着刻意去寻找。一丛生长在路边的野蔷薇,花开花落全是它自己的事,多少年后还是那个老样子;栖息在豆青河畔的那只孤独的游隼,每天初阳出现时便会从土崖上准时起飞,先绕着村庄兜一圈,撒下几粒叫声,然后向远方缓缓飞去;还有我家门前那棵黄楝树上的鸟窝,冬天自然掉落后,春天不愁鸟雀不来筑巢……世间的一切都暗中遵循着某种秩序,该生的生,该长的长,该死去的死去,一切就这么简单。是的,那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过于复杂的事情,季节轮回,河水一眼见底,天空透明,星星一颗就是一颗,雪花守约,节令一到不请自来,夏天热到极顶时,自会有一场酣畅淋漓的风雨……人也跟着简单,想法很少,欲望有限,人们从大自然中拿取讲究分寸;用得也细,一根草绳先是用来拴牛,断了以后再用它捆扎柴草,最后和柴草一起塞进土灶煮饭。就我所见,人们从不轻易地砍伐一棵树,弄脏一条河,毁坏一座山。更不会去琢磨头顶三尺以上的事。那里有着他们敬畏的神明。你可以嘲讽这是落后,然而,当“生态”一词被反复提起时,“落后”就该另当别论了。现在我会想,那些失去的东西要是丢落在某个地方,我们宁可多走一些路,还可把它们找回来,但若是被彻底打碎了,你找回的只能是悔恨和叹息了。
譬如特雷莎的寂静。
那时候我不知道寂静是什么,就像襁褓中的婴儿不明白母爱是什么一样。白天大人们都出工去了,四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只剩下祖母和我。祖母仿佛有着永远也做不完的事,她那佝偻的身影一会儿出现在菜园里,一会儿又移至井台边。只有我是个闲人,要么没头没脑地坐在门槛上,看村前水田里成群的白鹭磕头磕脑地觅食,苍鹰在瓷蓝的天上不厌其烦地画着圈圈。白鹭有时候会将一只腿提起来,久久地立在那儿看我。于是,我捡起一颗小石子扔过去,白鹭似乎并不介意,它歪着脑袋瞅瞅,更多的时候连瞅都不瞅,还是那副神闲气定的样子。这时,我会唆使我家的那只大黄狗,去把那群白鹭撵走,可黄狗压根儿就不听我的,只管趴在地上闭目养神。我真的替那只养尊处优的黄狗担心,村庄的过于寂静,会不会使它失去吠叫的本能。当然,黄狗偶尔也会发出叫声,那多半是因为来了陌生的客人,或者村庄里出现了不速之客——野兽和邻村的狗。这时的我就像黄狗一样显得特别的兴奋,这不仅因为来了客人祖母会做出一顿好茶饭,更重要的是寂静的村庄总算有了一点儿声响。
被寂静包围的村庄,并非是黯哑的世界,其实到处都充斥着各种美妙的声音,只是我们充耳不闻,习焉不觉罢了。譬如风,就是一个声音的制造者与传播者。风虽然自己不说话,但它每经过一个地方,那些沉默的东西在它的蛊惑和煽动下,一个个心旌摇动而不能自持,争先恐后地诉说着自己寂寞的心声。大风来临时,满世界都在狂舞、呼喊,树枝折断声,瓦片破碎声,波涛拍岸声,房椽瞿瞿声,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就像是由多种乐器合奏出的交响曲,二胡的舒缓悠长,琵琶的嘈嘈切切,萨克斯的低沉忧伤,小号的高亢嘹亮,钢琴的热烈奔放……听起来反而觉得幽寂无比。若是微风,庄稼和草木们会交头接耳,彼此窃窃私语,仿佛在传递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时候,我的听力特棒,即便是一片恋枝的黄叶、一根经霜仍不肯倒伏的草茎,它们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声音,就像纤指轻轻拨动着丝弦发出的妙音,如泣如诉。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过日本文学,但是,凭着生命的本能,我也能够多多少少体悟到“哀物”的隐情。
在有声世界里,雷声贵为众音之王,它有着开凿鸿蒙、廓清宇宙之功。一记春雷,就将赖着不走的残冬收拾殆尽;又一记夏雷,溽热的空气被炸得粉碎。记得一天晚上我在瓜棚下睡觉,朦胧中,我听到一阵阵蟋蟀的唧哩声,就像多重奏的美妙大合唱,空气里带着潮湿的味道。显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暴雨落下之前,雷声先在田野上响起,轰隆隆地自远方翻滚而来,回响不绝:磅礴、深沉、原始,大地和灵魂都为之震撼。雷雨过后,田野一片寂静,我的耳根也像被擦洗过一般清爽。后来我混迹城市,所听到的雷声仿佛被阉割似的,已没有“如雷贯耳”的气势与力道了。
四
在我的印象里,早年的豆村是一块安静的乐土,它使我学会平静的聆听。夜半花开的声音,月光翻窗入室的声音,竹笋破土的声音,我仿佛都能感觉到。有时耳朵好像都是多余的。在一次次无言的聆听中,我窥见了大自然的一些隐秘。譬如来自秋夜长空的一声雁叫,我能从它的叫声里分辨出是孤雁还是雁阵。曾有一些读者问我,一颗豆粒大的村子,你何以能够不断地发现新东西,我回答他们:因为我曾经拥有寂静。如果再加上一句,我会说:唯有平静的心,才能感知丰富的世界。
时隔几十年后,豆村的寂静就像一杯夏日午后的清茶,让我在日益泛化的尘嚣中,体味到它的美好。
譬如,豆青山上的那片野栗林,就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对这片林子的来历,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说不清是那代人留下的,我估计很有可能来自鸟雀,因为在离豆村二十里外的黄坞山中,就有着大片的天然野栗树,一些鸟雀在豆村与黄坞山之间来回穿梭。我排除人为可能,是因为人类具有一种天生的功利性,做什么,不做什么,其背后都有着精明的计较与选择,而鸟雀显然是做不到的。在豆村,人们植树大致出于两种目的,一是果树,桃、李、杏、枣、石榴之类,它们可以带来口福之快;二是椿、楝、槐、朴、松、榆等,以满足用材需要,像柳这种树就很少见到,即使有那么零星的几棵,也是自生自长。显然,野栗树自然不在这两类树木之列。但鸟雀、野兔、山鸡、昆虫们喜爱。我也喜爱。没事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溜进野栗林中,瞅瞅哪棵树上垒有鸟窝,哪棵树干上雨后生了菌子,或是在林间的草丛里寻找金龟子、地牛、蚱蜢,说不准会幸遇一窝山鸡蛋。我喜爱这片林子,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祖母找不着我,她老是像风婆子似的絮絮叨叨,我烦。躲进野栗林里,祖母呼喊的声音就被层层叠叠、密密实实的树叶过滤掉了,耳根清静啊!若是秋天,野栗子成熟了,太阳一晒,树上的刺果球会哔哔啵啵地炸裂开来,一颗颗雪霰似的果实从树上落下来,发出轻微的啪啪声,在地面上乱滚一气,它们好像脱离母亲怀抱的孩子,呼喊着冷呀,冷呀。于是风听见了,急匆匆地从远方赶过来,使劲地摇晃着树冠,摇着晃着,树叶便纷纷落下来,给裸身的栗籽盖上一层厚厚的被褥。此时的我显然是藏不住了,然而并不沮丧,因为寂静的野栗林给了我不一般的快乐。
几年后,疼爱我的祖母走了,家人把她埋葬在豆青山上的那片野栗林中。亲人们哭过了,祭过了,一阵秋风走过来,把黄色的落叶覆盖在祖母低矮的坟茔上。那一刻,我觉得祖母也变成了孩子,她在另一个世界里想必也像野栗籽一样,不会感到寒冷了。我离开豆村后,不论行脚远近,每年总要回去看看祖母,和陪伴她的母亲和妻子,在她们的坟旁坐一坐,吃一支烟,什么话也不说,好让自己漂泊的灵魂静一静。
美国音乐指挥家安德烈•科斯特兰尼兹曾说,完全圆满的寂静,是世上最伟大的声音之一;对我来说,寂静也是声音。我想,作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安德烈•科斯特兰尼兹对音乐演奏中短暂静场的至深体会,肯定来自其对音乐美学的深刻颖悟。作为乡村的孩子,我道不出,却也能够多少感悟到“寂静也是声音”的妙谛。
现在反观过往,寂静似一袭长袍披在豆村的身上,它护佑着那方水土上的一切生灵,使他们得以安静地繁衍生息。其实,寂静也是一笔隐形的巨大财富,它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改变着世界,甚至改变着人性。据我观察,豆村人身上有一个共性:木讷、胆怯、厚道、沉稳、温和,且富有想象力。不是自我吹嘘,这些品质在我的身上也有体现。我曾经鄙弃过它们,觉得它们似一道屏障,阻碍了我融入喧嚣的城市生活。如今我想通了,自己就是豆村的一株水稻,用不着变成城市的一根旗杆。
五
早在一八五五年,西雅图一位酋长为印第安部落土地购买案,在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的信函中说,如果在夜晚听不到三声夜鹰优美的叫声或青蛙在池塘的争吵,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深深地感到羞愧。
除了羞愧,还有苦恼。自我的左耳失聪后, 我更无法适应城市的噪音,白天走在马路上,一辆汽车在我身后使劲地鸣喇叭,我也判断不了发声源来自哪里。有几次,气愤的司机故意用车体蹭我,然后甩下一句恶狠狠的“想找死呀”扬长而去。若是雨天,车轮溅起的污水会把我搞得狼狈不堪。有时参加宴会,一桌子人争相说话,我瞅瞅这个,看看那个,听不清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于是,我开始尽量回避充满声音压力的活动,特别是有着巨大声响的活动;它们只会给我带来刺耳的不和谐音,几乎把我逼疯。
如今,声音污染已成扩大与蔓延之势,在偌大的地球上,哪里还能找到“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戈登•汉普顿、约翰•葛洛斯曼语)”呢?更令人忧虑的是,人们在制造了海量的噪音后,自己也变得内心焦躁、易怒、失眠、恐惧,缺少安全感。时下人们热衷于消费绿色食品,纯净水,近年来又出现买卖清新空气的行当,然而,他们却买不到寂静。
就像无法修补旧爱,即使给我一亿两黄金,我也无法赎买破碎的寂静。
创作谈
我给自己的散文写作设立了一条规矩 :不妨小声说话。
其实散文就是说话,以平朴的语调,把自己想说的,别人又不曾说的,你把它委婉地表达出来即可。
常常,我们习惯于对听众大声说话,高谈阔论,否则,仿佛就没有存在感。我却反其道而行。在进入写作状态时,我会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微弱些,再微弱些。因为,我面对的“听众”是自己敏感的心灵。
跟自己的心灵说话,你只需娓娓道来,如轻风行于荷塘,细流穿过石缝,不必遮遮掩掩,不必装腔作势,更不必喝断行云的高声大嗓。
这个世界已经过于拥挤和喧哗,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诉求被遮蔽或覆盖,尽量提高自己声音的分贝。却很少有人在乎离自己最近的心灵。
责任编辑 吴佳骏
——给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