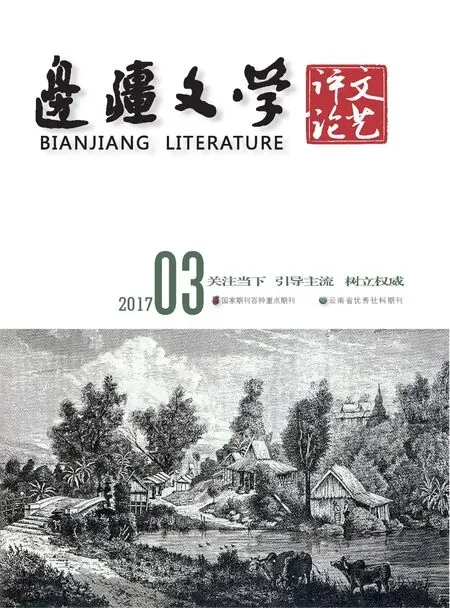边地历史的见证与想象
——论白族作家彭愫英长篇小说《枣红》的叙述姿态
张羽华 白 瑶
边地历史的见证与想象——论白族作家彭愫英长篇小说《枣红》的叙述姿态
张羽华 白 瑶
彭愫英是怒江州一位土生土长的白族作家。在她的创作世界里,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几乎都是以个人记忆的方式来见证边地社会的发展,并且以现代文明的审美视角去关照人们的心灵世界和生存方式,从而表达出个体的生存哲学。 目前,彭愫英的创作主要有散文集《盐马古道》《兰馨一瓣为你开》《追风逐梦》《怒江记》,小说集《古道碎花》,长篇小说《枣红》等。她在《民族文学》《边疆文学》《厦门文学》《剑南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和小说百余篇。在当代多元化的社会,她“知觉到自己深深植根在一个世俗的、连续的时间之中,并且知觉到这虽然暗示了连续性,却也暗示了‘遗忘’这个连续性的经验——这样的知觉,引发了对‘认同’的叙述的需要。”基于这样的生活认识与感受,彭愫英一边在校园里教书,一边足迹怒江州的各角落,从本民族文化里寻找生命的价值。
在文学阅读与文学批评异常躁动的时代,作为一个地处边缘地域而始终坚持文艺创作的民间作家,我们或许一直没有特别关注彭愫英的存在,但我们仔细阅读其作品后,就更增强了对其创作的肯定和赞许,认为作家以切身的体验和丰富的想象,建构了怒江边地美好的社会人生图景,给我们了解边地风情和人的生存哲理提供了一种途径。从长篇小说《枣红》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迹象。小说隐含了作家的人生经验并参与了历史的、民族的想象与建构,并通过文学想象的艺术方式来对即将遗忘的民族生存历史做出一次精神的特殊旅行与记忆重构,表现出一种情感的内在真实,生活的点滴记录。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主要以姑婆为叙述视角,审视着历史的变迁,见证了本民族的情感历程。彭愫英的最大艺术发现在于隐去了政治的时间并以苦难的姿态叙述着本民族的历史与情感的创伤,用卑微的心灵照亮边缘的世界,用博大的情怀叩问与思考人的情感世界,以民俗学者的身份考证少数民族的世态风情,体现出作家独特的人文关照与审美感知。
一、历史记忆:以姑婆的叙述见证历史的变迁
小说以一位经验非常丰富、能够穿透历史时空的主要叙述者进入故事,叙述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往往能够增强叙述艺术的真实度。“历史的书写是整个记忆的过程。”小说选择老枣树下姑婆所讲的杨将军历史故事作为叙述的开始,来讲述故事。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了老枣树这一意象。作家通过对它的叙述,能够在日常经验中体现出内在的意义和价值。显然,它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老枣树的成长象征着族人的成长,象征着家族的历史变迁,更象征着整个人类在蹒跚的进程中所遭受的沧桑历史。在姑婆的眼中,柱子、兰儿、树仁、萍妹、黑妹、秀琴、晓榆等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就是一部真实的人生经历史。他们在老枣树下相互依偎,在杨将军的故事中不断领悟,在生命体验中逐渐感受经历的酸甜苦辣。
“当前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现象之所以引起学界的重视,并不在于民族文学是否应该大量书写本民族历史,或者如何书写历史,而是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在重述历史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与既往的历史书写相比发生了质的嬗变。”这在彭素英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家以姑婆的叙述眼光对民族历史的反复追寻和对现实生活的考量,确立了现实的价值取向与本民族的立场。当然,小说中的叙述者并不是由固定的某个角色承担,故事也并不是由某个人一直在讲述,但姑婆几乎是以全知叙述者的姿态进入故事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姑婆仿佛站在制高点上,过去的历史和正在经历的事情,一直被姑婆这一叙述者控制着。在我们看来,姑婆对本民族历史表现出一种隐痛。姑婆的心灵创伤只有通过历史的记忆和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才能够抹去,并在重建历史话语的过程中,赋予了本民族历史新的生命。姑婆对柱子和兰儿的成长是非常关注的,可以说她想把自己未实现的事业让青年一代去完成,从根本上去改变贫苦落后的面貌,继承民族的光辉事业,以此确证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而弥补心灵的创伤。
在老姑婆眼中,兰儿有着美好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兰儿从小就不满足于这片大山,想要迈出大山,出去走走时不满足于只是过客而是想要扎根,并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面得到最大的满足。当兰儿奋不顾身去追求精神的满足时,却换来的是家的背离与伤痛,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而柱子却一直在身边选择把她拉回来,可是他了解兰儿,明白兰儿的精神世界和人生价值追求。她决定着她自己的一切,不受任何所牵绊,即使牵绊也会最终为她的梦想而妥协。树仁的人生就像村子,愈来愈兴旺,其中不免于酸甜苦辣的滋味。柱子的起起落落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一个人为了梦想而努力,虽然儿时的梦让现实所击破,但生活是美好的,只要懂得幸福是什么,最终收获的肯定也是美好。兰儿的波折是滚滚红尘中的一粒细沙,沙子是否精细需要时间打磨,她的一生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不是人一定要去奋斗,而是人一定要在某个时刻懂得知足,在于自我满足是否幸福。
“理性地审视、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其中的某些价值精神,即使是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也仍然有其值得保持和发扬的价值”不可否认的是,地处边缘的云南怒江州的一个村庄,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非常丰富的代表性村寨。在全球化语境下,这些边远地区文化的某些精华仍然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它是见证一个民族成长历史的标志。在阅读《枣红》中,我们自然地感受到,老姑婆自觉地传承本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的火把节、尚旺节、“二月八”节等传统节日,尽管是一种象征性符号,但对民族精神的传播,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服饰上来看,兰儿的衣装打扮体现出这一少数民族风情习俗的精神面貌。白色长袖口拼接着带图案的青布,蓝、白色镶接的对襟领褂上卧着红蜻蜓般的布纽扣,后面系着白色百褶裙,前面系着围腰,白色围腰边拼接着布,最下端绣着花,青色围腰带上绣着白色的不规则图案,盈盈一握的腰身,把那马少女的服饰衬得如此美丽。更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红梅这一女性,她是村里当之无愧的山歌王后。她头盖蓝色布巾,黑油油的一对长辫盘在布巾里,白色右衽长袖短衣,衣袖口绣着花边,蓝色对襟绣花绾边领褂,腰系绣花边花衿围腰,黑色宽口筒裤,脚穿自制的千层底绣花布鞋。这一身装扮是那马少女内在心灵世界的自在呈现。可以说,作家对精美艳丽的那马服饰的描写激活了人物个性,展现出少数民族的生活品格,呈现出鲜明的美学特征。
可以说,“西部民间文学的当代再创作,已经构成西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大特点,值得我们去关注。”怒江边地的大量民间山歌,参与了小说的整体建构,真切地表达了作家的民间立场,从而增强了小说的艺术内涵和民族特色。叙述者让红梅扮演了唱山歌的角色。林中只要一响起歌声,兰儿和柱子准知道是红梅姐又在为生活增添色彩。“情小哥,花开自有蜜蜂采,口渴要找山泉喝。阿小妹,弩弓射箭有目标,燕子筑窝选人家……”朗朗上口的歌词,既押韵又流露那马人的独特情感世界。在交通与信息不便利年代,生活在怒江州的澜沧江边上,少数民族青年往往通过对山歌的形式找到意中人,决定一辈子的婚姻,这给青年人的生活染上了浪漫色彩。同时,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山谷中传出天然的歌声,更彰显出人们的一种精神力量。
对本民族英雄人物的反复叙述,可以说是作家反现代性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式。小说中几代人都是在老枣树下听着姑婆讲杨将军的故事长大的,他们都在与老枣树相伴而终,但却只有兰儿离枣树已经越来越远了。柱子、树仁一直依偎着老枣树,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下一代都扎根在银涧村。这里承载着不仅仅是这一代代的人,而是一种精神品格和民族的生长力量。老枣树下杨将军的故事,被姑婆反复的叙述,这不仅是叙述者对历史故事本身的回忆,更是叙述者通过讲述历史中的英雄故事来激励下一代人,传承历史中的英雄文化,表达出一种民族历史的忧患意识。当然,这也是作家按照本民族的生活习性和固有的思维习惯对抗性书写的一种叙述姿态。
二、爱情叙事:在日常生活中演绎
作家将这部小说置于特定的政治历史话语中来讲述少数民族边地的特殊情感故事,没有过分去渲染浓烈的政治氛围以及给人带来的精神创伤,而是淡化了政治叙述的激情,把各种情爱放置在特殊的时空,自然地展露各自的情感世界。我觉得一些因素导致作家偏离主流的叙述,首先是地域位置决定了故事的讲法,作家的日常生活意识足以让历史中的历次政治运动远离文本叙述的主流,同时,作者的叙述姿态始终是站立在本民族的立场来审视历史的社会变迁,更集中体现在对本民族的心灵世界和人性品格的把握和思考,而不是依赖政治环境左右人的生存命运。
情爱叙事不是小说的创新,但是想象一个特殊的边地世界来营造少数民族的爱情故事,也是足够引起我们重视的。爱情的温床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小说中那一对对年轻人的爱情本有着美好的前途,但各种原因没有走在一起,使得他们在以后的人生中多少显得有些遗憾。柱子和兰儿幼小的情感是纯真的,但后来还是没有走在一起。
兰儿:“老兵叔叔说,海很大很大,望不到边。蔚蓝色的海面辉映蔚蓝色的天空,白帆将大海从酣梦中唤醒。海鸥追逐着船犁出的浪花,海滩上洒满五彩缤纷的贝壳……美啊!我们这儿的山太高了,怎么望也望不到头,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到外面看看大海呢?”
柱子:“到海边的路很遥远,以后我们会有能力走出大山去见大海的,会去坐轮船坐飞机的。”
在小小的玉龙河里飘荡一艘优美质朴的语言纸船,承载着年轻人美好的人生理想,吟唱出一首首质朴的、具有本民族风味的情爱的理想之歌。
“两性情爱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文学中的情爱叙事常常表现出超时代的深层意蕴,这种深层意蕴不仅呈现了情爱本身的真实性,而且也超越了情爱本体,从而表现了人类生存的永恒性境况,体现出文学中哲学之思的魅力。”大山边地的少数民族情爱是纯真而质朴的。柱子和兰儿的爱火一天天地燃烧着,在蓝月田里充满暧昧如简·爱与罗切斯特般的爱情想象,“傻哥哥,我爱的是你,自你从澜沧江死里逃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注定和你有着解不开的情结。”多么美的时刻,多么明朗的语言,将两颗年轻而期盼已久的心紧紧靠在一起。可是现实的残酷使得青梅竹马的柱子和兰儿不能走在一起,两人之间美好的爱情理想被现实打破,后来各自成家。
如果说柱子与兰儿的爱是出自于纯真的情爱意识的话,那么柱子与秀琴的爱却是现实日常生活处境强拉在一起的。秀琴的父亲因公瘫痪在床,母亲远走他乡,年幼的妹妹无人照管,饥饿的袭击让秀琴从小就懂得了人生的真谛与爱意。同时,秀琴家现实的处境震撼了柱子的父亲秦贵善良的人性,他牺牲儿子的婚姻自由而强制秀琴与儿子成婚,以致改变秀琴一家人的命运。还有胜保、海贵与黑妹的情感纠葛,在作家的叙述里,显得异常生动而感人。
悲剧可以说是文学永恒的题材,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在作家的叙述中,红梅的悲剧最具有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思想意蕴。红梅是银涧村宣传队的骨干,担任主角,而海贵是配角。两人在对山歌中有那么一阵默契,本有着美好的未来,可红梅偏偏爱上了村里文化宣传队队长小禾。因为红梅作为银涧村的山歌歌后,自然与村文化宣传干事小禾有着共同的话题,频繁的交流让他们情愫渐生。凭这种感觉,她选择了这个男人,自愿地把最为宝贵的东西献给了他。她为了爱而奋不顾身,没有考虑之后要承受的痛苦,即使痛苦她也会接受,因为爱情在那个时候对于她来说就是人生的一切。海贵一心爱红梅,即使红梅已经对不起他,他也还是要娶她;即使红梅怀着小禾的孩子,给他戴了绿帽子,他也还是坚持要娶她。“你将我当成了懦夫和下三滥!狠心的女人,拿软刀子杀人……不管你爱不爱,我娶定你了!”海贵咬牙说道。“你容忍不了爱人在婚前就给你戴了绿帽子,你没有勇气面对众人的口舌。”事已发生,红梅心态坦然。而海贵怯怯无语,痛恨人生。最后,红梅在强大舆论压力下,跟着马锅头和松远走他乡,组成完美的家庭。
在笔者看来,就爱情的叙事而言,这与路遥《平凡的世界》中有某些相似之处。彭愫英的《枣红》更多的是反映了女性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故事,是怒江州第一部展现白族支系那马人和勒墨人精神风貌的小说,传递着温情主义的光辉。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生存境遇时,有着柱子收留曾伤害兰儿的杨黑旦,有着秦贵(柱子爹)让柱子娶秀琴,把秀琴弟弟当自己儿子养大……有着《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一家人的勤劳朴素,善解人意,帮助他人的少安、少平、兰香的一步一步克服困难的决心和行动,即使是消极人物田福堂、孙玉亭、王满银也是有人性光辉在里面。
小说饱蘸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蕴藏着人与人之间美好的爱意,凸显出纯洁而优美的情感心理。路遥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构想了孙少平与田晓霞在杜梨树下的恋爱,纯美而感动的画面;同样,彭愫英在长篇小说《枣红》中也描绘了柱子和兰儿青梅竹马式的爱情终未修成正果,美好而无奈的人生图景。但在爱情的描写中两部小说不乏相似之处,少安和润叶,柱子和兰儿都是彼此许下诺言要终身在一起的人,后来却因种种原因而身不由己,不得不放弃彼此。少安选择了秀莲,润叶嫁给了李向前,柱子娶了秀琴,兰儿嫁给了晓榆,命运的捉弄让四个年轻人不能入了心愿。最大的不同其实源自人物的性格,润叶为了爱情不管不顾,奋力争取直至少安抹掉了她最后一丝希望;兰儿却是选择另外的让姑婆满意的方式不声不响地在那个时候嫁给晓榆似乎是在报复柱子,但是她的心却怎么也恨不起来。
三、生存命运:继续以姑婆的叙述视角展现人生图景
虽然“优雅的爱情本身并不能提供小说所需要的那种连接性的或结构性的主题”。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会左右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从而改变小说的主体价值取向。姑婆的命运更是让人有一种挣脱束缚充满勇气的力量,在封闭的社会边界,她没有妥协,而是选择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独立生活。后来尽管没有后代,孤独而寂寞,但她依然自乐地感受美丽的人生图景。
正是姑婆的影响,才会有后来兰儿在那个时代成为少见的前卫女性。这种精神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姑婆对兰儿有着隐约的感悟,也正是有着姑婆对兰儿的时时念叨,不停地呼唤才会有着兰儿最初的婚姻。而无论老姑婆的呼唤有多么地期盼,多么不舍,最终还是没能唤回兰儿。因为兰儿的文化基因还没有被埋在老枣树下,她还是想在时代的脚步下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姑婆对兰儿的呼唤与思念,姑婆关于杨将军故事的讲述,姑婆对柱子这代人的影响,一直都在渲染着,一直都在传承着。其实杨将军,老枣树都是姑婆的精神延续,她希望兰儿是这样的,可她没想过兰儿远远超过了世俗对她的束缚。尽管兰儿的丈夫晓榆有稳定的工作,但她作为一个精明的女人还是不安心小家庭平静的生活,想去做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她先是在小镇贩卖蔬菜,最后在外界生意人耿一民的鼓励和推动下,在镇里开了一家既有民族风味又有现代气息的兰馨酒家,还在省级开放口岸片马开了兰馨酒家分店,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可以说,是历史的具体语境与姑婆的影响左右了兰儿的人生命运,也是她自己对爱情的独特体验和生活感受,促使她学会了独立,学会了与众不同的生活风格。
在作家的叙述中,生活的记忆回到了最基本的自然状态,回到了对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感受,回到了对个体的心灵揣摩与人生命运把持。兰儿波澜起伏的一生,值得我们关注。她很小就有着走出大山的强烈愿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求知欲和独立意识也逐渐增强。她果断地抛弃青梅竹马,而后选择与不爱的人另外组成家庭。她不甘于过着像一般农村妇女普通的生活,她要独立地谋一份职业,哪怕失败也会执着地去践行。事实证明,兰儿在经历了几次失败后,最终在事业上还是取得了成功。
在对爱情与事业的选择中,兰儿宁愿淡化情感而全身心地投入到瞄准的事业中去。在与晓榆的简单生活中,她终究还是得不到满足,最终选择踏上创业追求梦想的道路。在这条创业道路上,她有过孤独,有过痛苦,有过失败,有过他人的非议,也有过商人投递来的温暖情爱,但这些都是她生活的外围结构。真正让她动心的,甚至孤注一掷地去实现的乃是那一份不甘心的事业探索精神。
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彭愫英的这部小说中,我们更能够发现作家通过爱情的叙述方式来展露人物的生存命运。写柱子和兰儿的爱情不是小说叙述的重心,而是从中去感悟到边地人特殊的生存方式和对生活的根本看法。柱子的担当让他舍弃儿时一起成长的兰儿的那份情,而为了遵循父母对他人的承诺娶了没有感情的秀琴,这是他善良、本真、淳朴的具体表现。爱情的温暖依靠双方的理解和包容。秀琴的温柔与满足也让柱子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她勤劳朴实,温柔知足,拥有幸福的人生。当她懵懂地喜欢上柱子,当她无意知道兰儿和柱子的过去,她也曾想极力保护自己的爱情不受伤害,她悄悄地选择和兰儿探讨,却不曾想到兰儿的话让她选择信任。即使她知道柱子和兰儿的爱情,但是她的聪明让她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美好的人生前景。在他们的独特生命体验中,显示出边地少数民族人们生命的力度,传达出较为广阔的生命感知。
彭愫英用细腻、深婉的感情,写出了树仁儿时的任性,成年后的稳重踏实美好的品性。他在经历了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后,逐渐醒悟,变得稳重、踏实。无论外界怎么变化,他和松妮始终沉浸在苦心经营果园的美好理想里,全身心发展水果产业。他也曾有过闯荡的勇气,但最终还是回到属于他的土地。在他的人生追求中,他知道什么才是幸福,什么是落叶归根。树仁的人生是他自己用踏实和诚恳换来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树仁的人生模式,也正印证着边地少数民族普遍的生存方式和美好理想。
晓榆在人生事业上有着明确的目的。他会处事,也懂得妥协,对人生有着美好的设计。晓榆在道班里是数一数二的好班长,心胸开阔,有事业心和进取心。后来尽管被爱人抛弃,但是他并没有气馁。或许晓榆作为普通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他的诚恳,踏实,打动了萍妹的心,最后俩人走在一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柱子在银涧村封闭的社会里,大胆组建建筑公司,干一番房产事业,后又从事桥梁施工,都有着现实的人生意义。 在《枣红》中,柱子、兰儿、树仁、松妮、萍妹等一代年轻人为了理想而追求,为了生活而奋斗,现实与理想并存的奋斗经历令人赞美。正是由于他们的年轻、冲劲、勇敢,才会有着那个年代看不到的光芒,才会经历着各种人生拼搏过程中的苦难,才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以小枣树到老枣树这一自然景观的成长来见证那一代年轻人的梦想与追求,着实体现出作家的人道关怀。从这里可以发现,作家在为我们揭示出一个道理,无论人生命运怎么样,总要学会取舍,学会知足,学会生活。那个年代想要的不一定实现,放弃也许是最美的祝福;不想要的却可能是要降临在你身边,这时接受往往比抱怨来得更坦荡些。
小说不仅通过人物的爱情故事来见证人生命运,而且还描绘了一幅幅澜沧江畔两岸五十多年来的变化场景,挖掘了那些美好而朴实的人物内心世界和精神品格。小说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对女性视角的描写,兰儿的桀骜致以最终的遥遥无尾,红梅的爱情执着与生活无奈让她选择相反的人生,秀琴的聪慧勤劳让她拥有美好的家庭幸福,松妮的能干朴实换来的是平淡令人羡慕的知足生活……可说是在细腻感人的文字情节中刻画了一个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文字背后的韵味更是让人产生无数共鸣。这与《平凡的世界》中把苦难转化成一种前进的动力的人性高度来说,《枣红》中的这一女性视角的刻画显得也是颇有深度。彭愫英与路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她独特女性叙述彰显了澜沧江两岸历史文化的精神和少数民族的生命意识。作为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营盘镇沧东村西营村人,她把怒江州的民族历史文化和人的生存状态艺术化地展现出来,体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蕴。在小说不同人物的性格描写中,作家倾向于从人物性格来挖掘人物的命运,无论是充满悲情、苦难,还是幸福、美丽,都在各自的人物性格发展中,做出较为完满的形塑。
“任何对于历史生活及现实生活的理论阐释与描述,都有初始的具象基点,都与所阐释与所描述的相关想象密切相关。”同样,任何对于历史生活及现实生活的体验与想象,都是有初始的具象基点,然后转换为艺术想象或者小说想象,使得作品的审美艺术得以呈现。长篇小说《枣红》最大的艺术发现就在于,作家以边缘创作者的身份,真切地体验和感悟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生存方式,把各种复杂人物放置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双重语境中,让人物性格去决定人物的生存命运。这部小说在重构边缘民族地区人的生活完整性上,在重建民族风情精神心态与民族地域文化的统一性上,有着深入地开掘和思考,体现出边缘作家创作的独特价值和民族文化立场。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M]. 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00.
[2]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7.
[3] 李长中. “重述”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深层机理探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4]陈继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化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315.
[5] 徐兆寿.论西部民间文学的当代再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6] 周志雄.论情爱叙事的深层意蕴[J].学术论坛,2005年第11期.
[7] (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M]. 高原、董红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151.
[8]高楠、王纯菲.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93.
(作者张羽华系南京大学文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白瑶系四川眉山市新四中心学校教师)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