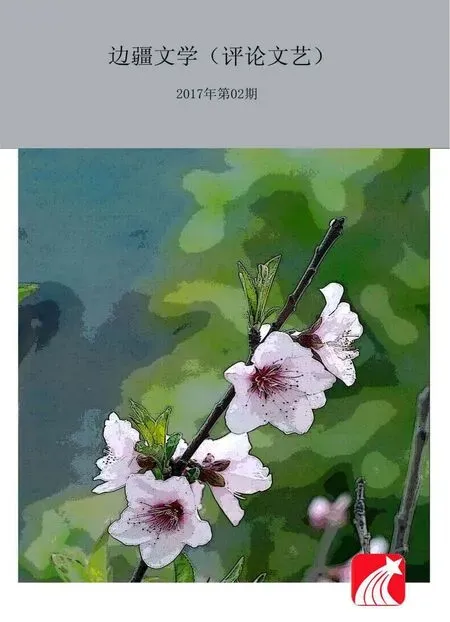走进一片妖娆的风景
——段海珍小说论
杨荣昌
走进一片妖娆的风景——段海珍小说论
杨荣昌
滇中地区悠远的人文历史和繁复的文化景观,是构成青年作家段海珍小说创作最可贵的灵感来源。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她公开发表了多部中短篇小说,并出版小说集《鬼蝴蝶》《红尘宝贝》和长篇小说《天歌》。这些作品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美学风格,集中表现出对人性的审视与拷问,尤其以讲述女性个体在时代嬗变中的遭遇,深度触摸到了一个民族充满痛感的神经。可贵的是,她的女性话语叙事,又与文化的批判或阐扬相结合,力图通过女性命运的流转,呈示一种历史或人伦的内在规律。
身为彝族和女性,段海珍在呈现社会律动、探掘人性幽微时有着独具只眼的文学观察与表达,在早期的小说中,已经初步显露出对民族与身份的敏感。她塑造了一系列女性人物形象,她们大都具有悲剧性的命运。如《红妖》中的秋水,年轻时跟随外出打工的小伙李阿根回到山里的麻湾,不幸的是,李阿根在一次失足落水后死去,她只好嫁给三公公张铁匠。可惜大儿子豆子落到江里少年夭折,老实巴交的张铁匠也在她中年时先于她而去,最后,漂亮的小女儿石榴也被淘金队员骗出大山,从此杳无音讯。生活的灾难全部压向了这个苦命的女人,囿于世俗的偏见,她一直无法与倾心相爱的阿宝生活在一起,精神饱受折磨,当“我”回到故乡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一个“蓬头垢面形体单薄的女人”。“旗袍”作为重要的叙事元素,在小说中的三次出现喻示着秋水命运的不同阶段,重重磨难最终耗尽了这个女人一生对美的追求热情。《鬼蝴蝶》中的阿姑婆,青年时被屌兵凌辱,村人视其为不洁之物。为了强化阿姑婆的不祥,村人一口咬定她会放蛊,会害人。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一种特有的民俗现象,“蛊”是邪恶的象征,巫蛊的神秘性、危害性一直为世人所诟病,放蛊之人,让人又怕又恨,欲除之而后快。小说写出了这种世俗力量的可怕,阿姑婆大半辈子被孤立,孤身一人住进村头的瓦窑里,成为边缘人,最终不堪忍受世俗力量的挤压而以自焚结束自己衰迈的生命。《桃花灿烂》中的桃花,与山外来的实习教师相恋,被村人视为不祥,家庭被罚“洗寨子”,自己也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爱情本是人性深处最美好本能的迸发,但在偏远之地的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之间互不通婚的封闭与偏狭,让无数怀揣美好憧憬的女性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之相关的男性,多半逃之夭夭。为爱情而遭受磨难的并非桃花一人,村里两位姑娘怀上了汉族人的孩子,受不了非人的折磨而跳河自尽。段海珍早期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女性人物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她们几乎都生活在命运的洪流中,要么成为男权社会的遗弃物,要么成为集体无意识的牺牲品,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群体。而小说中的男性是怯懦的,或霸道的,很少有正面形象。村里的人尽管没有典型的坏人,但他们受传统延续下来的愚昧思想的推动,加上各自或多或少的私心杂念的驱使,形成一种对女主人公造成伤害的共犯结构。这种看不见的力量由多种因素交织,常以看似道德化的面目出现,其指向却是违背道德与人伦的。作者以冷静而饱含理性思辨的笔触,把审视民族痼疾、批判男权社会与透视人性之恶相结合,抵达了极深的维度。
在发表了多部中短篇小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小说表现技巧之后,段海珍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首部长篇《天歌》便被中国作家协会列入“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出版。《天歌》中的人物依然是女性为主角,在一个充满天崩地坼的社会中,作为地主家小姐的徐梅兰必然要迎来生命的激荡与撞击,偏偏她又是接受过一定知识教育的新女性,对自由和爱情有着属于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尤其是后者,几乎影响了她一生的命运。在那一切都未可知的年代里,爱情既要受到传统伦理,尤其是封建家庭的制约,也将受制于革命名义的约束,但爱情毕竟有伟大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末世恐慌终究被新生希望所替代,对心上人的一次次寻觅,是支撑徐梅兰经受残酷命运洗礼的精神支柱。小说中的“天歌”即梅葛,是彝族民间歌舞和民间口头文学的总称,其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反映了彝族人民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的全貌,被视为彝家的“根谱”、彝族的“百科全书”和长篇叙事史诗。“梅葛”包括“青年梅葛”,主要反映彝族青年男女纯真情爱生活,属于情恋山歌性质;“中年梅葛”主要是青年男女所唱成家后生产生活的艰难困苦,内容曲调比较凄惋忧伤;“娃娃梅葛”是彝族的“儿歌”,一般由成群结伙的彝族青少年和儿童对唱,给人一种浓郁的民族乡土生活气息和质朴悦耳的美感。徐梅兰一生的欢乐与忧伤,除了对爱情的忠贞坚守,还与产生于本土的天籁梅葛调紧紧相连。可以说,是爱情与音乐支撑她活到了86岁的高龄。这种坚守,表达了作者对女性主体命运的深切感悟。
在《天歌》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段海珍写作风格的某种转型,她一改之前那些沉郁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写作,转向了明朗化,抒情化。从早期作品中女性惨遭蹂躏到《天歌》中坚忍不拔的生存,从人性恶的透视与鞭挞到近期作品中蕴含的脉脉温情,小说的叙事伦理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写作技巧来看,《天歌》作为典型的历史小说,但叙事重点不在于表现历史事件的正统性和宏大性,尽管读者可依稀从中捕捉到正史的影子,她更多是将历史幻化为一种叙事背景,为衬托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命运服务。在大的史观统领下,还有许多虚构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绝非可有可无,或漫不经心,而是潜隐着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思考和安排。小说还写出了土地改革后家族伦理的崩溃,导致宗法制的瓦解,这一变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相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因为太“实”之缘故,通常有太多禁忌,反倒束缚了作家的想象力,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间,几乎都是按现实规律来写的,极为简略。
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其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序言中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程度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种种情感和思想的表现。”在云南这片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土地上,每个民族背后都敞开了一块充满魅性的神秘世界,长久以来,一代代云南作家以绚丽的笔触,点染了奇幻的高原色彩,形成了以民族性和地域性为核心的云南文学审美传统。但这类写作容易流于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表层抚摸,文学的核心在于写出人物的命运和心理,只有达到心理之深,才能树立文化之魂,实现文学的有效表达。云南的民族作家一直在努力,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无论是为民族代言还是持审视态度,他们都力图尽可能沉入人物心理的深层,探究民俗、民族文化后面所蕴涵的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妖娆的文学风景,段海珍多部小说中均把民俗作为独特的叙事元素,充分采撷滇中地区特有的文化元素,经过审美化的重述,写出一类人乃至一个地区的文化精神。《杏眼》中,方言俚语、民谚童谣和花灯唱腔的一招一式,被她一一缝合在对一个民间艺术家执着守望花灯艺术的文学表现中,显现出深厚的艺术积淀和绵密的叙事耐心。这种中国式的故事,呈现的是中国式的情感,亦具有鲜明的中国式美学特质。此外,多次描写毕摩祭祀的场景,写到彝族人“神药两解”的自然观和生命观,等等,营造出一种人神共居的文化氛围。
在当下,作家的责任担当已不表现为单纯地汇入众声喧哗的宏大赞美之潮,而是以其追求深度的书写,观照民族的根性与魂魄,从而超脱于民族自身的狭隘视域,实现全人类视角的整体性书写。这种双重眼光,使民族作家身具民族歌者和智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一方面倾情歌颂聚居地秀美的山河与绚丽的文化,一方面又对本民族愚昧落后的生存世相发出痛苦的疾呼,以一个在场者的敏锐直觉,对社会文化生态做出深刻思考与理性批判。段海珍的小说对彝族毕摩文化的演绎及对巫蛊迷信的鞭挞,重现了彝族人特殊而异样的生死观与鬼魂观,寄托了对受迷信祸害的“蛊女”命运的深切同情。她采集丰富的地方民族文化元素,借用现代小说叙事手法,激发出来自民族心灵深处的自我批判意识和基于人存在价值的现代性省思,使小说传递出一种批判与启蒙并存的精神指向,从而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与人性内涵,由此呈现出民族文化的神髓与地域文学的质感。
(作者系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