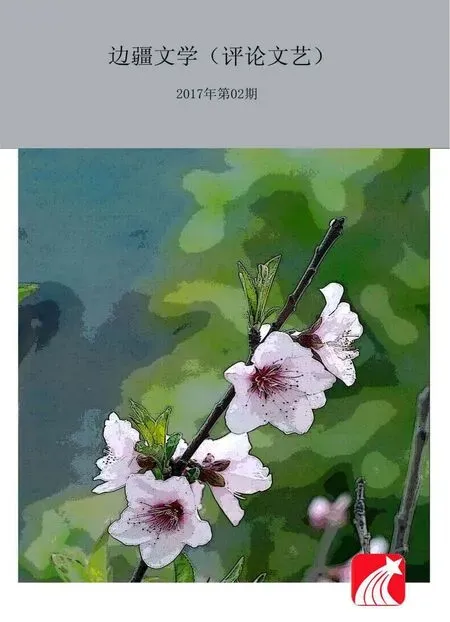金沙走笔,故土情深
——评马淑吉散文
黄 玲
边疆阅读
金沙走笔,故土情深——评马淑吉散文
黄 玲
·主持人语·
服务基层是本栏目的一项工作任务,关注基层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关注基层的文学写作者。马淑吉、张学康、段海珍是楚雄的写作者,以前关注较多的是段海珍,也发表过评论张学康散文的文章,以马淑吉的文学作品作为评论对象还是第一次。南马长期关注红河州的文学发展整体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很有心得,这篇对弥勒诗人黄光平的部分诗作进行点评,是他在对红河州文学进行宏观研究之后的个案微观研究,注重文学的地域性和乡土特色。基层的文学经常在语言特色、叙事风格、表现手段等方面有别样的味道。(杨林)
出生于彝州大姚县湾碧傣族傈僳族乡的马淑吉,对金沙江畔的故乡始终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她近期出版的两部散文集的书名,都深深地打上了金沙江的烙印。一本是《金沙人家》,一本是《金沙傈僳》,全部取材于故乡的人和事,抒发着作者对故乡的浓浓情意。
《金沙人家》的副标题是“沿金沙江‘环百草岭’区域风情散记”,《金沙傈僳》从书名上就透露了这部集子的选材范围,是以金沙江沿岸傈僳族的人文风貌为内容,还配以精美的摄影。两部作品都是以金沙江的地理区域为中心,看似范围比较小,但深入阅读会发现小的视角后面隐藏着大的情怀。作家的视野与文笔,全都紧紧扣住金沙江沿岸的民族风情和各民族的现实发展而展开,和那些单纯的观光者心态有很大区别。要解读这两部散文集,就得对写作者的文化身份、文学追求进行一番梳理,才能更好地把握住其散文的内在意蕴。
一、基层干部和文化行吟者的双重视角
在阅读散文作品时,应该看到作者的身份对散文选材的影响和制约。
不同的写作者,面对生活时的角度与选择是不相同的。一名外来的观光者,他的目光更容易被陌生的风景和民俗所吸引,产生审美的冲动。他的作品可能会体现出漫游的特色,和走马观花式的新奇感。而一名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写作者,对他来说故乡的风景和民俗已经化在血液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写作应该是沉入式的,能从生活中选择最有感受、最能体现情感的内容进入散文。这样的作品可能没有外来者的新奇感,但却会有一种外来者所没有的深入与厚重。这是植根于生活土壤里,充满泥土气息的写作。
读马淑吉的散文,就有后一种感受。
马淑吉的身份比较明确,她首先是一名国家公务员,一名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基层干部。同时又是一名热爱文学的写作者,可以用文字表现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收获与思考。其深厚的生活底子,会让很多作家羡慕。从书的扉页的简介中可以了解到她的工作简历:七十年代出生于彝州大姚湾碧,金沙江畔一个傣族、傈僳族杂居的地方。参加工作后,从事过民政工作,担任过副镇长,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县广电局党委书记、现任县文联主席。这样的人生历程,完全可以积累下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经历,也能具备一定的写作高度。如她自己所说:“对彝州这方水土的丰富地域文化有着浓厚的热爱之情。”这不是客套话或者矫饰之语,而是发自内心真诚的抒怀。
这样的人生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马淑吉散文选材上的独特性。如青年批评家杨荣昌在为《金沙人家》所作的“序”中所概括的:“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一名对家乡本土文化有着强烈热爱的文化行吟者,马淑吉的文字中充满了对现实民生的倾情关注。”和一些专注于审美追求的散文不同之处正在于此,马淑吉的散文中随时可以体会她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的视角和情怀。
《金沙人家》由八章构成,每一章都有三个层面的内容互相交织。一是大姚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展示,二是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资源的汇聚,三是现实生活中各民族群众的劳动创造与精神追求。三者之间互为表里,体现了马淑吉散文选材上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第一章“铁锁印象”,是对一个基层乡镇民俗风情和现实生活的叙写。需要注意的是,马淑吉曾经担任过铁锁乡的党委副书记、乡长的职务。她对铁锁的关注和一般的观光者自然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作为一名在铁锁工作生活过的干部,她的散文中肯定会有一些对铁锁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的描写介绍,比如壮观的梯田,火红的攀枝花,还有流于民间的各种传说,都为铁锁这个偏远的乡镇增添了异彩。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作者对这块土地的熟悉、亲切,还有一份真挚的情怀。她不是这里的过客,而是一名与山水结缘的文化行吟者。但是,她同时还是这块土地的领导者,是上级方针政策的执行者。所以从一些篇幅中可以体会到这一视角对马淑吉散文选材的影响。她在《2010年那场干旱》中记录了干旱对民生的影响,充满焦虑和渴求。甚至对那一年的每一场雨到来时的时间、雨量、心情都有详细描写,既传达了一位基层领导的责任感,也能体会到一位写作者的忧思。她还用文字记录着铁锁的建设与变化,《渔泡江畔灯火明》,就是对建设铁川桥水电站的侧记,并对铁锁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记。在《风情铁锁》中,她对铁锁的历史、民情、风物特产都有细致的描述。还用文字记录下了自己对这方土地的一片真挚情感:“一点一点了解铁锁,走进铁锁,它的每一点美丽都令我欣赏,每一点变化都令我兴奋鼓舞。与铁锁血脉相连的不解之缘,让我朴素的生命永远不能与它分离。”
在马淑吉的散文中,铁锁只是一个点,也是她人生中的一个驿站。但她却投入了深深的情感,记录下自己与铁锁的一份情缘。这些文字虽然不够精致,但其中洋溢的情怀和朴素的叙事,却仍然能打动读者的心。
从马淑吉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因为工作和职务的变动,她取材的目光和视野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在《金沙人家》这部集子中,还有这样一些内容:金沙人家、水乳湾碧、咪依鲁的故乡、中国核桃之乡、祭孔圣地等等,差不多囊括了大姚重要的文化现象。所以杨荣昌在本书的“序”中评价说:她“从立体型、多维度的层次上勾勒了‘文化大姚’的风采”。
大姚的文化特色很多,比如“中国核桃之乡”、“中国彝剧的诞生地”,资源也非常丰富,素有“三乡露铜”“五井喷盐”“文化名邦”等美称。这里还有世界上现存体积最大的孔子铜像。这些特色在《金沙人家》中都有涉猎和表现,马淑吉以“文化行吟者”的角度,用文字细致描绘着这些人文景观,为外界了解认识大姚文化创造了很好的文本。
长期基层工作的实践,为她深入认识了解大姚提供了条件,文化行吟者的视角则为她的散文增添了丰富的内涵。在另一部散文集《金沙傈僳》中,她把视角聚焦于彝州境内的傈僳族,对他们的民族文化、现实生活进行忠实记录。既写出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对他们生存环境的艰辛有深入理解。阅读这些作品,能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文情怀。在马淑吉这样的写作者这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早已经是一种自觉的行动。所以她的散文既是长期深入生活的积累与收获,也是接地气式的写作,其精神和态度都值得提倡。
二、对故乡山水民情的深情书写
从马淑吉的经历和文字中都可以体会到,她是一名金沙水养育的彝家女儿,对生养她的土地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所以,她才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提笔写下记录故乡变迁的文字,还摄下无数记录故乡发展进步的图片。
热爱故乡,并歌颂赞美它,是很多游子在文学中书写的永恒主题。但是多数人取的是离乡之后的回望视角,是距离产生美的“思乡”与“怀乡”。马淑吉的散文则不同,她是始终站在故乡的土地上,与之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以一腔热情为它的发展而讴歌。所以她把《金沙人家》的第三章命名为“水乳湾碧”,就是在暗喻自己和湾碧之间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里是她的出生之地,也是她身上另一半傣族血统的发源地。但她取的写作视点不是个人情感式的表达,还是从文化行吟者的角度侧重对湾碧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内涵的表现。比如傣族的“窝巴节”“金沙傣”“金沙傈僳”的独特习俗,都从马淑吉的笔端流淌出来,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受。
虽然她努力把视野投向文化和民族,个人的情感表达不是那么突出。但是认真阅读作品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和个体生命成长有关系的片断,它们散落在作品中,犹如断线的珍珠,可以串起作者成长的痕迹,找到她和故乡之间内在的联系。在《炳海渡口》一文中,马淑吉以略带忧伤的笔调写到外婆,也写到自己的成长。从中可以感受到金沙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风俗,是她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也是她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以故乡的山水人情作为写作对象的一个注脚。
在《村头有棵万年青》中,马淑吉穿上傣族服装,很快又融入到傣族文化的文化氛围中去。她的血液中原本就有彝族和傣族两种血缘,两个民族的文化在她身上融合得如此奇妙与和谐。在《水巴崖》中她对家族祖上的历史有比较细致的叙述,从“老祖”打土匪的光荣历史中也可以窥探到一个家族曾经的艰辛与曲折。
但类似的个人成长史和家庭历史,在马淑吉的散文中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穿插散见于其散文篇章中。她更多的笔力还是放在对故乡文化和民俗的描写中。或者说她更集中表现的是大姚这个故乡的人和事,而不仅仅局限于湾碧这个出生之地的小故乡。这是一种开阔的视野,也体现了其散文意蕴的深度。
《金沙人家》第四章“桂花飘香”,第五章“咪依鲁的故乡”,集中对彝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民俗文化进行了深入表现。百草岭的绚丽风光,和彝山文化的丰富多彩,体现了作者对故乡的一往情深。
《金沙傈僳》是一部独特的作品集,作者在书的“前言”中透露了写作的动因:“随着水电站建设移民搬迁和‘现代化’洪流滔滔,一些民族文化遗产濒临消失”,所以这部作品的写作意图是“为加强金沙江岸傈僳族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同时促进金沙江流域文化旅游发展”。为了写作这部作品,马淑吉调动了自己多年的生活积累,希望能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一个个古朴、厚重的傈僳村庄,让古老的民族文化魅力得到展示。在《一湾碧水》《一方山水》《江外姜驿》《江有浣女》等篇章中,浓郁的傈僳族生活扑面而来。生存条件的艰辛和民族精神的顽强,都能给人深深的感染。
就如马淑吉在“后记”中所总结的 :“我感受到傈僳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傈僳族人的坚毅、质朴、乐观。他们的顽强和精神感染了我,连我也顽强起来 ,有一种力量,有一种精神,鼓舞我完成了这本书稿。”和那些依靠观光采访获得素材的写作相比,这种与生活本身建立起密切联系,从写作对象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的写作,更具有一种深沉的内涵。
这两部散文集的另一个特色是马淑吉充分利用了自己喜爱摄影的特长,采用了图文相配的方式,通过摄影和文字的结合,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大姚的文化风采。各民族地区的风情和多姿的文化特色,在镜头和文字的双重作用下焕发出全新的光彩。这是一个大姚女儿对故乡的深情回报。
三、马淑吉散文的优势和局限
马淑吉的散文已经体现了她所具备的优势,那就是扎根于生活,与故乡的土地和人民保持水乳交融的关系,用一颗多情的心灵拥抱世界。自然会获得丰富的写作资源,也能让情感之渠永远流淌出滚滚碧波。
散文是叙事的艺术,也是抒情的艺术,它对情感的追求是自然、真诚和朴素。这点在马淑吉的散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对故乡的情感是建立在相生相依,休戚与共的基础之上,和山水草木有天然的亲近感。她是大山的女儿,也是金沙江养育的女儿,所以她的文字自然纯朴,较少修饰,写人叙事都是以亲切的语气娓娓道来,有如和朋友交谈一般,毫无矫饰之感,这是一种难得的散文风格。
她散文中的抒情,不追求气势的强烈和情感的冲击,而是如溪流一般自然纯静,又能带给人清风扑面的质朴之感。似乎能让人体会到职业和性别对写作的潜在影响。比如在《村头有棵万年青》一文中,有一段文字对村头万年青进行描写:
“远远就看见了村头那棵万年青,风风雨雨中依然枝繁叶茂地挺立着。从记事起,这棵树就这么大,年复一年,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依然如故。村里的老人说,这棵树叫万年青,这种树长得慢,却长寿。”
这段文字里,作者的情感是隐忍而含蓄的。下面这段文字随着回乡时间的增长,对景物和往事回味的加深,情感才开始慢慢升温:
“在这从小长大的家园里逛来逛去,摘食着从小就喜欢的吃的红心果。思绪飞扬中,眼前,我们家族姐妹分明还在那块大滑石板上‘梭耥耙’,分明还在那棵洋茄树后面躲迷藏……”
或许是因为工作和职业的关系,马淑吉的散文涉及个人情感的内容比较少,情感表达也比较节制。而写到一些和工作有关系的内容,或者描写民族生活和节日的气氛时,她的语言才会张扬起来,体现出个性和风采。比如《窝巴节》这篇描写金江傣族节日的作品中,对傣族人过节的气氛就营造得很生动,场面和细节的描写都能体会到作者主体情思的渗透,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象脚鼓铿锵有力,葫芦丝婉转悠扬,小卜炒股的火草筒裙衣袂飘飘……欢快的舞曲鼓舞了情绪,大家开始互洒吉祥水,互道祝福的心愿。人们提着桶,端着盆自由追逐,肆意泼洒。水花四溅,笑声飞扬,人头攒动,人们尽情享受着这场民族的盛宴。”
这个场面的欢乐是放松而尽情尽性的,作者的情感也在场景的生动描写中得到了有效的抒发和倾泄。作为一位民族干部,是否可以说她的抒情方式也已经染上了职业的特点,既具备一种大气的姿态,也保持着一定的理性和节制。适合写群体性的快乐,不擅长写儿女情长。
所以我注意到马淑吉的一些散文中其实还隐藏着许多线索和秘密,可以成为下一篇作品的开掘内容。比如《江有浣女》中那位80岁傈僳婆婆的爱情悲剧,《爱药》中的孤儿美女,那些行走途中遇到的人物,因为作者表现视角的原因他们只是一些带着故事的匆匆过客,引而未发。如果认真深入进去,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在作者今后的作品中成为主角。
任何人的写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以客观的态度对创作中的问题和局限进行分析研究,也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进步,写出更有特色的作品,所以最后要对马淑吉散文中的某些存在问题进行评说。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才是真正科学的批评态度。
第一,《金沙人家》作为散文集,文体属性不统一。其中甚至收入了几首诗,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它作为一部集子单纯的文体特色,这是出版编辑时的不严谨。另外,从具体作品上看,艺术水平的高低也有不统一之感。虽然大部分作品艺术性比较强,审美特性比较突出,写景抒情能引人入胜。但也有一部分作品从文体上看是可疑的,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而是把新闻通讯或者工作报告参入其中。比如《金沙人家》第五章的“中国核桃之乡”,在整部集子中就显得不太协调。第八章“金马碧鸡的故乡”中的一些篇幅也有同感。其中的《三岔河扶贫整乡推进绘蓝图》,更像一份工作报告,和散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到目前为止,马淑吉已经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还出版了好几部作品集,又担任着大姚县文联的领导工作。所以我认为她已经到了可以对自己的创作进行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以期在写作上能更上一层楼。比如散文的文体意识需要明确,散文的文学性需要提升,主题可以考虑从时政的层面向人情人性的纵深有所倾斜,进行比较深度的开掘。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生活积累,又对文学怀有深爱的写作者,只要善于总结,扬长避短,相信她一定能写出更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