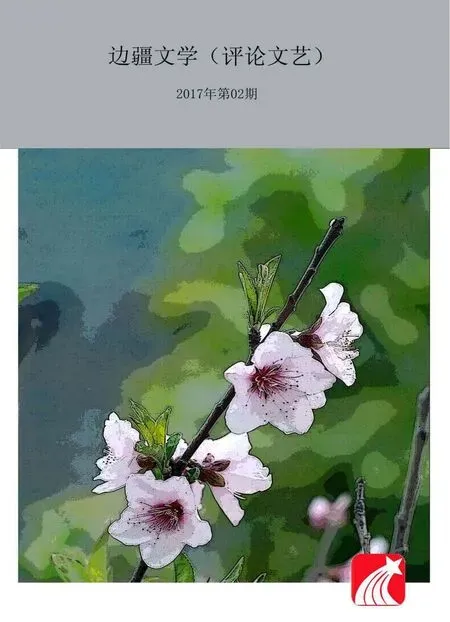情迷乡土 放歌彝山
——彝族诗人黄光平近作简论
南 马
情迷乡土 放歌彝山——彝族诗人黄光平近作简论
南 马
光平是大山里的彝家孩子,亲近乡土是他的宿命。他仿佛被笼罩在与命运相关的气场,草木、庄稼、河流、炊烟、白鹭等一切土生土长的事物中,乡土上俯拾的皆是“暖玉般”的恩情,阳光一样透亮着他的目光和语言,树根一样盘踞在他的心里。
按照时下中国诗评界的时尚划分,光平是属于“中间代”(20世纪60年代)的。“中间代”诗人“贯穿式的写作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界的历史进程”,作为这一代的诗歌创作抒情主体,光平的劳动起到了为“见证进程”添砖加瓦的作用。有论者指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在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诗歌失踪”现象。“诗歌在实现了个体化写作与个性化美学追求之后,彻底迷失在以准沙龙形态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接受的民间丛林。20世纪现代汉语诗歌催爆的中国诗魂的碎片闪烁在晦暗的诗歌夜空,诗歌灵光的闪烁随机而又短促。这个时期,诗歌和诗人都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诗歌现状的界说变得十分困难。至少在研究视野中,诗歌失踪了。”(《寻找当代汉诗的矿脉》,傅元峰著,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034页)这个基本判断读起来有些拗口,但其基本意思还是明确的,那就是:诞生不到百年的中国新汉诗在当下的高端阅读中消失了。这只是所谓诗歌阅读(研究)者或者是诗歌“顶层设计者”一厢情愿的表述。失踪不是消亡,是失联,是另一种方式的存在(民间化)。众所周知,中国的诗歌从《诗》滥觞,先是繁荣于民间(现在叫底层)。曾几何时,中层以上的“白领”出现了才子佳人,有了以吟咏风花雪月为能事的文人及其作品。中国的诗歌之河一分为二:一是上流在飘然于高空,不食人间烟火;一是下流在乡野大地,与引车卖浆者“同流合污”。脚踩大地,亲近乡土,向泥土鞠躬的诗人和他们沾着青草香味的诗歌向来就没有“失踪”过,包括新世纪。
光平最近几年诗歌创作颇丰,发表了近百首诗,收在新近出版的诗集《在乡土上》一书里。这是他在乡土上的一段诗意行走的“诗歌聚落”。先后发表于《文艺报》《云南日报》《红河日报》《诗林》《百家》《滇池》《红河文学》等,受到了读者的厚爱。这些作品在诗歌的能指维度上,前有精英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叙事”,如《烈士纪念碑》《1941年春天摄的一张照片》《遇见……》等诗的抒写,后有后现代《做一棵小草我已经很幸福》《一只小鸟在窗外喊我》《石榴花》等诗的“个人化”吟唱。这就是一种“贯穿式的写作”。
我曾在《红河文学创作的当下姿态和突围的可能——2013年红河文学创作管窥》一文中,对他的诗歌有过“定位”:情迷乡土。他的诗歌来源于乡土,沉迷于乡土。他宣称:“我的诗行照搬您的土墒,抄袭您的炊烟/借您盛满大土碗的酒/浇开灵感的花朵……您是缀连我所有诗行的衣胞、血脉、肤发。”
彝家汉子情迷乡土迷到什么程度?在《在乡土上》这本集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真正的乡土叙事,每首“诗眼”全扣在与乡土有关的意象上——《这片田野盛大如天》《一群白鹭从田野上飞过》《垂向泥土的鞠躬》《大哥一样的村庄》等,诗人从取象、立意到情感的宣泄,审美认知的确立,都是建立在大地和泥土之上的。他“写诗只会散发泥土的味道/和汗水落地的声音,甚至/把心掏出来挂成草尖上的露珠。”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的危险在于,面对乡土,情迷得难以自拔,只能把心都掏出来了!这是其一。
其二,诗人情迷于乡土的另类抒情表达,就是对“母亲”的疼。在本书中,诗人用了《娘咳一声,家就颤抖一下》等9首作品来表达对母亲的感恩。“娘咳一声,家就颤抖一下/这白霜如刃的寒月/一刀赶一刀,斫伐家的梁柱/停不下的揪心/明晃晃刺入骨髓”。(《娘咳一声,家就颤抖一下》)“如果可能,我愿把我化作点滴/输回娘的血管/还原高大的亲亲的娘”。(《点滴的意义》)“娘的手牵握在我手中/像我童年的手牵握在娘手中/慢慢走下医院门口的台阶/阳光豁然扑面/娘的手在我手中脉动/如一棵老树被春风唤醒/整个寒冬郁积我心的酸楚/顿时发酵成蜜”。(《紧紧牵着娘的手》)。作者从母亲生病住院,陪护,给母亲戴上佛珠到痊愈,握着母亲的手再次走向阳光这一时空流程,运用具有张力的诗歌意象,把一个乡村苦难妇女的形象高高地耸立在我们面前,读来令人怆然涕下。毫无疑问,这里的“母亲”已经不是个体生命意义上的母亲了。
其三,诗人情迷乡土的第三视角是对当下乡村社会以及城市扩张后“准乡土”的准确把握与呈现。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疯狂掠夺,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消费社会的形成,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被吞噬得无以复加。准乡土中的后工业文化开始登陆并撞击着诗人的心灵。这种视角主要表现在《一切,都会消失》《髯翁巷》《走过髯翁路的七天清晨》等作品中。
一切,都会消失/当家园需要寻找/刀斧遗忘忏悔/那一片给予血和气的乡土/布满堕落的悼词/一个人走在路上/悲伤如撒落黑夜的买路钱(《一切,都会消失》)。
诗意栖居数百年/难抵挡一朝钱眼觊觎/只落得灵土迁移,髯园灰飞/大观长联,写尽滇云苍茫/料不及商界魔道/挥舞着杀猪刀(《髯翁巷》)。
一位负重挑担的大娘/茫然落入一场惊慌/蹒跚着犹豫,蹒跚着提防/满脸的汗水/和草帽下的白发/被前后快速绕过的车灯/一闪一亮(《走过髯翁路的七天清晨》)。
近些年来,乡土诗歌的书写,的确出现了一些“偏锋”:有的诗人一写乡土,扑面而来的尽是鲜花美草、蓝天白云、小桥流水人家,一派美不胜收、乐不思蜀的“南山”景致;有的一面对乡土,就是苦难啊、破败啊、被侮辱被损害啊,好像中国当下的乡土只能是美好和丑陋的二元对立。光平情迷乡土,亲近乡土,他对乡土的美丑不做对立观,不虚美,不隐恶。这才是对乡土的“一步步踩深依恋”。
其四,对乡土全面而诗意的表达,来源于诗人高蹈的诗语给力。所谓诗语,就是诗歌语体色彩、语言风貌和话语特征的综合而形成的诗歌语言范式。光平在诗语运用中,割裂了平庸的词语链接,嫁接上自己独特的感触,形成了新的语序。他写甘蔗:“站着的甜/甜甜地站着的汁液/一节比一节高/高过这片土地所有的作物”;写石榴花:“一朵血/一朵又一朵朵/被春风剥开嫁衣的/少女的脸”;写春天小鸟的叫声:“清脆的甜/像一粒童年的水果糖/在我的心上洇开”;写白鹭的飞:“一群白鹭的翅膀,驮着家书在飞/它带给我的温暖,像蒙汗药/迷醉了我的魂”;写山丫口:“丫口呈V形,一座山的嘴巴/被水喊开/一条通江达海的路/甸溪河无休止欢呼”;写田野的暮色:“天上的星,从地上的一盏灯开始/逐一闪亮/暮色已经从草根升起/笼罩田野”……这样的诗语在书中不胜枚举,为诗歌作品靠近诗歌史给出了力量。
以上4点所及,归根结底就是诗人面对乡土,面对时代,面对民族,“一步比一步踩深对您的依恋”的结果。
尽管有了收获,诗人并没有停下坚强铿锵的脚步。他仍然走在他的“血地”,走进乡村,走进田野,走进泥土,走进石头。不要让我们被孤独,我们也不会孤独,我们的旁边站着一棵小草。他说:人生在山里/魂就在山里生根/爬过大山的人没有过不去的坎/走出大山的人不会忘记大山的恩情”。让我们成为乡野路埂上的小白花,被踩倒后又悄悄站起,托出笑脸——
让苦难没有怨怼的表情
让草根绽放灿烂的心境
(作者系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