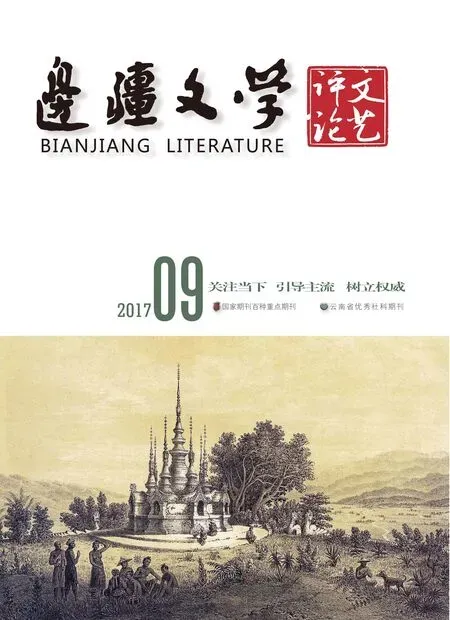在精神废墟上寻找依托灵魂的云
——读朱镛的《依托之地》
尹宗义
在精神废墟上寻找依托灵魂的云——读朱镛的《依托之地》
尹宗义
什么都空了。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都重来。
——朱镛《依托之地》
“一撮毛”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手,却不安心种庄稼,最先往外面跑,去了浙江、江苏、上海。衣锦还乡,成大家羡慕和崇拜的神。许多人都想巴结他,想跟着出去闯一闯。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外面的所作所为,直到警察来抓走他,才幡然醒悟。“一撮毛”蹲了三年的牢房回来,什么都空了,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都重来。他把生了锈的锄头找出来,翻挖土地,再也没有离开过村庄。三年后,外逃的妻子也回来了——但女儿们无脸回到这个地方,已经出嫁在外了,儿子出去好吃懒做,偷东西被人活活打死。眼泪落下,一砸一个坑。从那以后他和妻子,很少出门,始终护卫着自己的良心。
我在朱镛的长篇散文《依托之地》里读到这个故事,想到作者作为一个离开故乡的旁观者,写故乡今昔对比,并不仅是简单地抒发依恋之情,也不仅是流露怀旧情怀,而是在精神废墟上寻找可以依托灵魂的云。虽然村庄早已不再是记忆深处的村庄,但一直生长着祖先们种下的精神大树。参天大树下,可以安放思想,可以栖息精神,可以畅谈人性,可以洞察社会。
一、做丰收的主人才会收割喜悦
人的生命和庄稼之间,有着最亲密的生死关联。那些曾经年轻力壮的大妈、婶婶、大爹、叔叔,不仅失去了充满活力的体态和容光,更失去了见到丰收后的喜悦,只有冷静,僵硬,木讷,任劳任怨。在作者的记忆中,庄稼收获,每家场院上的谷堆,都是金黄黄,沉甸甸。人们相互谈起丰收,就让人激动得发抖,话语结巴。而如今,没有一个人说丰收,说的是,谁家的儿子儿媳过年才回来了。说着说着,就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什么也不再说了,自顾自地默默做事。
丰收了为什么不再有喜悦?因为年轻一辈背叛了与人性完全融合的土地——“人的离开,加剧了这块土地的虚空速度,使得这块大地,虽然不呆板,也不沉闷,但却多了份冷清,仿佛被亲近的故乡人冷落。”年轻人都进城务工了,不愿继承父辈,成为土地的主人;只能坚守在土地上的老一辈,他们老了,只是暂时代替年轻守着家,种着地,领着孩子,早已不是土地的主人。
被边缘化的村子,成了孤独的荒岛。一切都开始散失,在精神上,谁都孤身一人。作者精神还乡,其实是想从城市的欲望之狱逃离。但是,他看不到春耕热火朝天的场景,看不到秋收的喜欢,只看到形单影只的孤独,看到机械的动作和木讷的表情。作者自己也迷惑了,失望了。他不禁发问:“是否还是让人们看见一座村庄的时候觉得,它的存在,不止是一座村庄,而是众神的现身。”
精神不在,众神难活。人要找回村庄精神,只有变成村庄的主人。老一辈农民,他们即将离开村庄,不再是村庄的主人;年轻一辈,他们挤进城市,成为村庄的背叛者,也不再是村庄的主人;离开村庄的作者,也成为村庄的远离者、旁观者。作者精神还乡,试着回忆童年的点滴,唤醒主人公的意识。今昔对比,逐渐找到了主人公的眼睛——“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乡村的画卷都是美的,纯洁的,妩媚的,生机勃发的。并且,它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斑斓多彩,与自然中任何一种植物一样,属于神造的东西,与万物同在。让人与这样美好的自然接触,心头即便滋生一丝恶念,也会被消除。因为阳光和风,会在这个季节洗净人与人之间的曾发生的过结,怨恨和恩仇,洗净平日里相互有点摩擦见面阴沉的脸,变得无比亲和。”
朱镛发表了这个长篇散文,曾感慨地说,他将沿着这条路子,继续写下去,写成一本更长的散文。他说,写《依托之地》,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向。在属于他的创作家园里,做自己的主人,让众神归位,最后自己就是众神中的一员。写作如春耕,令人激动;作品发表如秋收,更让人喜悦。
二、充当一棵树的灵魂才会心存虔诚
树木,作为一种普在的生命,一般人不会去注意它。它虽然只是一个村庄的陪衬,但它会给村庄提供一种安全感,使得村庄在内部,在深处,在有着遮挡物的中央位置;它虽然不能像土地神一样让人们内心充满着敬畏,但它会让村庄对它充满敬畏的。它永远是村庄的守护神,需要我们每年去祭拜。每次祭祀树,都可以让人与神灵对话。
作者在文中详细描写了过年时父亲祭树的情景——父亲提一把斧头,端着一碗米饭和肉,带上我去充当那棵树,实质是充当树的灵魂与父亲对话。父亲用斧头轻轻砍开树皮的一个小裂口,问,“你结的核桃多不多?”我就站在核桃树旁替树回答,“多!”父亲就喂了那个裂口一嘴米饭和肉。接着,父亲又砍一斧头,再问,“结的核桃大不大?”我就答应,“大!”父亲又再次喂一口。核桃到底有没有结得又多又大,我真不知道,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故意捣蛋那年,那棵核桃树结的核桃真的又少又小。我后悔至极,准备来年一定要非常虔诚地好好回答。不幸的是,我换牙了,大人们说换了牙的人说话不灵验,我以此再没有资格去充当那棵树的灵魂了。从那以后,我真的相信,万物都有灵,山有灵,树有灵,一棵小草也有灵,即便一只蚂蚁,上帝都赋予了它一个灵魂,所以,对于村庄的一切,看见它,总会让我变得虔诚起来,尊重起来,谦卑起来,内心永远充满着敬畏。
但如今,村庄里的树没有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也挤进城去了。作者怅然若失,感到沮丧。村公所后面的一棵桂花树,它也离开村庄跑到了某个城市里,并充当着某个城市政绩的小数点。卖掉那棵桂花树的村长,丧失了对神灵的虔诚,沉浸在肉体的满足上。因为某种精神不在了,某种品德、良心、悲悯和理想正在散失,仅止于一个肉身,仅剩下对金钱的多少和物质的追求,和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人沦为物质、欲望的附属品,没有了灵魂,就犹如村庄失去了树,没有了灵魂,在天空之下,它们显得很小,有些空,甚至渺茫。世俗的人不仅掉了牙,而且失去了灵魂,从此就不再虔诚,不能再与神灵对话。
没有了树的村庄,推动主人的村庄,变成了精神的废墟。作者要重建精神家园,不仅需要当自己的主人,而且还需要心存虔诚。看到一个村庄,感觉它的存在,不止是一座村庄,而是众神的现身,那么,我们的灵魂就归位了,就可以充当一棵树,与神灵对话了。只有这样,才能重读那本隐藏在村庄内部的不灭经书,才能让人迷途知返。
三、不慌不急不赶才会知足自满
作者在文中记录了一次葬礼,感叹生命离去,谁都无可奈何。并由此引发对时间概念的思考。现代人,谁都仿佛被时间俘获,焦虑和忙碌成了一种生活的主旋律。城市快节奏生活,早已成为常态。时间变成了分秒,时间被过度地剥裂和缩小,把所有的东西卡在时间中进行,秩序反而会混乱。因为当快节奏反过来推着人向前跑时,它会瓦解人的精神。人类失去的不止是信仰,还有内心的安静和纯净,人人会在千篇一律的生活节奏中,将丧失飞翔的梦想,丧失本源,丧失对自然的敬畏。几千年传承的一些优美的德性,将会被割碎和撕裂的时间耗掉。时间的细化,也正在一丝一丝地抽走一些东西。
没有想到,在闲适的农村,老人们不但要耕种土地,而且还要帮着儿子女儿照顾下一代。他们不得不尽心尽力去把时间撕开,把生活切成片段。日子,仿佛成为一种空白,被不停的忙剥夺掉。作者记得,以前在村庄,时间是以白天和黑夜来计算的,一天就是一天,不会支离破碎,没有小时,没有分,没有秒。如果人们想知道时间,白天就抬头看看天空中太阳的位置,夜晚醒来凭大地的感觉判定是,三更还是五更。即便是春耕与秋收,也不会急急忙忙,遇上熟人,也要站着拉拉家常。生活在模糊的时间概念里,有一种亲和,一种温暖,一种最真实的生活味道。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不仅是表现人活得逍遥自在,而是容易让人知足自满。
当时间被割碎,时间就像催命鬼一样,不断地催着人往前跑。时间的精确它逐渐地成为了充斥着人们的内心世界,成为控制人们生活节奏的工具,它割裂了生活的整体,人就变得焦虑不堪。其实,时间让生命诞生,也让生命死亡,这是铁定的规律,谁也改变不了。所以,对于时间,谁也不慌,不急,不赶!让时间像神灵一样长驻于心,我们才能更好地与生活对话,最终获得精神悦乐。如果时间像流水一样,从我们的身子里快速地流走,我们的身子就变成了装时间的空壳。冲走的不仅是我们短暂的生命,而且还有长驻于心的神灵。我们最终被时间冲洗,变成精神惨白,灵魂虚无。
作者从快节奏的城市暂时逃回村庄,虽然没有寻找到往昔的时间概念,但明白模糊的时间更容易让人满足,精神更富有。静下心来,淡忘欲望,模糊时间,就能找到生活最真实的味道。
朱镛的《依托之地》还写了许多可能依托灵魂的云:人事、田野、父老乡亲、年关、村庄等等。它们都曾是作者精神殿堂的柱子。当这些柱子或被现代欲望的蠹虫蛀食,或被我们自己拆除,昔日的精神家园,变成了众神消退的空壳。作者要如何才能重建自己的精神殿堂,笔者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以上三个方面,即做丰收的主人,收割成功的喜悦;做个纯真的人,虔诚地与神灵对话;做慢节奏的人,知足自满。
阅读《依托之地》,可以让飘浮的灵魂归位,可以让四散的精神着陆。在朱镛的散文天空里,天空很蔚蓝,云朵很洁白。乡村的精神云朵,是灵魂的依托之地。
(作者单位:昭通市教育局)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