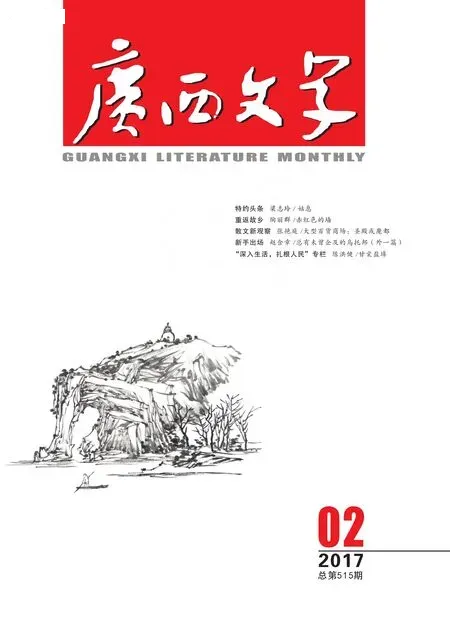敲着门的女人
短篇小说·白 琳著
1
她敲门的时候,我正在看一本书。书的页码很多,内容曲折拐弯。我很想越过纸张的阻挠跑到文字的尾巴上一看究竟,然而我还是很耐心地坐在一张人造革沙发上表演进行时态。这张沙发,陈女士引以为傲地从新疆运到盘海,它坐过火车,也上过大巴,在某一个夜晚,忽然重新降临在我的面前。无论是我,还是陈女士,都没有办法舍弃它。陈女士舍弃不了的东西很多,都来源于故人。我舍弃不了这张沙发,是因为我就在这上面长大。我坚信自己额前的两个鼓包,就是那年从沙发上摔下来之后生长出来的。然而我并不会埋怨它的失职,我恋慕它,熟悉它的每一个细节。在它的扶手上,有一个小洞,小洞四周的皮肤开始皲裂,透漏出一点浅黄色的纹理,其实我早已探知了它的究竟。在赭红色的人造革下面,是木头和海绵的尸体。
我常常坐在这张沙发上看书,也偶尔,只是很偶尔的时刻,会在沙发上想起一个人。我记得他的片段中,就有发生在这张沙发上的瞬间。有时候我会想起他坐在这张沙发上,默默注视着我,手里拿着一本儿童漫画,我最喜欢看的一本,如今无从记忆的那一本。我忘记了自己最喜欢的书,然而却记住了他的眼睛。所以偶尔,我会承认,我想念那个故人。
门被敲响的时候,我并不愿意起身。我的眼角膜,就像是快要被文字扯下来一样,在一堆半文不白的词语中粘着。然而很快,门外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呼叫,她的叫声里有我非常熟悉的反感,就像是每天晚上她都要走上几步路来到我家监督我洗脚洗袜子的那种厌烦和浮躁。她讲着普通话,即便是呼叫的时候。然而尽管她在这个闭塞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小县城里讲着普通话,也阻挡不了音质里喷发的庸俗。她声音的频点幅度粗糙干扁,频率响应曲线蜿蜒不平,却在这样的时刻表达了急切的原来面目,恰如其分。
我可以感觉到虽然焦急,她仍然保持着咬字的准确度。可惜那语言从喉管里激荡出来的时候,和她的人一样干涸,没有任何的弹性,不留任何尾韵。软的、松的、拖的,太快 、太短、太瘦,像坏掉的弹簧,弹出去收不回来。因为那声音薄得像是她的嘴唇。密度不够,疏散而无法凝聚。
在小县城里,讲着普通话的人很少,讲普通话的我和陈女士,既被新奇的眼光盯视,也被厌恶的眼光排斥。那时间那世界,容不下与众不同。可是,叫着门的这个女人不一样。她是土生土长的县城人,甚至从来没有去过四百公里之外的省城,但是她自发地说着普通话,把每一个e n和e n g,c h和c搞得很清楚,也从来不把“说”念成“书”,把“书”叫作“本本”。
敲门的,是我的卫生老师。
2
陈女士是数学老师,在小县城最好的小学任教。学校操场一排杨树边上,盖着一溜平房,那里住着除了数学老师之外的语文老师、体育老师,还有卫生老师。
卫生老师,隔着一间房子的宽度与我们比邻而居。我念到三年级时,她成了我真正的老师,讲生活课,教大家叠衣服做墩布,在流感把手放到学校大门口剥了漆的铁栏杆上之前开始传授预防知识,在铁炉子上泼醋熏出一屋子的浓烟。她很爱强调洗手,如果上的是早晨最后一节课,她一定要说的一段话,就是大家回家先要洗手,要记住正确的洗手步骤,先把手淋湿,在手掌上抹肥皂,搓出泡沫,让手掌、手背、手指、指缝等都沾满肥皂泡沫,然后反复搓揉双手及腕部。两手心互相摩、擦手心、手背相互搓、揉两手交叉着洗,清洗手指间隙……我们一哄而散,没有几个字真正地落入我们的耳蜗。从那时候开始,我虽然不知道一个好女人的要素是什么,但是先收纳了一个坏例子。重复的话不能重复说。
成了我的老师之后,之前因为隔着五年级语文老师而没有办法和我们的墙体紧密接触的她,有了频繁出入我们家的理由。念完了半个学期的生活课,这门课就完全消失在县城小学的课表上了,卫生老师变成了卫生所阿姨,回到她原本应该站立的岗位上去。我对于她职务的变动漠不关心,只在意究竟什么时候她才不会在每天晚上八点半来我家盯着我洗脸刷牙洗脚洗袜子,什么时候才不会在我做这样的事情时停下她那张不断挑剔着的嘴。有几次,在她喊着口令的间隙,陈女士略显尴尬地代我说话,告诉她我下午刚洗过澡似乎可以不用洗脚,然而她严肃又深刻地注视着陈女士,说,一个女孩子,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这些生活习惯,是每一天每一天积累起来的……我对于她的厌恶,是赤裸而明显的。在后来的很多年,每当我良心发现或者被人毫不遮掩地说出自己冷漠的个性,卫生老师就会从记忆幽暗的底层浮上来。我从小自私自利,对人没有热情也不期待别人的热情,懒于应承所有的情感曲线,如果有了厌恶也总是不穿衣服,不屑遮蔽。而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就是卫生老师。
3
卫生老师,或者说,卫生所阿姨,一直是县城小学里面的边缘人。有时候,她往里挤一挤,勉强有半个身子站在教师的队伍中去,更多的时候,她悬在崖边,带着即将坠落的惊慌。
她来我家,常常引着一团黑雾。陈老师假装心理医生,充当了能量供应站。她说自己的人生。考大学失败,不然就能上某个知名的医学院。以前有一个男友,人家去省城念书了,所以她就随便结了婚。妈妈身体不好,在乡下被姨妈照顾着。自己有病,下体总是莫名出血。虽然代了课,工资怎么还只是人家的一半?高中生就不能当老师吗?到大专随便进修一下不就好了?孩子奶奶太精明,把他哄得和自己不亲……
后来,我看过很多人捂耳朵。我的一个女朋友, 哭的时候不是捂眼睛,也不是捂嘴巴,而是捂耳朵。另一个女朋友,在听到自己不想听的任何话的时候,都会捂住自己的耳朵。这些动作被捆绑在肢体上,它们诚实、守信地完成了所有最痛快的行为。由是,我的朋友在公司年终总结大会上,在老板讲话的当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坚决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我没有,也不会这么做。我的手懒得抬起来,而是直接回避了从卫生老师嘴巴里跑出来的长串名词动词形容词,和间歇性的副词。她的嘴紫白紫白的,像梧桐花瓣阴阳两面的交界。
我看着那两片轻薄的嘴唇上下翻飞,舌尖顶出一个又一个伪装普通话的音符,总是忍不住从心底泛起恶意。那些缠绕在这个女人心中的结点,它们是那么琐碎,比起陈女士浑圆的整个的巨大的痛苦,散漫而无趣。
日子久了,她把所有的不幸说了个天翻地覆,说了个索然无味。身上冒着的黑漆漆的浓烟也化成灰白的雾气。她终于有了想到别人的空白,于是,在说着自己的中间,她开始隔三差五地问陈女士,你不再寻一个男人吗?你该寻一个男人。我给你寻寻吧。“寻”是县城里爱讲的一个词,原本没有这么文绉绉,发“行”音。她把所有方言里的词汇转成正音念出来,带着一点古老的糊涂的昏庸的土味。
我一边洗脚一边斜睨着卫生所的这个女人,她穿一套红色秋衣秋裤,下边趿一双钴蓝色的塑料拖鞋。拖鞋的边缘开着几条线,参差的塑料伤口里刺进去黑色的陈旧的污垢。她的脚又干又白,像是晒过的鱿鱼的肚皮。脚指甲很长,一部分扣着长到肉里面去。指甲盖是坚硬的贝壳,上面还有横亘着的海的纹路。
我擦干净脚,坐在沙发上剪脚指甲。脚趾甲的顶端,被切下一片片的弧形,它们充满力量地四下奔走跳跃,像是要跃到生命最远处。有一些落到了沙发上,有一些落到了她红色的秋裤上。我奋力而有耐心地剪着我的指甲,幻想它们可以刺入红色秋裤下的皮肤,然而它们最后还是软弱地在陈女士的斥责中被扫走。
4
期末一天,我的膝盖磕坏了,去卫生所包扎。她一边唠叨着,一边给我消毒。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刘宝玉,站在她的身后,紧紧贴着一溜白得发蓝的铁皮柜。柜子的上层是玻璃门,门里关着很多种瓶瓶罐罐的药材。她给我处理伤口的动作很慢,慢到夹起一团药棉也可以呼吸三五个轮回。我看着她打开生理盐水的瓶子,倒在一个医用铝盒的盒盖子上,她用这些消毒液刺激着我的腿,就像我假想用指甲盖刺伤她的腿那样,她深深刺痛了我。她在我的哀号中沉默。慢腾腾夹着药棉蘸碘伏。刘宝玉像是在铁皮柜上落下的画,他终于忍耐不住,接住了我瘸着拐进卫生所之前的话头。
他说,不管怎么样,你得赔。你不但得赔,你也不能在这里干下去了。
她抬头,说,等一下给孩子弄好了再说。
他们都讲着县城的土话。
我从来没有听过她讲土话,现在她讲了,我忽而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她。像是终于解下冬天里缠绕在脖颈中间的围巾,她深长喘息,如释重负。
可惜她没有如释重负。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肌肉僵硬,像是提前死去了一样。
刘宝玉没有要放过她,这个低矮的戴着眼镜穿着在谷裕市场裁缝店里做的西装,腿没有两尺长的男人,恶狠狠地说,你的账对不上吾都要去告你,你不要以为你男人是个主任就木有人扰你。
我糊糊涂涂听着,碘伏在我的小腿上流成了一条线。
她总是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卫生所的女人独身。实际上,她不过是在独自生活。这个我知道。在我的世界里,独自生活的女人并不奇怪,比如说陈女士,或者有一天,还有我。
她终于站起来,仰着头,对着刘宝玉说,你对不上价,吾现在开了柜子让你对,看看你还有什么讲头!
她愤愤地说,土话流畅无比。她一边说一边拿钥匙开柜子。柜子的门像刚蜕了一半壳的蝉被扯张了翅膀般一扇扇打开。
你查,有多少药吾都列在此地。
刘宝玉哼了一声,他慢慢地说,你把每个瓶子里的药片片都给倒出来数数,不能缺!
你怎么能这样!这样不卫生,还让人怎么吃药!她忽而又讲了普通话,正气凛然。普通话给了她更高的指责的身份,让她可以对刘宝玉发出蔑视的质问。一瞬间她充满力量,像是病入膏肓的人的回光返照。
我偷偷摸摸地站起来,出了卫生所的大门,拉开双腿跑了。我跑得飞快,膝盖上的伤口在肌肉的运动下拉扯出更多的液体,红红黄黄地散落在我的皮肤上。我对这个小县城的厌恶,在奔跑中加深了一层。
1992年的这个夏天,她最终没有拿到正式的聘用合同。她不再属于县城小学。或者从来没有属于过。几乎是,刚刚经历过站在讲台上的快感,还没有攀爬到顶峰,忽然就再也抓不住这快感的任何一丝尾气。学校的卫生所也关门了。本来就立在校门边边的这个小房子,被腾空了以后就好像更不属于大门内的世界了。有一天,搬来一家守门的人。很久之后的另一天,守门人的女儿从家里端出一窝粉红色的小老鼠,她摸着它们,找出来不知道从哪里寻到的药瓶,一只一只把它们装进去,盖上盖子。老鼠们还不会叫,它们在那些药瓶子里面化为静寂。
5
我见着她的时候,她是一个有婚姻的独自生活的女人。虽然不爱剪脚指甲,但是手指一直干净利索。以前,她用一排干净的手指给我们打针,旋开一罐一罐的药瓶,在小小的方块纸上倒出几颗来。那时候她的身上总是有消毒水或者酒精的味道,这味道可以让白色更白。
我以为此后从她的门前走过时带起的风里,会有那种味道的消失。然而她仍然在我们隔壁的隔壁住着,这大概是学校和她最后较劲中唯一的妥协。她真的有一个老公,这个男人是教育局里的某位主任。
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主任,主任从来没有主动找过她。常常在周末,她打扮一新,手上提满袋子,盈盈往校门外面走去。她在周日傍晚回来,不到片刻,就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出现在我家门板外侧的凹槽里。她到我家来,就是为了讲一些少儿不宜的情色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她自己的床事——对于我们而言,都是额外的折磨。我不喜欢听她的故事,那故事里面充满血液的腥臭。她很仔细地描述自己的病症,说一切源头都来自偶然的宫外孕,那次流产之后,她的身体就垮掉了。她举起灰白的手,告诉陈女士,它们以前是多么的饱满,那些血管里的血液挤得饱饱的,而现在,只剩下一些青灰色的躯壳蜿蜒在手腕上。
我对于子宫和手腕,产生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很深地纠缠着,直到现在都无法消除。每一次想到子宫,我所能感受的只有疼痛。因为她说,主任很想与她做爱,但是,每做一次,她的下体就会淌出连贯的血水,无休无止持续几天。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在一起,他就要做爱,她就要流血。
有一天她回来得比往常都要早,敲开我家的门,还没有把臀部凑近那张故人留下的人造革沙发,语言就来不及涌出嘴面。昨天晚上,她说,我不愿意让他弄我,可是他硬是要进来。我们打了一架,然后我被他强奸了,现在,我下面流个不停。我总有一天要死在这上头。我们在这些话里适应了好半天,陈女士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要她去医院看看。她说,看什么呀?上次找了个专看妇科的中医给我看,说是和王熙凤的病一样,是血山崩,难治。陈女士是真的担心,说中医不一定能确诊,你不是也懂西医吗?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她说,我自己的病我心里有数,就是那个畜生搞出来的,他把我的身体搞垮了。
我竖着耳朵听着她们的对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子宫在哪一个位置,但是我的身体忽然生出一种沉重,这点沉重坠在我的小腹,我以为那里会忽然涌出血液。
男人们都是这样,就因为我不愿意让人占便宜,就想法子把我开除。卫生所的女人,失去卫生所之后,把这句话反复挂在嘴上,但是这句话终于有一天了结在一个女人的巴掌之下。我没有见识这巴掌的本尊,但我用耳朵听说了它。它从刘宝玉老婆手心里来,打掉了她嘴里含着的那些“冤枉好人”的词汇。
陈女士劝说她搬回自己家,她却执拗地断然拒绝了。她的血液有限,经不住日复一日的流淌,她在血液的涌动下逐渐干涸,变成了一个枯巴巴的人,从肉体到精神。她从来没有完整地解释过自己为什么一个人住,但是在积攒的词语里,她的恐惧重重叠叠,如同她皮肤下面日益隆起的血管。这些恐惧战胜了很多事情,譬如夫妻之爱母子之爱。
她最后把母亲接过来和她一起住。每一天每一天,两个人似被嵌在隔壁的隔壁一样,深居简出。她母亲来了之后,她来找陈女士的次数少了很多。她更干更瘦,脸色黄白,像极了莲花池里败落的荷叶。减了秋香,越添了黄,老柄风摇荡。
6
我终于站起身,把书倒扣在沙发扶手上,掩住了那个孔洞,给她开门。她哭过了,并且仍然纵情哭着。她含含糊糊地说,我妈不行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软弱胜过我告别那个故人。我终于发现我的冷漠从哪里来。我丢下书,那些故事在我身上消失了,我开始四处寻找陈女士。
陈女士帮忙料理了她母亲的后事。在红白事宜都被烦琐的旧传统箍住的小县城里,这个丧事办得简单凄凉,像是一场真正的丧事。等那个每天都静默着的老太太静默地消失在隔壁的隔壁之后,隔壁的隔壁就真正成了她的家,除此之外,她无处可去。我们都不知道的是,她在此之前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从此之后,她更是离群索居,甚至再也没有浪费十步路,敲开我的家门。然而有一天,她从隔壁走出来,桃红柳绿,她穿了一条裙子,裙子下面的腿上,有几条断裂的血线。再有一天,她开始胡言乱语,说哪个女人和主任滚在床上的时候被她揪住了。接下来,她开始无休止地爆料,在曾经讲给陈女士的床事原料上染满血液。接下去,她开始讲自己考上了医学院,但是她放弃了,还有新加坡的人叫她去工作,她也放弃了。我怎么能丢下辉辉和我妈呢?她说。——一切都是臆想。往后,有人开始说她疯了,再往后,人人都说她疯了。没多久,刘宝玉跳出来,说学校这种地方,怎么可以有个疯婆子?
她离开县城小学,并没有像她曾经对陈女士说的那样,离开这个鬼地方,去这个省的另外一端念卫校。她说那里有她的高中同学在当老师,她说她念完书回来就可以自己挂牌开诊所,她说那个学校现在开始往新加坡输送高护人才,她充满憧憬地说着,用可惜做结尾。“可惜我有家庭。”她很遗憾,好像这个是她不能实现所有梦想的原因。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也不过三十二三岁,我那时候觉得她已经足够老了,老到还有这些梦就显得十分可笑。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年纪的女人更爱做梦,也更有行动力。
然而,她离开了,并不是去实现她的梦,而是成为一个有梦的疯子离开。在她离开的前半年时间里,她还被人们挂在嘴边。我和陈女士也是如此。开始,她是陈女士唇纹的裂痕,一扯就疼,陈女士想起这条裂纹,就用舌尖濡湿它灌溉它。后来,裂纹渐渐消失,关于她的最后话题,在县城小学所有人的嘴巴里消失。她开始大大地疯了,游窜在县城的各处角落,自说自话。她的疯很节制,她从来不像街边的流浪者,裹着破烂不堪的布条,满面污泥。她疯了,疯了之后她仍然讲普通话。比起别处,她更喜欢在学校门口看看,到了下课时间,就有成片的小朋友拥出校门,他们不知道她是我的卫生老师,她看上去虽然干净,但没有一点老师的样子。她总是嘟嘟囔囔说着什么,脸部露出各种各样的表情,像是角色扮演,拼出一场喜剧。孩子们用对待攻击性不强的疯子的方式对待她,他们戏弄她蔑视她,在她的身后追逐挑衅。我上初中,他们这样对待她,我上高中,他们仍然这样对待她。有一年我抓住两个往她身上扔鞭炮的小孩,我抓着他们的手,恐吓他们,两个孩子畏缩在我的手下。但是等我放开那些细小的手腕,他们风一样跑开,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叫,先骂上一句土话,接着说,你也是个疯女子,讲普通话的都是妈×疯女子。
我很气,想要追上去恶狠狠揍他们一顿,但是我很快就消了气,我还指望这个小县城给我什么惊喜呢?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有抱持着期待。我不期待接近人们,也懒得应酬想要接近我们的人。我望着她的背影,她对身后发生的事情无知无觉,她依然照样走路,照样说话,照样演戏。我想起那年我倒扣在沙发上的那本书,在她敲响门之后,我就失去了阅读的高潮。那本书再也没有吸引过我,我很潦草地看完它,很潦草地扔进书柜里,开始寻求下一本书的刺激。
7
我后来倒是知道了很多关于主任的故事。在我念到高中的时候,主任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每一个周一,我们都站在操场上听他训话。他中等身材,看上去显得年轻,也很干净,头发一丝不苟。我总是喜欢这么打量这个男人,打量了一次又一次。我的思维发散开,想到了千头万绪的故事。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子宫,已经经历了流血的疼痛,于是我更感受到了卫生所女人的恐惧,我看着他,很想用一个浅薄的没有什么智慧的词形容他,比如说,道貌岸然,但是我厌恶不起来他。他风度翩翩,很热心很有趣,是个好校长。他说,昨天下午我在操场上散步的时候,看到篮球筐下有一摊血。咱先不说篮球架是不是被谁拽到了,倒是流血的那个同学你有没有事,那么多血,看着都可惜,有情况来找我,我带你去看看。大家注意安全。
他讲话时说的是方言,并没有一点点普通话的影子。学校大扫除,我被分派去给他清理办公室。他不认识我,一边整理书柜一边问我的学习情况。我拿着拖把在他的地板上晃荡,想起小时候卫生老师教给我们做拖把的情形。他看着被我拖得花花绿绿的地板,笑着说,你在家没干过活吧?我这里没事了,不用打扫,去看看书吧。他接过拖把,从头到尾,拖得干干净净。
这个人原本有可能成为我的继父。我站在他的身后想。在卫生所女人疯了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有一个媒人上门来和陈女士说“寻男人”的事情。应该说,一直有很多人愿意来找陈女士说“寻”的故事。这是她们对于我和陈女士最大的好奇。陈女士让这份好奇持续了好多年,于是在这些年里,我听说了很多有几率的人的故事。校长是在卫生所女人的坚决要求下离的婚,据说,他苦苦哀求,她歇斯底里。这样有鼻有眼的情节从哪里来,我不得而知。媒人拎着几袋子礼品上门,详细说明他的情感履历。离婚之后,他和一个女子同居半年,但是那个女人对他的儿子不好,让他无法忍受。他要找实诚的人。媒人说。
陈女士未必实诚。实诚不实诚,用眼睛看得出来吗?但是陈女士漂亮,这一目了然。
念高中之前,我就知道他即将是我的校长。我和陈女士去一家羊汤面店吃饭,看到了他和他的儿子。两个成年人都假装没有看到对方,这是冷静清晰的表达。陈女士想也没想地回绝了媒人的话题。那些欲放不放的礼品也被陈女士的一双手强劲地推了出去。我们一对母女,他们一对父子,各坐各的桌子,互不相识,相安无事。
校长一直都没有结婚,他一个人带大孩子,那孩子很优秀,拿过国家奥林匹克竞赛的银奖,念大学,全额奖学金留学。去念比省城卫校更好的学校,去比新加坡更遥远的国外。只是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再过十来年,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准确知道子宫的位置,略微懂得一些妇科病状。陈女士更年期到了,状况突发,我陪她去检查。妇科医生和陈女士认识,在小县城里,似乎人人相识。她们聊来聊去,我权当听众。不知为何,两个人竟然讲到她去,医生说,前一段她侄女带着她来看病了,我给她一检查,其实就是个小病。她宫颈口长了几个小瘤子,良性的。你说就是这几个小东西折腾了她一辈子。陈女士应着,两人来来去去说了许多前因后果人事变化。陈女士的普通话早已经算不上普通话了,和那些年卫生所女人的发音一样,总是把方言词硬生生地转化为正音。但是我也早听习惯了,我原谅她的古怪,因为她是陈女士。
带卫生所的女人来看病,是那个儿子从美国传达来的指示。我对于卫生所女人最深刻的记忆,停留在她最后敲我家门的那一天。我对于这个孩子的最后的印象,停留在高三的一场运动会。
我念高三的时候,他念高一,我们学校举行运动会。我坐在观众席心不在焉,旁边有女孩子郑重介绍即将出场的校长公子。她们的恋慕异常鲜明。这是任何一个品学兼优且热爱运动的男孩子都可以获得的关注。我把眼睛往下放,看到他,和那年在羊汤面店见到的样子区别不大。他并不高大,而是苍白瘦弱。但是他跑得很快,面目狰狞。仿佛在追逐,在冲破,也仿佛在回避,在逃离。